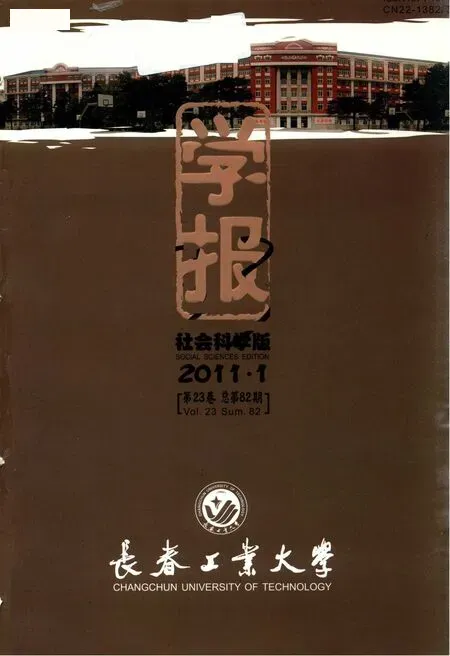现实沃土之沉思 爱情王国之绝唱
——《呼啸山庄》与《简·爱》对比研究
2011-03-31王喆
王 喆
(四川文理学院 外语系,四川 达州 635000)
现实沃土之沉思 爱情王国之绝唱
——《呼啸山庄》与《简·爱》对比研究
王 喆
(四川文理学院 外语系,四川 达州 635000)
虽然《呼啸山庄》与《简·爱》无论在主题、爱情观还是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不一样的风情,但相近的家庭背景,类似的文学熏陶,决定了两姐妹的文学创作有很强的可比性。在《简·爱》里夏洛蒂·勃朗特更多的是披露个人的情怀,而妹妹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本身就是一本社会小说,更多的是对近代文明的控诉。《呼啸山庄》代表的是英国小说的一条绝径,而夏洛蒂对女性内心痛苦的现实主义刻画却带给英国小说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姐妹俩屹立在现实的沃土上反抗现实,但都难以超越“我爱”,“我恨”,”我受苦”,最终不免为现实所牵制。
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夏洛蒂·勃朗特;《简·爱》;对比研究
被马克思称为“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1](P296)中,夏洛蒂·勃朗特和艾米丽·勃朗特姊妹分别创作的《简·爱》和《呼啸山庄》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考验,已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据了不可动摇的地位,是英国文学史上两座不朽的丰碑,荣耀和声誉永远环绕她们的坟茔。相近的生活背景,类似的文学熏陶,决定了两姐妹的文学创作有很强的可比性。她们创作的根基,深深地扎根在英国生活和文学的现实沃土上,虽然常常幽禁在霍渥斯牧师住宅四壁之内,但是我们无法忘记在她们娴熟老辣的笔锋下那为了爱情双双步入天堂的凯瑟琳与希斯克利夫和历尽凄苦终于幸福地结合在一起的简·爱和罗切斯特,他们的“伟大爱情”已成为英国文学的千古绝唱。
一、《呼啸山庄》与《简·爱》的共同性
艾米丽和夏洛蒂继承了父亲那充满激情的爱尔兰性情,父女们都赞同华兹华斯的观点——自然美是仁爱的力量。姊妹俩常常漫步于荒野之上,从中获得宝贵的文学创作灵感。她俩对大自然神秘力量和生活中美的敏锐觉察和顿悟,都很好地融进了各自的杰作中。她俩热爱自然,更渴望自由;她俩极度鄙视社会习俗,更盼望美好婚姻爱情。
(一)相像爱情主题
无论是《呼啸山庄》还是《简·爱》,他们都以爱情开始,又以爱情结束,向人们传递着不管是凯瑟琳与希斯克利夫或是简·爱与罗切斯特,他们的爱情都有着深厚的基础,他们都属于同一类型人——感情充沛,充满激情,敢爱敢恨,敢作敢为,他们反对传统婚姻,藐视社会习俗。凯瑟琳和简那发自肺腑的爱情直白永远萦绕在每一个人耳边:“我爱他并不是因为他英俊,耐莉,而是因为他比我更像我自己,不管我们的灵魂是用什么做成的,他的和我的是一样的”;[2](P103)“我不是根据习俗、常规,甚至也不是血肉之躯同你说话,而是我的灵魂同你的灵魂在对话,就仿佛我们俩人穿过坟墓,站在上帝脚下,彼此平等。”[3](P284)
在《呼啸山庄》中,虽然凯瑟琳坚信她和希斯克利夫的灵魂是一样的,但她还是放弃了希斯克利夫而选择了埃德加,这是由于她的虚荣所致,为了追求物质享受,“成为附近一带最尊贵的女人”,[2](P99)她背弃了自己的心,从而加剧了《呼啸山庄》的悲剧情调。然而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的爱已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超越了生与死的界限。在得知凯瑟琳死讯后,希斯克利夫挖出她的尸体,把她搂在怀中,以求二人永不分离,这进一步证实了凯瑟琳的话——“他比我更像我自己”。虽然为了复仇,希斯克利夫致使两个家庭毁灭,但他对恩肖和林顿两家的打击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在《简·爱》中,简与罗切斯特的爱情和凯瑟琳与希斯克利夫的爱情有异曲同工之妙。罗切斯特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父母和哥哥都强迫他和种植园主女儿伯沙·梅森结婚,就是为了那三千英镑的嫁妆。不幸的是,后来妻子变疯,由此自己生活颓废,几度绝望,整日沉溺于肉色之中,以求自慰。而简的出现,让他再次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他对简说:“在一半是难以言传的痛苦和一半是意气消沉的孤独中,度过了我的少年和成年时期后,我第一次发现我可以真正爱的东西——我找到了你。你是我的共鸣体——我的更好的一半——我的好天使——我与你紧紧地依恋着。”[3](P358)这里“我的更好的一半”就如同“他比我更像我自己”。简和罗切斯特的爱是深挚、牢固的爱情,坚贞不变,是建立在完全相互了解和爱慕基础上的。最后俩人破镜重圆,互诉哀肠,白头偕老。
(二)共现哥特风格
“哥特式”这个术语来源于故事经常发生的背景,如中世纪时期荒废的、长满苔藓的尖顶、高柱城堡,用于文学主要指怪异、神秘和超自然的东西,旨在使读者产生悬念和恐怖。哥特小说为后来的小说揭示了人类本性中隐秘、没有理性的一面:野蛮的利己主义,不正当的冲动和约束的、有序的意识表像之下噩梦似的恐惧感。在维多利亚早期,哥特小说就已十分流行,在《呼啸山庄》与《简·爱》中,这种风格体现的淋漓尽致。
在《呼啸山庄》中,房客洛克伍德睡在像棺材一样的带着嵌板的床上,梦见了凯瑟琳的鬼魂,那一幕被称为是“整个英国文学中最动人的场面”,[4](P478)一只血迹斑斑的手从打破的窗玻璃伸了进来,那张苍白的脸孔要求进屋来。于是梦中的洛克伍德为了阻止它,把“它的手腕拉过来放在打碎的玻璃窗上,一左一右来回锯,直到血流下来浸湿了床单。”[2](P29)在故事的结尾,牧羊童哭着告诉大人们他看见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一起在荒野狂奔。“《呼啸山庄》那么迷人,那么震撼人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哥特形式与激情内容的完美结合”。[5](P54)这种哥特式风格在《简·爱》中也得到了很好地运用。夏洛蒂在小说中不停地给读者摆迷魂阵,迫使读者带着巨大的好奇心去一一解开这些谜底:谁是陌生人梅森?为什么他的到来会打乱罗切斯特的平静生活?梅森为什么对罗切斯特说“她吸了血,她说要把我的心吸干”?[3](P240)为什么罗切斯特在向简求爱时咕哝着“会赎罪的,——会赎罪的”?[3](P287)为什么在简婚礼的早上,两个陌生人潜伏在教堂里?如果罗切斯特丢弃了桑菲尔德,他会去哪里呢?加之在《简·爱》中充满着神秘的大笑、若隐若现的疯女人、毛骨悚然的噩梦以及种种不祥的预兆,这些因素使得哥特风格表露无疑,“简来到桑菲尔德庄园做家庭教师,等于来到一个哥特式小说中的古堡”。[6](P153)相比之下,艾米丽运用哥特手法更胜一筹,在《呼啸山庄》一开始就让读者喘不过气来:那个鬼孩是谁?谁是希斯克利夫?1500年和哈里顿·恩肖的名字有什么特殊意义吗?在窗栏上刻着的三个名字——凯瑟琳·恩肖、凯瑟琳·希斯克利夫、凯瑟琳·林顿又是怎么回事?要解开谜底,我们必须坚持读下去。随着管家耐莉·丁的露面,故事的真相才得以慢慢揭开。
(三)同具反叛精神
无论《呼啸山庄》还是在《简·爱》中,都很好地体现了主人公们为争取爱情自由的斗争精神。在实现自我、追求幸福生活的道路上,他们敢于冲破世俗枷锁,在夹缝中抗争不屈,个个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可以说《呼啸山庄》和《简·爱》就是维多利亚时代妇女争取解放、实现自我的宣言书。
在《呼啸山庄》里,凯瑟琳是个极具反叛精神的女子,在荒蛮的山庄里成长,她最大的快乐就是和心爱的希斯克利夫在田野里追逐狂奔。“他俩之间特殊的亲密关系大部分是共同反叛辛德雷和约瑟夫的残忍统治的产物,是共同反叛当时成年人主要通过宗教对孩子施行的暴虐的产物”。[7](P240)凯瑟琳死后,令村民吃惊的是她的坟墓并未选在小教堂里林顿家族刻了字的石碑下面,而是安葬在了教堂墓地的一角的一个青草坡上,“这里围墙很低,荒野上的荆棘、覆盆子树爬过墙来,泥煤土丘几乎要把它埋没了”,[2](P220)这无不体现她对上帝旨意的不屈和反叛。因此,在艾米莉笔下,凯瑟琳有着十足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会被任何力量摧垮,就连希斯克利夫也深信她的灵魂不会入地狱,定会上天堂。“《呼啸山庄》在控诉扭曲人性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合理的同时,作品表现了被压迫者强烈的爱憎和顽强的反抗精神”。[8](P138)和妹妹艾米莉相比,夏洛蒂却有过两次尝试当教师的经历,这些经历大都不愉快,甚至带有羞辱性,因而她这一不幸的遭遇很好地赋予了她的杰作《简·爱》中,让她的女主人在这不公的社会里去体现出那种不容动摇的自尊自爱和意志自由的性格。受人鄙视、无人保护的简,她的反叛举动从在约翰·里德家就表现了出来。面对里德对她的百般恐吓和欺辱,她终于忍无可忍,像发疯似的“猫”给了里德无情的还击;面对里德夫人的无端指责,她针锋相对,坚持己见,维护自己的诚实和清白,并告诉里德夫人是最令人讨厌的,她第一次在“权威”前道出来了自己的心声:“你以为我没有感情,以为我不需要一点抚爱和亲情就可以打发日子,可是我不能这么生活”。[3](P36)简强烈的反抗精神,不愿受人摆布的意识以及不懈追求平等的意志使得《简·爱》独具魅力。无论在艾米莉还是在夏洛蒂的作品里,处处浸透着“拜伦式英雄”的模型,这一模型对上一代产生的深远意义在刚刚崭露头角的维多利亚年轻女性作家心里也是挥之不去。拜伦式的英雄都是敢于与命运抗争,敢于藐视现存制度,而勃朗特姐妹通过她们的主人公的斗争很好地彰显了这种对黑暗社会永不妥协的反抗精神。无论是有着一双紧锁眉毛下猜疑地望着他人的黑眼睛的希斯克利夫,还是那个有着深黑眉毛、两眼发亮、咬牙切齿的罗切斯特,他们都有着神秘的过去,不信宗教,充满激情,对物质世界的伦理道德敢于挑战,可以说他们就是“拜伦式英雄”的代言人。
(四)雷同象征手法
我们都会记得弗吉妮亚·伍尔夫的著名评论:“艾米莉和夏洛蒂两人都经常借用大自然之力。她们都感到需要言语或行动所难以传达的更为强有力的象征,来表达人性中那些巨大的沉睡的激情”。[9](P294)姐妹俩都感到沉睡于人性中巨大激情超乎语言,两部杰作中的风暴、荒原以及季节的变幻绝非仅仅用来装饰门面,它们预示了姐妹俩锐利目光对现实的洞察,承载了女作家们深厚的思想情感,因而使得《呼啸山庄》和《简·爱》更加灿烂无比。
在《简·爱》中,那横遭洗劫的栗树预示了简就要和罗切斯特伤心别离。但尽管这些栗树已被撕裂,它们却也依然挺立,“坚实的树基和强壮的树根使底部仍然连接着”。[3](P312)这进一步预示了他俩现在虽不能喜结良缘,但他们彼此力量和激情必将会使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同样的象征在《呼啸山庄》中也得到了印证。在一个暴风雨的傍晚,响雷震耳,狂风四起,山庄屋角的一颗树被劈成了两半。这一情景预兆了希斯克利夫已从山庄悄悄消失,他带着羞辱和自卑愤然离开,三年后心怀企盼,回到了山庄。他随后实施了一系列复仇计划,曾对哈里顿说:“现在我的好小子,你是我的啦!我们来看看,要是让同样的狂风去吹它,这棵树会不会像另一棵树一样长得弯弯曲曲的!”[2](P244)希斯克利夫要用当年辛德雷贬低他那样来贬低哈里顿,女作家在暗示读者逆势的环境刮起的大风会造成人性的扭曲。后来洛克伍德再访山庄时,这里的变化着实让他吃惊不小,他此时的面前是一轮正在升起的明月,他不必从栅门上爬过去也无需敲门,顺手一推,门就开了。这时已是四月的天气了,“天气暖和宜人,一场雨水和一片阳光把青草滋养得要多绿就有多绿,靠南墙的两颗矮苹果树开了满树的花”。[2](P427)随着希斯克利夫的死亡,这里已恢复了其当初的自然美,失去的人性终得以回归。
二、《呼啸山庄》与《简·爱》的不同性
人们很难想象,两个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经历相仿,又感情甚笃的两姐妹,会创作出风格如此迥异的作品。本是同根生,但两部杰作无论在主题、爱情观还是宗教信仰仍存不一样的风情。夏洛蒂是位“天才”作家,而妹妹艾米莉则是位“悲剧的天才”;姐姐的《简·爱》更富有诗意,而妹妹的《呼啸山庄》独树一帜,有种异常韵味,本身就是一首诗;姐姐联系自身家庭和身世背景,在《简·爱》里更多的是披露个人的情怀,而妹妹的《呼啸山庄》本身就是一本社会小说,更多的是对近代文明的控诉。
(一)分外的主题
在小说《呼啸山庄》中,艾米莉所描写的爱情故事是关于一种超越时空充满激情的爱、恨和复仇的故事,借此女作家告诉读者“资本主义社会中充实完整的人类生活是不可能实现的”。[10](P378)主人公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为追求他们崇高的“精神之爱”不惜毁灭自身。像他们一样,女作家明显地表露出对“肉体之爱”的极度不满,因为后一种爱使得心灵受限,分隔了恋爱双方和他们的自然本能,而前一种爱则能考验真爱和真爱的力量,尽管这种考验有时是痛苦的,甚至要遭受打击的,但“精神之爱”可以升华双方的忘我境界和洞察力,更有助于恋人们全身心的投入而不顾身旁的世俗。女作家在强烈地向我们传递这样的信息:为了爱情永久,必须抑制肉欲招引,为了爱情延续,必须克制物质诱惑。除了爱这一主题,艾米莉也在时时刻刻地关注着人和世界的本来。在儿时就失去母爱的希斯克利夫身上,女作家向我们很好地诠释了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想要告诉的一切——这样的儿童在其成长中很难觉察到人间真情,甚至会有一种颠覆的方式去滥用人间真情。而与此同时女作家也向我们揭示了和平与暴力、自由与枷锁、平静与喧闹之间的种种冲突。和妹妹不同,夏洛蒂却独树一帜,《简·爱》中一个中心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在小说中她为我们耐心地讲述了女性实现自我和个人意识唤醒的奋斗史,小说中的女主人简孤独、遭人唾弃,但她仍然热爱生活,向往爱情。小说真实反映了女作家悲惨的童年,深刻地揭露了教会控制下的寄宿学校的种种罪恶,明显地是在讲述个人奋斗历程,探究底层的女性是如何为自己的基本权利和平等而奋斗,并最终走向成熟的个人成长史。对于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小说中的简坚持认为应该和男性有平等的权利。
(二)别样的爱情
尽管《呼啸山庄》的起点和终点都是“爱”,但艾米莉却极力突出一个“恨”字,尽写恨的力量、恨的恐怖。女作家无视世俗规则,把爱情提升到人性的高度。《呼啸山庄》更近似一个关于生命体的寓言。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的关系,已超出了男女之爱的范畴而升华为某种超验的东西。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之间爱的魅力在于他们炙热的激情,他们的爱犹如蛮荒、原始的沼泽地,每次爆发就会将对方吞噬,他俩有着同样的灵魂,同样深切的心,他们追求自由不仅仅在于逃避辛德雷的迫害,还在于他们敢于摆脱世间羁绊。她俩自始至终深信他们永不分离,那怕双方揉碎了对方的肉体,他们的灵魂也会永远相伴在一起的。随着他们双双死亡,他们又能终于一起在荒原上狂奔了。他俩之间“喷涌而出的令人惊异、带有强烈占有欲的爱情,之所以余响一个多世纪仍使读者获得最尖锐的感受,正是因为这种奇异的感情传达的是整个生命与存在的同一”。[11](P60)
和妹妹不一样,姐姐夏洛蒂缺少艾米莉那种荒野剽悍的精神,她甚至反对妹妹在书中所描写的那种狂暴,那种野性,她注重爱情的道德性,对社会有所反抗但也有所妥协。在《简·爱》里,对“爱”的追求始终贯穿整部小说。夏洛蒂所描写的男女主人公间的爱是基于社会的伦理道德,简·爱对爱情的追求始终不偏离传统道德的规范,她在个人情意和世俗观念的冲突中寻求着两种统一的方式。同时,“《简·爱》在感情表现上具有一种高度浪漫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赋予本书以独特的魅力,又与它的热爱自由的叛逆精神分不开。”[12](P445)罗切斯特和简的重逢被安排在一个美丽的果林里,这里周围的树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空气里弥漫着茉莉、玫瑰的香味,此时月儿正在升起,他们的重逢显得是那么的平静,那么自然舒坦。尽管简一直顽强地独立生活着,但她和其他维多利亚的女人一样,认为婚姻是人生最美满的结局,“更乐于趋从罗切斯特而不是坚持自己的意见”。[13](P116)因此,她最终投入了罗切斯特的怀抱,愿意去过那种中产阶级悠闲自在的生活。简和罗切斯特的爱是一种相互的付出,相互的牺牲,而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间的爱更像是一种相互的征服,相互的吞噬。
(三)另类的宗教
在《简·爱》里,女作家夏洛蒂常常把和那些信奉宗教的人等量齐观。小说中人人都坚强地维护着他们各自的基督信仰,简也在不断的追寻着教义的真谛,寻觅着那海伦·伯恩思曾信奉过的教义。基督福音强调人内心的真实性和人性的缺失,推崇人和造物主间的密切联系。简和罗切斯特的爱就是建立在一个以牢固的宗教理念为基础,符合人们习俗的爱。她深知她和罗切斯特的关系如同她和上帝的关系,正如她所承认的那样:“我的未婚夫正成为我的整个世界,不仅是整个世界,而且几乎成了我进入天堂的希望。他把我和一切宗教观念隔开,犹如日蚀把人类和太阳隔开一样。在那些日子里,我把上帝的造物当成了偶像,并因为他,而看不见上帝了。”[3](P310)简总是把信奉上帝和履行义务作为幸福的首要条件,她对罗切斯特就曾经说:“相信上帝和你自己,相信上天,希望在那儿再次见到你。”[3](P360)上帝最终把她带回到了罗切斯特身边。经过在桑菲尔德府的那场浩劫,罗切斯特也意识到了精神世界的真实性,他祈求上帝赐予他力量,保佑他过上美满生活。无论在简还是在罗切斯特身上都表现出对上帝的笃信,这进一步证明了《简·爱》确是一部宗教之书。
与此相反,妹妹艾米莉的《呼啸山庄》却“真实刻画了一个无关道德的世界。这是一个人类的世界,而非上帝主宰的世界”。[14](P257)女作家借用希斯克利夫表达了父母之爱的缺失和对世俗、伦理以及人间理性的强烈不满,因为这些仁义道德阻碍了个人的自由,限制了个人的欲望。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火一般的爱颠覆了传统的宗教,他们的爱冲破了世间的尘土。在有宗教的世间,凯瑟琳不像一个好女儿,好妹妹,好妻子,但在没有上帝的世界里,她和希斯克利夫却能丝丝入扣,合二为一。
三、结语
生活在英格兰北部这片平静、偏远的土壤上,自由的荒原占据着勃朗特姐妹的心灵。然而除了思考人间的爱之外,妹妹艾米莉“关注的是尚无定数的未来世界。她的呼声超越了那个时代”,[15](P144)更愿探究更深远的主题——人和宇宙的本能,比起姐姐夏洛蒂,她很少受到外界的干扰。夏洛蒂九岁时,母亲就离开了人间,她便接替母亲的职位来管理这个家务,其艰辛可想而知,因而可以说她笔下的《简·爱》更像一部关于女性的天路历程。在《简·爱》里,简和罗切斯特的爱是那么地柔情似水、缠绵悱恻,而在《呼啸山庄》里,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的爱却又是那么的原始和粗野。在形式上,《呼啸山庄》不同于自传体小说《简·爱》,艾米莉更愿疏远社会群居生活而形成了自我的创见,荒原切断了她和常人的来往,在充满丰富想象的个人世界里默默地度过了自己短暂的一生。虽然夏洛蒂努力尝试和外面的世界紧密联系,但和妹妹一样,也未能走得太远,英年早逝,她的这种顺从物质世界的情怀在她小说的主题和结构上得到了很好地印证。如果说《简·爱》有某些作者的生活经历和性格特征的元素,《呼啸山庄》则把它的作者盖得严严实实。然而,“《呼啸山庄》代表的是英国小说的一条绝径,而夏洛蒂对女性内心痛苦的现实主义刻画却带给英国小说一个新的发展方向。”[16](P323)姐妹俩屹立在现实的沃土上反抗现实,但都难以超越“我爱”,“我恨”,”我受苦”,最终不免为现实所牵制。
[1]〔德〕马克思.英国资产阶级[A].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三卷[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2]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M].王蕙君、王蕙玲译.奎屯:伊犁人民出版社,2001.
[3]夏·勃朗特.简·爱[M].黄源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7.
[4]格拉日丹斯卡娅.勃朗特姐妹(1955)[A].杨静远.勃朗特姐妹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5]蒲若茜.《呼啸山庄》与哥特传统[J].外国文学评论,2002,(1).
[6]高继海.英国小说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7]王国富,等译.英国古典小说五十讲[Z].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
[8]罗英.世界文学名著精要导读[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
[9]弗吉妮亚·伍尔夫.《简·爱》和《呼啸山庄》(1925)[A].见杨静远编选.勃朗特姐妹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10]刘炳善.英国文学简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11]陆小宁.《呼啸山庄》与《金锁记》感情世界之比较[J].外国文学研究,2000,(1).
[12]蔡文显,等译.英国文学史(1832-1870)[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3]王帧.英国女性文学的两座丰碑——《简·爱》与《呼啸山庄》比较研究之一[J].贵州大学学报,2005,(4).
[14]常耀信.英国文学简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15]常耀信.英国文学大花园[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16]钱青.英国19世纪文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四川省教育厅2010年度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多维视野中的《呼啸山庄》”(编号:10SA 092)。
王喆(1969-),男,四川文理学院外语系副教授,英语语言文学硕士,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