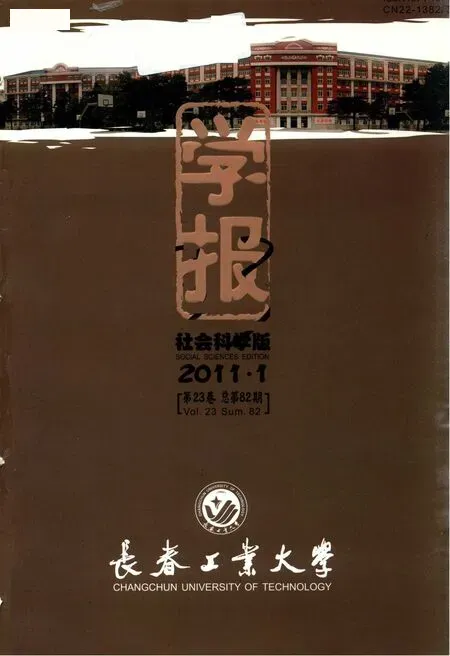从文学观转型看现代作家创作心态
2011-03-31郭长保
郭长保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7)
从文学观转型看现代作家创作心态
郭长保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7)
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发生着剧烈的变动,在这一过程中文学比社会的变革更直接预先地体现在文学作品中;那就是表现出来的近代文人的忏悔意识,这种现象在“五四”文学的创作中表现的极为鲜明,它预示了中国文学将从19世纪末对旧文学破坏之后的混乱无序状态中建立一种新的秩序与感情表达方式。新文学从他一开始就试图找到与世界文学发展相一致的契合点,同时也表现出极为复杂的开放性创作心态。
文学秩序;抒情;忏悔意识;开放心态
一、开放心态的文学理念
近代以来的文学思想和中国社会现实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从它一开始就不可能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形态的,它的胃口是现实主义的,但它完全可以吸收浪漫主义、唯美主义,乃至现代主义象征主义等有益新文学发展的一切流派。正如《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中所宣称的:“同人以为今日谈革新文学非徒事摸仿西洋而已,实将创造中国之新文艺,对世界尽贡献之责任:将欲取远大之规模尽贡献之责任,则预备研究,愈久愈博愈广,结果愈佳,即不论如何相反之主义咸有研究之必要。故对于为艺术与为人生两无所袒。必将尽忠实介绍,以为研究之材料。”“我们主张为人生的艺术,我们自己的作品自然不论创作译丛论文都照这个标准去做但并不是欲免强大家都如此,所以对于研究文学的同志们的作品,只问是文学否,不问是什么派,什么主义。”譬如,以宣传现实主义为己任的《小说月报》在改革以前主要发表“礼拜六”派的小说,但在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新潮栏宣言中就指出“现在新思想一日千里,新思想是欲新文艺去替他宣传鼓吹,所以一时间便觉得中国翻译的小说实在是都不合时代,况且西洋文艺已经由浪漫主义(Romantcism)进而为写实主义(Realisrn)表象主义(Symbolicism),新浪漫主义(New Romanticim),我国却还是停留在写实以前,这个又显然是步人后尘。所以新派小说的介绍,于今实在是很急切的了”。《小说月报》从十一卷一号开始由沈雁冰主编“小说新潮”栏进行了革新,这是大势所趋,新文学新观念逐渐占领了上风。《小说月报》的革新,说明孕育中的新文学已到了它的产期,尽管在此之前《新青年》已诞生出鲁迅的《狂人日记》,北京大学也办起了《新潮》以发表新小说为主,但那只是报春之花,而真正的百花争艳的时代应该是《小说月报》革新以后。说它是在重新寻找新的秩序,新的体系,说它是成熟的,我们从改革宣言中便可略知其大概。首先,他们“深信文艺进步全赖有不囿于传统思想之创造的精神”,以介绍西洋名家著作为己任;其次是对中国旧有文学,他们认为“不仅过去时代有相当之地位而已,即对于将来亦有几分之贡献。所以“甚愿发表治旧文学者研究所得之见”。这对近代梁启超所提倡的现实主义文学既是接轨,又是发展。
新文学家们认为建设新的文学,不仅仅是创造我们的“国民文学”,而且要把文学作为“沟通人类感情代社会人类呼吁的唯一工具”,文学能使世界不同色的人种可以融化可以调和,所以“文学家要在非常纷扰的人生中寻求永久的人性。要了解别人,也要把自己表露出来使人了解,要消灭人与人之间的沟渠”。这样的文学就是“为人生”的文学。王统照说:“我们相信文学为人类情感之流底不可阻遏的表现见,而为人类潜在的欲望的要求”。[1]实际上对于一个刚刚从几千年沉睡中觉醒的民族的文学来说更是如此,被压抑的欲望必然会通过文学表现出来,它不可能以纯客观的角度来观察人,观察社会,观察生活,它既有新奇的感受,也有不安的焦虑,既有对未来的向往,亦有对前途的茫然痛楚、兴奋、悲哀交织在一起,这是觉醒时期文学的特征。正像郑振铎在《文艺丛谈》中所说:“文学不惟是最好思想的记录,爱默生(Emerson)所说的,并且也是人们的一切感情的结晶。他把我们的笑,我们的哭,我们的叹息,我们的崇慕,恨怒,以及我们的一分一秒间的脑中的波动与变化,微妙而且感人地写下来”。
二、抒情为主旋律的初期创作
新文学早期小说创作固然庞杂多样,作家总的倾向、艺术风格也不尽一致,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可以在庞杂多样中找出一个较为普遍的特点,初期的创作“抒情”多于冷静思考。无论是“创造社”的浪漫主义代表作家郁达夫还是追随“文学研究会”“为人生”艺术的庐隐和冰心,即使被称为杰出的现实主义大师的鲁迅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更何况鲁迅在民元前留学日本时期的长篇文言论文《摩罗诗力说》就主要介绍的是英国东欧和俄国的浪漫主义诗人,试图为死水一潭的中国文坛激起一点浪花,为黑暗中生存的中国国民输入一丝新鲜血液,他写《摩罗诗力说》的宗旨在于“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这说明在鲁迅早期的文学观中认为,在压抑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浪漫主义是激起国民觉醒的最好方式,也是作家抒发内心苦闷的最佳选择。不妨仔细阅读和体会他的第一篇开山之作《狂人日记》,其中就充满激情,不乏浪漫主义特征,这篇作品从某种意义上看,可以说是一首抒情诗,是对旧文化和旧道德的诅咒诗,是一声绝叫,是黑暗的铁屋子中的绝叫。
这篇作品一般认为是现实主义的,但它同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截然不同。它给人的感觉是作者压抑已久的内心世界的一种释放,它更像鲁迅在散文诗《死火》中曾经描述过的那种被冰冻了的火,有焰焰的形,但那是“死火”,不过总有复活的时候,爆发的潜力。在鲁迅所有的作品中我们都能感觉到这种极具爆发的张力的存在,“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这足以证明鲁迅就是一团火,但又是被冰冻的火,他没有简单的乐观,更没有单纯的表露自己的内心世界,而是选择了理性的冷静的视角来观察人生和社会,因而表面看,鲁迅是那样的冷静,很容易被人们看作是一个冷峻的现实主义作家,当你真正能够解读了他的内心世界的时候,他的本质其实激烈的,这种激烈不仅仅来自他文章中的好斗精神,而是对未来充满憧憬和希望,但现实却不能使他看到希望和光明后被抑制的激情。因此,鲁迅本是一个充满个性的极具张力作家。只是鲁迅的作品同现代文学史上的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作家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已。
所以我们不难看出,“五四”时代启蒙文学的总体特质是充满激情的,是对传统几千年来人性被压抑后焕发出来的激情。
三、时代转型期的忏悔意识
忏悔意识是初期小说创作中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一类小说多采用第一人称的手法,以描写下层贫民的生活为主,但目的不仅是写下层贫民的苦难生活,而且是通过对某一事件或生活情节的描绘叙述,来反映“我”的思想感情和态度,由“我”的感情波动变化来思考人生,因此多数小说情节非常简单,这些小说还不能普遍深入地反映下层贫民的生活,几乎也没有写什么人物性格,“我”和所叙述者的感情融在了一起,构成了一幅具有巨大精神包容量的写意画。带着强烈的从朦胧中苏醒过来的知识分子对于“人”的重新发现而产生的感慨诗绪。
“人”的发现,一方面是自我的发现,另一方面又是通过自我对于他人的发现。对于自我的价值,又是对他人的价值的发现。忏悔意识正是在对于他人的价值发现中窥察到了自我。这也是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的一种新的意识,是近代以来所提倡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人道主义只是一种精神,一种倾向,一种人民性,其中几乎没有真正的自我。如杜甫的“三吏”、“三别”它只能反映出作者对于那些不幸者的同情、怜悯,其实质是在通过描绘现实来讽喻封建统治者,目的无非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而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却是对“人”的真正发现,是对人生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它不仅仅是一种“同情和”“怜悯”。正如周作人在《平民文学》中所说的,“平民文学者,见了一个乞丐,决不是单给他一个铜板,便安心走过;捉住了一个贼,也决不是单给他一元钞票放了,便安心睡下,他照常未必给一个铜子或一元钞票,但他有他心里的苦闷,来酬付他受苦或为非的同类人,他所注意的,不单是这一人缺一个铜子或一元钞票的事,乃是对于他自己的与共同的人类的运命。他们用一个铜子或用一元钞票,赎得心的苦闷的人,已经错了”。[2]如果说胡适的《人力车夫》还只是知识分子对于贫民的同情和怜悯的话,鲁迅的《一件小事》则是知识分子从劳动者的形象中对比出了自己“渺小”的一面,忏悔意识也不仅仅是发现下层贫民的“崇高美德”,而是对于整个人生的思索,他们因此而苦闷和忧患。表现出了一种深刻的自我启蒙精神和虔诚的反省精神,是以往时代的文学中没有的。这种忏悔意识是想摆脱传统束缚的心态,是对传统的绝望,对新生活的憧憬。
其实在“五四”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中,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时候,也有意或无意地和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思想融汇在了一起,其忏悔意识和忧患意识便是一种传统文人品格。西方的人道主义特别强调的是自我,是“个性”,只有在自我的价值的实现中才体现了对于人类的爱。对他人的爱首先应该是对自我的尊重。“创造社”的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似乎更体现出这种西方式的“个性”。然而,终因不符合中国人的精神而不得不逐渐转向现实。
“五四”文学的忏悔意识还表现在小说中的主人公颇像俄国十九世纪中叶文学中“多余人”形象,他们“苦闷”、“彷徨”,绝望于社会,也厌恶自己,他们感到自己在社会中是没有用的。正像赫尔岑《谁之罪》中的主人公所说,“……为甚么人生而有这样的力量和这样的憧憬,而无用武之地呢?这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自己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是如此微弱、渺小。庐隐笔下的那些凄凄切切的哀怨的女性,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都感到自己的“多余”。他们不但经济拮据,而且在思想转型时期,体现出了对国家、民族和自我的忧虑。这使他们和社会的下层有了密切的思想上的联系,很容易和被压迫者结合起来,谋求新的生活。不仅仅是我的生活,而且也包含着对民族生存前景的思考。所以,“五四”后新文学不同于传统的一面,主要体现在是以“自我”的形式表现的,把“自我”意识和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不断地反省自身存在的传统道德观,这就是“五四”文学中忏悔意识形成主要原因。
四、“爱”和“美”的追求
对“爱”和“美”的追求也是当时许多作家表现的主题。“五四”时期对于“爱”和“美”的理解,和封建的“爱”和“美”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是对人的内在生存本质的追求。正像茅盾所说:“我们觉得文学的使命是声诉现代人的烦闷,帮助人们摆脱几千年来历史遗传的人类共有的偏心与弱点,使那无形中还受着历史束缚的现代人的情感能够互相沟通,使人与人中间的无形的界线渐渐泯灭,文学的背景是全人类的背景,所诉的情感是全人类共同的情感。”[3](P45)这说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在思考问题时把中国放在全人类的文化背景中思考的,而传统民族主义思想中的“夷夏之辨”思想已荡然无存。而在传统文化中,民族主义不仅在人与人之间筑起了一堵厚厚的墙壁,而且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也隔开了一道厚厚的墙壁,无法有真正的感情的交流。“五四”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寻求突破这种“隔膜”的途径。鲁迅在《故乡》中就沉重地感觉到了这种“隔膜”的痛苦,是封建礼教使他与闰土之间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他希望下一代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再不要像他们似的存在精神上的“隔绝”。但鲁迅并没有指明如何消除这“隔绝”,而冰心则想以“母爱”、“童真”去感动那冷冰冰的超人,她希望人类就像母亲爱活泼天真的儿童一样去相爱,使爱变成一种天性,消除“隔膜”。她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写“母爱”,歌颂“母爱”的作家。固然,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找到许多“母爱”的例子,但那都是带着封建理性色彩将“母爱”赋予了浓厚的封建理性思想。所以,这样的思考,在“五四”时期是有积极意义的,她把母爱赋予了现代色彩。
另外,叶圣陶对“自然之美”和“童稚之爱”的歌颂,王统照对于超越现实人生的“爱”和“美”的追求,也都是觉醒者的对于人的思考和追求。这也是觉醒时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不是在幻想,而是在追求,它不是飘渺的,而是充实的,正是在对“爱”和“美”的追求中表达了“五四”后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
五、“国民性”主题的发掘
对“国民性”主题的发掘,也是当时文学创作所关注的问题。二十世纪初,改良主义者梁启超就提出了“新民”的主张,他说:“现在的民德民智民力,不但不可以和他讲革命,就是你天天讲,天天跳,这革命也是万不能做到的”。[4]而在近代,真正拿起改造“国民性”武器的是鲁迅。《小说月报》的改革宣言中也说:“同人深信一国文艺为一国国民性之反映,亦惟能表现国民性之文艺能有其价值,能在世界的文学中占一席地”。对于一个刚刚从沉睡中醒来的民族来说,对于一个落后的民族来说,对于一个有进取精神的民族来说,对有反思精神的民族来说,它必然有着反省精神,它必然正视国民性的弱点,对于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民族来说,既有闪光的珍宝,亦有积淀的沉疴。
“五四”文学的启蒙性质,需要以揭示国民性的弱点为主。它是一种更深层的文化反省精神。在“五四”后的文学创作中反映国民性题材的作品,除鲁迅外,还体现在二十年代中期受鲁迅影响的“乡土文学”中,他们对农村的落后、闭塞、愚昧陋习的展示,使我们不仅看到了那些淳朴的风土人情画面,而且也看到了中国农民习惯于逆来顺受的听天由命的落后意识。如许杰的《惨雾》、《赌徒吉顺》就是在通过野蛮愚昧的互相残杀,恶劣的民风;做着发财美梦的赌徒的堕落来写中国传统乡村的国民性。“乡土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二十年代中国农民的落后和牢国的传统意识。
为什么在1923后会兴起“乡土文学”难道仅仅是寓居都市的作家对于故乡的怀恋和反省?难道仅仅是对于淳朴风土人情的赞美与歌颂?其实它蕴含着在现代意识冲击下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乡村民俗社会的重新审视,是“五四”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把启蒙转向平民的重要特征,也是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向底层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譬如这一时期,即使以反映知识分子题材为主的郁达夫,同样一改过去的狭隘圈子,写出了《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把自己的视野转向平民社会,开始关注平民的生活。
[1]王统照.本刊的缘起及主张[N].晨报副刊,1923-06-11.
[2]周作人.平民文学[J].每周评论(第五号),1919-01-19.
[3]茅盾.创作的前途[J].小说月报,1921,12(7).
[4]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郭长保(1958-),男,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