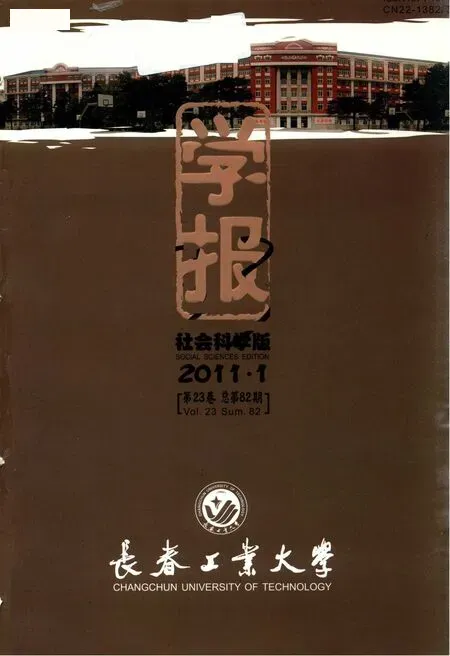城市化进程中岭南文化的当代转型
2011-03-31陈超
陈 超
(广东金融学院 财经传媒系,广东 广州 510521)
城市化进程中岭南文化的当代转型
陈 超
(广东金融学院 财经传媒系,广东 广州 510521)
城市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由此引发的文化转型是不容回避的命题。作为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快速的城市化不仅直接改变了其传统的社会生产模式、消费模式和人的生活方式,还造成了对传统岭南文化精神内核与价值伦理的强大冲击。因此,从现实情怀出发,关注转型期岭南文化的传统嬗变与新质素的产生、渗入,审视岭南文化在这一过程如何更好地构建其新的精神与时代品质,这既是“岭南文化”这一概念获得当前学理价值和丰厚时代内涵的现实要求,又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文化转型过程中的理论需求。
城市化;岭南文化;转型
中国的城市虽然已有两千多年甚至更长的历史,但结束城市与乡村的无差别并开始培育一种现代城市意识和文化精神,却是近百年的事。1840年,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清朝的大门,中国从进行防御性的现代化开始,几经浮沉,几经波折,中国城市化从上海到香港,从香港到广州、深圳,已经碾过了一个半世纪的风尘,至今仍在延续。中国城市生活被大量的描写最早出现在明朝的《三言》、《两拍》,而从城市意识观照现代城市化过程、描摹城市人处境、反思现代性问题的作品,则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当时上海作为中国大都会,凭着租界所提供的文化资源、经济依托和制度保障,使置身其中的人们在感受现代生活欢乐刺激的同时,也体味着现代生活的苦楚,这种两难的境地在旧海派作家“新感觉派”里表现明显。如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头一句就是“上海,建在地狱上面的天堂”。梁得所在《上海的鸟瞰》写道:“黄浦滩的景象,足以代表上海,使我们知道她是一个现代物质文明的都会,同时是情调深长的地方”,上海“很有诗意”。他们不乏对城市的批判和揭露,但这种批判又是根植于他们对物质世界迷恋之上的,因这种暧昧的立场,展现了旧上海现代性和城市意识的不彻底性。1940年代末,随着一轮一轮城市改造运动,工商业文明下培育起来的城市人格和市民精神受到质疑,在强势的体制文化和农业文化威压下,城市化的内在制约和精神质素都渐渐消失。于是,在冷战格局下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城市被纳入新的轨道,并中止了它在过去的发展——只有香港、澳门作为西方殖民地在全球城市化的浪潮中得以同步前行。1979年之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才从广东开始重启从传统到现代、从乡村到城市的城市化进程,中国社会由此开始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变迁”。
然而,随着这场变革的深入和扩展,城市文明与生态文明的悖反日益突出,对“城市化”的批判渐呈汹涌之势,其主要集中在对城市造成的生态污染、人性异化、人种退化和精神之根的丧失等方面。于是,一方面,张炜、贾平凹、迟子健等人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出发对当下城乡伦理歧境进行了揭发,在皈依传统和反叛超越中,体现着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坚守;另一方面,当前“底层”叙事和打工文学却从城乡二元对立导致人的困境出发,通过“贵乡村、抑城市”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窥视着底层生存的“无根”状态和精神沦丧。但总的来看,当前批评界存在着说教意味过浓,对城市化所带来启蒙理性的认识不足,和对市场化变革和现代化进程存在隔膜和疑虑的现状。如单世联在《都市文化的反讽》一文中所言:“城市文化市场的消化力越来越强,昨天还闻所未闻的,今天可能十分平常,过去的对手,现在可以成为座上客,文化史上生前憔悴死后殊荣的现象并不罕见。凡·高生前贫苦至死,死后作品价值连城,整个现代主义文化都经历了从异端到正统的角色转换。”[1]
这同样体现在对当前岭南文化和广东人文精神的认知上。快速的城市化在给广东带来纸醉金迷、夜夜狂欢的繁华背后,在让视听艺术、网络文化、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畅通无阻的同时,也使传统岭南文化的弊病与消极因素日趋体现明显:追求效率、急功近利却过度掠夺自然、污染环境;追求世俗却使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一度盛行;务实过头同时陷入了经验主义的桎梏;注重个人生活感觉却为黄、赌、毒提供了温床等。面对这些问题,虽然社会媒体和文化理论界相继开展了诸多讨论和研究,但从当下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其中的策略、意见和建议缺乏足够的深度和应有的现实情怀,亟需得到进一步的梳理和提升。
目前,中国城市化过程所带来的“趋同化”现象日益表现严重,主要体现在城市建设与旧城改造致使城市面貌日趋于同化、大众文化与流行文化致使地方文化特质日趋于同化、快餐文化和洋文化使人们生活方式日趋于同化,现代人功利虚荣、唯利是图、个人至上的恶俗化和趋利化日趋严重,等等。在此种背景下,岭南文化的社会弊病与时代痼疾也相应产生并表露明显,其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追求效率却急功近利,过度地掠夺了自然资源。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耕地锐减,污染严重,令人担忧;(二)务实过头却致使思维封闭,成为持续进取和发展的桎梏;(三)追求个人感官却使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盛行。个人过于满足感官的享受,为消费主义打开方便之门,广东一度的黄、赌、毒泛滥,与这种文化观念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四)追求速富却使迷信复活,近年来特别是潮汕一带沉迷“六合彩”的现象就是这种思维的结果;(五)小富即安,沉醉于昔日的荣光,等等。这些文化消极困素的影响日趋于严重,急需得到进一步地纠正和反思。
事实上,当前中国“城市化”其认识本身就存在误区,即一方面缺乏把农村作为现代进程的积极因素纳入经济框架结构的实践,另一方面又缺乏把农村人尊严融入城市提供应有的知识和思想豁蒙的保障,造成了长期“城”、“乡”二元对立的文化心理。而现代文明所暴露的弊端也使人们一方面先入为主地将城市文明定性为“恶”、把乡土文明定性为“善”,另一方面又从日常生活到个人精神追寻和理性维度上对“城市”持有好感,这一矛盾的社会心理,让当前广东文学(特别打工文学)在或维护、或批判的套路上不断徘徊。因此,对岭南文化的内部肌理和思想探寻,应积极审视城市化进程中农裔知识分子、农裔官人、农民工、农裔女性等的行动选择及心路历程,在广度和深度上寻求传统文化与城市建设和发展最为关联的价值所在。
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认为:“伦理道德是文化的核心价值。如果一个文化的伦理道德价值解体了,那么这个文化便有解体之虞。所以,谈挽救文化的人,常从挽救伦理道德开始。”[2](P94)“城市化”实现了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地域转移,并以其特有的社会分工改变了人们原有的职业价值观并铸炼出城市生活所特有的现代性质素。一方面,“城市化”使传统道德价值观念日趋缺失,使城市过客与新移民的物质欲望不断膨胀,对传统岭南文化气质造成了疏离。另一方面,由于现代性的渗入与生长,使社会文化心灵秩序重整和社会规范得于整合的同时,也催生了人们新型伦理建构和具有契约理性特征的行为选择,以至于新的生活方式涤荡了农民身上积累的传统因子,使他们的伦理价值观和社会行为发生了巨大转变,并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新的现代思维——当然这里边也包含着传统“美”的沦丧和现代“恶”的增殖。对此,岭南文化理应拣拾那些因历史功利目的而沦落或丢失的人文关怀意识来作为当下的强调,以人道主义的悲悯让其中传统、古朴、谨严的品格留驻,以保持历史行进中人生命的庄严和文化模式的康健。
同时,在具体的文化发展战略和设计中,笔者认为可以运用“减长”(de-growth)模型来确立岭南文化精神内涵生态发展的观念。“减长”模型是洛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于1971年建立的一个减长和生物经济的模型,他认为物理上的有限性以及热动力的第二定律表明:当熵增加时,有用的能量被不断耗竭。基于此,人类不能设计和追求一种无限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因此,当代岭南文化的精神构建,宜通过适度消费、设计和发展来淡化对发展硬度、速度、频次的崇拜,将社会资源重点转移到具有公共性的艺术、家庭、社区、人伦等文化项目,以提升文化品质和精神内涵。
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是具有历史性、发展性与创造性的延伸,而不是毁灭的、虚无的与消解的断裂。1970年代霍·廉姆的政治学经典《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提醒人们,城与乡的问题不再是隔离孤立的,而是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的。这种观点为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的思想提供了支撑,她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提出:“缺乏研究,缺乏尊重,城市成了牺牲品”,“不相信我们以及城市的存在本身就是自然不可分割的、合法的一部分”是危险的,[3](P127)她批判源远流长的“反城市”思想只不过是一个骗局。这无疑为当下中国城市改造法则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也为方兴未艾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当前岭南文化面临的内涵构建提供了启示。因此,面对现代城市的高速发展,当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以“三位一体”之势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时,岭南文化理应在对历史文化、建筑文化、自然环境文化、风俗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的融合与拓展基础上,寻求“激活优良传统、融通历史与现实、整合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途径,以此来形成一种既具现代“都市”文化底色又有地方传统特色的文化品质,建构“延续传统、突显特色”的岭南文化新内涵和新质素。
[1]单世联.都市文化的反讽[J].现代与传统,1993,(7).
[2]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
[3]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上海:译林出版社,2006.
广东金融学院2010年度校级青年课题:“城市化进程与岭南文化的现代转型”资助项目(编号:10XJ03-01)。
陈超(1981-),男,硕士,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讲师,主要从事文学批评与艺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