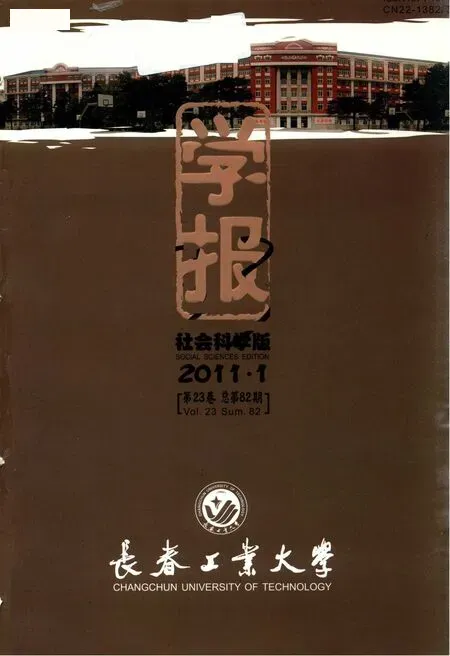论李白政治悲剧与古代“士”文化精神之关系
2011-03-31祝江波
祝江波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涉外学院,湖南 长沙410004)
论李白政治悲剧与古代“士”文化精神之关系
祝江波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涉外学院,湖南 长沙410004)
李白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但在“科举”已成为士人入仕之重要途径的盛唐时期,这位平生夙愿是以布衣直取卿相的诗人,却未能实现其政治理想,从而导致一生之政治悲剧。这一悲剧的原因除了李白自身的性格、气质以及政治素养之外,还有在其身上体现出来的古代士“志于道”的文化性格,以及盛唐时期所彰显之“儒道合流”之士林风气。
李白;士;文化性格;士志于道;儒道合流
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李白卓越的诗歌成就让后人产生无穷的探究热情,其生平遭际与个性、理想也同样让人感慨不已。李白自少年起就有“济世达己”的政治抱负,其《与韩荆州书》自言:“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偏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皆王公大人许以义气,此畴囊心迹,安感不尽于诸侯哉!”[1]成年后更是矢志不渝,且清高自许,一生希望能获帝王权臣拔识,为争取不朽功名,甚至使用“干谒”这种与其超然绝世的人生理想及当时士子仕晋之道极不谐调之世俗手段:“不愿也不能象同辈与当代其它文士那样,卑躬屈膝,奔走于势要之门,求得举荐,去走科举的道路”。[2](P383)然而,李白的政治之途显然是失败的,其中原因,学界颇多争议,或以为李白不甘作御用文人,主动告退;或认为李白为佞臣所嫉而遭谗被逐;还有学者则从李白之政治见识入手,指出其并无高明的政治见识与才能,故玄宗不予重用。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现实及其个人遭遇来看,皆不足以解释李白失意于政治之深层原因。本文以为,李白一生表现出古代“士”之文化性格,如“士志于道”、“儒道合流”等,而这也恰恰是李白既汲汲于功名未能如愿又隐逸退让却终不能忘怀,及其狂傲、果敢之个人品格之原因。
一
盛唐为古代中国极臻鼎盛之时,文化态度极为开放,各种思想盛于一炉。受此风影响,李白对儒、道、纵横家诸家兼收并蓄,一生都不曾彻底抛弃或皈依任一思想,此为多数论者所赞同。因而形成李白那种狂傲、自信的性格与气质,前人诸多遗产中符合“自我”之因素,李白皆取之,但又“不凝滞于物,而与时推移”,所谓“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1](《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序》)颇近道家,然其向名立功之心终其一生也未曾消歇,有儒者济世之气。而其求功名所取之径则为战国纵横家之惯伎。三者皆为李白所摄,却又不为所囿。李白此种看似高标独立的执着并非凭空而来,实有深远之历史文化传统。这一传统主要就是由形成于先秦时期的“士”阶层的文化性格构成的。
无论“士”阶层究竟崛起于何时,但西周和春秋前期,士为低级贵族之推论应可确定无疑,顾颉刚先生指出:“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戈以卫社视之义务。”[3](P85)另外,《左传》桓公二年:“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4]《国语·晋语》:“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5]都足以说明“士”属低层贵族。春秋“士”为“四民之首”,社会地位比其他平民高,有的还可任官,或佐贵族管理采邑。①如《诗·周南·兔罝》说:“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肃肃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肃肃免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便是当时士状况之真实写照。春秋末至战国时,随着封建等级秩序的崩溃瓦解,士逐渐从日趋没落的贵族阶级中游离出来,并开始脱离生产劳动,逐渐形成“游士”集团,周游列国,求得谷禄,执相礼之职业。士之成份随之不再限于低层贵族。士阶层的出现,乃是“起于当时社会阶级的流动,即上层贵族的下降和下层庶民的上升。由于士阶层适处于贵族与庶人之间,是上下流动的汇合之所,士的人数不免大增。这就导致士阶层在社会性格上发生了基本的改变”。[6](P12)同时,礼乐崩坏,原为贵族阶级所控制之礼制开始为平民阶层学习与掌握。身份与社会地位的丧失,使“士”对外在秩序之义务感消失殆尽,自我地位的重视和物质利益的追求代之而起,器用之学始为士之仰禄手段。为施展抱负,士需依附君主和权贵,而后者也同样需士之智慧和能力助其掌握政权、巩固统治,在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中以立不败之地,结成所谓“主卖官爵,臣卖智力”之政治交易关系。“道”和“器”的分离使战国诸子皆纷纷言“道”。
“道”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在西周曾经是包括士在内的贵族阶级为自己树立的政治和道德的准绳,然至东周时代,由于社会关系的激烈变动和“士”的分化,“道”观念已呈现了多元化演变的趋势。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曰:“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皆务为治者,直所言之异路,有省不肴耳。”[7]诸家“皆务为治”之具体内容虽并不一致,但此种历史责任感的存在本身,却己形成士阶层共同的文化心态。儒家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先前“道”观念的一些积极内容,一方面强调“士”要“志于道”,即固守自己的精神家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8](《泰伯》)“道”是崇高而神圣的目标,乃士人从事各项社会活动的内在动力,士对自己实现历史责任的能力极为自信,如孟子就自诩五百年一出的“名世者”:“如欲一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8](《公孙丑下》)正体现士阶层自信自尊之心理状态。基于此种心态,士独立不羁、刚毅果断、傲视群雄,并对“道”之追求锲而不舍。另一方面,为实现其“道”,士又需自我克制:“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8](《颜渊》无“克己”精神,一味放纵,自然难行其道。①《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蔺相如事迹就典型地表现了士阶层“克己”美德,当蔺因“完璧归赵”、“渑池之会”等功绩拜为上卿后,主动回避廉颇的嫉妒与羞辱:“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死。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终使廉感愧,遂为刎颈之交。但这种自我克制与自我牺牲之精神,与自信自尊的心态并不矛盾,两者相辅相成,都是实现“志于道”必不可少之条件。
李白一生之政治追求体现的就是古代“士”这种“志于道”之精神,李白自言“奋其智能,愿为辅弼”,[1]数游长安,从未参加科举考试,期望君臣际会、平步青云,以谋臣、策士身份位登宰辅,其行径固然体现了其早年受纵横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但另一方面显然更是“士”之自命不凡的自我意识与人格力量的表露与支配之结果。
李白每以前代那些因特殊机缘而位登宰辅或因献策而立功的谋臣策士自比,“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1](《梁父吟》)对吕尚由贫困到宰辅的热情赞颂,实亦包含着李白对自己的期许,进而以严子陵与汉光武喻自己与玄宗的关系,“自是客星辞帝座,元非太白醉扬州”,[1](《酬崔侍御》)足见其平交王侯、兀傲不屈的精神状貌。也正因其强烈之入世精神与自命不凡的自我意识,故对抱残守缺、皓首穷经的俗士进身方式极为蔑视,公开宣称“予为楚壮士,不是鲁诸生”。[1](《淮阴书怀寄王宋城》)很显然,李白此种入世精神在体现建功立业的进取热情与宏远的襟怀志趣之同时,更深藏着一种正直高尚的品格情操与自尊自重的人格力量。海外学者余英时先生在考察古代“士”文化时,曾指出古代士的价值取向是“以‘道’为最后的依据”,[6](P44)士必须自觉继承文化传统,弘扬人文精神,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以内在超越方式追求现世社会的和谐安宁。他们治平理念来源于一种顺应天地自然、人类和谐相处并以“仁德”为己任、仁孝遍天下、礼义占主导的“礼治”传统,是为“道”。“道高于势”是士始终坚持的批判精神,更是其不屈于强权之最好精神阐释。孟子曾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8]士与世俗政权的合作只能建立在“道”的共同基础之上。虽然不能把“士志于道”说成是古代士阶层的整体性格特征,但不否认其中确有道德理想和政治信念之固守者,一旦所守护之文化理念与世俗政治权力发生冲突时,他们必须坚持以道为己任,甚至不惜以身殉道,东汉“党锢之祸”便是证明也。
同时,士具有“辨然(否),通古今”[9](《佾言》)之文化特质,从而形成了独立不羁的自我人格和坚定不屈的个体尊严。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8](《子罕》)“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8](《滕文公下》)都表现出士高度重视个体尊严的文化心态。如果说,孔孟所言还只是理论形态,那么颜回处陋巷箪食瓢饮,“也不改其乐”[8](《雍也》)、庄子“曳尾于涂中”[10](《秋水》)、颜斶“生王之头不若死士之垄”[11](《齐策四》)、鲁仲连“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汕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7](《鲁仲连邹阳列传》),则是各以不同的生活全面而生动地展示了“士”之自我人格和个体尊严。因此,李白一面“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1](《为宋中垂自荐表》),既积极进取以求仕,又抗节自立不媚世;另一面又为自身设计好“事君之道成,荣幸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1](《从驾温泉宫醉后赠杨山人》)那样高度理想化的整个人生,实践着“士志于道”的人生理想。
二
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社会处于一种极度繁盛又隐忧潜生的特定状态之中,科举虽为士人入仕拓宽了晋身之途,然这种可能毕竟有限,特别是士族势力因“循资格”考选制度而再次得到稳固之际,士人“登龙门”之愿并非总能实现。这种隐忧投射在希望以进取为主体趋向的士人心头,再加之个人遭际而演为不平。至开元后期到天宝时期,社会隐忧加剧,仕路因士族控制中枢更加困难,士人心中之不安不平益重,竟至于幻灭境地。王维的皈依空门即是士人失落感的时代缩影。
在这种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社会环境里,士人应如何选择出处?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8](《卫灵公》)所谓“有道”、“无道”,指政治状况之好坏而言,士人在其中作出合理选择才是依道而行,“危邦不入,乱邦不居”[8](《卫灵公》),选择出世入世也就成为士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最佳精神归宿。士人孜孜不倦的仁爱、大同、和谐社会理想形成了他们对时政的终极关怀和对当权者及时势的批判精神,其内省又形成了自我修为、追求精神至境的崇高理念。于是,儒道互补已深深融入“士”之灵魂深处。当儒家“入世”之价值取向难以实现抱负时,士人便向道家寻求纯粹精神与崇尚自然的“出世”归宿;当儒家讲求“文饰”而逐渐陷入浮华不实、名利累心之泥淖时,道家的向往自然、清心寡欲之思想便为解脱之径;当儒家的“有为”,强调个人对民族、国家的责任,令士人陷入危境与困惑时,道家之“无为”为其追求个人对社会、现实的超脱提供了理论依据。①需注意者,尽管士在不得意时常以“独善其身”相慰,常作悠然自得之态,然内心终不能忘怀世事,犹心系天下,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岳阳楼记》)是也。士人就在这样的两极之间徘徊游走,终千年犹不能摆脱儒、道之共同影响,而学养与生活旨趣游于儒、道间之李白更不能例外。
李白出蜀之际所作《大鹏赋》序曰:“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著《大鹏遇希有鸟赋》以自广。”[1](《大鹏赋》)大鹏形象显然源出庄子:“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10](《逍遥游》)纵观李白一生,“飘然出世,洒脱不羁,傲岸王侯,不受羁绊,所追求的,也就是《逍遥游》中大鹏形象所体现的超越世俗的境界”[2](P164)。有趣的是,李白虽自比庄子笔下“大鹏”,似有庄子之风貌,实际却不然也。
对于中国思想史来说,庄子绝非仅仅是对老子哲学的发展,在建构士人个体尊严之文化性格上,影响更巨。尤其是战国末至汉初,老子之道与法家、黄帝之学结合形成黄老之学,越来越被人从政治权谋角度去诠释之后,与庄子的分殊更成必然,如陈鼓应先生所言:“……若论到哲学论题的深度、广度及其繁复性,庄子则大大超过了老子。老庄之间虽有密切关系,但彼此之间也有很大不同。”[12](P5)而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对世俗王权的精神超越。庄子生于“道术将为天下裂”之战国晚期,在春秋时便已开始崩坏的以周礼为根本制度的政治格局此时到了最后溃亡的前夕,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之中,诸侯征伐,篡弑之事层出不穷,道义为赤裸裸的暴力所代替。这样的时代容易让人产生对政治的憎恶感,乃至对生命变幻、人生无常的绝望感。庄子的无为适己即与这样的政治局面直接相关。当政治暴力发展到可以随意摧残个体生命之时,个人之抗争也就微不足道,个人内在精神世界的重要性便开始突显。出世的隐逸人格、自然人格是庄子理想人格的主要表现,适己之学是庄子在出世精神支配下的人生取向。庄子追求“独与天地精神独往来”与对世俗王权的超越之精神,渴望“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友”[10](《天下》)之境界。于是,其笔下之大鹏“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追求的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
李白则生于政治相对宽松、物质文化生活较为丰富的盛唐,这一时期,士人皆热心国事,再加上科举制度的兴起,庶族出身的士人也有入仕之可能。这一切使得唐代(特别是盛唐)士人与社会生活之联系更趋紧密。李白追求安社稷济苍生的理想,幻化成大鹏形象,就是风驰电掣的主动追求,“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1]。因而即便被逐,远离政治是非倾轧之所,漫游名山大川,巢云松、受道篆并广交隐者道流,生发“永结无情游,相期邀云汉”[1](《月下独酌》之一)之避世隐逸思想,自称“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1](《送蔡山人》),将自身与整个时代社会对立起来,真有惊世之慨也。但在追求隐逸之同时,又常为“明主倘见收”美梦所绕,其仙道思想本质上与道家之遗世独立有很大不同,所谓“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1](《拟古》之三)、“蟹鳌即金液,糟丘是蓬莱”[1](《月下独酌》之四),即透露了对仙道世界的忧疑。李白在失意境遇中数次宣称要远济沧海,高飞蓬该,实则是“挥斥幽愤”[1](《暮春江夏送张祖监示之东都序》)之心理渲泄。李白的这种心态显然与庄子要求摆脱一切物累至“逍遥游”之绝对虚化境界迥然不同,反与讲究积极入世之儒家孟子相近。
孟子虽积极入世,主张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8](《万章上》),以“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自许,但周游列国数十年,四处鼓吹仁义之道,非但未受到诸侯礼遇,其救世思想反常被讥以“迂阔”。在数遭挫折后,便从极度之自尊自信滑入极度之自哀自怜。与庄子一样,孟子的极度自尊是以天道与我心相通为理论依据的,这是战国诸子以人为本位对传统的天人相应论的重要改造。庄子说“以天合天”[10](《达生》),孟子则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存其心,知其性,所以事天也。”[8](《尽心上》)庄曰“入山林,观天性”[10],孟则主张“吾善养我浩然之气”[8]境界。虽然庄以自然虚无为天道,孟以仁义为天道,但二人皆有以我心通天心的观念,有对自我价值的夸张性的认定与对自我精神的极度张扬,这种气质在罕言天道与性的孔子与以天为“混沌”之物构成的老子身上皆不得见也。
庄孟这种共同的性格成为古代“士”之主要文化性格。依时代与个性、经历的不同,士人们出此入彼,以不同色调重现庄子、孟子或者庄孟合流的精神。然要使二者得到完美结合,则有待适宜的时代条件与个人禀赋。而李白之性格与精神气质既有庄子的桀傲与逍遥,也有孟子的积极与孤愤,同时也兼具二者追求超越世俗政治之理想,从而在“儒道合流”的时代精神中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总之,在短暂的政治生涯中,李白因其特殊的气质与素养,屡遭挫折,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为“士志于道”之精神诉求。失意后仍能安然自处,则是承续魏晋以来“儒道合流”之趋势,不再刻意出处也。也正是这种对功业的九死不悔之追求及屡遭失败之悲剧,“穷而后工”,李白将其满腹才情与高节之风挥洒成诗章,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史上一座后人难以逾越之高峰。
[1]李白.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周勋初.李白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3.
[4]洪亮吉.春秋左传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薛安勤,王连生.国语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6]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7]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刘向.新序·说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0]庄周.庄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1]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7.
[12]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祝江波(1974-),男,硕士,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教师,主要从事思想哲学及中国文化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