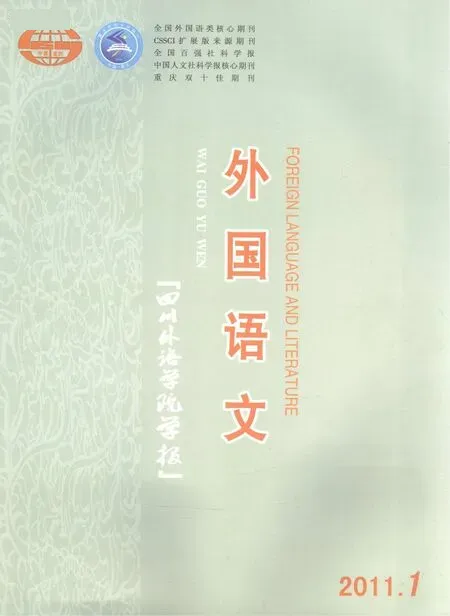多样与统一:认知诗学学科理论的难题与解答
2011-03-21熊沐清
熊沐清
(四川外语学院 教学改革与外语教育资源研究所,重庆 400031)
多样与统一:认知诗学学科理论的难题与解答
熊沐清
(四川外语学院 教学改革与外语教育资源研究所,重庆 400031)
由于发展时间短暂,认知诗学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还存在一些理论上的分歧与含混,概括为三个主要问题,即:认知诗学是一门学科、一种文学理论体系或者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认知诗学的目的是对文学作出某种新的解释新的发现,还是仅仅对已有结论作出新的解释?如何实现认知诗学的本土化?作为一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学科理论方面的多元性、多样性有利于它的丰富和拓展,但一定程度的“统一”也是必要的,即是在学科理论上坚持认知科学的理论基础,研究对象上始终聚焦于文学(包括文本研究和理论研究),研究目的上追求新的发现,从而保持学科理论的完整性、连续性,研究对象的确定性,方法论的独特性,如同美的事物一样符合多样统一的法则,它就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认知诗学;学科理论;多元性;统一性
1.引言
认知诗学(cognitive poetics)在国外的蓬勃发展虽然还只是近十年的事,但从以色列学者Tsur发表论文“什么是认知诗学?”(What is Cognitive Poetics?1983)和出版专著《走向认知诗学理论》(Toward a Theory of Cognitive Poetics,1992)以来,至今已有近30年了。在国内,从清华大学刘立华、刘世生2006年发表“语言·认知·诗学——《认知诗学实践》评介”(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年1期)一文至今,也已有五年时间。与其他学科尤其它发端于斯的认知科学(主要是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相比,时间虽短,但却日益显示出盎然生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2008年,四川外语学院在广西南宁主办了首届全国认知诗学学术研讨会,今年8月还将在银川主办第二届全国认知诗学学术研讨会。2010年11月,首届认知诗学高层论坛在北京中国石油大学召开,国外认知诗学领军人物之一Freeman,以及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社科院、苏州大学、四川外语学院等高校的数十位学者和博士生在认知诗学学科理论、认知诗学方法的应用、认知诗学本土化等领域作了精彩发言,显示了认知诗学在国内的良好发展势头。
但是,由于发展时间毕竟短暂,认知诗学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还存在一些理论上的分歧与含混,这些问题在首届认知诗学高层论坛已有显露。这些问题的产生一方面源于认知诗学发展时间的短暂,另一方面也表明认知诗学学科理论的多元性特征,当然,多元性之中也隐含着含混性。笔者将这些理论上的分歧与含混概括为三个主要问题,即:认知诗学是一门学科、一种文学理论体系或者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认知诗学的目的是对文学作出某种新的解释新的发现,还是仅仅对已有结论作出新的解释?如何实现认知诗学的本土化?笔者将自己在首届认知诗学高层论坛的发言加以整理、扩充,撰就此文,就上述问题陈述己见,供感兴趣的同人参考。
2.文学理论还是文学分析方法?
认知诗学是一门学科、一种文学理论体系或者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这个问题其实笔者在“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新接面:两本认知诗学著作评述”(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4期)和“故事与认知:简论认知诗学的文学功用观”(载《外国语文》2009年第1期)两篇文章中已有论及,此处略作补充。
作为“认知诗学”一词的发明人(Stockwell,2009:16),Tsur的确是将认知诗学仅仅视为一种研究方法。在新版《走向认知诗学理论》(2008)第一章中,Tsur明确指出:认知诗学是运用认知科学提供的工具研究文学的一种跨学科分析方法,其目的在于发现信息处理过程是如何制约和影响诗歌语言和形式或批评家所作的评论的。他认为,20世纪文学批评一个重要的不足就是:批评者们沉湎于文学文本的效果,却难以把这些效果与文本结构联系起来。另一方面,虽然有一些分析学派和结构主义的批评家在描述文学文本的结构方面做得很出色,但他们对这些文本对人的意义却不甚了了,或者,他们所感知到的效果难以解释清楚。相比之下,认知诗学提供的认知理论可以系统地解释文学文本结构与效果之间的关系。(Tsur,2008:1)
但是,Stockwell和 Gavins、Steen等人的观点则不同。Steen和Gavins认为,存在着两种认知诗学,一种与认知语言学的崛起有密切关系,以Burke和Crisp为代表。另一种则属于更为广义的认知科学,以 Tsur、Gibbs和Oatley为代表。而比较典型的、更有特指意味并建立在认知语言学基础上的是Turner的认知诗学。(Steen& Gavins,2003:4-5)
关于认知诗学是一种研究方法还是一种文学理论,Steen和Gavins与Stockwell的观点是一致的。Stockwell强调:认知诗学不仅仅是文学批评重心的一种转向,更是对整个文学活动过程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估。因此,认知诗学是对文学的基本的思考方式,而不仅是框架本身(Stockwell,2002:5 -6)。Steen和Gavins(2003:5)也明确提出:认知诗学并不仅仅是认知科学的一个分支,它首要地是一种新的诗学。
那么,Steen和Gavins等人的“诗学”与Tsur心目中的“诗学”是否可以等同呢?两者间其实有着微妙的差别。Tsur在新版《走向认知诗学理论》开篇处援引德国语言学家Manfred Bierwisch的“诗学”定义说:“诗学的真正目标是出现于文学文本并决定诗歌特定效果的那些规律性的东西;归根结底,是人类能够创造诗的结构并理解其效果的那种能力,换言之,就是某种可称为诗的能力(poetic competence)的东西。”(Tsur,2008:1)而 Stockwell(2002:8)在《认知诗学导论》“前言”中则强调“在现代文学理论中,诗学逐渐含有‘理论’或‘系统’之意”。这表明两人之间有两点不同:第一,Tsur的“诗学”概念恪守传统,仅聚焦于“诗”。事实上,他运用认知诗学方法所分析的文学文本也都是诗歌而不包括小说或戏剧,而Stockwell等人所分析的文本既包括诗歌也包括小说和戏剧文本。第二,Tsur的认知诗学是用以分析或解释文学——确切说只是诗歌——的效果,而 Stockwell则更注重“诗学”概念的现代性,把它视为关于文学的系统理论。
当然,两者都注重效果分析,把认知诗学视为文学效果分析的一种方法(approach),但Tsur止步于此,而Stockwell似乎更具有雄心,他打算走得更远。在《认知诗学导论》一书中,他不仅运用认知科学的某些概念、方法来分析文学文本,而且还专辟章节探讨了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功用、人物类型以及若干文学基本范畴如摹仿(mimesis)、文本肌理(texture)、话语(discourse)、意识形态(ideology)、情感(emotion)、想像(imagination)等。他在2009年出版的新著《文本肌理:关于阅读的认知美学》中,提出了“认知美学”的概念,并讨论了移情、身份认同、伦理等较新的文学论题,这就使他的讨论不仅超越了一般批评方法的范畴,而且也超越了文体学的一般讨论范围。不难看出,Stockwell以及Steen等人更多地是在现代意义上使用“诗学”概念,即“诗学”意为系统的文学理论。
既然是一种新的文学理论,认知诗学就不仅仅是认知语言学的应用。理由主要有三点:
(1)认知诗学应用的不仅仅是认知语言学的概念与方法,它还运用了认知心理学、文体学、叙事学、传统文学批评等来自多种学科的方法。比如,《认知诗学导论》及其姊妹篇《认知诗学实践》中论述的脚本、图式、寓言、世界理论、叙事理解、意识形态、情感、想像等,这些概念或命题都不是认知语言学固有的或主要的命题,而且大多超越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范围。
(2)作为“诗学”,它不仅注重语言分析,也注重情感、美感乃至社会层面的分析,这些也不是认知语言学所能包容的。这一点,在 Stockwell于2009年出版的新著《文本肌理:关于阅读的认知美学》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在该书第一章,他(2009:2)指出:认知诗学的分析模式、方法、理论假设和有效性来自认知科学多个分支学科。但这些借鉴而来的东西都已与它们的源学科(source disciplines)有所不同了,因为它们已被置于一个新的“移植语境”(transplanted context),受到了重新铸造和重新界定,一切都指归于文学分析,因此,认知诗学既是认知科学的一种应用形式,又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他所说的认知科学主要包括: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心灵哲学以及神经科学的某些方面。
(3)仅就“认知”而言,在认知诗学兴起之前就有学者从认知角度对文学进行了分析。比如,Hobbs在1990年出版的《文学与认知》(Literature and Cognition)一书中,就从心理学角度,在话语分析框架内对文学作了认知分析,他关注的是虚构、想像、叙事、隐喻、连贯等问题。这些问题除了隐喻外,其他的都不是认知语言学的经典命题。该书的参考文献也没有一部认知语言学著作。
3.“本土化”实现途径
“本土化”是近年来国内许多人文社会学科共同的呼声和追求,它一方面反映了国内学者在引进、吸收西方学术新成果时表现出的那种不甘落后的理论焦灼;另一方面,许多西方理论或研究方法也的确显露出不足,尤其当这些西方理论移植到东方文化语境中时更是如此。没有那一种理论是万能的、无需发展或不可超越的。因此,“本土化”是中国学人的合理诉求。
认知诗学的“本土化”也是此次北京“认知诗学高层论坛”的主题之一。什么是认知诗学的“本土化”呢?我们认为,有意义的“本土化”应该在以下三方面努力。
3.1 完善认知诗学学科理论
我们认为,认知诗学学科理论及方法论还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认识不统一;学科理论不完备;研究目的缺乏独特性和统一性;重方法借鉴,轻理论建构;研究方法不够完备,偏重于语言学。
“认识不统一”指以Stockwell和Tsur为代表的两种意见。我们倾向于Stockwell的观点,认为认知诗学是一种新的文学理论而不仅仅是一种分析方法,但它的确是以方法论创新为基础、以“认知”分析为特色的文学批评理论——不是一般的文学理论而是批评理论。
“学科理论不完备”指目前Stockwell的理论体系虽然号称是一种文学理论,但仅仅关注阅读即读者接受这一方面是不够的,它实际上还只是一种分析方法。
“研究目的缺乏独特性和一致性”实际上也是“学科理论不完备”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按照Tsur所说,认知诗学只是一种分析方法,它就与文体学尤其认知文体学等同了,其研究目的缺乏自己的独特性;而按照Stockwell所说是一种新的文学理论,但它的实际操作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囿于文体学范畴。虽然Stockwell等人论及了意识形态、情感、想像、美感等一般文学理论范畴,但并没有深入、充分地加以论述并结合到分析实践中去。比如“情感”。Stockwell(2002:171)认为,情感概念显然是文学与认知的交汇点;最近,认知诗学领域一直有很多人呼吁给予情感这一现象更多关注,在将来的认知诗学中,对情绪与情感的研究看来会是更受关注的焦点。不过,他(2002:172)认为情感问题不好分析,因此,不仅他没有提供分析例证,Oatley在《认知诗学实践》中写的那对应的一章也没有提供例证。这一缺陷表明:目前的认知诗学在研究目的方面缺乏一致性。
“研究方法不够完备,偏重于语言学”是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认知诗学在方法论上就无法与认知文体学区别开来,也无法完成其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所理应负载的任务。若要完备其方法,目前看有两方面需要加强,一是认知心理学方法,二是美学方法。Stockwell对此似乎有所考虑,所以他在自己2009年的新著中提出了Cognitive Aesthetics(认知美学)这一新的说法。
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认知诗学应该在学科理论上具有完整性、连续性,在研究对象上具有确定性,在方法论上具有独特性。中国学者从中国的文学研究(既包括外国文学研究也包括中国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实际出发,在继承传统和引进新学的基础上对认知诗学理论与方法做一些补充、完善的工作,不仅使之更为完备,而且使之更适合中国的文学研究,这应该是认知诗学本土化的着力点之一。
3.2 注入本土元素
“本土化”的第二个努力方向是在认知诗学理论与方法中注入本土元素。所谓“本土元素”,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国元素”,指那些为中国人所认同、代表着中国文化精神,体现了中国人所共同接受、认可、传承的价值观体系、审美理想、运思方式等各种文化符号和象征体系,包括历代学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至于哪些本土元素可以注入认知诗学,本人另有专文探讨,兹不赘述。
3.3 解决本土文学问题
这里的“本土文学问题”,有如下涵义:一是指本土文学理论乃至文学地位存在的问题或有待解决、有待深化或完善之处;二是指在本土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有待改进的地方。比如,针对文学批评实践中一些过于主观化、印象式的断言,认知诗学可以提供一个更为准确、客观的分析模式;针对市场经济语境下对文学功能的忽视,认知诗学可以从人类认知能力与文学功用的关系中展开新的探讨和论证,从而对偏见给予某种程度的矫正。
概言之,它应该能够对本土的文学研究——理论建设或批评实践——作出新的贡献。
4.效果与解释
无论是Tsur还是Stockwell,都认为认知诗学的根本目的是解释文学效果。关于“文学效果”,我们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已知的效果,比如,大家公认某一首诗的意象很独特,或是音乐性很强,那么认知诗学的任务就是对此作出更为客观、准确的解释。如William Black的London一诗,人们认为它具有一种打铁般铿锵的节奏(anvil rhythm),但这只是一种印象似的比喻性说法,这样的节奏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它又如何产生、如何界定?如何为读者所感知?这些在传统文学批评那里是难以解释清楚的,认知诗学则试图对这类问题作出系统、客观的解释,即前面提到的Tsur的主张:解释文学文本结构与效果之间的关系。这一种对效果的理解并不要求对文本读出新意。
第二种对效果的理解则包括读出新意,即发现新的效果。我们在这里可以较为宽泛地界定文学效果,它可以包括两种涵义,一种是意义,另一种是美学效果或艺术效果。这是我们对效果的理解。我们认为:认知诗学不仅要解释已有的效果,还应该能够发现新的效果。
不过,Tsur和Stockwell他们并不在乎读出新意,因为他们主要还是沿袭了文体学传统,注重文本的文体效果而不是文本的内涵意义。他们关注的主要是效果的解释而不是文本意义的解读。对此,Stockwell(2002:7)明确表示:“认知诗学的研究目的是对读者如何在当时如此理解文本做出合理的解释,从这点来看,认知诗学没有预测能力,而且,自身也不能产生解释。”这里的“自身也不能产生解释”蕴涵了“不能或无需读出新意”的结论。Stockwell还说:事实上,我们会抛开表面的阅读和不精确的直觉,而对文学文本中所发生的作精确而系统的分析。从这种方法论的角度而言,我们可能主要将兴趣放在文学阅读和非文学阅读之间的连续性和连接上,而不会对文学价值或地位作太多的讲述,仅仅提到有这么一回事而已。例如,我们会把文学批评中所主要关心的东西看作与我们无关,仅把它看作是共同兴趣领域中的同一学科的不同部分,这对我们最不重要,而且是不相容的对立面。(Stockwell,2002:5 - 6)
Steen和Gavins也有类似看法。他们很推崇结构主义诗学,认为:最近的一种成功的诗学是结构主义(诗学)。他们指出,结构主义在英语世界明确地以“结构主义诗学”名义崛起,其代表人物乔纳森·卡勒于1975年出版了《结构主义诗学》一书,引起了轰动。该书对长期来在文学界占主流地位的无论是形式批评还是道德批判,都提出了挑战。Steen和Gavins大段引用了该书前言中的话,因为这段话不仅表明了卡勒的主要观点,而且它显示了卡勒的观点与认知诗学的内在联系。
结构主义使人们看到的那种文学研究,其基本上不是一种阐释性的批评;它并不提供一种方法,一旦用于文学批评就能产生迄今未知的新意。与其说它是一种发现或派定意义的批评,毋宁说它是一种旨在确立产生意义的条件的诗学。它将新的注意力投向阅读活动,试图说明我们如何读出文本的意义,说明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究竟建立在哪些阐释过程的基础之上。恰如以某种语言说话的人吸收同化了一套复杂的语法,使之能将一串串的句子读作具有形式和意义的一首一首的诗或一部一部的小说。文学研究与具体作品的阅读和讨论不同,它应该致力于理解那些使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程式(conventions)。(Steen & Gavins,2003:5-6)
Steen和Gavins(2003:7)认为,卡勒这段话里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点是批评与诗学之间的差别。按照卡勒的观点,“诗学”指的是完整、系统的文学理论,它可以也可以不必应用于对具体文本进行解读的那种实际的文学批评。第二点是“产生意义的条件”这一问题。卡勒认为,阅读(reading)、解意(making sense)、阐释(interpretive operation)是文学研究的真正目的。第三点是语言处理和文本处理之间的区别和联系。20世纪60年代生成语法的成功引发了一场“乔姆斯基革命”,影响甚广,甚至文学也被看作是由意义程式所管辖的象征系统、符号系统,就像语言被语法规则和语用规则所支配一样。直到70年代,这种探索仍在继续。但是到了如今,认知心理学、话语心理学以及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使原来的许多未解之谜变得清晰多了。显然,70年代的研究在探索一般意义上的阅读过程和特定意义上的文学阅读过程这两方面,缺乏有意义的成果。而现在认知心理学、话语心理学以及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正在认知语言学和认知诗学领域得到利用,并促使“诗学的轮子转向”(Steen&Gavins,2003:8)。
从以上摘引和分析可以看出,目前的认知诗学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在研究对象上聚焦于阅读,更确切地说是读者的接受过程;二是研究的目的聚焦于效果解释,而不是“发现或派定意义”,不期望“产生迄今未知的新意”。换言之,它更关注的是“试图说明我们如何读出文本的意义”,是How(如何)而不是What(什么)。Stockwell(2009:13)最近也承认:认知诗学在解释文学阅读中的意义和信息监控方面特别成功,当它基于文体敏感性时尤其如此。它能够以某种原则性很强的方式解释文学阅读,说明意义的解读是如何为特定读者所获得的。
当然,当代文学理论流派纷呈,各有特色,各有侧重,相互间不宜评判高低。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一种特定的文学分析方法应该有特定的功效,它不仅能够对已有的效果作出自己的解释,“为把直觉阐释形成可表达意义的过程提供一种模式”,“提供相同的框架作为描述和解释阅读的一种方式”(Stockwell,2002:8),而且应该能够发现新的效果(包括新的意义)。
5.从解释到发现
认知诗学的根本任务或存在根据是什么?我们认为,首先是要实现“转型”或延展:从解释到发现。
Tsur和Stockwell等人都强调认知诗学的解释功能,这本身无可非议,关键在于解释什么?作出什么样的解释?我们认为,可以在两个不同方面来理解“解释”,一是解释文本,二是解释阅读,即,解释读者是如何解读特定文本的。按照第二种对“解释”的理解,重心当然不在解读文本本身,更无需读出新意。显然,Tsur和Stockwell等人持第二种观点,虽然他们没有断然地、明确地反对第一种观点。
我们的观点则不同。我们认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或者一种新的阅读理论,不仅应该能够解释阅读过程或阅读机制,解释特定文学效果,还应该解释出用别的分析方法不能解释出的文本涵义或美学涵义。独特的方法产生出独特的功效,这才是认知诗学的价值,也是它存在的根据和理由。否则,它既不是一种文学理论,甚至也不是一种具有独立品格的分析方法,而只不过是认知文体学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认知诗学有超出文体以及文体效果的研究对象,这是它作为一个独立学科与认知文体学的区别性特征;它也要在认知科学框架内对文学包括文学阅读、文学批评作出自己的解释和贡献,这是它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理论的质的规定性。
而要做到这些,认知诗学就要实现从“解释”到“发现”的转变。我们这里说的“发现”,有三方面的涵义,即:发现新的原因、发现新的涵义、发现新的美感。
所谓“发现新的原因”,即目前Tsur和Stockwell等人所做的那种工作,对人们业已感知的文学效果作出新的解释,或对读者的阅读作出新的解释。“发现新的涵义”则是要对文本读出新意,发现别的阅读方法未能读出的涵义。而“发现新的美感”则是对文学效果的进一步发掘,得到新的审美体验。
接下来的问题是:认知诗学能不能做到这三个“新发现”?我们认为,从理论上说是完全可能的。我们以Alfred,Lord Tennyson的The Eagle(《鹰》)一诗为例做一简要分析。原诗如下:
He clasps the crag with crooked hands;
Closed to the sun in lonely lands,
Ringed with the azure world,he stands.
The wrinkled sea beneath him crawls;
He watched from his mountain walls,
And like a thunderbolt he falls.
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只简要分析本诗的情感、想像和意义问题。
不难看出,诗人是欣赏鹰的,但是,诗人并没有在描述情感,更没有暴露情感,而是在表现情感。全诗除了一个明喻外再没有一个字眼直接表达甚或暗示了诗人的情感。他的情感需要我们自己去“认知”,去感觉和体味。诗人的情感和描述影响着读者,吸引着甚至控制着读者,我们的视线和注意力为诗人所牵引,我们的情绪随着诗人的笔触而起伏而兴奋,最终,我们会对鹰产生由衷的赞赏。
诗人是如何投射他的情感的呢?我们只能通过他留下的语言产品——这是他的情感证据——来加以推断。所以,我们的考察或推断从语言本身开始。
首先,诗人用于描述鹰的词语都没有否定性内涵(negative connotation)。其次,语言所描述的鹰的行为是肯定性的。第三,鹰的姿态、位置也是正面的,处于中心的,意喻着力量和崇高。认知诗学的图形—背景理论很适于这种分析,此处从略。第四,老态的大海成了它的陪衬,并且相形见绌,强化了鹰的正面形象,或者,用认知诗学的术语说,鹰作为“图形”(figure)得到了渲染和突出。第五,尤其不能忽略的一点是:他把鹰拟人化,诗人将自己与鹰化而为一,将全诗聚焦于鹰,有时还采用了鹰的视点,浓墨重彩描绘了鹰的力量、高傲、非凡。通过这些手段,诗人把他的肯定性情感投射到了鹰的身上。由于诗人的导引,我们读这首诗时产生的移情也必然是沃林格所称的肯定性移情。(沃林格,1987:5)
读者此时得出的鹰的形象是再造想像的产物。诗人利用想像创造出诗中的鹰的形象,而读者根据诗人的言语叙述和文字描述对鹰再次进行想像,形成相应的新形象。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创作还是欣赏都需要体验,需要某种内摹仿。内摹仿与移情是相辅相成的,犹如硬币的两面。比如,当鹰雷霆般俯冲而下时,我们可能会有某种畅快、自由、豪迈等感觉,这种内摹仿就是审美的摹仿。诗人调动自己的全部生活积累,通过想像进入艺术幻境,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象中去,从对象的角度感受、体味一切,与对象融为一体,力求准确地传达出对象的内在精神。而读者深刻地把握对象、理解对象,只有通过想像这条唯一的途径才能实现,因为我们事实上既不能进入诗中的世界,也不能进入诗人的世界。所以,科林伍德(1985:146)说:“真正艺术的作品不是看见的,也不是听到的,而是想像中的某种东西。”通过创造性想像,读者完成了概念的融合,产生了新的概念。
那么,诗人到底要借这只鹰表达什么理想呢?我们作为一般读者,不可能也未必非要去考证诗人的创作意图,所以此处我们撇开认知诗学所注重的语境分析以节省篇幅。我们只需推测。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个坐标,那就是诗人的基本态度和取向。很显然,诗人对鹰是肯定的,是赞美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确定诗人写鹰是另有所指的。这两点就构成了一个坐标,由此我们可以去填补诗留下的“空白”或“未定点”。根据这个坐标,我们认为,诗人是借鹰表达对力量、崇高、孤傲的赞美。当然,也可更升华一步,是对某种理想人格的向往与憧憬。人达不到鹰的那种境界,但可以想像,可以憧憬。诗人就这样获得了康德所说的心灵的自由。
从以上简要分析可以相信,认知诗学实现从“解释”到“发现”的延展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6.结语:多元与统一的辩证法
以上我们指出了认知诗学目前面临的一些困惑与分歧。我们同时认为,这些困惑与分歧都是一个尚未完全成熟的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难题。一些不同的观点虽然造成了人们理解、运用这门学科时的某些困惑与不便,但这也反过来说明它的多元性、多样性,这有利于它的丰富和拓展。不过,对认知诗学学科理论的一些统一认识也是必须的,比如它到底是一种文学理论抑或仅仅是一种分析方法?它的目的是解释效果和文本意义抑或仅仅是解释阅读和效果?这些问题关乎认知诗学的存在依据和发展前景,认知诗学的研究者对这些问题应有更深入的思考和探索。正如Steen和Gavins(2003:11、161)曾经指出的:认知诗学是一个新的、发展中的领域,正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它可能向若干不同的方向演化。所以,认知诗学的未来极大地依赖于新的探索。
在新的探索中,坚持多元与统一的辩证法是很有必要的。这里的“统一”,即是在学科理论上坚持认知科学的理论基础,研究对象上始终聚焦于文学(包括文本研究和理论研究),研究目的上追求新的发现,从而保持学科理论的完整性、连续性,研究对象的确定性,方法论的独特性。而所谓“多元”,一方面保持认知诗学理论与方法论方面的资源多样性特征,广泛吸收各种相关学科的成果;另一方面,对不同取向的不同“流派”持开放的态度,使研究形式、目的、方法、成果等更为丰富多彩,寓变化于整齐,如同美的事物一样符合多样统一的法则,它就会具有强大的内在生命。
[1]Gavins,Joanna& Gerard Steen.Cognitive Poetics in Practice[C].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
[2]Hobbs,Lerry R.Literature and Cognition[M].Stanford,CA: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1990.
[3]Stockwell,Peter.Cognitive Poetics:An introduct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
[4]Stockwell,Peter.Texture:A Cognitive Aesthetics of Reading[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9.
[5]Tsur,Reuven.What is Cognitive Poetics? [M].Tel Aviv:The Katz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ebrew Literature,1983.
[6]Tsur,Reuven.Toward a Theory of Cognitive Poetics[M].Amsterdam:Elsevier(North Holland)Science Publishers,1992.
[7]Tsur,Reuven.Lakoff’s Roads not Taken[J].Pragmatics and Cognition,2000(7):339-359.
[8]Tsur,Reuven.Deixis in Literature—What Isn’t Cognitive Poetics? [J].Pragmatics&Cognition,2008(1):123-154.
[9]Tsur,Reuven.Toward a Theory of Cognitive Poetics Second,expanded and updated edition[M].Brighton/Portland:Sussex Academic Press,2008.
[10]科林伍德.艺术原理[M].王至元,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1]沃林格·W.抽象与移情[M].王才勇,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责任编校:蒋勇军
Multiplicity and Unity: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Poetics
XIONG Mu-qing
Due to its brief development,cognitive poetics encounters some theoretical divergence and ambiguity,either at home or abroad.The divergence and ambiguity can be summarized as three problems:Is cognitive poetics a kind of literary theory or just an approach?Should it aim to make a new explanation of literary texts and their effects,or just that of the known effects?How to realize its localization?As a developing discipline,multiplicity is helpful for its prosperity and expansion.Unity,however,is also necessary for a discipline in its own right,which means sticking to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cognitive sciences,focusing on literature(literary texts and theory)as its targets,and aiming at new findings,so as to keep integrality and continuity of its theory and practice,specificity of its objects,and uniqueness of its methodology.Consequently,cognitive poetics can have great vitality as any beauty accords with the law of the unity in variety.
cognitive poetics;disciplinary theory;multiplicity;unity
H0-06
A
1674-6414(2011)01-0033-06
2010-11-23
熊沐清,男,四川外语学院教授,博士,四川外语学院外语教学改革与外语教育资源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叙事学、认知诗学和话语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