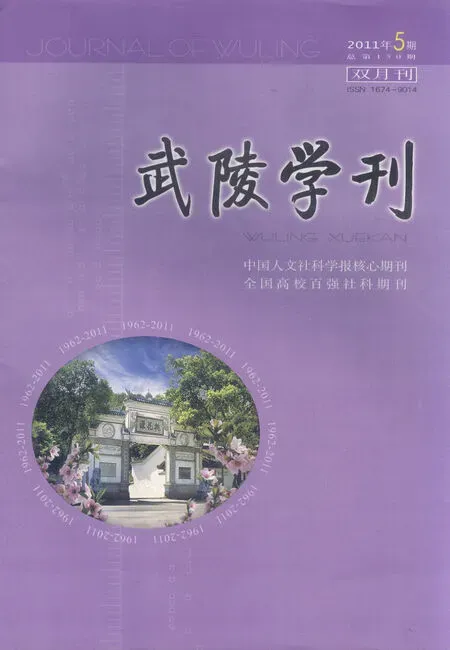话本研究的背景、问题与态势
2011-03-20向志柱
向志柱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3)
话本研究的背景、问题与态势
向志柱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3)
话本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还是比较薄弱的环节,这与话本研究本身的许多制约因素分不开:话本的命名受到了严峻挑战、宋元话本的存在也受到了质疑,动摇着研究的根基;话本研究资料散佚严重而杂乱;话本研究对研究者提出了较高的资质要求;话本研究有待进一步取得突破。话本研究应该是综合性和跨学科性研究。
话本研究;学科背景;问题;态势
话本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独具民族特色的重要文体样式,其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相对于中国古代其他文学文体来说,还是比较薄弱的环节,这是与话本本身的许多制约因素有关的。
一 话本研究背景的尴尬性
话本研究,离不开“话本”和“拟话本”这两个概念,但其概念命名,受到了严峻挑战。
最早提出话本理论的是鲁迅先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二篇《宋之话本》中认为:“说话之事,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而仍有底本以作凭依,是为‘话本’。”[1]112此后郑振铎、胡士莹等都承认“话本”是说话人的底本,鲁迅的理论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但是1965年日本学者增田涉发表《论“话本”的定义》一文,对鲁迅关于话本的定义提出了异议,列举了20个实例,反复论证“话本”一词除偶尔可作“故事的材料”解释外,其他只能作“故事”解。“‘话本’一词根本没有‘说话人的底本’的意思。”①此论对学界震动甚大,《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也表示:“‘话本’二字就是‘故事’的意思。迄今为止,在现存的话本中,并没有确凿证据可以表明它们是说话人或者说话艺术的‘底本’。”[2]
拟话本一词,最早见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三篇《宋元之拟话本》:“说话既盛行,则当时若干著作,自亦蒙话本之影响。”[1]119认为《青琐高议》、《青琐摭遗》、《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大宋宣和遗事》等四书就是当时蒙话本影响的“拟话本”。但是现在学术界通用的拟话本概念实际上是第二十一篇《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的“明之拟宋市人小说”概念:“宋人说话之影响于后来者,最大莫如讲史,……惟至明末,则宋市人小说之流复起,或存旧文,或出新制,顿又广行世间,但旧名湮昧,不复称市人小说也。”[1]197可见拟话本概念已经不是鲁迅的本义,而是经过了偷梁换柱的推衍。
正是这种话本概念的歧异,几乎每本话本小说研究著作、每篇博士论文在开始部分都必须进行一番大同小异的论证和陈述,徒费笔墨。现在许多学者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对话本概念进行了一些修正,如提出统称“话本小说”,取消拟话本概念,或者提出“准话本”、“文人话本”、“说书话本”、“市人小说”等概念②,但由于鲁迅先生的历史地位和话本概念影响的深远,这些提法的影响甚微,无法得到广泛认同。
宋元话本的存在也受到了学者的质疑。章培恒先生认为:“就现在所知的宋、元话本来说,哪些属于宋,哪些属于元,已经很难剖明。以前认为是宋代话本的,今天看来基本靠不住。”[3]现在几种重要的宋元话本和资料都已经受到质疑。
《清平山堂话本》收录和《宝文堂书目》所著录的小说,一般认为多为宋元话本,但是日本学者中里见敬进行了否定:“晁瑮《宝文堂书目》里著录的基本上都是以《六十家小说》为主的明代小说,所以宋代有话本或《六十家小说》是根据宋元原本重刻而成的说法,没有文献上的依据。”③又通过考证《宝文堂书目》与《六十家小说》的关系,进一步认为“《宝文堂书目》所录小说的主要部分是以清平山堂《六十家小说》为主的明代刊本。”[4]
《京本通俗小说》在出版当时得到了鲁迅、胡适、孙楷第等人的认可,认为“的是影元人写本”,但是后来被马幼垣、马泰来兄弟和胡万川、苏兴等充分证伪④,并得到学界公认。
《醉翁谈录》收录很多故事梗概,一直被认为是“话本”的一种。但是日本学者金文京先生认为:“《醉翁谈录》不是抄本而是刊本,尽管它原来是说话人的底本,但还是应该将它理解为以广大读者为对象的一种读物。”
《绿窗新话》的传本是抄本,周楞伽先生(即周夷)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的后记中,认为《绿窗新话》是“南宋说话人的重要参考书”,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前言中却改变了观点,认为《绿窗新话》“节引这许多故事情节,究竟作何用途?……既不是为说话人提供演述资料,那么编者的目的就是想印成书供人看了。”⑤
中里见敬在否定《清平山堂话本》的基础上类推,其余白话文的话本也是供人阅读的。“《全相平话五种》、《五代史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大唐三藏取经记》、《新编红白蜘蛛小说》等元刊本都是以刊本形态出版的,这意味着它们是读物而不是说话人的底本。”[5]
以上尽管是一家之言,但确有合理性的一面,这就给话本研究带来了复杂性和艰难性。现在话本研究没有大师级人物,缺乏对学科的整合力和凝聚力,不同的观点相互碰撞,动摇着话本研究的根基。
二 话本研究资料的散佚与杂生性
话本原本因遭禁而散佚。据《中国禁毁小说百话》可知,单话本资料等就有《剪灯新话》、《剪灯余话》、《艳异编》、《国色天香》、《情史》、《拍案惊奇》、《石点头》、《欢喜冤家》、《无声戏》、《十二楼》、《五色石》等十多种先后被禁毁[6]。而且选本流行也使原本失传。如“三言”刊行后不久,由于姑苏抱翁老人辑录的话本集《今古奇观》选录了“三言”、“二拍”中的大多数佳作,问世以后,风行不衰,“三言”很快便为《今古奇观》所代替,冯梦龙的“三言”的完整面貌便长期鲜为人知。明清易代的变故也使大多数话本散佚了。
回厂第二天就忙开了。老外们不过春节,专等春节一过,拿我们当纸篓,大批订单往里塞。抛光车间每天忙得团团转,日夜硝烟弥漫,车间像蒸馒头的大蒸笼,雾气腾腾地与我们周旋。我又抓管理又抓质量,抓得头昏脑胀。
现在许多珍贵的话本资料仅藏日本、韩国、法国等,发现和公布较晚,甚至鲜有研究。谭正璧、谭寻《古本稀见小说汇考》(1984年)所论古本稀见小说163种,也以国外佚本为主。如其所言:“传奇集如《剪灯新话》、《剪灯余话》、《效颦集》,传奇总集如《绿窗新话》、《风流十传》、《文苑楂桔》,传奇杂俎集如《醉翁谈录》、《万锦情林》、《燕居笔记》等等,都在中国早已失传,而仅日本藏有最早的精刊版本。”[7]《清平山堂话本》现存29篇(包括残本),其中15篇为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型世言》在国内也久已亡佚,今藏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直到1987年左右才发现,1990年才出版影印本和点校本;《醉翁谈录》二十卷本,此书在我国久已不见著录,日本观澜阁藏旧刻孤本,1941年才影印出版;被冯梦龙在《古今谭概》和《情史类略》中摘引了20多条故事的《耳谈》一书,1977年才由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在“秘籍丛编”中公诸于世。由于这些资料湮没和晚出,限制了话本研究的发展。后来许多学者四处访书,撰成书目,如董康《书舶庸谈》,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王古鲁《稗海一勺录》,郑振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1927年),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谭正璧《日本所藏中国佚本小说述考》等的出版,才给今天的话本研究带来了很多便利。
留存的话本资料少而杂乱。最重要的话本研究资料如《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关于话本只占很小篇幅(1981年中国商业出版社把这4种作“烹调丛书”出版),而且仅有的记载也因作者的文字功力或者历史语境的缺失而语焉不详甚至颠三倒四。如宋代“说话四家”就成了一段公案,以致近代以来,对说话四家的分法作过深入探讨的学者就有王国维、鲁迅、孙楷第、谭正璧、赵景深、陈汝衡、李啸仓、严敦易、王古鲁、胡士莹以及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等,所列家数不下十来种之多⑥。
话本研究资料具有伴生性。戏曲与小说往往是糅杂在一起的。例如关于话本的重要体制入话形式,一般认为与静候观众入场和收费有关。如果清楚做场和收费形式,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是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记载。而现在小说、戏曲里面见到的几则资料却有抵牾之处:其一,《水浒全传》第51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在郓城县勾栏做场的白秀英中途收费,随多随少不定。其二,《南宋志传》第十四回大雪小雪在南京御勾栏唱罢,下台遍问众人索“缠头钱”。其三,《事林广记》癸集卷一三《花判公案》:“建安留守判道士归俗”条云道士“见宋月英唧溜而伎能又高,遂多与索子之金”。此处“索子之金”是门票还是赏钱不清楚。其四,《醒世恒言》第三十八卷《李道人独步云门》:东岳庙前一个瞎老儿在路边唱道情,“待掠钱足了方才又说”,到了半本,又要收钱。并且还明确言明:“待掠钱足了方才又说,此乃是说平话的常规。”其五,杜仁杰的【般涉调】[耍孩儿 庄家不识构阑]:“见一个人手撑着椽做的门……要了二百钱放过咱”,采取门票方式。所以有许多论文往往执一端,或言门票方式,或言中途讨赏,或者就将二者结合,认为存在两种方式。但是由于这几则材料时代不一,却往往用来证明宋代勾栏的演出情况,似有不妥;又因为戏曲和小说的文学虚构性,其可信度更要打折扣。
另外,即使笔记、方志资料也应该考辨。《东坡志林》卷一《涂巷小儿听说三国语》条:“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因其所蕴涵的说书水平、说书地点、说书酬劳、说书效果以及三国故事的成书等丰富信息而被广泛引用,但已经受到学者的置疑:“这条所言的情状不可能出于苏东坡的时代,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和尊刘反曹的戏剧大量流传开来的明代情况则甚为相近。……五卷本《东坡志林》本不尽可信,则此条亦当为后人所造。”[8]这就提醒话本研究使用资料时应该综合判断,不能各取所需。
除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之外,笔者没有发现专门的话本研究资料汇编,更没有话本研究论文的汇编,甚至关于20世纪总的话本研究的综述论文也只发现1篇⑦。话本的基本文献零碎和杂乱,许多资料不易找到和没有出版,而且话本研究在现代技术的使用上也很落后,相关文献也不能上网进行检索和查找。
三 话本研究资质的制约性
话本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鲁迅、郑振铎、孙楷第、赵景深、谭正璧、叶德辉、胡士莹等研究名家,后来也出现了缪咏禾、陆树仑、程毅中、章培恒、张兵、欧阳代发等学者,然而现在看来,后继乏人。绝大多数的话本研究者只是匆匆过客。我曾对我国大陆1950年到2004年的800多篇论文进行过详细统计,第一作者多达522人,但发表2篇以上的只有118人,304人仅发过1篇论文。1994年以来,约有60多人选择了话本研究作为硕士或者博士论文,但是往往学位到手即改行事它,甚至有些学位获得者没有发表过一篇与话本相关的专业论文。话本研究队伍确实堪忧。
雪上加霜的是,话本研究又特别要求研究者具有广博的文化视野和完备的知识储藏。据《醉翁谈录·小说开辟》“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辨草木山川之物类,分州军县镇之程途”而知,宋说话艺人的知识谱系跨越了文学、史学、生地等。而我们今天的专家之学却将已经很小的中国古代文学这棵大树再按照朝代和文体将研究范围日益分割与局域化,搞唐诗研究的一般不再搞宋词研究,搞诗词研究的一般不再搞小说研究。而小说也具体细分为传奇、话本、《红楼梦》、“三国”和“水浒”等,真的各有“家数”,各有“门庭”。我们研究的是树枝和叶子,而不是整棵生机勃勃的大树。关于宋元话本的区分,胡士莹先生提出了八条推勘方法:“1、依据话本的体裁、语言风格;2、话本中叙述的社会语言风俗习惯;3、话本中反映的社会思想意识;4、以同一内容的话本互相比勘;5、考察地理、官职及典章制度;6、从官吏、杂史、笔记及诗文集等互相参证;7、依据宋戏文、杂剧、金院本,证明话本中的故事,以当时的表演情形和话本所反映的时代背景来探讨其成篇时代;8、参考现代人研究所积累的见解。”[9]就牵涉到舆地、政制、官制、风俗、语言等,运用到版本目录学、文献学、语言学、社会学等方法,需要研究者深厚的治学功力。章培恒先生在《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文中即历举地理志、选举志、兵制、职官制等史书、方志等材料,充分体现了话本研究者的广博见识⑧。
话本研究还有愈进愈难之势。话本往往内容短小而故事种类繁多,单是“三言”、“二拍”199篇(去重1篇),入话和正话故事就约有400个,《情史》有870多则,《艳异编》有361篇,《艳异续编》有163篇。而且话本一般有本事来源,那么,故事数量就要成倍增加。仅谈“三言二拍”的本事来源及影响,谭正璧辑引书目就达367种,其中包含二十四史、《太平广记》、《夷坚志》等皇皇巨著。不假以时日,很难产生经典性成果。话本研究容易出现投入与产出不平衡的现象。在学风比较浮躁的今天,研究者需要比其他文学研究者有更多坐冷板凳的精神和心态。
四 话本研究的局限与突破
话本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优秀且堪称经典的成果。如鲁迅先生的话本理论的开创,郑振铎、孙楷第、赵景深、谭正璧、叶德辉等人的本事来源考证,胡士莹先生的话本通论,缪咏禾、陆树仑的冯梦龙和三言研究,陈汝衡先生的说书史研究,程毅中先生的宋元话本研究,陈桂声的话本叙录,以及张兵、欧阳代发等先生的话本小说史研究等。
但笔者据全国报刊目录索引和中国期刊网统计,1950年至今,发表的话本研究论文大约是1 100多篇,相关研究专著约有30部。如果用陈大康先生的标准来看:“古代小说研究可大致分三个层次:钩稽考辨作者生平、成书年代、本事源流及版本嬗变等;分析作家作品艺术上成败得失及思想倾向;宏观考察各创作流派乃至整个小说发展历程、特点与规律以及种种文学现象”[10],现在话本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第一、二层次上。它们局限于“三言”、“二拍”、《十二楼》、《无声戏》等名著和冯梦龙、凌濛初、李渔等少数作家,造成了畸形繁荣,其中“三言”和冯梦龙的研究论文就占一半左右。话本的早期研究,“基本上停留在作品的整理和出版;小说本事的来源及流变;话本艺术体制特点的介绍;话本及与此相关的名词诠释;作者和版本的考订等方面”[11]。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论文则将话本与当时的社会现实联系和进行文化解释,或者采用西方的叙事学原理,大谈结构叙事视角和叙事特点等,对特别具有民族特色和个性的话本,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而且对话本缺乏一个分期的历史意识。现在许多论文谈话本的叙事特征和美学特点,往往以“三言”、“二拍”为依据,这是不科学的。宋元话本和明清话本具有不同的艺术特色,不能因为“三言”代表了话本的最高水平而以之为圭臬,正如古典小说的最高峰《红楼梦》不能代表中国古代小说的传统一样。
话本的评价和阐述应该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语境。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就犯过类似的错误。在《论“三言”的叙事模式》(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的最后一章对话本套语作评价时,就认为:“这种缺乏文学创造力的描写,更是说明‘三言’写作的商业目的。而这种写作又是仿话本小说而来。据此我们可以对套语做出比较全面合理评价。由于听众、场景的变换,这种套语可能在另一听众、场景那里并非套语;由于韵语的特殊讲述方式,同样的内容在不同的说书艺人那里有不同样的舌辩风采。而对强调现场效果的听众来说,通过对同一套语宣讲的效果比较,更能体味到不同说书艺人的说书技艺,从而选择所喜欢的说话艺人。但是,一旦离开这种说书环境,有声音的套语走上案头,便成了纸上苍白的陈词烂调,因此此类套语便不折不扣地成了艺术缺陷。艺术的生命是创新!”如果针对宋元话本,直到现在看,应该没有问题甚至还有自己的个人见解,但是“三言”已经失去了说书环境,只能作为案头文学看待,那么这种评价就有点不切题了。而学界还是一直在犯类似的错误。
话本的研究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如“瓦子”的释义和性质问题,就是一个较好的例子。瓦舍又叫瓦子、瓦市、瓦肆,简称瓦,但是其名何来,往往众说不一。大致有四种,其一是字义角度,认为从“瓦”字有“瓦解”义而得名。耐得翁《都城纪胜》之《瓦舍众伎》认为:“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梦粱录》沿袭之也认为:“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或者指瓦房。周贻白认为瓦舍“实则指为旷场,或原有瓦舍而被夷为平地”[12]。谢涌涛说瓦舍“是简易瓦房的意思,其含义即指百戏杂陈、百行云集的娱乐兼商贸市场”[13]。其二是语言学角度,认为“瓦子”源于唐代的“互市”。如丁伋认为,瓦字由牙(互)字讹变而来,“这个瓦字可以指肆舍的鳞次栉比,也可以指群众纷至沓来,它的意义仍是和互市联系着的”[14]。其三是演艺角度,吴晟认为,瓦是“八音”中“土”的别称。瓦舍之瓦的本意当作土类乐器或俗乐解比较合理[15]。 “瓦舍”即通俗音乐(以俗乐为主也包括雅乐)流行的文化娱乐市场。其四是佛教用语角度。康保成认为,“勾栏”是佛教所谓夜摩天上的娱乐场所,被借为演出场所。“瓦舍”、“勾栏”,从名称到内涵都反映出佛教对我国戏剧文化的巨大影响[16]。如此等等,体现出话本研究的综合性和广博性。
话本的研究应该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因为话本的起源与发展的复杂性,主要就牵涉到:社会学(社会思潮)与话本的创作与出版、城市研究与勾栏瓦舍的繁荣及娱乐业的发达、军事学(主要是禁军制度)与瓦舍的创立、民俗学与民间说唱文学、典章制度与话本具有的民间文学和书面文学的特点、赋税制度与说书艺人的生活状况、版本学和校勘学与话本小说的伪佚等,只有多学科的融合,才能更加深入地研究话本。
如果结合话本文体的自身特点和逻辑起点,我们必须正确把握作为说书场的文学与作为案头的文学、作为综合艺术的说书与作为文学艺术的文学、独创性的文学与程式化的文学、经典作品研究与流行作品研究的区分与研究。话本的最大特征应该是说话技艺与文学艺术的结合。话本留下的不是文化遗产,而是作为文学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话本研究期待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其一,文献的。资料性的话本研究资料(论文)汇编、话本研究参考资料(古籍论著)等。其二,理论的。话本学科的命名问题;话本文体化;话本独特体制的演变等;文学文体的变革与生长(如词是音乐与文学的结合,话本小说是说话技艺与文学的结合,拟剧本是剧本的案头化,网络文学是电脑技术与文学的结合)等。其三,方法的。借鉴史诗研究和口头文学研究的成果;话本的生成;话本的生态环境;说话技艺与话本的关系;口传性民间叙事研究等。
注释:
①原文发表在日本《人文研究》十六卷第五期,汉语译文(译者为前田一惠)刊载于1981年台北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第三集,《古典文学知识》1988年第2期摘要转载。
②参见周兆新《“话本”释义》(《国学研究》第2卷,1994年)、张兵《“准话本”刍议》(《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傅承洲《文人话本与艺人话本》(《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等文章。
③分别参见中里见敬《关于清平山堂〈六十家小说〉——〈宝文堂书目〉所录话本小说新探》、《从清平山堂〈六十家小说〉版面特征探讨话本小说及白话文的渊源》(原载《山形大学纪要(人文科学)》1995年第13卷第2号,又见中里见敬《中国小说物语论的研究》第七章,汲古书院1996年版)。
④参见马幼垣、马泰来《京本通俗小说各篇的年代及其真伪问题》(《清华学报》1965年新5卷第1期)、胡万川《京本通俗小说的新发现》(《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10卷第10期,台北1977年版)和苏兴《〈京本通俗小说〉辨疑》(《文物》1978年第3期)等。
⑤但是日本学者大塚秀高认为此说纯属谬论,因为作者皇都风月主人为南宋人是不变的,《醉翁谈录》有元人的诗是众所周知的,而从《绿窗新话》中的避讳可见是南宋抄本或是南宋抄本的过录本。具体详见大塚秀高著、柯凌旭译《从〈绿窗新话〉看宋代小说话本的特征——以“遇”为中心》(《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3期)一文。
⑥参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严敦易《水浒传的演变》(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70页)、孙楷第《沧州集·南宋说话人的家数问题》(中华书局1956年版)、陈汝衡《说书史话》(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和《宋代说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李啸仓《宋元技艺杂考》(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王古鲁《二刻拍案惊奇》附录《南宋说话家数的分法》、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4章(中华书局1980年版)、程毅中《宋元话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皮述民《宋人“说话”分类的商榷》(《北方论丛》1987第1期)、张兵《话本的定义及其他》(《贵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刘兴汉《南宋说话四家的再探讨》(《文学遗产》1996年第6期)、张毅《关于宋人“说话”的几个问题》(《南开学报》2000年第3期)、李亦辉《宋人“说话”四家数管窥》(《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等专著和论文。
⑦参见张兵《新时期话本小说的回顾与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⑧参见章培恒《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上海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刘世德,主编.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修订本)[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185.
[3]章培恒.中国文学史: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35.
[4][日]中里见敬.反思《宝文堂书目》所录的话本小说与清平山堂《六十家小说》之关系[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28.
[5][日]中里见敬.从清平山堂《六十家小说》版面特征探讨话本小说及白话文的渊源[J].山形大学纪要(人文科学),1995,13(2).
[6]李梦生.中国禁毁小说百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7]谭正璧,谭寻.古本稀见小说汇考[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4.
[8]章培恒,徐艳.关于五卷本《东坡志林》的真伪问题——兼谈十二卷本《东坡先生志林》的可信性[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4):163-173.
[9]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196.
[10]陈大康.关于《西游记》的两次论争[N].文汇报,2004-02-29.
[11]张兵.新时期话本小说的回顾与思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4).
[12]周贻白.中国戏曲史发展纲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72.
[13]谢涌涛.瓦市勾栏是南宋庙会习俗的延伸[M]// 浙江省艺术研究所,编.艺术研究论丛.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301.
[14]丁伋.“瓦子”解与“行院”解[J].艺术研究,1985(2).
[15]吴晟.瓦舍文化与宋元戏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7-43.
[16]康保成.“瓦舍”、“勾栏”新解[J].文学遗产,1999(5):38-45.
(责任编辑:田 皓)
I207.41
A
1674-9014(2011)05-0083-05
2011-07-1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稗家粹编》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11BZW077)。
向志柱(1970-),男,湖南绥宁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古代小说及其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