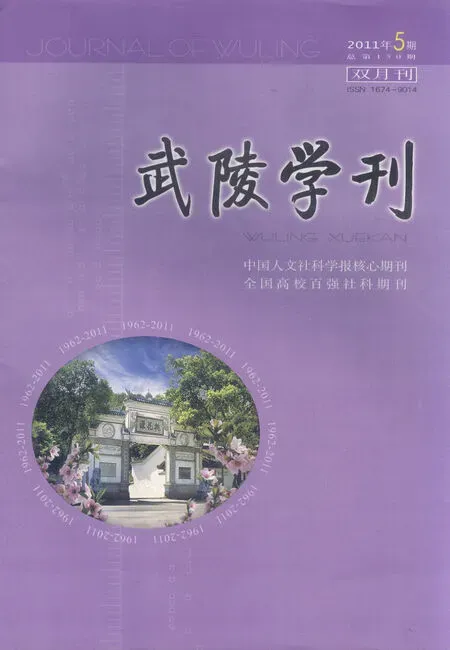傅斯年史学本体论思想探析
2011-03-20程鹏宇
程鹏宇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9)
傅斯年史学本体论思想探析
程鹏宇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9)
傅斯年是近代著名历史学家,他在史学本体论上有比较独特的认识,其史学本体论思想大致涉及史学对象论、史学目的论和史学工具论三个部分,概括起来是:历史学是一门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史料,进而求得真实的历史事实的学科。但傅斯年的史学本体论本身并不十分体系化,所遗留的问题仍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
傅斯年;史学理论;史学本体论
对于“什么是历史学”的回答一般被称为“史学本体论”。“本体论”一词是从哲学里借用过来的,本来指哲学中“关于‘是’的一般理论”[1],史学理论中借过来,造成“史学本体论”一词,指关于历史学的本原或本性的认识。需要指出的是,“史学本体论”与“历史本体论”两个概念是不同的,“历史本体论”回答的是“历史是什么”的问题,这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属于历史哲学的范畴。我国史学理论界曾经存在着以历史哲学(主要是唯物史观)代替史学理论的做法,从而造成在第一问题上的混乱 。在当今的史学界,史学理论问题逐渐被历史学家们所重视,史学理论的研究也从对史学方法论的探讨逐步深入到了史学本体论——即史学理论的第一问题——的探讨,如庞卓恒 、李振宏等学者都对史学本体论进行过独到的论述,但最为系统地论述史学本体论的当属赵兴彬先生的《史学本体论》一文,在这篇文章里,赵先生比较系统地解决了史学本体论的定义、史学本体论与历史本体论的关系、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的关系等史学理论中最急需解决的问题[2]。近代历史学家傅斯年先生对于史学本体论有所建树,他关于史学本体论的论述对于深化今天史学本体论的探讨不无启示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他的史学本体论——史学理论中最基础的部分,即对“历史学是什么”的回答——进行研究。在傅斯年的史学理论中,“历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又可以大致分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历史学的研究目的是什么”以及“历史学的研究工具是什么”三个问题。
一 傅斯年的史学对象论
关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的问题,一般有两种看法,即历史说和史料说。当今史学界,大多数学者尤其是老一辈学者一般持历史说,如何兆武先生说:“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文世界的历史,所以历史学家所追求的不应该仅仅是考订史实,而且还须解答史实背后的人文动机。故而它不能停留在物质史的表层上,还需深入到人文精神的深处。”[3]宁可先生也说:“以历史(过去的、本来的、客观存在的历史)为认识对象(经过中介)所形成的一门学问,叫史学或历史学、历史科学,即一种知识体系。”[4]9虽然何兆武先生与宁可先生的认识稍有不同,但都是主张史学对象论的历史说。当然也有持史料说的学者,如河北大学雷戈先生便是当今史学界史料说的代表人物。
傅斯年的史学对象论非常明确,即史料说。研究傅斯年,我们不得不提到这个命题——“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个命题最先出自《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原文是:“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5]3由于这段话太长,我们可以简称之为“傅氏命题”。在这里,我们很明确地看到,“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一句实际上就是傅斯年的史学对象论,即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史料。在《史学方法导论》中他更明确地提出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6]308在《考古学的新方法》中也提到:“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5]88可见,傅斯年认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客观的、实在的史料,而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或者其他的东西。
正因为把史料看成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傅斯年才十分强调史料的意义,他把史料看成一切史学研究的立足点,声称:“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5]10把史料当成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就必然要遵守史料的不可创造性,史料的不可创造性对历史学的研究范围进行了天然规划,因此,傅斯年说:“我们应该于史料赋给者之外,一点不多说,史料赋给者以内,一点不少说。”[6]51又说:“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5]10可见,他把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严格地限制在其研究对象所规定的范围内。
傅斯年十分欣赏西洋学者重视史料的治学方法:“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5]6从而认为:“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5]6史料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研究的前提条件是史料的占有,所以傅斯年认为:“史料集中,始可与之言研究。”[7]62如果没有史料,那历史学便失去了研究的对象,没有研究对象自然就不能成为一个学科了。因此,傅斯年才主张扩大史料的范围:“能利用各地各时的直接材料,大如地方志书,小如私人的日记,远如石器时代的发掘,近如某个洋行的贸易册,去把史事无论巨者或细者,单者或综合者,条理出来,是科学的本事。”[5]5主张通过扩大学科的研究对象来发展学科自身。
一门科学成立的前提是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但是,很长时间里,人们都没有在史学领域里重视这个问题,傅斯年的这一论述,对历史学家来说应该是一个警钟。一些学者以“史学只是史料学”为理由认定傅斯年的史学理论是片面的,认为把“历史学”看成“史料学”是不够的,如徐晓旭、朱丹彤认为:“可以说‘史学便是史料学’是傅斯年在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影响下对史学的一种武断的阉割,它必然造成史学某些社会功能的丧失,无助于人们正确地认识历史、正视现实和预知未来。”[8]当然也有一些史家注意到傅斯年这一思想的深刻含义,如李泉认为:“有人从‘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个简短的结论着眼,说傅斯年把史学和史料学完全等同了起来,这是一种误解和错觉。如果我们不是望文生义或仅仅局限于这个口号的本身,而是比较客观、全面地考察、分析其史学思想和治史实践的话,就不难发现,傅斯年这个口号中的‘史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学,而是狭义的史学:不包括历史哲学、历史评论,也不包括史书的写作,而是专指史事研究。”[9]这种观点虽然不像前一种观点武断,但仍然把“傅斯年这个口号中的‘史学’”和“一般意义上的史学”对立起来,这恐怕还没有理解到傅斯年的本意,如果我们把“史学只是史料学”与“史学的对象是史料”这两个命题结合起来理解的话,就不难看出“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本意是为了指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而近代学科的名称往往是以其研究对象来命名的,如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地质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如果按照这个规律来命名“历史学”的话,那“历史学”也就只能叫“史料学”了。事实上,在傅斯年的史学理论中,并不存在两个不同的概念—— “历史学”与“史料学”,那种认为傅斯年“把史料学与历史学混而为一,甚至以史料学代替历史学”[10]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二 傅斯年的史学目的论
一门学科的成立,除了要有客观的研究对象之外,还要有其明确的研究目的。达到了这个既定的目的,就意味着研究过程的结束。历史学的研究目的就是历史学家从事历史学研究工作所希望达到的某种结果。另外,我们应该明确一个事实,即历史学的目的与历史学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很多人经常把历史学的目的与历史学的功能混为一谈,或以目的代替功能,或以功能代替目的,都不能形成对历史学的正确认识。关于学问的目的与功能的区别,顾颉刚先生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11]功能与目的的价值标准是不一样的,而且目的是在研究之前所考虑的,而功能是在研究结束后考虑的。
傅斯年认为历史学的研究目的是发现真实的历史事实。过去一些学者认为傅斯年只是为整理史料而整理史料,却没有看到他整理史料的目的。如苟兴朝认为:“他(傅斯年——笔者注)又认为史家的任务就是整理史料。”[12]但我们可以看傅斯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中的一段话:“此项旨趣,约而言之,即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如是伸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7]9可见,傅斯年认为“问题之解决”才是历史学的目的,历史学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那么,史料与工具都不是历史学的研究目的,整理史料只是研究过程,不是终极目的。什么是问题呢?笔者认为当是史料中未解之处、史料中相互矛盾之处或前人认识错误之处等,例如傅斯年评论王国维的成绩时就说:“王君拿直接的史料,用细密的综合,得了下列的几个大结果。一、证明《史记》袭《世本》说之不虚构;二、改正了《史记》中所有由于传写而生的小错误;三、于间接材料之矛盾中(《汉书》与《史记》),取决了是非。这是史学上再重要不过的事。至于附带的发现也多。”[6]312由此可以推断出傅斯年所理解的历史学的研究目的。而所谓“问题之解决”,当是发现真实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分析傅斯年的大部分史学著作,无一不把发现真实的历史事实作为历史学研究的目的。
傅斯年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多次谈到了历史学的研究目的。
其一,在理论层面强调历史学的研究目的。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傅斯年说:“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5]9-10过去我们在理解这段话的时候过多地注意“整理史料”这一处,却忽视了“事实自然显明”的结果。但由此可见,整理史料只是历史学的工作,而非其目的,目的是为了使事实明显,即得到真实的历史事实;在《史学方法导论》中他也说:“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或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6]308傅斯年认为整理史料的唯一方法就是史料比较法,他说:“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6]308通过比较史料可以得到最为真实的历史事实;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傅斯年说得更明白:“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5]335“就史料以探史实”七个字可以说是傅斯年对历史学过程的一个简要描述,史料是其研究对象,而研究目的则是发现历史事实。
其二,在实践层面强调历史学的研究目的。傅斯年在《姜原》一文开头说道:“民族的观念,他们没有,但我们颇可因他们神话世系的记载寻出些古代的民族同异的事实来。”[5]46这就是讲历史学家通过研究史料寻求真实的历史事实。在《东北史纲》 中,傅斯年也说道:“吾等明知东北史事所关系于现局者远不逮经济政治之什一,然吾等皆仅有兴会于史学之人,亦但求尽其所能而已。”[6]374在民族危难之际,傅斯年认为历史学能做的就是找出历史事实,进而驳斥日本帝国主义炮制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论。在《夷夏东西说》文末,傅斯年也提到:“认识此四地在中国古代史上的意义,或者是一件可以帮助了解中国古代史‘全形’的事。”[5]232所谓“中国古代史‘全形’”,即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整体面貌,这也是主张通过史料认识历史事实。
以上的几则史料可以证明,傅斯年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把发现真实的历史事实作为历史学的研究目的,他之所以反对“史观”或“历史哲学”,是因为所谓的“史观”或“历史哲学”不是真实的历史事实,而只是人们的主观构建,如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5]12又在《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中说:“因人类接触,发生世界史要求,以解决新问题,同时一般哲学家以为历史无非事实之记录,事实之演变,必有某种动力驱之使然,如能寻着此种动力之所在,则复杂之历史,不难明其究竟,因是而有史观之发生。所谓史观,即历史动力之观察,观点不同推论即异。”[5]156可见傅斯年认为“史观”或“历史哲学”是哲学家们的一种思想,而不是历史学家们所研究的目的,历史学家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发现真实的历史事实,与哲学家发现驱使历史发展的“某种动力”的目的是不同的。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傅斯年绝不是一个以整理史料为目的的历史学家,而是一个以发现真实的历史事实为目的的历史学家。我们可以仔细研究他的史学作品,无一不是“就史料以探史实”的典范,“就史料以探史实”这七个字既包含了傅斯年的史学对象论,又包含了他的史学目的论。
三 傅斯年的史学工具论
任何学科都有其研究所凭借的工具,历史学也不例外。史学工具论不同于史学方法论,史学工具论是对历史学家从研究对象到研究目的之间过渡的一种凭借的界定,史学方法论是与史学本体论平行的、研究历史学具体运行过程的理论。如对于傅斯年来讲,史学工具论就是“就史料以探史实”之所以能够成立的可能性。史料观在史学对象论和史学工具论之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如果不把史料看作对象的,就会将之视为工具。上文说到,傅斯年认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史料,因此,他认为历史学的工具就是整理史料的凭借。傅斯年早期思想中就有对学术研究工具的论述。在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中,傅斯年发表《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谬误》,其中就谈到:“凡治学术,必有用以为学之器。学之得失,惟器之良劣足赖。”[13]认为研究工具的优劣是学术进步与否的关键。192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他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
在“傅氏命题”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傅斯年对历史学研究工具的认识,即“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这里所讲的“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容易被理解为物质的工具,这是不完整的,这里的工具除了物质的工具外还包括方法的工具,甚至主要是方法的工具,因为凡是一种物质的工具都是某种方法的体现,如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5]7可见他认为方法就是工具,因此,我们可以说傅斯年认为历史学的研究工具是科学的方法。因此,傅斯年又被称为“科学史学派” 的代表人物。尤其是在新兴的考古学中,科学方法的运用更是显得必不可少,傅斯年说:“没有科学资助的人一铲子下去,损坏了无数古事物,且正不知掘准了没有,如果先有几种必要科学的训练,可以一层一层的自然发现,不特得宝,并且得知当年入土之踪迹,这每每比所得物更是重大的智识。”[5]7-8进而认为:“古史学在现在之需用测量本领及地质气象常识,并不少于航海家。中国史学者先没有这些工具,那能使得史学进步?”[5]8可见,傅斯年认为科学的方法是历史学能够进步的必要条件。
傅斯年十分强调工具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认为:“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5]7将工具作为衡量一个学科是否进步的标准,这在学术史上还是很少见的,而他对“工具”即“方法”本身的论述也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他认为:“所谓方法,无所谓新旧。所谓新方法,不是在好高,不是在务远。假定这个方法,用来可以得到新的知识,就是好的方法。若是用来得不到新知识,即不可靠,就不算是好的方法,也就不是新的方法。”[5]88工具的价值以是否能得到更多的知识为标准,并不是庸俗地追求新出现的方法,也就是说,早出现的方法如果依旧有生命力,依然能够得到更多的知识,那便不应该将之抛弃,这样,对传统学术方法便可以采取一种较为实际的态度,而不是对传统进行彻底否定,而对于新出现的方法,也不至于迷信之,一味求新而忽略学术研究的本身需求。
经济生产的发展,靠的是生产工具的革新。类似的,学术的发展,也离不开工具的革新。近代史学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于研究工具的进步,以近代科学的方法去做古老的历史学,是傅斯年的学术风格,正如他本人所言:“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故如以历史语言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今者决意设置,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7]9为了达到“发达近代科学”的目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三条宗旨之一就是“扩张研究的工具”[5]9,试图从工具革新的角度促进历史学的发展。
四 傅斯年史学本体论的学术意义及反思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傅斯年的史学对象论是以史料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史学目的论是以发现真实的历史事实为历史学的研究目的,史学工具论是以科学方法为历史学的研究工具。将其综合起来就得出了傅斯年的史学本体论:历史学是一门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史料,进而求得真实的历史事实的学科。通过对傅斯年的史学本体论的探究,我们可以明确一点:“史料派”代表人物傅斯年并非只是为整理史料而整理史料,也并非不讲理论。
学术界在讨论傅斯年的史学思想时,往往会提到其学术渊源,苏全有、郑伟斌的《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一文,总结了近年来傅斯年史学思想研究的一些成果和不足,其中第一点就是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来源问题。可以看出,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来源不外乎中西两方——虽然在具体问题上,学者们有所争论,但在这一点上基本上是达成了共识。但是,具体到傅斯年的史学本体论上,我们很难看出他是承袭了谁的观点——司马光、钱大昕固然不可能,软克、莫母森也没有直接的证据——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傅斯年总结了中西史学史的发展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他对历史学的理解,从另一方面讲,这又是他对新的历史学的一种畅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傅斯年只活了54岁,这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讲的确是英年早逝,因此,他没有系统地把自己的史学思想通过专著表述出来 ,致使今天史学界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研究,甚至有一点“猜谜”的感觉,说“傅斯年史学思想的逻辑结构至今仍不是十分明晰”[14],的确是非常有道理的。就傅斯年史学本体论来说,还有一些遗留问题需要我们当代学者继续予以关注和反思。其一,是否存在客观的历史学?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后,科学主义在中国思想界取得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几乎可以说“科学和理性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无论什么样的知识、观念、制度和行为,只有贴上科学的标签才是有权威和可以被接受的”[15],历史学也不例外。傅斯年便是典型的科学主义史学的代表,然而,他似乎又对历史学的“客观性”产生怀疑,如他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说:“史学可为绝对客观者乎?此问题今姑不置答,然史料中可得之客观知识多矣。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此命名之意也。”[5]335傅斯年“不置答”的原因是什么?是否是他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困惑在哪里?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个“傅斯年难题”?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其二,历史学的“两个层次”的问题。傅斯年史学思想中被后世误解最多的就是他的“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个命题,该命题被一般人认为是他把历史学的范围缩小了,变成了史料学。虽然这个误解在本文中已经澄清,同时我们可以这样说,史料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史料学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历史学,狭义的史料学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史料学。但是,随之而来的还是有很多问题,如我们如何处理两种史料学的关系?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吗?如果后者是前者的基础,那么基础之外是什么?甚至我们要怀疑,在历史学中,是否真实地存在所谓的“两个层次”?如果存在,那么为什么是两个层次而不是三个或四个抑或更多?如果存在“两个层次”,它们之间的“界线”是如何存在的?这个“界线”的存在的合理性又是什么?在这些问题上的继续探讨,对深化我们的史学理论是十分有益的。
总之,傅斯年先生留下的思想是十分丰富和值得我们研究的,给我们史学理论的发展所留下的空间也是巨大的,今天的史学家们,应该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学术思想,更好地促进史学理论的发展。
[1]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08.
[2]赵兴彬.史学本体论[J].泰安师专学报,1999(4):63-67.
[3]何兆武.对历史学的反思——读朱本源《历史理论与方法论发凡》[J].史学理论研究,2003(4):19-24.
[4]宁可.史学理论研讨讲义[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5:4.
[5]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6]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7]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六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8]徐晓旭,朱丹彤.论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J].人文杂志,2003(2):131-135.
[9]李泉.“史学便是史料学”渊源得失论——傅斯年史学思想论稿之一[J].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3):78-84.
[10]栗彦卿.论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下)[J].广西社会科学,2007(12):109-112.
[11]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上[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42.
[12]苟兴朝.郭沫若与傅斯年史料观比较研究[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9):34-38.
[13]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一卷 [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24.
[14]苏全有,郑伟斌.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1-4.
[15] 孔润年.两种炎帝观:科学主义与信仰主义[J]. 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6):24-29.
(责任编辑:田 皓)
K092
A
1674-9014(2011)05-0075-05
2011-04-12
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北大学古籍善本书目提要”(06M003S)。
程鹏宇(1988-),男,山西忻州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