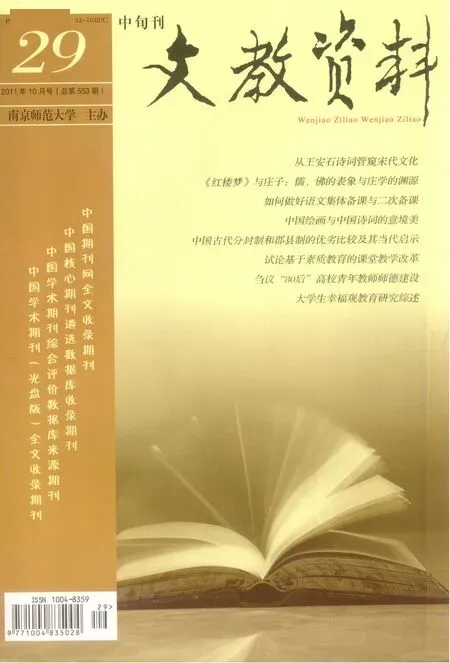论晏殊忧乐冲突中的“知足境界”
2011-03-20李万堡
李万堡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中文系,广东 汕尾 516600)
叔孙豹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孔颖达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立功,谓扼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虽没,其言犹存。”(《春秋左传正义》)简言之,“立德”指道德操守,“立功”乃事功业绩,而“立言”则是著书立说以传之其人。其实此三者皆旨在追求某种身后“不朽之名”。古圣先贤的这种追求,正是超越个体生命而追求精神永存的贵族价值观,同时这种追求又恰好以符合社会群体利益的道德、事业、言论为个体精神价值无限延续的条件。但是这三者又不是并行的,立言只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自韩愈倡言复古之后,“立言传道”、“文道一统”已经成为正统文学的人本意识中最基本的共识之一。彭亚非说:“在写作理念中有意将意识形态言说的必要性与参与政治权利的运作区分开来,而与文学性追求合二为一。就中国文人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视而言,这一理念的实质便是,当不能实现权力话语的直接在场的时候,文学写作可以帮助缺席者达到间接性的和永久性的话语在场……因此,文学立言观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中国文人意识形态权利话语的在场追求。 ”[1]
一、名利知足
晏殊对生命体悟极深,其内心深处有三忧。
其一,生忧——哀叹人生苦短。晏殊二十岁时,与自己一齐被选入宫伴读,年仅十八岁的弟弟晏颖去世;次年父亲在杭州病逝,晏殊本应守制,但又被仁宗以“思臣心切”为由召回;回京不久,母亲又病逝;他的第一个妻子李氏是官宦之女,成婚两三年后便去世了;约在二十七岁时与第二个妻子孟氏结婚,在他近四十岁时又病逝;他的第三个妻子王氏算是陪伴了他的后半生。经历了一系列的死亡事件,过早地经历了太多不幸的晏殊心理创伤极大,因此对生命及其敏感,哪怕在开心时,也能引发他深沉的忧伤。
其二,情忧——屡尝情感缺失。前两位妻子都可谓红颜知己,可惜短命,唯独河东狮王氏却偏偏长寿。晏殊曾有一个家妓,才貌双全,深得晏公爱怜,但是因妻子王氏妒忌,无奈只好将她卖掉,致使她流落街头,后来词人张先著词描绘其惨状,晏公不忍,又将其召回。晏殊的一生,喜欢的人,无法长久拥有;不喜欢的人,却又挥之不去,始终不能圆满。表面上富贵荣华,实际上大半生都在忍受情感的煎熬。
其三,宦忧——忧谗畏讥。晏殊仕途一生都伴随着党争,宋真宗时寇准和丁渭,仁宗时吕夷简和范仲淹。晏殊身处其间,一生如履薄冰,三次遭贬。
于是在晏殊的作品中人生苦短、及时行乐便成了主旋律。然而这一思想又与淡泊功利、乐天知命常常绞在一起。《酒泉子》:“三月暖风,开却好花无限了,当年丛下落纷纷。最愁人。 长安多少利名身。若有一杯香桂酒,莫辞花下醉芳茵。且留春。”暮春花谢,感人生之易逝,名利之虚逐,绝非仅仅叹老嗟伤之闲愁。《喜迁莺》:“花不尽,柳无穷,应与我情同。觥船一棹百分空。何处不相逢。 朱弦悄,知音少,天若有情应老。劝君看取利名场,今古梦茫茫。”看穿名利,古往今来名利场好似梦渺茫,这是对生命本体的感悟。《菩萨蛮》:“高梧叶下秋光晚,珍丛化出黄金盏。还似去年时,傍阑三两枝。 人情须耐久,花面长依旧。莫学蜜蜂儿,等闲悠飏飞。”以蜜蜂酿蜜暗喻官场争名夺利的生活。用唐代诗人罗隐诗句解释颇为贴切:“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以奉儒守官者视之,晏公乐天知命,而以道心法眼观之则安之若命。
二、富贵知足
行乐是晏殊排解苦闷的方式之一。叶梦得 《避暑录话》记载:“晏元献公虽早富贵,而奉养极约,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而盘馔皆不预办,客至旋营之。”晏殊虽喜宾客宴饮,然从不铺张,但求菜蔬随时,从不追慕权贵们的竞豪奢式的生活。晏殊延客之意不在酒菜,而在乎诗词管弦之间也。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了一件事颇能说明晏殊人生观的感悟:“一日,游涡水,见蛙有跃而登木捕蝉者,既得之,口不能容,乃相与坠地,遂作《蜩蛙赋》。略云:‘匿蕞质以潜进,跳轻躯而猛噬。虽多口以连获,终扼吭而弗制。’”[2]由于当时摄于明肃刘太后的权威,他在撰《章懿太后墓志》时隐瞒了仁宗身世的实情,而今仁宗亲政,遂贬晏殊知亳州。现在偶见蛙捕蝉的情形,忽悟得人生之真谛——贪多勿得,反受其累也。欧阳修《晏公神道碑铭》曰:“其为政敏,而务以简便其民;其于家严,子弟之见有时。事寡姊孝谨,未尝为子弟求恩泽。在陈州,上问宰相曰:‘晏某在外,未尝有所请,其亦有所欲耶?’宰相以告公,公自为表问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赐予加等。以其子承裕为崇文检讨。孙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看来晏公的廉洁自律是得到皇帝首肯的。
晏殊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从不矜夸骄纵,他在与兄书中告诫家人说:“古今贤哲有识知耻者,量力度德,常忧不能任者不妄当负,以重愧责”、“人事有何穷尽”、“大抵廉白守分为官”、“安泊家属,不必待丰足”(《答赞善家兄书》),就是说做官守住本分就好,不要奢求高官厚禄,不要追求奢华,生活够用就好。有一次,皇帝说喜欢他不爱好嬉游宴赏,但他却实告曰:“臣实非不喜爱嬉游宴赏,奈无钱为之。臣若有钱,嬉游宴赏,岂肯落人之后耶?”这段话十分巧妙,表面上是据实以陈,实则既以“自诩清廉”溢于言外,又规避了对同僚的品评。要解释晏公此种行为之冲突,须深入其心灵深处,晏著《解厄学》(善本)八卷便是金钥匙。其《解厄学》曰:“欲大无根,心宽无恨;好之莫极,强之有咎。君子修身,避祸也;小人无忌,授首也;一念之失,死生之别也。”(《戒欲卷三》)强调把握自己,修身避祸。晏公有超强的自省力和自我控制力,他时时刻刻告诫自己“欲”乃祸之端也。又曰:“悟者畅达,迷者困矣。”(《戒欲卷三》)晏公的“行乐”是以“洁身自好”为前提、以俸禄供给为前提,其“乐”者,是知足常乐、是乐天知命。
三、谨言远祸,知足常乐
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但其“游于艺”是以不放弃伦理道德理想为前提的,并不等于玩物丧志,其“艺”中自然应该包含着礼乐文化的风雅精神。“游于艺”虽不一定像经史那样述往思来,但应该在一定的意义上促成道德的艺术化。孔子又曰:“有德者必有言。”虽然道与文常常不能完全统一起来,然而晏殊之“游艺”果真未“志道”、“据德”乎? 自陈子昂倡言“风雅”、“兴寄”之后,诗歌就渐以社会性的群体情感为主,偏重政治主题,多抒写国家兴亡、民生疾苦、胸怀抱负、宦海浮沉之情怀,而个体的自我情感则以“小歌词”出之,故词则偏重以描写男欢女爱、相思离别。自花间派之后,宋初文人已有“诗庄词媚”的认识,但晏元献填词不离歌儿舞女,赋诗也必调风弄月,其诗词也清词丽句常有互见。在晏殊这里,诗词是一体的,同为释恨佐欢之作,这又令后人十分费解。晏殊一生著述颇丰,然而大多散佚,所以我们只能从仅存的两百多篇诗文中“以意逆志”。但是为了避免更多的解读者偏见,参合正史稗言“知人论世”以观其“小园香径独徘徊”是否仅是富贵闲愁,其“风雅”精神是否“在场”。王国维说:“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解则寡矣。”(《玉溪生年谱会笺序》)“逆知”晏公诗词中风雅精神往往“缺席”之背后的思想皈依则可待矣。
晏殊对社会人生的思考总是充满着矛盾,因此他无时无刻不体味着人生的无奈与苦涩,其诗词总是被寂寞孤独的失落感所笼罩,如“好月谩成孤枕梦,酒阑空得两眉愁”,“闲役梦魂孤烛暗”,“酒醒人散得愁多”,“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窗间斜月两眉愁,帘外落花双泪堕”,“独凭栏朱,愁放晴天际。空目断,遥山翠”。他以艺术的方式感知生活和理解生活进而超越生活,他的艺术思考和哲学思考都来自所处的政治环境,他用忧患苦涩搅拌着心安逸乐来品味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他的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把这种充满冲突的心境抒发得淋漓尽致。诗人内心是挣扎的,他的追名逐利之火涌动的同时,他的汪洋淡泊之水也在起伏。家庭中不能我行我素,朝堂上身居要职却不敢据理力争,好人不好做,大事不敢做,进退维谷,最后他只好把“知足”融入“独徘徊”之中。不可摆脱的深刻的忧患意识与不可推却的人生责任感交织在一起,使晏殊身上充满了复杂的“心灵冲突”与理性涵养。知足既是禀赋,又是感悟;既是枷锁,又是解释。
[1]彭亚非.中国正统文学观念[M].社会科学文学出版社,北京:2007:126-127.
[2]宋元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07:26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