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给农民国民待遇不是那么可怕
2011-03-20马国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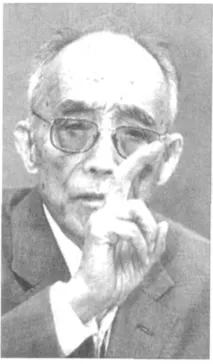
农民独立发展的机会还不充分,他们还缺乏充分的市场自由和迁移就业自由,经营的自主权是残缺的。我们正在一步一步地深化改革,希望能尽早走出过渡阶段。
作为中共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杜润生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2001年,他为《我给总理说实话》一书作序时,大胆直言,“我们欠农民太多!”他建议,“宪法要加上一条:中国的公民有迁徙的自由。城市不论大小都要向农民开放,让他们可以在城市安家落户。怎样保证农民的自由选择权,已经成为中国新一轮城市化的关键所在。假如农民没有自由权,即使“出发点”良好的改革之举,也有可能蜕变为“恶政”。就此话题,《财经》记者曾数次采访杜润生,形成了以下对话。
《财经》:您在农村改革中坚持的原则是什么?
杜润生:我在农村问题上有一条原则:尊重农民,让农民真正解放。
《财经》: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公有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提高了农业生产能力,但是质疑的声音一直存在。您怎么看?
杜润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家庭经营是应该受到肯定和维护的农业经济形式。国家应该有一系列保护农民权益政策,走出“负保护”。必须提高城市化水平,扩大就业机会,大量外移农村劳动力。政府应腾出资金,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和文化教育科技事业,适度扩大经营规模,逐步走向土地资本化,技术现代化。给农民自由权我现在脑子里有两个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放心不下。第一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组织好农村人口的转移,使农民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第二个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可否恢复农民协会?
《财经》:使农民变成有完整权利的公民,就是给农民完全的国民待遇。
杜润生:在本世纪的中期,转移出去2亿左右的农民,使农民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现在有近亿人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摆动,城市要把这些人安排好;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最好建立农民协会。
《财经》:由于农民不能恢复成立农会,也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使得农民很难有力量抵制来自权力的侵害,所以有人说农民其实是这个社会的二等公民?
杜润生:“二等公民”的说法不确切,但反映了部分真实存在,值得关注。林肯在签署《解放黑奴宣言》后,有人问他:你怎么敢将成千上万的黑奴从奴圈里解放出来呢?你不怕天下大乱吗?林肯很平静地回答:政治家做很多事情需要的仅仅是勇气而已。可怕的是对一些不确定性的恐惧。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将他们从土地和其他约束下解放出来,并不是有些人想象得那么可怕。
《财经》:作为一代改革家,您对中国改革有什么希望?
杜润生:我不是改革家,只是个改革者吧。我认为,中国改革要过两大关,一是市场关,一是民主关。市场关很明确,过民主这一关比过市场关还麻烦,弄不好就带来政治波动,可能会动乱。但反过来说,不搞民主,就不会乱?可能出现权贵资本主义,可能有更大的动乱。民主在有利于稳定的前提下,在法制的约束下进行,才是最好的选择。对中国农民来说,除了市场关、民主关,还有自由关。要给农民自由权,没有自由不行。
(文/马国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