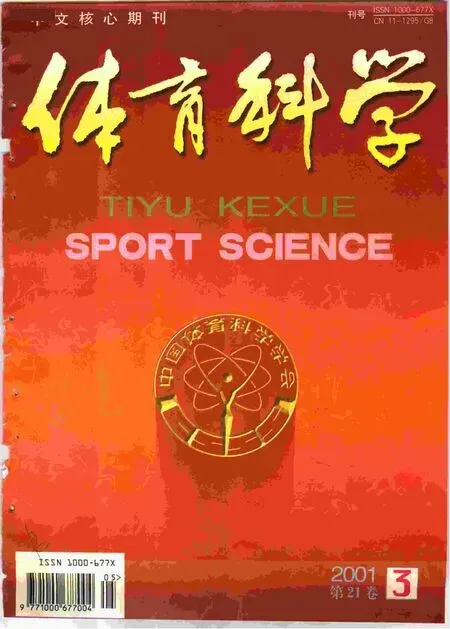中国近代体育发展阶段的历史审视
——一种身体社会学视角
2011-03-20程卫波张志勇
程卫波,孙 波,张志勇
中国近代体育发展阶段的历史审视
——一种身体社会学视角
程卫波1,孙 波1,张志勇2
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承载了中华民族实现国富民强的民族诉求,也是中华民族在器物发达和典制进步遭到挫折之后实现民族强大的希望所在。从身体社会学的角度对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进程进行历史态的考察,将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把握中国近代体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更好地为当今中国体育事业的改革提供借鉴和新的思路。
近代;体育;发展阶段;中国;身体
前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历经长期挫败,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掠夺的严重危机,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忧患意识深入人心。当时一批政治改革家推动改革的首要目标,就是积极探求中国积弱不振的根源与如何救亡图存的有效途径。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中国近代体育开始产生和发展。中国近代体育只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在这100多年里,西方体育开始传入中国,并逐渐得到普及与发展;在这100多年里,中国传统体育在不安定的环境中艰难地奋进;中国体育在这两大不同体育体系的相互排斥与相互吸收中走过了它的近代发展历程——留给人们的是一部恢弘而艰辛的近代体育发展史。
毫无疑问,体育不仅仅指向个体,它更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意义,包涵着特定时代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和理想追求。中国的近代体育所包含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体育自身,我们要把近代中国体育放到一个更为开阔的、更为深远的历史背景中加以研究。对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而言,体育更是承载了国人对于民族复兴之渴望,体育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是国家强盛和振兴的象征。因而,我们不能仅将注意力放在1904年《癸卯学制》以后学校体育制度沿革、体育政策法令的颁布以及个别教育家的体育思想等具体内容上,而更应放到一个民族振兴的历史场景中,充分发掘其社会历史意蕴。
需要指出,尽管本研究探讨的问题似乎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体育史事,但这些近代体育事件生成的重要过程和影响却事关此后数十年甚至百年中国体育的发展。因此,本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除了对这一段体育历史的演变有一个客观陈述外,也期望通过“历史的视野”对现今中国体育的样貌和其所以然有一个更加清楚的理解。历史是一种人类生活的绵延,而非可以人为切割的对象,中国近代的体育发展史也不例外。事实上,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历程并没有一个绝对的起点和终点,也没有一个惟一特定的主导力量始终在牵引着它的展开,因此,要形成一个对近代中国体育绝对单线式的、没有任何时间重合叠加的发展阶段的探讨,就变成了一个很难进行的工作。本研究所归纳的中国近代体育的几个发展阶段,仅仅是作者基于特定的研究视角对中国近代体育发展历史的一种描述的尝试而已。
作者单位:1.鲁东大学体育学院,山东烟台264025;2.山东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1 国家化生成:军国民运动下的中国体育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体育所进行的身体改造与近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密切相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身体并非属于个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个人身体具有强烈的家庭和宗族意味。在近代中国面临国力衰落、民族危亡的历史背景下,身体改造甚至成为包括民族、社会、国家在内的整体改造的基础与希望所在,而这,在当时几乎成为所有渴望民族振兴的仁人志士的共同理念。体育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浓缩了国家的发展,体育的振兴在一定意义上表征着民族的振兴。在一种内外交困的艰难时局下,体育似乎成为一根救命稻草,承载着国家强盛和民族振兴的希望。于是,本来伴着传教士、洋商、外交官和军人蜂拥而来的作为一种强身健体方式而引进的近代体育,并没有对“天朝上国”的子民的日常生活产生多少影响,也没有为社会大众的身体强健发挥多大作用。相反,许多仁人志士却将体育看作是西方人所以身强力壮、军事强大,能够侵犯我“天朝尊严”的重要基础,进而产生强大的学习动力。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体育具有了一种巨大的感召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凝聚人心,实现民族团结和自强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分析中国近代军国民体育思潮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内容时,我们除了留意体育具有直接改造身体的功能的表象外,也必须留意这些内容与国家势事的关联。
1902年,留日学生奋翩生(蔡愕笔名)在《新民丛报》发表“军国民篇”,成为军国民体育思想的嚆矢。他在文章中指出,军国民主义的渊源是:“昔滥筋于希腊之斯巴达,汪洋于近世诸大强国”[1],由此,他详细阐述了中国之所以缺乏军国民主义的8条原因。1903年,蒋百里在《新民众报》上译介了“军国民之教育”一文,不仅介绍了日本军国民教育的实施办法,而且基于自身理解和中国实际国情做了一定的发挥,阐述了在中国推行军国民主义的方法和途径。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军国民教育就是培养全体国民的爱国心、名誉心、公德、素质和忍耐力,以使得每个国民个体具备军人和国民的意志,其途径为“凡社会上一切之组织,皆当以军事的法律布置之,凡国防上一切之机关,皆当以军事的眼光建设之;社会之精神之风俗之习惯,皆当以军人之精神贯注之。军人形质之在于外者,国家赖之以安宁,军人之精神之在于内者,则国家之所由立也,民之所由生也……军人也,国民也,则一而而已矣”[5]。1912年,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在“对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指出:“在他国已有道消之兆,在我国,则强邻交逼,巫图自己,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且军人革命以后,难保无军人执政之一时期,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将使军人社会,永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而无以平均其势力。则如所谓军国民教育者,诚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也”[2]。之后,贾丰臻、张謇等人相继对军国民主义提出自己的看法。可以说,这个为时将近20年的军国民身体改造运动,使体育的工具化价值空前强化。在他们的思考中,体育与国家的关系被进一步理清,最后形成一个国家高于个人、统摄个人的权力状态。这种由知识分子觉醒在前,然后通过各种不同的论述与社会文化活动推动在后的体育国家化发展,正是军国民体育在近代中国演变发展的过程。
当然,军国民体育思潮的兴起,决不仅仅是由于有志之士的传播和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局势,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体育对人性和民族性情的激发。军国民体育思潮,在古斯巴达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剽悍勇侠之风,在19世纪的德意志帝国所表现出来的铁血政策和雄飞气势,在俄罗斯所表现出来的斯拉夫精神和西驰东突能力,在日本所表现出来的尚武精神等,都使当时中国的有志之士看到了尚武对实现“驰骋中原、屹立地球”的重要性[4]。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每个市民绝不能成为体育的门外汉,应该有最坚实的身体条件,一旦国家危急便能随时出征,尽自己保卫国家的义务”[6]。在近代中国,军国民体育思潮呈现出一面倒的接受形势,成为应对时局的一种救世方略。这个以国家和民族生存为动力的军国民体育思潮,契合了近代中国不同社会群体的心理需求,受到不同阶级、阶层的附和与响应。更进一步说,既然在近代,中国国民的身体被国家化、工具化,那么,为规训国民身体的体育,则注定是一种工具。于是,在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过程中,不论是最初的兵式体操,还是本土的传统武术,都无法摆脱工具化的命运,体育的发展直接指向国民的身体素质,而最后的目的还是挂靠在救亡的旗帜之下[9]。因此,军国民体育思潮之所以在近代中国成为一种权威性语言,除了国人对军国民体育思潮在西方各国所造成的优势的向往外,对近代中国国民孱弱身体的担忧,也是军国民体育思潮最终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潮的原因。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军国民运动改造下的中国体育有着严重的排他性功能定位。“一战”之后,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以打倒孔家店,提倡新文学和发挥个体自主性等作为革命召唤的新文化运动;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个人文化生活的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尽管在内容上以其鲜明的科学主义内涵和独特的人本主义精神强烈地冲击着军国民主义下的中国近代体育。但是,在近代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仍然是农业社会,不论从国家宏观经济状况或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存状态来看,中国还没有形成让西方体育在大范围内的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和土壤[13]。因此,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中,我们既要看到当时体育思想中所蕴涵的“为个人生活”的新文化思潮和自然主义的体育思想,更要深入理解这种思想背后所裹挟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救亡开始压倒启蒙”的民族自救、民族自强的社会心理。于是,军国民体育思潮以体育军事化、体育全民化的面貌出现,体育的国家化价值取向和民族主义意旨再次得以强化并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应该说,这一时期的体育发展已经超越了体育自身发展的逻辑要求和价值归依,具有了更多的政治和民族解放意味。
军国民体育“这种以国家和民族生存作为身体开发的依据,虽然是一个十分时代性的结果,却也造成中国人的身体自此步入一个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的状态,在国家、国权成为主要价值所在的情况下,身体的欲望成为首先需要节制的对象,其次则是对身体机能进行一个军事化与规格化的调养,希望借此达到重振国权与国力的目的”[4]。长期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都在宣扬这样一种理念,个人的身体是渺小的,只有放到“民族”、“国家”的宏大视野中才能呈现出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只有在“我们”之中才能成为“我”,“我”只有在“我们”之中才能获得发展,才能实现超越。于是,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体育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一种救亡图存的工具性策略选择。可以说,在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的目标之下,近代中国体育和国民身体必须服从国家未来的命运选择和发展规划。于是,人们获得了这样一种普遍认识:体育的目的就是“强身健体、救亡图存”[9]。我们看到,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体育始终无法摆脱国家的价值取向,它的兴衰跌宕极大地影响了社会民众对体育的普遍认知,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体育观念以及近代体育的发展指向。并且,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现在,当今中国体育实践中,仍然可以看到军国民体育思潮的影子在国人体育意识中忽隐忽现——在国人普遍的意识中,作为国家在世界上“考试成绩”的奥运会成为体现国家精神和综合实力的展台,而奥运会金牌则以最简明直观的数字形式,暗示了一个国家在国际竞赛中的地位和位置[10]。
2 法权体育的开启:礼法斗争下的中国体育
清末以前,中国的法律基本上是以儒家伦理作为制法与执法的依据,而且,这种发展自唐代以来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改变。也就是说,清末以前的中国法律基本上是沿袭汉唐以来的“以礼立法”的作风。这种礼刑合一的发展是中国法系的特色,也是“儒学法家化”和“法律儒家化”等论辩所以能够兴起的基本原因[12]。究其机理,就是中国的旧律基本上采用王权、父权、夫权和家长权贴近加身的方式管制个体身体的进展。这种以身体作为管制对象的安排,说明身体在近代中国之前一直是礼法竞相争逐的场域。但必须留意的是,这一现象在清末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身体被礼教控制的倾向开始出现松动。自此以后,中国人的身体开始了从礼法身体到法权身体的艰难漫长征程。本节的讨论,就是理清权利法的引入对中国人身体所造成的影响,同时,也透视近代中国法权体育的诞生。
仔细审视晚清以后国人身体和近代体育之间的关联,以及这种关联产生的缘由发现,为了争回国家司法主权而进行的修律工作,使中国人的身体自此步上脱离父权、夫权与家长权的路径。尽管其初始动机不是为了身体的解放,但却在实际修法的过程中使以礼入法的原则不再作为中国法制的主导势力而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更具权利法形式和人道意义的法律制度。于是,身体获得一个独立于家族之外的法定地位,向一个具有独立人格概念的人的方向发展,同时,也使得天赋人权的观点第一次在中国的法制上得到了认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表明,新的法权下的身体正在取代家族化的身体成为近代国人身体的新特征。
1912年,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身体、居住、财产、营业、集会、结社、通信、信教、著作和出版的自由,以及“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8]的规定,这个约法条文,除了将过去的中国礼教和伦常对身体的过度束缚一一松绑以外,也使个体权利本位的法权化身体首次在中国社会登场,并且,逐渐成为日后近代中国制定各种法令的参考范本。这一规定显示,人们已经开始法制化地审视自己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不再片面地从属于皇权、父权、父权和家长权的垄断与统治——这是近代以来所进行的现代性启蒙教育的结果,同时也表明,我们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感在增强。通过对自身身体的理解与态度,我们看到了个体价值观逐渐增强。对于一个迫切渴望独立和自主的民族来讲,这一点意义非凡。以西方近代体育的传入而言,虽然,它有一个为维护国家主权而出现的最初动机,但其后的发展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却使得中国近代体育重新融合并进入到中国社会的文化生活中。
通过近代中国体育发展的艰难历程——从清末开始的修律活动到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一些法律条文——我们看到,礼法斗争下的身体和法权体育在近代中国的确经历了一个未曾有过的转变。身体开始脱离家庭和宗族的束缚,以强健身体为目标的西方体育在传入中国后也逐渐失去了其原来的意义,而被强行纳入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这一重大的历史潮流。其实,在身体社会化的过程中,将个体身体与国家旨归联系在一起本身是没有太大问题。因为身体不仅仅是纯粹生理意义上的肉体,而是要承载更多的社会意义和政治价值,这样才能使身体在人的主体意识确立过程中产生积极效应。把身体和体育置放于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之中,是近代中国礼法斗争下的身体和法权体育的进化难以回避的历史趋势。
3 教化体育的演进和实践:世界时间建构下的中国体育
世界时间并非以一种偶合的形式出现于近代中国,世界时间的采纳和开展牵涉近代中国对世界整体形势的觉醒,以及对自身处在这种形势中的地位的体认。在一个民族历史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在一个资本力量横扫一切顽固旧势力而确立其世界新秩序的时代,在一个封闭落后就要挨打,开放自强才能获得承认的时代,中国这只沉睡的雄师在西方坚船利炮的震击下慢慢觉醒了。我们不能再抱着老祖先的牌位酣然沉睡,西方国家要把我们强行拉入以当下和未来的生存竞争作为首要考量的世界时间之内,传统的计时方式及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必须被扬弃,全新的世界时间及其内涵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逐渐成为我们行动和生活的参照系。这个影响后世深远的时间形式——世界时间(钟点的采用、西历纪年和阳历的使用),不但对近代中国传统的时间意识产生巨大挑战,同时,也对近代中国身体的开发和教化体育的演进与实践产生了巨大的规范作用。
实际上,在世界时间的采纳上,我们主要是以流通性和使用这些世界时间的国家的国力强弱作为选择的标准。世界时间所展现的是西方国家宗教改革以来自然科学发展的巨大成就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世俗化的发展状态,是对西方中世纪宗教神圣时间和永恒观念的超越。这种采纳,然后加以制度化使用的过程,在近代中国学校有着清晰可循的轨迹存在。因此,以世界时间建构下的身体观来检视近代中国教化体育的演进,不但可以使我们对近代国人身体的遭遇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是,透过身体的工具化和使命化的发展,可以让我们对近代中国学校体育的实践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
众所周知,清末的学校教育变革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在这期间,将“臣民”改造为“国民”的思想,推动了这场教育变革从“制度”转向“身体”的重心转移。因身体素质的低劣而引发的“教化身体”的议题传递出身体改造的努力与强国强民共识之间的逻辑关联。我们知道,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兴起于1903年的《癸卯学制》,这个在光绪年间颁布的学校制度,不但将戊戌时期“变科举、兴学校”的呼吁,透过蒙学院、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和大学学堂等的设立具体实现,同时,也将学校体育教育的主导权正式纳入国家的统御范围[4]。在学校体育改制的过程中,清廷除了对当时体育课的内容、目的做了严格的规定外,也对上体育课的时间做了严格的规定。譬如,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各级各类学堂都要设立体操课,初等小学堂体操课各年级均为每周3小时,以保证对学生身体的规训和提高[7];1913年的《壬子·癸丑学制》中规定,小学体育教育要“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为宗旨”,中学体育教育的要旨是:“在使身体各部平均发育,强健体质,活泼精神,兼养成守纪律尚协同之习惯”[14];1922年的《学校系统改革令》将“体操科”改为“体育科”,扩大学校体育实施的范围,开始重视体育教育方法的研究,废除兵操将体育科内容设置为田径、体操、球类和游戏等,丰富了体育课的教学内容,使之更加适合学生的身心发展;1929年的《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中规定:“凡大学、高级中学及专门学校、大学预科并其他高等以上学校,除女生外均应以军事教育为必修科目”,认为“军事教育之目的在锻炼学生身心,涵养纪律、服从、负责、耐劳诸观念,提高国民献身殉国之精神,以增进国防之能力”[11];1931年的《初级中学体育课程标准》中规定:教学时间每星期3小时,每学期1学分,练习时间每星期2小时,每学期0.5学分,以保证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由此可见,清末的学校体育变革是一场外源促动并经内部改造的复杂互动结果,当学生身体成为学校体育教育关注的重点后,学校便不仅仅是学生汲取知识的场所,也是学生规训、指导、改造身体的场所[3]。可以说,身体塑造与学校体育教育的接轨,不但给了学校体育教育变革一个必要的社会支持,使普及体育成为世所公认的重要工作,同时,也为学生身体的开发觅得一个合法化的场域。
学校体育教育的开展是清政府进行国民素质改造的一个具体实践,这种实践具有自己明确的价值指向,那就是通过强健国民体质来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这种将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目标奠基于学体育的愿望和现实追求,使得中国近代体育教育的工具化和使命化合情合理。于是,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中国近代学校体育教育积极吸纳西方体育教育的时间安排方式和训练手段,甚至以此来衡量国民素质的高低,乃至国家实力的强弱。因此,这种以国家的生存作为无限上纲的近代中国体育教育的发展形式,自然和以学生个体身心谐和发展的现代体育教育模式有极大的不同。
4 结语
身体生成并不仅是一种肉体的生物性生成,更是一种在肉体既存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政治、军事、社会或文化的模造。在近代中国人身体改造生成的历史中,身体被时刻地关注、塑造和干预,并处处体现着国家的控制欲望。身体不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身体的发展和变化深受当下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环境之制约影响;身体的存在和意义随着国家命运一起被积淀、塑造出来[4]。体育是一种人为的和为人的文化存在,体育的存在是为了个人及人类更好地生活而增进人和文化的发展。因此,体育事业的发展必然是社会历史文化的综合系统的进步,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也是如此。
透过身体社会学的视角对中国近代体育进行历史的考察,挖掘影响近代中国体育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我们看到,身体的改造和优化一直是近代中国体育追求的价值目标。这一价值目标反映了近代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使命:在一个民族衰败、国力羸弱的特殊时期,赋予身体以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历史使命和任务也具有其时代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在近代中国,随着体育观念的变革,“改造人作为改造一切的基础”的观念被逐渐接受,体育作为一种国家生存手段的认同,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模式对近代乃至当代中国体育的模式产生深远影响。时至今日,功利化、工具化地对待身体和看待体育,忽视个体身体发展的需要似乎依然存在于我国体育发展的理念之中。这是我们今后应该注意的,同样也是我们今后在谋求体育事业发展和变革的过程中需要反思和批判的。
今天,我们的综合国力已经飞速提升,我国已经渐成世界强国,已经无需通过竞技体育金牌的获得来向世界昭示。当今时代背景下,让身体和体育回归其本真状态,减少对体育的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追求,防止体育本来所具有的自我实现、追求自由的特质被异化,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来看待和对待体育事业和体育运动,这是当今社会发展和时代精神的呼唤。
[1]蔡得 .蔡松坡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8.
[2]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J].东方杂志,1912,8(10).
[3]何芳.清末学堂中的身体规训[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社会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7-8.
[4]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5]蒋百里.军国民之教育[N].新民众报,1903.
[6]今村嘉雄.西洋体育史[M].东京:日本体育出版社,1961:34-35.
[7]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体育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387.
[8]南京临时政府.《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5条[Z].1912.
[9]庞念亮.近代中国军国民体育思潮之研究[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体育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61-62.
[10]商汉.超越奥林匹克国家观[N].国际先驱导报,2004-08-19.
[11]宋恩荣,章咸.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17.
[12]余英时.历史与思想[M].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1:31-46.
[13]袁旦.中国群众体育管理体制研究[Z].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
[14]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353.
A Historical Review on the Stages of Sports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A View from Sociology of Body
CHENG Wei-bo1,SUN Bo1,ZHAN G Zhi-yong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 modern China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environment.It carries the national aspirations of Chinese for a wealthy and strong nation,as well as the hopes to make the nation strong after the artifacts developed and the code system progress have suffered a setback.Making a historical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 moder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of the body will help us grasp more clearly the history of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ports and will better provide references and new ideas for today’s sports undertakings in China.
modern sports;development stage;China;body
G80-05
A
1000-677X(2011)03-0093-05
2011-01-06;
2011-02-10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10CTYZ01)。
程卫波(1977-),男,山东青岛人,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人文社会学,Tel:(0535)6685326,E-mail:weiboch@yahoo.com.cn;孙波 (1972-),女 ,山东威海人 ,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人文社会学,E-mail:sunbohzh@yahoo.com.cn;张志勇(1962-),男 ,山东济宁人,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人文社会学,E-mail:zhang9955@126.com。
1.Ludong University,Yantai 264025,China;2.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 250014,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