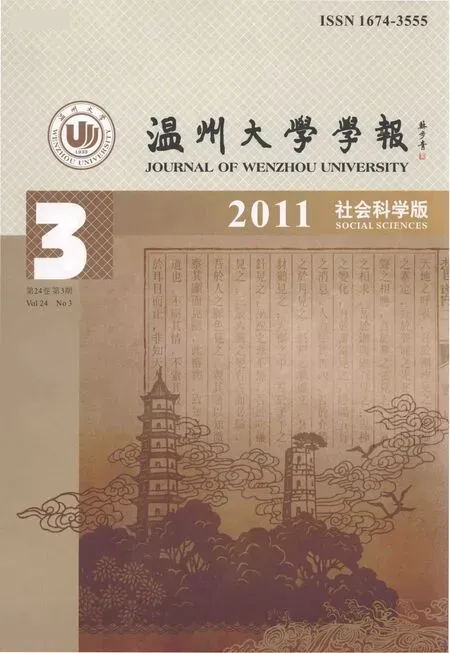近年来中国民俗学研究趋向的新观察—— 从两个语境和一个意识切入
2011-03-19庞建春
庞建春
(弘益大学教养外国语学部,韩国首尔 121-791)
近年来中国民俗学研究趋向的新观察
—— 从两个语境和一个意识切入
庞建春
(弘益大学教养外国语学部,韩国首尔 121-791)
从时代语境、学术语境和学者问题意识的角度,考察近年来中国民俗学的研究趋向,提出当代中国民俗学正经历从学科身份确立到学术品质更新的过程,包含了传承经典和知识创新两大主题。首先评述中国民俗学界建立和发展社会科学性质的民俗学的主张;其次评述中国民俗学界有关田野民俗志的新学说;最后讨论历史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和传统节日、民间信仰等领域的新动向。
民俗学;社会科学;当代中国;田野民俗志;历史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关于“两个语境”和“一个意识”
题目中的“两个语境”具体指时代语境和学术语境,“一个意识”是学者的问题意识。这一切入点的选取在方法论上借鉴了吕微提出的一种审视学科理论史的新视角,即,从研究主体的角度,通过考察研究主体如何借由个案将问题意识转化为带有普遍性的学术理论来考察学科理论史,从中发掘学科的生命力所在[1]。
正如吕微所言,当前民间文学界寻找学科出路的一个途径仍然是讨论研究对象“民间文学”本身的定性问题而不是“研究”本身[1]。也就是说,用讨论“什么是民间文学”代替讨论“什么是民间文学研究”,希望借助民间文学自身的生命力来证明民间文学研究的阐释力。从索绪尔命题的角度来看,很多论述和研究企图排除所谓干扰“内在”的“外在”以挖掘出研究对象的本质规律,将研究的理论建立在这一规律之上。但是吕微借助解释学同时通过分析中国民间文学学科中的新研究趋势提出,纯粹的内在性研究是不存在的,即使那些看上去尽量泛化或者边缘化研究对象主体性的研究,实际上也不可逃避研究主体本身主体性的介入[1]。这意味着决定学术研究性质的不是研究对象本身,而是研究主体。我认为,不必批判索绪尔“内在”和“外在”二分法在这里表现出来的局限性,因为他所面对的理论问题是不一样的。重要的是,从只看研究对象的“外在”,到只看研究对象的“内在”,再到审视研究主体的“外在”介入“内在”认识的形成过程。这种对于研究本身的反思,考察以外化形式存在的研究者问题意识如何内化为研究理论的生成,不可谓不是一个考察学科史的新视角,尤其对于希望借助学科理论史的探讨来发现学科绵绵不断的生命力所在而言。在我看来,这是民俗学研究中从“文本”到“表演”的理论转变在自身学科史研究中的一种尝试。具体来说,对于学科理论价值和意义的认识并不停留于对理论本身(表述的文本)的考察,而是研究“语境中的理论”。吕微已经涉及到了对当代部分民间文学研究趋向的阐释,不过他主要是提出和倡导从研究主体的角度,从研究语境的角度来重新解读当代民间文学的学科动力[1]。本文应该说是借用这样的视角对近年来中国民俗学研究趋向做出的新观察。具体来讲,就是考察学者在何种时代和学术语境里,如何提出和解释自己的问题意识,进而如何把个案性的问题意识转化为具有全局意义的学科理论。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本文关注中国民俗学的主体性问题,希望找到今日民俗学的阐释力所在。在现代社会,学科的成立意味着这门学问可以相对独立地承担起构造某种知识体系和形成理论阐释工具的作用,用以帮助人们认识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以及我们的生存方式,进而对于我们当下的和今后的生存有思想上的启迪意义。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回顾中国民俗学萌芽与学科身份确立历程,则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与她在社会转型期表现出的思想力密切相关。中国现代民俗学萌芽于五四时期,这是一个被中国人认为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思想和文化启蒙意义的重要社会转型期。民俗学在当时虽然新生而稚嫩,但是充满朝气与力量,不仅参与的学科门类多样,而且学者们的探讨往往都成为学术界和思想界发聋振聩的声音。民俗学作为一种思想,在当时回答社会转型期民族何去何从、知识分子何去何从的各种声音中,显得异常强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积累,民俗学幼芽终于长成临风的玉树,由此奠定了她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地位。当代中国学者非常关注我们刚刚经历和正在经历着的社会变革,比如新中国建立、文革十年、改革开放前十年、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等等。一部分民俗学者欣喜并满足于看到民俗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复兴”,将这个直接作为民俗学存在和发展的正当性的依据;一部分民俗学者却是喜忧参半,他们看到的是“民俗热”热了民俗学,但是民俗学却没有像五四时期一样热了学界和思想界。是民俗学冰冻了?还是什么出了问题?针对民俗学生存危机和机遇的讨论从 1990年代开始渐趋强烈,大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气势。只是在大讨论还没有任何公论之时,形势却突然发生转变。进入千禧年后,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为全球化浪潮中的核心话题之一,民俗学者一下子成为诠释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和价值的主要力量,民俗学仿佛不用正名就再次火了起来。简单地说,社会、知识界和学界都在这样的社会潮流中需要认识传统是什么样子的知识,民俗学正好可以满足这一点。但仍然有好事者想知道传统到底对我们现在的社会和我们当下的生存意味着什么,一些民俗学者发现我们的解释对圈外人尚有些新鲜感,但是对于圈内人而言却仅仅是常识,远不能像她萌芽之初那样扮演思想弄潮儿的角色。是民俗学本身出了问题?还是我们没有掌握拔出民俗学思想之剑的力量和方法?
近年来已经有学者开始反观五四以来中国民俗和民俗学的命运,从当代立场和提升学科阐释力的角度呼吁中国民俗学的学术品质更新,本文就从这里说起,从当下学术发展动力和方向的角度,重新审视本世纪以来中国民俗学的研究趋向。根据上述方法论视角,本文的问题意识聚焦在两个层面上。一是时代语境和研究主体的问题意识。近年来学者们所关注的时代话题到底是什么,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时代话题被民俗学者拉入了自己的视野;他们关心这类话题的出发点和目标是什么?二是学术语境和研究主体的理论建设。这是紧接着上一视角的,考察学者在选择和论述问题时,是运用既有的民俗学理论,还是借用别的学科的理论,还是创新理论;最后他们是否成功地让个案性的研究带动了整个学科理论的新生。根据主题的不同,正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学科性质的讨论,第二部分关于学科理论体系的建设;第三部分关于研究领域的创新。就各部分涉及的学科领域而言,第一部分有关理论民俗学发展;第二部分有关民俗志发展;第三部分分论历史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和传统文化研究、民间信仰研究等领域的新发展。
必须要提前说明的是,本文没有任何点评、评价的意味,只是一种理论史研究视角的尝试。因此题目中只称“观察”为新,而不称“新趋向”。对于下面将提到的各个研究,笔者不持任何高下之分、差别对待的立场;同样,没有刻意选取或者回避某研究成果的意味,仅仅是就笔者所收集到的研究成果来论述,完成这个视角的分析而已。
二、关于学科性质的讨论:如何发展作为社会科学的民俗学
学科性质的认定是引导一门学科发展方向的大事,我认为这是现代民俗学发展中的核心命题之一。中国学者的回答经历了一个从确定民俗学是社会科学,到讨论如何发展作为社会科学的民俗学的过程。由此也可以相对划分出两代学者的理论构建工作。
第一代学人是以“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他们亲身参与了民俗学在中国萌芽、兴起到成立和学科身份确立的曲折历程,既看到了民俗学与国家、民族命运相联系的实际,也看到了将民俗学学术目标的设定和学术性质的界定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确定其国家级学科的地位是必须且重要的。因此,如果关注 1980年代以来界定民俗学的论述,尤其是钟敬文先生的文章,不难看到社会科学的视角在现代中国民俗学界并不算新鲜事。但是他们大多是文学、民间文艺学出身,虽然提出民间文艺的研究必须联系到民俗,必须将视角转向更为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研究方法也不能局限于文学的和史学的,还必须有人类学的、社会学的,可是在具体的研究概念和研究问题的设置上,做法跟传统的国学非常接近,注重文本型民俗资料的辑录工作,分析上以民俗文本解读为本,以民俗生活解读为辅;以民俗的客体解读为本,以民俗的主体解读为辅。我认为,这表明这一代学者主要是在整体概念上认同了民俗学的社会科学性质,从国家性和民族性的高度来界定民俗学在现代学科群中的重要性。但是这个体系内部的概念,尤其是核心概念的阐释还有待于从社会科学性质的角度加以强化和系统化,使之真正成为理论分析的工具,或者说找到理论新的生长点。这就是我说的第二代学者的工作①需要再次强调的是, 这里的代际是相对的, 主要以学科发展的历史阶段性为划分标准. 实际上有些学者是跨代的, 而且所指第二代学者的层次更为复杂, 不过这里针对的不是第二代学者群的差异性而是一致性, 所以做了笼统的归类.。
第二代学者的民俗学理论起点是第一代学者提供的,但是历史给后代学人提供了更多新的学术资源,同时也提出了新的社会命题。首先,第二代学者和第一代学者之间不仅仅在时间上有交叉,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大多数人之间有着师承关系。也就是说,双方在民俗学领域享有共同的理论知识基础。不管后代学者是吸收还是批判这个基础,都可以说他们的理论发展是对前人理论的继承。第二,第二代学者处于一个全面的“跨学科”学术语境中。除了文学以外,第二代学者对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宗教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的认识都是“跨学科”的吸收,而不是简单的理论借鉴。如果说第一代学者要求学生掌握一些相关学科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基本理论认识,那么第二代学者则是主动投入到某相关学科中去,不仅借鉴其基本理论,而且直接与该学科的前沿理论进行学术对话,在互动的刺激中发展民俗学的理论。第三,第二代学者面对着 21世纪的新命题。第一代学者对民俗学命运的认识来自五四启蒙运动,他们将民俗学作为帮助国家、民族摆脱贫瘠和苦难的思想力量。第二代学者则有着更强烈的当代感,如何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找到民族自立和与世界和平对话的平台,是这一代学者的历史使命。2000年以来中国学界多次召开有关学科发展立场的研讨。归纳来看,发展作为社会科学的民俗学,阐释民俗在现代社会中独特的社会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作用,是当代中国民俗学界经过反思后提出的当代研究立场、重要研究取向之一,它不仅存在于一些具体的研究个案中,而且已经有学者从学理上进行了论述。
(一)从“民俗生活”说到“日常生活的后现代救助”说和“民俗的公共性”
高丙中是中国学界较早对民俗学理论整体进行思辨性探讨的当代学者。1994年他的博士论文《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以与中外传统的民俗学理论对话的方式,提出了自己对民俗学学科定位的认识,其关键词是“生活文化”或者“民俗生活”。理论部分他认为以往民俗学的取向是“传统和历史”的,这个学术传统“在过去极大地推动了民俗学的形成和发展,但是现在民俗学迫切需要面向当代,面向现实生活”[2]8。他提出要让民俗学“转向生生不已的现实人生而使它充满活力”[2]6。除了源自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外,其主张的提出得益于一位社会学界学者观点的启发,他就是美国民俗学者威廉·格拉汉·萨姆纳。借鉴萨姆纳从社会生活角度阐释的民俗学理论,高丙中围绕“面向现代社会”的命题,对比地提出五个关于如何研究民俗的做法,它们是[2]109-111:第一,关注作为生活事实的民俗,而不是作为文化现象的民俗;第二,建构民俗的发生情境,而不是只看到静态的民俗;第三,抓住民俗的当代性、现实性,而不是历史性、传统性;第四,通过田野作业到活动中去进行研究,“充分把握扑面而来的复杂整体”,这是研究的基础手段,而不是辅助手段;第五,关注民俗主体。
高丙中的这个理论建构出现在 1990年代前半期,这之后有很多研究虽不是直接受其影响,但选取的视角多半和这个理论有关联。但就其本人来看,他没有沿着自己搭建的理论框架在民俗学的学科领域里研究下去,而是转向了文化人类学。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民俗学,其实这种转向也来自他对自己“民俗生活”学说的进一步思考,即,如何建立起这个理论主张下的民俗志体系。2006年他发表了《日常生活的现代与后现代遭遇:中国民俗学发展的机遇与路向》[3]一文,发展了自己的“民俗生活”学说,提出了中国民俗学发展的方向是在当代“给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自由运用民俗的正当性提供思想的空间和知识的条件”。这个新学说的核心词是“日常生活的后现代遭遇”。日常生活是一个社会里普通人每天过的日子,社会科学的功能是解答人们为什么这样过日子,而不是那样过日子。但是问题没有那么简单。社会科学的存在本身也是社会化的,它在解答问题的同时也产生社会问题。高丙中新学说的要害就在于反观学术理论对普通人日常生活形态的作用。从这个认识出发,他开始不把民俗等同于生活,而是谈“民俗与日常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民俗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在民俗学的意义上,民俗是被民俗学家发现并表述出来的那部分日常生活”。
这和他以前的主张并不矛盾而是各有针对性。“民俗生活”说是为了批判固化民俗活态性的研究理论,而新学说则是激发民俗学者反思民俗知识生产和一个社会普通人日常生活形态形成之间的关系,从而发现理论的生长点。具体来讲,他提出[3],“可以更多地投入关于民俗的公共性的知识生产”;在当前“让普通人有一个更多正面意义的日常生活,是中国的经济(小康)、政治(民主)的大政方针的目标”;民俗学应该为其“创造文化和学术的知识条件”。在我看来,这个新学说有鲜明的破旧立新色彩,在概念建构上基本脱离传统的民俗学领域,从社会科学时代使命的角度回答民俗学当前的发展方向问题。其关于“民俗公共性”的学科方向提法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回应和学界的广泛认同。
(二)一国民俗学和现代民俗学
如果说高丙中的社会民俗学是破旧立新,那么董晓萍的现代民俗学理论则是在继承传统、跨学科对话、立足国际视野的辩证思考中建立起来的,有更鲜明的民俗学本体性。从其近年的重要理论著作来看,可归纳出两个关键词:一国民俗学和现代民俗学。
中国学界的一国民俗学不是董晓萍创立的学说,而是钟敬文先生在民俗学获得国家级学科地位后的最重要理论建构工作,即提出“中国民俗学派”。但是 2003年董晓萍在《田野民俗志》中将之作为一种理论视角,有联系地考察了日本、芬兰、德国和中国的民俗学发展历程,提出当代民俗学的一种研究取向就是“一国民俗学”,具体来讲是“把目标放在本国范围内,搜集本国的民俗资料,做本土的民俗研究。它提倡民族文化认同体系,争取自我文化发展的机会,呼吁从人类共有的文化精神上,建设和平文化的格局”[4]49,“研究稳定出现的民俗事象对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和意义。”[4]50我认为,这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的视野下对民俗学性质的适时界定,提出了作为社会科学的民俗学的当下研究目标。它的重要意义有二:第一,在各种扩大民俗研究领域,模糊民俗学和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界限的观点中,“现代一国民俗学”的提出重申了民俗学的本体性意识;第二,这一学说继承了将学科价值和意义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起来认识的民俗学理论传统,但结合当今的时代命题,提出了民俗学的新主题“认同”[4]42-49。
更具本体性的理论构建表现在董晓萍 2007年的专著《现代民俗学讲演录》中。这部书的重点是“在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根据现代高校民俗学教育的发展需要,重点根据我国实际,以框架的方式,阐释我国现代民俗学的学说体系和基本研究方法。……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民俗的变迁、危机和利用方式加以研究和阐释”①参见: 文献[5]之内容简介.。具体来看,她的理论特色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对照不同阶段的中西学说,为提出应对当前社会背景的民俗学主张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其次,建立新的分析概念体系是该书理论建设的又一特色。仅以第二节“民俗学的范围”来看,这里提出了四组分析术语:历史划分与政治划分、进化划分与进步划分、书面划分与口头划分、阶级划分与文化划分。这些术语单个来看熟悉民俗学的人都不陌生,但是将它们集合起来进行成组对照性的认识,就不能不说一种启人深思的理论构建工作。最后,提出新学说“三元论”,建构相应的理论体系是该书的要害所在。“三元论”指的是“要对民俗社会的人、自然和社会三要素的研究和阐释进行理论整合。在此基础上,对民俗学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交叉互补”[5]74。在这样观点的支持下,董晓萍从研究的角度提出了新的民俗学领域分类,包括粮食民俗、水利民俗、土地民俗、性别民俗和宗教民俗。这个类别体系的建立鲜明地带有以社会学为基础的民俗学研究倾向,但也是立足于民俗学自身的。仅从粮食、水利和土地三项来看,明显是在发展前人以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和农民社会为范畴的民俗学研究取向。
无论是推陈出新还是继承创新,前后两代学者的认识都不是截然断裂的,也不是并行发展的,而是在不同时期有联系地回答民俗学是怎样一门社会科学,如何发展作为社会科学的民俗学。后一个问题实际上还只是刚刚展开,但它无疑是今日中国民俗学的一个重要命题
三、关于理论体系的建设:有关民俗志学说的讨论
尽管对于当代中国民俗学取向的认识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况,可是各种主张无一例外地强调了同一个理论建设工作,那就是民俗志。第一代学人在民俗志方面的理论贡献有二:一是提出中国存在悠久的民俗记述传统;二是提出通过实地调查撰写民俗志是当今民俗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对于第一点,当代学人已经开始着手进行中国古代民俗文献的整理和阐释工作,这一内容本文放在第四节中介绍。对于第二点讨论很多,问题集中在撰写民俗志的学科立场是什么?民俗志撰写的科学规范又是什么?
中国学界对民俗志理论的思考除了来自民俗学内部以外,更多来自民族志的理论冲击。从民俗学内部来看,如前所述,新一代学人越来越强调民俗学对于当代社会问题的学术承担,因此他们不能满足于传统的记录民俗志,认为过于宏大或者过于零碎的民俗记录根本不可能接近调查对象的实际,更无法发挥民俗学的阐释力。与此同时来自西方学界的民族志,无论经典还是新成果,都显示出强劲的理论力量。在广泛借鉴民族志理论的过程中,大多数学者开始发觉并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应该模糊甚至取消民俗志和民族志的概念界限,直接用民族志代替民俗志。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我认为这一类坚持树立民俗志独立性的观点非常可贵,真正有助于寻找到和发挥出民俗学的理论和实践生命力。下面介绍其中三个代表性观点。
(一)区别于民族志的民俗志
高丙中2007年发表了《“民俗志”与“民族志”的使用对于民俗学的当下意义》[6]。总结起来他的看法有两个层次。首先,从学术传统来看中国学界存在民俗志和民族志的区分。其次,民俗志和民族志可以从理想概念的层面上加以相对的区分,由此推进具体研究的有效发展。这一点需要略加说明。高丙中提出的区分策略是从“知识关注的约定”的角度来看,两者的区分在于“一个是我对我群的参与观察和文化书写,一个是我对他群(国外社会和国内的其他族群)的参与观察和文化书写。”这样的相对区分可以照顾到学术传统的承继,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双方的各自发展和相互丰富。我认为高丙中的观点实际上还隐藏了一个重要的批评,即与民族志相比较来看,民俗志尚缺乏当代经典,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还需要援用民族志理论原则和方法,直至建立起自己相对完善的学术规范。我想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会产生放弃民俗志概念的主张。这样高丙中的主张对于强化当下民俗学的学科本体性就是非常重要的,提出的建立民俗志学术规范的问题也是任重道远的。
(二)田野民俗志学说
与高丙中相比较,董晓萍更倾向于站在本学科发展的立场上提出田野民俗志学。她在《田野民俗志》的绪论里是这样谈论田野民俗志的:“现在国内民俗学者有几件要紧事要做,例如,深化理论研究、提升资料学的层次和拓展民俗学教育等。在它们中间,有一项联通式的工作,就是田野民俗志。”[4]13-14“它的存在还是一种标志,可以从一个角度,展示民俗学的学科理念和现代视野。”[4]3
至于民俗志和民族志的区别和联系,董晓萍站在当代的时代语境和构建学术平台的立场上,更强调相互借鉴[4]37:“新民族志借鉴民俗学的成果,可以利用民俗学的本土传统和优势积累,少走弯路,集中学术研究的注意力,并能学习用局内人的眼光去阐述和撰写民族志。民俗学界借鉴新民族志的理论和方法,可以学习用局外人眼光去有距离地认识本土民俗和民俗学史,开阔视野,发现问题,也增加让别人了解自己的主动意识。”这段话值得细细推敲。首先相互借鉴说并不算新颖,但是仔细阅读会发现她提出各自借鉴对方的因素是不一样的。一个借鉴成果,一个借鉴理论和方法。由此来看她也认为田野民俗志在理论范式上势弱,但是她也提醒了我们田野民俗志“局内人”眼光的重要性,“本土传统”的重要性。其次,她也谈民俗志和民族志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之间的族群关系的不同,但是她谈差别是为了讲“相互借鉴”而不是强调区分。在她看来,这个差别在学术认识层面上的显现是两种田野作业碰撞的结果,这个差别让本来自足于各自田野研究成果的学者发现,无论是民俗志的还是民族志的田野作业,主体与客体间的固有关系都会给主体的调查带来认识上的盲点。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董晓萍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相互借鉴,在田野研究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不同视角的碰撞,以期最后的研究成果获得多维、多元的认识角度。
从这个角度解读董晓萍的著作,我认为就树立田野民俗志的本体性而言,她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学者反观和民俗认同。学者反观是一种具有研究规范性质的概念。董晓萍提出新一代学者站在当代的立场上反思研究传统,认为老一代学者的民俗资料采集工作“都是以民俗学者自己的观念为主”,而在当代,“民俗收集工作的结果,应该是民俗被记录在搜集者的学术档案里、与民俗被保存在‘民俗承担者’的头脑里,两者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检验民俗学者把一种事实当作民俗的时候,是怎样去描述和撰写它的过程,是考察这时民俗在民俗学者的眼里被看成是什么和可能不被看成是什么。”[4]40具体到研究工作来讲就是意识到学者的自身观念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田野研究成果的品质。这就是学者反观。至于民俗认同则是涉及研究取向的概念。其实“认同”在民俗学中不算一个新颖的概念,但是在当代的学术立场上它是有当代内涵的,通过比照新老两代学者的工作原则和方法,提出在今天民俗认同不仅仅意味着肯定民众认同自身文化传统这个概念,更重要的是解读民众“认同的过程、观念和产品”[4]43。就民俗田野工作而言,其意义在于在传统分类表格式的调查方式中植入了新的问题意识,使得实地调查从单纯田野搜集转变为田野研究,时刻关注民俗的传承和变迁。新民俗志理念类型的研究成果有三元论现代民俗学理论[5]74-75视野下的水利民俗志撰写《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①详见: 董晓萍, [法]蓝克利. 不灌而治: 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以及新型民俗资料的撰写《碑刻民俗志——北京旧城寺庙碑刻民俗分析及其数据处理》②详见: 鞠熙. 碑刻民俗志: 北京旧城寺庙碑刻民俗分析及其数据处理[D].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7.。
(三)“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文化志
还有一部分学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语境里,开始撰写具有普及民俗学理念意义的系列民俗志,面向大众介绍传统民俗文化,说明民俗文化与我们今天生活关系的意义。比如刘铁梁进行的“中国民俗文化志”工程——《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门头沟区卷》③详见: 文献[7].和《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宣武区卷》④详见: 刘铁梁. 中国民俗文化志: 北京宣武区卷[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这是“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项目之一,任务是以县、区为地域单位,对全国的民俗文化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普查和全面的记述。这样一个大型的普查项目,选择被记录文化事象的理论依据,以及记述方式选择的理论依据,都是具有鲜明学术意义的问题。刘铁梁将这套志书的书写模式命名为“标志性文化统领式”,其定义是[7]8:“对于一个地方或群体文化的具象概括,也就是从生活文化中筛选出来的体现一个地方文化特征,包含丰富与深刻意义的事象本身。它一般是不同程度地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一,能够反映这个地方特殊的历史进程,代表这里的民众对于自己民族、国家乃至人类文化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二,能够体现一个地方民众的集体性格、共同气质,具有薪尽火传的内在生命力;三,这一文化事象的内涵比较丰富,深刻地联系着一个地方社会中广大民众的生活方式,所以对于它的理解往往也需要联系当地其他诸多的文化现象。”
上述三个原则的订立顺序和内容是值得分析的。首先,他确定的顺序是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历史认同、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社会认同、地方文化的自我认同。这三个认同赋予了民俗地方性特征概念以新的内涵,体现了对民俗在现代社会发挥文化整合、社会稳定以及精神传承作用的关注。其次,将传承主体而不是传承事象作为进行选择的视角,将生活的有机联系整体而不是被分割成文化类别的单个事象作为描述的对象,符合当代将民俗还原到民众生活中去研究的总体取向。至于具体的记述方式,这个模式特别提出的是“尽可能使用鲜活的民俗语汇,最好结合集体生活事件和个人经历的叙述等个案材料,对重要民俗事象进行深入的叙述,做到既能见事又能见人”[7]10。这显示出对民俗志记录语言的新追求,既不同于以往解说词式的民俗说明,也不同于田野研究报告似的民俗阐释,而是叙事式的写民俗。
四、研究领域的创新之一:历史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
从学科身份的独立到学术品质的创新,中国学界除了探讨学科性质和民俗志理论外,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分支学科的成立和发展。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学科身份独立过程中,划定研究领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随着研究朝向更广更深领域的拓展,随着学科间交叉研究的普遍化,民俗学科内部也开始出现了产生分支学科的可能,尤其是传统根基深、研究积累相对丰厚的领域,比如历史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
(一)呼之欲出的历史民俗学
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在研究实践中,中国学界很早就解决了民俗学要“重史”的问题。关于建立“历史民俗学”的设想和理论依据的讨论也很早。近年来,随着有目的、有计划的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作为民俗学分支的历史民俗学已经呼之欲出。2002年历史学出身的民俗学者萧放就曾撰文总结前人的历史民俗学的经验[8],2009年的民俗学年会又有专文正式立论创建新分支学科,系统地界定历史民俗学的定义、范围、特征和研究方法等概念[9]。
站在分支学科体系的角度来审视历史民俗学类论著,归纳起来有三种新取向值得注意。第一,建立新的民俗史资料体系。中国是文献大国,历史上就有不少记录、记述民俗的史书、志书和类书。但是缺乏当代学者撰写的基于现代民俗学理论框架的民俗史。近年来这方面有重大突破。首先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先秦史学者晁福林的《先秦民俗史》,填补了民俗断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空白。紧接着人民出版社 2008年出版由多学科多位学者参与撰写的六卷本《中国民俗史》,这是一个以国家、民族为整体编写的民俗史,与面世的各类社会风俗史著作相比较,这部丛书中按照民俗学理论框架对民俗事象进行分类描述,同时兼顾表现不同类型事项反映出的共同民俗特征。另外同年杭州出版社还有一部新的地方民俗史出炉,即陈华文的《浙江民俗史》,这是当代不多的地方民俗通史类著作。第二,对古典文献进行民俗学视角的系统梳理和分析,总结本民族历史上对于民俗的理性认识。这方面的研究选题大多具有开创意义。比如对中国最早的一部专门记载古代岁时风俗著作的研究①详见: 萧放.《荆楚岁时记》研究: 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念[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对中国最早的百科全书式地理书《山海经》的研究②详见: 刘宗迪. 论《海外经》与《大荒经》与上古历法月令制度的关系[D].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1.,对位列中国二十四史之首的史学名著《史记》的研究③详见: 郭必恒.《史记》的民俗学研究[D].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2.,对中国古代重要典章制度选编著作《礼记》的研究④详见: 武宇嫦. 礼与俗的演绎: 民俗学视野下的《礼记》研究[D].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7.。另外关于风俗的通论或者地方风俗志的专题民俗文献研究也在以硕博论文的方式有指导地进行着。第三,构建新的民俗文献史。民俗文献史的传统做法是借助于史学界的历史分期,对不同时期里有关风俗或民俗的记录和评论进行梳理和总结,从中勾勒出民俗学史的脉络。现在出现了另一类回应社会发展需要,带有应用民俗学意味的民俗文献史研究,比如 2007年黎敏的博士学位论文《建国初十年(1949–1959)民俗文献史》⑤详见: 黎敏. 建国初十年(1949–1959)民俗文献史[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8.。其理论依据是民俗不仅仅是民众日常生活中无意识地发生和进行着的具有模式性的部分,而且是被社会各阶层和知识界一起根据时代需要有意构建的、用来维护社会的稳定性和显示文化的延续性的文化产品。从这个角度构建新的民俗文献史,展现不同历史时期在创建社会和谐中利用和构建民俗的理念和方式。新研究选择的时间段远远短于以往的研究,主线不是文献本身,而是社会事件,更近距离地关注在社会事件中民俗文献的形成过程和产生的社会效应。
(二)老树新枝的民间文艺学
如果说历史民俗学在中国学界的成立是呼之欲出、水到渠成的,那么今天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则可以比喻成一棵发出新芽的老树。现代中国民俗学的萌芽就是从民间文艺的研究开始的,而且由于特定的社会背景在很长一段时期只有民间文艺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民俗学的整体研究却是停滞的。在那一段时期里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关系表现为将民俗作为民间文学语境进行研究,但根本上还是一种文学的研究、文本的研究。发展到今天的民间文艺学拉近了跟民俗学的距离,其重要转折点在于认为:民间文艺,包括神话、传说、故事这类口头民间叙事,其传承的核心不在于文本,而在于文本讲述活动,在于讲述活动发挥的维系社会运作秩序的途径和功能。这样的认识在中国学界占了上风,来自西方民俗学界的表演理论、口头诗学理论很快传播开来,同时也出现了对传统理论当中有关故事讲述和故事传承人研究的再认识。如此一来,民间文艺学的研究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就有了明显的不同,而真正成为一类民俗事象被描述和阐释。其表现概括起来有两个领域值得关注①参见: 祝秀丽. 辽宁省中部乡村故事讲述人活动研究[D].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2002; 林继富. 民间叙事传统与故事传承: 以湖北长阳都镇湾土家族故事传承人为例[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西村真志叶. 日常叙事的体裁研究: 以京西燕家台村的“拉家”为个案[D].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7.。一个是以故事传承人或讲述活动为主体的新研究,表现出两个共同的视角取向转变,一是以村落为范畴对故事家和故事的讲述进行中观的研究;二是将故事传承中的个人因素、个体性的表现还原到讲故事的活动中去认识,将故事的讲述活动还原到民众生活过程中去认识。具体研究的新动态有:关注社会制度变动对讲述活动的影响;研究讲述活动过程听讲之间的互动;将当地人的日常说话作为民间叙事的原生态,重新提炼故事的讲述体裁。再一个是借鉴口头诗学理论的中国史诗研究。当今中国民俗学界各领域研究的一个共识是必须通过田野的现场观察获得对民俗事象包括民间口头叙事的活态认识。这样当口头诗学学说一经引入就受到了普遍的关注。但不同的是,大多数新近的研究学说仅仅在意识层面上发生影响,真正利用其理论模式进行模仿研究的很少,而口头诗学的借鉴则不一样,它依托于中国史诗界真正走入了中国学界,同时中国史诗研究也开始成为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领域,不仅有专门的译著②详见: [美]约翰·迈尔斯·弗里. 口头诗学: 帕里-洛德理论[M]. 朝戈金,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而且有全面的介绍性论著③详见: 尹虎彬. 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另外还有双方学者、机构上的机制化合作和共同研究课题开展,而且已经产生了中国模式的研究成果④详见: 朝戈金. 口传史诗诗学: 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0.。
作为中国民俗学界发展较早、成果相对丰富、积累相对深厚的领域,民间文学的研究这两年还出现一些“大作”,或者回顾学术史,温故知新;或者在理论建构相对稳定和成熟的学说领域,整理和书写成研究型资料分析著作。其中有四类新成果值得评说。一是民间文学学术史的梳理,比如刘锡诚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⑤详见: 刘锡诚. 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6.,评述百年学术史,资料翔实、细致,评介中肯、深入,不啻为民间文学理论史的典范著作,具有填补空白和研究示范的重大学术意义。二是故事类型学领域祁连休编纂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三卷本)⑥详见: 祁连休. 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上, 中, 下) [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7.,故事史领域顾希佳的《浙江故事史》①详见: 顾希佳. 浙江故事史[M].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8.。祁作仅仅是在分析工具的层面上借鉴了传统的类型学理论,实际操作中没有采用任何一种现成的“分类法”。我认为在强调民俗学中国立场的今天,祁连休的集大成工作给予学界的启示是民俗学的中国立场不仅仅是一种观念,更是一个学术实践,它需要切实的研究成果去展现中国学者站在当代立场上对本国文化的整理和理解。顾希佳是浙江民间文学研究的专家,代表着在学科理论框架下立足于地方资料的研究取向。顾作是中国首部地方民间文学史,以时代和关联文化事项为主线分章架构,以体裁和母题为横线分节铺成,完成对一地民间文学历史全貌的细描。三是神话学领域吕微的专著《神话何为——神圣叙事的传承与阐释》②详见: 吕微. 神话何为: 神圣叙事的传承与阐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如果说祁连休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工作是完全站在中国资料立场上进行的,那么吕微的中国神话起源研究则是借助西方学说的理论工具,利用中国的材料,为神话学的研究提供一个立足当代的阐释。吕微研究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在基于文本内容的研究中引入多学科的知识体系,显示出当代民俗学研究中的跨学科视野具有普遍意义。四是以单一故事类型为对象的专题研究,我特别想介绍陈岗龙的《蟒古思故事论》③详见: 陈岗龙. 蟒古思故事论[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和祁连休、吕微一样,陈岗龙在研究中立足于民间文学传统研究领域和方法,这不仅是他研究的起点也是研究的主体。但是当今民俗学界田野作业几乎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因素,他也不例外地在进行文献资料分析的同时采用了这一方法而给自己带来理念上的重要收获。在这部著作里传统的故事起源、功能和形态研究,与故事文本流传、说唱艺人及其表演的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其做法在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的结合上有研究范式意义。
五、研究领域的创新之二:节日文化研究和民间信仰研究
下面要谈到的是中国民俗学在完成经世济民的当代命题中凸现出来的两个研究热点:节日文化和民间信仰。它们都与一个社会实践有关,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学科的当代立场是近年来中国学者探讨较多的一个问题,而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扩展,民俗学者将回应锁定在这个社会实践当中,除了参与政府主导的实际工作外,积极探讨和提出学理上的依据,以期在理性地推进这项工程的同时抓住时机发展民俗学的理论,其核心是回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中国社会重构的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代表的地方文化、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复兴问题。这时复兴和重建中最为突出的两个领域节日文化和民间信仰进入了民俗学者的理论视野。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在学界不是新鲜事,但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深入,它逐渐上升为当今民俗学的核心议题,打开了原本局促的研究视野,在研究理论和资料建设上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一)节日文化研究的新命题
在传统民俗学构架中节日文化的研究主要属于岁时民俗的范畴。节日问题成为当代民俗学研究中的弄潮儿并不完全是学者追求的结果,而是时代思潮和包括基层大众在内的社会力量共同合力的结果。具体来讲,首先是社会自身产生了通过传统节日的新生来构建当代公共文化时空的需要,接着通过敏锐的学者和政治精英的呼应和力促,传统节日正式登上了当代代表性文化的舞台,成为国家时间制度中的重要角色。在这个实践过程中,民俗学者积极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发展了自身理论的阐释力。打开研究视野的标志性事件是 2005年中国民俗学会和北京民俗博物馆联合召开的第一届东岳论坛暨“民族国家的日历: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国际研讨会”和同年9月中国民俗学会下属机构召开的“乙酉中秋论坛”。2006年和2007年又分别召开了第二届和第三届东岳论坛,主题分别是“中华民族新年的庆典与习俗”和“文化空间——节日与社会生活的公共性”。这些前沿性的研讨相对固定和具有延续性,吸纳了多种学术资源的参与,使得传统节日的研究本身广泛化、深入化和现代化,同时民俗学理论的应用得到了深化。
需要多加说明的是,除了理论探讨外还出现了两类新的研究成果。第一是文化志书类的系列传统节日民俗志撰写,比如 2009年三联书店的《节日中国》系列丛书,撰写者均为民俗专业的学者,他们结合史志文献和地方节俗调查报告,按照溯源和分项节俗深描的方式展开叙述,向社会大众提供认识传统节日文化形态和意义的普及性读物,为这类节日的公共化提供理论支援;第二是开辟“岁时节日”研究的专门领域,比如已经有学者撰文梳理 1980年代以来的岁时节日研究学术史[10]。
(二)民间信仰研究的新动向
民间信仰是中国民俗学界当代立场下选择的另一个提升阐释力的研究领域。它被选中的代表性学术事件是“海峡两岸民间文化学术论坛”。这个论坛是近年来中国学界较具分量的研讨会。首届举办于 2007年,主题是“中国民间文化研究的新视野”,研讨并非具体个案交流,而是就当前社会巨变期民俗学的理论应对进行认识上的沟通,寻找并促成今后具体领域里的合作研究。首先被选中的就是民间信仰。2009年第二届论坛的中心议题是“文化传统与民间信仰”。这个题目本身蕴涵了中国学界当下提出和探讨这个问题的理论出发点。首先是文化传统问题。学者们提出近代以来知识界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是有很大偏差的,甚至是有偏见和谬误的,突出表现在对民间信仰的界定和社会功能的认识上。近年来的传统文化复兴热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现象却恰恰又是民间信仰的全面复兴,比如重建民间庙宇、恢复民间仪式活动、重新传讲各种信仰故事等等。如何反观学术界对民间信仰界定和阐释的政策影响和社会影响,如何为民间信仰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复兴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持,由此提升民俗学的当代阐释力,成为民间信仰研究当下热的必然性所在。
和节日文化新研究一样,民间信仰领域本身也是研究传统的,但有待于站在新立场和视野下的反观。有的学者从这样的角度提出了问题[11-12]。有的学者则是从政策导向和文化建设的角度提出加强民间信仰的调查研究,重新衡量其在一个社会文化建构中的地位和价值[13-14]。不过与节日文化新研究不同的是,这个领域研究的新思路提出略晚,尚待时日去具体化和深化。
六、结 语
综上所述,从时代语境、学术语境和研究者主体意识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今日中国民俗学的研究趋向可以归纳为传承经典和知识创新两大主题。
所谓传承经典指的是站在当代立场上的中国学者虽然看到了以往理论框架不适应于当下国际视野、跨学科发展趋势的需要,但是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也认识到这个传统框架奠定的中国民俗学基础是深厚的。如果轻易地抛弃这个传统,那么我们的研究将离民俗学的主体性越来越远,以至于被涵盖到其他学科中去。因此他们充分肯定传统理论的历史合理性,然后站在学科主体性的立场上,根据今日的社会需要提出新的理论框架。前面已经谈了很多创新点所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加强民俗学的主体性并不是一种浪漫主义情怀的呼唤,而必须是继承的创新。今日中国学界如果轻易地抛弃学术传统无异于放弃站在巨人肩上的可能,而只有站在前人奠定的基础上才可能真正发展出巩固学科主体性的新学说。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认为今日的传承经典有两个表现,一是传承传统理论;二是立足于传统理论框架完成新时代的资料研究体系工作,比如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中国民俗史的当代撰写等。
所谓知识创新当然指的是在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上的新主张、新学说。在这里特别要补充说明的是一些看上去相对偏激的批判理论,虽然对待学术传统的态度不够中允,但是过激的论点却起到了刺激学界反思学科理论生命力所在的积极作用。除了正文中分论的新领域开辟外,这里还可以归纳出一些中国学界的新共识,比如关注社会结构变动对于民俗传承和变迁的影响。再如重新从书写与口传双重性的角度,还原民间文献的流传原生态,建构分析活态性的民间文献的研究模式等。另外创造当代书写民俗的模式,也是今日中国学界知识创新的重要领域。
总之,当代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表明,社会思潮为民俗学的诞生创造了理论生成的土壤,同时民俗学的研究也必须具备推动社会思潮发展的力量才能具备旺盛的生命力。我认为具有创造性和推动作用的阐释力不仅是民俗学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更是民俗学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所在。作为一门传统学问,民俗学的兴起大多与文学和历史学相关,而随着时代和这门学问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现代民俗学者关注到民俗和现代化的关系,中国也不例外。认识到这一点的学者一方面紧密地和传统民俗学重视的“传统”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密切与迅速变化着的当代社会相联系,直面现代化给我们的社会和生活提出的问题。虽然这些学者的学术背景各不相同,但是笼统地来看有一个共同点是从社会科学的视角来描述和阐释现代民俗,发展出具有推动力的学术主张。目前我们还非常缺乏的是充足的具有研究范式探索意义的研究成果。换句话说,我们还有待于在民俗学的不同领域里构建起新视角立场下相对成熟的研究概念体系和分析模式。
[1] 吕微. “内在的”和“外在的”民间文学[C] // 周星. 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94-116.
[2] 高丙中. 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3] 高丙中. 日常生活的现代与后现代遭遇: 中国民俗学发展的机遇与路向[J]. 民间文化论坛, 2006, (3): 6-14.
[4] 董晓萍. 田野民俗志[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5] 董晓萍. 现代民俗学讲演录[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6] 高丙中. “民俗志”与“民族志”的使用对于民俗学的当下意义[J]. 民间文化论坛, 2007, (1): 23-26.
[7] 刘铁梁. 中国民俗文化志: 北京门头沟区卷[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8] 萧放. 历史民俗学与钟敬文的学术贡献[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2, (2).
[9] 萧放. 历史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刍议[EB/OL]. [2009-11-16]. 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NewsID=6263.
[10] 萧放, 吴静瑾. 中国岁时节日研究综述(1983–2003) [C] // 中国民俗学会. 民俗春秋: 中国民俗学会20周年纪念文集.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6: 334-362.
[11] 高丙中. 30年的民间信仰表述路向: 从他人的传统到自我的文化[EB/OL]. [2009-09-22]. 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NewsID=5865.
[12] 赵世瑜. 民间信仰研究如何推进? : 对近期关于华琛“神明标准化”的讨论之反思[EB/OL]. [2009-09-22].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NewsID=5864.
[13] 萧放. 文化遗产视野下的民间信仰[EB/OL]. [2009-09-22]. 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NewsID=5878.
[14] 叶涛. 民间信仰的当代价值刍议[EB/OL]. [2009-09-22]. 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NewsID=5876.
New Review on Recent Trends of Folklore Studies in China—— Examining From Two Contexts and One Awareness
PANG Jianchun
(Divi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Hongik University,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121-791)
In this paper, the recent trends of the Chinese folklore studies were carefully stud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xt of the time and the academia and problem awareness of scholars.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from discipline identity establishment to updating of academic research area, the folklore studies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a is experiencing, was proposed to further evidence the two main features,inheritance of classics and innova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review, the Chinese folklore studies circle’s proposition, establishing and developing the Chinese folklore studies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science,was mentioned firstly. Then, the new theory of fieldwork reports introduced by the Chinese folklore studies circle was commented. And last but not the least, the new trends existing in fields like historical folklore, folk literature and arts, traditional festivals and folk beliefs were studied.
Folklore; Social Science; Contemporary China; Fieldwork Reports; Historical Folklor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编辑:赵肖为)
C953
A
1674-3555(2011)03-0049-13
10.3875/j.issn.1674-3555.2011.03.008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2010-11-27
庞建春(1974- ),女,四川成都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民间文学
特约栏目主持人语·Words from Special Column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