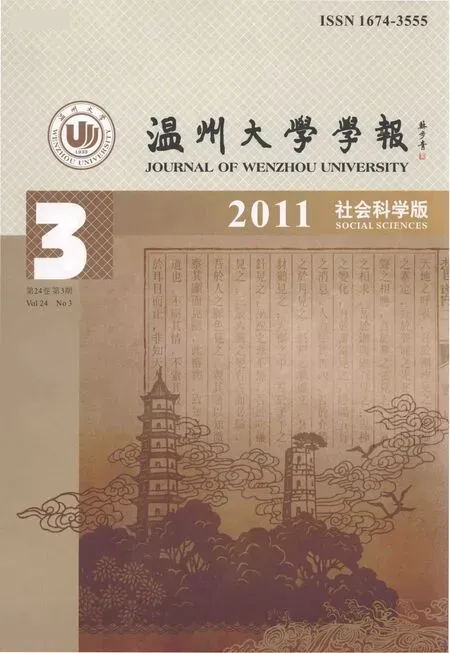智者想象: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王小波与鲁迅想象精神之比较
2011-03-19童志祥
童志祥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智者想象: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 王小波与鲁迅想象精神之比较
童志祥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王小波的后期创作逐渐从《黄金时代》、《青铜时代》中的顽童想象走向《白银时代》中的智者想象。随着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理性多于感性,观念大于形式,其想象精神也由起初卡尔维诺式的“轻逸”逐渐嬗变为鲁迅式的“凝重”。尤其是在受虐倾向、孤独情结、悲观意识等三个方面,王小波小说创作中(尤其是后期小说)的想象精神与鲁迅在《野草》中的想象精神,显然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王小波;鲁迅;想象精神
长期以来,学界对王小波和鲁迅之间的比较研究并未予以足够的关注。已发表的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中,论者基本上都聚焦于王小波和鲁迅身上所体现出的“文化批判意识”,或更多地强调他们作为“智者”的愤世姿态和反叛精神。如有论者认为,“从鲁迅到王小波,贯穿的是20世纪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特有的文化批判意识以及‘文化-国民性’主题。”[1]另有论者则直接以“文化批判意识”为线索,将王小波与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两个独特的个案来比较,认为“他们坚持独立撰稿人的自由立场,以犀利的杂文和批判意识的小说著称于世”[2]。然而,除了鲜明的批判意识之外,我认为王小波与鲁迅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相似之处,即他们在创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想象精神。事实上,王小波和鲁迅都属于那种想象力无与伦比的作家。对王小波来说,想象天赋无疑就是一对灵动的翅膀,他常常驾着这对翅膀扶摇直上九重天,彻底沉浸在自我欢腾的愉悦中。就像一个小孩举着纸飞机迎风奔跑一般,他所追求的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有趣,小说创作成为摆脱尴尬现实的最佳手段。想象的世界,成为他拒绝庸俗的最后一方乐土。至于鲁迅,他似乎是将想象天赋化作了一柄利铲,直掘自己的灵魂深处。《野草》①参见: 鲁迅. 野草[C] // 鲁迅. 鲁迅全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下文论及该作品, 均出自同一版本, 不再一一作注.便是这种想象精神的结晶。
尽管王小波和鲁迅的想象精神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骨子里,他们却是“殊途同归”的。笔者将从受虐倾向、孤独情结、悲观意识等三个方面来具体比较王小波小说创作中(尤其是后期小说)的想象精神与鲁迅在《野草》中的想象精神,以厘清两者之间存在的一脉相承的关系。
一、受虐倾向
关于鲁迅作品中的受虐意识和自虐倾向,近年来,已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虽然鲁迅小说中有诸多被迫害妄想和受虐倾向的人物,如阿Q、祥林嫂、吕伟甫和魏连殳等等,但他们基本上都属于鲁迅笔下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角色。在我看来,最能反映鲁迅个人心理特征的作品还属《野草》。而在《野草》中,同样有着许多关于受虐或自虐场景的想象。一般来说,鲁迅笔下的受虐形象可以概括为两大类:一类属于被迫害被欺凌且麻木不仁的弱者形象,鲁迅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都属于这一类;一类属于以牺牲自我与敌偕亡的报复者形象,《野草》中所塑造的主要是这类形象,恰如鲁迅在《野草》题辞中所刻画的“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在这里,“野草”以自我毁灭的方式暴露地面的丑陋,便是一种典型的自虐式报复精神。而在《复仇(其二)》一文中,受难的耶稣扮演的正是这种牺牲者的形象。无知愚昧的以色列人残忍地谋杀了自己的“救世主”,而“救世主”也以自身的牺牲,使得那些愚蠢的人们堕入生命的苦海,并永世不得超生。事实上,正如吴俊先生所言,“只有在牺牲者的牺牲正是刽子手的劫难之源这一意义上理解‘复仇’,才能真正体会出鲁迅为什么会把耶稣的受难称之为‘复仇’的心理动因。”[3]毕竟,倘若仅仅是牺牲的话,并不能构成复仇;只有在牺牲给对立面造成伤害时,牺牲才能成为复仇。“突然间,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看得出,“耶稣”在受刑或受虐过程中遭受的苦痛越大,他所感受到的复仇的快意也就越深。这是一种近乎悖谬的反抗,但也恰恰是最为彻底最为决绝的反抗。无独有偶,在《颓败线的颤动》里,那个最终被子女遗弃的老妇人,也是在被遗弃的同时,彻底弃绝了她的子女。类似的主题在《死火》中也有所体现,如该文结尾处:“有大石车突然驰来,我终于碾死在车轮底下,但我还来得及看见那车就坠入冰谷中。”“‘哈哈!你们是再也遇不着死火了!’我得意地笑着说,仿佛就愿意这样似的。”这种“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复仇精神,可以说是鲁迅在苦闷的彷徨期最真实的心灵写照。总之,在《野草》中,几乎所有关于受虐的想象,都是鲁迅对黑暗现实的一种决绝反抗和报复。
然而,在王小波的小说里,受虐想象始终同“施虐-受虐”模式紧密相连。至于受虐场景,要么是虐恋游戏,要么是刑场狂欢。前者如《革命时期的爱情》①参见: 王小波. 革命时期的爱情[C] // 王小波. 王小波文集: 第1卷.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下文论及该小说均出自同一版本.中“王二”同X海鹰之间的性游戏。后者如《寻找无双》②参见: 王小波. 寻找无双[C] // 王小波. 王小波文集: 第2卷.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中鱼玄机受刑的场面。无论如何,王小波笔下的受虐想象,实际上也是一种反抗,一种弱势文化对权力机器的曲折反抗。王小波的反抗逻辑是:代表着权力一方的施虐者,当然渴望看到受虐者在受虐过程中遭受痛苦并以此来彰显自己的权威,然受虐者偏摆出一副无所谓甚至嬉皮笑脸的姿态,如此一来,施虐亦或刑罚的庄严意味便被消解殆尽,作为施虐者的权力机器自然也就丧失了权威性。在《2010》中,王小波这样描写王二挨鞭刑时的感受[4]:
在X架上,最能感觉重叠自己是个造型艺术家,有丰富的想象力。比方说,有一鞭是斜着下来的,你马上变成两块硬面锅盔,或者是cheese cake,对接在一起。假如有一鞭横着抽在腰眼上,就会觉得上半身冲天而起,自己有四米多高。假如鞭子是竖直地抽下来,你就会觉得自己像含露的芙蓉,冉冉开放。
受虐者居然以一种近乎把玩的心态对待鞭刑,如此一来,整个刑罚的震慑意义也就荡然无存了。施虐者的期望落空,受虐者的反抗目的也就达到。
虽然相对于鲁迅的庄严和沉重,王小波笔下的受虐场景多了几分笑谑性质,但显而易见的是,两者的受虐想象都是以牺牲自我为前提的反抗手段。
二、孤独情结
通常意义上,智者都是孤独的,正所谓“众生皆醉我独醒,举世混浊我独清”。王小波和鲁迅都属智者,尤其对个体的生存境遇都极为敏感。正因为这份清醒,才使得他们对现实始终抱着一种拒绝的态度。而这种拒绝姿态,某种程度上也必然导致了他们被俗世排斥的不幸命运。鲁迅生前备受攻击,已是不争的事实。王小波则一直被拒斥于文坛之外,小说出版屡遭挫折。鲁迅心情寂寞时,曾一个人呆在幽僻的绍兴会馆抄古书长达数年,真的可谓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王小波本来在大学有教职,但因为不甘受体制的钳束,毅然辞职回家,埋头写作,过起了几近隐居的生活。可见,两人在生活中或多或少都有“避世”的孤独情结。当然,鲁迅最终还是将韧的战斗精神贯彻到底,即便是“独彷徨”,也要摆出“荷戟”的战斗姿态。但更多的时候,他似乎是站在同时代人无法企及的思想高度上徘徊于希望与绝望之间。至于王小波,小说成了他一个人狂欢的最佳舞台。在想象的世界里,他蔑视一切约束人性的禁忌,时而放浪,时而深沉,更多的时候是忘我地沉湎在一个自由、诗意、有趣的虚拟时空里。
正因为孤独情结在现实生活里如影相随,所以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将自身的孤独心态投影到作品中的人物身上。鲁迅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阿Q、狂人、孔乙己、祥林嫂、魏连殳等,还是大禹、后羿、老子等,都是孤独的化身。至于《野草》,可以说就是鲁迅一个人的心灵史。《野草》中的“我”,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一种孤独的情境里挣扎着。在《过客》中,鲁迅甚至还塑造了一个孤独的寻路者,“他”不停地跋涉着,即便被“老翁”告知前方只是一片坟地,“他”也要坚持往前走,因为“他”还想探索“走完了那坟地之后”的世界。显然,这位孤独的过客形象就是作者自身真实的写照。而在《死后》一文中,作者甚至连死后的孤独,都清晰地预见了。无尽的孤独让鲁迅最终在《希望》一篇中不无悲凉地喊出了一声:“我的心分外的寂寞。”
再看王小波的小说,主人公“王二”虽古灵精怪,毫没正经,但多数时候,他是孤独的。就像一个游离在现实边缘却又不怎么安分的局外人一般,他恣情嘲弄世俗的清规戒律,且常常满怀诗意渴望着一个有趣的美好世界,可问题是这个世界就像是巴比伦花园一般,始终悬浮在虚拟时空。早期的《黄金时代》①参见: 王小波. 黄金时代[C] // 王小波. 王小波文集: 第1卷.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下文论及该作品均出自同一版本.中,“王二”多少还有一个狂欢的舞伴陈清扬(小说结尾时,两个人到底还是分道扬镳)。到了《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王二”不论是和少年时认识的那位姓颜色的大学生,还是和帮教自己的X海鹰,基本上都是“貌合神离”。即便是《青铜时代》②参见: 王小波. 青铜时代[C] // 王小波. 王小波文集: 第2卷.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下文论及该作品均出自同一版本.中的李靖、薛嵩、王仙客等人物,也都沉浸在各自的孤独里。李靖后来虽然贵为大唐李卫公,且有红颜知己红拂的陪伴,但极权体制束囿了他自由的心灵,他不得不佯睡装傻来浑浑噩噩地度日,即便是在红拂面前,他也不得不装糊涂。失去自由心灵的李靖只能躲藏在一个人的孤独里度日如年。至于薛嵩,更是无法摆脱孤独的魔影。尽管身边有个红线,但他骨子里却始终有汉族的大男子主义思想,总想把这个自由的精灵给驯化掉,可问题是红线根本不吃他那一套。红线平时动辄喊薛嵩“老爷”,或自称“小奴家”,在她看来,也仅仅是出于好玩罢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薛嵩和红线之间,实际上也是貌合神离的。再看王仙客,直到小说结束,也没有寻到无双,其孤独自不必说。
如果说王小波早期小说中人物的孤独情状还不够明显的话,那么到了《白银时代》①参见: 王小波. 白银时代[C] // 王小波. 王小波文集: 第1卷.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下文论及该作品均出自同一版本.和《黑铁时代》②参见: 王小波. 黑铁时代 // 王小波. 王小波文集: 第3卷.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下文论及该作品均出自同一版本.中,孤独几乎就是小说的主人公们无法规避的生存背景了。无论是《未来世界》中的“我的舅舅”,还是《2015》中的“王二”,他们的身上几乎都笼罩着一层孤独绝望的气息。他们的命运,要么死于非命,要么被劳动改造。即便是《白银时代》里那个于 2020年时还在写作公司工作的“我”,最后也在突围无路的孤寂中变得绝望了,用小说中的话来说就是“既然生活是这样索然无味,只有想办法把它熬过去”。在王小波勾勒的未来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即便是身边的人,也毫无信任可言。比如在《未来世界》下篇《我自己》中,那个和“我”住在同一个房间的女人竟然是“社会治安公司”派来暗中监视“我”的特务!在这样的环境里,人物身心所遭受的孤独境遇也就可想而知。
总而言之,孤独,可以说是王小波和鲁迅的想象精神共通的情结。如果说有不同之处的话,那就是鲁迅笔下的孤独,是“静”中的孤独,而王小波笔下的孤独,却是“闹”中的孤独。它们虽“静”“闹”有别,却殊途同归。基本上都是作家对现实的一种倔强的拒斥和反抗。毕竟,有时候,孤独也是洁身自好者的一方灵魂栖息地。
三、悲观意识
王小波和鲁迅有相似的学科背景,一个工科出身,一个医科出身,鲁迅学医前还曾在南京矿务铁路学堂学过地质学。此外,两人都有留学海外背景。他们都具有很强的科学理性精神。尽管身处不同时代,但都经历过社会浩劫,以致两人都对中国封建文化中压抑健康人性的忠孝意识和愚昧思想极为反感。五四时期,鲁迅声嘶力竭地诅咒过“孔家店”;20世纪90年代,王小波亦对孔孟文化不屑一顾。鲁迅究其一生都在反抗专制统治,也为广大国民身居黑暗而不自知的麻木感到痛心;20世纪末,王小波也以自己的文革记忆为背景,纵情戏谑权力话语,极力呼唤个体尊严,以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勾勒出一道道充满趣味和诗意的文学风景。
之所以在此不厌其烦地列举王小波与鲁迅的相似处,就是为了引出两人骨子里具有相通的悲观意识这个话题。前文中我们已经指出,王小波和鲁迅在各自的时代里,几乎都属于那种孤独的反抗者。这一点,在鲁迅身上表现得尤为强烈。他是一位超越了时代的伟人,然而先知先觉注定只能与孤独结下不解之缘。尤其是民众的愚昧更使他感到了思想启蒙的沉重困难:中国实在是太难以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几乎也要流血。因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5]尽管他曾声嘶力竭地呐喊,并以战士的姿态向黑暗的社会扔去“投枪”和“匕首”,可遗憾的是,鲁迅最终还是发现,自己的力量是多么的软弱和渺小。一种“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痛苦和绝望如同毒蛇一般缠绞着他。以至于在《复仇(其二)》中,他不得不借受难的耶稣来宣泄心中的悲哀、孤独和愤怒:
四面都是敌意,可悲悯的,可咒诅的。/“我的上帝,你为甚么离弃我?!”
而在《希望》一文中,鲁迅甚至引用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话来表达自己的心声:“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是一种极其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觉得希望渺茫;另一方面,他又不甘心于绝望,对绝望也产生怀疑。这使得鲁迅一度成为悲观的怀疑论者。在《影的告别》中,鲁迅这种否定一切的态度更为决绝:“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尽管《野草》几乎通篇都弥漫着一层悲观绝望的阴郁基调,但我们仍不能据此便认为鲁迅是个消极虚无的人。事实上,纵观鲁迅一生,他都在实践着韧的战斗精神,几乎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对黑暗势力的诅咒和攻击。在我看来,《野草》中的悲观意识,实际上反映的正是鲁迅的理性。他清醒地意识到了通往光明之路的艰辛。茫茫黑夜无边无际,他只不过不愿像某些自欺欺人的家伙借助空虚的幻想来麻醉自己,他只不过是想让自己更冷静地面对现实的苦难和前途的迷茫而已。虽然有时候,鲁迅也会情不自禁地做些美丽的梦,譬如《好的故事》中所描绘的绚丽图景。但梦终归是梦,终归是要醒来。这点,鲁迅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说到底,这就是一种现实主义精神。保持清醒的目的,归根结底是让自己保持最佳战斗姿态,随时向黑暗阵营发起猛烈攻击。
“但我总记得见过这一篇好的故事,在昏沉的夜……”我想,在无边的暗夜里,这既是一种告慰,也是一种激励。我想,《过客》中的那位过客之所以会近乎固执地坚持走下去,恐怕也是心中始终深藏着一个“好的故事”吧。如果说这不是希望,那么希望又是什么呢?
尽管王小波因个人的偏好,作品不像鲁迅那样充斥太多的政治意识形态,并且两人对现实的反抗姿态也天壤有别——鲁迅是直接同“暗夜”肉搏,而王小波则以戏谑的姿态调侃现实。但他们反抗现实和追求个体尊严的信念是一致的。只不过,王小波的勇气更多体现在以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对权力话语进行挑战。然而,跟鲁迅一样,王小波无法摆脱现实环境的压抑,更无法凭一己之力改变社会。王小波曾在《茫茫黑夜漫游》中引用塞利纳的诗句[6]:
我们生活在漫漫黑夜,/ 人生好似长途旅行,/ 仰望天空寻找方向,/ 天际却无引路的明星。
现实中无力突围,王小波只能在想象的时空里实践暂时的狂欢,然而,理性的精神又使得他总是在沉迷的同时保持了一份清醒,这就是他的小说为什么总有个阴郁尾巴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到了后期创作,他对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反思仍基本停留在“文革”时期的感性记忆,未能“与时俱进”,使得他轻盈的想象逐步被“刻意为之”的寓言化倾向所束缚,小说的整体风格也因此无可挽回地滑入了难以稀释的悲观情境之中。当然,如同鲁迅将自己视为茫茫黑夜中的过客一般,王小波也曾以行吟诗人自比。在此,不妨引用他在《三十而立》中写过的一段话[7]:
在这种夜里,人不能不想到死,不能不想到永恒。死的气氛逼人,就如无穷的黑暗要把人吞噬。我很渺小,无论做了什么,都是同样的渺小。但是只要我还在走动,就超越了死亡。现在我是诗人,虽然没发表过一行诗,但是正因为如此,我更伟大。我就像那些行吟诗人,在马上为自己吟诗,度过那些漫漫的寒夜。
可见,王小波其实懂得在现实的悲剧中提炼诗意。就像“过客”心中始终珍藏着一个“好的故事”一样,这种悲观但不绝望的想象精神,正是“暗夜”里的探索者们永恒的信念和动力之源。
四、结 语
王小波并非始终沉迷在想象的世界,事实上,他的小说自一开始就充满了人文关怀,这一点甚至可以追溯到他最早的作品《绿毛水怪》①参见: 王小波. 绿毛水怪[C] // 王小波. 王小波文集: 第3卷.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主人公妖妖最后皈依的那个充满自由和趣味的海底世界,无疑是对现实世界的荒诞无趣最好的反讽。不论《黄金时代》,还是《青铜时代》及后来的《白银时代》、《黑铁时代》,王小波的小说始终有个不变的主题:个体尊严在权力话语统治下的现实环境里如何才能得到充分保障?他认为只有个体尊严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才是健康的社会,才是充满诗意、自由和趣味的社会,而这样的美好图景正是王小波在想象时空里孜孜以求的理想国度。显然,王小波探讨的仍是一个棘手的现实问题。正因为太过于现实,所以王小波的想象才不可避免地多了一份沉重,而正是这份现实关怀的沉重,直接导致了最终与鲁迅殊途同归。
王小波注定无法走出一条开满牵牛花的“竹篱笆路”[8],也许他不愿承认,但最终还是走了安徒生所谓着火的荆棘路,就像当年的鲁迅一样,最终光荣地倒在了为自由摇旗呐喊的征途上。
[1] 丁琪. 鲁迅的文化批判及为当代提供的文化参照意义: 鲁迅与王小波及王朔[J]. 社科纵横, 2000, (5): 64-65.
[2] 房伟. 从强者的突围到顽童的想象: 鲁迅与王小波之比较研究[J]. 文艺争鸣, 2003, (5): 0-54.
[3] 吴俊. 暗夜里的过客: 一个你所不知道的鲁迅[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6: 99-100.
[4] 王小波. 2010 [C] // 王小波. 王小波文集: 第3卷.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550.
[5] 鲁迅. 灯下漫笔[C] // 鲁迅. 鲁迅全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212.
[6] 王小波. 茫茫黑夜漫游[C] // 王小波. 王小波文集: 第3卷.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329.
[7] 王小波. 三十而立[C] // 王小波. 王小波文集: 第1卷.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110.
[8] 王小波. 我的精神家园[C] // 王小波. 王小波文集: 第4卷.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311.
Wise Man Imagination: Burden that Life Could Not Withstand—— Comparison of Imagination Spirit between Wang Xiaobo and Lu Xun
TONG Zhixi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The imagination spirit of Wang Xiaobo’s later creation had transferred from the urchin imagination inGolden PeriodandBronze Ageto the wise man imagination inSilverTime. In the creation process, Wang Xiaobo gradually preferred rationality to sensibility, and value to form. In the meantime, his imagination spirit was gradually transmuted from the initial Calvino’s style of “lightness” to Lu Xun’s style of “profoundness”.Obviously, in the aspects of inclination to be abused, complex about loneliness and pessimistic consciousness,there is a successive relationship existing between the imagination spirit in Wang Xiaobo’s novels(particularly in his later novels) and that in Lu Xun’sWild Grass.
Wang Xiaobo; Lu Xun; Imagination Spirit
(编辑:刘慧青)
I206.7
A
1674-3555(2011)03-0093-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1.03.013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2010-09-15
童志祥(1982- ),男,安徽无为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