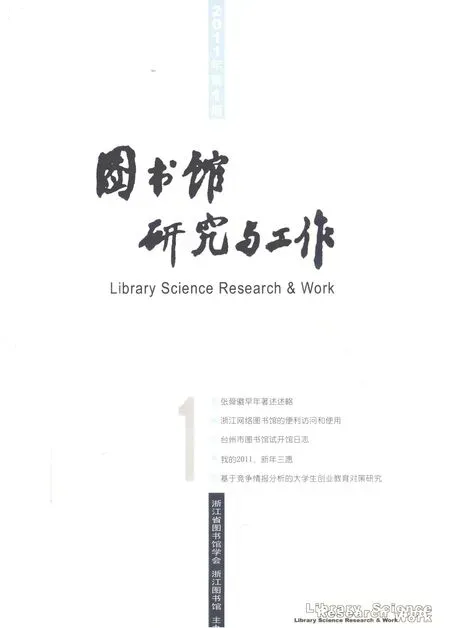毛奇龄与《金华文略》
2011-03-19李敏
李 敏
(东阳市图书馆,浙江 东阳 322100)
〔作者信息〕李敏,女,馆员,馆长助理。
毛奇龄(1623—1716)原名甡,字大可、于一、齐于,号秋晴、初晴、晚晴,清代经学家、文学家,浙江萧山人。以郡望称“西河先生”。清初举博学鸿儒,授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等职,参与《明史》修撰。后引疾归里,不复出专事著述,以辨定诸经为己任,曾称“宋元以来无学人”。学识渊博,博览群书,经学文词,各擅胜场。一生著作丰富,《西河合集》共计493卷。学者阮元称赞他对乾嘉考据之学有开山之功。
《金华文略》,清王崇炳编,二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书“编录金华一郡之文,始自汉尚书杨乔,迄于国朝徐腾,共一百一十七人,而崇炳之文亦自隶焉”。但“选汉文不及长沙家令,选宋文不及苏学士矣。故惟侧词艳语,在所禁绝。他则悉凭文章,不区疆域”。全书按照赋序碑记、辩论议跋、箴札策表、书疏传铭等文学体裁,以文取长,以文传人,撷取历代金华乡贤硕儒撰写的诗文词赋,“掌纶代草之言,刊之琬琰以为宝;纳诲陈谟之作,勒之竹素以为光”,“表彰先哲”,“表式且学”〔1〕。
文献记载,王崇炳(1653—1739)字虎文,号鹤潭,浙江东阳人,为毛奇龄入室弟子,学识渊博,但人生坎坷,举试不利,即弃举子业,专心著作,编《吕东莱先生本传》,订《(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四先生书》等,以振兴婺学为己任。康熙癸未(公元1703年),王崇炳应邀来到浙江兰溪,完成当地“好古之士”唐圯葊“综其遗文、诠次排纂”,编著地方文献《金华文略》之遗愿。康熙己丑(公元1709年),经过六年时间的努力和辛苦,其书正式编著成稿。王氏称,“敷陈道德、表彰节概、扬励风教,而一切裁之以文。盖性道者,文章之本干也;文章者,性道之葩萼也”。“理则以圣为宗,不标门户;文则以为雅为的,不列蹊途”。所以《金华文略》一书取消学术门户争端,“所重在文,而人附见,盖文而兼献也”。“因人以录文,且以文而传其人也”〔2〕。入编其书者,皆为历代金华乡贤的嘉言美文。雕版刻印之前,王崇炳请昔日恩师毛奇龄为自己的著作写篇“序”言,同时也就一些问题提出请老师指点。
接到王崇炳来信,已是八十七高龄的毛奇龄相当欣慰,寄予厚望的学生没有辜负自己的期望。《王鹤潭先生行状》称,毛奇龄十分器重王崇炳,送客“必至舟次”,并“嘱云勉旃,婺州理学复振,惟视子矣”。费平生心血撰写的《六经全集》,摒弃名家巨卿之文章不用,独取王崇炳所作之“序言”,“弁其首”,“相契孚有特深矣”。即使年至九旬耄耋之年,仍与王崇炳“书札岁往来不绝”〔3〕。所以在读了以表彰前贤先哲为内容的《金华文略》后,毛奇龄回复王崇炳的信札中,大力赞扬王氏之举,“辑乡先进文集,表彰先烈”,“总是快事”〔4〕,是一件传承地方文脉、弘扬地方文化的“不朽大业”,其文献取舍、章节删录,精确严肃,极具章法。因为王崇炳十分推崇唐仲友,誉之为两宋时“最为名家,与吕成公(祖谦)、陈同甫(亮)鼎立”,可谓“学问精博、经济通贯、一代伟儒”,但与朱熹交恶,“为朱子所排”,人与文湮灭不传,“止《(金华)文征》所载二十篇而已,今仍旧贯,不敢出入”〔5〕,全文收入《金华文略》中。好持异说而又敢于立言,曾著《四书改错》攻击朱熹《四书集注》的毛奇龄,对此更是赞誉有加,称唐仲友所著《井田纲领论》上、下二篇论文,虽然援引司马法“兵车之制”等内容有待商榷,但全文气势恢弘,论辨极至,“条理穿贯,衔接上下”,既“通乎(井田)乡遂都鄙贡助军赋之异制”,又明确授田、沟洫、税敛、兵赋、力役、畜牧、蓄毓、训农、祈报、赏罚、补助、治兵、厚俗、育材、典贤诸内涵,“条目粲然,一览可识其大”〔6〕,为“果真纯学”,唐宋以后学者无人能出其右,“宜其睥睨一切”,给予极高的评价。
至于作“序”一事,毛奇龄一开始自谦道,自己学识浅薄,孤陋寡闻,“从前搦见勤可读经史诸子,而踈可读集,且宋元以后尤为忽略,以故宗(泽)、王(祎)、陈(樵)、吴(莱)诸名集,并无遐录”,诸地方“名贤在前,实不敢窥见底里”,所以作“序”“弁言之属”,以“八十七之年,耳目心力,日败一日”,自己身体每况愈下、“日来戒为文”为由辞推之。但在王崇炳的再三请求下,毛奇龄最后还是认认真真地写下了洋洋洒洒近千言的“序言”,并就其书的取舍得失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从而为后人留下当时人称“毛字难求”的珍贵墨宝:
“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夫之杞而犹不足征,其故何也?谓夫文与献之有未备也。夫如是,则文献要矣。然而献何能征?献年不满百,而无文则亡。结绳以前,未闻能道一人也。亦有文在,而仍难征者。三代饶策书,且殷周祚长,合不下千数岁百,而人文之盛,则止《春秋》二百年,而无他闻焉。何则,以《春秋》一书,其文有定之者也,而不惟是也。予尝读江左五书,叹其人其文,何减三代,即十国棼轮其所著编年旧文,亦复如是。而修五史者,寥寥焉。此真目不见国书,所云无知而妄作也者。然且宋元各有词。宋词虽清班道学,皆有薉词存集中。而元词千本,则并当年功令,所称十二科取士之法,亦蔑之沫之。迄于今,诸词繁然,不知为何代之书,何王之文?非天降,而非地出,公然若鬼伥之游人间。则可谓信史者乎?则无征而已。金华自颜乌、许孜以后,多忠孝节烈之士,而各有文章。在唐则骆丞最著,而舒侍郎与冯节度继之,顾专以诗名。至宋元迄今,则道学如吕伯恭、经学如唐与政、史学如陈同甫,以及元之金、许,明之王、宋,辉煌彪炳,指不胜诎。文献之盛,未有若斯之盛者。然而全文未易辑,而从前会粹,若《文统》、《文宪》、《文征》、《婺书》类,又多所阙佚。王子虎文起而选定之,而唐子中舍受其尊人圯葊之遗命,而为之校录。凡夫大经大法、典礼制度,以至帝王之升降、时代之得失,或阐发理学,或表彰人物,稍有系于匡时救世之作,必概括而探存之。然且前贤不幸,有为门户所排弃而遭焚弃者,亦竭蹶搜讨,不遗余力,将所谓阐幽之功,多于纪盛者非耶。虎文父子皆有学,其文致足传,以视前贤,祗接踵闻耳。予邑多文献,而继起乏人,以萧山名邑,昉自《汉志》,而改名萧然,以唐贺学士知章,生斯卒斯者,而认作鄞人,以予先司马公作《三江水利碑记》,树之郡门,而旧时郡志并亡其文,此何为者也。夫而后,丑可知已。康熙己丑仲秋月西河毛奇龄老晴氏敬题于书留草堂时八十七岁。”
在《金华文略序》中,毛奇龄首先阐述了文献的重要性,孔子因为“文与献之有未备”,无法“观夏道”、“观殷礼”、“观周礼”,只能遗憾地感叹道,“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文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谓“要矣”。但有文无征,盲目迷信,不加鉴判,则古人文章“不知为何代之书、何王之文?”有“无知而妄作”之嫌疑,“公然若鬼伥之游人间”,害人误己,贻误后世。其次对《金华文略》的成书背景,也就是对金华的历史人文作了总结和回顾。金华一地人才迭出,文献大盛,唐有诗人骆宾王、舒元舆、冯宿,宋有学者吕祖谦、唐仲友、陈亮等,元有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金华四子”,明有开国文臣宋濂、王祎等,辉煌彪炳,留芳史册,得到中原文献之真传,形成宋元以来前后相继、文脉可寻,颇有影响力的“婺州学派”,可谓“文献之盛,未有若斯之盛”。这既是金华誉称“东南小邹鲁”的坚实基础,也是王崇炳编著《金华文略》的文化基础。充分肯定了王崇炳编著《金华文略》的历史功绩。自晋留叔先、南朝郑缉之等人以褒扬金华历史名人为宗旨,编撰《朝堂赞》、《东阳记》等地方性史书后,元吴师道、明阮元声、赵鹤等人起而继之,辑录乡贤著作,编著《敬乡录》、《金华文征》、《金华文统》等文献。由于师承不同,学识有异,各人辑录的文献长短互见,各有千秋。王崇炳“起而选定之”,“竭蹶搜讨,不遗余力”,集众人之长,摒弃学术门户之偏见,搜残辑佚,编定成书,其“所谓阐幽之功,多于纪盛者非耶”,给予充分褒奖。
美中不足,一是毛奇龄虽然盛赞唐仲友“果具纯学”,文章“条理穿贯,衔接上下,在唐宋后文人,谁有者近?宜其睥睨一切,”王崇炳“特为表出为妙”,但在撰写《金华文略序》时没有直书唐仲友其名,只是委婉地称“前贤不幸,有为门户所排弃而遭焚弃者”,说明毛奇龄仍然无法摆脱社会正统思想的束缚,不敢公开与正统的朱熹学说相抵触。二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正式雕版印刷《金华文略》时,没有采用毛奇龄书写体的“序”,仍然使用宋版体的“序”,并且改动其中的个别文字,如“合不下千数岁百“改为“合不下千数百岁”、“文献之盛”改作“东南文献”、“阐发理学“改为“剖析理学”、“有为门户所排弃而遭焚弃”改为“有为门户所排弃而遭焚灭”,让人失去一睹笔势挺拔、儒雅清奇的毛氏书法的机会。
注释
〔1〕〔2〕清咸丰年间刻本《金华文略·王崇炳叙》
〔3〕2000年出版《厚田(王氏)纪念册》
〔4〕以下毛奇龄所述诸语,均见东阳博物馆收藏的《毛奇龄信札》
〔5〕清咸丰年间刻本《金华文略》卷七唐仲友著“井田纲领论下”
〔6〕清咸丰年间刻本《金华文略》卷七唐仲友著“井田纲领论下”戚雪厓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