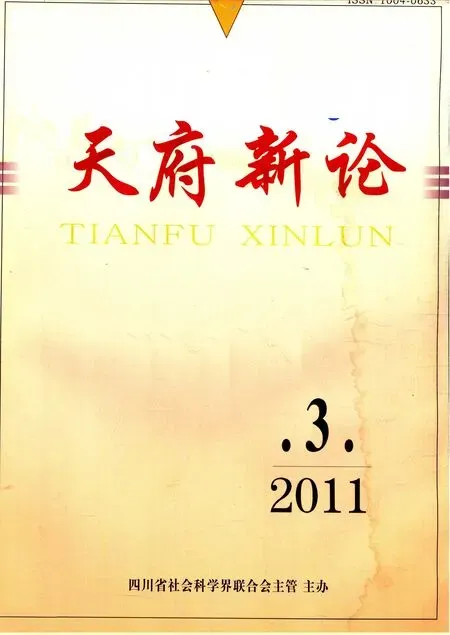自首从宽原则与量刑公正的实现
2011-03-18王燕莉唐稷尧
王燕莉 唐稷尧
自首从宽原则与量刑公正的实现
王燕莉 唐稷尧
自首从宽处罚的主要根据不是节约国家司法资源,而是行为人的自首反映出其对国家法律规范对立态度的降低和对社会的危险减少。基于刑罚正当性的要求,只有在我们能够以确切的证据证明自首犯具有掩盖罪行、逃避国家惩罚的动机的情况下,才可以对自首犯不从宽处罚。
自首;量刑;宽严相济;量刑公正;自首从宽原则
量刑,或曰刑罚的裁量,是刑事司法活动的重要环节,对已经实施犯罪者的惩罚、教育,对潜在危险分子的威慑,对守法公众的鼓励等刑罚目的最终都必须通过刑罚的裁量来实现,如何在刑事司法活动中求得刑罚裁量的公正,是刑罚目的实现的重要保证。而自首制度,是刑法体系中的一项重要而复杂的量刑制度,世界各国无不通过各种形式将其规定在刑事法律中,并运用于刑事司法实践。当一个犯罪人在诉讼中存在自首情节时,我们在司法活动中如何根据该情节给予其适当的刑罚处罚就成为影响量刑公正,进而影响刑罚目的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序论:问题的提出
我国刑法第 67条、68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刑法分则第164、390、392条规定,犯有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行贿罪或介绍贿赂罪的犯罪分子,在被追诉前自首的,“可以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根据这一规定,一般情况下,自首在我国量刑制度上只是任意从宽理由,而只有在特别条件下,才是必然从宽理由。
理论上,我国刑法学界普遍认为,尽管一般情况下的自首都不属于 “应当型”从宽量刑情节,而只是一种“可以型”从宽处罚情节,对量刑的结果不是必然产生影响,但立法者的态度与价值取向则是明显的:自首从宽是原则,不从宽处罚应当是例外。〔1〕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情形只占少数,绝大多数自首的犯罪人都不具备重大立功表现这一条件,法官在对其量刑时就必然存在着不给予其从宽处罚的选择。在具体案件的司法判决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类似的判词:被告人“作案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虽自首不足以从轻 (或减轻)处罚”。从社会的一般观念来说,包括犯罪人在内的社会公众通常都是将自首与从宽当然地联系在一起,但是,法律一方面将普通自首仅规定为任意从宽理由,但对在什么条件下自首犯不从宽处罚缺乏明确的原则和具体规定,因此,有关自首犯不从宽处罚的判决就常常令被告人、其他犯罪人、社会公众对量刑产生疑惑、不解,甚至对判决产生对立情绪。这种疑惑与对立事实上反映的是社会对量刑的公正性的追求,如果我们不能在自首犯的裁量选择上建立一个正当化的标准,不仅会削弱自首制度设立之感召犯罪人认罪自新、节约国家司法资源的积极效能,还有可能因此失去其他社会公众的理解和支持,甚至会使犯罪人做出与国家法律继续对抗到底的消极选择。①显然,从反面而言,对没有重大立功表现的自首犯不予从宽处罚的条件的确定,是自首犯处罚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对实现量刑公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10年 9月,最高法院正式颁布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将规范量刑活动作为当前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和保证司法公正的重要环节,其中一个重要的精神和倾向,就是要使现行刑法各种量刑情节在适用方法与标准上规范化、可操作化。遗憾的是,该文件在相关规定中仍然没能对自首犯不予从宽处罚的条件予以规范和确定。因此,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对于深化当前我国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大有裨益。
二、本论:自首犯的处罚与量刑公正
我们认为,要解决对自首犯的公正量刑问题,明确对于没有重大立功表现的自首犯可不予从宽处罚的条件,关键在于对三个问题的正确认识,即各国及地区刑法对自首犯在量刑上采取任意从宽或必然从宽的原因;量刑的根据;自首从宽的根据。如果明确了这三个问题,我们就可以找到对自首犯不予从宽的基本条件。
1.各国对自首犯处罚的基本规定及其理由
从世界各国及地区的刑法规定来看,对一般自首犯的处罚基本采取两种原则。一是任意从宽原则,在刑法规定上一般表述为“得”、“可以”从宽 (包括轻、减、免)处罚。例如,日本刑法典第 42条规定,“犯罪人在搜查机关发觉前自首的,可以减轻刑罚。”韩国刑法典第 52条规定,“犯罪后向搜查机关自首的,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2〕我国刑法典也采取了类似的规定。德国刑法典虽然没有在总则部分单独规定自首条款,但在第 46条第二款中明确将“犯罪后的态度,尤其是为了补救损害所作的努力”作为法院在量刑时必须权衡的情况,而犯罪后的态度显然包括自首情节,不过,德国刑法同时也将针对该情形量刑的裁量权力交由法官独立行使。〔3〕因此,我们也可认为,德国刑法对自首犯的量刑同样采取的是任意从宽原则。
任意从宽原则的核心在于,法律只是对自首犯的从宽处理表达一种倾向性意见,并不限制法官根据具体案件做出相反的选择,只要这种选择具有惩罚上的正当性。但是,为什么只是任意从宽,究竟根据什么标准,法官可以做出不从宽处罚的相反选择,各国刑法却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我们只能从学者的论述中发现这种立法的根据。例如,德国学者指出,德国刑法典第 46条第 2款的规定只是对客观的量刑因素的列举,其对犯罪人量刑的作用是双重的,在具体情况下可能有利于行为人或不利于行为人。〔4〕而我国学者更是明确指出,自首只是表明犯罪人的悔罪态度,但由于犯罪性质、客观状况和自首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为了防止犯罪人利用自首钻法律的空子,自首从宽只应当是相对的。〔5〕他们进而还提出了自首不予从宽处罚的具体情形: (1)罪行特别严重、动机十分卑劣、手段或其他情节特别恶劣的自首犯;(2)所犯罪行特别严重,民愤极大的自首犯; (3)必须判处最高法定刑,否则不能发挥刑罚一般预防作用的自首犯; (4)犯罪前预谋自首,妄图钻法律空子,逃避惩罚的自首犯;(5)迫于打击犯罪活动的形势,意图自首一部分罪行而逃避另一部分罪行,或意图以自首轻罪而掩盖重罪的自首犯; (6)虽然有自首情节,但归案后态度恶劣,毫无悔罪之意,明显蔑视社会和法律的自首犯。〔6〕
必然从宽是针对一般自首犯的另一种处罚原则,法官没有自由裁量的余地。例如,俄罗斯刑法典第 61、62条规定,犯罪人自首的而又同时没有法定加重情节的,刑罚的期限和数额不得超过分则有关条款规定的最重刑种最高刑期或数额的四分之三。〔7〕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 62也规定,“对未发觉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减轻其刑”,且这种刑罚减轻系绝对减轻。〔8〕在美国刑法中,自首是被告人认罪 (guilty plea)的一种形式,而认罪作为辩诉交易 (plea bargains)的主要条件则是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美国联邦《量刑指南》第三章 E部分“承认罪责”规定,如果被告人明确表示承认并肯定接受因自己的犯罪行为而产生的个人责任,降低两个犯罪等级。〔9〕
至于为什么要对自首犯做必然从宽的规定,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也从理论上给予了分析。当代俄罗斯学者认为:自首证明“犯罪人认识到自己犯罪行为的违法性,……,从而大大降低犯罪人的危害性,同时也证明他意识到自己的罪过,对所造成的损害表示后悔和弥补损害,而这也证明他可以较快地得到改造。”〔10〕美国学者指出:“就政府而言,对认罪者的从宽符合刑事司法制度规训 (administrative)犯罪人并使之复归社会 (rehabilita-tive)的目的。政府通过给予被告人某种利益以换取被告人给政府的实质利益,通过认罪,被告人表明其准备并愿意承认其犯罪的态度。”〔11〕我国台湾学者更是直接指出:“一九二八年刑法 (即旧中国刑法,作者注)规定自首得减所首之刑三分之一,减轻与否其权操之法院,以致犯人虽有投诚之意,终不免疑惧不前,殊不足以资激劝,故现行法改为必减,同时分则中对某数种特定犯罪之首,更设有减轻或免除其刑之规定,以期刑罚之轻重与犯罪恶性之大小相适应。”〔12〕
2.刑罚裁量的标准和自首从宽的根据
从上述各国和地区关于自首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在自首从宽这一普遍原则的基础上,一些国家着眼于自首犯的一般属性而采取必然从宽原则,另一些国家则出于实践中可能出现某些特殊自首行为考虑而采取了任意从宽原则。由于公众从社会一般观念上都将自首与从宽当然地联系在一起,这就要求司法机关所做出的对犯罪人自首而又不从宽处罚的刑罚裁量必须有充分的正当化依据,要作到这一点,则有赖于我们对刑罚裁量标准 (即决定裁量刑罚的要素)和自首从宽根据的正确认识。
从目前世界主要国家的刑法规定来看,刑罚裁量标准虽然在文字规定上各有千秋,但基本内容大致相同。我国刑法第 5条明确规定,刑罚的轻重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对于这一刑法规定,学界流行的观点是,刑罚的轻重必须与罪行的轻重以及犯罪人的社会危险性相适应。其实质在于:坚持以行为的客观侵害性与主观罪过性相结合的犯罪危害程度 (罪行的轻重),以及犯罪人本身对社会的潜在威胁和再次犯罪的危险程度作为量刑的尺度,前者考虑刑罚报应的正义要求,防止为过度追求预防目的而出现畸轻畸重的刑罚,后者考虑预防犯罪的国家目的,使刑罚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其中累犯、自首、立功等情节正是能够说明犯罪人对社会的危险程度的最主要事实。〔13〕德国刑法典第 46条规定了德国有关量刑活动的基本准则,其第 1款规定,“犯罪人的责任是量刑的基础,且应考虑刑罚对犯罪人将来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德国学者指出,根据这一规定,德国刑法“量刑的基础是行为人的罪责”,即刑罚的度应当首先与罪责的度相适应,同时还要考虑到刑罚效果对行为人“再社会化的利益”。而第46条第 2款则“列举了法院在量刑时所应当注意的有关‘情况’”,它们是量刑时体现犯罪人罪责及其特殊预防需要的各种具体因素,包括能够反映“客观的行为不法”的事实 (行为方式、犯罪结果、违反职责的程度)、反映 “犯罪行为内心态度”的事实 (犯罪动机、目的及行为时表露的思想)以及反映“行为人人格、刑罚效果必要性”的事实 (犯罪后的态度、犯罪人履历、人身和经济状况)。〔14〕当代英美法系国家在量刑标准问题上超越传统的报应与预防理论的对立而建立起量刑的该当性 (desert或 deservedness)理论,根据该当性原则,刑罚惩罚的轻重取决于犯罪的严重性,而决定犯罪严重性的要素则是危害与应受谴责性,前者指“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或者有造成的危险的损害”,后者指“犯意、动机与决定罪犯应被主张因为其行为而应受多大谴责的情节方面的因素”。〔15〕俄罗斯刑法典第60条第3款规定,“在处刑时应考虑犯罪的性质和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及犯罪人的身份,其中包括减轻刑罚的情节和加重刑罚的情节”。〔16〕对此,俄罗斯学者指出,这意味着法院在量刑时应当衡量犯罪社会危害性的性质和程度,并考虑刑罚的个别化,前者由犯罪客体的性质、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人的罪过等内容组成,后者包括犯罪人实施行为后的态度在内的能够评价犯罪人身份的各种事实。〔17〕由此可以看出,包括我国在内的上述各国刑法有关量刑标准的基本内容大体是一致的。
在明确了量刑的基本标准以及影响刑罚轻重的因素后,我们就需要进一步探讨自首情节到底基于何种原因对刑罚轻重产生影响。从目前各国、各地区学者有关自首的论述可以发现,无论是主张任意从宽原则还是主张必要从宽原则,自首从宽的根据主要有两个:一是自首犯因为悔罪和接受国家司法审判而对社会的危险降低,更易于改造和回归社会;二是节约了国家的司法资源,国家对犯罪人的奖励。但如果对照各国有关量刑的标准,我们会发现,犯罪人在诉讼中是否节约了国家的司法资源并非是影响量刑的因素,它既不属于反映行为社会危害性或罪责的事实,同时也与衡量犯罪人是否存在对社会的危险及危险程度无直接的关系,它并非自首从宽这一量刑规则的基本依据,充其量只是一个对自首犯从宽量刑的次要理由。从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在采取任意从宽原则的国家,即使自首犯实际上确实节约了司法资源也并不是必然导致从宽处罚。
我们认为,自首从宽的根据只能从刑罚惩罚犯罪的理由和目的中去寻找。我国学者指出:在现代刑法理论中,犯罪行为同主体所进行的任何活动一样,都是“主体的存在和表现形式”,“犯罪行为的特殊本质实际上就是犯罪主体的特殊本质”,犯罪行为是一种必须归因 (归责于)于主体的意识和意志层面的行为。这意味着任何犯罪的成立,都必须以行为人敌视、蔑视、漠视刑罚所保护价值的态度为根据,这是刑罚惩罚犯罪人的正当性之所在。因此,一切包含于犯罪行为之中,或者通过犯罪行为表现出来的主体对刑法所保护价值的敌视、蔑视或漠视态度,无论是作为犯罪的原因 (罪前情节)还是结果 (罪后表现),自然都成了决定行为的性质及其社会危害程度的重要因素。累犯、自首、立功等说明主体“社会危险性”及其程度的情节,实际上都是证明犯罪人对刑法保护价值所持的态度的重要事实。①引自我国著名刑法学家陈忠林的论述,具体可参阅,陈忠林:《中国刑法第一至十二条的解释》(未刊稿),第 76页。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要一方面强调“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另一方面,又将犯罪归结为“不法意图的实现”,归结为犯罪人作为“孤立的个人反抗统治关系的斗争”〔18〕,是犯罪人“蔑视社会秩序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19〕的原因。所以,就刑罚惩罚的正当性而言,犯罪人的自首行为主要不是因为节约了司法资源而影响量刑,而是由于折射出行为人的悔罪心理和接受国家司法审判的主观态度,最终反映了行为人对国家法律规范对立态度的降低、行为人主观可谴责性的减弱、对社会的危险减少和更易于改造和回归社会的可能,从而成为量刑标准的内容之一,而对犯罪人刑罚轻重产生重大影响。
就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而言,惩罚犯罪的根据在于支配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是主体对刑法所保护价值的敌视、蔑视或漠视态度,即由行为所表现出的反社会意识,“从根本上讲,我们惩罚犯罪就是惩罚和改造犯罪分子主观中的这种反社会意识,防止它们再具体化为支配犯罪行为的主观罪过”。〔20〕从纯粹的功利角度出发,即使自首犯因自首而节约了国家司法资源,但如果其主观上是希望通过自首掩盖更大的罪行或逃避国家的惩罚,其反社会的意识就不能或很难得到改造和消除,对这种自首犯的从宽处罚就不能达到刑罚预防犯罪的目的,单纯为了奖励而从宽处罚行为人,从功利角度看也是因小而失大。因此,我们认为,综观当代世界各国及地区刑法的量刑标准,自首从宽的主要根据不应当从节约国家司法资源的角度去理解和诠释,自首从宽处罚的根据是:行为人的自首能够反映其对国家法律规范对立态度的降低、行为人主观可谴责性的减弱、对社会的危险减少和更易于改造和回归社会的可能。只有从这一角度出发并遵循这一原则,我们对自首犯的从宽或不从宽处罚才可能是正当的。
三、余论:自首从宽处罚的例外
既然自首从宽的根据在于由于自首而反映出的行为人主观上对国家法律规范对立态度的降低、对社会的危险减少,同时,鉴于社会公众对自首从宽的普遍性认识,在我国采取自首任意从宽原则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自首从宽处罚的例外必须要坚持以下基本立场:只有在我们能够以确切的证据证明自首犯具有掩盖罪行、逃避国家惩罚的动机的情况下,才能够对自首犯不从宽处罚。为此,刑事司法实践应注意把握三点:其一,自首是与行为人主观人格、主观心理态度相联系的客观事实,而与已经实施完毕的犯罪行为的客观方面 (包括手段、结果、其他客观情节)、实施行为时的犯罪动机、目的以及民愤无直接关系,同时,这些内容在根据刑法分则决定犯罪人基本刑 (即暂不考虑犯罪人有自首情节时对其所应判处的刑罚)时已经考虑进去,因此,不能作为考虑是否适用自首从宽原则的客观理由。如果在确定是否对自首犯从宽处理时再考虑,不仅违背自首从宽的法律和法理根据,同时也违反了刑法禁止“双重评价”的原则,必然会导致量刑的不公正。此外,自首从宽的处罚方式是与刑罚的个别化及特殊预防为出发点的制度,因此,也不应当以一般预防 (即威慑)为由而对自首犯不从宽处罚。其二,决定自首犯是否从宽的核心事实是自首的动机,即行为人是否存在利用自首掩盖罪行、逃避国家惩罚的企图,而是否具有这种动机则主要根据行为人在自首中和后的客观表现来体现。如当代俄罗斯学者所指出的,“自首要求犯罪人不仅自愿到执法机关去,而且还要详细地叙述所实施的犯罪,真诚悔过和谴责自己的行为,真实地揭露他所知道的一切情况,只有犯罪人这样做时,自首才具有减轻情节的刑法意义。”〔21〕其三,从量刑公正和获得包括犯罪分子在内的社会公众对判决的认可的角度出发,对于不从宽处罚的自首犯,司法机关必须在判决中明确指明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此外,如果能够在刑法总则关于自首制度的规定中或者在司法解释中明确自首不从宽处罚的基本条件,对于完善自首制度,鼓励犯罪人自首,提高公众对刑法及刑事司法的认同度都会有着重要的作用。
〔1〕高铭暄.刑法学原理 (第 3卷)〔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361;周振晓.关于自首及立功者处罚中的几个问题 〔J〕.人民检察,2002,(8);王艳.论自首的认定与处罚 〔J〕.当代法学,2002,(3).
〔2〕日本刑法典 〔M〕.张明楷译,法律出版社,1998;韩国刑法典及单行刑法 〔M〕.[韩]金永哲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10.
〔3〕德国刑法典 〔M〕.徐久生,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57.
〔4〕〔14〕[德 ]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 (总论) 〔M〕.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1055-1056,1047-1049、1055.
〔5〕高铭暄.刑法学原理 (第三卷)〔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360;马克昌.刑罚通论 〔M〕.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5.411.
〔6〕高铭暄.刑法学原理 (第三卷)〔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361-362;马克昌.刑罚通论 〔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411;王艳.论自首的认定与处罚 〔J〕.当代法学,2002,(3).
〔7〕〔16〕俄罗斯联邦刑法典 〔M〕.黄道秀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28,27.
〔8〕〔12〕韩忠谟.刑法原理 〔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300,301.
〔9〕储槐植.美国刑法 〔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33.
〔10〕〔17〕〔21〕〔俄〕库兹涅佐娃,佳日科娃.俄罗斯刑法教程 (总论)上卷·犯罪论 〔M〕.黄道秀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667-668,648-650,668.
〔11〕Jerold H.Israel、Wayne R.Lafave:Criminal Procedure,法律出版社 (英文影印本).1999.427.
〔13〕高铭暄.新编中国刑法学 〔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25;张明楷.刑法学 (第二版)〔M〕.法律出版社, 2003.72;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 〔M〕.法律出版社,1999.288.
〔15〕[美 ]冯·赫希.已然之罪还是未然之罪 〔M〕.丘兴隆.胡云腾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68-70.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卷 〔M〕.人民出版社,379.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卷 〔M〕.人民出版社,416.
〔20〕陈忠林.刑法散得集 〔M〕.法律出版社,2003.277.
(本文责任编辑 谢莲碧)
DF613
A
1004—0633(2011)03—089—05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从文本中的刑法到司法中的刑法》(07CFX031)的阶段性成果。
2011—01—12
王燕莉,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唐稷尧,法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四川成都 61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