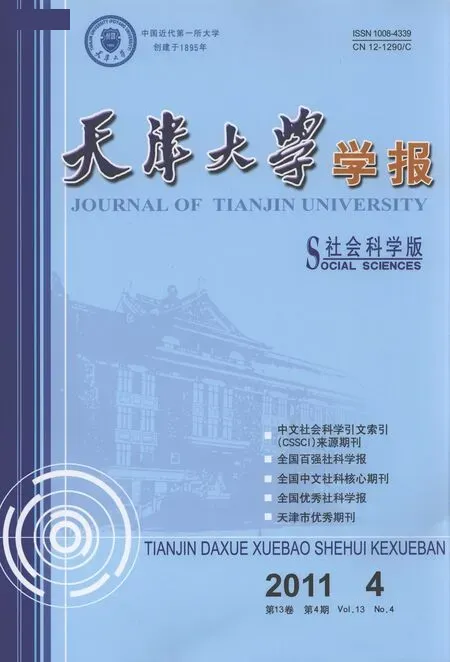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的情感解读
2011-03-17刘春芳
张 洁,刘春芳
(1.天津大学文法学院,天津 300072;2.山东工商学院外国语学院,烟台 264005)
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的情感解读
张 洁1,刘春芳2
(1.天津大学文法学院,天津 300072;2.山东工商学院外国语学院,烟台 264005)
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通过细致入微地刻画人物的情感世界,深刻地展现出了现代人的情感困境。普通人的情感处于一片荒漠,在爱情追求中,人们同样面临无法摆脱的情感困境。不同的阶级之间更是有着无法跨越的情感鸿沟。曼斯菲尔德面对无所不在情感困境,试图通过建立空中楼阁般的心灵花园作为解脱的途径,最终只能成为一种无奈的逃避。
曼斯菲尔德;情感;逃避
在工业文明、物质迅速丰富使人的精神世界面临危机的时代,人的本真情感被普遍忽视。曼斯菲尔德深受这种大环境的影响,在自己的作品中诉说对真挚情感的崇尚与追求。由于受她个人生活小环境的深刻影响,其作品表现出与其他作家迥然不同的观点和态度,因而也创作出了独具魅力的作品。她个人生活中情感的失落、理想的破灭,以及自己爱情与婚姻的曲折遭遇,再加上时刻伴随着她的孤寂无着和病痛的折磨,使她的作品弥漫了一种挥之不去的忧郁。不论是描写爱情婚姻、普通小人物的生活和心理、还是不同阶层之间的隔膜,她都刻画得细腻入微,不惜笔墨在细节上精雕细刻,从最精细的角度展现出人们的情感困惑与情感寂寞。通过阅读她的作品,可以感受到她对于时代普遍存在的情感荒漠的深刻认识及其表现出的深深的无奈。
一、普通人的情感荒漠
曼斯菲尔德小说中的人物,不管生活是否困窘,工作是否如意,都处于一种情感孤立的状态。《罗莎蓓尔惊梦记》中的罗莎蓓尔,在女帽店辛苦了一整天,却因为买了一朵紫罗兰而无法填饱肚子。要让情感得到慰藉,代价是昂贵的,即满足情感就要付出肉体的代价。罗莎蓓尔这样的小人物的情感、愿望无人理会,她一个人蜷缩在冰冷的小屋里,只有无边的幻想替她打发寂寞。而她的幻想完全不着边际,建立在一个轻浮浪子的一句轻佻问候之上。在现实生活中,她的情感完全是一片荒漠,她得忍受顾客对她的尊严的践踏,对她情感的忽视。只有在幻梦中,她才得到一些虚无飘渺的安慰。“她睡着了,还做着梦,睡梦中还在笑,有一回还伸出手臂去摸摸那不存在的东西,又继续做梦了。”[1]
最惨痛的像巴克妈妈,她经历了死了丈夫和7个孩子这种难以想象的痛苦生活。而更让她无法忍受的是她的痛苦不但无处倾诉,更可怕到连哭的地方都没有。“难道真的没有可以让她藏身的地方,让她独自一人,愿意呆多久就呆多久,不打搅别人,也没有人来麻烦她吗?难道世界上就没有个地方可以让她好好哭一场吗?”[1]72这是曼斯菲尔德对生命的痛切质问,也是对情感关怀的最深切呼唤。如果人的情感无法得到理解,无法得到释放,无从得到关怀,那这个世界与地狱何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克妈妈为一个文人工作。文人本应代表社会良知,而小说中的文人毫无情感、好像例行公事一样问候巴克妈妈的外孙,巴克妈妈告诉他孩子已经埋藏,他不是关心巴克妈妈的情感,而是问她葬礼是否顺利。文人的冷漠与无情被揭示出来。当巴克妈妈说到自己曾嫁给一个面包师傅时,文人首先想到的是干净。而事实是巴克妈妈的丈夫却因为工作的劳累使肺里全是面粉,最终致命。当巴克妈妈沉浸在无以复加的丧亲之痛中时,文人居然怀疑巴克妈妈偷掉了他的一点点可可,并为自己颇有技巧的询问得意。一个需要捕捉生活、理解情感的人对待巴克妈妈的生活如此冷漠,对待巴克妈妈的感情如此无情。这样的知识价值和世界状态没有一丝用处,没有一丝温暖,人的生命如同鸿毛,人的情感如同草芥。
曼斯菲尔德的情感困境同样也延伸到了小孩子的世界。《阳阳和亮亮》中的阳阳和亮亮虽然被大人宠爱,但是那种宠爱却仅限于表面,无法到达心灵。两个孩子穿戴整齐漂亮,却不过被客人们称作“啊,这两只小鸭子!”“啊,这两只小羊!”然后他们就忍受没完没了的亲吻。忙于准备舞会的父母顾不上他们。而在厨娘那里,他们看到了为舞会精心准备的食品。在孩子们的眼里,这些食品的美丽无异于美丽的童话王国,是孩子们心中最珍视的地方。而在孩子们眼中的美丽王国却被舞会的客人们吃掉、破坏掉。当阳阳看到这些美丽食品不复存在大哭起来时,他心中的痛苦和难过不但没人理解,反而遭到爸爸的呵斥。可怜的小阳阳内心柔嫩的情感世界横遭践踏,却无人能懂。《小姑娘》为了讨爸爸高兴而用心为爸爸准备生日礼物,却不小心在做礼物时用了爸爸的讲稿,结果挨了爸爸一顿好打。《六便士》中的爸爸同样不分青红皂白,在工作了一天回家后听了妈妈的一堆抱怨和让他去打孩子的要求后,闯进孩子的卧室狠狠打了小迪基。这些故事里的孩子天真可爱,他们挨打的原因是由于他们单纯、真挚的情感,自然、快乐的性格。而这些自然的、纯洁的性格正是文明社会中的人所欠缺的。曼斯菲尔德认为,正是文明社会中人们对情感的忽略和冷漠,导致了自己情感的缺失,因此对情感无情践踏却不自知,最终导致他人情感的困境。
二、同床异梦的爱情困境
曼斯菲尔德的许多小说都描写爱情和婚姻。在她笔下,本应承载人类最美好感情的爱情和婚姻却充满了陷阱,充满欺骗,很难找到情投意合的爱情关系。《鸽子先生和夫人》中的雷吉深深爱上了安妮,然而雷吉的家庭状况、社会地位却远远不如安妮。这就导致他们不能相爱,因为相爱的基础是一条条的外在标准,丝毫与情感无关。他们不能像没有社会规则束缚的鸽子先生和夫人一样简单地相爱,什么都不要,只要情感自身。正如安妮所说“鸽子先生和鸽子夫人好倒是好,可是想想看,在现实生活中——想想看!”[1]120现实生活是一个抹杀了情感的无情世界,在现实生活中,真正的爱情无处容身,只有男女在外在条件合适基础上的匹配。像雷吉心里那种最热烈、最本真的爱情无人理睬,连安妮也是一直嘲笑他的不合时宜、不切实际。
就算男女二人彼此相爱,心心相印,也常常不得不屈服于现实。《稚气可掬,但出于天然》中的亨利与爱德娜两人的爱情很单纯。亨利是一个颇有浪漫气息的男孩。他因为陶醉于一首名为《稚气可掬,但出于天然》的小诗差点误了火车。而这首诗便是他们的爱情本质的写照。在火车上他与爱德娜一见钟情。两人没有比较衡量彼此的外在条件,而是因为气质相近、爱好相投而产生爱情。而他们的爱情在爱德娜那里一直存在阴影。爱德娜躲避亨利的亲近,因为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就是爱德娜问亨利的致命问题“你有信心吗?”他们要相爱,必然要面临现实的诸多问题,而爱德娜对此毫无信心。他们的爱情在真实的现实世界里,就是一场梦,是他们一起做的梦。他们最后的约会中爱德娜没有来,只让人捎了一封令亨利心碎的电报。亨利在等待爱德娜时想起了那首名为《稚气可掬,但出于天然》诗:
“但愿我是一只羽毛丰满的小鸟,
有两只小小的翅膀,
我会向你飞去,亲爱的——”[1]143
这只是一个愿望而已。亨利忘了诗的后半句:“然而这样的思绪本来无聊/我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的爱情抵挡不住现实的威胁,就像诗中所说“爱在破晓时苏醒”。纯洁的爱情、真正的爱情只存在于梦境,存在于幻想之中。现实世界不允许这样的情感自由生发、自由成长。
由于人性本真的情感被无情压制,导致在爱情上已将情爱二字视为奢侈,而只专心于外在的形式与他人的评判。《唱歌课》中的梅多思小姐给学生上课时无法控制自己痛苦的心情,大唱哀歌,因为她的未婚夫给她写了一封绝交信。但是细读这篇小说可以发现,梅多思小姐的痛苦并不是因为爱情的破灭,爱人的离去,她更多考虑的是她如何面对理科女教师,如何面对学生。也就是说,如何面对外界的评判是她最在乎的。当她后来收到未婚夫收回前言的信后,心情立刻好转,给学生大唱欢歌。她并不在乎为什么爱人会说分手,为什么又收回,也不介意这种爱情是否发自内心。她快乐的源泉是因为能保住在同事前的面子。曼斯菲尔德笔下少数的美满结局的本质却与真爱无关,爱情的悲剧更是把情感完全排除。
在以《幸福》为标题的小说中,曼斯菲尔德对“幸福”做了最深刻、最无情的讽刺。《幸福》里的贝莎在等待丈夫哈里回家、为客人准备水果的时候,觉得自己无比幸福,觉得一切都那么顺心如意。她觉得她什么都拥有:
“真的——真的——她什么都有了。她年纪还轻,哈里跟她彼此相亲相爱,一如既往,相处十分融洽,是对真正的好夫妻。她有个可爱的小宝宝。他们用不着为钱操心。他们这所花园住宅也非常称心满意。朋友呢——都是时髦人物,谈笑风生,有作家,有画家,有诗人,还有热心于社会问题的人士——个个都是他们愿意结交的。家里要书有书,要音乐有音乐,她还找到了一个手艺高明的女裁缝,夏天他们还到国外去游览。他们家的新厨子做的蛋卷味道真是美得无以复加。”[1]177-178
这种表面看来完美到极至的幸福,本质上却如海市蜃楼般飘渺。事实是贝莎最爱的丈夫和她最愿意结交的女友之间却有着不可告人的龌龊关系——一种足以摧毁贝莎所有幸福的龌龊关系。这种关系证明了她和女友富尔顿的友谊是一种欺骗;她和丈夫之间的爱情根本就是一种幻梦,现实中根本不存在,她和丈夫之间的关系正如《陌生人》中所表现的,是一种本质上完全陌生、情感上完全疏离的关系。贝莎看着花园里美丽的梨树,认为她的生活就像那株梨树,无比艳丽,开满繁花。
“推开客厅的窗子就是阳台,正好看得见花园。花园尽头墙根下,长着棵修长的梨树,正盛开着娇艳的花朵;梨树亭亭玉立,衬着碧玉般的青空,似乎凝止不动。虽然隔得这么远,贝莎还是不由得觉得树上既没有一朵含苞欲放的骨朵,也没有一片凋谢的花瓣。”[1]177
梨树的美丽正是因为遥远的缘故。她只看到花朵,没看见枯枝。幸福就像是这棵梨树,虚无、遥远,完全存在于想象中。那一树幸福的梨花因为隔得远,所以看不见凋谢的花瓣,因为不了解,所以完全被美化。贝莎就生活在这样一种虚无的幸福感中。她和富尔顿小姐一起看梨树,两个人都被深深感染,被那遥远的、不可企及的幸福所吸引,同时又不由自主地去美化那遥远的幸福,使这种幸福变得更加不现实。而回到现实生活,情感的沙漠却是两个人共同的不幸根源——她们面对的是同一个没有真正爱情、充满欺骗与轻佻的男人。她们两人都无法得到真正的幸福,正如那一树不败的梨花根本不存在一样。可以说,女主人公用想象“来填补情感的真空,给她们关于自身的故事输入虚假的意义”。[2]她不知道如何面对真正的现实生活。她的情感只飘荡在纯想象的、纯虚拟的世界,在现实世界中不知如何容身。
在《毒药》中,曼斯菲尔德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情感缺失、情感疏离的婚姻的本质——毒药。“每天发生多少毒害的罪行?难得有几对结婚的夫妇他们彼此不互相毒害——夫妻们、情人们。”[1]202夫妻间是“陌生人”,彼此之间没有感情、没有信赖,甚至成为彼此的“毒药”。“幸福”只是一种幻觉,遥不可及。这无异于是对没有真正情感的婚姻的最无情诅咒,也是对真挚情感的最热切呼唤。正因为如此,曼斯菲尔德将爱情视为幸福的对立面,“爱情是世上唯一重要的东西,这种教条极其残酷地阻碍了我们的发展。我们必须摆脱这一妖魔,摆脱之后就会得到幸福和自由的机会。”[3]曼斯菲尔德在这里提出了令现代人痛苦而又警醒的问题,正如有人认为曼斯菲尔德小说写的是“叶子下面蠕动的蜗牛”[4],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的问题——一片新鲜完好的叶子后面,总会发现令人烦恼又无法避免的蜗牛。
三、阶级间的情感鸿沟
曼斯菲尔德除了写爱情婚姻和小人物的孤独,还写了许多表现阶级隔膜的小说。她在作品中通过崭新的视角,毫不留情地揭示出现实的悲凉。作为一个女性小说家,她直面现实的勇气首屈一指。她指责伍尔夫在小说中略去战争的作法,认为这是一个灵魂在撒谎。她认为“我们的全部力量决定于我们是否面对现实。我是说毫不保留、毫无约束的面对现实。”[5]面对由于阶级界限、阶级分化而造成的情感丧失,并导致人的无情与冷酷,她在作品中一再地进行深刻揭露。《花园茶会》中富有奢华的贵族之家对于死去穷人表示出的无边的冷漠,就是曼斯菲尔德对于社会现实的深刻揭示。然而,身为女性作家,她笔下的世界也有充满细腻婉转的一面,在无边的冷漠中她描写了一丝温情,表现出作者对于真挚情感的渴望、对于未受世俗污染的情感的赞美及呼唤。
在《花园茶会》中的萝拉散发着这样一种天真烂漫的情感之光。当搭帐篷的工人来时,她天真地拿着黄油面包出来与他们说话。她本想模仿母亲的做作,努力板着脸,但是工人的随和友好使她恢复了本来模样。工人们丝毫没有萝拉所代表的贵族阶级的虚伪做作,更多的则是纯朴和美丽。当一个高个子工人弯着腰在捏薰衣草的嫩枝,轻轻闻着香味时,萝拉觉得工人可爱得出奇,而她的贵族朋友只会和她跳舞,没有这种天然的、纯真的情感。她希望和质朴可爱的工人们相处。她觉得“一切过错都在那悖情背理的阶级差别。在她这方面,她可没有感觉到这种差别。一点也没有,一丝一毫也没有……”[1]3她与她的母亲、姐姐之间的分歧根源在此。当听到住在她附近的工人意外死亡时,她觉得茶会无论如何不能照计划进行。因为她们不能用欢乐的茶会场面去刺伤别人的丧亲之痛。对她来说,这是对他人情感的起码尊重。但是她的力量太过渺小,根本不可能阻止茶会的正常进行,她的姐姐和母亲认为她的想法简直不可思议。在她姐姐和母亲眼里,穷人的情感根本算不得情感,穷人的痛苦也不值得同情。虽然小萝拉有着单纯的情感关怀,有着善良的愿望。不过,她的愿望在本质上也是短暂的,她不会坚决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茶会按计划进行,而她依然穿着漂亮的衣服在茶会上出尽风头。就好像《洋娃娃的房子》里善良的凯济娅,虽然因为同情凯尔维姐妹,把她们带到家里来看她家的洋娃娃的房子,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她们的命运。
萝拉在茶会结束后得以去看望死者。当她面对死者的尸体时却产生了非常奇怪的感觉:
“一个年轻人躺在那里,正在酣睡——睡得这样熟,这样深,使得他远远离开了她们两个。呵,这样遥远,这样宁静。他在梦乡。永远别叫醒他。他的头陷在枕头间,眼睛闭着,在合拢的眼皮下,什么也看不见。他把自己交给了梦。花园茶会,食物篮子,还有花边衣服,这些和他有什么关系呢、?他离这一切都太远了。他是奇妙的,美丽的。在他们欢笑着,音乐飘扬的时刻,这奇迹来到胡同里。幸福……幸福……一切都好,那沉睡的面孔在说。原该如此,我满意。”[1]17
爱似乎与死有互相依存的关系,只有体味过死,才能懂得爱。曼斯菲尔德笔下的和谐与幸福来得多么荒唐。这是一种与现实完全脱离、与真实完全脱离的美丽。曼斯菲尔德本人热衷于艺术创作。她说:“这维系人心的、无法描述的艺术激情,有何可与之相比!还有什么更令人向往呢?”[5]她衷情于艺术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她特别敏锐、富有天赋,更因为艺术可以为她带来一个远离现实的理想王国,这个王国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绘制而让它充满光彩,陶醉在短暂的虚无的美丽中。然而这种美纵然再迷人,也丝毫无法减轻现实的苦恼。正如她自己所说“艺术家的工作不是去磨斧头、去把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强加于现存世界之上。艺术不意味着艺术家要把存在与艺术家的观点调和为一体;艺术是试图在这一世界上创造出一个艺术家自己的世界。”[5]154
正如小说中贵族的小姐虽然有同情心,但也根本不可能真正了解贫民的生活与需要。一位正值壮年的男子撇下老婆和5个孩子撒手人寰,怎么可能安宁,怎么会感到幸福。他的死去带给家里的痛苦和残酷的生存问题也不是戴着漂亮帽子、穿着花边衣服的贵族小姐施舍的一篮子食物所能解决的。贵族小姐的关心正如她自己所感觉到的,是那么不合时宜,那么刺眼,那么毫无意义。在《一杯茶》里,贵族小姐生活奢华无比,舍得用28个金币买一个小盒子。当她的同情心突然地降临到一个乞讨女孩身上时,那种同情与施舍显得那么令人难堪,同时毫无价值。她要带乞讨女回家,却吓得女孩子以为她要报警,同时又为她的举动感到不解和疑惑,以至颤抖。这就是贵族女郎的同情心换来的结果。而她自己却觉得她的用意是好的。哦,何止是好意呢。她还打算向这姑娘证明,生活中确实有怪事,神话里的好心仙女确实是有的,有钱人也有好心肠,女人家都是姐妹等。正是这位仙女把乞讨女孩领回家后,不知道女孩已经饿得快要晕倒,而是按贵族的生活习惯为女孩脱帽脱衣的礼仪罗嗦;她不知道女孩最需要的只是普通的食物,而是要拿白兰地给女孩喝……然而这可怜的、毫无意义的同情心也止步于她丈夫夸奖女孩漂亮的一句戏语。当她在丈夫故意说乞讨女漂亮后,她不加思考地、迅速地将其赶走,最后给女孩施舍钱物时左右掂量,拿了5张一英镑的钞票又放回两张。她的施舍同她要买的28个金币的盒子相比多么廉价、多么滑稽!
作为一个作家,曼斯菲尔德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使用一些现代派的手法,打破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客厅小说的沉闷气氛,她是美丽和忧郁的守护者,揭示现代生活丑陋的外衣下潜藏的爱和美。1918年,她曾给自己定下理想,要表现这个世界最微妙和宁静之美。而纵观她的小说,在一种笼罩万物的情感困境中,那种最微妙和宁静的美丽无处可存。曼斯菲尔德只好让它存在于虚无的幻觉中。她自己有时候陶醉于幻觉,觉得幻觉“比现实更真实、更详尽更丰富。而且我相信这种幻觉可以持续到……那是无止境的。”[5]106正如《花园茶会》中的萝拉所感觉到的虚妄、不可捉摸奇怪的美感与幸福,在现实生活中毫无根据。
在她那短暂的人生里,她一直挣扎在复杂变幻的人际、贫病交加的处境和永远的旅行里,只有写作显现出某种永恒和平静。曼斯菲尔德通过作品、通过生活方式的选择,努力寻求自己的精神家园,她被朋友们戏称为“旅行小姐”。她的一生,就像一次漫长的旅行,永远动荡不安,不可捉摸。“我是谁?”这是她终其一生在追寻的问题。为了找到统一稳定完整的自我而奋斗,在纸上,她总是反复回到她那“孤独女士”主题。作品中的世界就是她的一个梦幻天堂。旅行是她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逃避方式,而写作则是她回归理想王国的途径。这种途径同样也是一种逃避,她对现实的丑陋丝毫没有改变的信念,只是希望寻找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如梦如幻的宁静。她本想要理清自己“乱七八糟的生活”,结果愈发栖身于无根无由的梦幻之中。没有幸福,她可以想象出幸福;没有朋友,她可以认为“人影、树影是我的朋友”[5]41。这便是情感的力量,“情感则像火柴一样,虽不能改变社会结构,左右社会发展,却能使人在绵长的生命中看到光亮”[6],使人能够在烦乱的现实中品味精神自由。
可以看出,曼斯菲尔德所追求、所执著的宁静幸福的世界无非是一个不许他人进入的心灵的花园,是一种空中楼阁。与她同时代的作家相比,曼斯菲尔德没有哈代的救世精神,没有伍尔夫令人温暖的情感关怀,她笔下的情感生发的根源虚无飘渺,不是自然真实的发自心灵的情感,只是一种独立于现实世界之上,是纯粹想象的、刹那间的激情与感悟,丝毫没有温度和力量,根本不能给人真正的慰藉,更谈不到拯救心灵,拯救世界。伍尔夫曾这样评价曼斯菲尔德:
“事实上,她的头脑是一片贫瘠之地,岩石上只覆盖了一二英寸的薄薄一层土。我恐怕只好接受这一事实了。由于《幸福》篇幅很长,原本可以挖掘得更深刻些,但曼斯菲尔德满足于肤浅的机智,想象平庸乏味,缺少求知者的憧憬。尽管这种憧憬本身并不完美,她写得很糟。其效果,要我说呢,我觉得她感觉迟钝、缺乏情趣。”[5]1
伍尔夫这段尖刻的批评根源于她和曼斯菲尔德世界观的不同。伍尔夫致力于挖掘能够真正唤起生命、打动人心的情感关怀,而曼斯菲尔德执著于寻找飘渺虚幻的情感归依。“曼斯菲尔德的作品仅仅存在于历史的边缘。”[7]而劳伦斯则认为:“她的写作精美动人,但并不伟大!”[8]本质上讲,曼斯菲尔德只希望能够做到情感转移、以逃避的方式来解决情感的困境。在她的墓志铭中引用了她喜欢的英国贵族霍特斯巴的一段话:“……但是我告诉你,傻瓜大人,我们从危险这刺丛中,折下了安全这朵鲜花。”危险的刺丛就是无法避免的情感困境,这朵鲜花正是不曾存在的虚无的梦幻。参考文献:
[1] 曼斯菲尔德.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M].陈良廷,郑启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35.
[2]Sandley S.Katherine Mansfield’s“Glimpses”,in Katherine Mansfield:In From the Margin[M].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1994:88.
[3]Murry J.Journal of Katherine Mansfield[M].London:Constable,1928:36-73.
[4]Murry J.Katherine Mansfield and Other Literary Studies[M].London:Constable,1959:76.
[5] 曼斯菲尔德.曼斯菲尔德书信日记选[M].杨 阳,印京华,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97.
[6] 刘春芳.《到灯塔去》的情感拯救主题[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162-165.
[7]Dunbar,Pamela.Radical Mansfield:Double Discourse in Katherine Mansfield’s Short Stories[M].London:Macmillan,1997.
[8]Lawrence D H.The Letters of D H Lawrence[M].Bolt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1979:520.
Interpretation on Emotion in Mansfield’s Short Stories
ZHANG Jie1,LIU Chun-fang2
(1.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d Law,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072,China;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dong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Yantai 264006,China)
Through the minute depictions of the emotional world,Mansfield’s short stories profoundly demonstrate the emotional plight of modern people.Feelings of ordinary people are alienated from true emotion.When in the pursuit of love,people can not escape from the emotional plight.Among different classes there exists the emotional gap which is hard to cross.Facing the pervasive emotional plight,Mansfield tried to build a spiritual garden as a means of liberation,but ultimately it could only be proved a helpless escape.
Mansfield;emotion;escape
I106.4
A
1008-4339(2011)04-0376-05
2010-03-26.
张 洁(1973— ),女,博士,副教授.
刘春芳,acatcherinthery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