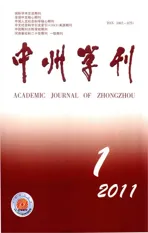明代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及其转向*
2011-02-21陈宝良
陈宝良
明代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及其转向*
陈宝良
按照传统的观念,家庭生活大抵表现为一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关系。作为以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明代社会,家庭结构中的女性,在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通过参与田作、纺织及其他手工等生产活动,成为家庭经济的一种补充。家庭生活史的演变证明,明代妇女不但在家庭中扮演着管理者的角色,而且广泛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进而出现了诸如三姑六婆、女贾、女佣、苏州梢婆、插带婆、绣花娘、赶唱妇人、瞎先生之类的职业女性群体。所有这些,无不说明妇女在家庭经济生活中开始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
明代妇女;社会经济;职业女性
按照传统的观念,男女之间的职责各有不同。男子“主四方之事”,女子则不过“主一室之事”,但是在明代,也存在着诸多劳动妇女,她们除了承担家务劳动之外,同时也在外从事一些生产劳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妇健”之风的盛行,在家庭职责分工上,妇女已不再局限于“主中馈”,亦即所谓的“下厨房”,而是走出家庭,从事社会经济活动,从而导致诸如“女贾”、“卖婆”一类职业女性群体大量涌现。
一、从妇职看男女经济活动之内外有别
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显然牵涉到妇女在家庭经济中的地位问题。按照传统的观念,家庭生活大抵表现为一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关系。妇女主要是在家庭中从事家务劳动,至于维持家庭日常开支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由丈夫承担。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导致明代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大多局限于家庭内的家务劳动,即使从事一些与家庭经济来源有关的工作,也不过是田作、纺织或其他在家庭内即可完成的手工劳动。至于像外出经商一类的活动,一般是由男子承担。换言之,妇女主要是在家庭中扮演自己的角色。
明代妇女的家务事,可以用“酒浆组纴”四字加以概括。如王述古之母郭氏,史载其日常生活云:“事姑暇,辄事织纴,机杼声昼夜轧轧彻户外,媟黩谇语,冥然若埽。阃以内米盐齑罋、豉酱醯浆,注造必时;菽粟稻粱、黍麻麦,盖藏必谨。稽出纳,量赢诎,口约腹裁,寸积丝累,一切倚办。”①明人顾起元的记载,也同样说明妇女的日常生活,不过是“深居不露面,治酒浆、工织纫”②。若是加以简单概括,所谓的“酒浆”,就是“主中馈”;所谓“组纴”,就是纺织一类的“女红”。
对于那些勤俭持家的妇女来说,她们的家务劳动有时也确乎能达到孟子所说“有时而养”的标准。换言之,妇女的家务劳动,尤其是她们勤于纺织,往往能起到补贴家用的功效。妇女家务劳动的勤惰,有时关乎一个家庭的兴衰。下举两位妇女,大抵可以证明妇职对于一个家庭的重要性。一是汪子建之妻李氏,为人精勤,即使是每年的三夏,还能纺绵数10觔,积一个多月就织成布二疋,而且还能帮助丈夫教育子女。另一位是沈介甫之妻某氏,每天纺木棉16两,每天至天亮尚未就寝,“长养子女,赖此以给”③。这两个贫儒家庭,一个凭借妻子之勤而起家饶裕,另一个则凭借妻子之勤而免于饥寒之患。可见,明代很多家庭的致富秘诀,其实就是夫唱妇随,既有丈夫在外的努力经营,也必须有妻子在家庭内操持家务,纺织补贴家用。
在一些家庭中,由于丈夫不理家事,那么作为主母就理应承担起主持家庭生产的职责。如钱蕡,字淑仪,杭州府钱塘县人。在她15岁时,嫁给仁和县人卓麟异为妻。卓氏为塘栖的望族,富甲一方,阡陌间架,牵连郡邑,童客数百人。钱蕡的公婆均在北京,而丈夫亦只是读书,不问生产。于是钱蕡就承担起家庭主母的职责,全家的生产之事,全由她一人操劳。她“以弱女子,未明而起,诸事填委候其指挥,左握算子,右征市历,官租岁计,转运贮积,会要不爽毫发,细至庭内洒扫,灶养柴水,亦经心目”④。而有些家庭妇女则相当具有经营才能,将一个大家族的产业经营得有条不紊。如明代著名文人王世贞笔下所记的“龚孺人”,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在盥洗完毕之后,坐在寝堂上,将家中男女数百口点数一遍,让他们各自汇报自己所承担的职责。凡是懒惰者,则加以扑责,而勤劳者则亲自调酒犒劳,于是家中所用之人,各尽所能。举凡畜牧、水产、瓜果、蔬菜,“诸水陆之饶,计口程其羡,时赢缩而息之,醯酱盐豉,不食新者,手植之木可梓而漆,寸石屑瓦,必任务废,以故孺人坐起不离寝,而子母之利归焉”⑤。其经营之才干,乃至勤俭持家,显然是保持家庭稳定的主要原因。
二、传统女性之主要经济活动
作为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明代社会,家庭结构中的女性,她们在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仍然不过是家庭经济的一种补充,具体表现在参与田作、纺织及其他手工生产等生产活动中。
妇女参与田头的农业生产活动,主要是小农家庭的妇女,亦即传统史料所谓的农妇。明代学者陈献章之诗有云:“夫出妇亦随,无非分所安。”⑥每当丈夫外出到农田干活,农妇亦追随其后,一同下田。明人沈氏所著《沈氏农书》亦云:“麦盖潭要满,撒子要匀,不可惜工,而令妇女小厮苟且生活。”⑦这段史料大体反映出,一些田主为了节省工本,不用雇工专门用来播撒麦种,而是由家中的妇女、小厮承担这种播种之职。可见农家妇女,照例应该下农田干活。收获之后,需要重新耕种。家中缺乏耕牛,就只好采用一种“耦耕”之法,其实就是农家夫妻的一种合作劳动方式。明代理学家吕柟记载:“自河以北,夫差之苦,不分男妇。又有男把犁,妇牵犁以代牛者。”⑧在江南松江府,妇女除了承担家中饮食之外,“耘获车戽,率与男子共事”⑨。妇女同样承担着田中耕耘、收割、车水等田间劳动。明代江北妇女,大多务农,插秧不过是其中之一,于是也就有了“插秧妇”之称。戴九灵《插秧妇》诗云:“青袱蒙头作野妆,轻移莲步水云乡。裙翻蛺蝶随风舞,手学蜻蜓点水忙。紧束暖烟青满把,细分春雨绿成行。村歌欲和声难调,羞杀扬鞭马上郎。”⑩明人田艺蘅也用自己的所闻所见,证明这种插秧妇的广泛存在。他所举的例子,就是按江北的习俗,妇女全都务农,而她们的丈夫反而不下田,仅仅是在田边“讴歌击鼓”。[11]
明代江南妇女主要从事纺织。如嘉定县,史称“妇女勤纺织,早作夜休,一月常得四十五日焉”[12]。明人徐献忠也说:“松人中户以下,日织一小布以供食,虽大家不自亲,而督率女伴,未尝不勤。”[13]除了说明妇女从事纺织之外,还指出了江南妇女的辛苦与勤劳。除女织外,妇女还要从事养蚕,凡是从事养蚕的妇女,称“蚕妇”,又称“蚕娘”。从明末人徐光启的家信中可知,他家就专门雇佣了“看蚕妇”,专门从事养蚕之事。又从另一封书信可知,这些在松江府的看蚕妇,很多来自浙江的湖州府。[14]这与湖州的蚕桑业发达有很大关系。史料记载显示,在浙江湖州府,除了正常的农事之外,家中又多养蚕。每当养蚕之月,“夫妇不共榻,贫富彻夜搬箔摊桑”[15]。一些富家养蚕,多由女仆承担。如朱国祯云:“一时任事诸女仆,又相兴起率励,咸精其能,故所收率倍常数。”[16]可见,湖州从事养蚕的女仆大多精通养蚕之术。至于蚕妇的劳动生活,明人李开先、江盈科分别著有《蚕妇》、《蚕妇吟》,给以详细的描绘。[17]在明代,棉花的种植相当普遍。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有一首《木棉吟》,其中有句云:“豆沟零落湿衣裳,捃拾提筐逐兄嫂。”[18]这一记载已基本说明,明代的劳动妇女同样从事棉花采摘的工作。
男耕女织,是江南农家的本务。在浙江桐乡县,几乎是“家家织纴”。至于织妇的劳动生产率,张履祥曾根据自己的经验,亲自算了下面一笔账:“其有手段出众、夙夜赶趁者,不可料。酌其常规,妇人二名,每年织绢一百二十疋。每绢一两,平价一钱,计得价一百二十两。除应用经丝七百两,该价五十两;纬丝五百两,该价二十七两;籰丝钱、家伙、线蜡五两;妇人口食十两,共九十两数。实有三十两息。若自己蚕丝,利尚有浮,其为当织无疑也。但无顿本,则当丝起加一之息,绢钱则银水差加一之色。此外,又有鼠窃之弊,又甚难于稽考者。若家有织妇,织与不织,总要吃饭,不算工钱,自然有赢。”[19]这是一种相当精明的算计。比较富有的自耕农之家,往往自己家中就有织妇。即使是雇佣织妇为其纺织,同样可以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据史料记载,三吴之地,其人大多以织作为业,即使是士大夫家,也多以纺织求利,其俗勤啬好殖,所以相当富庶。如内阁首席大学士徐阶在位时,也“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20]。松江府是明代棉纺织业的中心,无论城乡,均从事棉纺织业。史称“里妪晨抱绵纱入市,易木棉花以归,机杼之声,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获,输官偿债外,未卒岁,室庐已空矣。其衣食全恃此”[21]。妇女的纺织收入,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在明代,流传着“北有姑绒,南有女葛”之说。姑绒其实就是羊绒,因为西域番语称之为“孤古绒”,所以又称“姑绒”。[22]所谓的“女葛”,主要产自广东雷州、增城。关于女葛,明末清初人屈大均有详细记载。[23]广东的织妇还善织蕉布。蕉布以蕉麻为原料,主要产自高要县宝查、广利等村。[24]除此之外,明代妇女尚通过从事刺绣、织袜及制作工艺品等手工劳动,藉此补贴家用。苏州城市中的妇女,大多“习刺绣”。[25]如明代松江露香园顾氏所出绣品,号称“顾绣”,在明末清初已是海内驰名。[26]松江府城西郊开了百余家暑袜店,专门生产用尤墩布制作的单暑袜,极其轻美,吸引了很多远方客商前来购买。这些袜店的产品来源,则是附近的“男妇”。他们都是以制作袜子为生,从“店中给筹取值”[27]。又在松江府嘉定县,当地的闺中女子“间剪纸作灯,人物如画,细见毫发,疑出鬼工”,只是不到市场上出售。[28]
三、妇女经济活动的转向及职业女性群体的崛起
尽管明代家庭的经济格局,仍以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为主,但家庭生活的历史证明,妇女参与家庭经济活动开始出现一些转向,最终导致职业女性的崛起。明代妇女经济活动的转向,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家庭经济格局中,妇女不再是夫唱妇随,而是直接参与经营家庭生计。这在传统的史料中,称之为“妇健”的一种行为,甚至被视为阴阳颠倒,其实却反映了家庭生活中男女角色地位的转换。
当然,在明代的家庭中,同样存在着妇女主持内外的例子,也即家庭中的主母不但承担家务劳动,而且还协助自己的丈夫管理外面的生产事宜。如李敬因为热衷于谈经乐道,不问生产,于是其妻子胡氏就“相其夫,检料内外,筹废举权,以笃其生者甚均且至,而有矩法”;又陈諆之妻劳氏,也是“外应里徭,内治生事”,内外之事一力承担。[29]作为一个读书人家的主妇,尽管自己可以免于下田干农活,但土地的经营,往往也由一些主妇亲自掌管。明代著名文人李开先记其父亲去世之后,因为家贫,他的母亲就“常为农事,一年有七八月在乡村”[30]。而明末清初学者陈确之母,更是深有感触地与儿子讲述了自己一生操持家庭生计的艰难生活,丈夫是一个只知读书,却不知“治生”之人,所以家里的生产,都需要自己亲自安排;因为家境穷困,不但自己需要昼夜纺织,以补贴家用,有时更需要将自己的衣服、首饰典当,使家中暂时度过困境。回到自己的娘家,又需要看娣姒的白眼。[31]
更有甚者,妇女不但在家庭中扮演着主要的管理者的角色,而且走向社会,成为一种职业女性。明代的职业女性众多,其最有代表性的当数三姑六婆、女贾、女佣、苏州梢婆、插带婆、绣花娘、赶唱妇人、瞎先生等。
古人将尼姑、道姑、卦姑称为“三姑”。其中的三姑,即为“觋”的角色。觋的名色,除三姑外,其他如尸娘、看香娘、看水碗娘,[32]均为觋的别名。而“六婆”则为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明代有人主张应将三姑六婆拒之门外,方才做得人家,显然是因为厌恶她们会贻害无穷,败坏家风。[33]
尼姑,在明代又称“女僧”。从小说《金瓶梅》中可知,这些尼姑通晓一些佛教经典,会讲说《金刚科仪》,以及各种因果宝卷。他们“专在大人家行走,要便接了去,十朝半月不放出来”。当然,这些尼姑也会替一些大家族女子寻找符药,以便能及时怀上孩子。[34]卦姑,又称卦婆,其职业是替人“卜龟儿卦”。小说《金瓶梅》是这样描写卦婆的:“穿着水合袄、蓝布裙子,勒黑包头,背着褡裢。”这些卦姑通常也出入妇女闺房之门。[35]稳婆,主要是指替人接生的妇女。牙婆,又称“牙媪”、“牙嫂”,主要是指以介绍佣工或买卖人口为职业的妇女。小说《喻世明言》第1卷中的薛婆,属于牙婆一类。从薛婆所从事的卖珠子的职业来看,所谓的“牙婆”,又可以视为卖婆。[36]卖婆所从事的事情,主要是兑换金银首饰,或者贩卖包帕花线、包揽做面篦头,甚至假充喜娘说合。[37]可见,有时卖婆也充当媒婆的角色。媒婆,主要是指替人说媒撮合之人。在明代,媒婆虽已成一种职业,但也不是专职的,往往是一些妇女的兼职。如小说《金瓶梅》中的王婆,其正业是开茶坊卖茶的,但也兼做媒人,小说称其“积年通殷勤,做媒婆,做卖婆,做牙婆,又会收小的,也会抱腰的,又善放刁”。又说她也会“针灸看病”,也会做贼。[38]上面所谓的“收小的”,即替人接生,属于稳婆的职业行当;所谓“抱腰的”,即指接生时抱产妇腰以助产。可见,王婆虽非专职的稳婆,有时也充当稳婆的助手,甚至直接充当稳婆。于是,小说中的这位王婆已是媒婆、卖婆、牙婆、稳婆、医婆诸种职业集于一身。师婆,主要是指那些巫婆。虔婆,即妓女的假母,俗称“鸨子”、“鸨儿”。药婆,又称医婆,通常出入大家之中,替妇女看病。如小说《金瓶梅》记潘金莲茶饭慵餐之后,吴月娘就让人请来了经常在家中走动的刘婆子前来看病。[39]这位刘婆子就是经常出入大家的医婆。更有甚者,明代还出现了专门的“女医”。从李东阳的记载可知,所谓的“女医”,不过是一些“不识文字,不辨方脉,不能名药物,不习于炮炼烹煮之用”的冒牌货,甚至丸、散一类的药剂,亦不过是用金钱购自太医,却是生意相当红火,甚至不乏为一些士大夫家庭所礼请。[40]
明代专门有一种“女贾”,出入于大家闺秀中间,收买她们的女红之作。从明人李开先关于他妹妹的文字记载可知,那些女贾经常出入于闺门,一方面是收买闺房女子的绣品,而另一方面则是向闺房女子兜售首饰与胭脂花粉。[41]此类女贾,在明代有一种专门的称呼,即卖婆。女商人的出现,足以证明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确乎出现了重大的转向。
自明代中期以后,妇女生活出现了重大的转向。从当时浙江永嘉县的实例来看,妇女不但“行鬻于市”,即公开在市场从事买卖活动,而且轻率出入官府公庭,涉足诉讼案件。[42]在广东的琼州,“妇女出街市行走买卖”[43],亦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以致不得不引起当地官府的注意,出榜禁止。而从事实来看,却是很难禁止。以广东南雄为例,一些山中的妇女,因为丈夫全都“担客装度岭去矣”,无奈之下,只好“跣足而肩柴入市”,做一些小买卖,以补贴家用。[44]从“趾相错也”的记载看,妇女入市做买卖已经相当普遍。
在明代,苏州专有一种“梢婆”,一般在游船上撑船。因为是劳动妇女,相对来说脚较大。[45]所谓绣花娘,即为一些善于针刺女红的妇女。她们凭着自己的技艺出入一些官宦大族,教导闺中女子学刺绣女红。时日一久,有的大家闺秀就被她们引诱成“花娘”。所谓花娘,即杭州人骂娼妓淫妇之称。插带婆,富贵大家的妇女去赴宴席时,往往满头尽是金玉珠翠首饰,自己无法簪妆,就需要专门雇用插带婆,由她们来妆插。首饰颜色间杂,四面均匀,一首之大,几如合抱。即一插带,顷刻间就费银二三钱。等到上轿时,几乎不能入帘轿。到了别人家里,入席,又需俊仆四五人在左右服侍,仰观俯察,但恐遗失一件首饰。而那些作为从人的俊仆,时刻跟随左右,难免熟视动心,以致做出通奸露丑的事情来。为了避免礼教之失,于是插带婆也就应运而生。这种插带婆主要存在于杭州,后在江西建昌也日渐流行。
在明代,专门有一些“赶唱妇人”,到处跑码头,赶场子,藉此糊口。如海瑞在浙江淳安知县任内时,就下过一道禁约,其中云:“各地方凡有赶唱妇人到,图里总人等即时锁拏送县,以凭递解回籍。”[46]妇人赶唱,既有单独行动者,亦有随全家一起外出逐食者。如史载唐姓妇女,为汝阳人陈旺妻,曾“随其夫以歌舞逐食四方”,正德四年(1509),陈旺携带妻子及女儿环儿、侄子成儿一同到江夏九峰山跑场子,[47]更可证明此类江湖艺人是全家一起行动的。可见,尽管自明代中期以后,社会流动更趋频繁,但这些赶唱的妇人并没有到处流动的自由。赶唱妇女中,有些是由“瞽妓”充任。如万历初年,京城有一游侠儿首领朱国臣,其初不过是一屠夫,专畜二位瞽妓,“教以弹词博金钱,夜则侍酒”[48]。明末文学家冯梦龙所称“弹词之盲女”与“行歌之丐妇”[49],无不说明很多赶唱妇女中,很多就是“盲女”与“丐妇”之流。从吕坤的记载可知,在河南归德府宁陵县,也有一些专门从事唱曲、说书的“瞽妇”。如嘉靖二十六年(1547)八月,吕坤的母亲李氏犯了眼病,随之失明。为了安慰母亲眼瞎以后的躁急之情,吕坤“乃召瞽妇弦歌以娱之。歌者辞穷则更其人。或令之说书,如前汉、前后齐、七雄、三国、残唐、北宋之类”[50]。
明代社会正处于一个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时期。妇女生活在像明代这样的社会中,一方面,无论是当时人关于妇女的观念,抑或朝廷所建立的立法制度与礼制规范,无不决定了妇女只能跼蹐于家庭一隅,无法获得参与政治乃至各项社会活动的正当权利。另一方面,自明代中期以后,由商品经济发展所引发的社会流动的加剧,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活力”与“多样性”,无不证明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动荡与变迁时期。社会的动荡与变迁,势必导致由法律与礼制所组成的国家控制力量的削弱,进而使妇女获得了较多的自由活动的空间,并最终决定妇女生活的多姿多彩。在明代,妇女生活渐趋丰富多彩。诸如岁时节日之外出游览,借助神灵信仰而朝山进香,因涉足诉讼案件而轻率出入官府公庭,为娱乐而在大庭广众之下看戏观剧,如此等等,无不说明妇女的生活空间已呈拓展之势。尤其是广泛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职业妇女的大量崛起,更是足资证明妇女在家庭经济生活中开始居于相当重要的位置。
注释
①焦竑:《澹园集》卷三二《封孺人王母郭氏墓志铭》,中华书局,1999年,第506—507页。②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正嘉以前醇厚》,中华书局,1997年,第25页。③[19]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四二《备忘》四、卷四九《补农书》上《蚕务》,中华书局,2002年,第1200、1405页。④黄宗羲:《南雷诗文集》,《碑志类·卓母钱孺人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87页。⑤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八五《龚孺人小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⑥陈献章:《陈献章集》卷四《庚子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华书局,1987年,第295页。⑦《沈氏农书》卷上《运田地法》,《学海类编》,上海涵芬楼据清道光十一年安晁氏木活字排印本影印,1920年。⑧吕柟:《泾野子内篇》卷十九《鹫峰东所语》第廿四,中华书局,1992年,第191—192页。⑨[2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九《松江府·风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⑩褚人穫:《坚瓠九集》卷四《插秧妇》,《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11]田艺蘅:《留青日札》卷廿一《插秧妇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04—705页。[12][28]万历《嘉定县志》,卷二《疆域考》下《风俗》、卷六《物产》,《中国史学丛书》,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13]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十二《风土类》,明嘉靖三十九年刊本。[14]徐光启:《徐光启集》卷十一《书牍》二《家书》三、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83、485页。[15]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中华书局,1981年,第70页。[16]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二《农蚕》,明天启二年清美堂刻本。[17]李开先:《闲居集》卷二,《李开先全集》上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184页;江盈科:《雪涛阁集》卷二《蚕妇吟》,《江盈科集》上册,岳麓书社,1997年,第106页。[18]叶廷琯:《鸥波渔话》卷四《吴梅村木棉吟》,《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20]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四《相鉴》,中华书局,1997年,第39页。[22]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乃服》第二《褐毡》,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第99页。[23][24]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葛布》,中华书局,1985年,第422—425、426页。[25]顾炎武:《肇域志》,《南直隶·苏州府》,引王鏊《震泽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61页。[26]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63页;杨复吉:《梦阑琐笔·识物》,《昭代丛书》,清道光间吴江沈氏世楷堂刻本。[27]范濂:《云间据目钞》卷二《记风俗》,清光绪四年上海《申报》馆仿聚珍版印本。[29]焦竑:《澹园集》卷三二《云南永昌府同知简斋李公配宜人胡氏墓志铭》、《太孺人陈母劳氏墓志铭》,中华书局,1999年,第508、505页。[30][41]李开先:《闲居集》卷七《亡妹卢氏妇墓志铭》,《李开先全集》上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582页。[31]陈确:《陈确集·别集》卷十一《先世遗事纪略·父觉庵公》,中华书局,1979年,第530—533页。[32]徐复祚:《花当阁丛谈》卷七,《续修四库全书》本。[33]吕得胜《女小儿语》云:“三婆二妇,休教入门。倡扬是非,惑乱人心。”其中的“三婆”,即指师婆、媒婆、卖婆;而“二妇”,则指娼妇、唱妇。参见陈宏谋辑《教女遗规》卷中《吕近溪女小儿语》,载《五种遗规》,清道光三十年重刊本。[34]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526、528页。[35][39]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609—612、148—149页。[36]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一卷,岳麓书社,2002年,第5、10页。[37]范濂:《云间据目钞》卷二《记风俗》。按:史载南京沈氏老妪,原本为富家侍妾。后老年无依,只好“卖翠度日”。由此可见,卖婆又多为中老年女性。参见周晖《金陵琐事》卷3《识宝》,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105页。[38]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32、34页。[40]李东阳:《记女艺》,《明文海》卷三四二,中华书局,1987年,第3506页。[42]姜准:《岐海琐谈》卷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20页。[43]海瑞:《海瑞集》下编《禁妇女买卖行走约》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445页。[44]王临亨:《粤剑编》卷二《志土风》,中华书局,1997年,第75页。[45]谭元春:《谭元春集》卷三二《寄四弟广陵买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91页。[46]海瑞:《海瑞集》上编《禁约》,中华书局,1981年,第188页。[47]《明史》卷三〇一《列女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7703页。[48]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八《冤狱》,中华书局,1997年,第479页。[49]冯梦龙编《挂枝儿》卷五《隙部·嗔妓》,《明清民歌时调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9页。[50]郑涵编:《吕坤年谱》,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页。
责任编辑:王轲
K248
A
1003—0751(2011)01—0176—05
2010—10—04
西南大学博士基金项目《明清儒家伦理与社会变迁》(150—432111)的前期成果。
陈宝良,男,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重庆400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