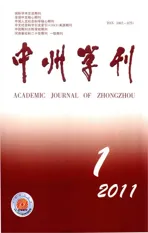孔子“序”《易传》五篇考辨
2011-02-21张朋
张朋
孔子“序”《易传》五篇考辨
张朋
《史记》有孔子“序”《易传》五篇的记载,但是太史公所谓的“序”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对这一关键问题,传统易学家和现代学者的解说都不能够令人完全满意。如果以原始材料为基础,从澄清孔子的易学思想本真和梳理《易传》各篇内容入手,可以另辟蹊径说明孔子“序”《传》的准确含义。因为今本《易传》的内容在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在孔子之前已经广泛流传的《周易》解说、孔子的思想、战国时期儒家学者的思想,所以就历史事实而言,所谓“序”字含有三重含义:整理;讲述;肇绪。只有在“序”字的这三重含义上,孔子“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可信记载。
《易传》;孔子;序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这是关于孔子与《易传》关系的最早记载。但是古汉语中“序”字的含义是比较丰富的,做动词用的时候可以是“排序”、“赠序”、“叙述”等不同含义,太史公所谓的“序”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就传统易学而言,从汉代直至唐代,都认为《易传》十篇全部是孔子所作,因此按照这种说解,太史公所谓的“序”具有“《序》”、“作”和“作《序》”这三重含义。比如《史记正义》就把“序”字直接解释为“《易·序卦》也”,就是指《易传》中的《序卦》这一篇——“序”就是“《序》”;但其又说,“夫子作十翼,谓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系、下系、文言、序卦、说卦、杂卦也”①——这就又把司马迁所谓的“序”字解说为“作”和“作《序》”两种含义。
再比如《汉书·儒林传》有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这就肯定了司马迁所列举的“《彖》、《系》、《象》、《说卦》、《文言》”都出自于孔子的创作,也就认定了司马迁所说的“序”有“作”的含义;而《汉书·艺文志》则云,“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与《史记》中的原话相对照可以发现司马迁所说的“序”字又被解说为“作”和“作《序》”这两个意思。
那么《易传》之中的十篇文字,即《彖》(上、下)、《系辞》(上、下)、《象》(上、下)、《说卦》、《文言》、《序卦》、《杂卦》真的都是孔子所作吗?现在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对于这一点学界已有共识。“战国秦汉之际,儒家学者继承孔子解《易》的宗旨,借助于《周易》筮法的独特结构形式,综合诸家之说,演绎儒家的价值观念,编成《易传》一书。”②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他本人并没有亲手写作《易传》全部篇章,“但不否认孔子曾经讲《易》,不否认现存《易传》中载有孔子的言论”③。所以,传统易学之中对“序”字的解说即使不是错误的,也是不完全正确的。
有些现代学者提出了对“序”字的新解说。比如金德建先生就认为这一句的句读是:“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④这里金德建先生把“序”字与“系”、“说”并列,都解释为动词,这样“序”字的含义就非常接近于“作”(创作),即传统经学之中“序”字的第二重含义。金景芳先生则认为对这一句的理解应该是“孔子晚而喜《易》”,著“序、彖、系、象、说卦、文言”⑤。这里金景芳先生把“序”字解释为名词,其含义是“《序》”,指《易传》中的《序卦》,即传统经学之中“序”字的第一重含义。一个拆拼词句,一个添字解经,现在看来,金德建先生和金景芳先生的解说都显得牵强。
另外,郭沂先生根据《史记·孔子世家》之中的孔子“追三代之礼,序《书传》”和“至于序《尚书》则略”,认为这里的“序”字“有两种解释,一是排列次序,二是序跋之序”⑥,可谓有据。但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理解“序”字,我们恐怕很难给司马迁这句话一个圆满的解说。《史记》作者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受《易》于杨何;而杨何为孔子易学传承体系中的九传弟子,这在《史记》之中有明言。司马迁的易学知识来源于其父,直接承续孔门正宗,所以《史记》中的这一段记载是比较可信的。如果认定太史公的所谓的“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是准确的记载,那么太史公在这里使用相对含混的“序”字而不用含义明确的“作”字就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所以只有在对《易传》十篇的内容进行一番比较彻底的梳理,特别是对孔子的易学思想有一个清楚的把握之后,我们才能够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回答。
孔子对《周易》的解释理路
《系辞》和《文言·乾》中有“子曰”共29句,应该是孔子之语无疑。⑦所以可以通过对这些孔子直接解说《周易》语句的分析讨论来考察孔子解说《周易》的学术理路。《系辞》之中“子曰”共23见,《文言·乾》之中“子曰”共6见,根据其内容不同,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对《易》的整体内涵、功用进行阐述,共计六次,侧重于对义理的阐发。比如:
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第二类是对《周易》个别爻辞的德义内涵进行阐述,共计23次。其中有一些是先在文本之中引用《周易》爻辞,然后引用孔子对这句爻辞的解释话语,共计16次,其中有一句重复。例如: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可以看出,孔子对《周易》卦爻辞的义理阐发非常纯粹也非常灵活,比如孔子解释“潜龙勿用”、“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中的“龙”是“龙,德而隐者也”,“龙,德而正中者也。”那么这个“龙”很明显就是指有德之人,或者说是“德而隐”或“德而正中”的君子、大人;而这种解说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史墨对龙的解说“龙,水物也”有着根本不同,甚至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孔子自己所说的动物之龙,即“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也是决然不类。所以,“《易》之要,德之谓也”⑧可以看做是孔子解说《易》的整体方向和核心原则,这一点绝不含糊。
在第二类之中还有一种情况是直接引用孔子所说过的话,在这些话里面包含着孔子对《周易》爻辞的解说和引用。这种《周易》爻辞引用意味着对《周易》爻辞的义理阐发已经非常彻底和充分,甚至《周易》爻辞已经有了完全义理化的倾向,即如儒家早期著作之中频繁出现的“观点——论证——《诗》或《书》文句”引述格式一样,出现了“观点或论述——《周易》爻辞”的例子。就是说,孔子在讲述一些道理后,往往会引述《周易》爻辞来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论述或观点,这就像是引述《诗》或《书》的文句一样。这说明就阐释其中义理的角度而言,《周易》已经与《诗》、《书》相等同。例如: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不难看出,孔子在阐发《周易》爻辞的“德义”内涵之时,不讨论更不寻求义理的卦象或爻象根据。⑨所以孔子在对《周易》进行“德义”阐发的过程之中,非常彻底地抛弃了《周易》爻辞的象数根据。这种义理改造完全覆盖了春秋时期原本“据象说辞”的解说逻辑,代之以纯粹义理推演和教训开示。
虽然在所有的例子之中孔子都是在解说《周易》爻辞而没有一例是解说《周易》卦辞,但是通过对这些实例的研读我们可以相信,孔子对《周易》卦辞的解说也是只阐发义理而不涉及卦象以及爻象。我们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孔子的义理阐发比较自由,其中没有追求体系化的诉求。
“唐以后人们才逐渐弄清了《易传》虽蕴含孔子思想,但非孔子亲笔所作,乃其弟子或再传弟子所作。”⑩准确讲,除了自古流传的思想资料外,《易传》中的很多内容是孔子口授而由其门人弟子们记录整理的,这是先秦诸子著作的惯例。当然,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况是,门人弟子们在文本之中又加入了很多自己的理解和阐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各自时代的思想。就整体而言,《易传》有一个长期的形成过程,即经过讲授、记录、整理、汇编等一系列的渐进和反复,所以《易传》的编纂者也不止一人,应该是从孔子到西汉儒者的这样一个“创作——编纂”群体。
针对这种情况,以孔子和孔子的思想为基点,我们可以将今本《易传》的内容在总体上分为三类:在孔子之前已经广泛流传的《周易》解说;孔子的思想(主要是孔子弟子对孔子言论的记录、整理和一些必要的补充、完善);战国时期儒家学者的思想——即如金景芳先生所说:《易传》“里边有记述前人遗闻的部分,有弟子记录的部分,也有后人窜入的部分”[11]。
基于对《易传》内容内在学术理路上的划分,我们可以区分出孔子对《易传》所作的三种工作。
整理、编排
毫无疑问,孔子对六经都做了整理工作。那么,孔子整理、编排了自古流传的哪些易学资料呢?
现在看来,这些思想资料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自古相传的对《易》或《周易》进行解释说明的比较系统的文字资料。从《周易》编创的殷末周初到孔子时代,对《周易》一定有一套系统的解说。《左传》、《国语》之中的22个筮例,以及《左传·昭公二年》所提到的《易象》都是这种典籍存在的明证。而且,由于这种资料对《易》的解释具有权威性,古代的学者对它都一定会极为重视。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12],他对这种材料最为可能的处理办法是按照原文直接抄录,对其中特别完整的内容的处理极可能是单独成篇。这种单列的篇章在孔子至西汉初年数百年的抄录、流传之中即使有意无意地混入一些其他的内容,或者部分文字有所改动,但这只是局部的情况,应该并不影响其整体和主要内容。
很明显《说卦》就是属于这一类,正所谓“成书迟,其中包含的思想可以很早”[13]。阴阳观念以及五行、八卦观念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只是由于古代文献保存极为困难,致使其见诸文字比较迟。从文本来看,《说卦》除了开篇的第一章、第二章很明显是战国时期编入的具有义理阐发性质的两段文字以外,其余的都是对八卦卦象的阐述和八卦取象的例证,这些是自古相传的对《易》或《周易》进行解释说明的文字资料。“从其内容言之,它专言八卦,是易学最基本的理论。也就是说,无论是解说《周易》,还是运用《周易》筮占,皆离不开八卦卦象的分析,而且这是重要的一步。”[14]《说卦》中保存的这些自古相传的解《易》资料很可能就是《左传·昭公二年》韩宣子所说的春秋《易象》的主要内容。只不过由于《易传》编纂者的改动,把这篇文字的标题写作“说卦”,却把“象”这个含义更为深刻的标题放在典型的儒家作品《象传》上面——虽然这个《象传》中的义理解说与原本的《易象》在学术理路上差异巨大,而《说卦》篇首则被加入了一些经过整理的孔子说《易》的文字,这就为《说卦》加上了一顶儒家的帽子。
第二种,自古相传的对《易》的口头解说,特别是对于《易》的创作、八卦起源、《易》的基本原理等最基本、最关键问题的解释。因为时间上溯久远,人们理解《易》的基础就是这些口口相传的对《易》的作者和《易》的创作情况的描述和解说。孔子等《易传》编纂者把听到的这些资料记录下来,再进行一定的加工和润色,就形成了《系辞》中的很多内容,比如“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值得注意的还有一些对《周易》的解说似乎是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形成的卦爻辞义理解说,这也在《易传》之中得到保存,比如《乾文言》之中对“元亨利贞”的解说则在《左传·襄公九年》穆姜的话语之中出现过。
第三种,关于《周易》占筮的资料,其中有些可能是文献,更多的可能就是口头代代传授。这些资料来自于与孔子同时代的卜官、筮者,或者是当时掌握《周易》占筮相关知识的学者的阐述讲解。“学而不厌”的孔子周游列国,拜访过很多学者,而其中很可能就有人特别擅长《周易》占筮。春秋时期《周易》的基本应用就是占筮,孔子自称“百占而七十中”[15],显然他专门学习过占筮并曾经多次实践——这是当时学习《周易》的重要方法。这部分内容包括《系辞》中有关于“大衍之数”的记载、占筮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操作、对占筮的评论等内容。
陈述、讲解
根据上面对孔子易学思想的讨论,《易传》中包含的与孔子思想相关的内容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孔子的原话,即孔子弟子门人对孔子的讲述进行记录和整理而形成的文字资料。《系辞》和《文言·乾》中共有“子曰”共29句,可以都归入这一种。
第二种,孔子弟子门人对孔子的讲述记录进行补充、完善后而形成的思想资料。沿着孔子的思路,儒门学者对孔子思想的补充和完善,比较严格地遵循了孔子的学术理路。虽然阐释角度、阐释重点不尽相同,但是总体而言,仍然可以归属为孔子的思想。
《系辞》之中还记录着孔子多次对同一问题或相关相近问题的申说,有的是论述角度不同,有些则仅仅是部分文字不同,但是也被忠实地一一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可能有不同的传承来源。可以想象,在一个比较长的成书过程中,《易传》中的材料不停地被儒家学者们收集和整理,进而被加工和补充,很可能经过了上百年才最终定稿,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具体而言,金德建先生曾经明言:“《系辞传》和《文言传》的产生,最迟不能再过于子思的年代。”[16]近年来李学勤先生根据其对古代典籍和出土文献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17]
肇绪
在《易传》之中,包含着很多战国时期儒家学者的思想,而这些思想的学术理路与孔子的解《易》理路并不完全相同。那么,这些思想之中的学术理路与孔子对《周易》的解说理路究竟有着怎样的差距呢?
与孔子的阐述思路相对照,我们可以发现,后期的儒家学者们以“德义”为导向继续对《周易》进行阐释时进行了“理论创新”,或者说他们对孔子的原有的学术理路进行了一些“修正”,而这种“理论创新”或“修正”就体现在讨论德义的象数根据和力图使《周易》卦德卦义解释系统化、完整化。因此这些晚出的《周易》解说与孔子没有直接关系,主要是后代儒家学者的思想。孔子的《周易》解说仅仅是“肇其绪端”,而儒家后学则紧紧抓住“德义”而大加发挥,多方铺陈而力求完备,从而形成了非孔子所“述”的《易传》的一部分内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了孔门传《易》的谱系:“孔子传《易》于(商)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这个传承过程长达两三百年,很可能只是一支主线,而这些儒家易学传承者肯定在《易传》里写下了自己的义理发挥和理论创造,而且字数不会很少。
就其学理内涵而言,这些儒家学者们的思想进路又可以分解为三个理论展开的维度。
第一个维度:以八卦卦象生发义理,即以八卦卦象作为儒家义理的根据,以《大象》为代表。这一个理论向度的理论发育完全,内容也非常完整。这个解说维度无疑与春秋易说有内在的承接关系,所以其出现应该比较早,很可能是在战国早期。
第二个维度:为儒家义理寻找爻象根据,即以爻象解说儒家义理,这以《小象》为代表。这一个理论向度的理论发育不完全,尽管在形式上其完成了对《周易》爻辞的全面解说;其产生可能是在战国中期,而对其解说方法的完善和补充则一直持续到汉代,并最终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爻象说”。
第三个维度:用义理解说《周易》卦序,即以义理解说通行本《周易》之中的六十四卦卦序,以《序卦》为代表。这一个理论向度的理论发育完全,内容非常完整。但是由于理论基础的先天缺欠,其论说往往缺乏说服力,可以说是一个并不成功的“理论创新”,但其在易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沿着孔子阐发德义的解《易》理路,很多儒家学者对《周易》解说都进行了一番发挥创造,导致儒家易学不断地被整理、完善,最后才形成了《易传》文本,并使得其中大部分内容具有明显的儒家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的原话里面没有提及《序卦》和《杂卦》。《序卦》“似当成书于战国末期,或秦汉之际”[18],《杂卦》则稍晚于《序卦》。所以《易传》之中的《序卦》和《杂卦》两篇距离孔子时间最远,其内容也与孔子思想基本没有关联。但是由于某些历史机缘,特别是由于汉代经学兴起,它们也堂而皇之地名列《易传》之中了。
结语
经过以上分析讨论,我们基本完成了对《易传》各篇思想内涵的梳理和分期断代,这样就得到下面这一张图表,其中符号“○”表示各篇之中有部分内容属于对应的种类(见表1)。
总体而言,孔子与《易传》的关系比较复杂,根据以上的原始材料分析,所谓“序”字应该含有三重含义:
1.整理、编排
司马迁所说的“序”字含义虽然比较模糊,但是无疑有整理、编排的含义在里面,吕思勉先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序者,次序之谓,原不谓其辞为孔子所自作。然则《彖》、《系》、《象》、《说卦》、《文言》盖皆《周易》之旧,孔子特序而存之尔。”[19]这里的“序”字含义也就与《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的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里的“序”字含义近同。
2.陈述
“序”即“叙”,陈述。孔子陈述《易》之大义,即“我观其德义耳也”[20]。这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的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里的“序”字含义相同。
3.肇绪
孔子陈述《易》之大义之后,战国时期的弟子又对《周易》卦爻辞的“德义”大加发挥,使之趋于完整和系统。所以对于《彖》、《象》、《文言》而言,“序”即“绪”,开启头绪,“肇绪”就是“序”的第三重含义。
只有在“序”字的这三重含义上来理解,孔子“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可信记载,而太史公使用含义比较丰富的“序”字来表述不妨说正是一种“模糊”的准确。
注释
《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937页。余不赘注。②③⑦杨庆中:《周易经传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前言第1页、第166、166—171页。④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94—95页。⑤[11]金景芳:《关于〈周易〉的作者问题》,《周易研究》创刊号,1989年。⑥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79—280页。⑧[15][20]帛书《易传·要》。⑨前面引述的孔子话语里面即使出现了“中”、“位”、“上位”、“下位”等字句也是义理概念,没有非常明确的爻象意义,这一点比较明显,比如第一类之中的“而易行乎其中矣”、“其言曲而中”,第二类之中出现的“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贵而无位”、“贤人在下位而无辅”、“龙,德而正中者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上下无常”等都没有爻象的意义。⑩刘玉建:《两汉象数易学研究(上)》,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9页。[12]《论语·述而》。[13]任继愈:《敦煌〈坛经〉写本跋》,《任继愈来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279页。[14][18]刘大钧、林忠军:《易传全译》,巴蜀书社,2006年,第33、35页。[16]金德建:《先秦诸子杂考》二十五,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17]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第102—105页。[18]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12页。
责任编辑:涵含
B222.2
A
1003—0751(2011)01—0155—05
2010—06—07
张朋,男,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200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