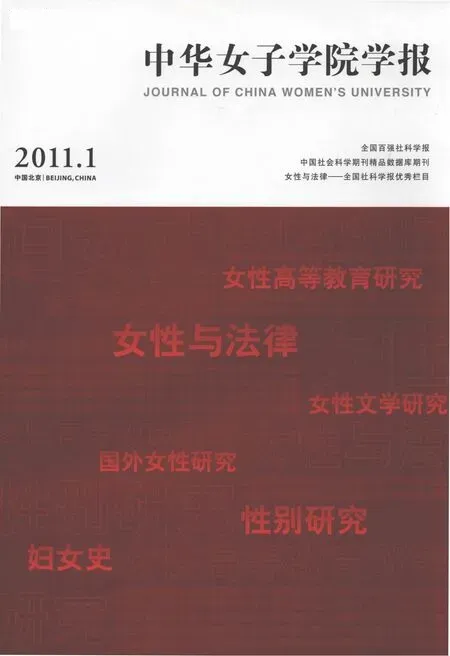略论法学教育中性别平等意识的培养
2011-02-20张敏
张 敏
略论法学教育中性别平等意识的培养
张 敏
我国法律笼统规定男女两性在各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然而这样的法律规定并未完全实现男女平等的立法目的,男女两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领域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平等。教师在教授学生法学理论与法律制度的同时,应注意将性别平等的意识纳入法学教育过程中,为学生讲解分析法律制度的同时引领学生观察和思考法律制度的实施后果,引导学生发掘并反思法律制度在中性化规定背后隐藏的性别不平等。
法学教育;性别平等;性别差异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法律制度中,除专门针对女性进行保护的特殊规定之外,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下将女性抽象为与男性相同的平等主体,对女性和男性进行统一规定,国家以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形式,自上而下赋予女性一系列的权利,如男女平等、选举权、受教育权、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力图保障女性“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我们在法律教学的过程中认为女性与男性是完全相同的平等主体,平等地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平等地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平等地履行法律赋予的责任。这种对两性不加区分的法律规定标志着旧时代备受压迫的女性法律地位得到了提高,是女性寻求解放追求平等过程中的巨大进步。然而回望我们的现实生活,女性在取得法定的财产权后,是否与男性在经济上真正平等?在取得选举权后,是否顺利地当选为人大代表、政府首脑或者国家元首?我们发现女性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非意味着女性能够在政治地位上与男性有相同的话语权,促进男女平等就业的法律规定也没能完全改变就业过程中广泛存在的对女性的歧视,女性与男性平等的继承权的法律规定在事实上也难以改变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传统继承制度。这些性别中立的法律规定在运行中产生性别偏差的原因在于我们传统法律制度设计中,忽视了女性和男性的生理差异和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而造成的女性在文化、经济、政治上的弱势地位和资源占有上的不利处境,使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很难实现法律所预设的平等权利。因此在当前的法学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不但要教授给学生基本的法律制度和相关理论,还要指导学生思考法律制度运行的后果,观察平等规定两性权利的法律制度如何在运行中产生性别偏差,引领学生从社会性别视角观察我们的法律制度,考察“性别中立”的法律制度中隐藏的性别倾向和对女性的不平等。
当前的法律制度和法学教育背后潜藏着传统文化观念对性别与性别角色社会化的认识,隐藏在法律制度和法学教育过程中的这些价值取向,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价值观。在法学教育中我们必须引导学生看清法律制度背后隐藏的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将性别平等意识的培养纳入我们的授课过程中。这就首先需要改变当前主要是根据男性思维方式组织和实施的法学教育,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当前的法学教育中,改变现代法学教育赖以建立的以男权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从性别视角改革法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因为我们的法学教育不只是教授学生学习法学理论与法律知识,同时也影响着学生世界观的形成,法学教育能否提供全面而准确的理论指引,将直接影响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如何将法律制度与理论背后潜藏的主流文化对性别与性别角色社会化的影响引入我们的课程,如何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到法学教育中,引领学生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客观公正地看待当前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将性别平等意识引入法学教育的必要性
1.法律在性别问题上的忽视
在当前法律制度、法律理论、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中,性别并不是法律要关注的重要问题。近现代法律的宗旨是追求自然人人格的一律平等,于是法律将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个体的国籍、年龄、性别、职业等因素都过滤掉,使其高度抽象后成为建立在人格基础上的平等个人,于是处于不同条件中的具体主体在法律制度中被抽象为平等主体:在公法统辖的政治国家中,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选举权,是自由平等的公民;在私法统辖的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自由意志和独立的财产所有权,是无差别的平等主体。这种高度抽象使平等主体呈现理想化色彩。生活在这理想化境界中的平等主体拥有独立的财产权和自由的意志以及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抽象的女性与抽象的男性享有相同的法律权利,法律不考虑性别因素对法律的作用以及抽象的法律对不同性别主体的具体作用与影响。然而这种“理论是在抽象人格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不考虑当事人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状态和联系。”[1]62法律将其主体认定为抽象的平等的个体的同时忽视了处于具体社会生活中的个体间的差别。我国的法学理论研究、法律制度建设和法学教育都是在借鉴移植西方法律的过程中完成的,我国法律制度中也如同西方传统法律制度一样,将法律关系中的主体抽象为全部平等的个体,忽略了其个性的存在,将女性与男性视为完全平等的主体,赋予女性与男性相同的权利与义务。同时在我们的法学教育中,一直以“男女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抽象原则和女性与男性享有平等的权利义务的法律规定教导学生。这样的法律规定和法学教育,将主体视为一律平等的个体,使女性在争取平等上获得了法律规定的机会,看到了更多解放自己的希望,但是这种平等规则无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处境而给予同样的对待,只会重复甚至可能加剧既有的不平等。事实上,纵观我们的生活,很容易发现抽象的平等主体离现实社会中的人越来越远,平等主体越来越成为空洞的说辞。如果法律不考虑性别问题,忽视男女两性在社会中的具体差异,用平等的法律制度通过无性别倾向的“中性”立法来保障和促进女性权利从而实现男女平等是难以成功的。只有将性别意识纳入法律的视野中,正视女性的性别特征及男权社会延续的性别观念,才能制定出更具可行性的法律规定,进而逐渐缩小乃至消除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机会、教育等方面受到的歧视性待遇。法律要实现对社会关系的有效调整不得不考虑性别问题。
2.法律制度中隐含的性别倾向
法律的创制都具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并内涵特定的价值取向,当审视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时,我们应该引导学生关注制约着法律制度设计的社会背景及其价值取向。传统社会制度包括法律制度主要建立在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观念之上,一直是按照男性的意志建立并运行,“法律用男性认识和对待女性的方式来认识和对待女性。自由国家按照男性这一个性别的利益来强制地和权威地建立社会秩序——通过其合法化的规范、制度、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实质性政策。国家的正式规范在(制度)设计的层面概括了男性的特点。”[2]233法律按照男性看待和对待女性的方式来看待和对待女性。法律作为一种男性统治的工具,控制和调节着男性获取各种资源,如工作、土地、财产、机会等特权。反过来,这些特权又巩固和加深了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和社会结构。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在教授学生学习理解法律的平等与正义原则的同时,应该帮助学生认识到法律的平等与正义的价值理念是根据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遗传下来的男性标准建立的。法律从实在法的角度论,倾向于反映现存的权力结构。[3]229现行法律规定对男性主体与女性主体不加区分统一对待,事实上是用抽象的平等、公平、公正的价值名义掩盖并不断复制与强化法律制度中隐含的男性特权。尽管法律常常以中立自居,但却包含了性别歧视的内容,并且也正是中立的标准才使社会性别的结果在法律上得以正当化。[4]34因此,我们需要引领学生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剖析法律制度所追求的平等价值理念背后潜藏的对男性特权的确认与维护,认清法律制度与其他社会制度一起对社会性别等级系统以及广泛存在对男性特权的支持与构建,在此基础上才能看清法律制度在性别中立与平等的表象下掩盖着对女性的不平等。
3.性别差异对女性实现法律权利的制约
由于男女两性自然性别差异和女性被压迫的历史传统观念,以及在现实中男性和女性在拥有社会资源这一关键条件上的不平等,导致社会中女性与男性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在社会中仍然处于弱者地位,他们对各种资源的实际利用能力弱于男性,他们对公共领域的参与能力也弱于男性,他们的权利实现能力自然也落后于男性。这就导致法律规定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婚姻自主等保障女性平等地位的制度无法转化为男女平等的社会现实。因为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社会制度的运行受社会观念的制约,制度转化为现实需要与其匹配的社会观念的支持。而我国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的思想已经沉淀到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一代代传递,不可避免地隐含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男权意识仍然积淀在人们社会观念深处。宪法和法律关于男女平等的规定无法对抗传统社会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观念和其他调整社会关系的制度规范。因此,虽然我们在法律制度中恢复女性作为权利主体的社会资格,但是延续下来的对性别的社会观念不仅制约着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待和价值评价,也制约女性的主体行为及其权利的实现。事实上性别“中立”的法律制度忽视了现实的女性和男性的生理差异以及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原因而造成的女性在文化、经济、政治资源占有上的不利处境,使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很难实现法律所预设的平等权利,使真正的性别平等难以实现。法律对性别差异的漠视造成了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将法律规定的权利转化为自己确实享有的权利。所以在法学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考虑法律规则,还需要思考法律规则实施的效果,反思法律无视两性差异导致性别不平等后果的制度缺失。我们在法律的教学中,如果不能帮助学生正确认识两性的差异及其对法律运作的影响,就很难将这些隐藏在调整日常生活的法律制度中的性别歧视识别出来,并加以改善,那么带有性别歧视的法律制度的施行会不断重复确认并复制新的性别偏见。
三、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法学教育的设计
性别平等应是法学教育的理念之一,应该体现在一套教学设计的有关环节中。但是理想的渗透着性别公平理念的法学教育并非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在教学实验中不断完善。在法学课程中加入性别意识的培养,将培养具有性别平等意识的现代高素质法律人才作为目标,通过案例分析、角色模拟、小组讨论、模拟法庭、影视评论等形式,采用互动教学法,为学生学习法律制度、分析法律问题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和先进的理念。下面我们以虐待罪为例,看一下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法学教育时的具体理论演进思路。
1.案情介绍
2009年10月19日,刚刚结婚10个月的26岁的董某被丈夫王某殴打致死。2010年7月2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对董某案作出一审判决,王某犯虐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零6个月,赔偿死者家属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81万余元。王某不服上诉后,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终审维持原判,以虐待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6年零6 个月。[5]
2.虐待罪的法律规定和立法目的
虐待一般被认为是指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经常以打骂、冻饿、禁闭、强迫过度劳动、限制人身自由、凌辱人格等方法,进行肉体上、精神上的摧残和折磨的行为。[6]1033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了家庭成员中一方对另一方虐待的犯罪行为及其刑罚。这条法律既规定了丈夫实施虐待妻子的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同时按照此规定,如果妻子虐待丈夫的话,那么妻子也应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从法律文本的规定来看法律对两性是公正和平等的。然而,十分明显,虐待是建立在家庭成员地位不等的基础上的,多是家庭中强势一方施加给弱势一方的,从两性关系来看,女性囿于体力和经济能力等原因往往在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而男性多在家庭中处于强势地位,两性间的虐待多是丈夫施加给妻子的。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的虐待罪的本意是为了保护家庭中的弱势者,是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精神,维护家庭中弱小成员的人权。从家庭中的两性来讲,是为了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
3.从司法实践看虐待罪隐含的对女性的不平等
如果关注虐待罪的司法实践,我们会发现虐待罪在司法中适用的结果与其立法目的大相径庭。正如董某案所示,虐待罪在司法过程中适用最广的是家庭暴力案件。现实中的家庭暴力源自一个家庭中各方地位和力量的不对等,多是家庭中处于强势地位的男性对女性施加的,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女性。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专门的“家庭暴力罪”,家庭暴力行为从理论上可能触及的罪名包括: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非法拘禁罪、侮辱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虐待罪等,常见多发性的犯罪类型主要集中在虐待罪、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上。[7]从审判实践来看,因家庭暴力致伤致死的案件常常以虐待罪处理,比如,在董某案件中,王某多次对董某施加暴力行为,最终导致董某死亡。而对这样的犯罪结果,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以虐待罪论处,使施行家庭暴力的男性在法律规定之下逃脱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等重罪的处罚。
4.从法理角度分析虐待罪的法律规定中隐含的对女性的漠视
王某对董某施加暴力的犯罪行为直接侵犯的法益是董某的人身权,同时对董某的精神造成更大的伤害,使其终日生活在不安与恐慌当中,另外王某对妻子的残忍暴力也是对家庭秩序和家庭伦理的破坏。在刑法中,这种伤害多重法益的暴力行为的刑罚却远远低于单纯伤害人身权的故意伤害罪的刑罚。虐待罪的刑罚设置是不是需要重新考虑?王某与董某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是否应使得王某对董某施加暴力的虐待行为具有更大的可非难性?同时我们观察刑法对同属于虐待型犯罪的虐待被监管人罪的规定,此规定相对于虐待罪的刑罚更为严苛,对出现重伤或死亡结果的直接适用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反思,法律为什么对处于婚姻家庭中的暴力行为规定与其危害后果不相称的法定刑?既然同为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都是虐待行为,为何法律要宽恕虐待家庭成员的犯罪人呢?为什么法律要在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杀人罪之外,为侵犯对象是家庭成员的施暴者另行规定一个虐待罪罪名,以帮助家庭中的施暴者逃脱法律的严惩呢?如果董某案件中的施暴者是一个陌生人,毫无疑问将以故意伤害致死或者故意杀人论处,然而就因为王某是与董某共同生活的亲人,他在家庭中扮演的丈夫的角色就可以使其逃脱重罪的处罚吗?
虐待罪本应作为对抗施暴者的法律武器,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家庭成员的基本权利。然而现实中虐待罪却成为家庭中的施暴者逃脱重罪处罚的避风港。“家庭成为那些日益兴旺的私人和自由领域的避难所……常规人权法中家庭神圣不可侵犯的根源存在于各种叙述的汇聚点。它使亲密关系的等级秩序合法化;它隐藏在叙述性主张的避难所之中。这些主张声称,作为社会单元的家庭在国家范围之外。爱和亲密关系成为把家庭单元置于‘公正之外'的边界卫士。”[8]108刑法规定的虐待罪虽然形式上平等适用于男女两性,在规范层面上保护的是每一个家庭成员免受另一个家庭成员的虐待,然而事实上掩盖着对女性主体的漠视和对女性的歧视。从虐待罪的法律适用后果可以看出,此法律规定保护了家庭中的施暴者,使家庭生活中的不平等被法律制度不断地重复与确认。在此,法律并没有起到其预设的保护作为弱势一方的女性的立法目的,此规定在事实上维护了男性特权,保护了在家庭中处于强势地位的男性的利益。由此可以看出,对两性平等适用的法律制度并不是平等对待每一个人,女性在刑法制度中仍然是受歧视的主体。
四、结语
法学教育是对法科学生进行性别平等教育的基本途径,要培养法科学生的性别平等观念,有必要在法学教育中传播性别平等意识,使学生系统地认识到社会中两性之间显性和隐性的不平等状况以及产生的根源,了解不合理的性别状况对两性发展的限制,善于对身边所发生的有违性别平等的事实和法律制度进行思考并提出质疑,积极探寻实现性别平等的现实路径,从而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为打破社会性别等级制度的束缚,不断开拓两性平等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而积极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性别平等意识的培养至关重要,因为只有教师具有性别平等意识,才能自觉地寓性别平等教育于教学之中。教师是推行性别公平教育最直接的传播者、施予者和参与者,在他们的思想中形成公正的性别意识,将直接影响到一代人,乃至整个社会性别观念的更新。[9]
性别视角是现今世界观察、思考、分析和评价社会现象的极其重要的思维方式。在法学教育中纳入性别平等意识的教育与培养能够拓展学生的视野,填补学生的性别盲点,提高学生的性别觉悟,促使他们的性别平等意识觉醒。只有意识到性别视角的重要性,并能够以性别平等的观点重新认识社会现实和法律制度,方会对自己身边所发生的有违性别平等的事情进行思考,并由此对既存的法律和社会制度提出质疑。当学生学会并善于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去观察、分析和批判某一法律和社会制度时,他们就会产生改变不平等现状的积极愿望,而这恰恰是逐步构建新的社会性别观念的希望。
[1]傅静坤.二十世纪契约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凯瑟琳·A·麦金农.迈向女性主义的国家理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3]王政,杜芳琴.社会性别研究选择[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4]周安平.性别与法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5]邱伟.新婚妻子遭家暴被殴打致死,曾8次报警不管用[DB/OL].http://www.chinanews.com/fz/2010/11-23/2675475.shtml,2010-11-23.
[6]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第三版)[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
[7]陈航.值得深思的刑法“宽”、“严”倒错问题——以常见多发型家庭暴力犯罪为例[J].犯罪研究,2007,(1).
[8]丽贝卡·J·库克.妇女的人权[M].黄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9]赵艳红,等.用社会性别意识审视中国的女性教育[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责任编辑:贾 春
Discussion on the Cultivation of Awareness of Gender Equality in Legal Education
ZHANGMin
(Law School,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s:Although men and women have equ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in our legal system,there are still gender inequalities in political,economic,cultural and other fields of our social life.In the process of legal education,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awareness of gender equality while teaching students to analyze the legal theory and system.We should also lead the students to observe and reflect on consequence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and guide students to discover the neutral gender inequality hidden behind the provisions.
legal education;gender equality;gender difference
10.3969/j.issn.1007-3698.2011.01.022
C913.68
A
1007-3698(2011)01-0119-05
2010-12-12
张 敏,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08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法。100872
本文系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一般项目“反歧视法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6SFB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