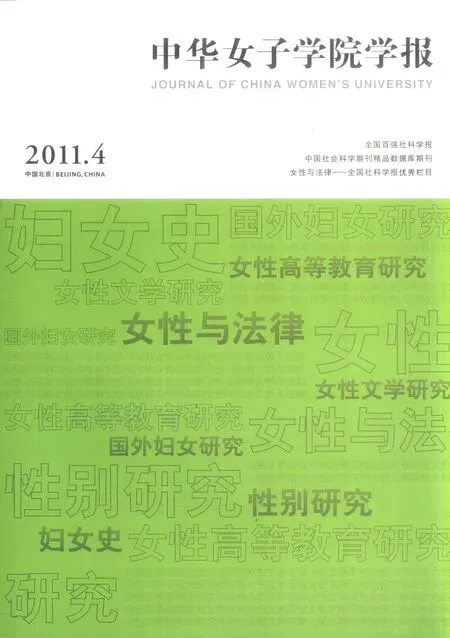妇女史研究的瓶颈
——关于史料鉴别问题
2011-02-20高世瑜
高世瑜
上世纪80年代,当我尽力搜罗资料、撰写那本后来将我带入一个全新领域的小书《唐代妇女》时,虽倍感艰辛,但心理轻松——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有什么“妇女史”,也完全不了解任何妇女学、妇女史理论方法;只是把它当做唐史、唐代社会的一个侧面,尽力将有限史料拼接成一幅历史文化图卷而已。应了“无知者无畏”这句话,因为无知,又没有现成模式可鉴,写作时也就率意任情,文史兼及,议论评说,了无顾忌。
90年代后,随着妇女史学科的逐渐兴起,先行者们翻译引进和探讨有关妇女史、妇女学理论方法的著作日渐增多。当我由于那本小书无意中被“裹挟”进这一全新领域,并为这一新兴学科所吸引,放开眼界,开始认真读书时,才发现原来还有如此新奇、奥妙的一个世界!尤其是于本世纪初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期间,集中阅读了许多以往没有接触过的国外及港台有关妇女史、妇女学、女性主义、性别学等理论著述和妇女史著作,接触了各种令人目眩、发人深省的五花八门的理论观点、研究方法,也看到了国外、港台等先行学者们的各种研究样本,并与学者们有了各种层次的对话时,我不免变得越来越胆怯了。我越来越弄不清到底什么是妇女史,林林总总的理论方法中到底哪些是正确和适用的,自己所作是否称得上“妇女史”,或者说以妇女为研究、写作的对象是否就能理直气壮说是“妇女史”。
困惑中,我曾将遇到的理论问题归纳为8条,即:1.历史的客观性与女性主体意识;2.解构、疑古与信古;3.共性、整体性与个性、个体差异;4.当代价值判断与历史人物的主体经验;5.被动与施动的两面性;6.生物决定论与社会造成论;7.性别与其他身份、等级的交叉;8.妇女“地位”问题。[1]多年后的今天,妇女史研究有了很大进展,不仅研究成绩硕果累累,学者们也做了大量的学科理论建设工作。当回过头去再看这些问题时,感到他们仍然是压在我心底的“问题”,仍有需要继续思考、探讨之处。而在当下着眼生活、注重细节的实证研究日益成为妇女史研究主流的时候,我感到,以上诸多问题中,最首当其冲也最困惑难解者应该说是以上第一、第二条,即“历史的客观性”和“解构、疑古与信古”所涉及的如何对待历史文献记载问题,或者说是史料鉴别问题。
毋庸置疑,无论信奉何种理论,史料永远是实证研究的根基。笔者曾将史料比作米,理论方法则如同烹饪方法,倘若没有米或米是假的,即使烹饪方法再好也无济于事;反之,倘若有了米,即使烹饪无方,至少还是饭食。也有学者将史实比作需要加工的鱼:“历史学家可以在文献、铭刻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那里获得事实,就像在鱼贩子的案板上获得鱼一样。历史学家收集事实,熟知这些事实,然后按照历史学家本人所喜欢的方式进行加工,撰写历史。”[2]90寓意大体相同,即史料、史实乃是实证史学最基本的要素。因而,史料鉴别问题也就成为从事妇女史实证研究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而这一令人困惑的难题也因此成为妇女史研究的瓶颈。
一
史料鉴别首先关乎历史文献记载的客观性、真实性问题。这一点对于古代妇女史尤为重要,因为古代史不可能依赖口述史、个人亲历等去建构。除了少量可信度相对较高的考古、文物资料外,它依赖的主要就是汗牛充栋的传统文献记载,而这也最受人质疑,因而也是最为需要鉴别的。
对于文献记载,传统史学领域本来就存在“疑古”与“信古”之争,在当代又面临后现代理论的挑战。传统的“疑古”学派对于古史记载持怀疑态度,认为古代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后现代主义则干脆断言:“历史学是一种文学的形式,根本不是一项科学的事业。不存在历史真实,而只有虚构。”[3]二者虽然背景不同、立意有别,但对待历史文献记载却有相通之处:都对史载文本的真实性、客观性表示怀疑甚至进行颠覆;或者致力于解读与解剖,试图发现文本背后隐藏的背景与密码。笔者认同其合理之处,即虽有客观存在的历史过程与事实,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没有完全“客观”的历史记载。“我们所接触到的历史事实从来不是‘纯粹的历史事实’,因为历史事实不以也不能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历史事实总是通过记录者的头脑折射出来的。”[2]106可以说,任何史载都是记载者的“记忆”与阐释,都加入了记载者的思想判断,都是史家的“建构”。
妇女史面对的问题更为棘手,因为它面对的全部是由男性书写、从男性视角观察、体现男性主体意识的历史,或者说是男性的记忆与阐释,撰述者站在男性立场或出于性别偏见对历史时有取舍甚至歪曲、杜撰,是可以肯定的;即使有少量的妇女文字,也很难说就是其内心世界的真实表达,而更有可能体现的是对男性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服膺与迎合。面对几乎全部站在一方、偏向一面的“男性制造”,完全中立、真实、客观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作为以妇女为主体的妇女史,又特别强调女性主体意识与女性视角,注重女性一方的生活体验与感受。从这一角度说,则客观、中立似乎更加遥不可及。而且,女性主义学者不承认历史记载的客观性:“所谓客观资料与普遍定律,皆是特定社会性别、阶级、文化、历史与权力体制下所建构的阅读与话语。”[4]换言之,即并无纯客观的资料与结论。一些妇女史学者也主张历史本无客观性和所谓真实性,认为历史本来就不是被“发现”的“事实”与“真相”,而是历史学家“建构”的对于过去的叙述方式,或者说任何历史记载与撰述都是史家主观意识的产物。以往的历史是从男性视角观察和撰写的历史,是男性主体意识的产物;妇女史则应反其道而行之,即从女性立场、视角和以女性意识观察和撰写历史。同时尖锐地批判对于“客观性”与“科学性”的迷信,提出妇女史应该反对“中立”,反对“伪客观”。①参见克莱尔·莫赛斯:《名字之中有什么?关于女权主义历史的书写》,载杜芳琴主编:《引入社会性别:史学发展新趋势——“历史学与社会性别”读书研讨班专辑》,天津,2000年,第92页;蔡一平等主编:《赋历史研究以社会性别——“妇女史学科建设”首届读书研讨班专辑》,天津,1999年,第139页。“男性制造”既不可信,妇女史学者又主张没有“客观”,那么,实证研究也就几乎无法进行了。这当然不是我们期盼的结果。
在笔者看来,以上观点自有其合理成分,因为任何历史撰述都肯定蕴含作者个人的观点、感情与评判,后现代主义对于研究者本身的阶级、种族、宗教、民族等立场、背景及由此产生的偏见等所持注意、剖析态度是可取的;但也存在偏激之处,即过分强调了文本制造者的主观意识,完全不承认有客观历史存在和客观历史记载。笔者认为,对于妇女史来说,即使是全部由男性书写的史载,于真相或有偏离,但也总有一些应该是真实存在、发生过的,不会全部是无中生有、捏造出来的。或者可以说是承认男性书写的历史仍具有一定的超越性别的真实性、客观性。例如,正史《列女传》类史载,所记虽然肯定包含史家出于自身价值观念的取舍、渲染甚至扭曲,但多半还应该不是凭空杜撰,在相当大程度上仍可作为其时社会真实状况的反映。如果完全否定此类史载的客观性,将其完全视作男性意识的主观表达,我们就几乎只能研究“观念史”,而很难书写“生活史”了。
无论男性“制造”的史载的真实性、客观性程度如何,要之,妇女史不可能凭空编造,不能不取用传统史载并建基于其上。那么,如何检验和证实史载中这些“客观事实”,哪些是真实可信的,哪些是因性别立场与偏见而应该提出质疑的,即如何鉴别与解读,就成为妇女史写作和研究的关键。
在此方面,笔者不仅自身存在困惑也始终面临质疑。小书《唐代妇女》由于出版年代较早及丛书性质所限,评论者给予了宽容,未予苛评,并肯定了书中提出的一些见解;但也同时指出,该小书重在分析史料以加强读者对唐代妇女的了解,欠缺深入考核有关史料的记载是否可靠。对笔者有关《列女传》的论述,论者也提出了类似问题,即立论重在传记书写对象所“反映”的时代,而忽略传记“产生”的时代背景,亦即缺乏从史学编纂角度分析这些传记资料产生的原因与背景。也有学者明确提出,《列女传》是书写者表达自身价值观与男性主体意识的文字,不能当做真实历史记载去使用。前者涉及了史料可靠性的考证问题,后者则注重将史载看做记载者本身思想意图的表达,反对将文献记载当做现实发生的,或者说将史载当做史实。两者虽然角度不一,但都牵涉到史料考证问题。
对于以上这些意见,笔者觉得确有切中肯綮、令人心服之处,论者对历史文献记载的质疑与谨慎态度是有价值的。但是尚不能完全接受历史不是被“发现”的“事实”与“真相”,只是史家“建构”的叙述方式一类后现代观点,故而觉得这种质疑也不宜走向极致,走上不相信任何史载的虚无主义立场,比如,完全否定《列女传》类记载一定程度的客观、真实性,将其完全视作男性书写者的自说自话。这些批评意见的价值在于提醒我们,对于妇女史来说,对于文献记载的鉴别考订,比之一般实证性研究更为重要,因为相对于其他史学领域,史载书写者的性别立场、性别意识及其对文本真实性的影响需要特别给予关注、剖析。
从事实证性史学研究,对史料的鉴定是必不可少且占首要地位的,因为它是一切立论的根基。但是也要看到,对于所有史载完全探明原委、辨明真伪是不可能做到的。建构中国古代妇女史,尤其是生活史所依靠的文献记载,包括正史、野史、碑刻、笔记、书信、诗文、小说等等,哪一种是完全真实可信的?可以说,几乎不存在。它们都经过了书写者的“再创造”,且不说作者出于性别偏见、男性意识而有所歪曲、甚至编造,即使是治史与写作态度极为认真求实,也有太多的因素诸如误听误信、以讹传讹等,使今人无法判定其笔下的记载的真伪。如,公认最具可信性的碑刻、书信之类,碑刻文字多溢美之词、为尊者死者讳,是众所周知的;书信一类,既无法确知其缘由背景,谁又能保证书写者不说假话?即使是相对撰写较为严肃的正史中,也有许多史实是永远无法判定其真伪的。例如,作为古代妇女史上重要人物之一的武则天,正史明确记载她曾为夺皇后之位而亲手扼死亲生幼女以嫁祸他人,对此早已有人提出怀疑,认为不合常情,有可能是史家对于这位女皇帝的丑化。但也有学者认为武氏本来就非常人,她后来对女儿太平公主的宠爱正是一种心理补偿。要最终判定此事的真伪,几乎不可能。另如,上述《列女传》所载节妇烈女类事迹,究竟哪些是当时确实发生的事实?哪些是史家为倡扬妇德而夸饰、渲染甚或完全杜撰?从史载的只言片语中,基本无法考证。以其中一位著名节妇的事迹为例,据《新五代史·杂传》载,李姓节妇因为被男子拉扯而自断手臂,因其惨烈,此事为后世反复征引,李氏被奉为节烈楷模。修史者欧阳修在传中明言此事得之于小说:“予尝得五代小说一篇,载王凝妻李氏事”,因感慨于五代时期伦常败坏,故特别录入史册,以与乱世中苟且无行的男子相对照。此事是否真实发生?修史者虽明言得之于小说,但其时小说体裁尚未完全走向创作,往往有所本,故而并不能排除其发生的可能,可以说是真伪难辨。其他列女事迹记载也基本都存在类似情况,多有得自传闻、小说者,但又不能排除其真实发生的可能性。
正史尚且如此,野史及文学作品类的可信度自然就更低,但此类史料又别有其价值。传统史家就颇为重视此类史料,如清人云:“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5]63陈寅恪先生也主张:“小说亦可参考,因其虽无个性的真实,但有通性的真实。”[6]267都对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给予了肯定。不过,援引使用此类材料更加不好把握其度,因为无法判断哪些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哪些是文人骚客的虚构与幻想。我们又不能完全摒弃这些文献记载,因为此类史料对于妇女生活史颇为重要。由于妇女群体的边缘性质,他们在正史中所占地位极其有限,有关下层社会、普通妇女生活等方面的记载甚少,但这些野史、小说类通常比注重王朝更替而缺乏人间烟火的正史更为有用。
综上,无论正史抑或其他文献记载,都程度不同地存在不可靠、不真实的问题。我们既然不能因噎废食地完全摒弃它们,唯一的路径也只能是披沙拣金,尽量进行认真的考订鉴别,利用这些并不完全客观、真实的史料构建妇女史。与一般实证性历史研究一样,首先需要慎重考察文献记载来源的可靠性与记述者个人原因等造成的误差;此外,还需要特别关注由于记述者的男性立场与偏见带来的偏差与不实,在使用尤其是根据它们做出结论时留有余地。但同时也要明白,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地进行考订鉴别,完全、绝对的客观、真实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如何从女性视角与女性主体意识出发,既鉴别、批判,又利用好传统史载资源,既发现、尊重史实,又从中剔除男性的偏见,发现其背后隐藏的性别密码,把握好疑与信的“度”,就成为需要我们不断探索、掌握的基本功。
三
在对于史载真伪的鉴别之外,还有如何解读的问题。
鉴于对“客观”历史的怀疑和再现历史“原态”的不可能,有学者提出,历史学实际上是一种“解释学”,“即解释出符号的历史涵义的艺术”。“历史学家在试图重新绘制或再现历史的时候,他无法摆脱‘自我’,无法摆脱主体的参与”,“无论主体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其途径只有一个,即‘解释’”。“历史学家所研究、所撰写的历史就不是什么‘科学’的问题,而是‘摹写’和‘解释’的问题,以及怎样‘摹写’和‘解释’的问题。”[7]
笔者认同以上这一看法,但这又带来新的问题,即面对同一种记载,因观察角度、思维方式不同,人们可以有各种解释,得出的结论可能完全相反。比如,公认的唐代妇女多改嫁事,虽然人们在史籍记载的真实性上并无争论,但有人提出这些事例并不能说明其时贞节观的淡薄,社会现实中实际上还是守节者居多。改嫁者多还是守节者众?何者是主流?这可以说是个无解的问题,由于没有统计数字,难有令人信服的定论。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在当时社会经济制度与条件下,守节者应该有很多是出自经济上的考虑,换言之,未必是出于贞节观念。另如,公认世风开放的唐代,女教著述却特别兴盛,有人认为反映了其时礼教加强的趋势,也有人解读为其时礼教不兴、妇行失范,故而才有人出来殷切呼唤礼教的回归。
更普遍的问题是,由于文献记载的缺略和史家的增删,对于史载的许多人与事,后人完全无法确知其具体情境,更难以揣度历史人物的心理,因而,如何“解释”它们也就成为难题。尤其是人的思想心理,千奇百怪、不可捉摸,甚至不可理喻、不合常情。我们无法走进历史,更难以走进历史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如历代多见的烈妇殉节事,当事人究竟面对何种处境?是出于自愿还是迫于压力?具体到个人,又是出于何种心理?每位事主的处境与心理,不仅今日无法确知,可能在当时,众人也无法完全知情。唐代名妓关盼盼,为节度使张建封纳为姬妾,张死后,独居燕子楼十余年,被后世列为贞节楷模。但是关盼盼究竟为何选择独居不嫁?是感念旧恩,还是固守贞节,抑或有其他原因?从其诗作中,只能看到她的寂寞、惆怅,无法深究其处境与内心世界。又如前举五代李姓节妇事,史载称其“夫病卒于官,其家素贫,一子尚幼。李氏携子负骸骨以归,东过开封,止旅舍。主人见其独携一子而疑之,不许其留宿,李氏不去,主人牵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长恸曰:‘我为妇人,不能守节,而此手为人执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断其臂。”作者既明言录其事入史,是出于矫正世风目的,那么其绘声绘色描写的李氏行动言语肯定有渲染之处。如此过激的行为,仅从简短记载中,既看不出当时情境如何,更无法判断李氏于受辱与走投无路之下自断其臂是否有其他心理原因。其他节妇烈女也同样,只从只言片语记载中,根本无法确知其所处外界环境与内在心理状态。正如有学者所描述的:“今天已经尸骨成灰、变为蜡像或铜像的那些盖世英雄或帝王将,想当年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的思想、心理究竟如何,当时的人——甚至他们本人——都未必说得清楚,更不必说隔着时间的长河的历史学家们。”[8]
如果说对于史载的真伪往往众说不一的话,那么如何解读就更是永远难以达成一致的谜题,只能任凭研究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做各的揣测、解释与描摹了。
四
综上所述,可以说,如果每件事都执著地“求实”,妇女史,尤其是生活史就几乎无法做下去。当笔者为此而纠结的时候,史学家的另外一些说法又令我感到峰回路转、豁然开朗。首先,他们告诫我们:放弃追求客观真实的努力,承认历史都是自我再创造。①笔者根据许倬云先生讲课内容整理而成,未经讲课者核对。“我们只能根据各种不同的史料来努力拼凑过去的事实,时过境迁,去今往往已经上百上千年,能够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乃是完全达不到的一个目标。……所有的论说都是尝试性的,都是有可能存在错误的。”[8]其次,承认研究者的主体参与和对历史“再创造”的合理性:“现代史学的发展早已告知我们,对史料解读的‘求真’往往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史学的魅力越来越多地体现在研究者对历史现象的独特理解和合理的想象上。我们对史料的解读也应该保有它的多样。”[9]“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2]115
由此再看妇女史的时候,我有了一种新的了悟。首先,我们可以将“客观”、“真实”悬为目标,但对于男性史载,不必苛求其完全客观、真实,宜采取信中有疑的态度,而不是全盘否定。我们应尽量通过谨慎考证、甄别以求真,但历史不可能再现、不可能复原,因而我们永远无法获得绝对的“客观”、“真实”。鉴于此,笔者认为,对于史载只能采取模糊与相对态度,史载未必每一件事都真实可靠,但是应该承认总体上还是反映了其时的社会状况与风气。
其次,笔者认同历史学是一种“解释学”的看法,服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说:“当我曾思考或将思考它们,就根据我的精神需要重构它们,对我来说,它们也曾是或将是历史。”[10]任何历史著述其实都是当代人对历史的一种解释、一种构建。我们实际上从事的只是对于历史的“解释”工作,或者说是进行自己对历史的构建。每个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认识、自己的解释、自己的构建。如何诠释、解读或构建是研究者的自由,“历史”正是研究者不断阐释和建构的结果。每一篇著述都代表了一个时代和作者个人的角度与声音,都有其认识价值和历史价值。没有所谓绝对正确,也不必追求终极真理。如此,妇女史才能走出瓶颈,一步一步向前走,并给未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些研究借鉴。
[1]高世瑜.发展与困惑——新时期中国大陆的妇女史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2004,(3).
[2]E·H·卡尔.历史是什么[M].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龚咏梅.历史学家不应只钻故纸堆——著名历史学家伊格尔斯访谈[J].历史学家茶座,2009,(15).
[4]周华山.女性主义田野研究的方法学反思[J].社会学研究,2001,(5).
[5]浦起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1.
[6]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笔记一则[A].追忆陈寅恪[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7]仲伟民.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J].史学理论研究,1992,(3).
[8]贺卫方.治史者当谦逊[DB/OL].http://blog.sina.com.cn/heweifang,2006-03-01.
[9]刘悠扬.寻找士人的“江南”[N].深圳商报,2010-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