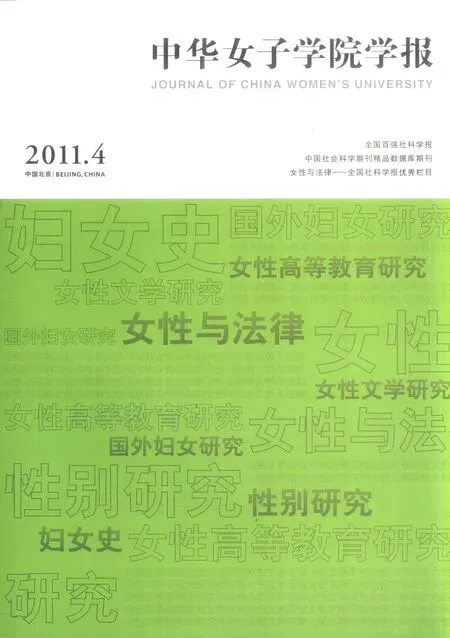《傲慢与偏见》中的女性教育
2011-02-20龚龑
龚 龑
《傲慢与偏见》中的女性教育
龚 龑
所及的题材而言,奥斯汀可谓第一人,或许也是最出色的一位“历史学者的小说家”。为了避免纯形式主义分析可能导致的误读,其小说《傲慢与偏见》被置于一个更大的历史语境中加以阐释,以期从中获得18世纪末英国女性教育状况的切身读解。奥斯汀的名著同《教育漫话》和《女权辩护》等历史文本并置一处,这有助于说明当时女性教育对中等阶层及其聚敛财富和谋求社会地位的重要意义。
傲慢与偏见;女性教育;中等阶层
自19世纪以来,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1775—1816)的影响持续扩大,她甚至被看做是与莎士比亚比肩的经典作家。其名著《傲慢与偏见》(1813)竟成为当代的畅销书,各式各样的影视作品、续作、戏仿文字层出不穷,构成独特的文化景观。《傲慢与偏见》一般被当做“家庭喜剧”,男女主人公达西和伊莉莎白历经一番挫折而终成眷属。本文将这部小说置于一个更大的历史语境中加以阐释,希图从中获得18世纪末英国女性教育状况的切身读解。这样的想法并非没来由,《傲慢与偏见》结束时,除了莉迪亚外,本奈特家四个姐妹都发生了变化。基蒂摆脱了莉迪亚的影响,又受到姐姐们妥善的关照,不再像以前那样“轻狂,无知,索然无趣”。[1]252玛丽居然乐于暂时放下书本,陪同妈妈和外界打交道。甚至连简都认清了宾利姐妹的真面目,决心不再一味逆来顺受。伊莉莎白的成熟更不必说,她依靠“理智”战胜了当初一见钟情的威克姆,选择了基于相互感激和尊重的爱情模式。总之,小说中女性教育的功效体现在思想道德方面,他们成了具有德行、智慧和教养的女性。
一、18世纪英国的女性教育
教育构成奥斯汀小说的一个主题,不仅《傲慢与偏见》,其他小说莫不如此。女性教育乃是英国18世纪的焦点话题之一。论者指出,自17世纪末以降,培根和洛克等人的经验主义哲学理论促成了一个现代意义的性别角色模式。概而言之,女人是可以教化的,男人不必使用压迫和暴力手段,而应设法让他们主动接受为之划定的社会角色。[2]292对英国妇女“教化”的早期文本当属1631年的《英国的淑女》(English Gentlewoman),此后又有《妇女的感召》(The Ladies Calling,1673)、《给女儿的建议》(Advice to a Daughter,1688)等,这些读物都是沿着“改造”妇女的思路来行文的。其中的说教看上去以《圣经》为基础,潜于其中的则是世俗化和功利化的劝诫。[3]917和18世纪之交,报刊和小说的兴起,对这一风气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艾迪生(Joseph Addison)主笔的《旁观者》(The Spectator)等报刊讨论妇女的衣着服饰和行为举止,深受中等阶层读者的欢迎,在塑造女性道德和文化意识方面功效不菲。[4]34稍后则有海伍德(Eliza Haywood)仿照前者的《女性旁观者》(The Female Spectator)面世,这可以算做英国历史上第一份专门面向女性读者的刊物。18世纪中期最重要的期刊要算《漫步者》(The Rambler),在其中约翰逊(Samuel Johnson)常常触及严肃的妇女话题,他对女性的同情是其前辈艾迪生所不具有的。[5]527
英国“心理小说之父”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意欲重塑英国社会绅士和淑女的行为规范,在《帕梅拉》(Pamela,1740)中他非但不掩饰自己的说教,反而有意识地强调它们。可以说,理查逊秉承对女性读者“教化”的传统,奠定了此后文学创作中的道德倾向。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文坛已经出现了数量不小的女性小说家,这些“理查逊的女儿们”专门针对妇女的道德行为而写作,最著名的非伯尼(Frances Burney)莫属,奥斯汀深受其影响。18世纪的布道文中也不乏针对女性的“行为指南”,影响最大的首推福迪斯(James Fordyce)的《布道集》(Sermons to Young Women,1766)和格雷戈里(John Gregory)的《父亲给女儿的遗产》(A Father’s Legcy to His Daughters,1774)。福迪斯的《布道集》到1768年5次修订,到1798年11次修订,到1814年14次修订。福迪斯无疑可算做女性读者品味的裁定者,在《傲慢与偏见》中,柯林斯第一次到本奈特家拜访,他故作优雅不屑选择从流通图书馆借来的小说,偏要给表妹朗读《布道集》的选文,引来玛丽强烈的反对。[1]47
18世纪迅速增长的社会财富使英国妇女,尤其中等阶层的女性,从劳动中解脱出来,享受闲逸的生活。当时的性别角色比较复杂,远非“两分领域”的理论说辞可以概括。公共领域并非完全属于男人,男人光顾咖啡馆和俱乐部,但女人同样可以进入某些社团、集会和图书馆。著名的“蓝袜子”等团体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妇女的行为规范成为社会大伤脑筋的问题,流行的道德话语是:既要让中等阶层的妇女参与公共生活,同时又不要让他们“堕落”。18世纪末,英国社会兴起一股人道主义的关怀浪潮,社会边缘化人物成为关注的焦点,妇女自然也在其中。[6]60-62总之,种种因素使得女性教育成为贯穿18世纪的热点问题。
当时的女性教育并非指专业知识的掌握,其内容大致体现在基础知识(写字、算术等)、家务管理、宗教教育和“才艺”(Accomplishments)等几个方面。操持家务是对女性最基本的要求,条件优越的中上等家庭还要求女性习得“才艺”,这是英国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通行的做法。所谓“才艺”主要指绘画、唱歌、演奏乐器和外语(尤其指法语和意大利语)。“才艺”具有象征性的作用,用以标榜“淑女”身份,扩大他们的交际范围,促进家族的利益关系。没有“才艺”、只会料理家务的女性只能算“善于持家”(Noteble),往往失去了社会交际的机会。[7]本奈特太太只有“持家”本领,不擅“才艺”,好在她天生貌美。玛丽是本奈特家唯一一个相貌平常(Plain)的女孩,不得不努力掌握“学识和才艺”,不失时机地卖弄一番。[1]17福迪斯的《布道集》告诫女孩子避免“学究气”,而玛丽却反其道而行之。
18世纪“女学究”或者“知识女性”的称呼尚带有贬义,甚至贵族家庭的女性都不被冠以这样的称谓,这里涉及对“学识”的态度问题。在《教育漫话》中,洛克讨论绅士应具备的品质时将“学识”放在末位,辅助其他三种主要品质:美德、智慧和教养。[8]194洛克的“绅士教育”乃是自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教育观,是一种以中上阶层子弟为对象的教育。值得注意的是,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女权辩护》的前言中也明确指出自己的教育对象是中等阶层的妇女。[9]9洛克认为淑女教育的内容应有所不同[2]292,但后来者使之变得越来越窄。《女权辩护》将批评矛头指向18世纪中后期的某些男性作家,尤其上面提到的福迪斯和格雷戈里,还有法国的卢梭。[9]77福迪斯标榜的“羞答之美”(Retiring Graces)一时间成为女性修身的圭臬,它们指胆怯、谦卑、羞涩、顺从、温柔和虔诚等品质。18世纪英国文学中常出现此种类型的女人:他们克己复礼、神经敏感,经常表现出天生的沉默和胆怯;或者思想细腻、情感脆弱,本能地回避性行为等等。在文学中他们变成了贞洁、沉默和顺从的女人,最后定格为维多利亚时期典范的妇女形象,也就是所谓的“家庭天使”。[3]9-10
奥斯汀写作的年代,男性教育已经变得专业化,不仅中等阶层的家庭,即便上层乡绅和贵族家庭的子弟也要接受相关的专业教育,从而获得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管理技能。妇女教育仅仅限制在持家、绘画、音乐等几个方面的做法引来了一些批评。早在18世纪初,在《给女儿的严肃建议》(A Serious Proposal to Daughters,1701)中,艾斯戴尔(Mary Astell)提倡建立修道院,思想严肃的妇女可以在那里静修和研读。18世纪末,上面提到的“蓝袜子”成员莫尔(Hannah More)出版了《对现代女性教育制度的批评》(Strictures on the Modern System of Female Education,1799),此书到1826年已经修订了13次,销售总量超过19000册。莫尔的观点比较保守,她认为妇女的命运不外乎为人妻、为人母和为人女;同时她也告诫读者,一味强调“才艺”会使妇女失去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表率作用。大力提倡女性教育的女作家麦考利夫人(Catherine Macaulay)在《教育书信》(Letters on Education,1790)中指出,男女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妇女的从属地位都是教育的结果。她谴责妇女热衷于专门取悦男人的“轻浮的才艺”,呼吁他们追求更加“坚实的美德”。[10]不过,真正针对女性的现代知识教育要等到半个世纪后才姗姗来迟。19世纪中期,英国重要城市里纷纷出现公立的女子学院,为了进一步规范女教师队伍,教学大纲、结业证书等现代教育措施开始出台并逐步完善。[11]
二、《傲慢与偏见》中的女性教育
奥斯汀并不像上述作家一样摆理说教,而是借助人物和情节更加辩证地展开女性教育的思考。让我们来看看小说人物对于“才艺”的解释。宾利认为装饰台桌、点缀屏风、编织钱袋就已经不得了了,这样低的标准自然遭到姐妹的讥笑。宾利小姐大献殷勤地帮达西定义“才艺”,它不光包括音乐、唱歌、绘画和现代语言,还要讲究仪表、步态、音调和谈吐。原以为自己的帮腔会得到首肯,没想到达西还给“才艺”补上“真才实学”:女性应多读书来增长心智。[1]27伊莉莎白虽然表示怀疑,但她心里明白,这一场谈话之前自己正在认真阅读,宾利姐妹则卖弄“才艺”,达西的话并非无的放矢,这是双方后来达成和解的基础之一。伊莉莎白拒绝柯林斯求婚时,一再表明自己并非假充优雅(Elegance),“请不要把我当做一个优雅的女性,存心想要作弄你,我是一个明白事理(Rational)的人。”[1]75在这两处,奥斯汀表示出对“才艺”和“优雅”的鄙薄,她更加认同开心明智和通情达理。沃斯通克拉夫特希望女性对丈夫的情感具有坚实的基础,而为了建立这样的基础,女性必须学会独立自主地思考或者行动。[9]47
《女权辩护》认为,个人教育(Individual Education)的主旨在于“逐渐提高认识能力,养成良好脾气,节制萌动的情欲,在身体发育成熟前锻炼儿童的理智。”[9]21沃斯通克拉夫特以为此前对个人教育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其实她的措辞和洛克同出一辙。洛克绅士教育的核心是“克服自己的欲望,抑制自身的本能倾向,服从理性指引”;他重视良好习惯的培养,告诫父母不能溺爱子女。[8]103-105在《傲慢与偏见》中,达西概括自己的品行时曾言:“虽然在原则上我不赞同自私,但实际上我是自私的。”何以如此?达西的父亲是一个善良的人,不过在向达西灌输正确的观念和原则时却又放任他骄傲自大。用达西的话说,他“怂恿我,甚至教我自私自利,高傲自大,除了自家人以外,不要关心任何人,看不起天下所有的人。”
在小说中,本奈特家也是一个父母教育失败的例子。伊莉莎白是五个女儿中唯一具有反思能力的一个,早在达西指责和批评前,伊莉莎白就意识到父母的致命缺点。本奈特先生年轻时贪恋美色,一时冲动娶了本奈特太太,造成了不幸的婚姻。[1]155本奈特夫人自私,只认得钱和钱所带来的物质利益。本奈特先生失望之余,或以乡村景色和读书消遣,或则公开逗引太太出丑取乐,夫妻生活几十年,他不曾做出努力使妻子少许改进。取笑妻子,尤其是当着孩子面,会使孩子看不起母亲。这不仅惹恼了妻子,更伤害了孩子。[1]155本奈特先生偏爱伊莉莎白,而本奈特太太则袒护莉迪亚。父亲的纵容和母亲的溺爱产生了恶果,且不说伊莉莎白一度受本奈特先生的怂恿追求威克姆,莉迪亚就是秉承了母亲的虚荣和浅薄,最终外逃私奔。幡然悔悟的伊莉莎白和恬不知耻的莉迪亚恰恰象征着“理智”和“情感”的较量。
父母在家庭教育中地位重要自有原因。从《傲慢与偏见》一书来看,18世纪女性接受教育不外乎三种途径。只有条件优越的家庭才能将孩子送进私立女子学校(Seminaries)或者精修学校(Finishing Schools)。[2]369英国最早的女子学校于17世纪初期建立,多集中在伦敦等重要城市,主要针对贵族和乡绅的女儿。淑女们在这里可以学习古典语言(比如希腊和拉丁语),不过这些都是装饰性的,以无害于“才艺”和“优雅”为前提。[2]375当时贵族家庭的女性往往有自己的女伴(Paid Companion),他们主要负责指导社交场合的礼仪等。达西妹妹从私立学校出来后,身边先后有两个女伴,曾经为第一个女伴(Mrs.Younge)所欺骗。[1]133宾利的姐妹也“曾在伦敦一流私立学校(Seminaries)受过教育”。[1]11家庭条件稍差的姑娘大多进入寄宿学校(BoardingSchool)或者日间学校(DaySchool)。这里汇集着普通乡绅的女儿,同时也杂有中下阶层家庭的孩子,日间学校尤其如此。[12]58-59难怪洛克认为此类学校的教育环境不理想,学生良莠不齐,如果孩子混迹其中,很难保证学到好的德行。[8]128-131最后,女性教育也可由家庭女教师来承担。在小说中,凯瑟琳夫人自诩善于给乡绅家庭推荐优秀的家庭女教师。[1]109在凯瑟琳夫人看来,家庭女教师可以提供“系统的正规指导”,这未免言过其实。实际上,家庭女教师的地位低下,收入微薄,奥斯汀在《爱玛》(1816)第35章告诉读者,家庭女教师们的生活竞还不如卖到美洲的黑奴。
凯瑟琳夫人对本奈特家五个女儿既没有进入任何学校,也没有雇请家庭女教师惊诧不已。倒是伊莉莎白的解释让读者明白,他们的家境足以负担这种教育开支,只不过本奈特先生偏爱乡村的悠闲和清净,厌恶伦敦的奢侈和浮华,不愿送女儿去那里修行。18世纪的女性大多时间待在家里,如果不请家庭女教师,则教育的重任就落在了父母身上。本奈特先生的教育理念并非全无是处,至少他给孩子作出选择的自由,这是比较开通的教育思想。伊莉莎白的三个妹妹年龄尚小就跟随姐姐出门参加“交际”(Out),对此凯瑟琳夫人认为不光彩,而伊丽莎白竭力为他们辩护,说这样或许可以促进姐妹之情。此等解释很能说服凯瑟琳夫人,她不得不承认伊莉莎白“很有主见”。[1]109
奥斯汀小说呈现一种模式,两个年轻人相互了解,通过亲身经历认清自我,最终在婚姻上走到一起。[13]这似乎开辟了学校和家庭之外“女性教育”的又一条出路。如果从洛克的四个品质(美德、智慧、教养和学识)来衡量,达西和伊莉莎白很“般配”。当伊莉莎白猜测达西可能放弃自己时,内心无限懊悔,认为只有他俩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佳的搭档。“他的见解和脾气虽然与她不同,但一定会让她称心如意。这个结合对双方都有好处:女方大方活泼,可以把男方陶冶得心性柔和,举止优雅;男方精明通达,见多识广,定会使女方得到更大裨益。”[1]202这是一段赞颂心灵互补的文字,不过“好处”和“裨益”兼有多重意思。伊莉莎白何尝不明白婚姻的经济意义。伊莉莎白对威克姆放弃自己转而追求金小姐(Miss King)表示理解。虽然伊莉莎白严厉谴责夏洛特纯粹为了经济目的的婚姻,不过后来到夏洛特家做客时,她对朋友婚姻的态度有所转变。实际上小说中伊丽莎白的人生轨迹和本奈特太太的生活追求相去未远。有意思的是,在《女权辩护》中,沃斯通克拉夫特以管理财产为例来谈论男女的情感和婚姻。服从成性的妻子嫁给了一个精明通达的丈夫,丈夫活着的时候,她“借助丈夫的理性”(Reason is Taken at Second Hand)尚能井井有条地操持家务。可是一旦丈夫去世,妻子就面临着双重责任:教育子女和管理财产。作者感叹道:“她自己从来没有独立思考过,更不用说自己去行动了。”[9]48又有谁愿意娶这样的女人呢?
三、《傲慢与偏见》中的“绅士”和“淑女”
由于法国革命造成巨大冲击,18世纪90年代英国思想文化界激烈地论战。《女权辩护》的作者属于重视理性和责任、强调自我节制的保守派。换言之,奥斯汀写作《傲慢与偏见》的年代,英国正面临着民族或者说帝国的危机,“女性教育”也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之争的概念。[14]197-198不过正如黄梅指出的,一些学者淡化了“另一个涉及面更广、延续时间更长的重大文化讨论”,即在一个正在生成的“敛财逐利社会”里,艾迪生、理查逊和约翰逊等一脉相承地就人的社会角色和行为规范所进行的思考和探究。[15]“敛财逐利社会”也就是欧洲近代出现的“市民社会”。众所周知,从“圈地运动”开始,英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商业和贸易的发展,使得一个新兴的市民阶层逐渐强大起来,与之相伴的则是市民社会的兴起。1688年以后,英国社会逐渐建立起比较稳固的社会秩序。土地贵族为这一社会秩序的基础,银行家、工商业者和不同的专业人士也参与维持这一社会秩序。
新阶层必然要求拥有自己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准则。人们不再以出身和血统来确认社会精英,相反却以财富和奢侈品为之定位。在16和17世纪,等级的划分实际上主要基于家世、血统和社会角色等,财富还只是外在标志。到了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期,由经商、投机和生产而带来的财富大量涌入社会,原来等级划分的标准受到挑战。英国18世纪著名小说家菲尔丁(HenryFielding)曾言:“没有任何事像商业引入那样根本改变人们的关系,国民从此面目一新。”[16]13然而历史的吊诡处在于,一方面人们越来越从财富和资产来定义新兴的中等阶层,另一方面中等阶层也羡慕贵族所独具的荣誉和举止,这就是所谓的“向贵族看齐”。在小说中,夏洛特的父亲本来是经商出身,但是发家后却购买爵位,置办地产,假充乡绅。这一暧昧态度说明以商业为本的中等阶层渴望融入传统的社会精英之中。[16]1518世纪流行的小说、道德期刊和“行为指南”不仅针对淑女,也针对刚刚暴富的商人子弟。其目的乃是汇聚财富和社会文化资本,整合土地贵族和商业精英,从而创造一个新的统治阶级。这样一个统治阶级正在形成,而绝非凭空臆想,土地贵族与富商之间的通婚便是一个绝好的例子。[16]19起初,达西希望自己的妹妹能够和宾利家联姻;同样,宾利的妹妹一直自信可以和达西结为连理;更不必提凯瑟琳夫人将自己女儿嫁给达西的如意算盘。达西的表弟菲次威廉姆上校烦恼多多,他心知肚明与殷实之家联姻对贵族而言不失为弥补家运的途径之一。可以说,这种贵族和商人的相互渗透构成了当时英国社会生活的一大景观。
在小说的结尾,达西夫妇跟加德纳夫妇保持密切的关系。达西和伊莉莎白非常感激加德纳夫妇,“他们把伊莉莎白带到德比郡,并最终促成这桩婚事。”[1]252宾利姐妹和凯瑟琳夫人经常表现出对本奈特娘家两个舅舅的蔑视,原因之一就是加德纳先生经商,而菲利普则是代理律师。加德纳先生虽为商人,但毕竟不同于夏洛特的父亲。他的举止深得邻里的赞美,尽管他每天同买卖打交道,却“知书达理”,颇有“绅士风度”,“无论在天性还是教养方面都不可和姐姐相提并论。”[1]93在小说中,加德纳先生处理事务有头脑、讲原则、求实效,堪称模范商人。达西的“贵族血统”在母亲家一面,他自己并没有任何贵族头衔。小说没有言明达西从事的行当,不过他在伦敦拥有自己的房产,经常往返于伦敦和德比郡,其从事商业等事务应该没有异议。达西的贵族形象显然不同于凯瑟琳夫人等辈。在德比郡,加德纳先生和达西偶遇,想必他们坦诚相见、观念投契,短时间给对方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要不然,达西怎么会认定本奈特先生办事不妥,坚持要跟加德纳先生仔细斟酌、妥善处理莉迪亚私奔造成的“烂摊子”。可以看出,这两个人具有共同的为人处世准则:不仅风度翩翩,更有实干精神。唯其如此,他们的行为才有助于家庭和社会的协调。洛克早就指出,绅士并不是只讲究出身,还必须具有实用价值。洛克奉劝乡绅子弟学习工匠和手艺以提高实用技能;如果其父母羞于这些行当,洛克建议小绅士们学习商人记账,以便将来能够保持家族原有的财富和地产。在传承财产的“实用和效能”(Use and Efficacy)上,没有其他的手段可与记账相比。[8]260-261
从宽泛的文化意义上说,小说中的商人、专业人士(比如代理律师菲利普,后来转为“正规军”的威克姆)、贵族和乡绅都可以称之为“绅士”。伊莉莎白甚至认为从家庭出身看,她和达西也算是门当户对,她称自己是“绅士的女儿”。小说所塑造的“绅士”和“淑女”都是市民社会里中等阶层自我塑形(Self-fashioning)的组成部分。如果说,达西和加德纳先生以其实干精神成为绅士的表率,那么伊丽莎白等淑女们的“实用价值”又体现在何处呢?与英国市民社会的兴起与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财产权,这是市民社会的基础。财产权构成17和18世纪政治经济思想领域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不难理解,近代以降的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休谟乃至康德和黑格尔莫不关心于此。英国18世纪的女性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参与男性财产的传承:生育、婚姻融资和社会文化资本。[7]此处暂且不提生育和财产权的关系。①休谟在《人性论》中提出以财产权为中心的正义规则,这些规则被看做是现代市民社会赖以存在的元规则。参见高全喜:《休谟的政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页。休谟在讨论完政府和国际法以后转而论述“论贞操与淑德”,他十分严肃地谈了妇女通奸行为如何导致财产继承上的混乱等问题。奥斯汀笔下的女主人公多是经济条件拮据的灰姑娘,这里也不必讨论通过婚姻来“融资”。奥斯汀的小说着力之处乃是作为社会文化资本的女性。换言之,伊莉莎白带给达西的是思想和道德财富,这就同女性教育息息相关了。乍看上去,奥斯汀的女主人公远离社会权力或者经济中心,但恰恰是他们通过上面所说的三种渠道(尤其最后一种)来协助维护市民社会的秩序。难怪有论者把伊莉莎白比作在男人之间流通的“货币”,或者在部落首领之间交换的“礼物”。她的流通和交换有助于达西、本奈特和加德纳先生等人达到各自的经济和政治等目的。[17]
四、结语
读者不能简单地认为奥斯汀的小说题材狭窄,更不必断言其写作动机是给后世提供一些消遣的闲话。奥斯汀珍视日常生活中的亲情和友谊,看重文明社会的温文尔雅,但同时她对其中表现出来的粗鄙和平庸也十分敏感。20世纪中期以降,越来越多的评论家意识到奥斯汀小说对当时社会观念的批评和讥讽。如果将奥斯汀小说看做是对当时社会生活和思想建设的深刻介入,那么其中屡屡出现的“学识”、“修养”或者“美德”其实是市民社会中权力分配时的一种自觉的文化武器。无论作为群体还是个人,中等阶层需要凭借这一武器来谋求更高的社会地位、争取更大的社会影响。[15]
[1]Austen,Jane.Pride and Prejudice[M].Donald Gray.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Company,2001.
[2]Fletcher,Anthony.Gender,Sex and Subordination in England 1500-1800[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
[3]Mitchell,Marea;Dianne Osland.Representing Women and Female Desire[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
[4]Wechselblatt,Martin.Bad Behavior:Samuel Johnson and Modern Cultural Authority[M].Lewisburg: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
[5]Demaria,Robert.The Eighteenth-Century Periodical Essay[A].John Richetti English Literature,1660-1780[C].Cambride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6]Ferguson,Moira Janet Todd.Mary Wollstonecraft[M].Boston:Twayne Press,1984.
[7]Gary,Kelly.Educationandaccompliments[A].JanetTodd.Jane Austen in Context[C].Cambride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8]Lock,John.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M].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
[9]Wollstonecraft,Mary.A Vinca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M].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Company,1988.
[10]Wardle,Ralph M.The Intellectu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A Vinca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A].Carol H.Poston.A Vinca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C].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Company,1988.
[11]Pedersen,Joyce Senders.Schoolmistresses and Headmistresses:Elites and Educ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ngland[J].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1975,(1).
[12]Erickson,Amy Louise.Women and Property in Early ModernEngland[M].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3.
[13]McMaster,Juliet.Education[A].J.DavidGrey.TheJaneAusten Companion[C].New York:Macmillian Publishing Company,1986.
[14]Butler,Marilyn.Jane Austen and the War of Ideas[M].Oxford:Clarendon Press,1975.
[15]黄梅.《理智与情感》中的“思想之战”[J].外国文学评论,2010,(1).
[16]Hudson,Nicholas.Samuel Johns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ngland[M].Combride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17]Fraiman,Susan.The Humiliation of Elizabeth Bennet[A].Donald Gray.Pride and Prejudice[M].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Company,2001.
责任编辑:贾 春
Female Education in Pride and Prejudice
GONGYan
Jane Austen was the first and is probably,within her chosen area,the finest‘historian’s novelist’.Aware that any formal approach to Austen runs the risk of grotesque distortion,this article intends to place her novel,Pride and Prejudice,in a broader historical context,with hopes of having some access to the felt reality of girls’upbringing in late eighteenth-centuryEngland.JuxtaposingPride and Prejudice with 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 and A Vinca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the author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female education to the middle class and particularlytotheir burgeoningacquisition ofmaterial interests and social privileges.
Pride and Prejudice;female education;middle class
10.3969/j.issn.1007-3698.2011.04.012
2011-02-18
I106
A
1007-3698(2011)04-0071-06
龚 龑,男,中华女子学院外语系讲师,外国语言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化进程中的英国文学。1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