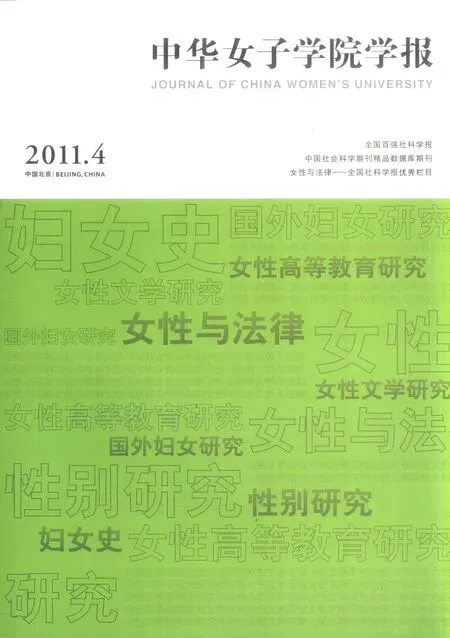村民自治规范与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保障
2011-02-20周应江
周应江
村民自治规范与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保障
周应江
部分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遭受村民自治规范的侵害是不争的事实。村民自治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农村妇女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土地承包经营权及相关土地权益的依据。村民会议的议事规则及传统的习俗与文化观念等,使得侵害妇女土地权益的村民自治规范获得了村民的认同和支持。法律在调适村民自治规范上虽有进展,但仍存在很大的局限,应该确立司法审查机制、行政问责机制等,以加强对村民自治的监督,保障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
村民自治规范;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法律的调适
女性主义法学理论认为,法律不仅仅是通过立法程序创建和制定的法律,即规范组成部分,还包括其他组成部分,即通过执行和解释正式制定的法律而形成的法律(结构组成部分)和由习俗传统、政治以及人们对正式颁布或正式解释的法律的认知和利用而形成的法律(政治—文化组成部分);[1]37将社会性别视角引入法学研究,能让法学从一个“有性人”的视角去考量法律,促使人们认识到性别因素对法律的作用以及抽象的法律对不同性别的具体影响,从而有助于揭示法律制度与其他制度一起对社会性别系统以及广泛存在的性别歧视的支持与构建。[2]27从一定意义上讲,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等村民自治规范,既可以说是一种法律,也可以说是一种公共政策,只不过是在特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适用的“土政策”。本文从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遭受村民自治规范侵害的事实出发,分析其作用的机理,检讨现有法律在调适村民自治规范上的缺陷与不足,试图揭示现有农村土地制度所存在的性别盲点和农村妇女遭受不平等待遇背后所隐藏的法律支持系统,进而为保障妇女的土地权益、强化对村民自治规范的监督等探寻相应的对策。
一、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受到村民自治规范侵害的现状分析
在我国,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根据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等规定,国家对于农村土地,即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在农村土地上可设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等用益物权,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还就集体土地征收补偿、集体收益分配等享有权益。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村妇女,依法可以享有的土地权益主要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分配权,以及承包地、宅基地被征收、征用时的补偿请求权等权益。
农村推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三十年以来的实践表明,农村妇女,特别是因婚姻等原因而流动的农村妇女,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及相关权益往往遭受到村民自治章程、村民民约、村民会议决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等村民自治规范的侵害,而这种状况至今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早在十多年前,全国妇联对15个省、市、自治区就农村第二轮承包工作中妇女权益被侵害的调查表明,自1983年第一轮土地承包起,在一些地区计算家庭人口时,妇女只能分到男性50%—70%的土地,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了40%的劳动妇女没有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情况。农村妇女土地权益被侵害的情况突出地表现为:农嫁非妇女在婆家、娘家都难以落实承包地,离婚、丧偶的妇女在回娘家后原在夫家的承包地被收回,多数出嫁不出村的妇女及其子女得不到土地补偿费,个别地区存在宅基地、责任田只分男不分女的情况,村规大于国法,村委会强行注销妇女及其子女的户口使其不能获得承包地等。[3]
《中国妇女报》上登载的一个实例,能很生动地说明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遭受村民自治规范侵害的情况。1982年,霍邱县城关镇城北村曾出台“村规民约”,其中规定:户口仍在本村的外嫁姑娘,宅基地和承包地全部收回,以后村队任何分红都没有已外嫁的姑娘及其子女的份。1984年与霍邱县师范学校职工黄朝宝结婚的吴国芳自然也在其中——尽管婚后户口一直留在城北村,但在1989年3月该村重新分配承包地时,吴国芳母子的责任田仍然被收回。“农村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土地承包权利,这是法律赋予她们的合法权益,怎能靠一纸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村规民约’说没收就没收?”在中专学校工作,对法律知识“有些了解”的黄朝宝,在仔细查阅了相关法律条文之后,提出质疑,并和村里45位“被收回土地的出嫁女”一起开始“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奔波”。“20多年来,为了维护出嫁女的合法权益,我一路奔波,从青年、壮年再到中年,却始终得不到应属于我们的这一点土地。还要坚持下去吗?还要坚持多久?”2010年11月5日清晨,站在霍邱县城关镇城北村村东头那块不足6亩的土地旁,46岁的黄朝宝无奈地连连发问。随即,他又痛下决心般地自言自语:“不能放弃,必须坚持!”[4]
最权威的报告莫过于2010年6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情况的报告》。该报告明确指出,要使男女从法律上的平等达到现实生活中的平等,仍然任重道远,其中“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受侵害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主要表现为:有的地方在发包时少分承包地给妇女;有的地方妇女出嫁或者离婚、丧偶即被收回承包地;有的地方土地被征后少给或者不给妇女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有的地方用村规民约或者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等形式限制甚至剥夺妇女的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权。”[5]全国妇联信访系统接收的信访事项也证实了前述情况:农村妇女土地相关权益最易受到侵害的四类人群是外嫁女、农嫁非妇女、离婚丧偶妇女和男到女家落户的家庭;受侵害的四方面的权益分别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征用土地补偿、宅基地分配、土地入股分红等相关衍生权益;有关妇女土地权益信访案件逐年上升,2010年此类信访事项达到11858件次,同比增加了25.8%。[6]
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被侵害或者剥夺,主要的途径是村规民约的规定或者村民会议的决定。从内容上看,涉及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分配权、土地征收补偿金等多方面的权益;从程度上看,有被彻底剥夺、逐步剥夺,或者部分限制或剥夺等不同的情形。实践证明,部分农村妇女在土地权益的享有上受到了歧视,法律所确立的男女平等原则,并没有在基层农村得到真正地落实。①相关调查还可参见:林苇著《妇女农地权益保护的实证再反思》,http://www.privatelaw.com.cn/new2004/shtml/20090428-161506.htm;蒋月等著《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96页;陈小君等著《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现实考察与研究:中国十省调研报告书》,法律出版社2010年3月版,第19—21页。
二、村民自治规范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机理
众所周知,我国法律确立了集体所有制和村民自治制度。在现有的制度下,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需要经由村民自治机制而实现。村民自治规范之所以能够对妇女的土地权益发生影响,进而被用以作为侵害农村妇女特别是流动的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的依据或者手段,其机理如下文分析。
(一)村民自治规范成为决定妇女是否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依据
在现有的制度下,妇女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征地补偿费、集体收益分配权等,都以具有特定的农村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为前提。具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是分享集体土地收益的关键所在,但现行的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等法律并没有就成员资格问题作出规定,使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界定长期处于制度调整的模糊真空状态。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时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问题事关广大农民的基本民事权利,属于立法法第四十二条第(1)项规定的情形,其法律解释权在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不宜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对此问题予以规定。[7]363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还没有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问题作出相关的法律解释。
在国家法律没有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界定提供标准和程序的情况下,村民成员资格的确定主要是村一级的权力,这种权力受到民众的广泛承认,具有相当的合法性。在村级确认和上级法律部门的确认发生冲突时,村民舆论甚至站在乡规民约一边。[8]92由于人口的增加或者减少会直接影响现有集体成员的利益,出嫁女等农村妇女的集体成员身份,往往被村民委员会或村民集体借助于集体决议或决定的形式予以否认,由此相关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被限制或者剥夺。一些出嫁的妇女或者入赘的男性,也因为原居住地不再承认其成员资格、新居住地不接收其为成员,从而丧失了承包地或者不能取得承包地。[9]
(二)村民自治规范是妇女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征地补偿费等土地权益的依据
在我国现有法律上,“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主体,也是法律上确认的土地承包的发包主体。这具体体现在以下法律规定之中。物权法第六十条规定:“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依照下列规定行使所有权:(一)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二)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三)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第三款规定:“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教育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的,不得改变村内各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所有权。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由使用该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发包。”
法律在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上述职权的同时,还规定了它们做出决定的机制。物权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下列事项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经本集体成员决定:(一)土地承包方案以及将土地发包给本集体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二)个别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之间承包地的调整;(三)土地补偿费等费用的使用、分配办法;(四)集体出资的企业的所有权变动等事项;(五)法律规定的其他事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一)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员及补贴标准;(二)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三)本村公益事业的兴办和筹资筹劳方案及建设承包方案;(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六)宅基地的使用方案;(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九)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法律对讨论决定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和成员权益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也规定,承包方案“应当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
总之,在土地集体所有和村民自治的制度下,作为集体土地发包方和集体财产经营管理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具有决定土地的承包方、宅基地的使用权人、集体收益分配、集体获得的土地补偿费的分配等权力,妇女要实现法律赋予的土地权益,需要经过村民自治机制,通过与本集体经济组织订立承包合同或者由集体经济组织决定分配而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权益。
(三)村民自治规范经由村民会议多数决而通过生效,占少数的妇女的土地权益请求难以在村民会议上得到支持
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需要经由村民自治机制才能实现,而村民集体是通过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形式决定土地承包、集体收益分配、土地补偿费的分配等重大事项的,在现有村民会议的表决机制下,在本集体中占少数的农村妇女特别是流动妇女,其土地权益请求往往难以在村民会议上得到支持。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或者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村民会议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法律对召开村民会议及作出决定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村民代表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有五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提议,应当召集村民代表会议”;第二十八条规定,“召开村民小组会议,应当有本村民小组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三分之二以上,或者本村民小组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同意。”可见在现有的法律中,村民自治进行民主决策的基本规则是少数服从多数,有关土地权益的事项也不例外。
从单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看,女性成员应该占了村民的一半左右,但在女性村民中,出嫁女、离婚女等群体只占了一小部分,因此在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表决作决议的时候,出嫁女和离婚女等群体由于本身数量少而在“民主决策”中处于不利地位。2006年,全国村委会委员总人数2429577人,其中女性人数562777人[10]202,女性人数占总人数的23.16%。在进入村委会的妇女中,正副主任更少,女村委会主任仅占1%左右。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应当有妇女成员”,这一保护性条款,在很多地方变成妇女有一个名额就行了。受到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在进入村“两委”的有限的女性中,能够以妇女代言人身份出发、积极维护妇女群体权益的更是少之又少了。根据联合国的有关研究,“任何一个群体的代表在决策层达到30%以上的比例,才可能对公共政策产生实际影响力。”[11]269女性利益的维护需要更多的女性参与到决策程序之中。在现有的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多数决的规则之下,占少数的流动妇女的诉求难以得到尊重和支持,村民借助于村民会议等决议形式而侵害或者剥夺这些妇女的土地权益也就不难理解了。
(四)传统的习俗和文化使侵害妇女土地权益的村民自治规范获得了村民的认同和支持
女性主义认为,传统和文化也是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取决于文化认可的合法性,而后者又取决于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者。[1]36因此,要分析妇女土地权益被侵害的原因,传统习俗和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可缺少的方面。
在影响流动妇女土地权益的诸多因素中,一种习俗被广泛认同,这就是:“姑娘迟早是别人的”,男婚女嫁,妇女“从夫居”。在这种习俗下,男娶进、女嫁出,妇女婚后到男方家落户和居住。正是在这样的观念下,妇女在婚前被其所在村庄视作暂时的成员。一些地方对未婚女性进行“测婚测嫁”,制定对妇女不分或少分土地的村规民约;还有的地方规定,女性到一定年龄不出嫁也要被收回土地。与此相对应的是,有的地方规定,要招上门女婿,必须经村、组同意,否则不仅男方和孩子不能享受村民待遇,女方的责任田也要被收回。
“各家的媳妇都是一样的”,这也是被许多村民广泛接受的一种认识。这种认识体现了村民的平均主义观念。在村民的观念中,对于新嫁入的妇女不分或者少分承包地或者集体收益,只要同村或者同组的做法一致,就可以接受。正是在这种平均主义的思想观念下,个别的或者少数的妇女,即使敢于维权、挑战众人认同的利益分配规则,在村民会议多数决的议事规则下也往往难以实现其愿望;妇女即使获得了法院的诉胜判决,也常因需要调整众多农户的承包地、法院的判决难以执行而难以实现其要求。
“出嫁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因此女儿出嫁如果要带走其承包地,不仅面临割断亲情的痛苦,还可能受到同村组其他村民的冷眼。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观念下,出嫁女、离婚或丧偶妇女的土地权益在婚姻关系的变化中被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中的许多人甘愿在出嫁或离婚后将属于自己的一份土地留给父兄、前夫或前夫的家庭,极少有通过法律获取自己应有的土地权益者,即或有这样的妇女,也很难得到社会习惯的支持。
总之,在传统的习俗和文化观念影响下,出嫁女等要实现自己的权益,不仅要有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与能力,更要有突破家庭和社区双重压力的勇气和决心,甚至要准备承受牺牲亲情和人情的痛苦。所有这一切,无疑都会成为妇女实现土地权益道路上的困难与障碍。
三、法律调适村民自治规范的努力与不足
应该承认,既有的法律也看到了调适村民自治规范的必要性,并为此采取了原则性的措施。1998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第二十条确立了村规民约等的行政备案制度和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原则,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决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的,或者因结婚男方到女方住所落户,侵害男方和子女享有与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权益的,由乡镇人民政府依法调解;受害人也可以依法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第六十三条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其负责人作出的决定侵害集体成员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集体成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10月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调适村民自治规范问题上有了积极的进展。该法仍坚持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原则,在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同时,该法还确立了对村规民约等的纠错机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三款分别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违反前款规定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第三十六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成员作出的决定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责任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村民委员会不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定义务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从上述立法的进展可以看到,国家法律努力加强对村民自治的监督,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特别是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增加规定了对村民委员会或者其成员的决定的行政纠错机制和司法审查机制,也设置了对村规民约等自治规范的行政纠错机制。可以预料,这些措施的设置会在今后的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是,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有法律在对村民自治规范的调适上还存在不足,甚至可以说是不够有力,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律仍然没有确立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等自治规范的司法审查机制。2010年6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指出,“现有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应当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等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对违法的予以撤销,导致一些地方出现‘村规民约大于法’的现象”,并提出“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修改村委会组织法,建议在该法中增加相应条款”。但修订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只是对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村民会议决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定规定了行政纠错机制,仍然没有确立司法审查机制。
第二,法律虽然确立了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的行政纠错机制,但是法律并没有规定如果乡镇政府不予纠错怎么办,也没有规定如果村民对乡镇政府的纠错决定不服该怎么处理。村民是否可以对乡镇人民政府的不进行纠错的行为或者不服其纠错行为而提起诉讼,现有法律并没有给出解决方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在实践中,一些基层政府往往以尊重村民自治为借口,对妇女等的正当要求不作处理或者处理不力。法律规定对村民委员会或者其负责人作出的决定,妇女作为本集体的成员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请求撤销,并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但依照法律,土地承包、集体收益分配、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等重大事项都是由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的,而村民委员会只是负责执行或者实施这些决定的事项,由此导致起诉村委会的妇女即使获得胜诉,也因村民会议的决定无法改变而难以落实其权益。
第三,被剥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征地补偿费请求权的妇女仍然难以通过诉讼获得救济。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五十五条虽然规定“受害人也可以依法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受制于村民自治原则,法院在处理土地权益争议问题上仍相当谨慎。200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明确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解释第二十四条进一步指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以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可见,在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中,农村妇女在没有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经济组织决定不予以分配土地补偿费等情况下,要实现土地权益还是没有诉讼救济的途径。
总之,在现有的村民自治机制下,法律为权益受到侵害的妇女提供的救济途径存在很大程度上的缺失,而这种缺失在土地资源有限、成员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往往使得在集体中处于少数的出嫁女等流动妇女的权益被牺牲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农村妇女迁徙的过程中,其是在两个以上的集体之间发生流动,由于赤裸裸的利益冲突,其成为利益分配中两个团体之间不受其他利害人欢迎的主体;当利益的获得主体彼此间互有利害冲突的时候,人们的行为极易异化为保障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很难给予其他主体一个相对公平的方案,并常以村规民约的方式等固定其既得利益,使农村妇女的利益在通过民间法的方式进行救济时也受到了很大的阻碍。[12]
四、强化对村民自治的监督,保障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
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乃至村民会议决议等,在学者们的论说中被认为是所谓民间法或习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依据某种社会权威和组织确立的具有一定社会强制性的人们共信共行的行为规范,在我国现有的规范体系中,不仅其存在具有国家法上的根据,更具有价值上的弥补性、转化性和共生性。[13]14-15这些自治规范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弥补了国家制定法的不足,甚至可以成为制定法的重要来源,是国家制定法得以实施和发挥效用的重要基础。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于国家法的局限和资源供给的不足,农村习惯法就以其内生秩序的特性自然地填补空白,以满足乡村社会的规则需要,但是农村习惯法对出嫁女及其子女土地承包权、集体经济分配权、宅基地分配权等财产权益往往进行剥夺和侵害,成为农村习惯法与国家法冲突的突出方面。[14]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2条(f)项规定,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修改或废除构成对妇女歧视的现行法律、规章、习俗和惯例。在我国现有立法的基础上,强化对村民自治的监督,特别是强化对村民自治规范的调适,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侵害问题的必要途径。
首先,应该确立对村民自治规范的司法审查机制。从职责上看,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对于公民、法人之间的各种争议都有终局裁决的权力,法院对村规民约,村民会议决定、决议的合法性和法律效力也有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力。因此,法律应该明确,对于农村妇女因自身土地权益被村民会议决定、决议剥夺和侵害而提起的诉讼,法院应该受理并进行审判,对村规民约,村民会议决定、决议中违反法律、法规的部分,应该依法撤销或者宣告其无效。
其次,应该建立对基层政府在纠正村民自治规范问题上的问责机制。法律既然已经明确基层人民政府有义务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进行备案,有义务责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正其违反法律的村民自治规范,也应该规定基层人民政府的相应责任。在基层政府不作为或者错误作为的情况下,应该赋予村民包括妇女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强化基层政府在监督村民自治上的责任,有助于从源头上减少或避免侵害妇女土地权益的村民自治规范的出现。
第三,应该尽快确立认定村民包括妇女的村民成员资格的标准和程序,同时为没有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妇女提供补偿机制,对集体收益和征地补偿费的分配和使用等明确法定的标准和途径。这些标准和程序的确立,将会为村民会议的决定提供具体的指引,也为法院受理和审理涉及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纠纷案件提供具体可适用的实体规范,从而可以有效地应对现存的无法律规定可供援引的状况。
第四,加强对相关法律制度的宣传,扩大农村妇女的参政比例。要通过深入的宣传教育,使更多的村民自觉地接受在土地权益上男女平等的原则。提高村民委员会中的妇女成员的比例,动员更多的妇女参加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等,使更多的妇女特别是流动的妇女参与到村民会议、村民委员会等的决策过程之中,从而促进农村妇女在分配利益的过程中表达和实现其诉求,减少或者避免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土地权益的侵害。
[1]陈明侠,黄列.性别与法律研究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周安平.性别与法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3]全国妇联权益部.土地承包与妇女权益——关于农村第二轮承包工作中妇女权益被侵害的情况的调查[J].中国妇运,2000,(3).
[4]王蓓.21年,出嫁女的土地之争——安徽霍邱县城关镇25户出嫁女土地被“抢”调查[N].中国妇女报,2010-11-22.
[5]李建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情况的报告[DB/OL].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npc/xinwen/jdgz/bgjy/2010-06/23/content_1578400.htm.
[6]全国妇联呼吁: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相关权益[DB/OL].http://www.women.org.cn/allnews/1301/19486.html.
[7]黄松有.农村土地承包法律、司法解释导读与判例[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8]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9]周应江.界定身份与调适民间法——因婚姻而流动的农村妇女实现土地权益面临的两个法律难题[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5,(4).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07)[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11]李慧英.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12]林苇.妇女农地权益保护的实证再反思[DB/OL].http://www.privatelaw.com.cn/new2004/shtml/20090428-161506.htm.
[13]田成有.乡土社会中的国家法与民间法[A].民间法(第一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14]高其才.新农村建设中的国家法与习惯法关系[DB/OL].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52481.
责任编辑:董力婕
Villager Autonomy Norms and the Protection of Rural Women’s Land Rights and Interests
ZHOUYingjiang
It is an indisputable fact that parts of rural women’s land rights and interests have been infringed by villager autonomy norms.To a large extent,these norms have become the basis for rural women to obtain membership of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the land contract management rights and related land rights and interests.The rule of decision making of villager meeting and the traditional customs and cultural values,bring about villagers’support and self-identify to the autonomy norms which infringe the land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rural women.Though the lawhas made some progress on adjustment to villager autonomy norms,some serious limitations remain.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about villager autonomy and protect rural women’s land rights and interests,judicial reviewmechanismand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mechanismshould be established
villager autonomynorms;rural women;land rights and interests;law’s adjustment
10.3969/j.issn.1007-3698.2011.04.004
2011-05-07
D923.9
A
1007-3698(2011)04-0024-07
周应江,男,中华女子学院社会与法学院法律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妇女法。
100101
本文为中华女子学院2009—2010年度科研项目“农村流动妇女土地权益的法律保护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KG09—0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