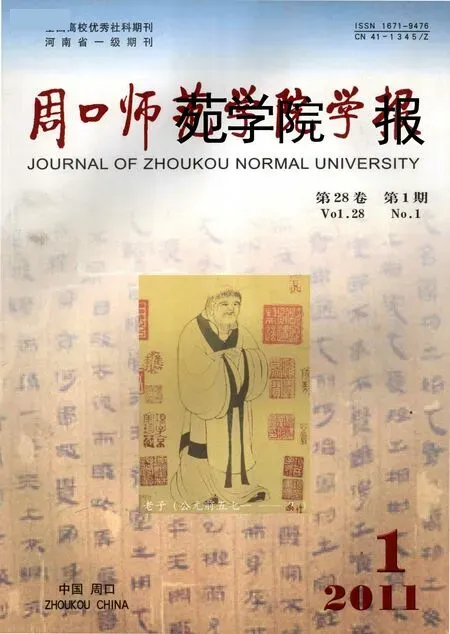王维诗歌英译本译文外的文化操纵发微
2011-02-20靳乾
靳 乾
(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00)
王维诗歌英译本译文外的文化操纵发微
靳 乾
(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00)
在翻译的“文化转向”背景下,根据文化操纵学派的理论,采用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对王维4个英译本译文外的文化操纵表现形式——选材、序言、注释等进行分析,考证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点对译著的影响,以及对读者理解范畴的功用,以探求在翻译过程中折射出的文化关系和译文的历史地位。
文化操纵;王维;译文外
传统意义上的翻译是语言与语言文字之间封闭的转换过程。此论断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已被突破,同时也映衬了1992年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的论文集《翻译、历史及文化》所掀起的翻译“文化转向”的变革。他们指出,“翻译的操作单位既不是单词,也不是文本,而是文化”[1]12。英国翻译理论家赫尔曼斯1985年主编的《文学的操纵》为此铺平了道路,它指出:“从译语文学的角度看,翻译意味着为了某一种目的对原文进行某种程度的操纵。”[2]11也就是说,翻译是对文学文本的操纵,是译者选择立场、翻译策略的结果;翻译本身“从作者转向读者,从原语文化转向译入语文化”[1]17,具有“译语文化对文学翻译文化的利用性质”[3]15。
中国古典诗歌的巅峰——唐诗,在国内外译界占据长盛不衰的地位。其中,王维的诗作因其情景交融、诗境蕴涵清远,对读者有着恒久的魅力,成为被翻译出版最多的中国诗人之一。以往对于王维的论文大多都是把眼光聚焦在译文上,或在译文之间做纵向对比,或看译文与原文之间的横向差别。但是译者的自身背景,译作的选材,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的读者意识,以及译作对文学、文化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单靠对译文的考证并不能够全面地加以证实。查明建认为,“译语文化对原文的操纵,除了译文层面,也对选材,译作在译语中的传播和接收进行干预和控制,其表现形式就是翻译的选择策略,译作的序跋,前言,注释和按语,文学评论等。这些操纵形式可以称之为‘译文之外的操纵’”[3]15。笔者选取了张心沧、庞德、宾纳与江亢虎以及王宝童的含有王维诗歌的翻译版本,对比研究各个版本的选材、序言、前言、注释、概论等译文外的文化操纵因素的表象,在对其各个版本加以介绍的基础上来考察它们在翻译过程中的功用,并考证中国古典诗歌对译语文化的接受与传播。
一、对翻译目的的解释——选材
勒菲弗尔指出:“翻译是对原文本的重写,所有的重写,无论其意图如何,都是对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反映,并通过意识形态和诗学对文本进行操纵,使其在特定的社会中以某种方式发挥作用。”[4]xi而每个译文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历史烙印。译者本着各自的目的选取翻译材料,意识形态自然会体现在选材上。所以考察译本的选材,探究历史背景、文化环境,对翻译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张心沧的译本《自然诗》(Nature Poetry)1977年在英国出版。译者在前言部分指出《自然诗》为他所编撰的《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系列丛书六卷中的第二卷。并说明,这套丛书不是包罗所有中国文学优美文章的杂集,目的是让西方读者或是西方中文专业的学生能够切实地近观中国文坛中的某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活动。所以每一卷都被限定为一类或两类主题,描述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方面,并针对此主题选取一些作品翻译成英语,以便展示给读者。本卷是对中国自然诗主题的独立研究和文选。张心沧在序言中,把自然诗的题材定为中国诗人对自然世界的反应所进行的诗歌创作。他注重诗人而非流派,所以选取了从东晋到唐朝5位重要的山水田园诗人的作品。张心沧指出:“每一个诗人的作品都是描写他们最为熟悉的地理环境,以及这些山水田园之景给他们所带来的亲身感受。”[5]18因此,王维是作为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而选取的,所选作品的创作时间也是他最优秀的山水作品的创作时期。“按年代来分,所译诗歌来自两组:一组是王维在归隐终南山时所作,其中包括《蓝田山石门精舍》;一组是王维在他的辋川居所作。后者是通过王维给裴迪的书信以及与裴迪合作的诗作为两组诗歌的衔接。”[5]62张心沧本人是英国剑桥大学的中文教员,从其选材可以看出他的译文版本是一种学术性的总结以及教材,选材也是围绕着山水田园诗歌题材的文选,译文是为西方学习者更好地理解主题服务的。
与张心沧的选材作为中国文学现象主题之一的阐述相比,庞德与王维的“关系”最为“淡泊”。1915年庞德在美国出版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集《神州集》(Cathay),完全是基于弗诺罗萨的手稿完成的。当时费氏遗稿有大约150首诗,而庞德只选取19首诗歌收录到此集中。其中,“屈原赋相当完整,都有中文、日本读音、单字释义和全句串解,包括《渔夫》《离骚》《九歌》的全文,庞德竟然一首没用”[6]164,可见庞德在翻译选材上的用心。从《神州集》的背景来看,西方社会步入20世纪,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出现了尖锐的矛盾,处于畸形的脱节时期。这些矛盾和现实境况使得西方敏感的知识分子变得日益焦虑不安,迫使他们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产生了重大怀疑[7]57。而在这期间,第一次世纪大战的浩劫也极大地冲击着欧美的传统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念。“《神州集》的面市,第一次把当时欧美读者和译者最感震动的题材——愁苦——突出地表现出来。”[6]166如肯纳所言,“这些诗歌是有关第一次世纪大战的诗歌中最具有生命力的。它们反映了以前所发生的和现在仍在继续的”[8]196。由此看出,庞德清楚自己所翻译的选材,理解读者需要什么样的题材来宣泄他们的情感。而另一方面,庞德从事此翻译的时期,正值英国末流的浪漫主义诗风统治美国诗坛。庞德痛恨并希望能够摆脱这种陈腐守旧、矫揉造作的诗风。从中国古典诗文找到的他所提倡的“意象派”,赋予了庞德诗歌中鲜明的意象和创作新技巧——“意象叠加”。《送元二使安西》是庞德所选取的唯一一首王维的诗歌,但他连这首诗是谁写的都拿不准,故注上李白(Rihaku)或者王维(Omakitsu)。但是从翻译目的上看,庞德的选材是成功的。因为他深入了读者的意识形态,满足了时代背景下的读者需要,并从中国诗中找出支持他的诗学观的例子进行翻译,强化了他的诗歌艺术以及创作理念。
庞德的《神州集》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中国诗歌吸引了美国诗坛的注意。宾纳与江亢虎的《群玉山头》(The J ade Mountain)随后于1929年在纽约出版。《群玉山头》是《唐诗三百首》的中国选本的原本照译,共译311首,里面包括王维29首各种体裁的作品。宾纳能够选取更有难度的翻译版本,是因为江亢虎为前清举人,有着良好的国学功底,而宾纳在着手翻译唐诗之前也积攒了丰富的经验,强强联手,珠联璧合,翻译较难的《唐诗三百首》是可以胜任的。但之所以去翻译一本中国古典诗歌的合集,对宾纳来说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宾纳认为,在面对不堪重负、纷争不断的西方生活,“这些诗歌呈现了内心的平和与美好愿望”[9]4,而他在序言中毫不避讳地表达了中国文化对于西方将会有着巨大的冲击力。他发现比起那些源于希伯来、雅典的文化,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更为崭新,美好和深刻”[10]xiii,“预示未来西方的诗人将会进入学校去学习唐诗……去学习如何最完美地表达激情的延续、生命的核心”[10]xvii。宾纳抨击了现代西方诗歌的状态——如“烛光或是贫血”渺小而微弱,但他的态度却是积极的,他的希望是殷勤的。他认为“美国诗坛现阶段,有着同样的热情,但因为一些特定的原因却没有导致诗歌创作走向更高的水准”,但本国诗人将经历“提升个人的魅力最好的考验”[10]xvi。
王宝童的译本是2005年上海出版的《王维诗百首》(英汉对照·图文本),是一本针对王维诗歌选集的翻译著作。王宝童在前言谈到此译本几经周折才得以出版,并谈及“我素爱王维,忽有天赐良机使我得尽所学,向世界展示这位‘诗佛’的风采”[11]1,其肺腑之言表达了译者对王维诗歌的欣赏以及将其翻译成英文的极大热情。序言中提及了译者在对王维诗歌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如诗中“道”“如意”如何翻译,本着“愿王维以王维的真实面貌走向世界”[11]2的目的,希望通过王维诗歌译本的结集出版将王维的诗歌艺术广泛传播于世界。
以上译者在对译本材料选取的目的中,或表现著作的主题,或张扬自己的诗学创作,或希望对译语文化起到深刻的影响,或希望弘扬原语文化、诗歌艺术等,都是在历史背景的框架下衍生的结果。而其选材的目的也伴随在作者的前言、序言以及著作的概论或是章节的导论中加以了暗示或说明。了解选材的目的,对译本的理解以及考察译作的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原语文化的承载与翻译策略的推衍——序言、前言和导论
译作的出版必然会有序言或前言,这是对译文的必要交代,若是省去,译文便会显得突兀而没有条理。也可以说,译作的序言或前言是译者翻译思想的重要载体,是译者与读者的对话平台。所以考察译作的序言等,有利于把握译作的整体性。笔者通过对4本译作的序言、前言和导论的研究,发现4个版本的译作中都对其翻译目的、原作背景和翻译策略有所强调,而第一点已在第一节阐述,在这里只对后两点加以说明。
张心沧的译本《自然诗》因其作为中国山水田园诗的主题而编撰,概论的行文中亦把中国山水诗歌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及宏丽流程呈现出来。文中穿插着山水诗文加以解说,简明又不失重点。从先秦直至元宋,中国山水田园诗的孕育、形成、勃兴、昌盛、滞待,绵延的历史脉络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值得说明的是行文中所穿插着的诗文的选取。其中,有吴均《与顾章书》的“森壁争霞,孤峰限日”和陶弘景《答谢中书书》的“夕日欲颓,沉鳞竞跃”这些优美的篇章,把祖国美好山河展示在了西方读者面前;所选《论语·雍也》“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和《庄子·知北游》“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却,忽然而已”,以及王羲之《兰亭序》“‘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5]2-17,又表达了中国古人宇宙人生观的哲学感悟;文中还提到了东晋著名战役“淝水之战”、郦道元的《水经注》、倪瓒和唐寅的诗画艺术。这里不仅把中国山水文学作品与文人的人生态度、自然诗观紧密结合,还把山水诗文与政治军事、地质绘画潜移默化地融合在一起加以考察,为西方的读者描绘出中国的壮丽山河,寄情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可见译者的用心良苦。
除此之外,张心沧和王宝童的译著版本都对王维的生平有所介绍,但重点不同。因张心沧的选材主要涉及的是王维在终南山和蓝田辋川归隐时创作的田园诗歌,其又以裴迪交流作为线索涉及到了裴迪的诗歌,所以张心沧在对王维生平介绍时,对裴迪的生平和终南山、辋川的景色都另起段落进行了简洁的描写与说明。王宝童在其英文的序言中简要提到了王维生平的一些重要事件。如734年王维受中书侍郎张九龄的汲引;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时王维扈从皇帝不及,被叛军俘获逼做伪官,含泪赋诗。译者提到的大多为王维的仕途起伏,为接下来要强调王维诗歌的禅宗特点作铺垫。张心沧与王宝童也对王维的写作风格和特色进行了阐述。在张心沧看来,“王维的相对舒适的个人环境,经历于繁荣稳定的盛唐时代、不矫揉造作的社会名望、温和的性情、对佛禅的虔诚、归隐都给予他的诗歌一种宁静与透明之感”[5]64。王维对自然的反映“是冥想的不是激情的”,使之达到“和谐与平静”[6]65。王宝童在介绍王维风格时更倾向于其诗歌中佛禅的特点,他说,“Buddhism was in his being and as a Buddhist he was forever after an intimation or sudden realization of oneness with the universe culminating in a final spiritual perfection thought as release from the troubled world”[11]4。
《群玉山头》译本中,江亢虎在题为《中国诗歌》(Chinese Poetry)的序言中,分7个部分对中国诗歌渊源娓娓道来,类似知识的讲解,给予西方读者一篇中国古典诗歌入门导论。同在《群玉山头》的译本中,宾纳的序题为“诗与文化”,他描述了中国因为拥有特有的诗人、诗情及读者才酝酿出美丽的中国古典诗歌。宾纳也说明了他和江亢虎的序言要探讨不同的问题,他说“我所谈及的不是技术上的手法,所谓的中国诗歌的形式优美,音律和谐”,而是结合着西方的审美,揭示中国诗歌的“实质”:“我们习惯去欣赏西方诗歌中一处处巧妙的细节”,而“中国诗人极少使他们诗中任何一部分去破坏整体感”;中国的古典诗歌“不会跃居现实的界限”,“相反西方诗人把现实作为夸饰与幻想出发点,或是与梦幻般非现实进行对比”;西方读者喜欢追求“在诗中达到戏剧的效果”,但是中国古典诗歌却是“温和的,甚至是琐碎的”,当西方读者能够沉下心来进行鉴赏就会发现这些都是“美的无际延续”,是“内心深处的文字。它们带来了真理、美好、永恒,简单容易地与人直接又自然的联系起来”[10]xiv-xviii。他指出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精髓,肯定了其艺术效应。
这些“潜藏”在序言、导论的原语文化知识成为读者了解译著和原语文化的巨大资源,除此之外,它们又是译者直接表白翻译策略的重要场合,成为读者探求译者在特定历史时段的翻译实践经验及构建翻译理论的重要线索。而在前言中,张心沧、宾纳和王宝童都对其翻译策略做了介绍。张心沧说,“我在翻译的时候,考虑整行或是对句,而不是词或是短语……我尽量避免逐字翻译而带来的笨拙不适宜……由英语的句法贯穿译文……通常每一对句中的第二行词序要么反衬,要么对比第一行”[5]18。而王宝童说“在诗歌翻译上,我主张以诗译诗,要译出原诗的意境和诗味;具体到王维诗英译,我主张译出他的禅意,译出他的‘诗中有画’,译出他独特的音乐美”[11]2。宾纳在序言最后也谈及了一些翻译策略,他指出,“因为时态、人称代词、连词的空缺,中国诗歌的翻译者就像中国读者自己,有大量的活动余地去解读释义”。宾纳多为英语为母语的读者考虑,“尽量少用那些对诗歌理解并不重要的地理和人物的专有名词”,“做一些合理的折中办法”,宾纳指出他使用了一些近似的词语,和对一些不重要意思的省略[10]xviii-xix。
通过4个版本的考证,可以发现前言、序言以及译文前的导论,都承载了非常丰富的信息,是译者让读者接收原语文化的最快捷、最直接的一条通道,也是译者为自己的翻译策略辩护的最有效场合。所介绍的信息可以分成三大部分。一种是对原语文化、原作者和原作的相对客观的介绍,如张心沧译对中国田园山水诗歌史的展现,以及与王宝童对王维生平背景的介绍;一种是译者加入其主观思想的介绍,如宾纳从西方读者的角度来说明中国古典诗歌与西方诗歌的迥异之处,以及张心沧和王宝童从不同的角度评述王维诗歌风格的介绍;第三种就是对译者自身翻译策略最直接的阐述。信息量的充足与丰富,都是开启对译著最深刻领会的钥匙。
三、意识形态的纹路——注释
除了选材、序言和导论外,注释也是重要的译文外的文化操纵因素。根据奈达定义:“注释是用来指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增补信息帮助了解文章中的一些历史文化背景问题。解释不同差异的习俗,读者不清楚的地理位置和物品,转换度量和对一些文字游戏加以解释,对专有名词的补充材料。”[12]239但注释是翻译过程中的产物,每个译者所用注释的数量、长度和内容都是不同的,这恰恰也成为意识形态的操纵作用在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的另一种暗示。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认为:“在处理文本之前,头脑中已经存在一个文本网格和一个概念网格”[13]8,而意识形态正是这样一个“概念网格”,它由“某一特定时期、某一特定社会中普遍接受的观念和态度组成,读者和译者都在这一网格框架所规定范围内处理文本”[13]48。这一定义体现了意识形态是人的思想观念或世界观。它可以是社会的、上层的,也可以是个人的。注释作为原语与译语之间文化沟壑的桥梁,译者也会依据自己的意识形态选择性地进行搭建。
笔者对4个译著进行考察,发现王宝童译本的注释最为丰富。其译著本身为中英对照,注释类型则是对原诗和译文各自对应语种的注脚,但中英文脚注内容的侧重点各有不同,笔者综合起来把它分为三个层次,即语言层次的注释、文化层面的注释和翻译层面的注释。第一种是语言层次的注释,一般指解词释句,而这种注释大多安排在汉语的注脚中。例如,《秋叶独坐怀内弟崔兴宗》解释了“岁晏思沧州”中“沧”字的意思。除此之外,译者还对王维诗作创作的主题、意图、手法、语言风格、背景等有简练的注释。不但如此,很少一些也呈现了译者一些读诗的心得体会。例如在《心晴野望》的脚注中,译者写道“雨过天晴,万物如洗,白水明田,峰峦叠碧,蓝天下农人在田野忙碌——多么清新明丽的自然画卷!”一个感叹符号,表明译者已经深深走入原诗的意境。第二种为文化层面的注释,也有所划分。一类是对源文本中的概念含义在目标语中的空缺进行注释,像人物地名、文化风俗、物品典故之类。另一类是对于两种文化上有冲突或有互动的地方的注释,多分布在英文的注脚里。例如,To Pei Di(《赠裴十迪》)对Pei Di(裴十迪)做了人物注释;Spring on the Farm(《春园即事》)中“还持鹿皮几”英译中的“Elbow prop(几)”做了物品的解释。而两种文化上有冲突或有互动的第二类注释的例子有《西施咏》。汉语的注脚中写道,“诗题借用英国诗人 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歌颂女性美的名诗She Walks in Beauty和另一位英国诗人Alfred Tennyson(1809—1892)的诗 Idylls of the King,故英文题目为She Shone in beauty—Idyll of Xishi”。最后一种翻译层次上的注释,是译者告知读者在遇到文化盲点时是如何解决的。如《赠裴十迪》中的“澹然望远空,如意方支颐”,译者在脚注中写道:“‘如意’是英语中没有的器物,可以音译为ruyi,但用roy可以省去一个音节,更易安排诗律,且 roy的发音也与royal相近,暗示这种器物给人的极大妙趣。”注释中译者还会列下英诗诗名,希望读者对比去读:比如译者把《观别者》与Byron的When We Two Parted对比;《鹿寨》与Wordsworth的She Dwelt A mong the Untrodden Ways对比。这些注释负载的信息丰富而巧妙,不仅为中外读者在诗歌理解上扫清障碍,而且为译者表现自己的诗歌领悟能力和翻译策略拓开渠道,由此加强了译者、原文本的作者和目标语的接收者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群玉山头》译本中,宾纳与江亢虎的注释也包含了释词、释典故、解释句意以及大量文学性注释。但是与王宝童相比,宾纳则以西方人的思维,从遵循西方读者理解的逻辑角度进行注释。例如杜牧《遣怀》中“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青楼”,是指妓院。但是对于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英美读者来说,他们对青楼所知甚少,于是宾纳对此辅以注释,将青楼翻译为“Blue Houses”,类比为“the quarters of the dancing-girls”,而在西方dancing girl是指以伴人跳舞为业的妇女。对李白《清平调》第二首“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的“巫山”的注释:“Wu Mountain was the abode of nymphs and fairies”。其中“nymph”,词源本身为罗马神化的居于山林水泽的仙女、女神,而宾纳用它来类比中国典故中楚襄王梦里相会在巫山兴云降雨的神女。宾纳运用文化范畴不同却有相似之处的词汇进行释义,使西方人能够心领神会,更好地理解译文。另外,宾纳对李白的《玉阶怨》指出,“Mr.Ezra Pound in his Cathy,translating this and other poems by Li Po,misled readers for a period by using the Japanese name Rihoku...”由此可以看出宾纳对庞德译本的姿态,暗示了庞德的《神州集》在当时对西方读者所起到的巨大反响。宾纳本着一个西方人的思维,以当时的西方诗歌文化背景为参照对诗歌进行注释,以求得读者最大限度地亲近和理解译本。
使用注释最少的是庞德的《神州集》,仅仅使用了两个注释。一个是集子的开头用注解的方式表明了《神州集》的产生是得益于弗诺罗萨的手稿以及森槐南、有贺两位日本学者对中国诗的注解,另一个就是《玉阶怨》一诗的翻译中用注释说明该诗的含蓄手法,而集子中所有涉及中国文化的翻译都没有采用注释。这种尽量少加注释的做法得到了英美读者的承认,也反应了庞德的主张。他在论及比尼恩对但丁《神曲》的翻译时说“我们要感谢比尼恩,他向我们展示(我们借此也永远地希望)但丁作品的翻译所用注释可以这样的少”[14]。而张心沧译本的注释,则采用了清朝赵殿成的《王右丞集笺注》。可见,其翻译策略还是尊重原著,保证严谨。
四、结论
4个译著的选材、序言和注释都阐释了翻译的目的,引出了翻译策略,表现当时的文化意识形态和作者的诗学观点对译著产生的文化影响和操纵。读者在此得到了更多文化意义上的收获,理清了特定历史时期通过翻译所折射出的文化关系,了解了当时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在翻译过程中的渗透,对整个译著有了深刻的把握。而那个中国历史上清秀典雅、多才多艺的诗人王维也披挂上译者赋予的历史文化长袍,步履徐徐地走进读者的眼帘。季羡林说:“文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化一旦产生,立即向外扩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交流’。”[15]所以,放在文化历史框架的译著,不再拘泥于是否忠实原著的唯一标准,而是更多去考察文化体系之间的相互借鉴、相互吸引。译文外的文化操纵是宏观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如查明建所说“将译文层面和译文之外的文化操纵结合起来,才能比较全面地分析特定时期翻译文学的性质,从而对翻译文学与译语文化的关系有更深刻的认识”[3]25。正是译文外的文化操纵,拉近了读者与译者的距离,为聆听历史的呼声和译者的心声提供了最理想的场合。
致谢:感谢河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马红军教授借与王维资料。
[1]Bassnett Susan,Lefevere Andre.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M].London:Printer,1992.
[2]Hermans Theo.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C].London:Croom Helm,1985.
[3]查明建.论译文之外的文化操纵 [C]//罗选民.文化批评与翻译研究.北京:北京外文出版社,2005.
[4]Lefevere Andre.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M].London and New York:Rouledge,1992.
[5]Chang H C.Nature poetry-Chinese literature 2[M].Great Britain:Edinburgurgh University Press Printed,1977.
[6]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7]蒋洪新.庞德的《华夏集》探源[J].中国翻译,2001,22(1):56-58.
[8]Kern Robert.Orientalism,modernism,and the Americar 1 poem[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9]Bynner Witter.Remembering a gentle scholar[C]//James Kraft.The works of Witter Bynner:selected letters.New York:Farrar,Straus,1981.
[10]Bynner Witter,Kiang Kang-hu.The Jade mountain[M].New York:Alfred A.Knope,1929.
[11]王宝童.王维诗百首(汉英对照·图文本)[M].上海:上海兴界图书出版社,2005.
[12]Nida Eugene.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13]Bassnett Susan,Lefevere Andre.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14]Eliot T S.“Hell”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M]//祝朝伟.建构与反思.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208.
[15]季羡林.东方文学交流史·序[M]//祝朝伟.建构与反思.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328.
On cultural manipulation beyond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in WANG Wei’s translation versions
J IN Qi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Hebei Norm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 050000,China)
With the“Culture turn”in translation studies,prefacing,forewords,introduction and annotate in translation are the manifestations of cultural manipulation.Based o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manipulation,this paper analyses the external manipulations beyond texts in four WANG Wei’s translation versions under the method of describing.It is to inspect the effect influenced by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different ideologies and different poetic point of view,and to find their functions for readers understanding the translation,then to explore the deeper problem of translation process.
cultural manipulation;WANG Wei;manipulation beyond the translated text
H315.9
A
1671-9476(2011)01-0077-05
2010-08-30;
2010-09-27
靳 乾(1984-),女,河北保定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典籍英译研究。
收稿日期:2010-09-15;修回日期:2010-11-12
200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秩序与自由:儒道功能互补的历史形态及其当代向度”(086ZX04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 静(1976-),女,河南焦作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及美学。
②《骈拇》有“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之说,指的是庄子对名辩学派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