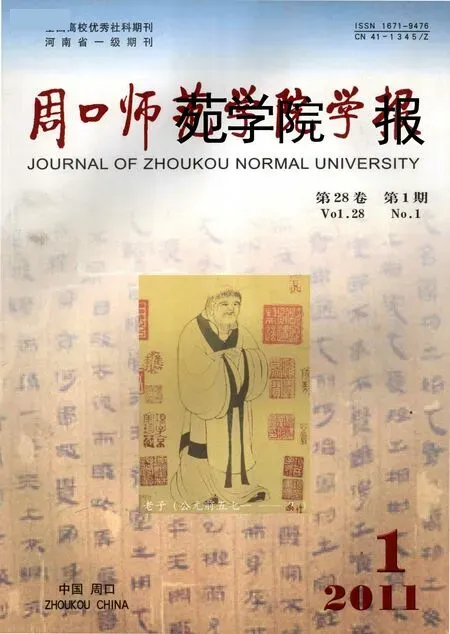红颜诗词中乐器意象翻译技巧论析
2011-02-20顾正阳施婷婷
顾正阳,施婷婷
(上海大学英语系,上海200444)
红颜诗词中乐器意象翻译技巧论析
顾正阳,施婷婷
(上海大学英语系,上海200444)
从描写宫廷女子、官宦女子和青楼女子的红颜诗词入手,探讨其中有关乐器意象的翻译方法和技巧,向译语读者展现其所带来的别样审美体验。
红颜诗词;乐器意象;翻译技巧
古诗词中的“红颜”,既可指宫中的“六千粉黛”、官贵胄家的大家闺秀,也可指寻常百姓家的“小家碧玉”,抑或指青楼坊肆间的“莺莺燕燕”。这些红颜,虽阶层不同,却都与乐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自《诗经》就有“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说的是少年弹琴鼓瑟向美丽贤淑的姑娘求爱。而南朝时期的《孔雀东南飞》“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则写出了弹奏乐器是古时少女养成时期必修的功课。在器乐艺术尤为繁盛的唐代,则有“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琵琶女借由“轻拢慢捻抹复挑”的高超技艺“说尽心中无限事”。到了词盛行的宋代,词人笔下的红颜乐器传递的依旧是浓浓的儿女情:“记得小苹初见”,“琵琶弦上说相思”。笔者现从描写宫廷之女、官宦之女以及青楼之女的诗词入手,探讨其中有关乐器意象的翻译方法。
一、宫廷女诗词翻译
宫中的年轻女子,大体可分成三类:公主、后妃和宫女。身份不同的她们都与乐器结下了不解之缘。公主的生活应是无忧无虑,但适逢乱世,则免不了成为两国邦交的和谈筹码,黄沙道上至今犹听得“公主琵琶幽怨多”。后宫佳丽有三千,幸运的得以“三千宠爱在一身”,“春从春游夜专夜”;不幸的只有在孤独长夜“拥衾欹枕暗伤心,起坐窗前弄玉琴”。宫女们的命运都是凄苦的。初入宫门的她们或许时有欢笑——“笑把瑶笙学凤鸣”,然而日复一日,随着生命的光彩和生活的乐趣逐渐消失,她们唯有“空余孤枕不成寐,拨碎琵琶弹泪痕”。试用以下方法展示诗歌意境。
(一)文化转换显里层意境
古诗词中的意象经常具有表里双重性,因而造成了意境的双重性——表层意境和里层意境。表层意境往往从描述性的意象示现和比喻性的意象示现中便可获得;而里层意境,则需透过表层意象与意蕴获得启示,并将其作为整体的象征性意象示现,如此方可“曲径通幽”。古诗词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象——神话传说、时令节气等,往往要透过其表层意境方能获得里层意境。而在诗词的英译中,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有的意象只按字面意思翻译,即只译出表层意境;有的虽被译出了里层意境,却太过直白,失去了原有的文化意蕴。两者皆阻断了读者由文化意象的表层对其“象外象”“味外味”的联想与想象。因此,在翻译此类意象时,我们不妨将东方的文化向西方进行转换——将代表东方文化的意象译成代表西方文化的意象。如李商隐《锦瑟》中的“沧海月明珠有泪”引用了东方鲛人泣珠的传说,西方读者不了解其中的文化,自然激不起审美情趣;但若将此传说转换为与之相似的西方美人鱼传说——鲛人的泣珠转换成美人鱼死前的泪珠,译语读者即可通过两个传说的共通点,经历与源语读者相似的审美历程——由表层意境进入里层意境。请看张祜《宫词》: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
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诗中的宫人在少女时代不幸被选入宫廷,远离了故乡与亲人——去家“三千里”,幽闭在深宫之中——入宫“二十年”,从昔日的“脸似芙蓉胸如玉”变成了如今的“红颜暗老白发新”。失去幸福、失去自由的她已是可悲,最后还得为君王殉葬。临死前,她要求唱一首悲伤的《何满子》,以表达内心的怨忿。在翻译时,应力求显示“何满子”一词的文化内涵,需从它的表层意境——人名或曲名,引导译语读者进入里层意境——宫人临死前悲歌一曲的情形。译文如下:
Home-sick a thousand miles away,
Shut in the palace twenty years,
Singing the dying swan’s sweet lay,
Oh!How can she hold back her tears![1]
译文将“一声何满子”译为 Singing the dying swan’s sweet lay(歌一曲天鹅的绝唱),实现了文化的转换。传说天鹅平素不唱歌,但在死前必定会引颈长鸣,高歌一曲,其声哀婉动听,感人肺腑。在西方,Swan song(天鹅之歌)常用来比喻某个诗人、作家生前的最后一部杰作。诗中的“何满子”是宫人死前最后一次歌唱,恰如天鹅垂死前的引吭高歌。译语读者通过对dying swan的理解进入里层意境,他们能想象到宫廷女子命运无法自我掌控的悲哀,甚至能体会到她们在歌声中流露的悲戚与绝望,得到与源语读者同样的审美感受。
(二)由曲入“境”拓展审美空间
何谓“境”,一般而言,境是景所带来的思想空间,是无形的、无限的,无比例、无尺度的,由景物而产生的想象空间。然王国维又语:“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2]故而,诗有诗境,画有画境,曲有曲境。张皓先生在论及“境”与“景”“象”之不同时曾指出:“境”的容量更广阔,空间感更强,整体化的程度更高。他引王昌龄《诗格》中的话指出,“境”“是指深深印在心中,能总揽万象众景的意想天地、如临其境的审美空间”[3]。因此,诗境、画境、曲境等一系列“境”之内涵远比诗、画、曲本身要高出许多。一如《春江花月夜》,既是诗,也是画,又是曲,其境也,生生不息,以至无穷。建构意境无穷的审美空间,是一切艺术创造的本质和最高追求。译者,虽扎根于源艺术,却也是艺术的创造者,应当给译语读者建构足够的审美空间。古诗词中涉及到的曲,很多只需直译其名,但有时需译出作者精心设计的延伸意义,为译语读者营造一个深邃的境界,让他们在审美的想象中尽情驰骋。请看白居易《长恨歌》选段:
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
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贪色、求色的唐玄宗几经寻觅,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妃。在那之后,他日夜沉湎于酒色歌舞之中——“从此君王不早朝”。杨氏族门因杨玉环“一人得道”而“鸡犬升天”。他们争权斗富、紊乱朝纲,最终酿成了“安史之乱”。叛军逼近长安,歌舞升平的华清宫一片慌乱。《霓裳羽衣曲》给君臣嫔妃带来了欢声笑语,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战乱和灾难。在翻译该曲时不应只译其名,而应深入其境——展示众人的动态神情,以拓展视听审美空间。译文如下:
The palace towering high on Mount Li soared to the cloud,
In the air the music,borne by the wind,was sounding loud.
Sweet songs and dancing,accompanied by the pipe and chord,
His majesty enjoyed all day long butstill didn’t feel bored.
One day at Yuyang the beating of war drums thrilled the ground.
And shocked the palace which was then in the music and mirth drowned[4]569.
译文将“惊破霓裳羽衣曲”译为(the beating of war drums)shocked the palace which was then in the music and mirth drowned(“战鼓”震惊了沉浸在音乐和欢笑中的君臣嫔妃),未译曲名,而是译出了众人沉浸在曲境中的乐态。宫殿之中,宛如仙女下凡的宫女载歌载舞、衣袂飘飘,歌者、舞者、奏乐者、听者皆陶醉其中的情境,会自然而然地打开译语读者视觉和听觉上的审美空间,他们会不由自主想象到,战争消息传来时殿中气氛及人物表情的戏剧性转变——乐境变哀境,喜情转悲情。
二、官宦女诗词翻译
官宦人家的女子从少女时期便养在深闺,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们渐渐知琴(情)懂琴(情)。卓家有女文君,听到司马相如以琴弹唱“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便按捺不住,与其私奔;黛玉听《牡丹亭》笛韵悠扬、歌声婉转,唱“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唐婉本与陆游夫唱妇随,却无故被陆母休弃,心痛难以自持,夜夜听“角声寒”,觉“夜阑珊”;李清照中年丧偶,每每感叹“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试用以下方法展示诗歌意境。
(一)调节审美心理距离
美,无处不在。生活离不开审美,文学更离不开审美。瑞士心理学家、美学家爱德华·布洛在他的《心理距离》一书中指出,在审美中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使得客观现象无从与现实的自我发生“勾搭”,因而能使它充分显示其本色。这个“距离”,并不是简单指时间或空间距离,而是介于我们自身和那些作为我们感动的根源或媒介的对象之间的距离,它是一种心理状态,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并且在“差距”和“超距”的情况下都会导致审美的“失距”——美感的丧失。“距离”太远,好比是“遗世而独立”的北方佳人,只能令人望美兴叹;“距离”太近,又好比是北方早春二月雨后的春草——“草色遥看近却无”。因此,在审美活动中若要发现事物的美和诗意,就必须在事物与我们的利害考虑之间,插入一段适当的不即不离的“距离”,既欣赏事物的最近距离而又没有丧失距离的那种状态。古诗词在遣词用字上一般简练、含蓄乃至晦涩,如若照译成目的语,未免离译语读者太远,令他们丧失对作品所传递的思想感情的碰触能力。因而在翻译中,译者应更多地拉近译语读者和译文的审美距离,帮助他们进入角色、产生共鸣,调动审美情感。请看李清照《孤雁儿》下阕:
小风疏雨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
这首词是词人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丈夫病逝之后,她一直过着“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生活。耳边熟悉的笛声不禁使她想起过去与丈夫一起听曲的时光,而如今“人去楼空”,只有屋外的“小风疏雨”伴着她泪流汩汩。“吹箫人去”借用了秦穆公之女弄玉与其夫君箫史的典故,“吹箫人”原指箫史,词人用以比拟自己的丈夫赵明诚,以含蓄的手法提及心中所念之人。在翻译时,“吹箫人”既不能翻译成“箫史”,让译语读者莫名其妙,也不宜按字面意思译为“吹箫的人”——不切合作者的心意。我们宜译出“吹箫人”的实指,以拉近读者的审美距离,让他们听到《梅花三弄》的曲调,看到词人的眼泪。笔者试译如下:
In the soft wind and light rains,
My tears flow like spring streams.
Already my beloved was gone,
And my house still and cold.
How can I bear to lean
On rails solitary and alone.
Still I plucked a branch of plum,
But to whom I could send with love.
译文将“吹箫人”译为my beloved(我的爱人)。如若直译成“吹箫的人”,译语读者只知词人在思人——一个吹箫的人,审美联想至此便无法延伸下去,因为与审美对象“吹箫人”的距离较远,而在翻译时将其明朗化为词人的爱人(beloved),甚至是丈夫(husband),那读者心里产生的审美效果将大大不同。译语读者在明白了作者的思念之人正是她深爱的丈夫之后,再读前文,便觉得审美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读者可以联想到昔日词人夫妻间的恩爱时光,词人痛失爱侣时的悲痛,以及如今恰似“湘江日夜潮”那样的“愁”。可以说,虽未译“吹箫人”一字,却尽显其中的深意。
(二)营造听觉上的空白美
当代著名画家李可染说:“空白,含蓄,是中国艺术的一门很大的学问。”[5]133宗白华先生则认为:“画家所写的自然生命,集中在一片无边的虚白上。”[5]144作画如此,作诗亦然。“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是谓真境界。严沧浪云:“诗之有神韵者”,“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5]147。李煜《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中词人导情入景,将“东流”的“一江春水”定格成一片空白;辛弃疾《丑奴儿》“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不正面“说愁”,却道“天凉好个秋”,戛然而止,“欲语不语,吞多吐少,以使读者宕出远神,另辟一个境界”[5]139。空白之美是靠译者的创造与读者的想象共同完成的。正如法国诗人马拉美所说,“一首好诗画出的不是事物,而是事物所产生的效果”[5]208,在翻译诗歌时,译者所需的不仅是呈现原诗的事物,更要不断提升译物所呈现的效果。在器乐的翻译中,译者应适时地营造听觉上的空白美,将读者调动到“此时无声”处尽享“胜有声”的艺术魅力。请看李清照《永遇乐》上阕: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元夕晚霞瑰丽,天气融合,佳节良辰也。当年在汴京,姑娘们必定盛装艳饰,结伴去赏灯游玩,姐妹们说说笑笑,边观灯,边争胜——谁的打扮最漂亮,最可人。如今,国破家亡、流落他乡,哪还有兴致去游乐。看到美景,不但不乐,反而悲伤。此时又传来令人哀伤的《梅花落》笛声,更是雪上加霜,她痛苦得不堪忍受——感到花落了,人也死了——她觉得自己在精神上已死了。我们在翻译“吹梅笛怨”时,应为译语读者创造一个听觉空白,产生“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前2句译文如下:
The setting sun like molten gold,
Gathering clouds like marble cold,
Where is my dear?
Willows take misty dye,
Flutes for mume blossoms sigh.
Can you say spring is here?[6]
译文将“吹梅笛怨”译为Flutes for mume blossoms sigh(吹着梅花曲的笛子发出叹息)。一声叹息,留下了听觉上的空白。Sign(叹息)一般用来表示人的动作,用在这里显然是赋予笛子人的感情色彩,因人在无话可说、无法可想、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会叹息。译者没有将“怨”直译为complain,因为它多给人以喋喋不休之感,不能激起审美情趣,而sign虽只一声,却足以引导译语读者去寻找叹息背后的深意,去想象词人喟叹物非人也非的无尽凄凉与忧伤,感受到其中的凄美。缪塞曾说,“最美丽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
三、青楼女诗词翻译
古代的青楼女子有很多脍炙人口、传颂千古的佳话。她们色艺双绝,士大夫甚至帝王家为之销魂夺魄。犹记得秦淮河上“金陵八艳”,犹记得钱塘名妓苏小小,犹记得沉箱投江的杜十娘。她们虽身在风尘,却有着不屈的傲骨和不尽的才华。诗人钦慕她们的才气,同情她们的遭遇,赞赏她们的节操,对她们的描述都是褒扬有加。试用以下方法展示诗歌意境。
(一)译质地,强化音乐视表象形象
任何事物映入主观后形成的感性反映形式基本只有两种:感觉映象和表象映象。音乐也是一样,它有“听感觉形象”和“视表象形象”两种映象。当声象“落”在听感官上,直接产生听觉映象,这就是“听感觉形象”(简称“听觉形象”或“听象”);而如果听乐时,还能间接于脑内引起视表象的浮现,这就是“视表象形象”(想象的视象,简称“视象”)。听象和视象合为音乐在主观上的“二重形象”。然而,一般听象常在,而视象不常在。这是因为听象是声象在主观上的直接投影,只要声象在,听象必在,而视象却不一定,并非所有的音乐都会将视表象带进音乐,或能直接引起视象的联想。因此,在描写乐声的时候,诗人总会不自觉地加入视表象的描写,以使听众获得视觉上的审美享受。如李贺听李凭弹箜篌,好像“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白居易听琵琶声,又似“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在翻译器乐的时候,我们应注意到器乐听象明晰、视象晦暗的特点,从多角度挖掘可联想到的音乐视表象形象,以使译语读者在视听上皆能得到美的享受。请看白居易《琵琶行》选段: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此段虽是乐声初起,却已充分展示了琵琶女的不俗演技。这全赖她年轻时的学有所成——“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她又颇有姿色——“妆成每被秋娘妒”。由于色艺超群,她声名大噪、红极一时。然而好景不长,“暮去朝来颜色故”,她只得“嫁作商人妇”,本想图个生活安稳,不曾想“商人重利轻别离”,留她一人独自在江上漂泊。此处的前奏曲好似琵琶女对往昔风光生活的追忆,是那么的美好,那么的令人愉快。“大珠小珠落玉盘”更是形象地反映了她雀跃的心情。在翻译时,我们可对“珠”的质地加以选择,译出最清脆圆润的声音,在给听觉感官带来愉悦的同时强化其视表象形象。后4句译文如下:
The loud pattering sounds from thick chords were like rapid shower,
The soft drumming sounds from thin chords like whispers in a bower.
Pattering sounds and drumming sounds,played in an intermingled way,
We heard big beads and small beads,of glass,fall on a jade tray[4]583.
译文将“大珠小珠”译成了big beads and small beads,of glass(大大小小的玻璃珠子),译出了珠子的颜色和质地,强化了音乐的视表象形象。在众多的制珠材料中,玻璃的色泽透明,不含杂质,制成的珠子像水珠一样,在下落时的视觉效果也如同落雨一般,与上文“大弦嘈嘈如急雨”的“急雨”不谋而合。而玻璃的质地使得玻璃珠子在与玉石相碰撞的时候声音清脆悦耳,不像木珠或珍珠那样发出的声音结实、沉闷,在听觉效果上更符合当时欢快的曲调。
(二)刻画细节,增强情感表现力
作家李准曾经说过,没有细节就不可能有艺术作品。细节描写是指对生活中的细微而又具体的典型情节,加以生动细致的描绘,它具体渗透在对人物、景物或场面的描写之中。前苏联作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说,“描写得出色的细节,且能使读者对整体——对一个人和他的情绪,或者对事件及对时代产生一个直觉的、正确的概念”[7]。早在春秋时期,老子就说过“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诗可谓“大事”矣,历代文人墨客孜孜以求,可谓做足了细工。郑板桥写《七歌》:“我生三岁我母无,叮咛难割襁中孤。登床索乳抱母卧,不知母殁还相呼”,通过对幼时自己丧母却无知地“登床索乳”“还相呼”的细节描写,无形中带给读者心灵上久久难以平复的冲击。译诗亦可谓“大事”矣。托尔斯泰说:“只有当艺术家找到了构成艺术作品的无限小的因素时,他才可能感染别人,而且感染的程度也要看在何种程度上找到这些因素而定。”[8]那么,译者便是要找到那“无限小的因素”,找到能引发读者“情感的炸药包”——诗的细节,最大限度地将其呈现,力求达到不减一分、反增一分的境界。请看周邦彦《少年游》上阕: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
此词描写歌女恋情。开篇即定格了一组画面:如水的“并刀”,胜雪的“吴盐”,“新橙”“纤手”。时新果品中透露出浓浓的爱恋与温情。将视线拉长到闺房内:香气弥漫中,男女主人公正相对而坐,以调笙的方式传递着彼此的情意,感情也在你侬我侬中逐渐升温。时间缓慢延伸至夜半时分,男子欲行,而女子婉言相留——“言马,言他人,而缠绵偎依之情自见”。在翻译“相对坐调笙”时,我们可刻画出能想象到的细节——男女双方轮流吹笙,既增添了情人间互动的趣味,又显现了二人的情深。上阕译文:
The knife is sharp,and clear as water,
The jade plate is whiter than snow;
She peels a fresh orange with fingers slender.
Silk screens and blinds warmer grow,
Wisps of smoke rise from the incense burner,
Face-to-face,they play by turns a pipe solo[9].
译文将“相对坐调笙”译为“Face-to-face,they play by turns a pipe solo”(他俩面对面轮流吹着笙)。原句也可理解为:他俩面对面坐着,女子为男子吹笙。然而,这样未免显得单调乏味,男女双方缺乏互动不说,还透露出一种男尊女卑的感觉,与作者极力想表现二人之间浓情厚意的初衷不符。译者将主语译为:they(他们两人),并加译 by turns(轮流),说明两人皆有动作,并非是一方传递情意,另一方只跟着接收而已,他们通过传接笙,你一句我一句地轮流吹奏,同奏一支曲,同奏一种情——爱。缠绵之情向译语读者流淌过去,进入他们的心田,再随着他们的思想流淌开来——流淌到他们以往的与其相似的男唱女随的记忆中去……
古代各种乐器一经红颜之手,便和她们的身世、情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诗人的笔下,上至宫廷,下至青楼,既有深锁宫闺、抚琴弄筝的帝女嫔妃,又有吹笙听箫、“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仕女名媛,还有历经沧桑、琵琶犹抱的艳姬名妓。这许许多多记载着红颜与乐器的诗歌,不仅是诗人个人有感而发的作品,也是无数红颜借乐器寄托的心声。正如罗曼·罗兰在《论音乐在世界通史中所占的地位》中说:“音乐的实质,它的最大的意义不就是在于它纯粹地表现出人的灵魂,表现出那些在流露出来之前长久地在心中积累和动荡的内心生活的秘密吗?”[10]因此,无论我们采用何种译法,都是为了通过展示乐器的意象,让译语读者体会到古代红颜通过音乐所倾诉的别样情感,从而在审美过程中得到与源语读者相似的愉悦。
[1]许渊冲,陆佩弦,吴钧陶.唐诗三百首新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7:323.
[2]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8.
[3]张皓.中国美学范畴与传统文化[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237.
[4]吴钧陶.唐诗三百首[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7.
[5]钟文.诗美艺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6]许渊冲.宋词三百首[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327.
[7]谢文利.诗歌美学[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
[8]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24.
[9]陈君朴.词一 О一首英译[M].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67.
[10]胡经之.文艺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326.
H315.9
A
1671-9476(2011)01-0072-05
2010-08-19;
2010-09-06
2008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古诗词英译文化理论研究”(2008BYY004)系列成果之一;第四届上海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古诗词英译中的乐器文化初探”(SHUCX102079)成果之一。
顾正阳(1948-),男,上海人,教授,主要从事古诗词曲英译、英汉互译研究;施婷婷(1987-),女,江苏如皋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古诗词英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