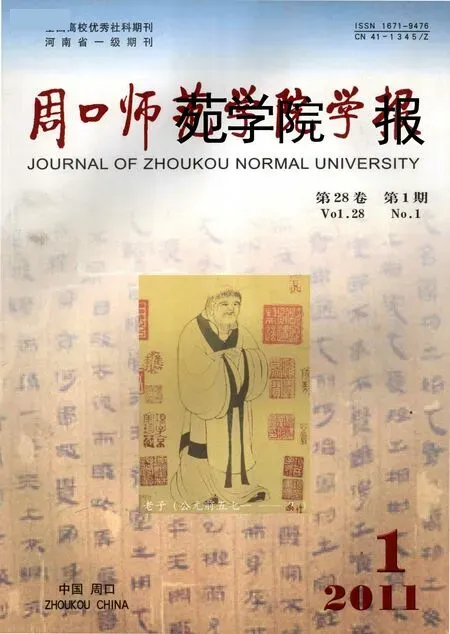略论宋濂的诗学观
2011-02-20任永安
任永安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略论宋濂的诗学观
任永安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宋濂论诗强调诗歌的伦理教化功能,认为诗、文在功能上一致,同为载道之具;诗歌要以得“性情之正”为标准,反对师心自用,主张向古人学习,以汉魏盛唐诗歌为师法对象;作诗要五美俱备,在此基础上,诗人还要注重养气。
宋濂;诗学观;诗文一原
宋濂(1310-1381年),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人,元末明初重要的文学家。对于其文学创作,研究者多认为他以文著名而不擅长诗,所以多论及其散文创作及文论。其实,宋濂不但擅长作诗①笔者从日本藏宋濂《萝山集》抄本中发现其元末所作诗歌500余首,这些诗歌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们显示了宋濂在诗歌创作上取得的较高成就。(详见拙作《日本藏宋濂〈萝山集〉抄本考述》),而且对诗歌理论也有独到的见解。本文不揣浅陋,从诗文一原、师法对象及作诗方法等方面阐述其诗学观,以期加深对宋濂文学观念的理解。
一、诗文本出于一原
受理学思想的影响,宋濂论诗强调诗歌的伦理教化功能,认为诗与文在内容及功能上是一致的。他说:“诗、文本出于一原,《诗》则领在乐官,故必定之以五声,若其辞则未始有异也。如《易》《书》之协韵者,非文之诗乎?《诗》之《周颂》,多无韵者,非诗之文乎?”[1]诗与文的区别只在音乐属性上,《易经》《尚书》中协韵者可以看做诗,《诗经·周颂》中无韵者可以看做文。诗与文在用词、内容上是一致的,不可“歧而二之”。因此,他反对后世的儒者、诗人之分,认为这导致了诗与文在表现内容上的差异,致使“仁义道德之辞”成为诗家大忌,而“风花烟鸟之章”则充斥于诗作。
诗与文不但在内容上没有区别,在功能上也要一致,都要有补于治化。宋濂《刘母贤行诗集序》:“诗人之吟咏夥矣,类多烟霞月露之章,草木虫鱼之句,作之无所益,不作不为欠也,华编巨册,摹印而行者比比有之,其视贤母之诗,有补名教者为何如哉?”[2]古今诗人吟咏之作很多,但大都是“烟霞月露”“草木虫鱼”之章。这样的诗歌作之无益,不作也没什么欠缺。而名士大夫所作赞扬刘母贤行的诗歌,能够“有系彝伦之重”,读后使人“感激奋励”,应当“刻梓传世”。
那么,什么样的诗歌才能够有补于治化呢?宋濂提出要以得其“性情之正”为标准。他说:“夫诗之为教,务欲得其性情之正。善学之者,危不易节,贫不改行,用舍以时,夷险一致,始可以无愧于兹,如君者盖近之矣。世之人不循其本,而竞其末,往往拈花摘艳以为工,而谓诗之道在是,惜哉!”[3]诗歌是“吟咏性情之具”,诗人因事触物,心有所感,发而为情,“情至而形于言,言形而比于声,声成而形诗生焉”。因此,要发挥诗的教化功能,就要在得其“性情之正”上下工夫。善于学诗之人,危难之中不改气节,贫困之时不易言行,“用舍以时,夷险一致”。此时,发而为诗就会“和而不怨,平而不激,严而不刻,雅而不凡”,可以使“读者鼓舞而有得,闻者感发而知劝”。这就是能够得“性情之正”,是作诗之本、学诗之道。
宋濂所谓的“性情之正”与元代刘将孙、杨维桢等人的“诗本性情”“人各有性情”并不相同,而与郝经、虞集的说法非常接近。南宋末年,随着江湖诗风乃至江西诗派的流弊逐渐表现出来,作家们开始对唐、宋两代诗风的不同进行反思。到了元代,他们更把目光投向唐代,宗唐抑宋,最终形成宗唐复古的文学潮流。元人宗唐复古思潮的实质就是“针对宋诗的弊病和理学家鄙薄诗艺的偏颇而要求恢复诗歌‘吟咏性情’的传统”[4],但不同论者所使用的“性情”概念含义并不相同。
元初刘将孙提出:“诗本出情性,哀乐俯仰,各尽其兴。后之为诗者,锻炼夺其天成,删改失其初意,欣悲远而变化非矣。”[5]他认为诗是作者感情的自然流露,诗歌抒发的情感是自由的、天然的,无需“锻炼”“删改”,这可谓是自然的性情论。元初赵文、元末杨维桢主张充分张扬个性的性情论。如杨维桢《李仲虞诗序》:“诗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则人各有诗也。得于师者,其得为吾自家之诗哉?”[6]结合他的诗歌创作来看,他所谓的性情就是指诗人任情恣性的个性。元初的郝经与元中期的虞集则提倡“情归雅正”“性情之正”。郝经《五经论·诗》:“诗者,述乎人之情也。情由感而动……美而不至于谀,刺而不至于詈,哀之也不至于伤,乐之也而不至于淫。”[7]虞集《胡师远诗集序》:“近世诗人,深于怨者多工,长于情者多美,善感慨者不能知所归,极放浪者不能有所反,是皆非得情性之正。”[8]他们都认为诗歌皆由感而发,但这种感情不是强烈奔放的个人情感,而是“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雅正平和的感情。“深于怨者”“长于情者”“善感慨者”“极放浪者”,虽然其诗歌也能达到工整优美的地步,但都不能得“情性之正”。宋濂的说法与郝经、虞集很接近。他主张诗歌中的感情要平和而不怨恨、淡泊而不激烈,这其实就是雅正平和之情,也就是《诗大序》的“发乎情,止乎礼义”之情。
宋濂认为《诗》三百篇正是雅正平和的典范,作诗欲得“性情之正”,必须以《诗》三百篇为宗。他在《林氏诗序》中说:“周之盛时,凡远国遐壤,穷闾陋巷之民,皆能为诗。其诗皆由祖仁义,可以为世法。岂若后世学者,资于口授指画之浅哉!先王道德之泽,礼乐之教,渐于心志而见于四体,发于言语而形于文章,不自知其臻于盛美耳。”[9]商、周之时,上自王公卿士,下至小夫编萌,都能够祖信仁义。仁义道德充于身心,发为诗文,“不自知其臻于盛美耳”。因此学习《诗》三百篇,可以得性情之正、道德之美,可以治身淑徒,所作诗歌也会精粹纯正。
可见,宋濂的“诗文本出于一原”论的实质就是主张诗歌要“载道宗经”,发挥经世致用功能,为文学事功论张本。除宋濂外,元明之际还有一些作家持相似观念。如刘基《苏平仲文集序》:“文与诗生于人心,体制虽殊,而其造意出辞,规矩绳墨,固无异也。唐虞三代之文,诚于中而形于言,不矫揉以工,不虚声而强聒也,故理明而气昌。玩其辞,想其人,盖莫非圣贤之徒,知德而闻道者也。”[10]上古诗文“理明而气昌”,能够使人“知德而闻道”,二者在内容及功能上有相通之处,其区别仅有外在体制上,而构思、用语及行文规范都相同。苏伯衡也认为文体之间并无绝对界限,“《易》有似《诗》者,《诗》有似《书》者,《书》有似《礼》者”[11]卷十六,诗文有相似之处,其区别只在语言上,“言之精者之谓文,诗又文之精者也”[11]卷五。明初,随着宋濂等人在文坛的崛起,他们的观念助长了文坛尚质主义文风的盛行,也使得元末以来刚刚复苏的文学审美化倾向遭到抑制。
二、师法汉魏盛唐
宋濂论诗反对师心自用,主张向古人学习。《诗》三百篇而下,他选择的师法对象仍然是能够得“性情之正”的风雅之音。他在《答章秀才论诗书》中历数古代诗歌的发展、演变及承继的轨迹时说:
《三百篇》勿论,姑以汉言之。苏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观二子之所著,纡曲悽惋,实宗《国风》与楚人之辞。二子既没,继者绝少。下逮建安、黄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刘公幹、王仲宣力从而辅翼之。正始之间,嵇、阮又叠作。诗道于是乎大盛。然皆师少卿而驰骋于《风》《雅》者也。自时厥后,正音衰微,至太康复中兴。陆士衡兄弟仿子建,潘安仁、张茂先、张景阳则学仲宣,左太冲、张季鹰则法公幹。独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虽出于太冲、景阳,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远韵,殆犹大羹充,不假监醯而至味自存者也……
开元、天宝中 ,杜子美复继出 ,上薄《风》《雅》,下该沈、宋,才夺苏、李,气吞曹、刘,掩谢、颜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真所谓集大成者,而诸作皆废矣。并时而作有李太白,宗《风》《骚》及建安七子,其格极高,其变化若神龙之不可羁。有王摩诘依仿渊明,虽运词清雅,而萎弱少风骨。有韦应物,祖袭灵运,能一寄秾鲜于简淡之中,渊明以来盖一人而已。他如岑参、高达夫、刘长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属,咸以兴寄相高,取法建安。至于大历之际 ,钱、郎远师沈、宋 ,而苗、崔、庐、耿、吉、李诸家 ,亦皆本伯玉而宗黄初,诗道于是为最盛……[12]
自汉魏至唐宋,每位诗人都有师承,历代诗歌因距离风雅精神之远近而各有盛衰。《三百篇》后为汉诗,苏、李之诗专宗《国风》及楚辞;建安、黄初、正始之间,诸人皆师少卿而上继风雅,诗道于此时大盛。太康之时,诸人或仿子建、或学王粲、或法刘桢、或出于左思、张协,都能够师法建安、正始而上继风雅精神,诗道于此时中兴。元嘉之后,风雅不传,正音难继,“诗之变极矣”。
直到初唐,张九龄、苏颋、张说以风雅为师,陈子昂专师汉魏、学习郭景纯、陶渊明,风雅精神开始复兴。开元、天宝年间,杜甫上继风雅并集诸体之大成;李白师法《风》《骚》及建安七子;王维依仿陶渊明,而陶渊明则是直超建安而上接风雅的诗人;岑参、高适、刘长卿、孟浩然、元结等人都师法建安。大历诸诗人本陈子昂、宗黄初,也是风雅之继。这两个时期风雅精神被诗人们发挥到极致,诗道也发展至全盛。风雅之丧、正音之衰,始自长庆以后。元稹、白居易、王籍、张建四人诗风虽然有轻俗、浮丽之弊,但仍能师法古乐府,除此以外,诸人诗作或气韵不足,或流于蹇涩,或涉于怪诡,或专夸靡蔓,“诗之变又极矣”。到了宋初,诗人承袭晚唐五代之弊,所作诗歌全乖古雅之风。天圣以后,王禹偁师法白居易、欧阳修,梅尧臣学习孟浩然,苏舜钦宗杜甫,诗道可谓中兴。自此以后,虽然诗人迭出,其间或有数人可观,但终究不能脱离“天圣、元祐之故步”,与盛唐诗歌相比差距更大。
这篇诗论集中反映了宋濂的诗学观,即以“风雅”为最高典范。而最能够代表风雅精神的诗歌,《诗》三百篇以后,当为汉、魏、盛唐诗歌。其中宋濂对盛唐诗评价最高,但并不像后来七子派那样唯盛唐是尊。他对初唐、大历、元和以及宋代的少数诗人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也是因为他重视诗歌的思想内容而以“风雅”为评价标准,不同于七子派重视艺术形式而以格调为准绳。他推崇汉魏盛唐诗歌的复古观念,从理论上开了明代诗学复古之先河。
三、作诗要五美俱备
宋濂主张诗歌创作在向古人学习的同时,也不排除作家才能、师友切磨、江山游历以及宵咏朝吟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他在《〈刘兵部诗集〉序》中说:
诗,缘情而托物者也,其亦易易乎?然非易也。非天赋超逸之才,不能有以称其器;才称矣,非加稽古之功审诸家之音节体制,不能有以究其施;功加矣,非良师友示之以轨度,约之以范围,不能有以择其精;师友良矣,非雕肝琢膂,宵咏朝吟,不能有以验其所至之浅深;吟咏侈矣,非得江山之助,则尘土之思,胶扰蔽固,不能有以发挥其性灵。五美云备,然后可以言诗矣。盖不得助于清晖者,其情沉而郁;业之不专者,其辞芜以厖;无所授受者,其制涩而乖;师心自高者,其识卑以陋;受质蹇钝者,其发滞而拘。古之人所以擅一世之名,虽格律有不同,声调有弗齐,未尝出于五者外也[13]。
作诗要触物而动、因情而发,固非易事。才质愚钝的人,思路必然迟缓而拘谨;师心自用的人,见识必然卑琐而浅陋;没有师承授受的人,诗歌体制必然生硬而乖违;不能专心致志的人,诗歌语言必定浅薄而杂乱;没有江山之助的人,诗歌感情必定沉郁苦闷。因此,诗人要想创作优秀的诗歌,必须具备超逸之才、稽古之功、师友授受、宵咏朝吟、江山之助。五美俱备,然后可以“擅一世之名”。
与论文的观点一致,宋濂认为诗人的气质、个性也会影响到诗歌的风格。所以作诗先要养气。他在《林伯恭诗集序》中说:
诗,情之声也。声因于气,皆随其人而著形焉。是故凝重之人,其诗典以则;俊逸之人,其诗藻而丽;躁易之人,其诗浮以靡;苛刻之人,其诗峭厉而不平;严庄温雅之人,其诗自然从容而超乎事物之表。如斯者,盖不能尽数之也。呜呼!风霆流形,而神化运行于上;河岳融峙,而物变滋殖于下。千态万状,沉冥发舒,皆一气贯通使然……世之学诗者众矣,不知气充言雄之旨,往往局于虫鱼草木之微,求工于一联只字间,真若苍蝇之声,出于蚯蚓之窍而已。诗云乎哉?[14]
诗人的气质、个性与诗歌的风格密切相关。凝重之人,其诗歌典雅严整;俊逸之人,其诗歌辞藻华美;躁易之人,其诗歌肤浅侈靡;苛刻之人,其诗歌峭厉奇险;温雅之人,其诗歌从容自然。所以作诗重在养气,气充则言雄。如果只求诗歌一字一句的工整,就犯了舍本逐末的错误。因此,宋濂对永嘉四灵进行了严厉批判,认为他们的诗歌“识趣凡近”“音调卑促”,最终会“误江南学子”。
总之,宋濂认为诗与文在内容及功能是一致的,都要承担起载道的功能。在风格上,诗歌要温柔敦厚,以得其“性情之正”为标准;反对师心自用,主张向古人学习,师法对象主要是汉魏盛唐诗歌;作诗要五美俱备,在此基础上,诗人还要善于养气,气充自然言雄而诗工。这些主张是他作为理学家的文学观念的集中体现。
[1]宋濂.题许先生古诗后[M]//罗月霞.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2086.
[2]宋濂.刘母贤行诗集序[M]//罗月霞.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1172.
[3]宋濂.故朱府君文昌墓铭[M]//罗月霞.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1333-1334.
[4]黄仁生.试论元末“古乐府运动”[J].文学评论,2002(6):148-159.
[5]刘将孙.养吾斋集:卷九[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杨维桢.东维子集:卷七[M].四部丛刊影印本.
[7]郝经.陵川集:卷十八[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十四[M].四部丛刊影印本.
[9]宋濂.林氏诗序[M]//罗月霞.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1729.
[10]刘基.诚意伯文集:卷七十五[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苏伯衡.苏平仲文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M]//罗月霞.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209-210.
[13]宋濂.刘兵部诗集序[M]//罗月霞.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608.
[14]宋濂.林伯恭诗集序[M]//罗月霞.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1008-1009.
A brief discussion of SONG Lian’s poetics
REN Yong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Culture,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SONGLian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education functions of poetry.He believed that poetry and the prose has the same effects,and poetry should express appropriate feelings.He advocated learning the ancients,especially Han Dynasty,Wei Dynasty and Tang Dynasty.
SONGLian;poetics;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oetry and the prose
I207
A
1671-9476(2011)01-0063-03
2010-11-01;
2010-11-26
任永安(1973-),男,河南开封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