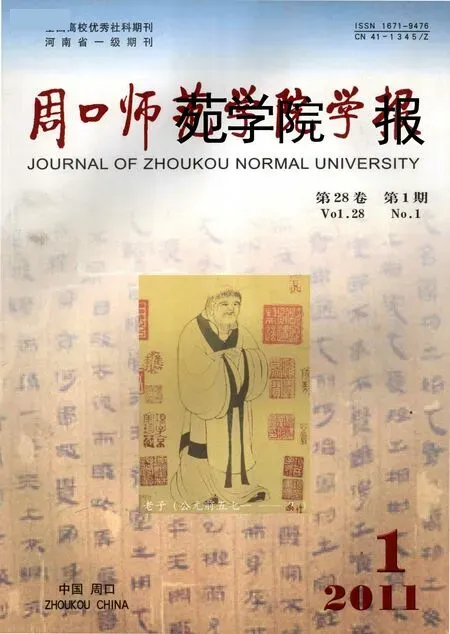周作人对20世纪中国散文创作的贡献
2011-02-20潘水萍
潘水萍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510632)
周作人对20世纪中国散文创作的贡献
潘水萍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510632)
周作人颇具现代性的散文创作是其文学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对20世纪现代中国散文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及理性启蒙。张扬“言志”派的个性文学创作倾向,强调文艺创作应持守“清醒的理性精神”来呈示人生之“现实感”,重申文艺创作应是“为人生”而非“为艺术”。对周作人于20世纪的散文创作中对现代中国文学的贡献作一深入的考论与透视,显得尤为必要。
周作人;新文学源流;散文创作
周作人对20世纪中国散文创作的贡献,值得当下人们以一种现代视野的眼光作出批判性的反思与再发现。1963年梁实秋为《西滢闲话》作序时,曾用“冷落冲淡”与“逸趣横生”八个字经典地概述了20世纪早期颇具影响力的散文作家周作人颇具大家风范的散文创作风格与基调内涵。“周作人先生的文字,冷落冲淡,而且博学多闻,往往逸趣横生。”[1]162梁实秋寥寥数言的点评,充分透析与揭晓周作人厚实的文学功底及丰富的人生体验阅历,从另一个侧面也映射出周作人洞彻人世沧桑的历史感的思想感情及创作文风。周作人曾指称:“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因为这有气质境地与年龄的关系,不可勉强,像我这样褊急的脾气的人,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作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2]238此段文字足可印证周作人一贯追求的“平和冲淡”的散文书写风格,这也是周作人对新文学小品文开拓性的独特构筑与个性书写的魅力。周作人以随笔式表述的散文创作文体可谓是独树一帜。一方面体现出其严谨的学术之风,另一方面又披露出他对生活体验之细微。只是迄今为止,学界却少有人对其“冷落冲淡”与“逸趣横生”的散文风格创作实践加以勾勒,也未曾对周作人对20世纪中国散文创作的贡献和当代启示进行实质性意义的解读、审视与梳理。这不能不说是目前学界对周作人文学思想研究的一大疏漏与盲点。毕竟,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是其文学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对20世纪现代中国散文的创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多元路径的启示指引。因此,对周作人于20世纪的散文创作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影响作一深入探究,显得尤为必要。
一、张扬“言志”派的个性文学创作倾向
就其整体作品创作向度的视点解读而言,周作人新文学散文之独特构筑与个性书写是以“言志”为内核路径,一方面因映现出一种担当时代使命感而极富真实而深邃的自省;另一方面因闪现着一股浓厚的民俗民间味和文人情调而显得澄明而深刻。20世纪20至30年代,周作人的“言志”美学旨趣与中国儒家传统道德理念内在结构的“载道”的文学思想观相似,主要是对“中国文学的变迁”和“文学革命运动”等新文学诸多问题作出的多维透视与批判性反思。一方面体现出其对古典传统文化之现代意义生成的弘扬与消弭,另一方面也颇受深厚的儒家思想与西方文化糅合性之研究范式的熏染。正是这一点,深深地影射出他对现代中国文学影响颇深的独特散文创作的新解及言说方式。他的散文创作因对中西古典传统文化的会通审视及反思而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和理想追寻,颇受现当代青年人的景仰。周作人的人生价值取向直接源于其文化心理的选择及姿态,他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小引》中直言不讳:“公安派的文学历史观念确是我所佩服的。”[3]47与前后七子那种载道之“假古董”文艺观相比,周作人对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清新流丽”之文学主张却情有独钟,甚至颇为赏识。因为他认为公安派的文学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加外来的佛教思想三者的混合物”[3]47。然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周作人也因此看到公安派过于“言志”所带来的流弊——文章趋向“空疏浮滑”“清楚而不深厚”。周作人的文学创作偏向于作为现代中国语境中散文创作一个重要问题,即“言志”与“载道”文学创作发展方向的个性书写的比较探微和透视。
事实上,五四前后的中国新文学在经受外来文学与传统文学理论框架构建的交汇、融合与选择中进行自觉的调适而获得新生,同时也在“自我”“他者”的话语价值观中渐趋形成一种开放的新视点的书写方式和言说力量。整体而言,周作人文学思想糅合了“载道”“言志”甚至中国禅宗佛学之“自性般若”思想高境。其实,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诗言志”“诗缘情”的文艺创作论的吸纳,足以印证其眼中的知识与思想智慧的光芒。关于其“言志”文学创作论的正当内涵及其现代意义,可以从他的系列散文和文学批评的文字深度阅读中审度出来。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单就他的散文创作实践进行多角度考察和比较思考,“言志”文学价值论是他对新文学重构与整合的一贯主张。周作人早年热心于民族革命的问题,这使得他日后渐趋接近一些民族、民间文学的“机缘”,他的散文创作可以说是这一特殊历史语境下的产物。不可否认,五四新思潮时期的外来文学对先秦儒家古典传统思想的内在冲击极大,同时对20世纪现代文学新视角创作发展的历史性趋势及其内在特征的整合也是极为鲜明的。周作人曾在《散文一集》序言中着眼提及:“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假如没有历史的基础,这成功不会这样容易,但假如没有外来思想的加入,即使成功了也没有新生命,不会站得住。”[3]320世纪的现代中国文学是在古典、现代与传统的边界中不断进行自觉的调适、回应中演变生成。周作人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充斥着一股强劲的生命力,即“言志”文学的现实性流变与新生。
周作人“言志”文学创作论选择的生成性思维结构所彰显的人文维度及其意义,主要昭示着他对新文学散文建构的根本性反思。他于《关于文学之诸问题》一文中强调人人都可以鉴赏文学。他偏重于性灵流露、理情互调且兼有“思想之美”切实注灌的文艺创作,同时认为唯有这样的创作抒写才能给人一种豁然开悟的新的“色味”。他在《现代散文导论》中启示性地诠释:“新文学的散文可以说是始于文学革命。”[4]78周作人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后勃兴的小品文散文正是“言志”派文学影响下独特的文学现象。“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文学却是不革命,能革命就不必需要文学及其他种种艺术或宗教,因为他已有了他的世界了。接着吻的嘴不要再唱歌,这理由正是一致。”[4]89他认为五四新思潮强烈要求反传统而力主“西化”,一方面主要是看到“载道派”作为正统文化迂腐、过于说教和封建保守性,另一方面五四新思潮值得肯定的一面就是激发了“独抒性灵”之“言志派”文学创作实践。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后勃兴的小品文、新诗创作正是得益于“言志派”呼声的复兴和“载道派”文学的暂时压制。“小品文则又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他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虽然在文学发达的程途上复兴与革命是同一样的进展。”[4]86-87
周作人对“载道”的文学创作维度始终操持着一种尖锐的现代性批判与考辨认知。毕竟,他偏好地认为文学负载的使命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我生活超越的“言志”情结。他在1933年2月20日撰写的《知堂文集·序》中自我剖白:“所说的话有的说得清朗,有的说得阴沉,有的邪曲,有的雅正,似乎很不一律,但是一样的是我所知道的实话,这是我可以保证的。”[5]细细读来,自然发现其散文书写继承了诗经、六朝和晚明文学的抒情传统之“言志”内蕴,往往让人读后于心灵深处获得愉悦审美体验的某种东西。他甚至指认:“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像一个水晶球,虽是晶莹好看,但仔细地看多时就觉得没有多少意思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他们的作品有时很难懂,而这难懂却是正是他们的好处。”[4]27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周作人的文学创作践行着“言志派”的性灵风格,同时他亦看到了在新文学思潮的引发“言志派”文学给催生了文坛新的文学创作实践。“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他们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其价值在竟陵派之上。”[4]88周作人认为文学只有感情没有目的。其散文创作与其说嗜好引经据典分而论之,倒不妨说其力主平和、冲淡兼而有之的风格。他对文学的理解颇为洗练,认为文学有“美妙的形式”,传达出来的是“作者独特的思想和感情”。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周作人注重内在情趣的安闲散文风格展现出不屑华美而独创新格。其圆润透彻的文字于述析人生的深处往往涵丰饶于淡味、蕴真实于简朴。可以说,周作人的散文全面地代表着五四新文学时期的高峰,也许这是他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之优良传统精华的成果。最为可贵的是,周作人有力地区别他所推崇公安派的是其“文学上的主义或态度”,这有别于平常人所强调的“文体”的问题。周作人内容丰富的散文作品表现为题材之迥异和构思之精巧,其思路清晰且写意较新的散文创作,另一方面因其在现代物质文明冲击下的失落感到惆怅,而这略带忧郁的特殊情怀为其生活化散文表写的方式增添了别样神采。
二、文艺创作应持守“清醒的理性精神”来呈示人生之“现实感”
总体而言,要考察对周作人现代性的“言志”文学创作深层意蕴的进路,首先要认识到周作人的文学思想是一种相对的“中道”观主导范式,即儒家古典主义的中庸哲学思想立场。这也是周作人思考、探析和批判现代性视野下的文学思想理论问题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和出发点。周作人强调文学创作应表现出与人内在精神相暗合的“清醒的理性精神”与“现实感”。这是当代散文创作生命力与未来出路值得综观探疑的问题,然却也是当下文艺创作者经常低视或疏忽的一个重要现象之维。事实上,任何经典的文学书写都是一种心理情感抒发的表现。“作为人对现实的对象和现象是否适合人的需要和社会需求而产生的体验,情感和其他心理过程一样,是人在实践中产生的。”[6]倘若要挖掘与探析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所呈示的人生“现实感”,就要深入到其具体的文本进行深层的解读。周作人在《初恋》一文中提起自己的初恋:“此刻回想起来,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但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的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了。我在那时候当然是‘丑小鸭’,自己也是知道的,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并不问她是否爱我,或者也还不知道自己是爱着她,总之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这是当时实在的心情,也是她所给我的赐物了。在她是怎样不能知道,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始终没有想到男女关系的问题。”[7]毋庸置疑,淡然而平实的文字品阅起来自然有一种朗朗贴心的美学体验。阅读周作人看似自有一种雅致出色、兴味浸润和空灵真实的散文,然却总给人一种难以弹除的平常心的隐味。因为其力透纸背的文字充满着平淡如水、自然如风的语言色彩。这大概与他素来经受、体悟的生命涩味和简单味有关。周作人《雨的感想》:“秋季长雨的时候,睡在一间小楼上或是书房内,整夜的听雨声不绝,固然是一种喧嚣,却也可以说是一种肃寂,或者感觉好玩也无不可,总之不会得使人忧虑的。”[8]颇为值得称道的是,周作人的散文以一种人生真实的再现笔调和最富“自我个性”的文人习气文风,描摹现代视域中所感所想所念所闻的一切。
需要注意的是,周作人散文创作主要是一些叙事或抒情性小品文,杂诗、杂信、杂感为多,其文艺创作思想观的文化意义散见于其系列的杂文、散文、序跋等文字中。周作人曾指认:“我的确写了些闲适文章,但同时也写正经文章,而这正经文章里面更多地含有我的思想和意见,在自己更觉得有意义。……我写闲适文章,确是吃茶喝酒似的,正经文章则仿佛是馒头或大米饭。”[9]3其散文貌似简朴甚至单调的文段,不仅深蕴着相当明晰的文学思想意识,同时也包孕着真切诚挚的人情味和不经意间流溢出的其内心深处淡淡的诗意。张菊香在《周作人散文选集·序言》指出:“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这与他的散文在艺术上的杰出成就分不开的。周作人散文艺术的主要成就,就是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成熟的散文艺术的风格——平和冲淡的风格。……周作人散文平和冲淡的艺术风格表现为:飘逸洒脱的文章笔势、平和恬淡的抒情特色、庄谐杂出的幽默趣味、舒徐自在的语言表达。……他的散文在用笔上从容不迫、流转自如,似名士清淡、娓娓道来,无所拘羁。”[10]8-9
周作人以冷静而理性的态度深度解析了现代文艺创作的现实出路,同时也从深层的学术视角重新梳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言志”与“载道”的新文学源流理论内涵的向度。梁实秋于1933年发表在《益世报·文学周刊》第57期《评〈周作人书信〉》一文溯源性地指出:“中国现下的文坛,可以说是战云密布,可以说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周作人先生则一向是保持他的冷静,众醉独醒,从没有一面失态的时候。”[11]在梁实秋眼中,周作人隐士之低调,文笔之明畅、隽永和轻灵,正是其“朴而不陋”甚至“华而不俗”的常态人性之描写。梁实秋对周作人的冷静、独醒的人性所体现的独特的价值给予了充分的历史界定。然而,他也警醒到周作人散文中所透露出来其人性之“冷傲”的一面。“鲁迅兄弟被寄养于亲戚家饱受白眼,因而养成鲁迅之偏激负气与周作人之冷漠孤傲的脾气。”[12]众所周知,人的心绪情怀总是不可回避地受制于其生活的特定年代的历史语境。周作人同样是一个受制于其生活历史时代的人物。“周作人在20世纪30年代不是没有文学思想,而是没有无产阶级的文学思想;不是对文学无知,而是对无产阶级的文学持一种不承认的态度,对无产阶级的文学不知。他代表的是一种非革命、非左翼的文学潮流,个人主义是其核心。”[13]
周作人一方面有极好的传统旧学知识结构功底,另一方面深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对于自身的写作风格,周作人曾委婉提及:“我们所希望的,便是摆脱了一切束缚,任情地歌唱,无论人家文章怎样的庄严,思想怎样的乐观,怎样的讲爱国报恩,但是我要做风流轻妙,或讽刺谴责的文字,也是我的自由,而且无论说的是隐逸或是反抗,只要是遗传环境所融合而成的我的真的心搏,只要不是成见的执着主张派别等意见而有意造成的,也便都有发表的权利与价值。这样的作品,自然的具有他应具的特性,便是国民性,地方性与个性,也即是他的生命。”[10]80从这段文字中可以迹出周作人对“自由”“个性”的人生价值追求。对于散文独特的品味,周作人在《谈文》中颇为自豪地摘引叶松石《煮药漫抄》的经典总概:“少年爱绮丽,壮年爱豪放,中年爱简练,老年爱淡远。学随年进,要不可以无真趣,则诗自可观。”[9]71说到底,周作人之苦雨斋那种现实生活之涩味正是一种中老年之简练、淡远之味的写照,无不透析着其以文艺创作之人生表现之浓烈的郁结心绪。简而言之,周作人散文蕴藉着一种独特的人文俗世情怀和平常心的人生态度,同时也紧紧笼罩着一股深沉而黯然的命运意识。
三、文艺创作应是“为人生”而非“为艺术”
周作人认为文艺创作的目的是“为人生”而非“为艺术”的理论内涵。在《自己的园地》强调一切文学创作的旨意在于“为人生”。他曾不失判决性地重释:“‘为艺术’派以个人为艺术的工匠,‘为人生’派以艺术为人生的仆役;现在却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艺术,即为其生活之一部,初不为福利他人而作,而他人接触这艺术,得到一种共鸣与感兴,使其精神生活充实而丰富,又即以为实生活的基本;这是人生的艺术的要点,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2]47由此足见周作人批判“为艺术”而创作的文学观。因为他认为既是独立的又是人性的文艺本来就是感情生活的表现,而“为人生”对人生有实利。实际上,针对周作人倾向于以一种古典主义“中庸”的文学思想观弘扬“言志”派性灵的文学创作主张,刘半农却持守着独特而严谨的看法。一方面他认为文学最重要的是“求辞达意适而止”,反对文学过于追求“性灵”“意识”或“饰美之意”;另一方面他反对文学过于讲求音韵、平仄。“然欲判定一物之美丑,当求诸骨底,不当求诸皮相。譬如美人,必具有天然可以动人之处,始可当一美字而无愧。若丑妇浓妆,横施脂粉,适成其为怪物。故研究文学而不从性灵中意识中讲求好处。徒欲于字句上声韵上卖力,直如劣等优伶,自己无真实本事,乃以花腔滑调博人叫好。此等人尚未足以言文学也。”[14]周作人强调现代文艺创作理应扬“古”开“新”。从周作人散文创作思想的溯源看,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尚“古”纳“新”的学者。“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淹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4]88
周作人的文笔书写追求一种简洁、隽雅、朴拙、恬淡而言之有物的文调意蕴,往往在一味再嚼之间自然感怀其“微言大义”之涵蕴深刻和豁然开朗的欣快。他认为文学是“人性”的披露与揭晓及对人身心本质的表达与境况显现。而文艺创作应该竭力避免“超出情理之外”的意气用事,而应用比较冷静的态度加以批评节制。周作人强调文学是人们心理苦闷积郁的表征与范式,它起源于一种内心情绪宣泄。文学正是人心世道的一种“言志”的写照与辐射,然而文字之“达意”、之“言志”又是有限的,文字往往未能尽表内在心绪情感。“文学,仿佛只有在社会上失败的弱者才需要,在际遇好,没有不满足的人们,他们任何时任何事既都能随心所欲,文学自然没有必要。”[3]16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是一种贴近平民生活之真实审视与再现。20世纪30年代他也曾一度醉心并沉湎于古典传统文化知识的精神熏染。他强调赏鉴文学作品最为关键的是要“有机缘”和“有兴趣”。周作人认为文学是一种普遍的人生审美的书写,把人生的一切似乎都看做若远若近的“浮云”,因此其文字也于无形中深深地弥漫了一层“惨淡”“孤寂”意绪。“我平常很怀疑,心里的情是否可以用言全表了出来,更不相信随随便便地就表得出来。……死生之悲哀,爱恋之喜悦,人生最切的悲欢甘苦,绝对地不能以言语形容,更无论文字。”[4]96从某种意义上说,周作人认为散文多是透析出其内心之孤独、自省、忧郁、消潜、悲情和沉浮的人生映象。周作人历来强调文学注重的是“认识人生”“真实生活”“心灵世界”“心性情感”“理性启蒙”等方面的内倾化诉说、审视与捕捉。他认为文学类似于宗教之“不可知”的学问。此外,也凝聚着他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文学思想建构提出诸多的独具新见的多维阐发。周作人散文于舒缓而自然的字句节奏中透示着一股命运深处的审美淡然之气,即是一种绚烂之极必趋归于平淡之内在生命的感怀。此外,其文字于苦雨惆怅或苦茶清冽之间,自然溢出一股丰腴且幽雅的人生致味。也许这正是其散文耐读耐味之处。
事实上,周作人的散文创作经历了由文言、文白兼杂渐已白话的过程,深深地浸染着中国古典文学的内在精神。“在周作人的散文生涯中,他写下了大量针砭时弊、批判封建文化、蕴含人生之情怀和个人趣味、性灵的散文佳作,具有冲淡、平和、舒展自如、自然幽默、风趣,同时又浮躁凌厉的特色,对‘五四’以来的散文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15]他的散文尽管够不上清隽逸秀,也够不上疏腴雅致,然读来尤为浅近、平实、直白、散漫、低调甚至寡淡、苦恼的审美体验,常常于隐然间给人们一种淡如和风而又余蕴徐徐、其味无穷的嚼味。显然,读周作人的散文,可以读到一种质朴、一种平常心、一种寡淡甚至一种深邃的高境人生。这正是其散文创作的独特生命力和认知的旨意所在。仔细分析与鉴照则可知,其文字深处蕴涵诸多的文学理论,一方面是针对现代中国文学潜在的某些误解、偏离甚至错误之隐然迹出或暗示,强而有力地折射出他对现代文学颇多“缺损”与“偏误”之纠偏或匡正;另一方面则折射出其深蕴的真挚性情。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后,周作人之新人文主义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儿童文学建构的独特重视、对“言志”与“载道”新文学源流的比照与反思、对“冷落冲淡”与“逸趣横生”的散文创作实践。张丽华在《周作人的杂学与文章》曾这样概述:“文化多元与‘思想宜杂’的主张,构成了周作人之杂学的思想支撑,与此同时,他对‘杂’的诉求,也是一种趣味化的个人选择。”[16]总而言之,其低调、简约的生命理念糅合而成的小品文风格的散文创作实践,标举了20世纪现代中国早期新文学创作实践的一代风气。周作人的散文书写是他对自身经历体验的一种审美心理的有感而发,正如其散文开阔的视野和敏锐纤细的文调,总给予人们一种曲尽其妙之美学感受。
[1]梁实秋.雅舍谈书[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
[2]周作人.周作人散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3]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M].止庵,校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4]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
[5]周作人.看云随笔[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197.
[6]张光芒.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35.
[7]周作人.流年感忆[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19-20.
[8]周作人.怀旧[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32.
[9]周作人.苦雨斋谈[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
[10]周作人.周作人散文选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11]周作人.生活的况味[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118.
[12]梁实秋.梁实秋杂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276.
[13]刘锋杰.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88.
[14]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M]//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学改革小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国革命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五四-1942):第1卷: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32.
[15]王景科,李掖平,贾振勇.中国现代文学专题研究十六讲[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254.
[16]周作人.我的杂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5.
I206
A < class="emphasis_bold">文章编号:1
1671-9476(2011)01-0059-04
2010-12-05
潘水萍(1979-),女,广东化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和中国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