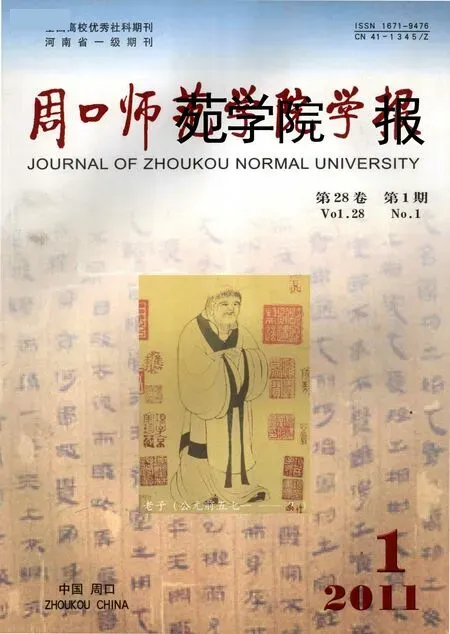另一种苦难的渊薮
——论刘庆邦小说中的“家族微观权力”
2011-02-20石长平
石长平
(许昌学院文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另一种苦难的渊薮
——论刘庆邦小说中的“家族微观权力”
石长平
(许昌学院文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在刘庆邦的众多乡村小说中,特殊的时代政治和社会历史背景构成了叙事不可或缺的要素,成为苦难叙事的重要泉源。但在他的不少文本中,“家族微观权力”也是形成其苦难叙事不容忽视的另一种缘由。由传统家族文化而形成的权势力量即家族微观权力,以其特有的消极、破坏作用产生新的苦难,成为底层小人物的另一种苦难渊薮。这类文本叙写对于我们从文学维度观照乡村社会生态,了解当下“风险社会”中潜存于底层的社会危机,提供了清晰的艺术视角。
刘庆邦;乡村小说;“家族微观权力”;苦难渊薮
刘庆邦的乡村小说以众多的苦难叙事显示了其独具魅力的艺术价值和美学品格。在这些苦难叙写中,特殊的时代政治和社会历史背景成为重要的泉源,它们不仅显现为特定的叙事情景,更构成了叙事要素,在叙事中这两者都是产生苦难的主要缘由。但我们注意到,“家族微观权力”因素也是形成刘庆邦苦难叙事不可忽视的另一种渊源,在某些作品中还作为极其重要的因素凸显出来。
一
“微观权力论”是福柯用“微观物理学”方式来思考权力的术语,通过考察微观层面渗透着权力效应与社会微观力元(个体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而解释这一机制对人的压抑的动力学理论。他认为,“不应该从合法性的角度来看待权利,而应该从它促成的压制方式来把握它”[1]。从相对主义的理论立场出发,福柯以一种微观的视角分析权力,强调权力是关系、是网络、是场,强调权力的分散性和多元性。家族“微观权力”与福柯的原义并不完全相同,但这种权力在机体组织上的微小、实施者身份的卑微以及社会等阶的底层性、运作机制的隐匿性和生产性等方面,有着与福柯的“微观权力”相似和相同的特性。家族权力正是以这样的“微观”特性表现着自身的存在,影响着微型的乡村聚落和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生存状况,真切地体现出了“权力在我们的身体中”的客观现实[2]。
家族观念在中国源远流长,家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一般而论,家族是按男系血缘关系的原则,以家庭为单位组合而成的群体。在传统社会中,农民安土重迁,长期在一地生活,以己为中心构成了一个家庭、家族甚至村庄。这使得宗族或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构成了农民家庭以上的另一个基本认同单位。聚族而居的村庄,构成中国传统农民生产、生活的场所,构成了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秩序。在某一固定地域或聚落内居住的同一姓氏世代相传,以其特殊的族群荣誉、物质利益和精神追求,产生了家族集体主义认同,血缘族群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由此而下形成了一种权势力量即家族权力,这一力量在很多情况下又与政权结合起来,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民的生存环境。乡村聚落的构成一般有三种形式,即单一型村落、姻亲型村落和杂姓型村落。中国历史上,由于朝代的变迁和战争的频繁,人口的不断流动使得杂姓型村落占绝大部分,在这些村落中,大的宗姓所具有的家族权力对于同宗人而言,可以让族人体验到关爱与帮助,减轻生活的压力,稳定农村基层政权巩固,而对其他小宗姓来说,则会产生排拒、压制等离散作用,显露出宗氏家族权力的消极或破坏作用,在苦难之外产生新的苦难,成为另一种苦难的渊薮。
刘庆邦的乡村小说中,家族这一微观权力被不断书写,在真实地展现乡村文化景观时,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因素影响着作品的整体结构和精神面貌。以第一人称为叙事者的作品中,这一因素在苦难日子里呈现了浓郁的人情温暖,尽管本族人里面也有这样那样的争斗,但关怀帮助却是主旋律。《远方诗意》中,“我”要到远方串联,一起走的几个孩子都是清一色同姓人,即便是年龄最小的人——云也是由于同祖同姓,“我”才无法拒绝他;毕业之后“我”无学可上,终于回到了黄土地上劳作。由于本家的堂叔是生产队长,“我”受到了很多特殊待遇,干活时让我干诸如浇灌田地时看水等轻活儿。《拉网》中生产队年终逮鱼,参加的家庭有份,没有人参加的家庭没有分鱼的资格。因为“我”父亲去世,母亲又不能参加这种劳动,所以生产队长堂叔一直等到“我”放了假才带领社员们去捕鱼,在捕鱼的时候,堂叔也格外照顾我,没有让“我”下到寒冷的水里撵鱼,而在分鱼的时候还给“我”家最好的部分。《平原上的歌谣》中的堂叔在工分上对“我”家的照顾等都显示了宗族亲情的温馨,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二
但显而易见,这种对关爱与帮助的叙写仅仅在其自传体色彩明显的作品中有些微表现,更多的却是家族微观权力作为“恶之花”绽放在苦难的岁月里。我们可以把这种表现分为两种:一种是一般构成性因素,一种是特殊支配性因素。一般构成性因素在文本里或者用以渲染苦难氛围、增添苦难色彩,或者作为一种现实生活的逻辑力量解释本事产生的缘由,以一种次要元素推动情节转进和发展。这在《黄金散尽》和《刷牙》等文本中得以体现[3]。
《黄金散尽》通过一个哑巴的人生苦难经历,展现了一个外姓人、残疾人的悲剧命运。哑巴的苦难是多重的,除了遭受语言的侮辱外,在劳动中生产队的刘姓干部故意把最重的活儿派给他,以致于脊骨被压骨裂了。这不仅因为他是哑巴,还有一重要原因是宗姓原因,村里人都姓刘,只有他一家姓成。虽然已经在这里住了两辈,但“村子里仍没有他们家插足的地方”。不仅哑巴被欺负,哑巴的亲人同样被欺负。哑巴的妹妹要出嫁给外村人了,但刘姓人还有不少光棍没有娶媳妇,于是刘姓人一商量,就在出嫁的途中抢了婚。尽管哑巴拼命反抗,但最后面对生米做成熟饭,只有无奈地默认冷酷的现实。哑巴的苦难在他家人的整体苦难中表现出来。在政治气氛浓厚的年代,他家的雇农成分并没有使他成为刘庄人的阶级弟兄,微末的家族权力是书写他苦难生活的巨笔,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宗族关系却依然以隐匿的方式照常运行着。这在《刷牙》中也有类似的反映。《刷牙》描写了给牲口刷牙的怪异故事,在令人哭笑不得的喜剧幕影下表现了悲剧内涵,记录了“大跃进”时代的荒谬给底层百姓造成的苦难。在刘岗村,村干部都姓刘,只有梁红彦是外来户,刘姓的人就合伙欺负他,有什么不好的事都是往他头上安,所以上级布置的给牲口刷牙的任务就落到了他头上。雇农成分的他认为应该让地富分子去做,但政治身份并不能成为他不遭受欺凌的原因,只要地富分子姓刘,就是自己人,他就是外人,家族血缘关系大于政治血统关系。当生产队刘姓干部们一致决定让外来户梁红彦干这件荒唐和极具危险性的事时,他们不约而同“开心地笑了”,在笑的背后,正是维护同宗排斥外姓的共同家族文化心理在他们意识深处的契合。以队长刘达本为代表的家族微观权力机制,把压在他身上的政治权力再生产和再演变成为家族权力,在转移和释放权力能量的同时获得了畸形的快感。
《双炮》中,范大炮娶了媳妇林翠环,这对于他这个外姓人在林家楼站稳脚“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因为在林家楼,林姓占了十成中的八成以上。日常生活中,“姓林的动不动就骂到姓范的家门口了”。即使在结婚以后,大炮也常受到媳妇林翠环的欺负,为家庭琐事骂了媳妇一句,翠环就说:好你个姓范的,在我们家门口,你敢骂我!大宗族的强势意识相当强烈。正是在她的逼迫下,大炮才做了不愿做的事,导致家庭悲剧的发生,翠环所依仗的正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微小的家族权力[4]。在这里,这一因素起着情节转进的推力作用。除此之外,渲染苦难氛围、增添苦难色彩等作用还细节性地表现在《五分钱》《平原上的歌谣》等文本中。
特殊支配因素是指在作品内部诸因素关系具有重要作用、使作品获得审美功能的一类因素,由于作品结构中不是各种因素在平等基础上的合作,而是像雅各布森所认为的存在一种支配因素,它制约、决定并改变着其他成分,作品依靠这一因素进入文学并取得文学性。刘庆邦的一些小说中,家族权力成为特殊支配因素,它不仅是使得文学事件得以发生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而且在叙述程序中处于决定性的地位,制约和规整着其他因素在叙事中的综合传达,最终使文本保持着结构的完整性并有效地完成作者对苦难主题的表达。这主要体现在《只好搞树》和《遍地月光》里。
《只好搞树》的主人公杨公才是外来户,大赵庄的赵家人经常欺负他,出于对赵姓家族权力的畏惧,他心中沉淀了深厚的委屈痛苦却不敢公然报复,而是暗暗地把报复对象转移到赵家的女性身上,并在黑夜里把赵长泰家的几千棵桐树苗子全部锯倒。由于赵家本姓人赵康和赵进曾经对赵长泰把桐树苗子种在他们农田旁边有过意见,认为桐树苗子歇了自家的地,把他们的地劲吸走了,影响了庄稼收成,但处于强势的赵长泰根本就不理会,他们两个就是直接的嫌疑人,尤其赵康还是一个木匠,有作案的锯子,于是跟赵长泰有关系的派出所长就派人把他们给逮去了,并且又把另外三个被怀疑的人也逮走了。赵家村的人终于恐慌了,不再像以前那么团结了,杨公才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杨家作为外姓,长期遭受欺辱,“在姓赵的大人小孩面前,他们家的人只能装三孙子”。解放前父辈受赵姓地主欺负,解放后他本人受姓赵的贫下中农欺负,改革开放了儿子还受欺负,总之,大赵庄的人排挤他家“好像形成了传统”。杨公才的人性扭曲而导致的悲剧,正是在家族权力一代接一代的欺凌压抑下发生的[5]。搞女人和锯树苗是整个文本所要讲述的故事,它的动力源是由苦闷屈辱而生成的仇恨,而仇恨来自一个大家族对一个小家族的世代排斥和压迫。家族力量在这里明显成为一种特殊的支配性因素,制约着情节的发生发展,在主题生成上较为明确地传达了作者揭示乡村宗法家族权力的危害性,表达出对苦难者的同情和对乡村传统文化痼疾的批判意识。
《遍地月光》是刘庆邦新近的一部长篇力作[6]。生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主人公黄金种是地主的后代,在劳动和日常生活中他时时受到杜老庄杜姓人的欺负侮辱,其人格尊严被随意践踏,做人的基本本能被压制,连恋爱的权利也被一次次剥夺。黄金种看上同是地主家庭的闺女赵自华,结果赵自华为给弟弟换亲被人换走了。大姐给他介绍了一个外村的傻闺女,因为他的地主成分,傻闺女在公社当干部的叔叔不同意。后来他又追求一个出身更为复杂的同村姑娘王全灵,由于政治队长杜建春想把这个姑娘说给自己的丑陋的外甥,因此黄金种受到陷害和批斗。在精神和肉体遭受双重的打击后,他的生存状况愈加窘迫严酷,他不得不两次出逃,但两次都被抓回,第三次才逃跑成功。纵观整个文本,黄金种的人生苦难史不是简单的血统论所能够铺设的,乡村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家族血缘论造成了他的人生悲剧;将他一步一步逼上绝路的,也不仅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气候和无产阶级专政权力,更是那个特殊的地域里特殊的家族势力。文本中这两种权力对于情节的推进和悲剧的演绎都具有重要作用,村里大大小小的干部都姓杜,阶级斗争的开展和政治权力的实现必需借助于家族权力,而在那个特殊年代,家族权力也必须穿上政治的外衣才可以合法运行,杜姓拥有和实施着政权和族权的双重权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两者是合二为一的,家族权力在文本结构中居于特殊的支配地位。
杜老庄的地主中,黄金种的父母被迫害、逼迫致死,赵大婶的丈夫被斗争致死,只有杜姓地主完好无损,杜建勋也是地主,“但一笔写不出两个杜”,所以就平安无大事。青年黄金种既是地主儿子又属外姓,既有政治身份的卑微,更有家族血缘的低贱。设若他叫杜金种,其命运就不会是这个样子,压迫、伤害、凌辱以及恋爱权的剥夺就可能不会发生,其惊悚人心的悲剧历程就无法完成,作者的主题传达也无法完满地实现。在文本中,雇农出身的王长轩受到的欺辱也不算少。在日常生活中,他遭人唾弃不仅是他下作的品行,也与其外姓人的身份有关。他的儿子和他本人都遭到杜姓人毒打,在婚嫁问题上,女儿王全灵的不自由选择等都确实地明证了家族权力对外族的排斥和伤害。在偏远的杜老庄,微小的家族权力被放大后生产出的巨大能量,深及灵魂、贯彻终生,成为苦难的渊薮。“文革”结束以后的80年代,流落外地的黄金种凭着辛苦劳动成了万元户,摘掉地主帽子也成为平等公民,其政治身份和经济能力得到保障后,他回到了阔别十多年的老家,但他一回到杜老庄,就受到了杜姓人的讹骗,连祖坟也被平掉了。扒坟的杜建忠的话语很能说明问题:杜老庄姓杜,不姓黄。得罪了我们姓杜的,我让你回得了杜老庄,出不了杜老庄。不管你怎样,杜老庄的天都在你头上罩着呢!显然,杜老庄的“天”就是杜姓的家族势力,只要你进入这个地域,就走进了这个家族权力场,其魔力就会发作,新的苦难就会纠缠上你。农民的行动逻辑,是受其文化所制约的。平掉祖坟具有一定的隐喻作用,它传达出杜老庄人要从这个地域内彻底排拒和清除外姓人的深刻的文化心理。这一叙事放在结尾,是作为支配性因素在整体结构发展中的逻辑必然,它再次明白地揭示了家族权力对人的挤压是超越政治身份和经济能力的。作为一种生长在某一特定地域内的个体所终身无法逃避的苦难渊源,极大地强化了文本的悲剧意蕴,加深了读者对痛苦意识的感受。
三
阿多诺认为,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的社会劳动产品,始终是一种社会事实。刘庆邦一直恪守“贴着人物写,贴着底层写”的现实主义原则,使得他的“创作是及物的,每一个细节都真实可信,充盈着饱满的情感”[7]。他在作品中所描写的家族权力正是对乡村现实生活的真切反映。在刘庆邦的作品中,从民国到“文革”前后再到当下,家族微观权力的运行在乡村一直没有消匿。土地改革、人民公社、改革开放等社会运动或制度变革并没有使其得到有效的削弱和遏制,它们冲垮的只是族谱、家祠、族田等外在表征和组织结构,人们基于血缘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和基于精神归依而编织起来的家族认同感与恃强心理并没有在社会变革中被完全损毁,家族微观权力在与不同时期的不同的政治权势的结合中,只是变换着不同的面具,其深刻而厚重的文化内涵并没有根本的变化,它在当前现代化进程中依然普遍存现着。从文本所展示的情况来看,其产生的消极作用也有增强的趋势。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家族文化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方面它衍生出一些新的文化特质如忠、孝等思想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其政治补充、经济互助以及文化归属等功能的发挥对乡村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带来的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更多的是,其“具有较强的狭隘性和排他性,家族文化不可避免地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诸多负面的影响”。家族权力作为家族文化的一种外现形式,其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8]。同家族为社会带来的正效应相比,其负效应更为突出和严重。当下家族势力干扰乡村选举、家族组织功能对基层合法组织的权力运行的干预等时有发生,很大程度上危及了农村组织建设,破坏了法制管理,戕害了民主自治,由此引发的矛盾加剧了农村的社会秩序动荡,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剧烈转型,我国仍处在一个新的社会不稳定时期,而乡村中普遍存在的家族微观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构成和加剧了社会风险。有学者指出,目前,“‘三农’问题还没有找到合理有效出路;弱势群体不断扩大以及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给民众带来的不满情绪等,源于经济扩张和社会转型的共同作用,总体上我们的社会张力还处于不断扩大之中,一遇某些事件的诱导,这些因素极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9]。对于有着9亿农民的国情现状,建设稳定的乡村社会秩序,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意义重大,而且从一定意义上看,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农民作为现代化的主体无论在思想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上都因袭着太多传统文化的重负,因此,反思批判乡村文化和农民思想观念中的消极因素是改造和促进农村现代化,进而构建稳定和谐社会的基础与前提。“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村落文化持何种态度,对村落家族文化的变化,如何应变。”[10]应变首先就应考虑如何改变,而文学对此不应当袖手旁观。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文学积极地参与到包括乡村在内的文化建设中,自当成为每一个有忧患意识的作家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鲁迅曾讲过: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刘庆邦在乡村苦难叙事中,一直着力于重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在他的文本中以其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敏锐的批判精神,向人们展示了详实而震撼人心的“第二现实”,这对于从文学维度观照乡村社会生态,了解当下我们所处的“风险社会”中潜存于底层的社会危机,提供了清晰的视角和真实的景况,为确切反思家族文化在现代化农村建设过程中的消极影响,也为有效引导家族势力对乡村治理起到积极作用,找寻着思想方法和改造理念,这也许正是刘庆邦此类小说的社会学意义了。
[1]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30.
[2]汪民安.福柯的面孔[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132.
[3]刘庆邦.河南故事[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
[4]刘庆邦.红围巾[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
[5]刘庆邦.到城里去[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
[6]刘庆邦.遍地月光[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7]刘庆邦.“喊”出地层深处的甘苦[N].文艺报,2008-10-07(2).
[8]疏仁华.村庄行为与农村家族文化的演进[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6):137-140.
[9]李宝梁.风险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危机与治理[J].理论与现代化,2009(2):13-18.
[10]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的一项探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06.
I206.7
A
1671-9476(2011)01-0055-04
2010-11-20
石长平(1968-),男,河南南阳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美学和文学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