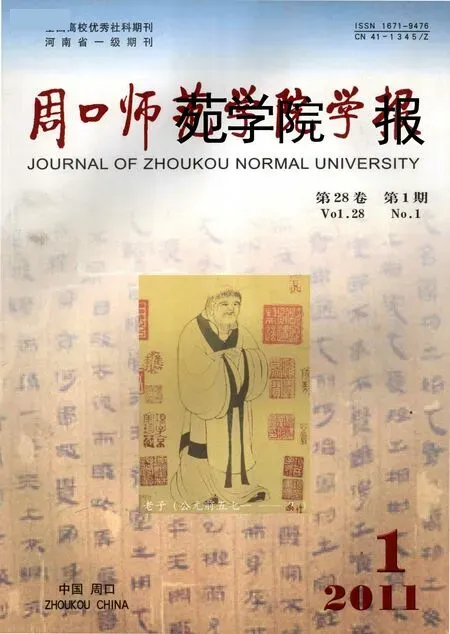庄子“游心于道”的审美实践方式
——作为“否定”和“化解”的心灵境界
2011-02-20张静
张 静
(郑州轻工业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河南郑州450002)
庄子“游心于道”的审美实践方式
——作为“否定”和“化解”的心灵境界
张 静
(郑州轻工业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河南郑州450002)
庄子选择的审美实践方式是“游”,“游心于道”意味着否定和化解。一方面否定智识和道德,另一方面用自然而然的至理化解俗情,这两者是统一的。由此可以引出审美心理的特征乃是超功利与非逻辑。“游刃有余”是游的心灵境界在现实层面的落实,它启发了艺术创作由必然到自由的过程。
审美实践;游道;心灵境界
庄子选择的审美实践方式是“游”。庄子开篇以翱翔于九万里高空的大鹏象征了“莫之夭阏”的自由境界,然而从“培风”的角度看大鹏之游依然是有所凭借的,真正的逍遥游是无待之游。如果说有待之游是待物而游,那么无待之游就是待道而游,即心游。无待是对有待状态的否定,这种否定的具体方法就是“无”,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就是对私我的彻底放弃。“坐忘”正是从否定的层面上进一步阐发了被否定的私我的具体内容:首先是对各种生理感官欲念和功名利禄之心的罢黜;其次是对知识判断和成见的克服,从而产生一个虚以待物的开放的“自我”,诞生一片灵虚不昧的审美心境,映照全类,引发万有,对人生世相作审美的自由关照。“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说明了审美心理的主要特征是超功利与非逻辑的理性直观,前者可以以西方的“距离”说加以阐释,后者可用移情理论加以阐释,但应注意中西思想的边界。“游”的双重主旨揭示了庄子思想中心灵自由与形体宿命的矛盾。对于这种矛盾最好的化解方式是技术艺术化、生活审美化,这两个层面在庄子之游中不可剥离,前者是后者的一种提示:游心于道的心灵自由感可以通过创造性的转化落实到现实人生中。技术艺术化的最好的注脚是庖丁“游刃有余”时所达到的技与道、感官与神遇、人工与天理的完美统一,这种统一说明了由必然到自由的可能性所在。同时,由必然到自由的创造过程显现了人与世界遇合的三个层次,由“人心之法天”到“人定之胜天”再到“人心之通天”,这三个层次分别所代表的艺术类型也有高下之分。由于对技术进行了道的规定,庄子的自由不再停留于纯粹精神超脱的领域,而是在现实的层面也有所成就,这种成就既是属于艺术的,也是属于人生的。
一、“游”的基本内涵
《广雅·释诂三》对“游”的解释是:“游,戏也”,“游”作为游戏是一种不固定、不受约束、从容而有意趣的消遣活动。《诗·邺风·谷风》说:“就其浅矣,泳之游之”,“游”作为游水是一种随意的和自如的身体活动。
“游”是《庄子》①本文《庄子》的文本引用皆来自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中出现最频繁和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在《庄子》中,“游”字共出现108次(人名除外),遍布内外杂篇,并以内篇出现的频次多。“游”可以体现《庄子》尚自然、重自由的思想主旨。从庄子的文本出发,基本上有以下两种用法:(1)一种身体活动,也就是游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含义“游历、游玩”,如“知北游于玄水之上”(《庄子·知北游》)、“黄帝游乎赤水之北”(《庄子·天地》)。(2)心灵的自由境界,如《人间世》有“乘物以游心”,《德充符》有“游心乎德之和”,《应帝王》有“游心于淡”,《田子方》有“游心于物之初”,《则阳》有“游心于无穷”,等等。庄子身体层面的“游”首先发生在天地之间,受到自然界客观规律的限制;心灵层面的“游”则把这种外在的规定转化为内在的自然性,因此心游也是一个回归天性的过程。在心灵层面的“游”也有一个区分,即是根据所游对象的不同,如“物之初”和“坚白同异”的不同,心灵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庄子的游心和道的虚无有关,和物的区分、辨别无关。有的学者将“游”区分为心灵之游、虚无之游、自然之游[1],事实上这种区分是从游和道的关系的不同侧面出发,从根本上讲是同一的。我们对庄子之游的区分在于,第一种含义表明了“有待”的状态,和陆地的行走或水中的游泳有关;后一种含义则表明了“无待”的状态,和天空的飞翔有关──鲲化为鹏的寓言暗示出庄子的游是无待之心游。
虽然徐复观先生在阐释庄子“游”的美学意义时,将它不受拘束、自由自在的特征解释为“游戏”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还是应该区分此“游”与彼“游戏”。他们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中西人生态度和思维方式上的不同。就中国思想而言,“人生在世”“人生天地间”,天地自然具有一种优先性,是人存在的根据,也是人思想的根据,中国的智慧是“天人合一”。因而,“游”也是一种“天人合一”式的活动,庄子的游更是游于道、游于天地之间。西方的游戏除了玩耍的含义,还有赌博、竞赛的意思①“英语的游戏(play)和德语的游戏(Das Spiel)在含有玩耍的意义之外,还意指赌博和竞赛。”(彭富春《说游戏说》,《哲学研究》2003年第2期)。抛开词的本义差别,西方的“游戏说”体现出“主客二分”式的人生态度和思维方式。“游戏”是一个可操作、可控制、可设定并且需要规则的整体,人先设置一个“游戏”以及游戏规则,然后进入“游戏”中。举不恰当的例子,西方的“嘉年华”的大型娱乐“游戏”与中国古人畅情山水之游相差不可以道里记。
“游”在庄子和孔子那里都具有精神自由的含义,他们都是在尘世中实现审美的超越,而不是在一个与此岸对立的彼岸中实现精神寄托。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②《论语》的文本引用皆来自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为方便故,下文征引《论语》原文只注明篇目。此处引自《论语·述而》。道、德、仁和艺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一种外在的规范,需要人去志、据、倚,而游则表达了一种与服从规范的束缚状态不同的自由感。这种自由感来源于人的自然本性如情感、欲求等,因此艺术活动就如同游戏那样可以给人带来快乐。这种快乐既是礼法森严的儒家政教体系的一个有益的补充,又是孔子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最高精神境界,即他所说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这种精神境界的涵养,就在于诗和乐的艺术活动。礼和乐因此在儒家所构想的社会中成为内和外相辅相成的两翼。孔子的“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活动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人类的社会生活,尤其以礼、乐为代表,是道、德、仁的具体化,其强烈的形式意味有着很强的审美性,所以都称为“艺”。孔子“游于艺”的感受除了自由感外,还有一种来自道、德、仁的完善感、充实感。“因而,儒家的‘游’,核心是仁。”[2]
《逍遥游》揭示了游的双重主旨,一方面是心灵对世俗的超越,一方面是形体对外物的随顺。前者是审美意义上的逍遥游,而后者则是庄子被人诟病最多的宿命的游世主义。游在应然世界中是逍遥的,这里大知实现对小知的超越,也就是审美的超越,体现出积极创造的意味。游在实然世界遵循的是无大无小的随顺原则,宇宙观在人生观上的泛化导致消极的游世哲学,逃避以求解脱。我们着重分析心游的意义,将后一个问题悬搁起来,后文再叙。但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庄子所说的应然世界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彼岸,它依然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根本上是一种心灵构造的境界。
逍遥游就是心游,心灵要抵达绝对的自由状态就需要让“真正的自我”(假定的精神性实体)从功名利禄、是非善恶乃至从自己的形骸和私念的限制中解脱出来。心游有否定和肯定两个层面,否定层面在于破除精神桎梏,超越自身局限,批判人性(人的天性)异化;肯定层面在于回归天地自然,获得绝对自由。否定方面,即从与人的本性相对立的异化了的世界(包括很多层次和内容)中逃遁出来。人的本性到底是什么,庄子没有回答,也无意回答,他只是醉心于抵达自由的过程。所谓“逍遥游”,这“游”正是对现实中名缰利锁的批判和脱离。肯定方面,强调人的精神自由就在于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也就是与道同一。道也是无具体规定性、无差别对立的精神实体,它是自然的本性。庄子的真正意图就是让人的本性效法大自然中无差别的绝对自由。这样,自然的本性就成为真正的人的本性的最终依据。并且无差别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它引导着一种无差别地、整体地对待事物的世界观、人生观。人和这一本体的连接不是通过认识论的方法,而是抛却了语言概念的直觉体验(在语言范围内就是对理性名制的颠覆)。在审美中,物我两忘的迷惘状态成为与道为一的形象表达。所以,庄子的哲学命题其实就是美学命题。
总体来看,逍遥游体现出精神层面的优游自在、无所挂碍的纯粹的、绝对的自由状态。应该指出,庄子的自由不是实然世界中已实现的自由,而是一种个人的自主选择,一种精神意志和思维趋向,境界层面上的体认、追求和创造。庄子的自由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自由感,具有很强的情感意味,从根本上也不同于西方建立在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实践基础上的自由。庄子的心游就是用心灵构造一个具有浓厚的审美意味的应然世界,这就是他生活审美化的精神所在。游具有的非身体化的倾向,使他创造了一个充满了形而上的生命意味的世界。形而上的生命当然不会是伦理道德意义上的,恰恰相反,它是以消除一切“欲望”甚至代表着文明的善的欲望为代价的。然而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对人的欲望的弃绝,不同于世俗宗教的禁欲主义,也不同于后期儒家对人的身体欲望的禁绝,而是在更高的意义上恢复自然生命的合法地位,在与道为一的指向中体现生命自身的本来面目。
二、游作为否定和化解
心灵在庄子看来,具有一种绝对的超越力量,这种超越以对智识之心和道德之心的否定、对情态之心的化解来实现。对这三种心态的超越实际上就是庄子弱化自我中心、克服私我桎梏从而返回人的本性的主要内容,由此所抵达的“与道(天)为一”的至高境界就是“逍遥游”。这种否定性的经验自身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
庄子的心游是游于虚无。《逍遥游》篇提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以作为“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的根据,庄子的“无”剔除了老子的“无”作为权宜之计的层面,赋予“无”以积极的精神超越的意义。庄子的“无”还体现在一些否定性词汇的运用上,如:“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胠箧》篇连续使用了“绝、弃、擿、毁、焚、破、掊、折、殚残、擢乱、铄绝、塞、灭、散、胶、毁绝、弃、攦、削、钳、攘弃”共 21 个否定性的动词。那么“无”的含义(也即“吾丧我”之丧,“坐忘”之忘)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无并不是对现象的描述,即空无一物或虚空,而是道作为本体的不可认识,包括目不能见、耳不能听,即它不是作为实物能够被人感知。在无形无象的意义上,类似于上文所说的虚的状态。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含义是否定。庄子在《逍遥游》中对于游进行了区分,即有待之游与无待之游。《逍遥游》的鲲鹏之游并不是逍遥游,它依然有所凭借,不能摆脱物质条件的束缚,但它是无待的心游的象征。庄子的本意并不是贬低鲲鹏的有待之游,他只是用他一贯的语言策略申述,精神自由的意义就在于摆脱了一切凭借。有待之游到无待之游是一个精神超越的过程,这一求道过程的实现依赖于“无”。庄子用鲲鹏之游寓指游于大道的无穷广大的境界,然而鲲鹏之游作为游自身的象征意义不在于所游对象的无限,而在于对有限的否定。游本身是对有限性和有待状态的一种否定①“这样无待之游和虚无建立了根本性的联系。它一方面是游于无穷,是对所游的有穷性的否定;另一方面是无穷之游,是对游自身的有限性的克服。”(彭富春《说游戏说》,《哲学研究》2003年第2期)。至于说游的对象是有穷还是无穷倒在其次,这也可以用来解释“小大之辩(辨)”和“小大齐一”的矛盾。“小大齐一”是《齐物论》的主旨,也是在认识论层面提出的从“道”“一”的角度去看待世间万物,取消物与物之间的等级差别,恢复物自身的自然本性,强调世界存在着整体的多元化。而“小大之辩(辨)”的意义则是在生存论层面提出的人获得精神自由的最终法则——超越,超越小知的偏于一隅到达大知的“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超越内在地包含了否定与肯定的意义。若将“无”理解为“去蔽”,那么,在否定意义上的“去蔽”正是为了肯定意义上的“显现”,道显现出来,于是人就“与道为一”。所以否定和肯定、遮蔽与显现、无和有是庄子精神超越的两面,它不是对立的矛盾,而是属于道这个事情本身。因此,“无”作为否定性经验不能仅从消极的一面理解,同时要凸现它积极的价值和重建的一面。
“无”作为道的“显现”的超越意义还可以通过鲲鹏形化的寓言得到进一步的说明。鲲游水,表明游本身是一种随意的和自如的身体活动,然而和大鹏展翅比起来,显得沉重了很多,是一种建基于身体的活动。鲲化为鹏,一方面在于强调自由感的增强,另一方面暗示了轻盈的心灵对沉重的身体的摆脱,也暗示了庄子主张人不当拘限于形躯我,当与大化同流,在自然万化中求生命的安顿。“化”事实上连接了3个环节:(1)世俗之人。其身体是局限在儒家以“仁义”道德规范的血缘身体,其心灵是小知者与外物纠缠的道德之心、智识之心和情态之心。由于身和心被外物控制,人呈现出异化的不自由状态。(2)上文所述的否定的环节,对世俗之人的否定在于身心皆忘,事实上人重获天/自然性的规定。同时,否定还意味着对无所窒碍的绝对自由的肯定,对道的显现,事实上是用天来规定人,将自然性内化到人之中,主要是内化到心灵中。(3)至人,天人。其身体是安定舒泰的,如同藐姑射山的神人水火不惧,其心灵则是大知者的体道虚心,身和心解除了与外物的紧张关系因而和谐相处,人回复到自身的本性,因而是绝对自由的。这个由人到天人的过程,说明了庄子用自然性来克服人的异化现实的用心,再一次证明了庄子的天不是原始自然,而是心灵体道从而返回天的自然而然本性的过程。
“无”的否定含义主要体现在“坐忘”中,它揭示了具体的被否定的对象。忘包括“堕肢体”“离形”,即对身体欲望的否定,“黜聪明”“去知”即是对智识之心、道德之心的否定。
游的超越性还体现在庄子的以无情为至情,这主要是针对世俗的情态之心。冯友兰先生用“以理化情”来概括庄子的这一思想。“不过这种畏惧和忧虑(情),可以由于对事物的自然本性有自己的理解而减少”[3]94。冯友兰所说的理是至理、“道”之理或“天理”,就是天、道大化流行自然而然的道理。从根本上不同于孔子的伦理。庄子以理化情是为了让情态之心获得自然状态,无情表面上是情的虚无化,其实质是对俗情的忘却、超脱,所谓“纵浪大化中,无喜也无惧”。与庄子的以理化情不同,孔子可谓是以情为理,孔子的情是伦理亲情,他进一步将之普遍化,本质上是对世俗之情的执著。两者的向度不同,前者的心灵是一个减少以至于虚的过程,而后者的心灵则是一个增加以至于实的过程。庄子的以理化情有积极的超越层面,也有消极的宿命论的层面。冯友兰先生说:“圣人由于对万物的自然本性有理解,他的心再也不受世界变化的影响。用这种方法,他就不依赖外界事物,因而他的幸福也不受外界事物的限制。他可以说已经得到了绝对幸福。这是道家思想的一个方面,其中有不少的悲观认命的气氛。这个方向强调自然过程的不可避免性,以及人在自然过程中对命的默认。”[3]96可以看出,庄子的心学已经内在地包涵了宿命的萌芽,而不仅仅是精神超越的积极力量。所以,把身体的存在与消亡看做自然界不可避免的规律以求从情感的悲哀中解脱出来,以理化情的本质依然是以天化人。
那么,最关键的问题何在呢?庄子是以什么为根据来否定诸如智识之心、道德之心、情态之心呢?难道这些不是世俗中已存在着的看起来最合情理的东西吗?笔者认为他的根据是道,是自然界大化流行的自然而然的本性。
庄子反对“机心”,因为机心表达的是心对物的区分、掌控、设定,然而物反过来又对心构成了压制和干扰。机心把物看做器具(“机械”),即这个物存在的意义在于对人的有用性,物自身存在的意义被剥夺。从心的角度看,庄子认为心自身是“纯白之备”。心有对物认识和占有的欲望,然而心并不是欲望。欲望必然有一个所欲之物,所欲之物的膨胀反过来充满了“纯白”,心自身因此变成了欲望,丧失了原本的“备”(全)即天性。庄子反对道德的深意也在于在善、恶的名目下,人的过度追求会反过来戕害人的自然生命。庄子的超道德立场和他对“知”的态度是一致的,也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根据,求知和求利都造成人与物的对立关系以及异化①“在中国缺乏纯知识活动的自觉中,由知识而来的是非,常与由欲望而来的利害,纠结在一起。”(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63页)。如儒家的智识之心表现在道德上就是“凡事分辨,如尊贤授能,先善与利之类”[4],“举贤则民相轧”,等级次序的建立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任知则民相盗”,智识使得人民失却淳朴、厚道的风气,同时使人心中追逐利益的层面膨胀。庄子批判儒家标举贤明(“契然仁者”)、任用心智(“画然知者”)(《庄子·庚桑楚》)。“契然”是标举显示的样子,“画然”是明察炫耀的样子,这两种状态与自然界春华秋实的自然而然的运转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因此,庄子反对仁、知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表现出的情态的不自然。仁、知不再作为人本性中的求知欲或善、恶之根这样本然的东西存在,而是演变为外在于人的本真生命的名器而存在。更何况,人的本性究竟是否有所谓的“善根”本身即是问题。道的根本特性是天/自然性,所以人性的根本特性也是自然性(自然而然)。正是在自然而然的意义上,庄子揭示出儒家“仁义”道德是外在的人为的狭隘专断的规定,对人的本性构成了钳制和压抑。孟子、荀子都是儒家学说的传承者,但对人性善、恶的辩论却至今无法有定论。这就说明,善、恶不能全面说明人性,至少伦理道德并不能对人构成根本性的规定。儒家学说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孟子的“四端”说,认为“仁、义、礼、智”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但相反的例证也很多,如荀子就曾说“性无伪不能自美”。人的本性究竟是什么?问题可能就出在这样的提问方式上。一旦回答,就势必落入是a、是b、是c这样僵固的答案上。庄子看出这个问题的虚妄,事实上他用否定也就是远离世俗观念的方式回避了“人性是什么”这个具体的问题,而是对人性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更本源性的规定——自然而然。人性就是来自自然的本性。他远离,然而恰恰走在一条返回家园的路上,也许这就是最高的智慧吧!
在庄子看来,“智知”和“善恶”、情态之心的度应该保持在自然的范围之内,对于生命而言,就是“缘督以为经”(《庄子·养生主》)。督有中空、虚的意思,凡事处之以虚,虚就是否定智巧、道德的过度,回到生命本源。只有这样,才能“保身”“全生(性)”“养亲(身)”“尽年”(《庄子·养生主》)。也只有这样,才能保全生命的大美。很多人把“游”的美学意义归结为它所体现的自由状态,事实上,对庄子来说,游不仅仅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返回本性的方法。逍遥游的境界所以美,在于它“游心于道”,即是合乎自然的至理。
三、游心于道的美学意义
(一)超功利、非逻辑的审美心理
游是人对待现实世界的超然态度,是对现实世界的否定、超越以至升华到一个审美的世界。康德认为审美的主要特点是“:不凭任何利害计较,而凭快感判断对象;不涉及概念而使人愉快;无目的而合目的。”[5]上文提到的对智识之心的否定其实是一种非逻辑的审美心理,而对道德之心的否定则是一种超功利的审美心理。
黑格尔说“:艺术兴趣和欲望的实践兴趣之所以不同,在于艺术兴趣让它的对象自由独立存在,而欲望却要把它转化为适合自己的用途,以致于毁灭它。”[6]庄子不可能完全脱离实践欲望,忘,只是要人与物保持适当的“距离”,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这种既(身)不离世而又(心)出世的精神就把人生艺术化、世界审美化了。一颗虚静的心灵把意识集中在具有审美特征的客体和审美客体的审美价值上,并且把审美无关的客体与其他都排除在外。正如布洛说“:人们平常看不到的事物背面的形象一旦突然出现就会成为对人的一种启示,确切的说,就是艺术的启示。从这一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距离乃是一切艺术的共同因素。”[7]朱光潜在介绍布洛的“心理距离”说时谈到“:距离含有消极和积极的两方面。就消极的方面说,它抛开实际的目的和需要;就积极的方面说,它着重形相的观赏。它把我和物的关系由实用的变为欣赏的。”[8]一旦把世界由实用变为可欣赏的,美就产生了。苏东坡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9]对人与物的“距离”谈得更透。寓意于物,是移情于物,是审美观照下的物我合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的审美体验;留意于物,则是实用目的、占有欲、执著、贪恋。凡物不唯可用,亦可观、可乐。忘其用则可观,可观则可乐。有这样的人生观,则世间无往而不乐,人生何处不是艺术!因此,从根本上说,庄子对物的态度就是“让存在”,也只有一个为了自身而存在的物才会是美的。
关于非逻辑的直觉的审美心理可以用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的故事得到说明。庄子曰“: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也?”惠子曰“:我非子,故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这段千古名辩费尽无数哲人心思,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论,究竟孰是孰非。在笔者看来,庄、惠的区别乃是智识之心和理性直观的区分。濠梁之辩庄子所以知道鱼之乐,原因在于他所说的知是一种当下的、非逻辑思辨的体悟,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庄子所以知鱼乐“,知之濠上”“,游”表明了一种当下的自由快适,无特定目的与特定时空限制,符合庄子追求美感经验时摒除知识限制与实用目的的那种逍遥与自由。“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鱼乐”境界事实上是一种物我合一的境界。徐复观先生将这种理性直观理解为一种孤立化的、以自身为目的的知觉心理,是很恰当的。在专注的知觉中,不旁迁他涉“,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而理性的智识首先在于对物进行区分,其次强调人与物之间的一种印证关系。人与物处于一种疏离甚至对立的状态,自然无法体会物自身的美。庄子看到鱼“出游从容”便觉得它乐,因为他自己对于“出游从容”的滋味是有经验的。假如庄子不是鱼就无从知鱼之乐,每个人就要各成孤立世界,和其他人物都隔着一层密不通风的墙壁,人与人以及人与物之间便无心灵交通的可能。这种通感现象与西方审美理论中的“移情说”相类。叶朗先生说“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其含义丰富而深刻,胜过厚厚的一大本美学著作。只有庄子那样的建基于人与世界的沟通基础上的直觉才能“彰显”出一个美的世界,而执著于分解性和概念性的认识活动的惠子则无从体会“游之乐”。
朱光潜《谈美》一书,提到对于古松的三种态度: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实用和科学的态度,都是逻辑的经验;美感的经验才是直觉的经验。在直觉的经验中,美是自成自足,别无假借的。也只有从实用和科学的态度中抽离出来,抱持“无所为而为”的想法,并在独立、绝缘的情况之下,才能享有完全的美感经验。时至今日,这种区分依然可以最充分地说明审美心理的特征。
(二)游刃有余的自由创造
在具备了审美心胸的前提下,审美主体只有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才能获得审美创造的高度自由。庄子书中有三个关于技艺的故事:庖丁解牛、轮扁斫轮、梓庆削木为。我们以庖丁解牛为例说明庄子将技术提升到艺术、在现实人生之上成就审美化人生的精神实质。
《养生主》中的庖丁在解牛时“游刃有余”“,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虽然庖丁的行为不是纯粹的艺术创作,但所谓“砉然响然,奏刀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就是说庖丁解牛符合音乐舞蹈的节奏,已经达到了审美的境界。并且,庖丁在把别人带入审美境界、让别人叹为观止的同时,他自身也得到了愉悦。这种愉悦来自创造的自由,这是进入审美境界而产生的一种精神享受,即审美愉悦,此时的庖丁“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这种快乐显然不同于世俗的功利欲望的满足,而是一种人的自由得到了显现,人的创造力量得到了肯定,而获得的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人们“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复现自己”“肯定自己”,人摆脱了被物压制的异化状态,人和物各自回归天性,这是最高的自由状态,也就是美的境界。
在庄子的美学思想中,审美创造既是主体心灵高度自由的表现,即游心于道的过程,也是主体在身体技能上的极其熟练精纯的现实把握,即游刃有余的过程。
艺术操作中的技,主要指艺术创作过程的技能与技巧,而艺术操作中的道,则主要指艺术意象创作与传达过程中自由无碍、充满生气的至高境界。艺术家在技巧的操作中,是可以体悟、把握道,进而达到道的。同时,道也可以通过技而体现出来。这种道、技合一的状态,乃是艺术家自如地将心中的感受自由无碍地通过高度娴熟的技巧表达出来,在技中可以发现道的真谛,道也在技中得到体现和表达。这种道、技合一的状态也就是美的境界。
庄子所说的美不仅仅是一种虚无化的心灵境界,还是现实层面的自由创造。如果技术达到一定地步获得道的规定就可以升华为艺术。在古代中国“,技”与“艺”这两个词就是一个意思。“Art”的本义也是技术,今义是艺术。康德分“美的艺术”与“手工艺”“:前者唤作自由的,后者也能唤作雇用的艺术。前者人看做好像只是游戏,这就是一种工作,它是对自身愉快的,能够合目的地成功。后者作为劳动,即作为对于自己是困苦而不愉快的,只是由于它的结果(例如工资)吸引着,因而能够是被逼迫负担的。”[10]这是有意义的。艺术不同于一般手工艺或技术的地方就在于它超越一般功利或实用,以自己为目的;艺术的创造是一种自由的、令人愉悦的活动。但费尔巴哈认为“:一般来说,艺术和手艺之间,有什么鸿沟呢?难道不是只有当手工业者、陶器匠、玻璃匠、泥水匠成了艺术家时,真正的艺术才得以表现出来吗?”[11]从这个角度讲,技术和艺术之间确实没有填不平的鸿沟,前者在两种情况下就可能发展为艺术,或最起码能视为艺术。一是技艺达到高度熟练、精湛、心手相应、挥洒自如的境地的时候。庄子谈到的庖丁、轮扁等能工巧匠,他们的“技”“巧”“数”“道”以及作品(如梓庆削木为)都臻至令人“疑神”的程度,出神入化,巧夺天工,这何尝不是一种美!《大宗师》说“吾师乎!吾师乎!……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所游已!”刻雕众形是“大巧”。说到底,技术是人在物质上对世界或自然的改造,当人掌握了事物的规律之后,也就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了,也就获得了自由,这时候,美就可以产生了。一是掌握技术者或创造者在劳动或创造时有一种自由的、无功利的心态。在异化劳动下人当然很难获得这种心态。
“游刃有余”所以是一种高度的创造性自由,还表现在“神遇”与“感官”的关系“,天理”和“人工”的关系。技艺纯熟的标志在于“指与物化”,当身体与外物没有区分时,这是身体所能获得的最大的自由,身体不再是对外物的限制,它们之间的对立消解了。三年之后“,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这时,工具、对象完全变成为人而存在的了,仿佛化为自身的一部分,成为人延长了的手和足,技巧也仿佛成了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一样,不假思索,随机应变。所谓技和道的关系,还可以理解为天理和人工的关系,人工如果和天理契合,那么创造出的艺术品就是“虽由人造,巧夺天工”。陈望衡先生在他的《中国古典美学史》中将三者的关系归结为“必然”与“自由”关系,认为要想获得现实中身心合一的自由,就“必须像庖丁那样通过实践去掌握牛之‘必然’”[12]。精湛的技艺实际上来自长期艰苦的实践。庖丁解牛19年,轮扁行年七十而斫轮,“大马之捶钩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吕梁丈夫更是生乎水边,长乎水中。陆机《文赋》开篇第一句话乃“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除了强调文学创作之前的虚静的精神状态之外,也指出具备相当的文学辞章素养的重要性,否则便无从达意传情。庄子以道来规定技,但他并非反对技术,而是通过道将技术所能有的创造性本质解放出来。钱钟书曾在他的《谈艺录》中谈到主体心灵和客观自然遇合与沟通的三个层次或阶段:人事之法天——人定之胜天——人心之通天。这是一个主客关系由相持相抗到相融相通的转换,也是由技入道、由必然到自由的创作过程。这三个层次在艺术中的境界也是不同的,有高下之分。“人事之法天”是主体追慕客观世界的自身规律性(真),是艺术家对客观世界被动的效法状态,表现为重视浅层客观的再现;“人定之胜天”体现了人类的主观目的性(善),强调人的情感、意志、理想对世界的占有和支配,在艺术中则是重视主观上的自由放达的表现;“人心之通天”是最高境界的天人合一,在完全的意义上体现了人化的自然,实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真正抵达艺术极致的美。这时,凛然的客观世界不再造成主体心灵的被动和疲落,自由的主体不再造成客观世界的破碎和消遁,两相保全而又契然融合,既不是萍水相逢,又不是侵略式的占据,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如登高山如临沧海,大乐与天地同和。
道创造万物,艺术家创造艺术品,人创造更自由的人生,这是一脉相承的。张璪论画时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意思是说,要像自然造化创造万物那样去创造艺术品。人在现实中也要如同操刀的庖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看透社会可以容身的缝隙,也并非总是毫无作为地悲观宿命。庄子提到了很多生活中的例子如佝偻丈人承蜩、吕梁丈夫游水、匠石运斤成风、大马之捶钩者捶钩、工倕旋而盖规矩,都能“自适”自处,将生活的矛盾消解……这里蕴涵着深一层的意思,庄子的“委顺”“因循”并不完全是一种消极的处世方式,而是一种非常“经济”的安身立命的途径,可以无心而得之。《达生》中的一则寓言中说仲尼到楚国,见一佝偻丈人在承蜩,就像用手拾一样简单,仲尼非常奇怪:“子巧乎!有道邪?”这时承蜩者道出其中原由:“……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丸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丸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吾处身也,若厥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从这里不难看出,承蜩者能使自己的技艺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是因为他的心境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能够抛开外物的影响。承蜩时,身体像竖起的树根一样不动声色;在这个世界上,只知道还有蜩翼的存在,把干扰自己性情的一切外物抛开,甚至完全忘记了自身的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何为而不得”,何为而不为!
[1]王凯.逍遥游:庄子美学的现代阐释[D].武汉:武汉大学,2002:18.
[2]成中英.本体与诠释:中西比较[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76.
[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97.
[5]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358.
[6]黑格尔.美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48.
[7]布洛.作为艺术因素与审美原则的“心理距离”说[M]//美学译文: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95.
[8]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M].长沙:湖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57.
[9]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356.
[10]伍蠡甫.西方文论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562.
[11]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M].北京:三联书店,1959:319.
[12]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126.
B223
A
1671-9476(2011)01-004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