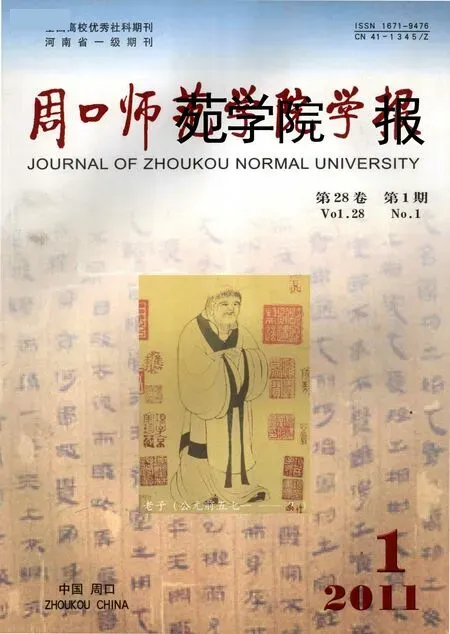论东周时期道家学派的精怪观念
2011-02-20翟胜利
翟胜利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论东周时期道家学派的精怪观念
翟胜利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庄子及其后学常常结合当时的精怪传说创造一些寓言作为自己的论据。道家学派对精怪现象采取相对崇信的态度,这与道家万物有灵的思想观念是有关的。精怪观念与远古传说的合流对这一时期人们的历史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道家学派;《庄子》;精怪观念;万物有灵
东周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期,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巨变,其表现之一就是精怪观念逐渐从鬼神观念中分化出来并得以迅速发展。用精怪观念来解释事物是人们认识、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东周时期的诸子学派是当时知识精英阶层的代表,他们的思想是大传统精英文化的集中表现。然而诸子的思想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流行于大众阶层的小传统文化的影响,道家学派也不例外。从精怪观念的角度来看,道家学派与小传统文化的关系尤为密切,他们的不少观念可能直接来源于小传统文化。大传统对小传统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或单向的,东周时期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常常保持着十分微妙的关系,二者之间甚至没有分明的界限。
一、道家学派的学说与精怪现象
先秦时期道家学派的精怪观念主要体现在《庄子》一书中。《庄子》是庄子及其后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寓言的使用是其特点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所载寓言往往并非向壁虚设,多有其神话传说背景,可以反映出某些思想观念。从《庄子》所载神话、寓言中,我们可以窥见先秦时期道家学派精怪观念之一斑。
《庄子》首篇的《逍遥游》即提到了一本志怪专书:“《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齐谐》是志怪专书,之所以名为《齐谐》,或因其出于齐地。此书的出现表明该地区精怪观念是非常盛行的。《逍遥游》中引述了《齐谐》中关于鲲鹏的记载,表明鲲鹏传说并非出于庄子杜撰,也表明《齐谐》一书是确实存在的。
《庄子·逍遥游》结合《齐谐》与相关传说引述了鲲鹏互相幻化的事: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
来自北冥的鲲鱼化而成鸟,显然属于精怪,能幻化形状正是精怪现象的特征之一。《尔雅·释鱼》:“鲲,鱼子。”所以郭庆藩等人认为鱼之至小者曰鲲,庄子取其齐物之意也。陆德明《经典释文》认为:“鲲,大鱼也。”并引崔撰说鲲当为鲸[1]。根据《庄子》对鲲的描述,笔者以为陆、崔之说近是。此处庄子所言齐物并非将小鱼夸张作大鲸,而是齐此处之鲲鹏与后文之蜩与学鸠。《说文》“:,海大鱼也,从鱼,声。”袁珂先生以为即《山海经》之“禺强”。《山海经第八·海外北经》“: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郭璞注:“字玄冥,水神也。一曰禺京。”[2]295此当即《庄子·大宗师》“禺强立于北极”之禺强。又《山海经第十四·大荒东经》:
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号。黄帝生禺号,禺号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号处东海,是为海神。
禺京,郭璞注“:即禺强也,强、京一声之转。”[2]403则《庄子》所载之鲲当即《山海经》所载之禺京、禺强。禺京、禺强人面鸟身,显然已经是精怪形象了,之所以称为海神,也必有其传说依据。《淮南子·墬形训》“:禺强,不周风之所生也。”《史记 ·律书》“:不周风居西北,主杀生。”则似乎禺强又曾被视为风神。
《说文》将朋及鹏都列在凤字之下,以为皆古文凤字也。朋鸟象形[3]148。前贤大都认为鹏即凤,是一种具有灵异性质的鸟[4]。袁珂先生谓《淮南子·本经训》中所载尧时害民之物有“大风”,即大凤,亦即《庄子·逍遥游》之大鹏,高诱注以为风伯[2]296。那么鲲鹏既为海神又为风神,有时似可看做一物,正与庄子所谓鲲鹏相化之意相合。
《庄子》一书常常引述有关传说人物的寓言以证明其观点,如罔两、夔、浑沌等,通过这一类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先秦道家学派的一些精怪观念。
《庄子·齐物论》记载了“罔两”嘲笑“景”行止坐立都仿照别人,不讲操守的事。罔两,典籍又作魍魉、蝄、罔阆、方良、罔浪等,所指皆为一物,古人称名往往取其音同而已。《说文》“:蛧,山川之精也。淮南王说,蛧状如三岁小儿,赤黑色,赤目,长耳,美发。”[3]67《2左传 ·宣公三年》:
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不若,杨伯峻先生注“:不顺,意指不利于己之物。”[5]应即指生于川泽山林的螭魅罔两,由此观之,当时人确实认为魍魉是生于山林中的一种怪物,铸鼎象物则可以使民远离这种精怪。魍魉有时候被看做疫鬼《,周礼·夏官·方相氏》“:及墓,入旷,以戈击四隅,驱方良。”郑玄注“:方良,罔两也。”[6]有学者认为罔两乃是无两、无双之意,本意并非指精怪[7]。然而无论如何,至庄子之时,魍魉已经作为一种生于山林的精怪出现在人们的观念之中,此后的流传中,尽管对其具体形态有不同说法,但都没有脱离精怪的范畴,是一种生于山泽之中的怪物。景即影子。罔两与影子的对话,今天称之为寓言,然而其本身也是万物有灵观念的反映,是古人的一种浪漫的想象。这与道家学派的精怪观念是相契合的,因为精怪观念的核心内容也是万物有灵。
二、道家学派精怪观念与历史观念的合流
《庄子·应帝王》记载了浑沌惨死的事:南海之帝倏与北海之帝忽相遇于中央之帝浑沌的领地,浑沌友好地善待他们。浑沌没有眼耳口鼻等七窍,倏与忽为了报达浑沌决定为他凿出七窍。他们每天凿一窍,浑沌七日而死。浑沌没有眼、耳、口、鼻等七窍却能生存,显然不是一般的人而是精怪。倏与忽为浑沌凿出七窍以利其生存,不料却害死了浑沌。浑沌既能生能死,应非特别神圣的神灵,可以视之为一般的精怪。
浑沌一名亦见于《史记·五帝本纪》: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舜宾於四门,乃流四凶族,迁
于四裔,以御螭魅,於是四门辟,言毋凶人也。《左传·文公十八年》亦有基本相同的内容,《史记》或源于《左传》。“浑沌”《左传》作“浑敦”,其实是一个人。浑沌一名应该是取材于历史传说中的人物,此时的浑沌已经完全被精怪化,具备了典型的精怪形象。精怪观念与历史观念合流致使部分远古传说人物、事件精怪化,这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
关于夔的传说是精怪形象与远古传说人物合流的典型例子之一。《史记·五帝本纪》:“三年丧毕,让丹朱,天下归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尧时已被举用的人里面即有夔。《尚书·尧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明确记载了舜命夔为乐正的事。另外,《史记·夏本纪》:“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荀子 ·成相》:“得后稷,五谷殖,夔为乐正鸟兽服。”这些材料都表明夔为舜时乐官。综合以上材料,我们推测,夔是传说时代的英雄人物之一,在尧时已经被举用,但未被授予专门的职官,而至舜时夔始被命为乐正。
《尚书·皋陶谟》记载了夔为乐正时候的表现:
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在重大的典礼上,夔率众演奏鸣球、搏拊、琴、瑟等乐器,使百兽率舞。《史记·夏本纪》的记载与此大体一致。夔指导奏乐、舞蹈以及舜以歌相和的盛况都表明夔完全能够胜任乐正之官,舜对此非常满意。
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夔摇身一变成了精怪。《山海经》描述了夔的精怪形象:“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夔的形象与黄帝的传说杂糅在一起,难分难解。
孔子试图对夔的精怪形象进行纠正。《韩非子》记载:
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孔子认为“夔一足”非谓夔仅有一只脚,而是说以夔之能力,一人足以领导声乐之事。虽然如此,夔为精怪的说法仍然流传了下来。《庄子·秋水》:“夔谓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予无如矣。今子之使万足,独奈何?’”夔以一足跳跃而行,则作者仍然认为夔乃是独脚的精怪。即使《韩非子》一书所载孔子纠正夔之身份的事属实,到了庄子及其后学的时代,人们仍然认为夔是只独脚精怪。这件事也表明道家学派受精怪观念的影响程度比儒家更深。夔本为舜时乐官,与精怪观念结合后夔又以生于川泽之中的独脚兽的形象流传于世。虽然此前孔子作为当时的大学者已经对此观念作了纠正,但精怪观念的流行是非常普遍的,非一人之力所能扭转。
三、精怪观念影射政治前途的一种趋势
《庄子》记载齐桓公遇鬼、臧文仲祀爰居等事,说明在当时的观念中精怪的范畴已经相当广泛,一些术士甚至试图利用精怪观念影响诸侯国的政治前途。
《庄子·达生》记载齐桓公田猎时遇鬼,田猎归来即大病,数日不出。齐国术士皇子告敖认为桓公之病与鬼无关,鬼并不能伤害桓公。忿滀之气“中身当心”,才是造成桓公大病的原因。桓公问告敖是否真的有鬼。告敖回答:
曰“:有。沈有履,灶有髻。户内之烦壤,雷霆处之;东北方之下者,倍阿鲑跃之;西北方之下者,则泆阳处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泽有委蛇。”
公曰“:请问委蛇之状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而朱冠。其为物也,恶闻雷车之声,则捧其首而立。见之者殆乎霸。”
桓公冁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见者也。”于是正衣冠与之坐,不终日而不知病之去也。这里面有3点值得注意:(1)从桓公的表现可知,桓公相信真的有鬼存在,而且他相信自己遇到了鬼。(2)齐国术士虽然认为桓公的病与鬼无关,鬼不能伤桓公,但他也相信有鬼存在,并且各种精怪都可称之为鬼,鬼与精怪之间是可以画等号的。(3)齐国术士消除桓公的畏惧心理后,又用委蛇昭示霸业的话来哄骗齐桓公。利用精怪来影射政治前途,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精怪观念很值得注意的一个发展趋势,后来谶纬之学的产生与此观念都是直接相关的。
《达生篇》还有一条关于鬼的材料:孔子游于吕梁,看到激流之中有人游泳,以为是有人要寻死,命弟子拯救水中之人。其人游了数百步后便从水里出来,披散头发高歌而行。于是孔子上前问道:“吾以子为鬼,察子则人也。请问,蹈水有道乎?”此条材料应该是假托于孔子,然而也体现了当时道家学派关于鬼的一种观念。此处所谓的鬼,大概是当时人对于具有某种神异能力的事物的一个通称,其实也是精怪。
由以上两条材料可以看出,当时精怪与鬼在观念上已经合流,鬼也是一种精怪,这与此前的鬼的观念已经大不一样。尽管鬼与精怪的范畴已经扩大,但从整个上古时期长时段的角度来看,当时人对此类事物迷信的程度反而是减弱了。他们对精怪之事不再恐惧或盲目崇拜了。
《左传·文公二年》记载孔子批评臧文仲有三不仁、三不智,其中祭祀爰居即为三不智之一。《国语·鲁语下》记此事较详:
海鸟曰“爰居”,止于路东门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国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孙之为政也!……今海鸟至,己不知而祀之,以为国典,难以为仁且智矣。”
《尔雅·释鸟》郭璞注:“汉元帝时,琅琊有大鸟如马驹,时人谓之爰居。”《释文》引樊云:“似凤凰。”《庄子集释》引司马云:“爰居,举头高八尺。”可见爰居并非一般的鸟,所以有人以精怪视之,臧文仲以为神,对之举行了祭祀。展禽却认为爰居仅是普通的海鸟,所以他批评臧文仲是有过失的,为政者不应该无故举行祭祀。如今海鸟到了鲁国,臧文仲因为自己无知而以国家典礼祭祀它,这是不仁不智的表现。
更重要的是展禽对爰居出现在鲁国的原因作了自然灾害方面的分析:“今兹海其有灾乎?夫广川之鸟兽,恒知避其灾也。”他认为爰居突然降临是海上气候异常所致。《左传》的编纂者也记载该年海上多大风,冬季比较温暖,确实异于常年,对此加以证实。
由此看来,爰居虽奇怪,但展禽等当时贤人是认识的,他们知道爰居乃是一种海鸟,因海上天气骤变,不得不徙往内地。看来精怪只是因其神秘性而引起人们的疑惑,一旦人们了解真相以后,其神秘性与神圣性都会荡然无存。把这一类的事物当做神,当时已经被看做是愚蠢的行为。所以孔子才把祀爰居看做臧文仲三不智之一,他是反对祭礼异常之物的。这反映了孔子较为理性的态度,对于奇异之物,孔子往往试图用现有知识去解释,而不是归之为鬼神,这是孔子精怪观念的特点之一。
《庄子·至乐篇》亦有关于爰居的记载:
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江湖,食之鳅鲦,随行列而止,委蛇而处。
海鸟即爰居,此处所载亦是臧文仲祀爰居之事。由此可知,祀爰居应当是鲁文公在臧文仲的建议下对爰居举行了祭祀,俨然已经是一种国家行为。然而此处《庄子》的作者亦只将爰居视为一般的海鸟,其反对祭祀的原因是应该以养鸟的方法喂养爰居。尽管与孔子的角度不一样,但我们可以知道对于被臧文仲视为精怪的爰居,当时社会上许多人是保持着清醒的认识的。我们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精怪观念的出现及其流行与当时社会神权的衰弱以及鬼神信仰的衰退是同时发生的,几种力量的消长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它们共同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中精神方面的重要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精怪观念已经较为流行,它在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中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道家学派对精怪现象采取相对崇信的态度,他们常利用精怪观念论证其学说,这与道家虚无缥缈的思想特点是有关的。庄子等人常常结合当时的精怪传说创造一些寓言来作为自己的论据。在这些寓言中,鸟兽甚至影子都有思想,有言语能力,这是道家学派万物有灵观念的重要体现。其中一些精怪形象与远古历史传说互相杂糅,这使得远古英雄人物被精怪化,人们的精怪观念与历史观念发生了合流。中国的远古历史传说从此充满精怪神话色彩。这一时期以术士为代表的一批人开始试图以精怪现象来影射政治事件,给政治事件笼上神秘面纱的同时,他们也为精怪观念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在先秦时期,精怪观念始终没有占据人们思想观念的主流地位,但它以非主流的方式对当时人们的历史观、世界观甚至其政治生活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后世的精怪观念也有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多属于当时的知识阶层,他们是当时社会大传统的代表人物,庄子学派亦是如此。不过庄子等人思想中的精怪观念显然并非向壁虚设,其来源应即代表小传统的下层大众文化。儒家学派的孔子等人曾试图重新阐释有关夔的传闻,尝试引导和影响小传统。但庄子等人则大量引用精怪传说,对精怪观念的发展客观上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精怪观念也成为道家学派思想内容之一。由此看来,相对儒家学派而言,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与小传统的大众文化关系更为密切,他们的思想接受了来自小传统的深刻影响。大传统通过儒家学派的方式引导和影响小传统,小传统也通过道家学派的方式渗透和影响大传统,二者之间相互作用,常常保持非常微妙的关系。
[1]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2]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3.
[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48.
[4]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3;622.
[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670.
[6]孙诒让.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2495.
[7]尚振乾.国语·季桓子穿井辨释[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4):60-64.
On the Taoist school concept of monster in eastern Zhou period
ZHAI Shengli
(Department of Histor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Chuangtse and his disciples often used legends of that time to create some fable as their argument.Taoist school believeed in the phenomenon of monsters very much,because they believe in animism.Integration of monster concepts and historical legends of heroes had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 in eastern Zhou period.
Taoist school;Chuangtse;concept of monster;animism
B223
A
1671-9476(2011)01-0045-04
2010-09-16;
2010-11-20
翟胜利(1982-),男,河南开封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文物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