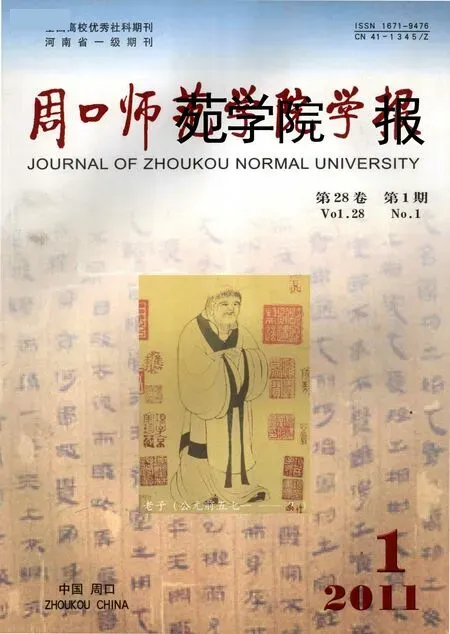韩愈读书目的论与当前大学生学业
2011-02-20丁恩全
丁恩全
(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河南周口466001)
韩愈读书目的论与当前大学生学业
丁恩全
(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河南周口466001)
韩愈读书的目的包含了功利性目的和非功利性目的,是孟子义利观的具体体现,读书的非功利性是根本,功利性是读书效果的显现,对当代大学生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韩愈;读书;功利;非功利;大学生
关于韩愈读书的研究,公开发表的论文有郑国民《韩愈的阅读理论》、刘国盈《韩愈的读书观》、廖昌胤《从〈进学解〉到〈论学习〉》、张维《书痴者文必工——试论韩愈的读书与作文》四篇,郑文、刘文、张文都介绍了韩愈读书的勤奋、读书的方法,尤以郑文最为深入全面:“文以明道贯穿阅读的全过程”“口不绝吟,手不停披”“沉浸浓郁,含英咀华”“贪多务得,学繇其统”,分别从读书要了解思想,读书要勤奋,读书要反复揣摩、仔细品味,读书既要广泛、又要有系统这四个方面阐述了韩愈的阅读理论[1]。廖文在韩愈《进学解》与培根《论学习》的比较中谈到了韩愈学习理论:“行成于思”的认知规律、“含英咀华”的创新要诀、“唯器是适”的个性化策略[2]。四篇文章富有启发性,但对韩愈读书目的的论述尚不清楚。尤其是在当代,社会发展的迅猛,社会变化日新月异,各种信息纷至沓来,使得大学生也日渐迷失,所以读书目的尤其需要明确。韩愈读书既有功利性目的,又有非功利性目的,可以有一些启示。因此,本文于韩愈读书的目的发表一些浅见,以就正于方家,也希望韩愈的做法能够给当代大学生一些借鉴。
一、韩愈读书的功利性
韩愈读书的功利性主要体现在两首诗中:《示儿》《符读书城南》。
示儿,即明示自己的儿子韩昶,符可能是韩昶小名,也就是说,这两首诗都是写给自己儿子的。据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示儿》[3]953写于元和十年(815年),韩愈48岁,《符读书城南》[3]1012写于元和十一年(816年),韩愈49岁。可以说这两首诗中所说正是大半生经验的凝结,其教育语重心长,寄寓着深沉的期望。《示儿》写自己仅靠读书在京师有了居留之所:“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4]669所居虽然不甚豪华,但“高树八九株。有藤娄络之,春华夏阴敷。东堂坐见山,云风相吹嘘。松果连南亭,外有瓜芋区。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虚。山鸟旦夕鸣,有类涧谷居”,景致很美。妻子儿女们也能够安享富贵,“主妇治北堂,膳服适疏戚,恩封高平君,子孙从朝裾”。所与来往都是权贵,“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问客之所为,峨冠讲唐虞。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4]670。言语恳切,其旨意却是富贵,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所以遭到了不少著名学者的批判。苏轼就说韩愈“所示皆利禄事”[3]956,朱熹从此出发联系到韩愈早年的《上宰相书》三篇,严厉地批评“《上宰相书》所谓行道忧世者,则已不复言矣”,进而直指韩愈思想之庸俗:“其本心何如哉?”[3]956邓肃也说韩愈“爱子之情则至矣,而导子之志则陋也”[3]957。
《符读书城南》开篇就说:“木之就规矩,在梓匠轮舆。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木之成为材而可以使用,在于工匠,人之所以成为人,则在于读书,读书的方法只有勤奋一途。至于读书的效果,韩愈详加论述:“欲知学之力,贤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学,所入遂异闾。两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长聚嬉戏,不殊同队鱼。年至十二三,头角稍相疏。二十渐乖张,清沟映污渠。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飞黄腾踏去,不能顾蟾蜍。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欤。金璧虽重宝,费用难贮储。学问藏之身,身在则有余。君子与小人,不系父母且。不见公与相,起身自犁锄。不见三公后,寒饥出无驴。”[4]722读书的效果可谓显著,两个同样的人,勤奋读书的可以成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不读书则“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即使是“三公后”,如果不读书,也可能“寒饥出无驴”。相反,即使是“起身自犁锄”,如果勤奋读书,也能够成为“公与相”。所以陆唐老讥刺韩愈“骇目潭潭之居,掩鼻虫蛆之背,切切然饵其幼子以富贵利达之美”[3]1015,陆象山批评韩愈“初头俗了”[3]1015。
然而也不乏学者为之辩护,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承认韩愈的功利性,肯定这种功利性。瞿佑就先肯定朱熹的说法,又肯定韩愈的做法:“朱子所以责备者如是,乃向上第一等议论。俯而就之,使为子弟者读此,亦能感发志意,知所羡慕趋向,而有以成立,不陷于卑污苟贱,而玷辱其门户矣。韩公之子昶,登长庆四年第,昶生绾、衮,绾咸通四年、衮七年进士。其所成立如是,亦可谓有成效矣。”不管怎么说,韩愈的教育效果是显著的。程学恂说:“教幼子止用浅说,即如古人肄雅加冠,亦不过期以服官尊贵而已,何尝如熙宁、元丰诸大儒,必开以性命之学,始为善教哉?此只作一通家常话看,绝不有意自见,而自有以见其为公处。‘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云云,岂真称羡语。少陵《七歌》云:‘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当与此参看。”[3]1016教育有规律,教小孩就应该是教小孩的方法,要用“浅法”,不能拿“性命之学”这样高深的命题去教育小孩。黄震更干脆:“亦人情诱小儿读书之常,愈于后世之伪饰者。”第二类是认为这两首诗不仅仅是“诱以利禄”,还有“行道忧世”的意义,甚至不承认这两首诗有“诱以利禄”的内容。王元启说:“《考异》云:‘《上宰相书》所谓行道忧世者,此诗则已不复言矣,其本心何如哉?’愚谓‘峨冠讲唐虞’及‘考评道精粗’等句,皆行道忧世之心所寓也。至于歌诗,特等戏剧,聊取讽口悦耳而已,具行道忧世之心者,不必时形齿颊也。如以辞而已矣,则如持筹钻核之徒,但使口不言利,即当以廉士推之乎?以此论人,徒使巧于言者务为矫辞欺世,而坦衷之士,反至无地自容。”[3]957-958就对朱熹的看法不以为然。郑珍评《示儿》诗说:“东坡论此诗所示皆利禄事,浅视诗旨也。读开门一段,是所指为利禄者,深玩之,诗言身为卿相,持国钧轴,而与同官往来,止以酒食征逐,博槊相娱乐,所为何如乎?则玉其带,金其鱼,峨其冠者,皆行尸走肉耳。其所讲之唐虞,亦止口中仁义,即公所云‘周行俊异,未去皮毛’者也。酒食联下接云:‘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郑重作一指点,语似熟眼,齿实冷极,重言其官职,正轻哂其所为,所为赞扬甚于怒骂也。不然,上言‘无非卿大夫’足矣,又着此二语,津津不置,不重复无谓耶?观又问四句,言过从讲道者,唯有张、樊,则自两人而外,皆无一可与言者。愈见上文所云,并非艳于利禄,夸诱符郎也。坡公特未细思耳。”[3]958郑珍的看法多少有些牵强。今人朱晓蓉《韩愈〈示儿〉诗考辨》认为:“示儿诗背后是诗人对家族的爱和责任、他的理想的生活模式,以及他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借此可以还原一个重亲情重责任不伪饰,既畏人命又积极有为不离世间常情又立志为圣的真诚文人形象。”[5]站在当代人本主义的立场上肯定了韩愈。第三类是站在学术的角度看待韩愈。赵翼说:“《示儿诗》自言辛勤三十年始有此屋,而备述屋宇之垲爽,妻受诰封,所往还无非卿大夫,以诱其勤学。此已属小见。《符读书城南》一首,亦以两家生子,提孩时朝夕相同,无甚差等,及长而一龙一猪,或为相公,势位赫奕,或为马卒,日受鞭笞,皆由学与不学之故。此亦徒以利禄诱子,宜宋人之议论其后也。不知舍利禄而专言品行,此宋以后道学诸儒之论,宋以前固无此说也。观《颜氏家训》、《柳氏家训》,亦何尝不以荣辱为劝诫耶?”[3]957赵翼承认宋人批评得很有道理,但也承认“宋以前固无此说也”,韩愈在这方面是与时代风气相契合的。最值得注意的是郑珍对《符读书城南》的评论:“陆唐老谓退之切切然饵其幼子以富贵利达之美,若有戾于向之所得者,非也。读书通古今,行身戒不义,学行并进,文质相宣,达则富贵若固有,穷则名誉不去身,为圣为贤,止是如此。论古今通理,有‘潭潭府中趋’之俗子,必无‘鞭背生虫蛆’之哲人,子孙苟贤,藏身有术,即不为卿相,亦免人仆人奴。必欲饿不任声,寒而见肘,是其时命所极,决非父母之心。若伏猎侍郎,弄麞宰相,固韩公不屑计较,于符岂有虑焉?如唐老者,吾知其必教子作木石矣。”[3]957和许多站在道德评判角度上的评论家不同,郑珍承认了人的亲情与发展,反对“教子作木石”,显得颇具现代眼光。
综上所述,韩愈教子读书的理念反映出读书的功利性目的。
二、韩愈读书的非功利性
功利性目的只是韩愈读书目的的一方面,非功利性是韩愈读书目的另一重要内容。《上宰相书》:“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着于农工商贾之版,其业则读书着文,歌颂尧舜之道,鸡鸣而起,孜孜焉亦不为利。”[4]1239《赠张籍》云:“吾老著读书,余事不挂眼。”[4]576韩愈一生勤于读书,其《杂诗》说自己“古史散左右,诗书置后前。岂殊蠹书虫,生死文字间”[4]25。韩愈元和十年写过一首诗《短灯擎歌》,“太学儒生东鲁客,二十辞家来射策。夜书细字缀语言,两目眵昏头雪白。此时提携当案前,看书到晓那能眠。一朝富贵还自恣,长檠高张照珠翠。吁嗟世事无不然,墙角君看短檠弃。”嘲笑“太学儒生东鲁客”未富贵时“夜书细字缀语言,两目眵昏头雪白”,“一朝富贵还自恣”[4]353,就把便于读书的“短檠”弃于“墙角”。读书已经内化为一种行为方式和评价方式,这种内化了的行为方式和评价方式本身就是超越于功利的。
但韩愈读书的非功利性集中体现在《答李翊书》一文中。
李翊是向韩愈求教的学子,韩愈自述其回信的理由是:“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4]1456正因为李翊“不志乎利”,所以韩愈就详述自己是如何读书作文的。
韩愈读书首在立志。何焯《义门读书记》说:“‘蕲至于古之立言’,是立志。‘戛戛其难’、‘汩汩然来’……而根却带立志。……气盛则言与声皆宜,然皆非无志者所能也,故仍收到立志上。”[6]355立志就是立言,所谓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是绝非利禄所能比拟的。一开始韩愈就站在了内圣的非功利立场上了。所以韩愈明确告诉李翊“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清沈闇《韩文论述》卷二:“此书备告翊以蕲至于古之立言者之道,而‘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是存心之旨要。”[6]356把握韩愈的思想是非常准确的。
清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读昌黎此书,其于立言之道,本末内外,工夫节候,一一详悉。”[6]355所谓“本末内外,工夫节候”,即韩愈自述读书之过程,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终身学习。韩愈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但却“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要“终吾身而已矣”。二是注重精神思想之所得,不依赖于他人之承认。“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耶?用与舍属诸人”,而是要“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韩愈写作《答李翊书》,是在贞元十七年(801年),他自述三个读书阶段的特征:第一个阶段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第二个阶段是“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第三个阶段是“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三是养气,所谓“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浩乎其沛然”是很高的修养,但不是最高的修养。清沈闇《韩文论述》卷二谈到此文时说:“非圣人之志不敢存,气不可以不养,是用功之终始。”见解是非常精当的。
韩愈在《原道》一文中说“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刘真伦认为是倡导了无功利的道德价值理性,都说明韩愈读书的非功利性的一面[7]。
三、功利性与非功利性之间的关系
功利性与非功利性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传统儒家哲学中叫做“义利之辨”,讨论得非常多。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就可看出这个问题的重要地位。
教军章《论儒家义利思想的逻辑体系及其意义》对义、利的概念进行了概括:“义首先是礼仪界限的学理性规定,是礼节仪式的抽象演化,而后被界定为严肃等级权益之分的伦理仪范。”“第二,义为‘宜’‘当’,即适宜、适当之义。此义之用大约从《中庸》开始,此后便广泛传播。……义所指称的宜与当主要在于说明人的行为的合理程度,是依托于政治伦理标准的人的社会行为规范。”“第三,义即为善,乃正确的判断与裁评行为。……这是说义是判断善与恶、当与不当、宜与不宜的标准,是对‘宜’的进一步升华和引申,也是义的文本内蕴的最终指向。”“第四,义为道德原则的总称。”“在义利之辨中,利主要是利益(物质利益),而在具体运用中,它又分为私利(个人利益)和公利(天下之利)。公利与义同语,表明先贤在处理义利关系时的基本价值取向一追求利与义的统一和一致。”[8]“义”作为道德原则统摄了以上所列四种概念,所以,在原始儒学那里,“义”作为至善代表着一种道德原则和道德理想,体现了人的自我规范和自我超越能力[9];“义”是可以带来“利”的,但当“义”“利”发生冲突时,“利”要屈居于次要地位。用王艳秋的话来说,“义以建利”和“以义制利”就是“以义为质”的两翼,在先秦儒家那里是得到了平衡的发展。然而,“义”与“利”之间的固有矛盾使得后世儒者有了不同的理解,宋代理学家的理解就是“义”的必然化与“利”的不合理性。“‘利’事实上被降低到维持生命存在的最低限度,已不具有任何道德价值,大概只有生物学意义了。所谓‘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的离奇论断即说明,人追求超出生存需要的一切行为均被视为不正当。因此,理学主张严辨义利。‘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的道德警戒显示,义利(理欲)两种价值观已背离到不复具有统一的基础,其内涵不但不具有任何可比性,而且一个的存在就是对另一个的灭绝。”这是宋儒批判韩愈读书功利性的出发点。
然而,韩愈继承的却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原儒义利观。《孟子·尽心章句下》:“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10]990《孟子·告子上》:“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岂有他哉?于己取之而已矣。体有贵贱,有大小。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10]789所以,从根本性上说,精神价值的追求和物质名誉的追求都是人们的内在需要,内在于人性之中,同样有着深刻的根据。但是,物质名誉的追求以欲望为动机,容易受外界物质条件、环境的影响,如果沉溺进去,就会丧失自我,产生始料不及的结果,从而违背精神价值的追求。精神价值可以对人的所有行为施以理智的引导、自觉的制约,清醒和理智地维护原则,把人们的欲望的满足限制于道义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承认义利之间的统一性,这是孟子义利观的先进之处。
韩愈在《孟子》一书地位提升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学者们论述已多,此不赘述。韩愈的读书目的论也是孟子义利观的具体化。韩愈被贬阳山期间曾写作了《五箴》,其中一篇是《知名箴》,谈到了读书与知名之间的关系:“内不足者,急于人知。霈焉有余,厥闻四驰。”内足与人知之间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韩愈读书的功利性在于承认了人对生理物质、名誉地位的追求,非功利性则肯定了人对仁义道德的精神追求,非功利性的一面可以确定功利的方向,因而属于更深层次的追求。沿着非功利的方向前进,可以达到功利性目的。
当前,部分大学生对待学业有直接的功利性目的,一是考试,二是就业,往往忽视了学业在人生之中的精神指引、知识支持等更加重大的意义,等于轻视了学业。部分大学生则极度重视学业的精神指引、知识支持,忽略了学业的功利性价值,导致“书呆子”的出现,适应社会能力较差。韩愈的读书目的论给我们的启示是:读书也是功利性与非功利性互相促进的,不能忽视任何一面。如果站在当前的社会现状角度上,或许读书的非功利性更值得提倡。
[1]郑国民.谈韩愈的阅读理论[J].中学语文教学参考,1999(4):25-27.
[2]廖昌胤.从《进学解》到《论学习》[J].甘肃教育学院学报,2000(2):76-80.
[3]韩愈.韩昌黎诗系年集释[M].钱仲联,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4]韩愈.韩愈全集校注[M].屈守元,常思春,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5]朱晓蓉.韩愈《示儿》诗考辨[J].佳木斯大学学报,2008(4):49-51.
[6]迟文浚.唐宋八大家广选新注集评·韩愈卷[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
[7]刘真伦.论韩愈性体道用的心性本体理论[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7(1):12-18.
[8]教军章.论儒家义利思想的逻辑体系及其意义[J].学术交流,2003(4):1-6.
[9]王艳秋.“义以建利”与“以义制利”:传统儒学义利观的二重义蕴[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3):106-114.
[10]焦循.孟子正义[M].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The purpose of HAN Yu’s reading and college students’studies
DING Enquan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Zhoukou Normal University,Zhoukou 466001,China)
That the purpose of HAN Yu’s reading had his utility and the values reflected MengZi’s opinion on right and justice.The values is the base of the utility and the utility is the result of the values.It has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HAN Yu;reading;the utility;the value;college students
I206
A
1671-9476(2011)01-0036-04
2010-10-12
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晚唐古文家孙樵研究”(2010FWX021);河南省教育厅规划项目“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大学生心理健康培育——以韩愈为例”(2010-GH-211)阶段性研究成果。
丁恩全(1977-),男,河南襄城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