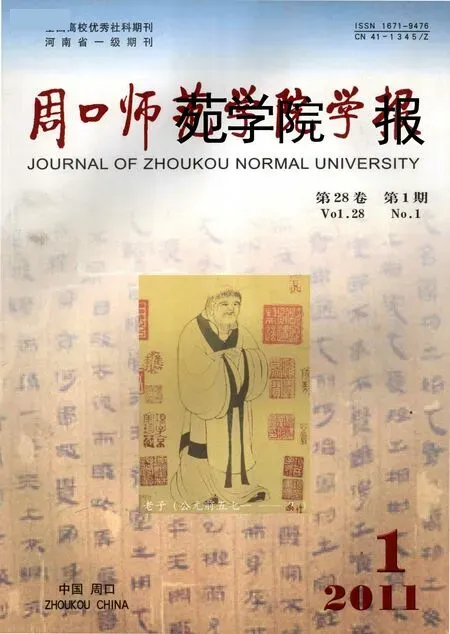论自己人纠纷与外人纠纷
2011-02-20刘燕舞
刘燕舞,桂 华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4)
论自己人纠纷与外人纠纷
刘燕舞,桂 华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4)
根据纠纷的关系结构、性质、表现形式与处理机制的不同,可以将纠纷区分为自己人纠纷和外人纠纷两种类型。从纠纷的关系结构来说,自己人纠纷主要发生于自己人内部,纠纷主体之间是一种等级关系,而外人纠纷则发生于外人之间,纠纷主体之间是一种平等关系。从纠纷的性质来说,自己人纠纷主要是因情感焦灼或情感期待不能获得满足而致,而外人纠纷则主要因利益冲突或利益侵害所致。从纠纷的表现形式来说,自己人纠纷更注重统一性,而外人纠纷更注重对立性。从纠纷的处理机制来说,自己人纠纷调解主要采用“和”的办法与“模糊处理”的策略,而外人纠纷主要采用“分”的办法和“清晰厘定”的策略。自己人纠纷通过将自己人外化可以转换成外人纠纷,而外人纠纷通过将外人自己化可以转换成自己人纠纷。自己人纠纷离法律的进入边界更远,外人纠纷离法律的进入边界更近,送法下乡遭遇困境的实质并不在于法律文本本身,而在于法律进入了本不应进入的自己人纠纷所发生的领域。
自己人纠纷;外人纠纷;区辨;转换;送法下乡
一、问题的提出
纠纷研究吸引了众多学科学者的关注,包括法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甚至历史学等学科研究者的重视,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具体来说,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纠纷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法律社会学和法律人类学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郑永流《当代中国农村法律发展道路探索》,郑永流、马协华、高其才、刘茂林等合著的《农民法律意识与农村法律发展》,苏力《送法下乡》《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强世功主编的《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何兵《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高见泽磨《现代中国的纠纷与法》,谢晖、陈金钊主持的《民间法》丛书,赵旭东《权力与公正——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权威多元》,朱晓阳《罪过与惩罚——小村故事:1931-1997》,郭星华、陆益龙等合著的《法律与社会——社会学与法学的视角》,等等。而法律社会史和法律文化研究领域亦有不少关于纠纷解决的重要作品,如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白凯《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等等[1]。这些代表性作品为我们研究纠纷提供了扎实的学术积累,开启了广泛的研究视角,展现了分学科和跨学科研究纠纷的魅力,并揭示了围绕纠纷发生和纠纷调解所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及其背后的内在逻辑。然而,即使如此,既有研究中主要探讨的是纠纷的调解机制,而对于纠纷本身是什么以及纠纷的类型则明显关注不够。因此,既有研究仍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研究空间。
正是意识到对纠纷本身及其类型研究的重要性,有学者将纠纷分为两类:一类是接触性纠纷,即因摩擦和芥蒂而起,不涉及重大的伤害、财产和侵权纷争,人们因为日常生活中紧密的接触和互助合作而发生摩擦;另一类纠纷是“侵害性纠纷”,是对他人名誉或财产的侵害而导致的村庄纠纷[2]。其后,杨华又沿此思路通过农民的公私观念的区分研究了不同的纠纷控制单位,并认为农村的调解工作大部分是自己人在处理,农村的纠纷处理就是自己人的调解。其具体方式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调动自己人的情感,使当事人产生或加深自己人的情感共鸣,从而使纠纷双方在自己人的情感世界中作出让步,达到解决事情的目的,并且还得使自己人的关系不因纠纷而破裂[3]106,[4]193。杨的研究显示了其发现问题的敏锐力,对纠纷类型的区分本身已说明其意识到既有纠纷研究的问题所在,遗憾就在于这两种类型的纠纷本质上是熟人社会内部的广义上的自己人纠纷,但杨的研究给予了本研究很大的启发。
本文的问题意识来源于我们在就纠纷问题展开田野调查时的困惑,我们在调查中总是面临婆媳纠纷、夫妻纠纷、兄弟纠纷、邻里纠纷等纷繁复杂的情况,但又总困惑于这几类纠纷之间的不同,甚至同一类纠纷内部也呈现出不同差异,比如,夫妻之间日常的争吵与夫妻离婚时的争吵,这两者之间在实践的性质上是同一种纠纷吗?同样是兄弟纠纷,在湖北大冶基本可以依靠家庭内部力量调处成功,而在浙江宁波则更容易走上法律诉讼的途径,这种虽然都是表现在兄弟之间的纠纷,但它们是同一性质的纠纷吗?在不断的调查与讨论中,我们发现,对自己人的认同程度是决定纠纷调解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进而,我们发现,虽然在同一熟人社会内部,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自己人”,而是有着明显的“自己人”与“外人”之分,而且,不同的地区,“自己人”与“外人”的关系内涵也不一样,因而也就决定了纠纷的类型实质上也不一样。据此,我们区分出两种纠纷类型,分别为发生于自己人内部的“自己人纠纷”和发生于外人之间的“外人纠纷”。本文首先将会对这两种纠纷类型进行详细区辨,然后将考察这两种类型的纠纷是如何转换的,并初步讨论这两种纠纷的区域差异,最后,我们要尝试性地借此来检视当前送法下乡遭遇困境的实质。
二、自己人纠纷与外人纠纷之区辨
我们首先有必要对自己人纠纷和外人纠纷作一简单的概念界定。所谓自己人纠纷是指发生于自己人内部的,主要基于情感焦灼或情感期待不能获得满足而致的,并以“和”的办法和“模糊处理”的策略来进行调解的争执不清的社会事实。而所谓外人纠纷,则是指发生于外人之间的,主要基于利益冲突或利益侵害而致的,并以“分”的办法和“清晰厘定”的策略来进行调解的争执不清的社会事实。对于这两种纠纷类型的区辨,我们则可以分别从纠纷的关系结构、纠纷的性质、纠纷的表现形式和纠纷的处理机制等四个方面探讨。
首先,从纠纷的关系结构来说,自己人纠纷与外人纠纷有着本质的不同。自己人纠纷只能发生于自己人内部,纠纷主体双方是一种基于血缘与人伦的等级关系。自己人的本质是生物性的血缘体,这种关系是天然的,当我们说我们是自己人的时候,我们首先是血缘意义上的。如果我们从生物性上不具备自己人的特征的时候,我们会说“把某某‘当’自己人”,这个“当”就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自己人的关系是建构的关系,而不是天然的关系。而外人纠纷则是发生于外人之间,纠纷主体双方是一种基于血缘以外的(在一个熟人社会内部则主要是地缘、趣缘和业缘等)、重契约性的平等关系。与自己人纠纷双方的不平等不一样,外人纠纷双方往往是平等的主体,因为不属于自己人范畴,外人纠纷双方也就不受制于生物性等天然生成的关系结构。比如,父亲对于儿子来说,就是血缘性的,这种结构是无法改变的。但外人纠纷双方不一样,比如张三和李四,也就是普通的村民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对等的,而非等级序列结构。
其次,从纠纷的性质来说,自己人纠纷与外人纠纷有着本质不同。我们认为自己人纠纷主要是因情感焦灼或情感期待不能获得满足而导致的。之所以如此,这与纠纷的关系结构有关,纠纷的关系结构是纠纷的性质的更为前提的因素。基于自己人是一个情感共同体,人与人之间所发生的主要是情感上的关系。因此,我们常说,家庭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其背后所强调的就是家庭这个最小的自己人共同体的情感功能特色。但在这样一个情感共同体中,人们相处时并非没有矛盾,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摩擦。而外人纠纷则因其发生的前提是外人,因此,其性质也就主要不是情感焦灼或情感期待不能获得满足,而往往是利益冲突或利益受到侵害。外人与外人之间要么不发生关系,要发生关系也不像自己人纠纷双方那样是通过情感、血缘等生物性来建立的,而主要是以利益作为链条建立关系。正是因此,当利益缠绕不清而杂乱纷繁时,外人与外人之间的关系就出现了问题,纠纷遂起。
再次,从纠纷的表现形式来说,自己人纠纷与外人纠纷亦有明显差异。自己人纠纷虽表现出冲突的一面,甚至是激烈冲突,但它更注重统一性。也就是说,自己人纠纷双方尽管在情感上发生龃龉,但最终的目标是自己人不能解体。因此,自己人纠纷表现出来的具体的纠纷事实往往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些事实的背后人们的情感矛盾。而外人纠纷则更注重对立性,因其本就不是自己人,因而也无所谓是否要统一起来。因此,外人纠纷更关键的是纠纷事实本身。也因此,没有“自己人”作为“统一性”将人与人整合起来,而仅仅是通过利益将人与人组合起来时,这种关系中的双方更多是对立关系,而非统一关系。
最后,从纠纷的处理机制来说,自己人纠纷与外人纠纷遵循着完全不同的逻辑。因为自己人是一个情感共同体,因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会发现,去调解自己人纠纷的人总是极力地调用“自己人”这个词来处理发生争执事实的双方的问题。调解的重点是要将冲突双方情感上的焦灼感融化掉,让人在感情上接受和满足对方的期待。而不是去鉴定和区分谁是谁非,谁对谁错。调解的办法往往是“和”,其突出特点就是“模糊”处理争议,放大共同点,这个最大共同点就是“自己人”。一句话,“自己人还有什么不能解决和不能想通的事吗?”调解自己人纠纷在很多时候对于纠纷双方是不平等的,因为自己人这个情感共同体单位本质上不是一个平等单位,而是一个差序格局式的单位。也就是说,自己人内部是有等级序列差异的。如当父子发生自己人纠纷时,调解的办法首先是要照顾到等级序列中的优势者,很多时候,在这种自己人纠纷中无法以“各打五十大板”的办法来处理问题。因此,我们常见的说法总是“你作为晚辈,作为儿子,你在自己父亲面前吃点亏算什么呢,都是一家人要分那么清吗?自己人能分那么清吗?”意识到自己人的另一方往往也会“算了”,“自己的儿子,认个错就可以了,何必为难自己人呢?”因而,自己人纠纷往往就在这种“自己人”的统一性前提下得以“调解了”。但这并不等于说“自己人纠纷”从此就不再有了,这一自己人纠纷调解了,将来还会有新的自己人纠纷,但新的自己人纠纷会在同样的处理机制下调解掉,正所谓“打不烂的祖宗牌”“肉烂在汤锅里”“打虎亲兄弟,上场父子兵”“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只要这个“自己人”不解体,自己人纠纷就有调解之道。
正是基于外人这个前提条件,外人纠纷的处理机制与自己人纠纷的处理机制也就不一样,又因为其冲突更多是利益纠葛而非情感期待不能满足,因此,外人纠纷的解决仅靠感情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甚至是无用的。外人纠纷的调解重点是要调整利益、界定和分清利益。所以,外人纠纷的解决机制与调解自己人纠纷中的“和”不一样,其重点是“分”,即分清楚利益,分清楚对错。它的处理策略也不是“模糊处理”的办法,而是要“清晰厘定”的办法。因此,当你张三侵犯了我李四的利益时,我要考虑的主要就是你如何赔偿我的利益,界定利益侵犯的程度,以及要赔偿的额度。进一步,我们会发现,调解外人纠纷的时候,要么捏拿准分寸,弄清外人纠纷的来龙去脉,从而公平公正地解决问题,要么从最低限度来说,只能各打五十大板,否则,另外一方就会认为偏袒,外人纠纷的调解也就会丧失公正性,调解也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外人纠纷调解不像自己人纠纷调解那样,可以通过使另一方“吃点亏”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外人纠纷中的“吃点亏”的逻辑是行不通的,因为,“这肉不是在同一个汤锅里煮”,“这牌也不是同一副祖宗牌”,简单说,就是外人纠纷的各方不属于同一个自己人的共同体。外人纠纷也不像自己人纠纷那样总是存在于自己人纠纷双方日常生活里,而是可以终结的,今天的张三和李四发生外人纠纷了,通过调解明晰各自的利益、是非后,大家大可不必再来往,也会因为外人纠纷中损害别人的权利后要进行赔偿而会在下一轮互动中有意注意,外人纠纷也就有可能不再发生。
三、自己人纠纷与外人纠纷之转换
自己人纠纷与外人纠纷一方面有着清晰的区分,另一方面也并非不能转化。自己人纠纷有时可以变成外人纠纷,外人纠纷有时可以变成自己人纠纷。自己人纠纷与外人纠纷的转换为自己人纠纷与外人纠纷的处理机制的转换提供了可能。不过,通常来说,我们要尽量不让自己人纠纷转化成外人纠纷,从而有利于我们运用自己人的感情、习惯、共识等来调解自己人纠纷。相反,我们要尽可能将外人纠纷转化成自己人纠纷,从而将原本在外人之间发生的问题内化到自己人中间来加以解决。
自己人纠纷转换成外人纠纷的机制简单说就是“自己人外化”的逻辑,也即将自己人变成外人。一般来说,只要自己人这个共同体不解体,发生在自己人内部的摩擦往往都是自己人纠纷,通过自己人的办法,不断调用感情的作用,并不断磨合是可以调解自己人纠纷的。但一旦自己人解体时,自己人纠纷往往会转换成外人纠纷,此时,仅从感情上去处理问题是无济于事的。这种情况最经典的表现模式是在夫妻之间。夫妻之间发生一些摩擦本来是经常性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自己人纠纷的解决前提就是夫妻这个自己人的共同体不解体,只要这一点没有变,我们经常看到的就是“床头吵架床尾和”“夫妻之间并无隔夜仇”的现象。举例来说,我们在某村调查时,村干部讲起一件如何调解夫妻自己人纠纷的趣事。事由是:夫妻俩在家吵了架,丈夫没有适时作出让步,妻子一气之下跑到外地的一个工厂打工,并且半年没有回家。到第七个月时,妻子很伤心,提出要和丈夫离婚的要求,这下丈夫才急了,便请村干部帮忙做工作。村妇女主任和治保主任到厂子里将女的叫回来后,便着手去调解他们夫妻之间的矛盾。但夫妻俩见面后妻子不搭理丈夫,不说一句话,村干部出面要他们谈情况时,双方互相指责。村干部听后并没有作出谁是谁非的判断,而是说知道了,晚上再来。晚上到了后,夫妻俩还互相不说话,村干部提议说要吃宵夜,要夫妻俩去张罗搞几个小菜。夫妻俩抹不开面子,妻子便在锅里炒菜,丈夫在灶下烧火。治保主任将丈夫叫出来说,等你老婆放油下锅时,你就将柴火烧猛点,这样油就会炸,你妻子忍不住就会开口,开口了事情就好办了。男人从其计,果然妻子本能地脱口而出:“你烧这么猛的火干嘛?想炸死我啊?”治保主任和妇女主任哈哈大笑进来说,你们自己吃吧,我们工作做完了,你们开口说话了就好了,一家人有什么想不开的呢。女的扑哧一笑,夫妻俩的矛盾基本就化解了。
这起自己人纠纷之所以能够调解成功,就在于夫妻这个自己人的共同体并没有解体,因此,实质上夫妻双方尤其是女方主要是要将情感上的焦灼释放出来,夫妻还是夫妻。相反,如果这一案例中的离婚闹剧最终变成事实,那么自己人这个共同体就解体了,这个时候夫妻不再是夫妻,而是互为外人,当自己人外化后,原本只是夫妻之间的自己人纠纷就会变成夫妻之间的外人纠纷。外人纠纷的解决显然是无法以调解自己人纠纷的方式来处理的,它往往更多是要明晰各自的责任和权利,如对财产的分割,对子女抚养权的争夺或讨价还价,等等,甚至为此告到法院以司法诉讼的形式解决争端,这些故事经常在上演。
外人纠纷转换成自己人纠纷的机制简单说就是“外人自己化”的逻辑,也即将外人当做自己人来处理。但外人自己化必须有一个限制条件,即外人的范围从地域上来说并不是漫无边际的,从农村的外人纠纷发生经验来看,外人能够转化为自己人的范围往往在一个熟人社会内部。也就是说,陌生人之间是无法外人自己化的。相比于自己人外化来说,外人自己化的逻辑更为复杂,其界限也更为灵活、模糊,而自己人外化简单说就是自己人解体后的必然结果。外人自己化之所以具有灵活性与模糊性,是因为其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性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关系建构的主体即外人纠纷的双方本身具有极强的主动性和权宜性。外人能否自己化受制于地域范围,因此,外人纠纷能否转换成自己人纠纷也就往往取决于人们对地域的认同。如果在同一地域内,如很多时候是在一个自然村或一个村民小组的熟人社会内部,人们有很强的“我们感”,那么外人纠纷转换成自己人纠纷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个时候,外人纠纷的调解就可以通过其成功转换成自己人纠纷后,调用自己人的资源来调解问题。所以,本来是一个利益上的外人纠纷问题,通过这种自己人的“我们感”(实际上是一种“拟我们感”),可以变成一个感情上的自己人纠纷的问题。我们在农村调查中,经常会发现村民之间很多外人纠纷最后都转换成自己人纠纷来解决,典型的如田边地角的外人纠纷,牲畜放养不当从而践踏邻居菜地等的外人纠纷,尽管有些是按外人纠纷解决的模式即界定清楚权利损害程度从而进行赔偿来解决问题的,但也有些最终以自己人纠纷的调解方式,仅仅以道歉或表示感情上的内疚而了事。而这种方式很多时候是将本来是外人的人当做自己人,只要将问题放进自己人内部,那么,一切问题总有解决的办法,因为自己人本身就是九九归一的最后的一个宗。将外人纠纷转换成自己人纠纷来解决显然是最好的处理办法,因为这种方式可以增强“我们感”,增强彼此的认同,从而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得熟人社会内部更加其乐融融。
能否将外人纠纷转换成自己人纠纷为我们理解农村的区域差异提供了一个视角。伴随现代性的进入,以理性算计为要旨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使得当前农村正经历着大量的自己人解体的过程。这种自己人的解体可以从很多方面去观察,如从自己人纠纷和外人纠纷的区分与转换来检视便是有力工具。并由此,我们会发现,不同区域的农村其能否转换的方式与程度均有较大差异。比如,我们看看兄弟之间的争执,本来从血缘与生物性的角度,兄弟是理所当然的自己人,因此,兄弟之间存在的应仅仅是自己人纠纷,而不是外人纠纷,但当前中国农村中并不是所有的村庄都遵循这种逻辑。以我们调查的湖北大冶农村为例,兄弟之间更多的只是自己人纠纷,而非外人纠纷,因此,作为自己人的兄弟关系并没有解体,相反,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我们在浙江宁波农村调查时发现,当地兄弟外人纠纷颇多,很多在大冶农村看来仅仅是自己人纠纷的事情在这里却成了外人纠纷。同样,婆媳之间的争执在这两地农村也表现出相同的逻辑。究其原因,两地农民在谈到这些事情时都有经典的说法,大冶农民说:媳妇是自己人,相反,女儿是外人,因为女儿是泼出去的水,而媳妇将来是要赡养老人的。宁波农民却说:媳妇是外人,毕竟不是自己亲生的,嫂子和弟媳也是外人,毕竟不是自己的亲姊妹。媳妇作为自己人本来应是社会性的建构,因为婆媳之间确实不存在血缘关系,嫂子与弟媳也是一样,但是这种社会性的建构能否在当前农村广泛而有效地起着作用,却因为不同的农村而有差异。也因此,不同的农村中发生在这些人之间的争执不清的事情,就可能因为作为自己人而成为自己人纠纷,作为外人而成为外人纠纷。由此一来,也就决定了完全在血缘关系之外的,家庭以外的,如邻里之间的争执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当自己人的逻辑更为普遍时,这种争执虽然是外人纠纷却可能转换成自己人纠纷处理,否则,本来可能是自己人之间的自己人纠纷也有可能转换成外人纠纷。
进一步,我们会发现,当前中国农村,有些地方自己人纠纷仍然很多,外人纠纷很少,如大冶农村。而有些地方则自己人纠纷越来越少,外人纠纷越来越多,如宁波农村。自己人纠纷仍然很多的农村说明其自己人的色彩仍很浓厚,村落的共同体性质仍较为牢固,传统保持仍较好,其现代性的色彩相较来说还比较淡。自己人纠纷越来越少而外人纠纷越来越多的农村并不是说自己人纠纷不存在了,而是很多本属于自己人纠纷的却转换成了外人纠纷,这个转换的过程其实质就是自己人的不断解体,村落的共同体性质逐渐消解,其社会性的一面不断增多,村落真正往更加“现代性”的方向过渡,但这种方向未必会是好事。
四、扩展讨论
理解了自己人纠纷和外人纠纷之差异及其转换逻辑后,我们再对当前关于送法下乡所遭遇的困境做点初步讨论。学界一些有影响力的学者已就此问题展开过深入的研究,本文的讨论既不是要否定已有的研究,也不仅仅是为既有研究提供更加完善的解释,我们的目的在于尝试性地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送法下乡遭遇困境的实质。
费孝通先生早年在其著作《乡土中国》中曾指出,送法下乡的困境在于乡土社会的既有结构及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没有发生适合于现代法律的变化,也就是说社会结构与思想观念同法律并不相适应,他说: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没有发生变化之前,就简单地把现代的司法制度推行下乡,其结果是“法治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经发生了”[5]。在费先生的观点里,这个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的最大特点就是“熟人社会”“亲密群体”和“差序格局”。苏力先生亦在这个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上思索了送法下乡的困境,他认为现代性法律制度的干预破坏了熟人社会中的社会关系,使得村庄秩序处于极其艰难的地位,一方面正式的法律制度没有能力提供村民需要的法律服务,而另一方面又禁止那些与熟人社会性质相符但却与现代法治相悖的实践[6]。董磊明先生认为最近的十多年,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巨变,今天的农村社会,已非“乡土社会”的理想类型所能准确概括,从某种意义上,今天的农村社会已经陷入了某种秩序混乱状态,这种混乱状态更是一种结构混乱,农村秩序正面临着各种因素的侵扰,村庄共同体趋于瓦解,乡村社会面临着社会解组的状态,送法下乡的困境也理应放到这种背景下进行分析和研究[7]。基于对这种结构变动的把握,董磊明等进一步提出在越来越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乡村社会,国家法律已日益成为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新农村建设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迎法下乡”已有了现实需求[8]。
以上三位学者均从各自的角度对送法下乡遭遇困境的现实作出了独到的解读,费老的研究虽然是60多年以前的观点,但放在当下中国农村现实处境中,仍不乏学理与方法论的意义。苏力亦以其敏锐的眼光洞察到了国家法与民间需求之间出现的“两张皮”现象,从而对忽视本土资源的国家法的匆忙下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不过,正如董磊明等叩问的,今天的中国农村还是那个“乡土中国”吗?中国农村经历60多年甚至上百年的现代性的持续进入,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无论是从社会结构、价值基础,还是从乡村治理的诸多方面,当下的中国农村均发生了巨变[9]。但是否如董磊明等认为的,乡村社会是否已经做好了“迎法下乡”的准备呢?“迎法下乡”是否又是乡村社会中的普遍需求呢?
我们认为,法律的进入应有其限度。也就是说,法律并不是对所有领域都适用的,在有些领域法律是必须的,而在有些领域法律并不是万能的。以万能的态度将法律渗入到乡村社会的各个领域必然会遭遇困境,这种困境并不受制于乡村社会结构本身是什么样的。法律的本质是要界定清楚个体的权利与义务,从而维持社会公平正义,以获致良好的社会秩序。但问题也就在这里,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是,一些村民之间争执不下的事情仅仅是自己人内部的纠纷,这种自己人纠纷是不能通过法律来界定或调解的。
比如父子之间因赡养而引起的争执,我们只能将其当做自己人内部的纠纷来调解。当我们将其作为法律问题进行审视时,本来是自己人内部的纠纷也就变成了外人之间的纠纷,这种自己人纠纷到外人纠纷的转换,也就使得自己人这个共同体解体,父子之间成为了外人。因此,尽管从手段上讲,法律进入本是自己人纠纷的领域可以解决问题,但却不一定能带来秩序。父亲得到儿子气冲冲地扔过来的粮食或钱财,不会是非常高兴地享受。相反,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因为自己人纠纷中的情感焦灼并没有得到释放,彼此的感情期待无法得到满足,他们接受不了本是自己人却以外人的方式扔来的嗟来之食,甚至因此而走上自杀之路。这种法律进入自己人领域虽然解决了问题却导致了悲剧的情况经常在农村上演。
自己人纠纷的本质在于其虽然有对立的一面,却因为自己人这个共同体的存在,最终要统一起来。而法律的逻辑进入自己人领域,虽可以解决自己人纠纷的对立面,却无法回归其统一性的一面。因此,法律在自己人领域的进入往往是加速了自己人的解体。反过来,在外人纠纷的领域,本应是法律进入的好地方,民众“迎法下乡”的需求主要发生在这一领域,但我们的法律有时又显得如此暧昧。最典型的莫过于对某些因外人纠纷而引起的上访事件的处理,本应厘清外人纠纷各方的权利与义务的,却经常看到我们在“讲感情”,其结果就是任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千万遍,在利益没有界定清楚和适当满足前,外人纠纷的各方一定是“上访到底”。
总之,我们有必要分清自己人纠纷与外人纠纷,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让法律正确地进入乡村社会,使送法下乡的运动得到成功实践,又能使“迎法下乡”的需求得到满足,从而既能营造法治的乡村社会,又不至于危害乡村社会原本的秩序。
在当前的纠纷研究中,人们普遍关注的是调解机制的本身,以及从中探讨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或国家法进入乡村社会后与民间社会如何调适的问题。而对纠纷本身是什么,以及纠纷类型的区分则关注极少。事实上,根据对纠纷两种类型的划分,我们发现,自己人纠纷并不同于外人纠纷,这两者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自己人纠纷是自己人内部的争执,虽有对立性,但终归会统一到自己人这个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上来,自己人纠纷的发生主要不是利益分配的问题,而更多地表现在情感的焦灼和对彼此情感的期待不能获致满足而致。相应地,自己人纠纷所对应的处理机制的核心是“和”,采用的策略是“模糊”处理。这种处理机制的特点就是要尽可能调动作为自己人的感情以及自己人认知上的共识来解决争执。外人纠纷是外人之间的争执,有对立性,却未必能统一起来。基于外人纠纷是发生在外人这个前提基础上,因而其产生的主要是利益问题,而非情感问题。相应地,外人纠纷所对应的处理机制的核心是“分”的办法,采用的策略则是“清晰”厘定,即厘清纠纷各方的权利与义务。自己人纠纷与外人纠纷并非不能转换,自己人纠纷通过将自己人外化的办法可以转换成外人纠纷,而外人纠纷则可以通过将外人自己化的办法转换成自己人纠纷。送法下乡之所以遭遇困境,就在于其本应在外人纠纷发生的外人领域起作用的,却错误地进入到自己人纠纷发生的自己人领域内,从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或者即使解决了问题,却造成了自己人的解体,从而破坏了乡村社会本来的秩序。
致谢:本文的写作受益于我们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第十五次硕博论坛上同与会者的讨论,感谢贺雪峰教授、陈柏峰、杨华、袁松、赵晓峰、宋丽娜、郭俊霞、王会等诸位博士的意见。
[1]董磊明.村庄纠纷调解机制研究的路径[J].学习与探索,2006(1):95.
[2]杨华.纠纷的性质及其变迁的原因[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10-111.
[3]杨华.纠纷的控制单位:私的程度与私的身份问题[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8(4):106.
[4]杨华.自己人的调解:从农村纠纷调解过程中的举例说明谈起[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9(2):193.
[5]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58.
[6]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7]董磊明.宋村的调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0.
[8]董磊明,陈柏峰,聂良波.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J].中国社会科学,2008(4):87.
[9]贺雪峰.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1-5.
C912.82
A
1671-9476(2011)01-0007-06
2010-09-25
刘燕舞(1983-),男,湖南平江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及其应用、农村社会学与乡村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