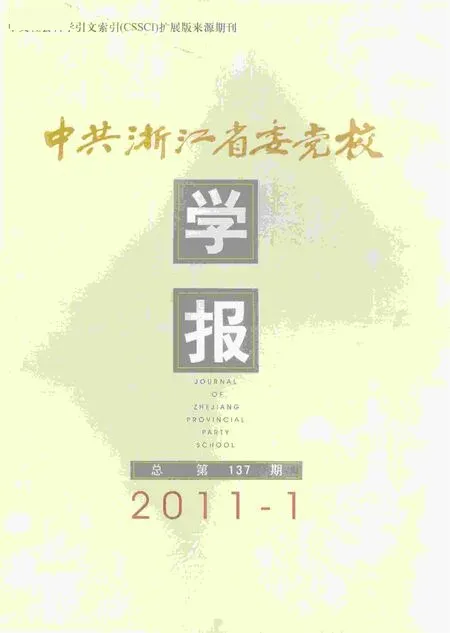公民意识的共时性考察
2011-02-19章秀英
□ 章秀英 万 斌
公民意识的共时性考察
□ 章秀英 万 斌*
公民意识作为个体对公民身份及其蕴含权利义务的主观体验,在逻辑上必然蕴含着其基本规定和属性;其内容主要包括:对政治共同体成员身份的认同和归属,由共同生活形成的“我们”概念,在心理上相互依存,彼此援助,荣辱与共;依照政治共同体法律规定所享有的权利观念与义务意识的统一;对以私人自由、安全、财富、偏好为内容的私人善与以公共理性为核心的公共善的统一。总之,特定历史时期的公民意识是其基本规定和属性的现实形态,是公民意识本质的丰富呈现。
公民意识;身份认同;权利;义务;公共善;私人善
公民意识是个体对公民身份及其蕴含权利义务的主观体验,在逻辑上必然蕴含着其基本规定和属性。此类基本规定和属性是公民意识横向沟通、对话的基础,也是把不同时代的公民贯通起来,构成公民意识纵向延续、积聚的纽带。而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公民意识状况只不过是公民意识的基本规定在历史时空中显现出的现实形态,公民通过自身的历史活动,与特定的历史环境、手段具体地联系起来,并使公民意识在特定历史时空中更充分、完整地展现自己的本质和风貌。
一、公民意识:对政治共同体成员身份的认同和归属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城邦既不是空间方面的共同体,也不是为了防止不公正的侵害行为或保证双方的贸易往来而形成的联盟,婚姻结合、宗族关系、公共祭祀和各种消遣活动都只不过是共同生活的表征,追求完美、自足生活的共同目标才是联结公民的认同纽带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8-90页。。在现代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政治国家之下,罗尔斯认为,“虽然一个良序社会被分成了不同的部分并且是多元化的……公众在政治正义和社会公正这些问题上的意见支持着公民友谊之纽带并确保社会结社之维系”②[加拿大]威尔·金里卡:《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44-345页。。金里卡也认为要把不同信仰、不同风俗的公民整合成一个统一国家的成员,并最终建立团结和信任关系,必须有一个共同的认同基础,即对共同的历史、基于共同语言的共同的社会和政治机构的归属感2。由此可见,拥有一定的地理疆界和人口只是形成政治共同体的外在形式条件,联结政治共同体稳固的精神纽带在于由共同生活而产生的“我们”认同,即自觉认同共同体成员身份,对政治共同体产生强烈的归属感,与其他公民形成集体自我意识——“我们”。“我们”在心理上相互依存,彼此援助,为彼此的成就而骄傲,为彼此的失败而羞愧;“我们”在政治共同体中依据共同认可的交往原则和谐而公正地共同生活;“我们”共同维护政治共同体的安全和稳定,在共同体危急时刻表现出团结一致,生死与共的集体情感。对政治共同体的归属感构成了政治共同体最深层和最真实的精神基础,它不仅维护了政治共同体的团结和统一,而且还孕育出公民强烈的公共责任感和服从政治共同体的义务感,并成为不同历史时期公民意识的共同特质。
公民对政治共同体产生认同和归属的基础在于一些基本的价值、需求和利益,这些基本价值、需求和利益是人类共同本性和教化在历史时空中的特殊体现,也是把社会结合成特定疆域范围内实施其权威的政治联合体的人性基础。现代心理学研究也表明,人类的基本需要可概括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各种需要之间表现出层次性,其中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最基本、最顽强的,同时也是低层次需求,获得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需要高于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而精神自我实现的需求则是最高层次的需求,个人生活的幸福体验与这些需求的满足程度相关。
可见,在人类基本的价值、需求或者根本利益中,追根溯源,维持个体生存是第一要义。任何个体生存都受制于相同的肉体需求,都需要空气、需要阳光、需要食物,这就使所有个体具有了共同的生存基础。共同的生存基础使个体之间具有了同一性,并为联合提供了可能性。而在追求共同的生存基础时,自我肯定的欲望导致不同的追求相遇、冲突、战争,甚至侵略,由此产生追求的正义性问题。由于人富有智能,若缺乏约束,则人会成为最残暴、最邪恶的动物,人的贪婪和奢欲会把人推向灭绝。正是基于对此一基本人性的认同,为了个体生命、自由、财产的权利获得安全保障,唯有联结成为一个共同体,由共同体依照公正的法则据以判决,个体的自然需要才能成为社会需要并具有实现的保障和可能。
但仅仅停留在利益的一致和生存欲望的满足,还不足以从需要满足的角度完整说明个体为何要归属于政治共同体。当个体满足了生理和安全需要后,他就会渴望有朋友、妻子(丈夫)或孩子,他渴望成为团体中的一员,避免成为孤独的人生过客,避免成为陌生人和他者,这就是爱和归属的需要,这种需要纯粹是对象性的,互动的,从而决定了孤独的个体不可能是自足的,他必须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才能获得爱与归属需要的满足。在政治共同体中,公民身份制度赋予了个体平等身份,并提供了公共交往的领域。在公共领域中,公民们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协商、互动和合作,交往过程中虽然有竞争和对立,但维持共同体存在的共识增进了公民之间的团结和友谊,频繁的交往和互动滋生了亲密感和温暖感,公民由此满足了爱和归属的需求。
尊重的需要是指个人对自己的积极情感和评价,即自己存在的价值感,包含着对自己完成任务的信心和能力,若个人丧失了自尊,那么人生就将失去尊严和意义,所有的活动都将虚无缥缈。正因如此,自尊在罗尔斯基本善的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①[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42页。。而自尊的满足往往与个体的自我概念相关,即主我如何看待客体的我。依照詹姆斯的分类,客体我分为物质自我、社会自我和精神自我,社会自我指的是我们被他人如何看待和承认,是个体的社会特性。“个体的社会自我是一种从同伴哪里获得的认可。我们不仅仅是喜欢被别人看到的群居动物,我们生来就有一种要被别人注意,被别人喜欢的倾向。”②[美]乔纳森·布朗《:自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1页。可见,社会自我无法依靠自身来完成,只有当个体自身的活动和努力获得他人的肯定和赞扬,只有在自己聪明的天资、才华、品德在与他人比较时获得的优越性中获得满足。在政治共同体的公共领域中,公民突破个人生存的有限性,满足被他人注意和肯定的渴望,体验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提升个体自尊。相反,个体若只是被动地纳入国家成员之中,那么他就只能被动地接受他人的治理,与他相关的法律、规则制定都与他无关,他的心灵只能成为他人意志的工具,在关键时刻甚至有可能被阴谋家所利用,成为毁灭国家的工具,同时也使自己处于奴隶的和臣民的状态,体验无力感和虚幻感,个人的自尊需要无法获得有效满足。
如果说个体加入政治共同体,认同公民身份,是因为政治公共生活能够满足公民生存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需要以及尊重需,是公民在对外界客观规律自觉认识基础上主动的价值判断和选择,是历史主体求善活动的体现。那么,精神自我实现的需求是一种“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也就是一种使他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①[美]马斯洛著《,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页。,因而是公民求美活动的体现。因为“在求美的活动中,求美主体摆脱了外在目的约束和利害欲念的限制,甚至把自身完全融合到客体之中,达到一种陶醉状态,忘记了自身存在”②万斌著《,万斌文集》第三卷:历史哲学,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政治生活不同于哲学的沉思生活,也不同于私人领域的享乐生活,它是行动的生活,通过言说、行动,展示聪明才智和个性,在行动中改造社会。而行动会生成预想不到的奇迹,生成意想不到的事物,开创新奇的能力实际上就是行动的能力③[加拿大]菲利普·汉森《:历史、政治与公民权:阿伦特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正如黑格尔说,参加普遍活动的需要④[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51页。对人类生活具有深远意义和独立价值,政治生活使公民超越自我,完善德性,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政治生活的价值受到共和主义思想家的肯定和推崇。
当然,维系政治共同体的认同纽带并非固定不变,与人类社会交往方式和生产力水平相关,并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方式的变革而变革、发展,从发展趋势看,政治共同体将不断地由狭隘的、地方的共同体走向更大、更丰富的多元共同体。血缘共同体是政治共同体的第一种类型,血缘共同体的认同基础是血缘亲属关系(即家庭、氏族、部落),对共同祖先的崇拜和敬畏是维持血缘共同体的精神力量,共同的信仰和风俗把血缘共同体成员统一起来,因而同根同种的种族认同是血缘共同体的认同基础。由于共同血统、起源和部落的认同是排他性的,随着人类生产力和社会交往的发展,血缘共同体被地域共同体所取代。地域共同体植根于邻里关系,通过普遍的公民权而制度化,公民权创造和分离了两种认同,即对种族的认同和对国家的认同,而且把不同种族、不同起源的人整合在政治国家之下,它依然承认最初的血缘和亲属的联系纽带,但把种族纽带放置在统一的政治国家之下,并把政治认同变成最重要的认同方式。但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依然是狭隘的、地域性的,体现了人类的差异与区隔。进入新的世纪以来,全球公民社会的出现昭示着作为伦理意义的至高境界——人类共同体曙光再现,在某些方面将会实现“我们”认同扩大的全球化,即作为一个共同生活于地球的人类而连结在一起。然而,完全摒弃人类特殊性,实现普遍性和统一性的理想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依然只是美好而高尚的理想。
二、公民意识: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的统一
从制度史视野看,公民身份制度是使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得以延续的一套行为规范、价值体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制度结构⑤Engin F.Isin&Bryan Turner,Handbook of Citizenship Studies[M],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2,105.。可见,公民身份制度包括一系列规范公民的权利义务关系,相应地,公民意识的共同本质中蕴含着对公民身份制度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主观化,即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的统一。
在政治和道德的话语里,权利意识是个体对自身在物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基本需求和欲望的自我肯定。由于生命的存在和延续是人存在的第一要义,而维持肉体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体现为生命、健康、栖息地、配偶权等人性的基本需要和欲望,这类需要和欲望与人的基本属性相联系,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同时,人类在求生的过程中还体现出不同于动物的高级存在者特质——精神性存在物,人类须有尊严和有价值地生存,对个体尊严和价值的肯定必然尊重个体自我选择的能力,相信个体有能力选择最有利于自我幸福的方式,体现出对个体人格、尊严、力量的肯定,并体现为对个体自由、平等权利的欲求和意识。可见,权利意识与个体最为原始和强大的普遍欲求联结在一起,对权利的侵犯就是对人生存资格和尊严的侵犯,对其自然生命和价值的否定,个体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利益和尊严,会不惜代价地计算、谋划、争取、奋斗,体现出顽强的主体性。
当然,个体的存在不仅是一种感性的自为,而且是理性自为,不仅看到人自然需要的合理性,同时还能反思生命存在中的不足和缺陷,发现肉体需求和感性生命的有限性,并将此一反思通过主动选择和设计制度的方式解决“实然存在”与“应然存在”的矛盾。公民身份制度正是个体通过法律形式将基本权利具体化为特定的法律规范,体现为自由权、财产权等一系列的法定权利,并以国家强制力予以保障。个体一旦依据政治共同体的法律规定获得公民身份,即获得由公民身份制度赋予的依法享受的选择权和获得资格的主张权。依法享受的选择权意味着他人不得干涉,无权阻止我做出该举动,例如公民自由处置财产。而获得资格的主张权则是若我要作出某一举动,他人或组织有义务让我做出该行动,例如作为公民我有选举的权利,其他人负有不得侵犯我的选举权的义务。因而,公民权利意识体现着个体作为政治社会的创设者和能动者积极向外拓展的主体性特征,是社会历史主体借助公民身份制度形式对自身本质的展开和占有。然而,公民权利并非抽象权利,而是社会关系的范畴,“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权利的制度化最终要在更适合人自主活动的前提下历史地确定其内容,在阶级社会中呈现出强烈的阶级性。正因如此,公民权利意识受特定社会规范、制度的塑造,在长期的劳动实践和历史文化的积累过程中体现出历史性和丰富性。
同时,公民不仅是公民身份制度的创设者,也是公民身份制度所联结的公民社会关系之网上的纽结,负有维护公民身份制度运行和政治共同体和谐的政治义务。由于公民身份制度渊源于西方,所以要准确地理解公民身份制度所蕴含的义务观念,必须从英语界中对义务的解释来理解。在英语界中,义务一般是指一种产生于一个人有意识的自愿行为的道德要求,在此意义上,承诺、同意与订约是最典型的产生义务行为②毛兴贵《:政治义务:证成与反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可见,公民义务源于公民与身处其中的政治共同体的订约行为,是公民同意因为公民身份而承担对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义务。从狭义讲,就是服从国家法律的义务,是一种回应性的或者说消极的义务,从广义讲,由于法律并不会提出政治生活的所有要求,所以公民的政治义务还包括以其他方式支持一个国家的政治机构或制度的义务,包括做一个好公民,努力捍卫自己的国家,积极参与公共政治和事务,是一种积极义务③毛兴贵《:政治义务:证成与反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由此可见,公民义务取决于公民的承诺和订约,是公民基于成员身份而获得的对政治共同体自愿担负的道德要求④[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60页。,体现了公民向里用力,自我约束和要求的道德意识。当然,公民各种义务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冲突,并导致道德两难的实践困境,而如何区分各种义务的优先性,即将公民政治义务看做是“初确义务”还是“最终义务”⑤“初确义务”是指有条件的义务或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的义务,其约束力是有条件的,有可能被其他的义务或道德要求所推翻或压倒。而“最终义务”是指“考虑了所有条件的情况下的义务”,是绝对的义务。参见毛兴贵编著《:政治义务:证成与反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不仅是区分专制与民主政治体制的重要标志,同时也体现出公民意识发展的历史差异。
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公民身份制度的“一体两面”,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一方面,公民享受权利须以履行义务为前提。权利意味着益处,包括物质利益以及和平、稳定等精神利益,这种益处单纯依靠个人无法获取,必须参与到正义且互利的社会合作事业中。由于人性的自利,为了保持公平,避免搭便车现象,政治共同体通过法律制定义务条款,强制所有公民为自己享受的权利而公平承担负担——履行义务,以保证社会合作事业的顺利进行,保证公民权利实现的可持续性。换而言之,公民权利不是抽象的人权,在其现实性上以政治共同体成员身份为前提,失去政治共同体的保护,单纯个体的存在根本无法产生任何权利,因而维护政治共同体的存在,缴纳赋税,为了保卫共同体安全而服兵役,特定时候牺牲个人自由、甚至生命的义务逻辑地包含在公民权利中。另一方面,公民履行义务的基础在于公民权利的享受。公民之负有对政治共同体的义务,归根结底是因为政治共同体保护公民个人利益以及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此一前提自然导引出公民对政治共同体的义务界限,即公民的基本人权是履行公民义务的合理性限度和范围。
一旦公民意识到义务与权利内在统一,两者须臾不可分离,就易超越于获得保护的个人私欲,找到自己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自我意识,找到自己在共同体中的价值和尊严,培养对共同体的挚爱之情,培养对共同体的责任感,进而培育了公民美德,并使公民生活保持了活力和生命意义。然而,在迄今为止的公民身份制度发展中,权利义务的统一并非均衡。古典公民身份制度是等级社会的组织工具,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群体社会特质不仅使社会成员权利义务平等意识未树立,而且强调义务观高于权利观,个人对城邦履行的义务是一种最终义务(conclusive bligation)。在现代社会,权利义务平等观念正逐渐成为公民的主导意识,但权利、义务的分离现实使特权观念和臣民意识无法抹去。并且,权利被视为王牌①转引[英]杰弗里·托马斯著《:政治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4-195页.,人权成为衡量人类行为的普遍性评判标准,是典型的权利本位意识,而政治义务一般被看成是“初确义务”。由此可见,公民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的统一是历史的、动态的,随着公民身份制度的变迁而变迁,表征着人类主体性的发展状况。
三、公民意识:公共善和私人善的统一
彼得·雷森伯格指出,Citizenship的传统“是公共的善一直都不得不与私人的善讨价还价和妥协退让的历史。”②P.Riesenberg,Citizenship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2,p.xvii,xvii,272,xv.这只揭示了事物的一个方面,即肯定了公共善和私人善相互冲突的一面,还没有揭示出私人善与公共善相互统一的一面。事实上公民身份的历史是公共善与私人善相互对立,相互统一,处于动态平衡的历史,而作为此一现象主观化的公民意识也是公共善和私人善的对立统一。
私人善是私人的益处,其基本内容包括自由、机会、收入、财富、安全、信仰、偏好等。公共善是维持政治共同体有序存在的公共理性,是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公共利益,为政治共同体中所有成员提供公共益品和益处。当公民在确定自身行动时,通常以私人善的实现为优先目标,并据此评估各种选择对其私人生活的意义,合理地选择有利于私人利益最大化,有利于个人财产、生命、自由、生活方式保障的行为方式。而公共善要求公民从普遍性而非个人的特殊性出发,遵从社会正义观念,以政治共同体至高利益为念,维持共同体的团结、和平与利益,甚至在适当的时候要牺牲私人善,例如约束个体的自由,放弃公民的财产甚至生命权,以实现公共善,在此意义上,私人善与公共善是对立的。
但是,公共善并非否认、搁置私人善,更不是压制私人善的实现,而是与私人善相互促进,辨证统一:
首先,公共善为私人善提供物质环境和条件,是私人善实现的中介。私人善包括维护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等需要的实现要求有一定的物质环境和条件,包括保护环境以保持洁净的空气;对外防御异邦人的奴役和征服,对内防止分裂和派系斗争,维护和平与秩序;促进国家工业、贸易等公共益品。由于个人存在的有限性,每个单独的个体根本无法获得和生产此类公共物品,唯有通过政治共同体的中介,通过公民的社会联合,由各个特殊性的单个美德、才能、工作汇成政治共同体的公共生活,共同创设公共善,从而使每个人既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又从政治共同体中获得更大的善。在此过程中,公共善不仅充当了个体的自由、生命、财产等私人善实现的中介,而且为私人善创设了物质环境和条件。由此可见,私人善只有在现实的政治共同体中,在公共善中才是可欲的。
其次,公共善并非是抽象、虚幻的,而是私人善的汇聚,体现着私人善的集体意志和理性。个体存在的社会性要求个体必须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参与多种形式的社会合作,而社会合作的实现要求个体遵循互惠的原则,以某种适宜的方式,共享利益,公平负担。对社会合作的普遍欲求促使个体改变自身的任性,服从理性,自我约束私人善的欲求,尊重他人同等的自由、平等和权利,将私人善的实现蕴含到公共善的目标之中,并且通过自身的社会活动,共同创设公共善,与其他公民共同享有政治共同体提供的公共利益和共同利益。可见,公共善并非先验地存在于政治共同体中,而是现实的公民个体主动发起、组织和创设而成,是私人善的共识和汇聚,体现着私人善的集体意志。在此一关系中,公民个体是公共善实现的调节者、控制者。因而,离开私人善,公共善将失去支撑而导致虚幻。
最后,公共善克服了私人善的局限性和短视,并使政治共同体获得和谐与稳定。当私人善指向公共领域,分配由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以及负担时,由于私人善要求每个公民从自利原则出发,寻求付出最少,得到最多,尽可能享受更多的利益,承担更少的负担,若任由私人善成为政治共同体的至高法则,则各个相互冲突的私人善会导致社会的对立甚至战争状态。而公共善则以政治共同体的整体利益为上,对私人善进行了必要的理性规范,限制私人善的随意性、任性和破坏性,进而维护政治共同体的和谐。在现实中,公共善的伦理实体——国家这一普遍性机构制定法律,并据此规定、协调着各个特殊私人善的要求,通过维护为各个公民所接受的正义原则,运用国家强制力量使私人善获得规范和实现。
当然,公共善和私人善的辩证统一并非抽象的,而是社会的、历史的。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为了保证城邦的安全、稳定和繁荣等公共善,被现代人视为弥足珍贵的私人善,例如婚姻、宗教信仰自由受城邦管辖,私人善领域狭小。与此相应,在公民意识中,公共善是至善的体现,私人善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公共善,强调公共精神和公民美德。在现代民族国家,人民主权原则肯定了人民在本体上优先于国家,国家的职能逻辑地成为保护公民在法律规定的界限内合理地追求幸福生活的有效工具,公共善成为实现私人善的手段和依据。尽管在一般情况下,国家应以公共善为政治决定的正当理由,且须对私人善进行限制和规范。例如为了保障政治国家的安全和秩序,要求公民放弃部分自由和偏好,包括转让自己的财产,开放私人空间,限制自由,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和个人的偏好不至于超越公共善的边界等。但总体而言,个人自由、生命、财产和安全等私人善的实现作为社会正义原则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即使以公共善的名义无故侵犯亦非正义。不仅如此,现代社会把婚姻、道德、宗教等全部置于私人领域,导致私人善领域不断扩张,公共善不断地妥协、退缩,最终留存政治公共领域只是基本人权。在此意义上,彼得·雷森伯格关于“公共善”不得不与“私人善”妥协退让和讨价还价历史的论断正确地揭示了公民身份制度的历史变迁,但仅停留于此还无法揭示私人善与公共善此消彼长的内在原因。
以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审视之,则可发现两者的张力和矛盾不过是人类主体性历史发展的结果。古典公民尚处于历史主体的初级形态——自在主体阶段,由自在主体构建的生产力主要是受自然制约的生产力,其整体的发展状况表现为“人的依赖关系”,个体要维持生存,须依赖于和服从于特定的政治共同体,否则可能失去公民身份遭受奴役,维持政治共同体存在的公共善必然高于私人善。而现代公民则是处于历史主体发展的中级形态——自立主体阶段,自立主体的存在已从合规律性向合目的性转轨,个体摆脱了各种自然和传统社会关系的束缚,有了个性的独立和按个人自由意志活动的可能性。而且,商品经济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使各种不同的私人善相互冲突且彼此不能调和,既然现代人无法确定和证明哪种偏好(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更好,也无法采用简单方法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他人,那么只有承认所有的偏好和所有文明都有存在的价值,正义的核心就是公平对待所有的偏好和文明,并把这些相互冲突的偏好、文明全都放入私人领域,隶属于私人善的范围,公共领域无权干预,导致公共领域不断地退缩,而私人领域不断扩张。由此可见,公共善和私人善的此消彼长、动态平衡是人类物质生产方式对公民意识塑造的历史体现。尽管如此,公共善和私人善的统一依然是公民意识的不变特质。
总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公民身份制度的变迁使公民意识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历史表象,并使不同时期的公民呈现出似乎截然不同的特质,形成不同的区别。但“公民意识”这一共同称号,意味着在变动不居的概念中必然存在某些不变的共同原则,共同规范,过分强调其差异性和历史性,忽视其内涵的共同原则将陷入相对主义。相反,若透过纷繁复杂的公民意识表象,考察其基本规定和属性,则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全面地把握公民意识的实质,并据以界定公民之所以为公民的普适性标准和原则,从而对我国公民教育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胡 建)
D648
A
1007-9092(2011)01-0058-06
作者简介:章秀英,浙江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万斌,《浙江学刊》主编,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公民意识测量体系与培育机制研究》(项目号:10Y JAZH12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