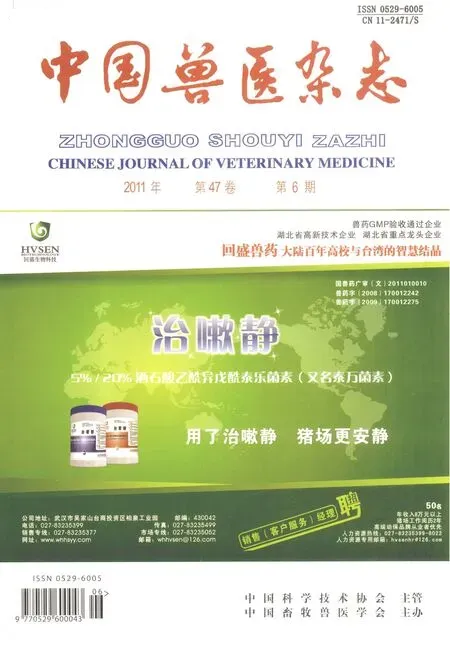口蹄疫传统疫苗和新型疫苗研究进展
2011-02-13张琳
张 琳
(1.甘肃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2.中农威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兰州 730046)
口蹄疫(FMD)是由口蹄疫病毒(FMDV)引起的急性、热性、高度接触性的传染病,有7个血清型,不同血清之间无免疫交叉保护性。口蹄疫的发生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至今尚未消灭。疫苗接种是特异性预防FMD的可靠和有效手段,安全有效的疫苗是成功的预防、控制以致最终消灭FMD的先决条件。疫苗作为预防口蹄疫的可靠手段目前正在广泛使用。近年来,随着生物工程技术的迅速发展,对亚单位疫苗、载体疫苗、基因缺失疫苗合成肽疫苗、核酸疫苗、植物反应器可饲疫苗及多表位疫苗等新型口蹄疫疫苗的研究已成为该领域的热点。
1 传统疫苗
1.1 活疫苗或弱毒疫苗 活疫苗是指经充分致弱,尚能在动物体内增殖,接种后能够引起动物发生无症状的感染,从而使机体产生免疫反应的生物制剂,又称为弱毒疫苗,常通过雏鸡化、鼠化、兔化、鸡胚化、细胞培养强化或人工诱变,使FMD田间流行的强毒或经人工接种繁殖的培养物致弱,经大量扩增病毒后,收集感染组织或细胞培养物,加入一定的保护剂、佐剂而制成的病毒制剂。1937年Negel将病毒接种于成年鼠脑内,证明病毒毒力可以被致弱。1948年Fraub和Schneider将豚鼠毒转接于鸡胚,获减毒毒株。Gillespic(1954)和Komorov(1957)将牛源毒适应于鸡胚和1日龄雏鸡,曾发表致弱毒株的初步应用报告。Gunha和Eichhom(1959)也在兔体传代成功[1]。其具有价廉、成本低及抗原谱对号、抗体持续时间长等优点,但其引起免疫动物病毒血症、长期带毒、排毒及病毒返强等缺点却一直无法克服。20世纪50、60年代许多学者用不同的毒株进行了各种途径的致弱,但迄今为止还无一个可以满足所有标准的口蹄疫弱毒疫苗株。1964年欧洲口蹄疫防治委员会决定欧洲国家不用弱毒疫苗免疫,停止了弱毒疫苗的研究[2]。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禁止使用此种疫苗,取而代之的是采用灭活疫苗。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育成O型弱毒株及A型弱毒株,并制成乳兔组织弱毒疫苗;60年代用A型兔化弱毒制造反应苗[3];70年代选育出OPK弱毒株试制疫苗,并进行A型、O型双价苗组织培养弱毒试验研究;80年代培育出温度敏感毒株,并培育了O型OP4细胞培养弱毒疫苗,这些疫苗在防止境外口蹄疫传入我国的防制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4]。
1.2 灭活疫苗 灭活疫苗是指用物理或化学方法使口蹄疫病毒丧失感染力而保留抗原性,再添加佐剂后制成的疫苗制剂。最早的灭活疫苗在欧洲于20世纪20年代出现,用动物病损组织经氢氧化铝吸附、甲醛灭活后制成疫苗。20世纪 40年代,Schm id t和Waldman等将口蹄疫病毒接种于健康牛舌皮内,等其发病后,采取病牛舌部的水疱皮和水泡液,经甲醛灭活后制成铝胶苗,获得了较高的免疫保护力。1947年Frenkel首次用牛舌皮碎块培养病毒获得成功,生产了甲醛灭活疫苗,改变了当时欧洲口蹄疫的流行态势。1962年英国Pirbright的Mowat和 Chapman等开始用乳仓鼠肾传代细胞(BHK-21)培养口蹄疫病毒,生产口蹄疫灭活疫苗,并很快商业化。1966年Lapstich和Telling等应用BHK-21细胞深层悬浮培养法制备口蹄疫疫苗,可大量培养细胞、增殖病毒和制造疫苗,20世纪80年代用大型发酵罐培养细胞、增殖病毒和制备疫苗获得成功[5],这些病毒快速、大量繁殖技术的诞生,成为口蹄疫灭活疫苗的迅速发展的基础。
在灭活剂方面,最早采用甲醛溶液灭活口蹄疫病毒抗原氢氧化铝胶混合物,但由于该混合物对细胞有毒性,且据报道,在欧美暴发的一些口蹄疫与灭活疫苗中残留活病毒密切相关[6],因此推动了后来作用于核酸的AEI和BEI作为灭活剂的研究。目前我国在牲畜口蹄疫强制免疫中主要应用细胞培养病毒的BEI灭活苗,对猪使用O型口蹄疫灭活疫苗,对牛、羊、骆驼和鹿等使用O 型-亚洲Ⅰ型口蹄疫二价灭活疫苗;其中,猪O型口蹄疫灭活疫苗(II)采用猪源口蹄疫强毒株,经BHK 21细胞增殖,应用生物浓缩技术提高疫苗中有效抗原含量,BEI灭活病毒,与矿物油佐剂乳化而制成的高效疫苗。2009年初,我国湖北、上海等地突现牛A型口蹄疫,国家口蹄疫参考实验室立即启动A型疫苗技术储备,迅速研制成功并推荐免疫A型灭活疫苗,对有效控制我国A型口蹄疫的流行做出了贡献。
2 新型疫苗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分子生物学、免疫化学和生物工程学的深入发展,对口蹄疫新型疫苗诸如合成肽疫苗、亚单位疫苗、载体疫苗及基因疫苗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
2.1 合成肽疫苗 合成肽疫苗是用化学合成法人工合成病原微生物的保护性多肽,并将其连接到大分子载体上,加入佐剂制成的疫苗,其特点是纯度高,稳定。理想的口蹄疫多肽疫苗应同时具有B细胞和 T细胞表位。Doel等1990年曾用 A、O、C血清型(FMDV)VP1序列的141-158和200-213肽段组成了40个氨基酸的合成肽,对牛和豚鼠均产生了特异的高水平抗病毒抗肽抗体[7]。由于合成肽疫苗本身的优点,极大的推动了这个领域的发展[8]。目前,我国也已成功研制出了猪O型口蹄疫合成肽疫苗,并投入生产应用于实践[9-11]。疫苗使用O型毒株的VP1结构中141~160氨基酸序列,利用化学方法人工合成这一肽段为抗原,同时为了增强疫苗的抗原性,在VP1上结合辅助T细胞表位的环状构造,克服了VP1环状多肽只有B细胞表位的缺点,借助内源性和外源性的Th位点,进一步加强了T细胞免疫,而且通过双硫键提高了环状构造的稳定性。此疫苗经实验室检验和临床试验都显示其高效的免疫力,同时无过敏等副反应,产品质量稳定,前景良好。
2.2 亚单位疫苗 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又称重组亚单位疫苗或生物合成亚单位疫苗,是利用DNA重组技术,将编码病原微生物保护性抗原的基因导入受体菌(如大肠杆菌)或细胞,使其在受体中高效表达,分泌保护性抗原肽链。提取保护性抗原肽链,加入佐剂即制成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FMDV衣壳VP1是主要的抗原蛋白,早期亚单位疫苗主要是利用各种表达系统表达VP1蛋白,或者VP1与免疫球蛋白重链稳定区scIgG基因构成嵌合体,制成疫苗。Kupper等1981年等克隆了FMDV VP1基因,将其插入到原核表达载体PL启动子的下游,实现VP1基因的原核表达,并通过间接ELISA和放射免疫试验证实了其表达产物具有抗原性[12],从而为FMDV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的研制提供了理论依据。目前,已经发现FMDV结构基因和非结构基因2A、3C串联起来表达,可以产生76S的类病毒粒子,提纯该病毒粒子,用来免疫动物,其免疫效果类似于全病毒,可产生高水平的中和抗体,能抵抗强毒的攻击[13]。除此以外,酵母和杆状病毒系统也用来表达VP1蛋白,解决VP1蛋白在原核表达系统中不被修饰加工等问题,以期提高其免疫原性。我国郑兆鑫等利用化学法合成了口蹄疫病毒VP1基因的两种抗原表位序列,将其串联后与半乳糖苷酶基因连接成融合蛋白基因在大肠杆菌中进行高效表达,提取的融合蛋白制成亚单位疫苗免疫猪后能有效地防制口蹄疫病毒感染。该疫苗已在南京药械厂完成了中试生产。
2.3 载体疫苗 随着基因工程技术的迅速发展,重组技术为开发重组FMD疫苗提供了技术支持。病毒和细菌都可用来生产口蹄疫疫苗。腺病毒的基因结构与功能研究得比较清楚。May r等[14]利用复制缺陷型的第5型腺病毒,构建了包含有FMDVP1-2A、3C蛋白前体编码序列的重组病毒。发现含有3C序列的重组病毒能有效地加工结构蛋白前体P-2A 成VP0、VP3、VP1,表达的蛋白具有类似病毒空衣壳的功能,能被免疫细胞识别,诱导动物机体产生高浓度的中和抗体。Du等[15]用腺病毒构建了含口蹄疫VP1的3个氨基酸残基表位(21~60、141~160、200~213)的重组腺病毒(rAd-GMCSF-VPe),并将其与猪的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混合(rAd-GMCSF-VP1)接种豚鼠和猪,结果能检测到特异性的体液免疫应答,高水平的 T细胞增殖,IL-4和IFN-γ。所有 接 种 rAd-GMCSF-VPe和 rAd-GMCSF-VP1的豚鼠和猪都能抵抗FMDV的攻击。
后来,研究发现痘病毒基因组、伪狂犬病病毒重组体(PRV-P1)、脊髓灰质炎病毒以及细菌(如啫酸乳酸杆菌)等均可以作为口蹄疫疫苗载体,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2.4 核酸疫苗 核酸疫苗又称基因疫苗,是将编码病原体免疫保护性抗原蛋白基因置于真核表达元件的控制下,并将其导入动物机体内,通过宿主细胞的转录系统合成抗原蛋白,从而诱导宿主产生对该抗原蛋白的免疫应答。最早开始核酸免疫研究的是Wo lff,1990年将质粒接种于小鼠肌肉,取得了较好的免疫效果。Benvenisti(2001)将口蹄疫病毒完整的结构基因P1和非结构基因2A、3CD串联起来,同时加入脑心肌炎病毒(EMCV)内部核糖体进入位点(IRES),并通过免疫荧光和免疫斑点技术检测到病毒蛋白在体外表达和加工,利用基因枪注射到猪皮肤中,部分猪获得抵抗FMDV强毒的攻击[16]。Shieh(2001)为了克服亚单位疫苗不能产生持久的免疫保护,通过基因免疫和亚单位疫苗联合免疫来增强其免疫效果,首先用含有口蹄疫病毒主要免疫原性基因VP1的质粒免疫鼠,接下来用VP1多肽偶合物(P29-KLH)刺激,免疫的鼠产生高滴度的抗体,并具有中和口蹄疫病毒活性[17]。
在利用这些DNA疫苗的同时,一些免疫增强分子佐剂也被应用进来。比如白介素和干扰素经验证也是很好的DNA疫苗分子佐剂。除了佐剂之外,补体也被构建进来。Fan等将VP1连到猪或鼠的补体上,将补体接种豚鼠,豚鼠能抵抗活毒的攻击。比较猪的补体和鼠的补体的免疫效果,连有VP1的鼠补体免疫效果更强,这为开发DNA疫苗嵌合体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核酸疫苗免疫期长,成本较低,容易构建和制备,稳定性好,抗原递呈过程与病原的自然感染相似,可通过 MHCⅠ类和MHCⅡ类分子直接递呈免疫系统,并刺激CD8+淋巴细胞产生免疫反应。研制成功的核酸疫苗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2.5 可饲疫苗 可饲疫苗是利用转基因技术将抗原基因导入植株中,获得表达抗原蛋白的植株,将该植株饲喂给动物后,可刺激动物胃肠道黏膜产生局部免疫应答进而获得全身性的免疫保护。1998年Carrillo等用表达了FMDV VP1基因的转基因拟南芥叶浸提取物腹腔注射免疫小鼠,诱导特异性抗体产生,该抗体能与VP1蛋白的第135~160位氨基酸残基的多肽和完整的FMDV颗粒反应,所有免疫的小鼠均能抵抗 FMDV强毒的攻击。2001年Carrillo等[18]在马铃薯中成功表达了VP1蛋白,动物试验证明免疫动物也能抵抗强毒的攻击。He等[19]构建的表达载体pBI121CTBVP1经农杆菌转化土豆,VP1和霍乱毒素B(CTB)的融合蛋白能在土豆中稳定表达,且具有一定的免疫原性。我国潘丽等[20]已在蕃茄中成功表达了口蹄疫结构蛋白P1-2A,3C和VP1,其叶片提取物接种豚鼠以后能抵抗活毒的攻击。除此之外,研究者还在玉米、烟草、豇豆等植物中表达FMDV的抗原保护性基因,均已初见成效。可饲疫苗使用方便、安全,为牛羊等草食动物的口蹄疫防制带来光明的前景。
3 展望
新型疫苗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目前大部分还处于实验室阶段,要使其规模化生产,应用于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新型疫苗必将大量投入使用,人类可以对口蹄疫进行有效地防控。
[1] 尹德华,韩福祥.家畜口蹄疫及其防治[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
[2] 王明俊.兽医生物制品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
[3] 程文运,张爱憎,高兰英,等.O型口蹄疫鸡胚化弱毒乳兔反应苗的研究[J].新疆农业科学,1997(3):134-135.
[4] 刘晓松.家畜口蹄疫研究概况及防制措施[J].内蒙古畜牧科学,2000,21(1):46-48.
[5] 潘丽,张永光.口蹄疫疫苗研究新进展.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口蹄疫学分会第九次全国口蹄疫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兰州: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2003:671-674.
[6] 赵启祖,谢庆阁.家畜口蹄疫疫苗简介[J].中国兽医技术,2000,30(6):43-44.
[7] Doel T R,GaleC,Do Amaral CM,eta l.H eterotypic protection indu ced by synthetic peptides co rresponding to three seroty pes of foot-and-m ou th disease virus[J].J V irol,1990,64(5):2260-2264.
[8] Greenw ood DLV,Dynon K,Kalkanidis M,etal.Vaccination against foot-and-mou th disease virus using peptides con jugated to nano-beads[J].Vaccine,2008,26(22):2706-2713.
[9] 陈方志,邱伯根,刘道新,等.猪口蹄疫O型合成肽疫苗抗体水平检测[J].动物医学进展,2009,30(8):120-122.
[10]司兴奎,戴宜发,罗汝灶,等.2种猪口蹄疫O型合成肽疫苗免疫后抗体水平的动态变化[J].畜牧与兽医,2009,41(11):70-72.
[11]张明.猪口蹄疫O型合成肽疫苗免疫效果试验[J].湖北畜牧兽医,2009(7):28-29.
[12]K leid D G,Yansura D,Sm all B,et al.Cloned viral protein vaccine for foot-and-mouth disease:responses in cattle and sw ine[J].Science,1981,214(4525):1125-1129.
[13]龚真莉,刘湘涛,刘磊,等.口蹄疫病毒P1+2A基因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J].甘肃农业大学学报,2006,41(1):14-17.
[14]Mayr G A,Chinsangaram J,Grubman MJ.Development of replication-defective adenovirus serotype 5 containing the capsid and 3C protease coding regionsof foot-and-mouth disease virusasa vaccine candidate[J].Virology,1999,263(2):496-506.
[15]Du Yijun,Jiang Ping,Li Yufeng,et a l.Immune responses of tw o recombinant adenovirusesexpressing VP1 an tigens of FMDV fused w ith porcineg ranulocytem acrophage colony-stimu lating factor[J].Vaccine,2007,25(49):8209-8219.
[16]Benvenisti L,Rogel A,Kuznetzova L,et a l.Gene gun-mediate DNA vaccination against foot-and-mouth disease virus[J].Vaccine,2001,19(28~29):3885-3895.
[17]Shieh J,Liang C M,Chen C Y,eta l.Enhancement of the immunity to foot-and-m ou th disease virus by DNA prim ing and protein boosting imm unization[J].Vaccine,2001,19(28~29):4002-4010.
[18]Carrillo C,Wigdorovitz A,Trono K,etal.Indu ction of a virusspecific an tibody response to foot andm outh diseasevirususing the stru ctural protein VP1 expressed in transgenic potato plants[J].Viral Immunol,2001,14(1):49-57.
[19]H e D M,Qian K X,Shen G F,et al.Stable expression of footand-mouth disease virusprotein VP1 fused w ith cholera toxin B subunit in the potato(Solanum tuberosum)[J].ColloidsSurf B Biointerfaces,2007,55(2):159-163.
[20]Pan L,Zhang Y,W ang Y,etal.Foliar extracts from transgenic tomato plants expressing the structural polyprotein,P1-2A,and protease,3C,from foot-and-m ou th disease virus elicit a protective response in guinea pigs[J].Vet Imm unol Immunopathol,2008,121(1-2):8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