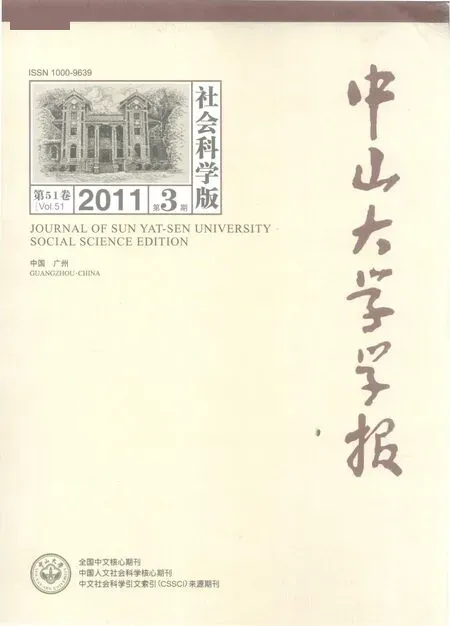汉儒之“师法”、“家法”考*
2011-02-10蒋国保
蒋国保
儒学在两汉衍为经学。经学乃儒家经典的诠释学。汉儒诠释儒家经典,恪守“师法”、“家法”。不明汉儒之“师法”、“家法”,则不明两汉经学,不明儒学在两汉的精神蜕变。问题是对汉儒所谓的“师法”、“家法”,学界缺乏应有的系统研究。从事儒学研究的学者虽然熟知汉儒恪守“师法”、“家法”,但对各自的含义及其同异却说不透彻、确切。有鉴于此,本文希望通过梳理《汉书》、《后汉书》的有关史料,分析“师法”、“家法”各自的含义及其同异,为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一孔之见。
一
虽然难以觅见有关汉儒之“师法”、“家法”的系统研究,但有关见解却一再有学者提出,而以下四种见解值得提出来讨论。
首先是皮锡瑞《经学历史》中的见解:
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师法、家法所以分者,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是师法;施家有张、彭之学,孟有翟、孟、白之学,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是家法。家法从师法分出,而施、孟、梁丘之师法又从田王孙一师分出者。施、孟、梁丘已不必分,况张、彭、翟、白以下乎!①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6页。
其次是徐复观《西汉经学史》中的所论“师法问题”。他认为:“师法”这一概念在《荀子·儒效》篇中就已出现,但汉儒之“师法”在内容上未必承自荀子,因为荀子所谓“法”是指“礼义”制度,而汉儒“不是说以师为法,而是把师所说的赋予以法的权威性,这完全是新的观念”②徐复观:《徐复观经学史二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75页。。徐氏进而指出:其一,“师法”之提出与确立,“不能早到设博士弟子员之前”;其二,“‘师法’的具体内容则是章句”③徐复观:《徐复观经学史二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75页。,“师法与章句之不可分”;其三,其他传授方式,如口头解说、传说、故训等,都“不易定以为法”,“只有博士为了教授弟子,顺着经文加以敷衍发挥,以为固定形式的章句,再加上博士在学术上的权威性地位,师法的‘法’的观念才得浮现出来”①徐复观:《徐复观经学史二种》,第76页。;其四,师法“是非常有弹性的观念”②徐复观:《徐复观经学史二种》,第76页。,博士们“有时重视,有时并不重视,有时讲,有时并不讲。其特别加以重视的,多半是把它当作排挤、统制的武器来加以应用,这在东汉更为明显”③徐复观:《徐复观经学史二种》,第76页。。
再次是张舜徽《郑学叙录》中的见解:
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博士才为五经之学所专有。当时学派很多,一经不祇一家,所以西汉五经博士,便有十四家。在当时,每一家的大师,都教授了许多学生,称为博士弟子。每个大师的经说,便称为师法;弟子们按照师法讲经,叫做守家法。④张舜徽:《张舜徽集·郑学丛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页。
复次是黄开国的《经学管窥》有专章讨论“汉代经学的师法与家法”。他先引皮锡瑞的见解,认为其得在于正确指出了“师法”在先,“家法”在后,其失在于“以有无一家之言作为师法与家法区别的根本所在”⑤黄开国:《经学管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24,25,26页。。然后表明自己的见解:“师法,实际上就是汉代经学中所讲的师说,因弟子尊奉其师说为法式,故又名师法。”这可谓“广义的师法”:“一切师说都是师法”,“无论是以经学名家的师说,还是未能以经学名家的师说,都包含在其中”,“所以,广义的师法是包含家法的,在广义的师法中,也就无所谓家法与师法之分了”⑥黄开国:《经学管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24,25,26页。。“家法”则是“特指经师传经成一家之言的师说”,在汉代经学中,具体含义有三层:第一,依五经不同而形成的家法,如言《诗》、《礼》者便称为《诗》家、《礼》家,此乃“汉代经学所言家法中最大的家法”⑦黄开国:《经学管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24,25,26页。;第二,“各经内的一家之学”,如《易》有施、孟、梁丘、京四家之学,《诗》有齐、鲁、韩三家之学;第三,“由一家之学所分出的名家者”,如《易》之施氏又有张(禹)、彭(宜)之学,孟氏又有翟(牧)、白(光)之学,梁丘氏有士孙(张)、邓(彭祖)、衡(咸)之学。“三个层次的家法之间,上一个层次包容下一个层次,下一个层次隶属于上层次,相互之间存在着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⑧黄开国:《经学管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24,25,26页。
以“师说”解“师法”、“家法”是以上各家的共识,分歧仅在于对“师说”何以是“师法”、“家法”做出了或广或狭之解释。广义的解释,如张舜徽以为“师法”即“家法”,“师法”是经学博士(师)讲授的“经说”,“家法”相对于“师法”而言,仅仅意味着博士弟子们“按照师法讲经”。皮锡瑞的解释也可以说是广义的解释,但与张舜徽稍有不同,他不是将“师法”与“家法”解释为等同关系;而是解释为继承关系:“师法”是某门学问的“师说”,“家法”则是某门学问属下之某一支的“师说”;“家法从师法分出”,所以从根本上讲,“家法”不会超出“师法”范畴,也就等于说“家法”就是“师法”。
较之皮氏、张氏,徐复观、黄开国的解释可谓狭义的解释。徐氏以为“师法与章句之不可分”,将“师法”等同于“章句”,排斥“章句”之外的其他讲授方式下的“经说”为“师法”。与此相反,黄开国将“师法”解释为“一切师说”,以为无论讲授“经”的“师说”还是非讲授“经”的“师说”(言下之意是说,即便是讲授子学,例如以讲授《老》《庄》名家者的师说,也属于“师法”)都属于“师法”。黄氏还进一步发挥了皮氏的“家法从师法分出”说,将“家法”解释为“特指经师传经成一家之言的师说”,并从三个层次揭示了“家法”的具体含义:其一,以《五经》而分的各类“师说”;其二,每一经说之内的一家之学(说);其三,由一家之学内再分化出来的“名家者”。
总括以上四家说,笔者认同四点:第一,汉儒讲“师法”在前,讲“家法”在后,换言之,西汉儒家讲“师法”,东汉儒家讲“家法”;第二,“师法”和“家法”都是“师说”;第三,“师法”与“家法”关联密切;第四,“师法”的产生与“设博士弟子”有因果关系。
也有几点是笔者所不能认同的:
首先,“一切师说”并不都是“师法”,因为“师法”是伴随着经学诠释出现的,与经学博士教授博士弟子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不是经学博士向其弟子讲授的“经说”,不属于“师法”。从经学博士主要采取“章句”的形式讲授其“经说”看,说“师法”就是“章句”有一定的根据,但“师法”不能完全等同于“章句”,盖“章句”只是“经”(五经)的诠释体式,而“师法”则是将对于“经”的某种诠释从精神上确立为不可违背、只可发挥的权威解说,因为这个解说出自师之口,而弟子必须依照着去发挥,就称为“师法”。
其次,就史料看,固然可以说西汉儒家讲“师法”,东汉儒家讲“家法”,但这决不意味着“家法”起而“师法”歇。实际的情况是,在东汉,儒家既讲“师法”又讲“家法”,是“师法”与“家法”并行。换言之,在东汉,对儒家来说,讲“师法”只是初步的身份认定,更重要的是要讲“家法”,讲“家法”才是身份的最终确定。这种重“家法”胜过重“师法”的现象之所以出现,并不是因为学术,而是因为利益,即把别家的“经说”排斥在自家之“家法”之外,从而确保一己之“经说”的权威,并立为博士官。这样做的必要性在于:照当时不成文法的规定,不守“家法”则不得立为博士官。
再次,“家法”固然是“经说”上的一家之言,但并不是任何解经上的一家之言都是“家法”,“家法”应是指发挥“师法”的一家之言,相对“师法”来说,它特指儒生(经生)恪守其亲炙之师(经师)的“经说”(师说)。
这些认识是笔者研读《汉书》、《后汉书》有关史料逐渐体悟出来的。为证明之,下面对有关史料做具体梳理。
二
《汉书》只出现过“师法”而未出现“家法”一词。由此可以推出:西汉儒者讲“师法”而尚未讲“家法”。西汉儒者所讲“师法”何意?这只有分析《汉书》的有关记载才能弄明。《汉书》使用“师法”一词者,较早见于卷75的《李寻传》:
李寻字子长,平陵人也。治《尚书》,与张孺、郑宽中同师。宽中等守师法教授,寻独好《洪范》灾异,又学天文月令阴阳。事丞相翟方进,方进亦善为星历,除寻为吏,数为翟侯言事。帝舅曲阳侯王根为大司马票骑将军,厚遇寻。是时多灾异,根辅政,数虚己问寻。寻见汉家有中衰阸会之象,其意以为且有洪水为灾,乃说根曰:“《书》云:‘天聪明’……忧责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败之机,不可不勉也。”①《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9、3604、3605—3606页。
这一记载暗指李寻虽与郑宽中同师,但他不能像郑宽中一样“守师法”。要明此记载中的“师法”何谓,当究郑宽中所守之“师法”何意。据史载,郑宽中师张山拊传小夏侯《尚书》,以博士授太子《尚书》。由此可以推出郑宽中所守之“师法”,不是仅仅狭义地指张山拊所讲授的《书》说,而是广义地指传自夏侯建门下的《书》说。《汉书·儒林传》载:“夏侯胜,其先夏侯都尉从济南张生受《尚书》,以授族子始昌。始昌传胜,胜又事同蕳卿。蕳卿者,倪宽门人。胜传从兄子建,建又事欧阳高。胜至长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传。由是《尚书》有大小夏侯之学。”②《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9、3604、3605—3606页。就夏侯建之学在思想渊源上包含倪宽、欧阳高、夏侯胜精神成分而论,则郑宽中所守之“师法”,也可以视为大小夏侯门下共通的“师法”。
以同门的“师说”为“师法”,其本义从《汉书》卷88《张山拊传》看得更明白:
张山拊,字长宾,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为博士,论石渠,至少府。授同县李寻、郑宽中少君,山阳张无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陈留假仓子骄。无故善修章句,为广陵太傅,守小夏侯说文。恭增师法至百万言,为城阳内史。仓以谒者论石渠,至胶东相。寻善说灾异,为骑都尉,自有传。宽中有儁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上吊赠宽中甚厚。由是小夏侯有郑、张、秦、假、李氏之学。宽中授东郡赵玄,无故授沛唐尊,恭授鲁冯宾。宾为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③《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9、3604、3605—3606页。
秦恭增“师法至百万言”,不是说他将张山拊的《书》说发挥扩充为一百万字,而是说将整个小夏侯门下的诠释《书》的章句发挥扩充为一百万字。颜师古早已看出这一点,故注之曰:“言小夏侯本所说之文不多,而秦恭又更增益,故至百万言也。”①《汉书》,第3606,3347—3348,3616,4170页。
西汉儒者所谓“师法”,不仅指同师门下的某一经的“经说”(师说),而且从受经者一侧来说,如某儒生从不同的老师受不同的“经说”,则他所受之诸“师说”(经说),都可谓他的“师法”。例如张禹从施雠受《易》,从王阳、庸生问《论语》,而他阐述《易》及《论语》大义又不违背这三家说,宰相萧望之就称赞张禹“经学精习,有师法”。《汉书》卷81《张禹传》讲得很明确:
张禹字子文,河内轵人也,至禹父徙家莲勺。禹为儿,数随家至市,喜观于卜相者前。久之,颇晓其别蓍布卦意,时从旁言。卜者爱之,又奇其面貌,谓禹父:“是儿多知,可令学经。”及禹壮,至长安学,从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阳、胶东庸生问《论语》。既皆明习,有徒众,举为郡文学。甘露中,诸儒荐禹,有诏太子太傅萧望之问。禹对《易》及《论语》大义,望之善焉。奏禹经学精习,有师法,可试事。奏寝,罢归故官。久之,试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郑宽中以《尚书》授太子,荐言禹善《论语》。诏令禹授太子《论语》,由是迁光禄大夫。数岁,出为东平内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征禹、宽中,皆以师赐爵关内侯。②《汉书》,第3606,3347—3348,3616,4170页。
《汉书》除了记载“守师法”,还记载了“不失师法”与“毁师法”。通过上面的梳理,“守师法”的含义已明,那么接着当考证“不失师法”与“毁师法”何意。“不失师法”说见于《汉书》卷88《胡母生传》:
胡母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亦颇受焉。而董生为江都相,自有传。弟子遂之者,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吕歩舒。大至梁相,歩舒丞相长史;唯嬴公守学不失师法,为昭帝谏大夫,授东海孟卿,鲁眭孟。孟为符节令,坐说灾异诛,自有传。③《汉书》,第3606,3347—3348,3616,4170页。
从“嬴公守学不失师法”看,“不失师法”似乎是指对胡母生、董仲舒的《公羊春秋》说都不违背,都遵为“师法”。胡母生、董仲舒是否师从相同的老师,现已难考。但史籍明载嬴公所受之《公羊春秋》学既得之胡母生,亦得之董仲舒。由此可推出,若师从不同的老师,即便他们之间并不存在师生关系,只要他们“同业“,学问上同道,如胡母生、董仲舒都学精于《公羊春秋》,那么对于受学的儒生来说,任何一家“经说”都是他的“师法”。
从字面上看,“不失师法”似乎同“守师法”,反之也可以说“失师法”就是“不守师法”。仔细推敲,“失师法”与“不守师法”又似乎存在着主观上的自觉与不自觉之分:“不守师法”一定是明知“师法”而自觉地不去遵循,“失师法”就有可能因不十分明“师法”而不自觉地违背了“师法”。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叫“毁师法”。“毁师法”的记载只见于《汉书》卷99下《王莽传》:
禄曰:“……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明学男张邯、地理侯孙阳造井田,使民弃土业。牺和、鲁匡设六筦,以穷工商。说符侯崔发阿谀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诛此数子以慰天下。”④《汉书》,第3606,3347—3348,3616,4170页。
仅从这则记载,很难明晰“毁师法”的具体含义,只可以推断这是比“失师法”、“不守师法”更为严重的现象,它直接消解“师法”权威,“令学士疑惑”,引起他们思想上的混乱。“毁师法”就等于“颠倒《五经》”,其罪严重到“宜诛”的程度。与“毁师法”相比,“失师法”、“不守师法”后果如何?这个问题可以在《汉书》卷88《孟喜传》中找到答案:
孟喜字长卿,东海兰陵人也。父号孟卿,善为《礼》、《春秋》,授后苍、疏广。世所传《后氏礼》、《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礼经》多,《春秋》繁杂,乃使喜从田王孙受《易》。喜好自称誉,得《易》家侯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又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饰《易》文……宾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为名之。后宾死,莫能持其说。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见信。喜举孝廉为郎,曲台署长,病免,为丞相掾。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为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学。①《汉书》,第3599页。
孟喜“改师法”,已非不自觉地“失师法”,而是自觉地“不守师法”,其结果是没能当上博士官。这足以表明“守师法”是汉儒博得博士官必须具备的资格,“失师法”、“不守师法”就失去了当博士的资格。
三
《后汉书》既出现“师法”一词,亦出现“家法”一词,“家法”在量上远多于“师法”。由此可以推论:东汉儒者虽“师法”、“家法”并讲,但更看重讲“家法”。东汉儒者口中,“师法”、“家法”何意?先看《后汉书》出现“师法”一词的两则记载。
其一见《后汉书》卷55《鲁恭传》所附之《鲁丕传》(鲁丕系鲁恭的弟弟):
侍中贾逵,荐丕道艺深明,宜见任用,和帝因朝会召见诸儒,丕与侍中贾逵,尚书令黄香等,相难数事,帝善丕说,罢朝特赐冠帻履袜衣一袭。丕因上疏曰:臣以愚顽,显备大位,犬马气衰,猥得进见,论难于前,无所甄明,衣服之赐,诚为优过。臣闻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相让则道不眀,若规矩权衡之不可枉也。难者必明其据,说者务立其义,浮华无用之言,不陈于前,故精思不劳而道术愈章。法异者,各令自说师法,博观其义,览诗人之旨意,察雅颂之终始,明舜禹皋陶之相戒,显周公、箕子之所陈,观乎人文,化成天下。陛下既广纳,謇謇以开四聪,无令刍荛以言得罪,既显岩穴,以求仁贤,无使幽远,独有遗失。十三年迁为侍中,免,永初二年,诏公卿举儒术笃学者,大将军邓隲举丕,再迁,复为侍中左中郎将,再为三老。五年,年七十五卒。②《二十五史》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23,128页。
要理解此中所言“师法”的含义,其关键在于须明“先师之言”与“师法”的关系。仔细分析之,可以这样理解:论辩时,凡属于“先师之言”者,不得相让;要驳斥对方也只能限定在所能驳斥的范围(非先师之言,只是论辩对方自己的说法),并且一定要“明其据说”,将自己驳斥对方的依据说得明明白白。若辩论双方都有明确的根据,“非从己出”,不是无依据地以自己的主观见解论辩,而是双方都依据“先师之言”,例如,言《易》,《易》之施氏门下都申明根据施氏说,但论辩各方说的却有别,这就叫做“法异”。所以会造成“法异”,是因为有的依据张禹、有的依据彭宜来把握施氏说。在出现“法异”的情况下,就必须“各令自说师法,博观其义”。在据“先师之言”以出现差异(法异)的情况下,必须以“自说师法”来定是非高下。可见,“先师之言”有别“师法”。这一差别,我们姑且谓之“本门师说”与“亲炙之师说”之别。例如张禹、彭宜的弟子,施氏(雠)的《易》说,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先师之说”,而张禹、彭宜对施氏(雠)的《易》说的解说,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师法”。
其二见《后汉书》卷57《吴良传》:
骠骑将军东平王苍……上疏荐良曰:“……齐国吴良,资质敦固,公方廉恪,躬俭安贫,白首一节。又治《尚书》,学通师法,经任博士,行中表仪,宜备宿卫,以辅圣政。”……每处大议,辄据经典,不希旨偶俗以徼时誉。③《二十五史》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23,128页。
《后汉书》注引《东观记》曰“良习大夏侯《尚书》”。大夏侯(胜)生活于西汉,吴良生活于东汉,则吴良不可能亲炙大夏侯(胜)学《尚书》。他只能通过间接的途径(自学或从其他学者学)学到了大夏侯《尚书》学问。可见,吴良“治《尚书》,学通师法”的记载不啻告诉我们:“师法”不是自己亲炙老师的经说,而是某门学问的“先师之言”。
上面已点破“家法”在东汉儒者那里有别于“师法”,特指自己亲炙老师的经说。现在要证明的是:在《后汉书》中,“家法”这个词,是否无一例外,都是特指亲炙老师的经说?笔者从《后汉书》中挑选九则史料来分析这个问题。
第一则,《后汉书》卷6《顺冲质帝纪》有云:
夏四月庚辰,令郡国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太学,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受业,岁满课试,以高第五人补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属,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经者,各令随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当以次赏进。①《二十五史》第2册,第26,122,136,150,150页。
章怀太子贤注:“儒生为诗者,谓之诗家;礼者,谓之礼家,故言各随家法也。”可明某儒者治《诗》有成就被称为“诗家”(《诗》方面的知识专家)、治《礼》有成就被称为“礼家”(《礼》方面的知识专家),那么所谓“各随家法”,也就具体指师从这样的知识专家学《诗》或《礼》。“各令”二字在这里不啻道明,对那些已经“能通经”的贵族子弟,要让他们各自跟随一个老师再深入学某一经,而不允许从不同的老师兼学数经。
第二则,《后汉书》卷55《鲁恭传》有云:
每政事,有益于人,恭辄言其便,无所隐讳。其后拜为鲁诗博士,由是家法学者日盛。迁侍中,数召燕见,问以得失,赏赐恩礼宠异焉。迁乐安相。②《二十五史》第2册,第26,122,136,150,150页。
鲁恭自升为“鲁诗博士”官后,学于鲁恭的人日盛,被叫做“家法学者日盛”(家法学者也就是学家法者)。这足以证明,“家法”是指亲自受业的老师的经说,而不是泛指本门“先师”的经说。第三则,《后汉书》卷60上《杨厚传》有云:
统作《家法章句》及《内谶》二卷解说,位至光禄大夫,为国三老,年九十卒。统生厚,厚母初与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岁,思令和亲,乃托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惧然改意,恩养加笃。博后至光禄大夫。厚少学统业,精力思述。③《二十五史》第2册,第26,122,136,150,150页。
统为杨厚之父,而统父名春卿。春卿善“图谶学”,临终时戒统修家藏“先祖所传秘记”,统不忘父遗言,先从周循学习其先祖所秘记的阴阳消伏之术,后又从郑伯山受“河洛书”。从杨统的学历来看,其所“作《家法章句》”,不是关于祖上所传之图谶学(家传之学),因为这应属于《内谶》解说的内容;而应是关于“河洛书”的学问,关于受自郑伯山“河洛书”说的解说。“章句”是东汉出现的一种诠释经的方式。将关于郑伯山“河洛书”说的诠释称为“家法章句”,说明“家法”就是指亲炙老师的经说。
第四则,《后汉书》卷65《郑玄传》有云:
论曰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经训而长于玄,常以为仲尼之门不能过也,及传授生徒,并专以郑氏家法云。④《二十五史》第2册,第26,122,136,150,150页。
王父即范晔的祖父宁,晋武帝时为豫章太守。范宁每论经义皆以郑玄为长,其教授弟子也就“专崇郑学”⑤《二十五史》第2册,第26,122,136,150,150页。。“专崇郑学”被说成“专以郑氏家法”。“专以郑氏家法”又是纠正“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的产物,意味着“专崇郑学”。这则记载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家法”特指某个经师而非某门诸经师的经说。
第五则,《后汉书》卷74《徐防传》有云:
上疏曰:“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汉承乱秦,经典废绝,本文略存,或无章句。收拾缺遗,建立明经,博征儒术,开置太学。孔圣既远,微旨将绝,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设甲乙之科,以勉劝学者,所以示人好恶,改敝就善者也。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议论纷错,互相是非,孔子称述而不作。”①《二十五史》第2册,第175,219,262,264,268页。
这是徐防批评当时太学不依据“家法”来考博士弟子。从上面“立博士十有四家”来推断,此所谓“家法”,具体就是指:说《易》的施、孟、梁丘贺、京房四家,说《书》的欧阳生、夏侯胜、夏侯建三家,说《诗》的申公、辕固、韩婴三家,说《春秋》的严彭祖、颜安乐两家,说《礼》的戴徳、戴圣两家。这十四人解经为业,“各自名家”,他们每一人的经说,对博士弟子来说,就叫做“家法”。太学考博士弟子,如不依据他们的经说作为标准,就叫做“不修家法”。例如考《诗》,“不修家法”应该是指不依据申公、辕固、韩婴三家中的任何一家《诗》说,而不是指未能对申公、辕固、韩婴三家一同依据。
第六则,《后汉书》卷91《左雄传》有云:
今孝亷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帝从之。②《二十五史》第2册,第175,219,262,264,268页。
上则史料说考博士弟子“不修家法”,此则说“诸生试家法”,以“家法”考诸生。根据章怀太子贤的注“儒有一家之学,故称家”,则此“家法”也就是指解经成一家之学者的经说,比如解《书》的欧阳说,或夏侯胜、夏侯建说。
第七则,《后汉书》卷108《蔡伦传》有云:
太仆四年,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雠校汉家法,令伦监典其事。伦初受窦后讽旨,诬陷安帝祖母宋贵人,及太后崩,安帝始亲万机,勑使自致廷尉,伦耻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饮药而死,国除。③《二十五史》第2册,第175,219,262,264,268页。
刘攽注曰“汉家法”之“汉”字是因为后人不明“家法”的含义而“妄加”。他指出:“诸儒各谓其师说为家法。”“各谓其师说”已点明“家法”不是师门所传的“先师”的经说,而是直接师从的老师的经说。例如,严彭祖、颜安乐的《春秋》说,均传自董仲舒,守“家法”,非只是指不违背董仲舒的《公羊春秋》说,而是指不违严彭祖或颜安乐《公羊春秋》说。就师门讲,严、颜两博士的弟子,只要不违背董仲舒的《公羊春秋》说,都可以说守“先师”的经说(西汉所谓“师法”)。但如严氏的弟子依据颜氏,或者颜氏的弟子依据严氏来发挥董仲舒的《公羊春秋》说,在东汉就叫做“不守家法”。
第八则,《后汉书》卷109上《儒林列传》有云:
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毛,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④《二十五史》第2册,第175,219,262,264,268页。
这里关于“家法”的记载,与上引第5则关于“家法”的记载大意相同。所谓“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也就是说“十四博士”各以自己的经说教授博士弟子。此“家法”,显然不是指“先师之学”,如就《易》来说,“家法”不是指田何的《易》说,而是指传田何《易》的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每一家的《易》说。虽然此四家中的每一家的《易》说都直接或间接地传自田何,但孟喜的弟子如果依据梁丘贺的解说来解《易》,这在西汉可以说不违“师法”,在东汉却肯定是违背“家法”,也即不守“家法”。
第九则,《后汉书》卷109下《儒林列传》第69下《张玄传》有云:
张玄,字君夏,河内河阳人也。少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建武初,举明经,补弘农文学,迁陈仓县丞。清净无欲,专心经书,方其讲问,乃不食终日,及有难者,辄为张数家之说,令择从所安,诸儒皆伏其多通,著录千余人。玄初为县丞,尝以职事对府,不知官曹处,吏白门下责之。时右扶风琅邪徐业亦大儒也,闻玄,诸生试引见之,与语,大惊,曰今日相遭,真解矇矣,遂请上堂,难问极日。后玄去官,举孝亷,除为郎,会颜氏博士缺,玄试策第一,拜为博士,居数月,诸生上言:玄兼说严氏、宣氏,不宜专为颜氏博士;光武且令还署,未及迁而卒。⑤《二十五史》第2册,第175,219,262,264,268页。
刘攽注曰“无宣氏学,盖下有宜氏,因误宣氏,长此两字也”,以为文中“宣氏”为后人误添。这并不影响我们的理解。张玄“少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几种家法),后补颜氏博士缺而任博士官,然不久因“兼说严氏”而被罢博士官。依颜氏为说,又“兼说严氏”,就师门讲,因不违背董仲舒说,这在西汉未必被视为不守“师法”,但在东汉就成为诸生反对张玄当颜氏博士官的正当理由。这表明兼说“数家法”就无资格当某博士官,要当博士官,只能以一种“家法”为说。要当颜氏博士官,就只能以颜氏说为说;要当严氏博士官,就只能以严氏说为说。
四
上面已证明“家法”、“师法”的本义。现在要说明的是:为什么东汉儒者更看重“家法”、严守“家法”?要弄清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弄明五经博士与博士弟子的利益关系。儒学在汉代已变为官方哲学,成为“儒术”,但它却呈现以“经学”之形式。经学是汉初变儒学为“儒术”的必然产物,它发端于文、景时期,正式产生在汉武帝初期。伴随着汉武帝的“独尊儒术”,经学适时而生,以便将“经”的大义做出合乎统治意志之需要的解释。而专掌解经事的职官就称作博士。博士制度的设立与完善,按照徐复观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文、景时期所立的杂学博士,然后是汉武帝时期所立的五经博士,最后是为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根据史料记载,汉武帝首次“为博士官置第子五十人”时在建元六年(前135年)。此后,“昭帝时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倍增之”,“元帝置博士弟子员千人”,“成帝末增博士弟子员三千人”。博士弟子一旦出现,博士与博士弟子就构成了密切的利益关系:博士凭博士弟子以巩固其博士官的地位,博士弟子凭博士弟子的身份取得当博士的必备资格。汉代著名的经学教师,其名下的学生,少则百千人,多则几千人,甚至万余人,都是因为虽入某门未必能当博士官,但若学无师门,无“师法”,便永无当博士官的可能。
由博士与博士弟子的利益关系亦不难推论,“师法”、“家法”作为两汉“经学”的特有现象①宋明儒口中的“家法”、“师法”,与汉儒所谓“家法”、“师法”,含义有本质的不同,另当别论。,其出现一定是在为五经博士官设置博士弟子之后。因为“家法”、“师法”者,说白了,就是本门经学有别于他门经学的自卫手段,是恪守本门经学传统以抗衡别门经学教义的利器。同出一门,必守同一“师法”。若不守“师法”,不但为本门所不容,甚至为别派所不齿,将直接影响前程。众人推荐孟喜补博士缺,汉宣帝因听说他“改师法”,于是不任用他为博士。这足以说明不守“师法”影响儒者前程的严重性。
就当博士官来说,从严守“师法”的必要性中又如何看出严守“家法”的必要性?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谈。首先,“家法”出于“师法”,不背离“师法”②秦恭能“增师法至百万言”,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因为若“家法”背离“师法”,秦恭不可能将其亲炙之师本不多的经说扩充为百万言;只有当亲炙之师的经说(家法)与其师的师门经说(师法)一致的情况下,他才有可能将两者糅合为一体,扩充到百万言。,故守“家法”等于守“师法”。换言之,守“师法”是守“家法”的前提,不守“师法”,就根本谈不上守“家法”。其次,守“家法”是更严格地守“师法”,是将亲炙之师的经说也纳入“师法”范畴内来严守,甚至是将守“师法”具体化为守“家法”。这表明东汉对于博士官的资格认定,不只是看其出自何门,而且更看重其亲炙何师。张玄早年学颜安乐的《春秋》学。颜安乐与严彭祖的《春秋》公羊学,都是传自董仲舒。从师门来说,无论是依从严、颜氏哪个人的经说,在西汉的儒者来看,都不违背“师法”。可张玄却因为既学从颜氏又兼说严氏而在补颜氏博士缺时遭到儒生的反对,儒生们说他既“兼说严氏”就没有资格担任颜氏博士。光武帝采纳了这一反对意见。可见,东汉儒者之守“家法”,是指严格地坚守亲炙老师的经说,所以张玄既学颜氏而又兼说严氏就被视为不守“家法”。从“师法”之不排斥兼(本门)诸师说到“家法”之排斥兼(本门)诸师说,说穿了就是“家法”较之“师法”是更为严格的身份认同。其目的就是杜绝不具备这一身份的人担任某名分下的博士官,而将担任某名分下博士官的权利只给予某博士亲授的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