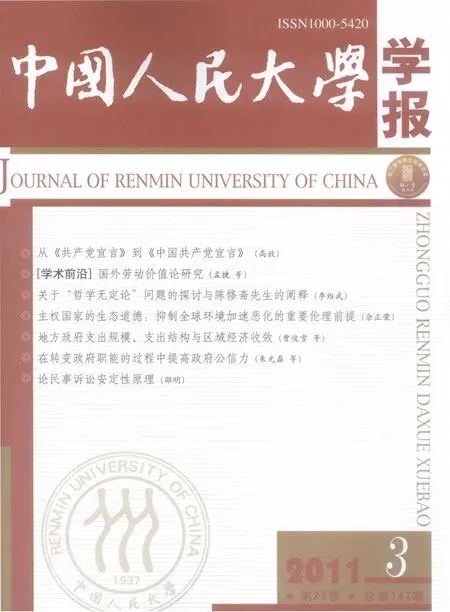权力关系视域中的社会图景——历史唯物主义的微观解释模型初探
2011-02-10王晓升
王晓升
通常,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宏观描述来展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图景。但是,如何深入到个人活动的微观领域来深入研究社会历史进程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的重大理论课题之一。在这里,我们试图从微观权力斗争的角度来说明权力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从而表明把人的微观活动的分析与宏观社会结构的分析结合起来对于进一步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可能性。
一、日常聚集中的微观权力关系
在社会生活中,所有的人都在规则化的权力关系中行动。我们所说的权力,是指人不顾一切阻碍而贯彻自己的意志并实现自己目的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在人和人相互之间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在权力关系中,有些人有更多的“权力机会”或“拒绝潜能”,有些人则具有较少的“权力机会”或“拒绝潜能”。①参见拙作《重新理解权力》,载《江苏社会科学》,2010(2)。而个人的行动就是要努力主宰这里的权力关系,争取更多的“权力机会”或“拒绝潜能”。
人们或许会说,这种泛化的权力观,不过是用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说法来描述历史,这种历史观实际上就是用动物之间的厮杀来理解人和人之间的权力斗争。然而,权力斗争是在人和人之间的依赖关系中发生的。人类历史与动物自然进化史的不同就在于,人和人之间发生了一种新的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正如哈贝马斯在谈到人类历史的起源的时候所指出的那样:“当家庭的社会结构补充了狩猎经济时,我们才能谈现代人所达到的人类的生活的再生产。这个进程延续了数百万年,这意味着动物的等级制被以语言为前提的社会规范系统所代替,这是不寻常的发展进程。”[1](P145)在动物世界,体力强的动物征服体力弱的动物,它们只有暴力上的征服这种一维的关系。而人类社会则不同,人们之间出现了一种以语言为前提的规范关系,人类开始使用社会规则来约束暴力关系。这种被社会规则所约束的暴力关系就是权力关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福柯才认为,人类社会中的规则不过是用来允许人们以暴力对抗暴力。他指出:“从冲突到冲突,直至以规则代替战争的普遍互惠,人性并没有获得任何缓慢的进步;它把暴力一一安置在规则系统中,由此,它从一种统治过渡到另一种统治。”[2](P155)谁制定了规则,谁就能够利用规则来制服其他对象。
在福柯看来,规则并没有废除暴力,不过是把暴力的使用合法化、规则化而已。福柯在这里所说的权力关系,主要是指在社会的等级结构中的权力关系。这就是说,在一定的社会机构中,一些人可以使用暴力来约束另一些人的行为。在他看来,这种约束最初是通过对身体的控制来实现的。这种对身体的控制最初是以公开暴力的形式进行的。在奴隶社会,奴隶主用公开的暴力来摧残奴隶的身体并借此来控制奴隶。福柯认为,虽然后来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的司法制度,反对公开的暴力,但实际上资产阶级所反对的不是权力的滥用,而是权力的使用没有规则或者无效率。资产阶级则用更加有规则或者有效率的方法来使用权力。福柯说:“对象变了,范围也变了。需要确定新的策略以对付变得更微妙而且在社会中散布得更广泛的目标。寻找新的方法使惩罚更适应对象和更有效果。制定新的原则以使惩罚技术更规范、更精巧、更具有普遍性。统一惩罚手段的使用,通过提高惩罚的效率和扩充其网路来减少其经济和政治代价。”[3](P99)在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的使用更加规范化、合理化。在这里,权力体现在一种温和的处罚方式之中。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历史就是权力斗争的历史,是权力斗争越来越规范化和合理化的过程。
按照福柯的分析,权力体现在对人的身体的处罚上。在人类历史上,对于身体的处罚越来越规范化、合理化,而这种规范化、合理化的过程是随着人们对人的身体的规训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传统上,权力通过对人的身体的规训而使人服从规则。福柯说:“古典时代的人发现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我们不难发现当时对人体密切关注的迹象。这种人体是被操纵、被塑造、被规训的。它服从、配合,变得灵巧、强壮。”[4](P154)在学校、家庭、法庭和监狱,人们受到了教育、训练。实际上,这种做法也显示了权力的实施使人把规则内化,从而使人自己对自己实施管理,自己对自己实施权力。于是,一种等级上的权力关系被根植于人的身体中了。一旦规则被根植于人的身体之中,人和人之间就出现了微观的权力关系。福柯对于权力关系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分析暴力对于人的规训。福柯对于权力关系的研究没有区分组织机构中的权力关系和普遍的人际关系中所存在的权力关系,而是把组织机构中的权力模式直接用于普遍化的人际关系的模式。他没有把这两种意义上的权力斗争区分开来,更没有说明这两种权力斗争之间的相互关系。[5](P108)我们可以进一步补充这其中的关系。
在被规训的身体中已经潜伏着权力关系。在日常生活中,那些习惯于监视人的人已经把监视融合到他们的躯体之中,他们看待人的方式不是审美的、道德的眼光,而是监视的眼光。他们在行为中常常是趾高气扬,目空一切,夸夸其谈。而那些长期受到监视的人,在行动中胆战心惊,畏首畏尾,胆小如鼠。于是,在日常交往中,虽然人们之间可能并不存在组织化的权力关系,但是,社会权力体系对人的规训已经把权力关系融入人的躯体之中了。在日常生活中,当社会底层的人们碰到那些地位较高的人的时候,他们唯唯诺诺,低声下气,一副奴才相。或许在某个具体的环境中,他们应该处于主人的地位,他们是主角,但是,当他们碰到了那些趾高气扬之人的时候,他们变成了仆人,变成了配角。朱时茂和陈佩斯在1990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小品《主角与配角》,就很好地说明了在身体化了的权力关系中人的日常行为特点。当然,也有人会发生人格分裂,对于一些人颐指气使,派头十足,对于另一些人则低声下气,唯唯诺诺,这是权力阶梯中的中层。如果我们用吉登斯的理论来说明的话,那就是制度化东西已经固化在人的日常行动中了。社会制度构成了一个等级化的权力体系,这种权力体系已经身体化了。这种权力关系会在人们的日常行动中体现出来。吉登斯说:“制度形式的固定性并不能脱离或外在于日常生活接触而独自存在,而是蕴涵在那些日常接触本身之中。”[6](P144)
现在,我们来考察人际互动中的权力关系。我们知道,人际互动可以用以下几个概念来描述:聚集、社会场合、非关注性互动、关注性互动(其中包括日常接触和例行常规)。按照吉登斯的分析:“聚集也可能非常松散,转瞬即逝,比如飞速交换‘以示友好的一瞥’,或者在大街上相互打打招呼。如果聚集发生在形式化程度更强些的情景中,我们就可以称其为社会场合。”[7](P147)在聚集或者社会场合中,都既包括关注性的互动也包括非关注性互动。无论是在聚集还是在社会场合中,都会存在身体化了的权力关系。在聚集中,人和人之间眼神的交换就包含了权力关系,那些社会身份略高的人对于他周围的同事或者熟视无睹,或者轻蔑地一瞥,而那些地位较低的人会以期盼的目光注视着地位较高者,期待地位较高者的关注,几乎会以祈求的目光等待着地位较高者的恩赐性的关注。地位较高者则不愿意和地位较低的人打交道,以免降低自己的身份或者地位。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更是躲之不及。地位较高者实际上也热切地期待与地位更高的人握手寒暄,他热切地抓住偶然聚集的机会而和上等人热乎一番,以在其他人面前显示出自己的高等地位。我们有时也看到,某著名教授家中会挂一张照片,原来这是他与国家的某个高官的偶然一遇而照下来的,那位高官则早已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但是,他却始终坚定不移地把这张照片放在显眼位置,以示自己在权力阶梯中的位置。当然,权力阶梯中地位较高者在不得已和地位较低者相处的时候,他总是要不断地以身体上的动作显示自己的高等地位。他的那些心不在焉的话语,他的居高临下的关怀,都是权力关系的体现。这种权力关系都体现在微妙的身体动作和语言中。当然,正如福柯所说的那样,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斗争。对于地位较高者的这种身体语言,地位较低者也会不屑一顾地扭头就跑,或在背后窃窃私语。同样,如果有一群陌生人偶然相聚,他们也会为权力而斗争。这种斗争的策略有许多。一些人会挽起手腕,秀秀自己的肌肉,以黑老大的姿势来震慑周围的人。也有一些人会相互之间称兄道弟,纠结一群从而使自己在周围的人中取得优势地位。也有一些人会穿着名牌,以一个大款的姿态来取得特殊地位。当然,他们也可以大声喧哗以吸引人的目光,或者秀几句洋文显示自己的特殊地位。所有这些都是权力斗争的策略。
而在社会场合,这种权力关系被更加微妙地制度化了。“社会场合是包含了众多个体的聚结,一般具有相当明确的时空界限,采用特定形式固定设施,比如有规可循的桌椅排放等等。”[8](P147)桌椅的排放、座次的排列、名字的先后都是权力关系的象征。社会场合的组织者对此慎之又慎。即使没有座次排列的问题,也还有谈话范围的问题。社会场合常常是一群人聚集了之后而又消散,消散之后又聚集起来。这种聚集和消散也是有规则的,而不是随意的。所有人都自觉地按照社会中的潜规则来行动。这种潜规则就是社会权力斗争的规则被身体化了。比如,同等地位的人围成一圈交谈,较高地位的人等待他人来“朝拜”,地位低的人会主动向地位高的人打招呼,主动和地位高的人握手,等等。在这里,身体感应、说话的语气、面部的表情等无不透露出人和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人们在日常的交往中,除了这些权力斗争的潜规则之外,还有许多公开的权力斗争的规则。戈夫曼认为,这种社会场合会发生众多聚集,这些聚集在其中“形成,消散,又再次形成,而个中的行为模式又往往被视为合乎礼节的,(经常还是)正式或者刻意而为的”[9](P147)。这表明,在社会场合中,人们的聚集都是有规则的,或者说是有礼节的。这种礼节不过是用来确认权力关系的,这就如同皇帝需要有加冕礼来确认他的社会权力一样,社会场合中的各种礼节同样也是确认社会权力的仪式。如果没有这种礼节,个人的社会权力就不被承认。
总之,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关系就体现在按照潜规则和显规则而进行的行动中。
二、社会场域与权力斗争
前面我们论述了一般的社会聚合中人们之间的权力斗争。这种权力斗争不仅在陌生人之间的聚集中进行,而且还在具有密切关联的人群中进行。或许他们也是陌生人,但是,他们由于特殊的社会联系而构成了一个特定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所有的人都占据一定的位置。这些占据了不同的社会位置的人构成了一定的场域。按照布迪厄的说法:“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10](P133-134)一个人可能生存于许多不同的场域中。比如,在亲属关系圈中一个人处于一定的地位,同样,在学术圈中人们之间也形成客观的关系网络,在这个关系网络中,不同的人也处于不同的社会位置。这些占据不同位置的人形成不同的权力关系。
社会场域中的人都处于一定的客观关系中,他们会不断地为改变自己在权力关系中的位置而斗争。无论是在人类历史的哪个阶段,场域内部的斗争都存在着一定的规则和潜规则。所有的人都会努力策略性地利用规则来进行权力斗争。在权力斗争中,人们都会利用不同的资源①权力资源在布迪厄那里也被称为权力资本。参见布迪厄:《国家精英》,序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来提升自己在权力阶梯中的地位。这些资源包括经济上的资源(经济资本)、政治上的资源(社会资本)或者文化上的资源(文化资本)。在不同的场域,不同的资源发挥的作用不同。比如,在经济场域,一个人可以运用经济资源参与权力竞争;在文化领域,一个人可以利用文化资源参与权力竞争;在政治领域中,社会资源就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大学教授要努力为自己的学术地位而奋斗,所有的人都努力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学术水平的竞争是教授之间学术地位竞争的根本。但是,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一种资源所能够发挥作用的范围都是被潜在地规定了的。或者说,在任何一个社会场域中,一定的资源所能够发挥的作用都是有边界的,超出了边界,这些资源就不发挥作用了,或者发挥的作用很小。比如说,本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从根本上说是由他的经济资本的力量来决定的。简单地说,如果他越有钱,那么他的社会地位就越高。但是,这也是在一定的限度内说的。在超出了一定的限度之后,其他的社会资源就会发挥作用。虽然许多企业家的经济实力都达到了同等程度,但是其社会地位却可能并不一样。有些企业家可能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比如,获得政府部门的特别认可,于是他可能获得某种特殊的政治荣誉;或者虽然他不能获得特殊的社会荣誉,但也可能努力获得某种学术荣誉,比如成为某某大学的博士;即使不能成为博士,也可以参加名牌大学的某个总裁班。政府中的官员也是如此,虽然一群政府行政人员都有同样的级别,但是,如果其中一个人在某个高校获得了博士学位,那么这也能够提高其地位。在这里,权力的竞争就是获得社会资源的竞争。
从历史上看,学术场域中的权力斗争有时和政治权力体系联系在一起。布迪厄认为,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场域,如哲学场域、文学场域都是被包含在政治权力场域中的。哲学场域内部的斗争还与整个社会场域中的权力结构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哲学场域中的斗争既和场域内部的逻辑有关,也与社会权力因素有关。哲学场域的斗争是“多元决定的”。布迪厄说:“哲学场域中这样那样的哲学竞争者与社会场域总体中这样那样的政治集团或社会集团之间,存在位置上的对应关系,通过这样的对应关系,这些哲学斗争产生了政治效果,发挥了政治作用。”[11](P145)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曾经出现的关于哲学研究中的学术性和现实性的争论实际上不过是一场哲学场域中的权力斗争。更直白地说,这就是一些人试图用学术的名义来颠覆现有的哲学场域中的权力结构。同样,各种学术的论坛、评奖等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维持权力结构和颠覆权力结构的斗争。各种社会场域中的权力斗争都不是简单地由一种权力资源所决定的。可以说,社会场域中的权力斗争是“多元决定的”。
在这种斗争中,人们不仅需要利用各种资源,而且要学会各种策略来利用资源。虽然权力斗争中需要有资源,但是有些人拥有这些资源却不会利用。如果是这样,他在权力斗争中也不会取得成功。利用社会资源是要有策略的。在学术圈中,学术地位的高低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权力。于是,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就成为权力竞争的根本。比如,某些人用网络上的炒作来提升自己的影响,某些人通过与名人的争论来提高自己的声誉,某些人借助于名人的推荐,请著名教授为自己的著作写序言,等等。如果著名教授能够吹捧自己,那么自己也就获得了特殊的学术地位。这些都是为争取学术地位而进行斗争的策略。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在任何社会中,学术资源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超出这个范围,学术资源就不发挥作用了。比如,在中国,一个人的学术地位不是完全由其学术成就决定的,还需要政府部门的承认。于是,一个人所拥有的行政资源就成为决定其学术地位的又一重要因素。一个人即使没有多高的学术成就,但如果是某个权威机构的评委,那么他就可以对于其他人的学术水准作出评判了。没有学术成就的人成为评判学术水平高低的仲裁者,于是,学术地位的竞争就转变为行政权力的竞争。
如前所说,社会权力关系是社会规则的内化。谁制定规则,谁就获得了权力。社会地位的高低是由一定的标准所决定的。在中国的学术圈中,掌握行政资源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掌握了学术的标准,他们在社会权力竞争中获得了优势地位。社会权力斗争实质上也是制定标准的斗争。谁掌握了制定标准的权力,谁就在权力斗争中获得优势地位。那些熟悉竞争技巧的人就会巧妙地运用这些规则而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在这个场域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人制定了游戏规则。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权力斗争就是争夺游戏规则的斗争。布迪厄认为,占据优势地位的人“有能力让场域以一种对他们有利的方式运作,不过,他们必须始终不懈地应付被支配者(以‘政治’方式或其他方式出现)的行为反抗、权利诉求和言语争辩”。[12](P140)占据优势地位的人在制定标准、解释标准中占据了优势地位,但处于劣势地位的人必定会对这些标准提出挑战。整个社会就是一个权力斗争的竞赛场。在布迪厄看来,社会历史就是在场域的社会斗争中发生的。如果社会场域中没有斗争,没有对于竞争规则的变革,没有对于优势地位的反抗,那么历史就停止了。在他看来,社会就是在场域的斗争中存在的,如果没有场域中的斗争,社会就会陷入到一种病态状况。
在权力关系中,某些人处于支配地位,某些人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不同的人对于权力关系就有不同的立场。布迪厄认为,个人在社会场域中的位置与个人对于权力关系的立场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在平常情况下,位置空间仍然倾向于对立场的空间起到支配的作用。”[13](P143)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人处于被支配的地位,那么他对于权力空间就会采取一种颠覆的态度,他会致力于改变权力空间的结构,而那些在权力空间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人,则倾向于维护权力空间。那些反抗现行权力关系的人或许可以被称为左派,而那些维护现行的权力关系的人就被称为右派。
三、权力的分化与规则制定者的出现
在社会空间中,个人的社会地位不仅与其所拥有的权力资源有关,而且还与其是否掌控规则有关。制定社会规则的人又是如何在社会中出现的呢?
迈克尔·曼区分了两种权力,即个人权力和组织权力。个人权力是个人相互之间所发生的权力关系。组织权力是人们在合作中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形成组织机构并在组织机构中形成的权力关系。迈克尔·曼把前一种权力关系称为等级关系,而把后一种权力关系称为层次关系。[14](P8-9)在前一种关系中,一些人由于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上的优势地位而取得了对于其他人的支配地位;在后一种关系中,一些人借助于组织结构而对组织中的其他人获得了支配地位。前一种关系常常是暂时的、非强制的;而后一种关系是固定的、强制性的。在这里,我们力图通过对个人权力和组织权力之间关系的分析来说明制定规则的人是如何产生的。从理论上说,个人权力和组织权力是密切相关的。一个人在一定的组织机构中由于自己的出色工作而获得了其他人的尊重,并由此而获得个人权力。他的这种个人权力也可能被组织所认同并获得组织权力。一旦获得了组织权力,那么他就成为制定规则的人。
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最初并不存在组织权力,而只可能存在个人权力。那么,个人权力是如何转换为组织权力的呢?一种可能的思路是,人们从人类社会最初的组织形成——家庭来考虑组织权力形成的问题。人们把最初的社会组织形式称为母权制社会,而把随后出现的社会组织形式称为父权制社会。应该说,母权制社会和父权制社会的家庭组织形式中存在着一定形式的组织权力,例如家庭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母亲和父亲。问题在于,这种家庭结构存在着一定的不稳定性。如果在父亲或者母亲组织的家庭中又有了下一代的母亲和父亲时,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处理呢?家庭的分裂必然导致父亲或者母亲的组织权力的削弱乃至丧失。最具有典型意义的组织权力关系应该用制度化的暴力组织的出现来说明,这种暴力组织主要是指在一定地域形成的国家。这里主要涉及两个相关问题:某些人是怎样获得支配其他人的生活机会的永久权力的?社会职权是怎样永久地授予集中的、独占的、强制性的权力的?这两个问题把我们引向对国家起源问题的思考。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哈贝马斯在他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曾经对各种不同理论进行了概括性的分析和说明。[15](P170-173)他既承认生产力的发展在国家政治权力形成中的作用,但又不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而强调政治权力关系的形成是在道德实践领域学习的结果。但是,他的理论无法说明一种临时性的社会职务,如他所说的“法官”,是如何最终被固定化的。
迈克尔·曼也对国家形成的各种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其中包括自由主义、功能主义和军事主义。自由主义用契约理论来解释国家的起源。功能主义从社会的功能需要出发来解释国家的出现,例如由于生产力的增长,社会财富出现了剩余,为了分配剩余产品,于是就出现了国家。军事主义则从暴力征服的角度来说明国家的产生。所有这些理论都能够从一个角度来说明国家的出现。但是,国家的出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孤立地从某个角度来说明国家的产生是不够的。尽管如此,我们又必须承认,国家的产生最终必定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必定会出现一些单个家庭所无法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需要由超家庭的组织结构来予以解决。
然而,问题在于,这种超家庭的组织结构中的权威究竟是如何被永久地确立起来的呢?迈克尔·曼紧紧地抓住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原始的集权化权威和分权化权威之间斗争的问题。他说:“在相对集权化权威和分权化权威的竞争中,尽管前者的集体性组织有令人惊讶的权力,但后者却获得了成功。”[16](P83)由此可见,虽然早期人类社会中曾经出现过一定的集权化的权威,但是这种权威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能取得稳定的地位。它的合法性总是会受到挑战。通过大量的人类学资料,迈克尔·曼证明:“社会的大部分前历史没有经历趋向分层或国家的持久运动。走向等级和政治权力的运动似乎是地方特有的,但却是可逆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是持久的。”[17](P87)由此可见,相对集权化权威的形成总是受到分权化权威的挑战。集权化权威可能在某个阶段或者某个事件中出现,但是,随后在分权化权威的挑战中可能失去其权威地位。这就是说,国家的形成过程不是线性的进化过程,而是曲折的过程,有时也会出现倒退。不仅如此,国家的形成也不具有唯一的原因,在不同的地区有其特殊的原因,我们不能用某个单独的原因来解释国家的形成。我们认为,迈克尔·曼的这个分析不仅有一定的人类学依据,而且在理论上也有一定的说服力。
在讨论了组织权力形成的历史过程之后,我们试图进一步用一个抽象的模型从理论上来说明规则的制定者的产生过程。埃利亚斯用游戏模型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讨论了组织权力的产生过程。对于这种功能主义的解释模型所存在的问题,我们暂不做讨论。
埃利亚斯在分析人和人之间的微观权力的时候区分了两人游戏中的两种不同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一个人的实力很强,另一个人的实力很弱。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强者有权力,但是弱者也有权力,如果没有权力,那么游戏就不存在了。然而由于前者太强,以至于他不仅可以控制其对手,而且可以控制游戏的结果。第二种情况是,对手之间的实力差别很小。这个时候没有人能够控制游戏的结果。在他看来,社会过程中所出现的权力关系类似于后一种游戏情况,任何人都无法最终控制游戏的最终结果。这表明,在人和人的微观权力关系中,只要人和人之间的差别被缩小到一定程度,那么,任何人都不能决定特定社会过程的最终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和人之间的微观权力关系具有博弈的特点。在社会生活中,两人游戏的情况几乎不会出现。
现实社会中的游戏是多人游戏。在多人游戏中,人和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在一系列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进行。在这里,埃利亚斯区分了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一个强者与许多弱者分别进行游戏。但是,强者与弱者之间的游戏是有限的。在弱者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强者的力量就会受到影响。第二种情况是,一个人与许多联合起来的弱者进行权力斗争。其结果类似于两人游戏的情况。第三种情况是,数个人相互之间进行权力斗争。第四种情况是,这些人分别组成了两个集团,两个集团之间分别进行权力斗争。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微观权力斗争往往是这四种情况的结合体。人就处于这些复杂的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当然,这里的集团不是组织化的集团,而是非组织化却松散勾连在一起的人群。在这里,人们之间钩心斗角、机关算尽。这种权力斗争是发生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在这个微观的网络斗争中谁都不能确定斗争的最后结果。
随着人数的增加,所有的人都无法认清游戏规模和特征,都无法理解和控制游戏,在这种情况下,层次性的游戏就会出现。原来所有的游戏者是在同一层面上参与游戏的,由于参与游戏的人数的增加,游戏者的压力增加,于是双层的游戏出现了,这就是其中一些人不再直接参与游戏,而是协调整个游戏并制定游戏规则。他们构成了第二层次的集团。这个集团比第一个层次要小,并与第一个集团相互依赖。第二集团内部人员之间也相互游戏,他们时而联合时而分裂并与第一层次发生联系。这两个集团之间的权力机会是不同的。有时他们之间的权力分配的差距很大,有时差距很小。现在,我们设想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只有第二集团的人参与游戏,而第一集团的人附属于第二集团,他们没有资格参与第二集团的游戏。第二集团的人数较少,每个人都希望根据自己在集团中的位置影响游戏的进程,他们对于游戏有较好的把握。但是,任何人,无论其权力有多大,都无法主宰整个游戏的过程。在这里,每个人“是根据相互依赖的游戏者构成的网络作出自己的举动,他的举动又构成了这个网络。这个网络里既有同盟又有敌人,既有合作又有竞争,情形错综复杂”。[18](P120)埃利亚斯把第一种情况称为寡头模型。这类似于两人游戏中,一个人非常强大,而另一个人力量较小。第二种情况是,第二集团和第一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两个集团之间的权力差距在缩小。这个模型被称为简化的民主化模型。两个游戏集团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被强化了。当然,随着社会的不断分化,社会上还会出现更多层次的游戏集团。在权力的阶梯中,每上升一个层次,人数就会减少一些,直到最高层次,其中只有少数人。这些人在权力的阶梯中占据了最高的位置。因此,无论是民主社会还是寡头统治社会,从政治权力这个维度来说,社会的权力阶梯就是一个金字塔形的。权力阶梯中的较高者就是权力斗争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四、权力斗争与阶级斗争
如果我们所描述的社会总体图景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联系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讨论权力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社会发展是在人们之间的权力斗争中进行的。这种斗争既发生在人和人之间日常生活、职业活动的微观领域,也发生在社会集团之间。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所描述的是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这种集团之间的斗争也包括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为了控制游戏规则而展开的集团斗争,这就是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之间的斗争;一种形式是为争取权力资源而展开的斗争。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斗争,都是为了争取特定集团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这就是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既是经济斗争,又是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传统上,人们只是强调无产阶级斗争的经济和政治性质,而忽视了其文化性质。实际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是为了争取身份的斗争,要求社会对于劳动者的社会价值予以承认。
阶级斗争有时在社会历史上表现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对于改变社会制度,对于在社会不同群体之间重新配置权力资源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因此,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分析社会领域中的权力斗争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在强调社会多元化的时候,否定了阶级斗争的作用,批判历史唯物主义是阶级还原论。他们认为:“两种类型的还原论妨碍了马克思主义准确把握现代类型的集体行动:第一,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还原论主张,一切具有政治意义的社会行动都导源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性的经济逻辑;第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还原论主张,最重要的社会行动者是由扎根于生产过程的阶级关系所决定的,并且所有其他的社会身份在构成社会行动者的过程中至多发挥次要作用。”[19](P442)埃里克·赖特也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的数量大为增加,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极对立的阶级观是不正确的。[20](P10)通过我们对于权力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只要社会上存在着权力关系,只要一些人掌握较多的权力资源,一些人控制着权力斗争的规则,那么就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也就是存在着阶级的差别。
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解阶级斗争问题时,把阶级关系简单化了。它或者简单地用经济标准来衡量阶级关系,或者用简单的政治权力关系来衡量阶级关系。按照这种阶级分析的逻辑,凡是掌握较多的经济资本的人就是剥削阶级,凡是掌握较多政治资本的人就是统治阶级,其他人则是被剥削阶级或者被统治阶级。同时,所有的阶级都是一个统一在一起的利益集团,似乎他们都有组织上或者情感上的联系。
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人则对这种阶级观点提出质疑和批判。他们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最大的错误就在于相信:社会能够被构想为“缝合的”,或者说完全符合规程的、整体的、被单一原则所支配的,也就是说,社会是按如此方式组织的,社会活动者的身份由社会结构所固定。[21](P67)在他们看来,社会是由许多不同的要素缝合起来的,社会是多元的、非决定性的,是按照话语的形式组成的,不存在历史的条件、联系和确定过程的可能性,只有任意并列、随机出现的偶然发生的各种事件。①参见孔明安:《论后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基础——拉克劳与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征剖析》,载《哲学研究》,2004(7);付文忠、孔明安:《‘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解读——拉克劳与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评析》,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2)。既然社会事件是任意和偶然构成的,那么社会运动就不是由确定的经济原因引起的,也不可能由工人阶级所主宰。他们强调说:“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化的特征不可改变地消解了那种政治虚构的最后基础。充满普遍主体和围绕单数形式概念化的虚构一直把社会假定为能够在某种阶级立场上被理智掌握和重构的概念结构。”[22](P2)换句话说,现代社会不存在统一的社会主体,不存在共同的阶级立场。
从我们对于社会权力关系的分析中,特别是社会权力关系的总图景中可以看到,一方面,社会权力和权力资源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因此,掌握不同社会资源的人之间必定会展开权力斗争。人的社会权力是由他在社会中所拥有的总资本决定的。拥有较多的经济资本的人会强调经济资本在社会上的重要地位,拥有较多的文化资本的人会强调文化资本在社会上的重要地位,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较少的劳动者会为体力劳动者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辩护。制定规则的人总是要保证规则的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在这里,他们之间必定会展开斗争,这种斗争就是阶级斗争,或者类似于阶级斗争。另一方面,所有人又都是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他们之间又会进行微观的权力斗争。他们之间所构成的群体往往是偶然的、随机的。这种微观的权力斗争却不是阶级斗争。我们不能用阶级斗争的模式来分析这里所存在着的权力斗争。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阶级斗争和权力斗争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说,阶级斗争是微观的权力斗争层次化的结果。在传统社会,政治权力上的层次关系的出现会导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权力关系的层次化导致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在这里,资产阶级制定了经济游戏的规则,并论证了这种游戏规则的正当性。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要否定这种游戏规则的正当性,重新制定经济游戏的规则。这种斗争就是阶级斗争。
社会的历史既是由阶级斗争推动的历史,又是由微观权力斗争推动的历史。
[1][15]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
[3][4]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5]路易丝·麦克尼:《福柯》,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6][7][8][9]吉登斯:《社会的构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0][11][12][13]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4][16][17]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8]埃利亚斯:《论文明、权力与知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9]Steven M.Buechler.“New Social Movement Theo ries”.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1995,36(3).
[20]埃里克·欧林·赖特:《阶级》,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1]杰弗里·伊萨克:《后马克思主义与新社会运动》,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6)。
[22]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