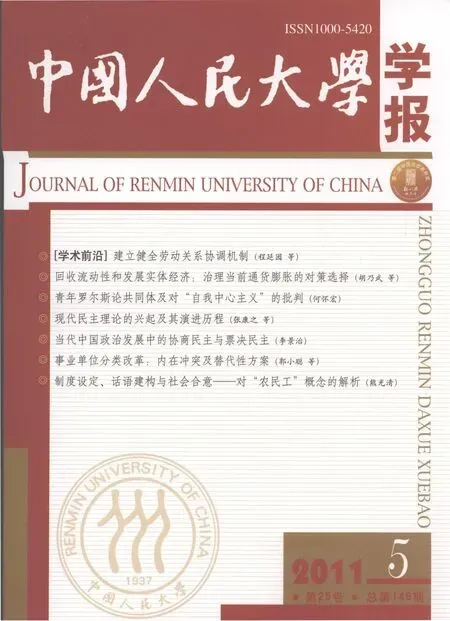韩非子与现代性——一个纲要性的论述*
2011-02-09白彤东
白彤东
一、韩非子的时代:中国向“现代化”之转变?
传统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是一个在当代中国哲学界存在广泛争议的问题。有些人承认传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同,但为了论证前者的重要,他们指出它是哲学,只不过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独特哲学传统。但是,一些批评者常常反驳说,中国思想只是不同于西方近现代思想,而与古代西方思想非常相似,比如天人感应思想与西方中世纪的思想。由此,中西思想之分就被描绘成了古今思想之别,并且,基于一种进步观念,中国思想(因为它被认为属于古代)也因此被贬低。当然,有趣的是,也有些人比如新儒家和言必称希腊与经学的中国的施斯特劳斯主义者中的一些人,在以古今之分来解释中西之别的同时,试图以论证古优于今来为中国哲学辩护。在其他地方,笔者批评了基于未经哲学反思的进步观对古代思想的贬低,以及我们在谈论中西之别时常有的大而化之的倾向。笔者同样也不同意那种“反动的”(对外来压力的反动的)对古代的盲目推崇。不过,这篇文章的重点并不在于直接处理这些大问题,而是要通过对韩非子及其所处时代的一些初步研究来展示:第一,在所谓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已经在某种意义上经历了向“现代性”的转变。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很多学派实际上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应对现代性问题,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第二,与其他同时代的思想家相比,由于韩非子最好地理解了中国的“现代化”转变的性质,所以他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思想家。如果这些猜测成立的话,那么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代”中国思想可以很容易地与现代相关,因为那时的思想家和我们都在处理一样的问题,即现代性问题。这些讨论也会加深我们对现代性本质的理解。第三,如果这种关联成立,那么,通过对韩非子的批评,我们也许能够发现今天一些主流思想的问题。
韩非子生活在战国末期。春秋战国时期充斥着社会与政治上的混乱和转变。在这一时代之前的西周的政治架构是一个封建的、金字塔般、扩张的系统。周王(尤其是最初几代的周王)分封(“封土建国”)他们的亲戚、忠实和能干的臣下(很多人同时也是周王的亲戚)、前朝的贵族等。这些人成为他们被分封的诸侯国的统治者。这些诸侯国中的一些是在周帝国的边远地带,因此他们可说是向这些“蛮夷”之地的军事殖民。[1](P57)这些事实上的殖民地的建立有助于帝国势力的扩张。当这些诸侯国通过蚕食其周围的“蛮夷”之地得以扩张后,它们的统治者常常会做与周王类似的事情,即分封他们的亲戚与亲信。就周帝国来说,周王统领诸侯,诸侯统领大夫,大夫统领家臣,而家臣统治他们属地的民众。因此,在每个层级上都是一个主子统领有限的臣属。这一现实使得统治者通过个人影响和以宗法为基础的礼俗规范来统治成为可能。但是,也许是因为宗族的纽带经过几代以后被削弱,而更可能是因为因领土扩张和人口增长使得礼俗不能再起到有效的约束作用,并且整个周帝国已经扩张到当时的极限从而使得内斗变得很难避免,所以这种等级、宗法系统在春秋战国时期渐趋瓦解。在春秋时代,与从前不同,周王只被给予了名义上的尊重,他实质上变成了诸侯之一,并且是实力很弱的一个。诸侯国的疆界不再被尊重,通过吞并战争七雄终于产生,也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乃至后来七雄的统治者不得不直接统治领土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的国家,而这些国家的存亡以及这些君主在其国内的存亡完全依赖于他们的实力。
上述这种转变与欧洲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转变有很多奇妙的相似之处。欧洲中世纪的政治架构也是封建的、金字塔般的,每一级都处于小国寡民的状态,其约束方式也是宗法。但是,这一架构在欧洲的现代化转变中也渐趋瓦解了,从中产生的广土众民的国家试图通过战争获得统治地位。当然,中西的转变还是不同的。比如,欧洲中世纪以前有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这给予他们的转型以独特的哲学、政治、文化资源。与春秋战国时的中国不同,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也没有“天下共主”式的对自身文明的统一和连续的想象。中世纪欧洲也没有世俗君主享有如周王那样高和长久稳定的地位。教皇的位置相对稳定,但其是否有公认的天下共主的地位是有争议的。中国的转变的一个驱动力量是农业革命,这使得它也许不像西方转变之始的商业革命,并且也肯定远不如西方转变后期的工业革命那么剧烈。欧洲在向现代化转变的同时伴有领土扩张(移民与殖民),而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文明已经基本达到了当时条件允许的领土界限。欧洲的“春秋战国”也没有能够达到中国所达到的统一,尽管它们确实成功地打了两场“世界”大战和很多较小规模的战争。但是,中国的春秋战国与西方现代化的转变的相似性是清楚和深刻的。与封建制度一起消失的是贵族阶级和他们的政治制度与生活方式。春秋战国时代,土地的贵族专有继承和旧有的公田系统被废除,土地自由买卖随之兴起。在西方则出现了臭名昭著的英国圈地运动,贵族礼法的消逝也带来了相应的种种变化。比如,钱穆先生指出,与封建等级摇摇但未坠的春秋时代的战争相比,战国时代的战争是残忍与丑恶的。[2](P88-89)军队被平民化了,贵族的行为准则也消逝了。战争服务于对资源的争夺,并成为以砍脑袋为目标的残忍的“竞技”运动。
总而言之,中国从西周到春秋战国之变与西方从中古到近现代的变化有所不同,但它们又有着不可否认的相似性。如果西方的转变被称作“现代化”的话,那么这种相似就意味着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在某种意义上经历了现代化。这一猜测也许会让我们重新审视现代化,理解现代性和古今之别的本质。在中国与欧洲的封建制中,在它们的金字塔的每一层级上,都只有常常是由宗法关系组织起来的几百或几千个人的共同体。也就是说,每一级都是一个实质上的寡民之小国,或“高度同质的熟人共同体”。而在现代化转变之后出现的国家都是广土众民的陌生人社会。这似乎是个不重要的变化,但在政治上大小很重要。比如,当一个共同体很小(“小国寡民”)的时候,基于一种对善的整全和相互分享的理解的道德和行为准则是可能的,但是,当这个共同体太大以至于不应再被称作共同体的时候,除非使用行之有效的压制手段,否则这种道德与准则作为独尊的整合社会的纽带不再普遍适用,因而在非压制的情形下价值多元就不可避免。这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事实,一个为一些西方近现代思想家和韩非子所共同把握的事实。①关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如何理解多元性与共同体大小的关系,参见周濂:《政治社会,多元共同体与幸福生活》,载《第12届中国现象学年会会议论文》;周濂:《最可欲的与最相关的——今日语境下如何做政治哲学》,载《思想》第8辑,237~253页,台北,联经出版社,2008。我们这里的论断并不是要否认韩非子与现当代自由主义者的分歧,这在下文会有论述。这里,我们的问题就变成:什么可以替代道德成为一个国家的黏合剂?这是一个西方近现代与中国春秋战国时的思想家们都努力回答的问题。一个相关的共同问题是:当金字塔式的封建架构消失后,新的统治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其统治阶层如何产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西方思想家(比如支持平等和大众教育的启蒙思想家)和古代中国思想家(比如认识到所有人潜能上平等和支持某种形式的大众教育的儒家)似乎也很相像:在“现代”条件下,我们需要一种向上的可流动性,使得以前的平民成为官僚(“士”),并在这个阶层中进一步升迁成为可能。但是,这些思想家对如何实现这种向上流动性有不同的看法,比如,韩非子反对儒家教育,而偏向于以军事和(农业)生产为基础的贤能政治。因此,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思想家与西方近现代思想家在思想上的相似也许反映了他们面对类似问题的事实。比如,笔者曾论述过,《老子》与卢梭都看到了现代化的问题,认为现代化的结果会很糟糕,并因此都呼吁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3](P481-502)又如,中国曾经被一些欧洲启蒙乃至近代思想家当做他们的理想和社会政治变革的方向的原因,可能不仅仅是这些思想家用曲笔的方式,借这个中国来批评现实,而是由于春秋战国之变与欧洲现代化之间的相似,使得哪怕是简单化甚至被曲解的中国思想也引起了欧洲思想家的共鸣。②Hobson,John M.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这是最近关于这个问题的一项有趣工作。谢文郁也指出了中国思想对康德的可能影响,参见谢文郁:《康德与君子》(未刊稿)。我们研究这个问题不应该只是为了一种文化自尊,而是应该通过揭示其背后的、深刻的原因,加深对现代性以及现代各种制度安排的理解。
简而言之,我们这里的一个判断是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所经历的可能是西方现代化的一个预演。这个判断预设了对现代性的一种理解,即“古代”到“现代”之变化的实质是(或部分地是)建立在血缘继承基础上的、在每一层级上都是高度同质的小国寡民的熟人共同体的封建等级制的瓦解与异质的广土众民的陌生人社会的出现。现代性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在这种转变下的各种政治、社会问题。有些学者可能会完全不接受我们对现代性的这一理解,而认为现代性应该是市场经济、平等、自由、权力合法性等观念,从而否定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所经历的变化是现代化。这里,我们首先要澄清,上面那些大胆的论断并不预设中西的现代性没有任何区别,也不否认中西间的这种巨大转变有其微妙甚至(时间与地域上)混乱的地方,它只是预设中西的现代性有足够的类似。比如,上面已经提到,西方的现代性有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资源(比如自由、民主等观念),而中国没有。但是,即使就这些差别本身而言,我们还要考虑,它们中的一些可能只是在深层相似上的表面差别而已。市场经济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也是逐渐出现的,而中国春秋战国时的土地自由买卖也是农业社会中市场化的表现。平等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先秦儒家大多认为人们在潜能上是平等的,或至少应该是“有教无类”。这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大众教育思想相呼应。韩非子也提出了法律面前(除了人主之外)人人平等的想法,而西方宪政之初,君主也常常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基于血缘的贵族制在中国的瓦解也造成了人们职业选择上的自由,而我们下面将讨论的韩非子对思想多元性的理解也触及了自由问题。关于权力合法性的问题,在“古代”(欧洲的中古与中国的春秋战国之前),统治者权力也有其合法性基础,只不过它是诉诸某种神意。权力合法性的现代性表现在不再诉诸这种神意,或用韦伯的术语来说,现代经历了去魅的过程。西方是以社会契约、民主政治来表达这种变化的。在中国,西周时“天命”已经被“人化”了、民意化了,所谓“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尚书·泰誓》),而先秦儒家尤其是孟子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权力合法性来自于满足人民物质与精神需要的思想。①需要指出的是,儒家的政权合法性虽然强调民意,但它同时也强调精英作用,它对民意的理解(同时强调人民的物质与伦常需要)也与当代西方民主国家的理解不同。参见白彤东:《旧邦新命:古今中西参照下的古典儒家政治哲学》,21~9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这些现代化的表现和处理方式虽然不同,但它们可能只是面对类似问题时的不同处理方式,而不是问题不同、话语不同的不可通约的理论与观念。另外,作为西方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看似独特的世俗化(去基督教化)过程,也许是上述一些根本变化的合力(新的权力基础与权力架构的要求、不可避免的多元化、民众教育的提高等)外加西方中古之现实的结果(宗教及其组织是维系欧洲中古封建制的重要纽带),而不是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如果上面的理解是对的,那么说中国春秋战国的思想在古今之分上属于古代就是错的。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和韦伯对中国古代思想的评判就也是错误的。而将中国古代思想标为“两千年封建专制的糟粕”就更糟糕。我们先撇开“糟粕”这个情绪性字眼不谈,中国秦以降的两千年的历史既不封建也不纯然是专制的。②春秋战国之后的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能是专制君主(皇帝)与士人精英阶层的张力的结果。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雅思贝尔斯这样的思想家把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和与其近乎同时的古希腊、古印度思想放到一块称之为“轴心时代”的思想[4],这种说法也忽视了中国传统思想与其他思想的一个关键不同,即中国先秦思想是关于现代化的思考,因而已经偏离了古代思想的范畴。在这个意义上,同情儒家的当代学者,如罗哲海,也以轴心时代的思想来理解儒家[5],因而也就犯了与雅思贝尔斯一样的错误。从春秋以降,中国两千年的政治思想与实践可能一直在处理现代性问题,并对其提出不同解决方案。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中国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历史不但不是糟粕,还是我们当今反思现代性问题的重要资源。
韩非子可能是在春秋战国时代第一个意识到并明确阐明时代变化本质的思想家。在这个意义上,他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思想家。因此,对他思想的研究也就对现代性诸问题的思考有着重要意义。
二、韩非子的政治哲学?
在考察《韩非子》之前,让我们首先回应一个问题:它是不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其作者是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海外学者A.C.Graham将韩非子思想描述为“非道德的统治国家之技艺的科学”(amoral science of statecraft),而Paul Goldin批评了这个说法[6],并正确地指出了韩非子的著作与西方政治哲学著作的区别。比如,韩非子有时给统治者甚至大臣教授无耻的自我保护的技巧,而这种厚黑之学在霍布斯与洛克的著作里似乎是找不到的。但是,在另一部通常被认为是政治哲学著作(有些人会说它是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之作)中,即在马基雅维利的《君子论》中,我们可以找到类似的教授。在其他一些西方政治哲学著作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类似于上述的厚黑教导的踪迹。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韩非子》及中国思想史上的很多文献确实与西方传统中的政治哲学文献不同。前者常常不是为了纯粹的理论讨论而写,而是对统治者的具体建议或是与其他大臣与政策顾问的争论之记载。钱穆先生指出,在秦以后的时代,也许是因为儒家的向上流动思想的贡献,有思想的学人常常成为统治精英的一部分。[7](P21)这与春秋战国之前和中世纪(乃至近现代的大部分时期)的欧洲不同。因此,过去中国的知识精英就可以把他们的政治思想和理论付诸实践,而没有太多需要将它们变成脱离现实的理论。钱穆先生没有指出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士人于政治的深深卷入,也使得他们没有理论探讨所必需的闲暇。实际上,卢梭的一段话可以用来支持钱穆先生的说法:“人们或许要问,我是不是一位君主或一位立法者,所以要来谈论政治呢?我回答说,不是;而且正因为如此,我才要来谈论政治。假如我是个君主或者立法者,我就不应该浪费时间来空谈要做什么事了;我会去做那些事情,否则,我就会保持沉默。”[8](P46)
与此不同,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政治思想家居于政治权力的核心。这一点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发生了。比如,西方也许与权力核心最接近的思想家之一马基雅维利,他的政治地位也不及身为韩国诸公子的韩非子。据《史记》载:“秦王见《五蠹》、《孤愤》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对于这种政治地位,马基雅维利和其他西方政治哲学家恐怕难以企及。
当然,这一辩护只是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很多思想家的作品与西方不同,并暗示,如果被剥夺了参与现实政治的机会,中国思想家也会写出与西方政治哲学著作相似的作品,而它并没有说明中国传统中的这些文献是政治哲学文献。但是,如果我们把哲学当做反思的工作,从而把政治哲学当做对政治事务的系统反思,我们可以看到,《韩非子》中确实包含有这样的思考。韩非子和传统中国的很多其他政治思想家都有着在最高层的政治实践,并因而可以用之以对政治进行反思,这就有可能弥补他们于建立在闲暇之上的思辨的缺失。笔者并非要否认《韩非子》包含厚黑术,实际上,这部书很可能是这类书籍的上乘之作。笔者在这里只是论证它包含应当是属于政治哲学层面的思想。
三、韩非子之死与“法家”思想的命运
另一个对韩非子思想的重要性的攻击集中在韩非子及分享他的想法的人与国家的命运上。尽管韩非子对政治有着深刻的理解,但最终还是成了昔日同窗李斯之政治迫害的牺牲品。反讽的是,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李斯说服秦王逼迫韩非子自杀的论辩有着儒家而非法家的味道。看起来,李斯并不相信韩非子所论证的,统治者可以通过赏罚使臣下变得忠诚。李斯自己也最终被秦二世残酷杀害。通过韩非子支持的政策来使秦国强大的关键人物商鞅也最终不得好死,通过实行这种政策而最终统一中国的秦朝也没有延续多久。所有这些历史事实被那些不喜欢韩非子思想的人(比如儒家)用来说明韩非子政治思想的邪恶本质与不足。①比如,明代的张鼎文写道:“非之书未行,止于狱司;斯之术已用,遂至车裂。天道之报昭昭哉!”参见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122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笔者虽然高度同情儒家的政治哲学,但是我不得不说,这种对韩非子及其政治哲学的批驳太过廉价。韩非子在《难言》、《说难》、《孤愤》诸篇中展示了他对能让君主听从正确建议的困难的深刻理解,因此,有些人就说他不能遵循他自己的哲学。②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后人赵用贤也指出:“韩非子非死于不自免于说难,而死于悖其术。”(陈奇猷,前引书,1226页)清代梅曾亮指出,韩非子不知道他不应该挑明君主不想为人所知之术,因而招致身死。(同上,1257页)但是,他的悲剧结局也许只是展示了“得君行道”的巨大困难,这一困难在某些情形下超越了此种技艺的大师的掌控。③王世贞指出,管仲与韩非的命运之别在于时机的不同。(陈奇猷,前引书,1228页)一般来讲,一个人不能遵循自己的哲学虽然很反讽,但并不能证明其哲学是错误的。至于秦朝的命运,也许是秦朝所带来的政治变动太过剧烈,以至于不能为它在短时间内消化。“暴秦”确实在它建立不久就被推翻了,但起义军及汉朝早期的重回封建的努力也迅速失败,被修正的秦制后来实际上也为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所大多遵循。事实上,一些看起来是儒家的政治安排,比如科举,可能也包含着韩非子的遗产。过去很多思想家对韩非子的政治哲学及其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的角色已经多有反思,我们今天讨论韩非子的哲学及其在传统中国的命运时,也应继续这种心平气和的思考。
四、韩非子:第一个现代思想家?
下面,我会给出与现代性问题相关的韩非子一些主要思想的概述。首先,如前所述,我认为现代性的一个关键特征是:人口膨胀、封建诸侯向“蛮夷之地”扩张接近极致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对日渐有限的资源的争夺,导致封建的、金字塔般的政治结构瓦解,替代它的是广土众民的大国。在著名的《五蠹》篇里,韩非子展示了他对这些变化的理解。比如,他指出“古”、“今”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古者……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因此,“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悍马,此不知之患也”(《韩非子·王蠹》)。可见,韩非子的关注焦点明显不是道德是否存在与真实,而是道德是否有效。事实上,他承认我们人类是能够善待他人的。他指出:“穰岁之秋疏客必食。”但在这句话前,他说:“饥岁之春幼弟不饷。”(《韩非子·王蠹》)在这一章和其他章节里,韩非子有力地展示了道德的无效,并论述说,为了管理民众的行为,法律方式和制度安排是关键,而专注于道德培养是危险的误导。为了让法律与制度的安排有效,民众必须被平等地对待,而他们的贵贱与亲疏不应被考虑。官爵的授予应该纯粹基于一个人在农、战中的成就。通过这些,韩非子支持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国家(君王除外),倡导基于具体、实在的成就、允许向上流动性的贤能政治。用这些成就而不用道德来衡量贤能是因为,道德不仅无效,而且还很混乱,会被任意解释,从而也就制造了不同的权力中心而使国家不稳定。这里包含着韩非子另外一个反对儒家德治的论辩。道德在大的共同体里不可避免地会变得多元,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变得无效。在《显学》一章中,韩非子指出,孔子、墨子死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儒墨两家“俱道尧舜”,但是“取舍不同”,给出的政治建议常常截然相反。可是,我们无法审核三千年以前尧舜的原意,而在这种无参验的情况下,我们也无法断定哪一家、哪一派的解读是对的。韩非子认为“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韩非子·王蠹》),它(比如儒家的道德形上学或后来的宋明理学乃至新儒家所看重的心性之学)无法“为众人法”,因为“民无从识”这些“上智所难知”的道德论说。与此相对,智慧德行有如孔子这样的“天下圣人”不过有“服役者七十人”而已,而“下主”的鲁哀公“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韩非子·王蠹》)。
由上述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韩非子有很多洞见是为后来的西方近现代乃至当代的思想家所分享的。他给出了大的共同体里道德价值多元之不可避免的原因,也理解使用简单与普遍可理解的东西(比如赏罚)的必要。①参见Bentham,Jeremy.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 les of M orals and Legislation.New York:Hafner Press,1949。该书开宗明义,认为痛苦和快乐是人类的唯一的和最高的主子。由于他有这种理解,他可以说与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罗尔斯是比肩的。②比如,Raw ls,John.Political L iber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在该书中罗尔斯给出了他的多元主义论述。至于他们之间的区别,我下面会加以论述。与之相对,很多西方近现代思想家简单地歌颂那些通常认为是卑微的东西(比如短期的物质利益),在打倒老上帝的同时又立起了新上帝,而并没有理解我们为什么不得不求助于它们的原因。这些人中的一部分甚至进而否认价值的实在。与他们的意见相左,但可以说与他们一样头脑简单的是很多现代道德保守主义者。他们看到了古人竞于道德而今人争于气力,但是并没有明白这个变故的深刻理由。他们哀叹现代人的道德沦丧、道德相对主义、道德虚无主义,并攻击那些他们以为推动和歌颂了这些潮流的近现代思想家,好像这些所谓的推动者导致了今人的道德沦丧。这反映了思想者的傲慢,以为思想者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大的影响。基于这种傲慢,这些保守主义者似乎觉得,如果这些“推动者”能被保守主义者的圣战所摧毁的话,如果我们重新培养出古代的绅士阶层的话,那么世界的秩序就会得以重建。这两类人虽然各执一端,但是在对古今之别之实质的无知上却是共同的。
当然,韩非子对道德多元不可避免的解释与当代自由主义者中有头脑的思想家的理解还是有区别的。韩非子的论述只给出了道德多元的现实条件,而这些条件的充分性有待考察。更重要的是,他没有给出多元性的可欲性。与此相对,现当代自由主义者强调自由选择的可欲性,而现代普及教育也增大了自由选择的现实可能性。这种自由选择的可欲性是多元性的可欲性的一个基础。换言之,对自由主义者来讲,统一思想是不可欲的,而韩非子的观点是它既不可能也不有效。但是,韩非子还是认为思想的多元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对多元性的承认完全可以到此为止。这种基于无奈的承认可能会在多元主义与道德一元的信念之间构筑一座桥梁。
有人会反驳说,大国里解决思想多元问题可以由极权主义来实现。但是,韩非子本人似乎并不觉得这是可能的。他关注的不是统一思想,而是统治者需要用那些每个人都不得不听从的东西(即赏罚)来控制所有人。他关注的是控制人的可以参验的行为,但并不在意控制人内在的想法。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韩非子与现当代自由主义者又有不同,即从思想的多元性出发,韩非子并没有给自由与权利留下太多空间。不过,如果我们想想西方近代早期政治哲学家,比如马基雅维利①马基雅维利是不是一个现代思想家、是不是第一个现代思想家,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参见Ivanhoe.“Han Fei Zi and Mo ral Self-Cultivation”,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forthcoming,2011。和霍布斯,对控制的强调,他的这种取向也许会显得不那么扭曲。更重要的是,他确实有一个合理的担忧:价值的多元会带来国家的不稳定。他的这一担忧似乎也为他所处的时代乃至中国及世界历史的大部分现象所支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不是韩非子,而是自由主义思想家欠我们一个解释,解释我们为什么现在可以同时拥有多元性和稳定。这恰恰是罗尔斯在他的晚期哲学里试图回答的问题。[9]但是,他的回答是否充分是可以考究的。比如,罗尔斯也许忽视了一点,即现代技术的发展(比如通讯)使得国家紧紧控制地方乃至个人事务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很反讽的是,当今自由民主国家所享有的自由与多元也许是建立在韩非子渴望的但是无法想象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基础上的。没有集权,也没有自由。因此,自由的理念可能确实是西方现代性的一个独立贡献,但是我们可以拥有它这个事实是对韩非子的驳斥与辩白。只有在韩非子的担忧被他所不能预见的技术发展所解决以后,他所忽视的自由才成为可能。当然,在没有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它的集权与极权也超过了韩非子的想象。
与现当代自由主义者不同,韩非子没有给出对统治者(除了国家兴亡之外)的任何制约。但是,与西方很多近现代思想家类似,韩非子为法律的绝对权威和法律面前(除统治者之外)人人平等辩护,这为现代的宪政播下了种子。②像我前面提到的,西方宪政之初,有些君主也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对韩非子与宪政主义的一般讨论,参见Schneider,Henrique.“Legalism:Chinese-Style Constitutionalism?”,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forthcoming,2011。
五、韩非子、儒家以及韩非子与自由主义者边缘化道德的问题
因为韩非子的思想对我们理解现代性是如此关键,所以考察他的思想如何与其他学派的思想互动就可能是一项卓有成效的工作。一个有趣且重要的问题是它与《老子》的关系问题,但本文会专注于韩非子与儒家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
与《老子》的世界观一致,韩非子也论辩说统治者应该遵循自然,人为的东西(包括儒家的道德)只会毁了一个国家。他也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在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里,基于微妙与深刻的哲学教导的道德不可避免地是多元的,因此就不能成为统一国家的政治系统的基础。也就是说,儒家建立道德国家的理想虽然美好,但是不切实际与无效的。因此,如果我们希望保持他思想的完整,就无法用儒家思想改造韩非子。但是,儒家思想里有无空间来采取韩非子的一些主张并加以修正呢?
笔者认为,儒家不仅可能而且还有必要吸收韩非子的一些主张。如上所述,春秋战国时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基于出身的封建等级制趋于瓦解的背景下,该如何设计一个政体来直接管理领土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于这个问题,儒家的解决是重建等级社会,但是它不再基于出身与血缘,而是基于儒家道德(包括官员的能力)。但是,在韩非子看来,儒家德治或礼治的理想是建基于已经消逝的政治现实之上的,无法满足新时代的现实。我想,儒家对这一挑战可以有两种回答。第一,儒家可以希望回到小国寡民时代,回到高度同质化的熟人社会以便重建道德。但是,如果我们不认为让韩非子所处的或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回到小国寡民状态是可能的或可欲的,并且如果我们想让儒家的一套政治哲学在现有大多数国家都已经是广土众民的现代世界还适用,我们就必须正面回应韩非子的挑战。我的一点初步的想法是儒家可以采纳韩非子的一些处理广土众民的大国不可或缺的制度上与法律上的设计。比如,虽然在理想状况下,孔子希望不用刑罚,但是在非理想的世界里,他并不反对刑罚的应用。①《论语》2.3,12.19与13.6节和《大学》的第三章讨论的是理想的或规范性的案例。而在13.3节中,孔子指出法律手段应被礼乐所指导,这就暗含了他并不反对应用法律手段,可谓其在非理想世界中的态度。儒家不仅仅是被动采纳韩非子的制度设想,还可以在制度与法律之上给出儒家的道德指引,并在制度与法律之下(之外)建立道德以便支持制度的稳固。这种道德建构对大国的良好运作会起到关键作用。
但是,这种儒家的改良与韩非子的一个基本判断相违背。他认为,在大国里倡导儒家价值就不可避免地毁了国家,其原因是价值多元和德治的无效。不过,也许有一种更薄版本的道德,它可以“薄”到让持不同的整全的道德观的人所采纳,成为他们的“重叠共识”,它也不对民众的道德心与智慧有过高的要求。儒家对日用人伦的很多考虑是可能符合这种设想的。比如,不管一个人的信仰如何,多数人可能会认识到家庭稳定对社会稳定的好处,而家庭稳定是儒家道德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就韩非子的以上智之人难知的微妙之言来为众人法的攻击来说,从一开始,儒家就致力于发展出一些为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社会底层人士所能理解的实践,而对这些民众的要求,也常常不比韩非子承认的丰年时候款待陌生人的爱心高太多。
如此理解道德及其作用,也会对西方自由主义者(比如罗尔斯)的一个想法构成挑战,他们坚持区分私德(古代人的道德)与公德(现代人的道德),坚持将前者推到所谓背景文化里去。②对这个想法的一般性的批评,参见Chan,Joseph.“Legitimacy,Unanimity,and Perfectionism”.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2000,29(1)。但是,从上面的理解出发,我们可以论辩说,也许可以有更薄的、可以在公共领域里存在的“古人的”的道德,它不导致压迫(与以赛亚·伯林所说不同)但又对国家的运作很重要。儒家因素可以渗透到传统的中国政治制度中,并且能为持有不同的整全观念(比如佛道)的人们所接受这个事实,也许就暗示着有些儒家因素是可以薄到足以成为拥有多元价值的民众的“重叠共识”的。有如儒家因素也许修正了只用韩非子想法的局限,从而强化了中国传统社会一样,发展类似的因素也许对今天自由民主社会的局限会有修正作用。
儒家对韩非子思想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补充是关于政权合法性的问题。韩非子担心稳定问题,从而不支持多元。现代自由民主社会除了通过集权维护国家稳定外,还通过民主选举所表达的民众认可来维护稳定。先秦儒家,尤其是孟子,也认为民意的认可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之一。并且,通过士人对人主的监督,我们也可能找到一个不通过国家兴亡的激烈手段来淘汰不合格人主的办法。这有可能反而促进了政权的稳定。
综观中国历史,与韩非子的初衷相违,儒法互补可能是历朝政府的指导哲学。比如,儒家从支持更适合小国寡民的举孝廉到接受更适合大国的科举就是对韩非子思想的一个整合的努力。传统中国所采用的官僚体系源自于韩非子的设计,但这个体系又有不可否认的儒家色彩,不同的朝代也曾尝试过不同的混合,有些混合的结果明显是坏的。韩非子的强势政府与儒家对道德的看重,有时候就混合成了比韩非子想要的更专制的政治制度,用韩非子的制度来控制韩非子并不太关心的思想。评估这些混合的好坏优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的政治史、儒法关系。这种评估工作,从我们对韩非子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论证中可以看出,还可能会为当今世界政治制度的改良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1][2]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白彤东:“How to Rule without Taking Unnatural Actions(无为而治):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e Laozi”.Philosophy East and West,Vol.59,No.4/October,2009,481-502.
[4]Karl Jaspers.The Origin and Goal of H istory.Translated by M ichael Bullock.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 td,1953.
[5]Heiner Roetz.Confucian Ethics of the A xial A ge.A lbany,NY:Suny Press,1993.
[6]Paul Goldin.“Persistent M isconcep tions about Chinese‘Legalism’”.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forthcoming,2011.
[7]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8]Jean-Jacques Rousseau.On the Social Contract w ith Geneva M anuscript and Political Econom y.Edited by Roger D.Masters and translated by Judith R.Masters.New York,NY:St.Martin's Press,1978.
[9]John Raw ls.Political L iberalism.New Yo rk,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