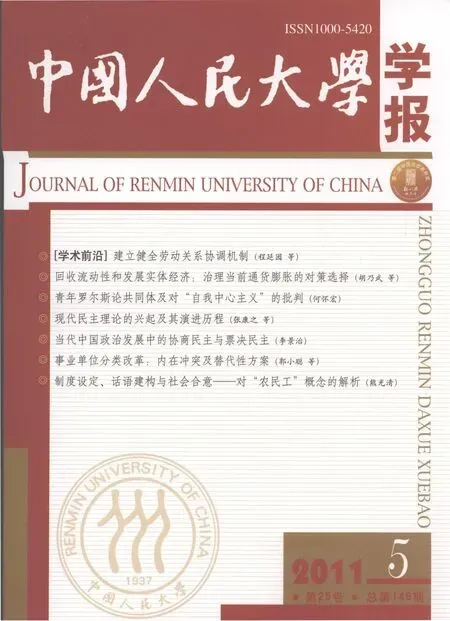重读经典文本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意义
2011-02-09陆贵山
陆贵山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有宏观视野、历史意识、辩证思维、实践观点、批判精神等,这是它的强项、优势和独特的学术品格。借鉴西方文论和中国传统文论的理论资源,提升当代中国文学的实践经验,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重要途径。重读、细读和精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本,对发展和重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拓展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人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本仍然具有蓬勃的生命力。经典文本是永远的,常读常新。由于历史和文化机缘的召唤和触发,我们可以从对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中,发现一些富有时代感和现实感的新思想和新的学术内涵。一方面,应当发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理优势,使原有的强项变得更强;另一方面,应当通过对经典文本的再阐释,开拓和发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中所蕴藏的、以往研究相对薄弱的理论空间,使其更加充实、完整和系统。
一些中外学者通常把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归属为社会历史学派。这种论断大体是正确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实际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没有关于人学的思想、理论和观点。通过重读、细读和精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本,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著中拥有丰富、深刻的人学理论和科学、系统的人学思想。梳理和提升这些人学理论和人学思想,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优化和弘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文精神、应对西方新人本主义思潮的挑战、寻求创新和发展的机遇,都有着重要意义,同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工作者的学术使命。
萨特曾断言,马克思主义“见物不见人”,独尊历史,无视人文。这种看法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诚然,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社会存在的优先性和第一性的原则。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忽略人,而是把人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里加以考察,认为人是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人。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的社会称为“作为主体的社会”[1](P42)。
实质上,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人学理论、史学思想和人学思想、史学观点和人学观点、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是有机融合在一起的。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是历史的人,历史是人的历史。历史活动是人的历史活动。人的劳动、实践和生产活动被视为“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2](P374)。“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3](P364)“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4](P247)“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5](P118-119)“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同时也是“人自身的生产”[6](P2)。
马克思、恩格斯既重视历史状态,也关注人的生态。当人的观念阻遏历史的发展时,他们主张通过社会革命,改变人的生存环境,推动历史转折和社会进步。恩格斯通过评论巴尔扎克的创作,列宁通过评论托尔斯泰的创作,都充分肯定了从封建农奴制向市民共和制的社会变革,从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方面,展现了新兴的市民阶级取代腐朽贵族阶级的历史过程。当历史状态和社会境况压抑人的生存和发展时,他们又倡导人文精神,提振人文关怀,反对现实生活中的鄙俗气。马克思、恩格斯满腔热忱地赞美和讴歌文艺复兴时代焕发出来的健全和高昂的人文精神,却对当时他们的祖国——德国人文精神的低迷感到焦灼和忧虑。恩格斯认为:这种积淀为习惯势力的鄙俗气是可怕的,即便是伟大诗人,“连歌德也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活;而他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却是很可怜的。他的生活环境是他应该鄙视的,但是他又始终被困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的生活环境里”[7](P256)。“黑格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是奥林波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摆脱德国庸人的习气。”[8](P218-219)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把历史拉向倒退的复古主义。他们抵制“用真正的田园诗的笔调”,“把已经在所有文明国家中成为严峻的社会变革的先驱者的现实社会运动,变为安逸的、和平的改变,变为宁静的、舒适的生活”[9](P639)。他们警惕和抵制当社会变革风暴即将来临时,“反动势力便发出悲叹,祈求回到封建主义,回到美好的宗法式生活里,恢复我们祖先的淳朴的风尚和伟大的德行”[10](P183)。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人的解放问题。他们把人的解放问题理解为一种历史的运动。他们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归根结底,人的解放问题不是靠语言修辞和审美救赎所能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中包含极其丰富和重要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理论包括语言所承载和叙述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论断,特别富有启发意义。一方面,他们非常强调正确的、科学的、革命的理论的重要性。正确的、科学的理论是达到预期目的和实现变革蓝图的必要前提,好比过河的船和航行的灯塔。另一方面,他们也强调理论必须付诸实践。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产生和实现真理的唯一途径。语言所承载的思想和理论都是有局限性的。理论和思想本身并不能实现什么东西。只有通过实践,转化为现实的物化形态,只有落实和兑现了的理论和思想才具有实效性,否则只能停留在人们的思维中和幻想里。语言承载着的理论和思想所蕴涵的意义、价值和作用是很不相同的:有的关乎人类的命运和社会发展的前途,有的则非常低微。即便是高超的理论和思想,也必须或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挣脱和超越人们的思维、心理和幻想的层面,变成现实生活中的事实。
人类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历史的转折和社会的进步都不是说出来和唱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是人类社会实践具有创造性的伟大成果。因为新事物和新人物的诞生不取决于理论本身的自我繁衍。“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1](P152)妄图通过审美乌托邦和审美救赎的理论预设来实现人的解放问题,只不过是被压抑又耽于幻想的知识分子的浪漫的美梦。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的:“否认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是“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认为这是幻想”[12](P121)。
二、发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关于文艺内部规律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关于文艺内部规律的论述是不多见或相对薄弱的。正因为如此,更应当从经典文本中挖掘和发现关于文艺内部规律的理论。应当承认,文艺是具有内部结构和内在因素的,存在着内部规律。矛盾分为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事物演变的原因分为内因和外因。实质上,文艺的外部规律即是文艺存在和发展的外因,文艺的内部规律即是文艺存在和发展的内因。著名文艺理论家杨晦曾把文艺的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比喻为地球公转和自转的关系,对我们颇有启发。一方面,应当尊重文论家们研究形式语言符号等特殊的内部规律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和克服在强调文艺普遍的外部规律时,忽视对文艺特殊的内部规律的研究。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地理解和阐发文艺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的相互关系。
(一)关于形式和内容的理论
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是辩证关系。经典文本中关于内容和形式的主要观点是: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依赖于内容,同时形式对内容具有反作用;内容是相对稳定的,而形式却是相对活跃的。新内容可以利用旧形式,新形式也可以表现旧内容。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是复杂的,但两者之间的基本规定是不可随意消解、颠倒和互易其位的。即便是从审美的意义上说,尽管审美具有相对意义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但这种特殊规律应当是对普遍规律的丰富和补充,而不应当是对普遍规律的否定和颠覆。在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中,内容起着主导、制约乃至决定的作用。
一些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也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关于形式和内容的理论原则。詹姆逊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世纪辩证的文学理论》一书中倡导“辩证的文学理论”,强调作品本身的辩证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形式与内容的适应性和社会历史因素对构成形式的根源性。他认为,形式作为与内容相对应的“深层的社会和历史结构的符号”,实际上是内容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完成。形式主义的探索,深化和细化了对文学形式的研究,丰富和拓展了文学外形式和内形式的理论空间。有选择地、批判地吸取这些成果,对发展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颇有裨益。
但有些形式主义的理论却极端地夸大了形式对内容的改制和重组的作用。完全脱离内容的形式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至于“内容是完成了的形式”和“内容是有意味的形式”等界说,在肯定形式组构作用的同时,也不可能排除“内容的意味”。诚然,在反作用的意义上,可以适度强调形式对内容的征服。席勒为了追求人的“审美自由”,曾在《美育书简》中表达和抒发“靠形式完成一切”的奢望。受到康德和席勒的形式主义美学思想的影响,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学,都无限度地夸大了文本、形式和语言的作用,使作品中的内容被淡化和弱化,同时泛化和强化了主体的随意性,不同程度地消解了客体的先在性和对创作的制约性。
(二)关于文本和语言的理论
语言本来是人的语言,本来是人的世界的语言。西方的“语言学转向”,尽管深化和细化了对语言的研究,但又极端地夸大了语言的作用和功能,实质上把语言与人的关系和语言与人的现实世界的关系搞颠倒了。这些语言学家们认为人和人的世界作为存在不是语言的家,反而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不是人塑造语言,而是语言塑造人。他们把语言视为第一性和第一位的东西,不适度地夸大了语言的地位、作用和功能。
西方现当代一些具有变革意识和注重批判精神的左翼知识分子,把对现实的变革一定程度上归结为对语言的变革,幻想通过语言变革实现对现实的变革。他们的动机可能是真诚的,但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的。
“语言学转向”实际上是20世纪60年代“五月风暴”失败的产物。由于法国爆发的左翼学生运动受挫,使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意识到当代西方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极其牢固,引发了他们对现行体制和结构的普遍反感,从而导致从现实批判向语言解构的转移。英国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以“后结构主义”为例分析了崇尚语言功能的现象,他说:“后结构主义是1968年那种欢欣和幻灭、解放和溃败、狂喜和灾难等混乱的结果。由于无法打破政权结构,后结构主义发现有可能转而破坏语言的结构。”[13](P206)他还指出:“后结构主义者们无力打碎国家权力机构,但是他们发现,颠覆语言结构还是可能的。总不会有人因此来打你脑袋。于是,学生运动从街上消失了,它被驱赶入地下,转入话语领域。”[14](P156)正是出于对现存牢固体制的反叛意向,一些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从对当局公开的斗争转向语言领域的变革。另外一些知识分子——主要是语言学家,他们的学术策略是通过修辞学从事语言改革,从而实现社会变革,这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词句革命论”。语言重组和文本颠覆并不意味着对现实生活能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语言和文本的自主性、本体性和独立性是相对的,是有边界的,语言的重塑功能是有限度的。语言在文本中所经历的命运,从陷入“文字游戏”到打破“语言的牢笼”,都非常有说服力地证明:语言只能在反作用的意义上决定现实。语言和“语言中的精神生产”包括语言所体现的思想、观念和意识都是人们的物质活动和实际生活过程的产物。精神生产中的语言,又是“与现实生活中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人们的生产,包括“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15](P29)。不能把语言的生产和“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仅仅局限在和归结为语言和词句本身的自我繁衍。
马克思、恩格斯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16](P525)。语言总会受到现实生活的“纠缠”,“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7](P34)。他们指出,用语言变革代替现实生活的变革,“从语言过渡到生活的整个问题,只存在于哲学幻想中”[18](P528)。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时说:“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人……说他们仅仅是为反对‘词句’而斗争。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现存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实际上只是通过词句来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而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19](P22-23)本身。
妄想通过对语言词句的主观解释和修辞,打乱和重组语言结构来改变现实生活中的历史结构和政治结构是不可能的。把语言批判作为反对现实生活的手段,并不意味着对现实生活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因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20](P43),“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要从人们的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只有靠改变条件,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21](P45)。这种语言的变革行为实质上是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发生,不会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尖锐地批评:“尽管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们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保守分子。”[22](P22)
西方的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发现了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的互文性,企图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带有解构主义意向和批判精神的阐释,对历史文本施加影响。这种互文性的理论既把历史和文本联系起来,同时又把历史和文本混为一谈。这种文本的历史观有悖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应当把“文献的历史”和“现实的历史”严格地区分开来,反对用语言和文本承载和包装的“意识、观念、圣物、固定观念的历史称为‘人’的历史并用这种历史来偷换现实的历史”[23](P200)。马克思、恩格斯反对一些人“把文献的历史和现实的历史当作意义相同的东西而混淆起来……他们把自己的始终非常丰富的幻想和现实等量齐观,以此来掩饰他们在现实的历史上曾经扮演过的并且还在继续扮演的可怜的角色”[24](P551)。
归根结底,文学文本不能不受到历史文本的影响和制约。文学文本所表现出来的复杂的思想矛盾,是由一定时代和历史条件下的复杂的社会矛盾决定的。文本结构非但无法超越和摆脱历史结构,反而是历史结构在文本结构中的投影和折光。正如恩格斯评论伟大诗人歌德的思想结构和文本结构时所指出的:“歌德在德国文学中的出现是由这个历史结构安排好了的。”[25](P254)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文本中的这些思想,对正确分析和评价形式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观点都具有深刻的方法论启示。
西方的批评理论多半局限于对文本和语言层面再创造的批评活动中。相对而言,在文艺创作的过程中,对语言本身的重释和重塑并不重要。文艺创作的基本问题是人物塑造和情节设计。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文艺创作的基本问题,反而被悬置或抛弃了。各式各样的批评理论,如修辞学、解释学、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对文艺创作可能具有这样那样的参照意义。但是,研究人物塑造问题,仍然是文艺创作的首要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关于人物形象塑造,特别是关于塑造新人形象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些思想是:倡导塑造新人形象是一脉相承的,从呼吁塑造“革命的和叱咤风云的无产者”,到反映“新事物”,到“表现新人物,新的世界”,到塑造现代化事业中的“创业者”和“新人形象”;坚持塑造人物形象的唯物辩证法,强调社会历史环境对人物形象的制约作用,认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26](P43);明确区别“新人”和“旧人”的首要标志是能否“改变这种环境”[27](P234);新人形象是具有变革意识和“实践力量的人”;只有新的社会状况和历史条件,才能为新人提供生存和发展良好的环境和土壤;只有新人形象作为新的历史使命的承载者,才能从正面体现出新的思想体系和核心的价值体系。
三、重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美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是从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联系中提倡美学精神的,是从史学观点和人学观点的联系中提倡美学观点的。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学精神,史学观点、人学观点和美学观点是有机地融为一体的。
美和美感都是人的劳动的产物。人的劳动创造形成了属人的世界,创造了人本身,也创造了属人的世界的美和人本身的美。“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28](P126)。美的存在和发展都是有规律的。对“美的规律”的阐释,尽管各有所解,但“两个尺度”对美的存在和创造,都是无法回避的。同时,审美特性不同于对象的物质属性和商品属性,而是一种特殊的与人相关的价值属性。“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29](P34)。“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30](P126)审美感觉表现为一种富有个性的情感、激情和爱憎态度。
美学的基本问题是审美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对审美关系的论述是既唯物又辩证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既强调美的唯物论,认为现实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主张艺术和艺术美是现实生活在作家的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同时又超越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的论断,特别强调美的辩证法,提倡艺术美应当比生活美“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即便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的历史条件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没有忽视对文艺创作审美品位的倡导和要求。
审美主客体的关系是审美关系的核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抵制黑格尔的“存在和思维的神秘的统一”,反对“抱着这个目的,用虚幻的联系、神秘的主客体来代替世界秩序和世界事件之间的自然的合乎人性的联系”[31](P213)。马克思非常强调审美主客体的关系的“交互作用”所产生的“规定性”。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32](P125)马克思反对“从现实的关系和运动中撷取一种规定性,把这种规定性变为想像的规定性、变为范畴,并把这个范畴充作产物、关系或运动的观点”,甚至“把现实的人变成了抽象的观点”[33](P246)。按照马克思的解释,“这种规定性”不能理解为抽象的和想像的“规定性”,而是主客体之间,即“对象的性质”和“与之相适应的”人的“本质力量的性质”这两方面的交互作用所形成的既唯物又辩证的“关系的规定性”。“这种关系的规定性”不可能是完全均衡的,如向客体方面倾斜,形成现实主义一类创作和作品;如向主体方面倾斜,形成浪漫主义一类创作和作品。诚然,马克思、恩格斯是倚重于倡导现实主义的创作和作品的。
反映在结构情节和塑造人物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主张遵循客观对象的逻辑来结构情节和塑造人物,并不认同像“欧仁·苏书中的人物”那样,“必须把他这个作家本人的意图……充作他们自己思考的结果,充作他们行动的自觉动机”[34](P233)。《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形象玛丽花本来是一个“朝气蓬勃、精力充沛、愉快活泼、生性灵活”、像太阳和花一样的少女,而欧仁·苏通过思辨哲学和基督教教义对她进行改造和重塑,使她变成“有罪意识的奴隶”,从“本来的形象”变成“批判的变态”。而当作者“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偏见”,“超出了他那狭隘的世界观的界限”时,读者“所看到的都是玛丽花本来的、非批判的形象”[35](P216-218)。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用“批判的原则”改制人物和环境,这样做的实质是用“思辨的黑格尔的形式恢复基督教的创世说”[36](P174)。崇拜语言批判的“自我意识”使其从“人的属性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这种自我意识的本质不是人,而是理念”,即“人化了的理念”[37](P175-176)。
反映在对作家艺术家的评价上,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应当遵循客观和公正的原则。如对歌德的评价,恩格斯反对一些有偏见的评论家只对所谓的“歌德的人的内容”进行片面的挖掘和夸张的解释,防止和克服只凸显歌德的所谓“人的内容”中的那些怯于变革,喜欢宁静、安逸、平庸、亲和、耽于幻想的一面,而故意遮蔽和掩盖“歌德伟大的一面”,甚至把歌德涂抹得与“德国的小市民一模一样”。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作为阐释者的格律恩之所以这样做的真正目的,实质上是用“被歪曲了的歌德的权威来支持自己的狭隘性”[38](P275)。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工作者,在重读、细读和精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文本的基础上,应站在时代前沿,增强问题意识,倾听实践呼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努力开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和发展的新局面。
[1][9][15][16][17][18][19][20][21][22][23][24][26][27][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4][6][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11][12][31][33][34][35][36][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7][25][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4]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28][30][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