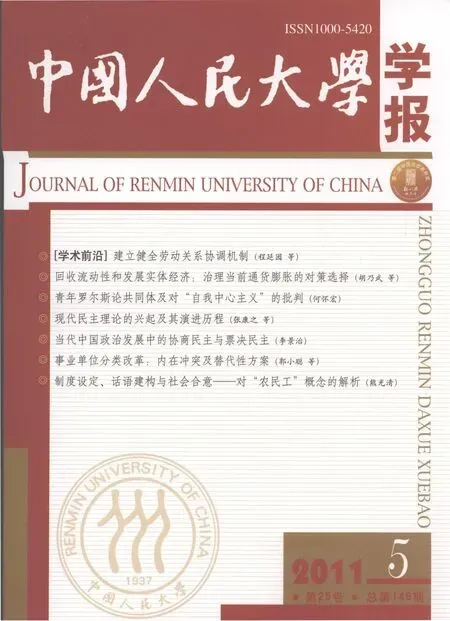论《洛丽塔》的解构主义倾向
2011-02-09李海英
李海英
自美籍俄裔作家弗拉迪米尔·纳波科夫的作品《洛丽塔》问世以来,对这部作品的意义、艺术手法和叙事模式的分析,一直是美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的热点。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洛丽塔》是一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美国文学作品。也是我国学者编写《美国文学史》或美国经典小说的必选作品。分析《洛丽塔》对世界文学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洛丽塔》讲述了一个“恋童癖”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位来自欧洲的移民知识分子亨伯特,因其少年时和少女阿娜贝尔的恋情,喜欢上12岁的少女洛丽塔。为了接近洛丽塔,亨伯特娶了她寡居的母亲夏洛特·黑兹,在夏洛特死于车祸之后,亨伯特就占有了洛丽塔,并带着她在美国各地旅行。在洛丽塔被奎尔蒂拐走后,亨伯特找到了奎尔蒂并将其击毙,入狱后写下了一段“白人鳏夫的忏悔录”。后来,在宣判前,亨伯特死于拘禁中。在同年圣诞节的前夜,洛丽塔死于难产。这段“白人鳏夫的忏悔录”由小约翰·雷博士整理并发表。
在对《洛丽塔》的研究中,目前,大部分学者都“将纳波科夫的创作归置于‘后现代主义’,将他视为与约翰·巴思、唐纳德·巴塞尔姆、托马斯·品钦一样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典型代表’,或把他看成‘较早崛起的黑色幽默作家’,或将其创作看成‘美国后现代小说的滥觞’”[1](P102)。笔者也认可对《洛丽塔》作者的这一基本定位。但是,《洛丽塔》如何体现了后现代性的写作手法,这一写作手法对文学写作有什么启示意义?与大部分学者将《洛丽塔》后现代性归于叙事角度或主题思想的看法不同,笔者认为:《洛丽塔》的后现代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解构意识和解构手法运用过程中。
20世纪中期兴起的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认为:西方文化中的形而上学传统一直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强调“整体化、结构化”,这一倾向体现在文学作品的创作和文本的传播过程中。在创作过程中,整体化、结构化的倾向体现为主题思想的明确性、人物形象简单化或单面化;在叙事过程中,强化作者从某一特定的视角透视人物;在阅读过程中,强化读者向某一特定意义的回归,这一特定的意义由作者或某个精英人物设定。德里达将这一倾向称为“中心化”倾向,他把“中心化”倾向与人类的极权主义精神联系起来,“中心的功能不仅仅以用以引导、平衡和组织结构的——其实一种无组织的结构是无法想象的——而且尤其还是用来使结构的组织原则对那种人们可称为结构之游戏加以限制的”[2](P502-503)。在解构主义的视野中,传统文学的作家、文本和阅读过程都有这种中心化的倾向。解构主义认为,如果说人类的文化本质是一种游戏的话,这一游戏的本质来自于“在场的断裂……总是不在场与在场间的游戏”[3](P523)。因此,解构主义要做的就是要找到这一中心化的路径并指出去中心化的方式。德里达进而提出了一系列手段保证人们做到去中心化。这一去中心化的路径和方式,在《洛丽塔》这一作品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本文旨在分析《洛丽塔》在人物形象、叙事模式和阅读模式三个方面的基本特点,探讨这些基本特点的解构主义倾向。
一、《洛丽塔》对单面性格人物形象的解构
解构主义认为:西方文化中的中心化、结构化倾向体现在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中,就是对单面性格主人公的塑造和解读。单面性格的主人公集中体现了人类对某一特定品质的向往并进而在作品中表达这样一种理想。因此,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单面性格的主人公表现在两个方面:作家在作品中强化人物性格的某一特定品质;批评家在作品分析中指出人物形象的单一性格。而《洛丽塔》的解构主义倾向首先就表现在对传统单面主人公形象的解构。
小说《洛丽塔》出现了许多人物:亨伯特、洛丽塔、夏洛特·黑兹、阿娜贝尔、奎尔蒂等,但这些人物的出场都围绕着同一个目的,他们都是为主人公亨伯特恋上洛丽塔、获得洛丽塔而设置的必要过渡,他们在作品中出现的目的就是为了表现亨伯特要占有洛丽塔的原因、障碍和失去洛丽塔之后的愤怒。《洛丽塔》整部小说的情节,就是描写亨伯特如何狂热地恋上洛丽塔并进而占有她的过程。亨伯特构成了本文的主要人物形象。《洛丽塔》对单面性格人物形象的解构主义倾向就首先体现在主人公亨伯特身上。
首先,《洛丽塔》通过设置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主人公形象,解构了传统小说中单面的主人公。在《洛丽塔》中,主人公亨伯特处于两种身份之中,这在其名字亨伯特·亨伯特的重复中可以看出:一方面,他是一个风度翩翩、受过良好教育、理性的大学教授,“还是让我们一本正经、彬彬有礼吧,亨伯特·亨伯特努力做一个正派人”[4](P17);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充满了畸形变态心理的恋童癖。“而内心里,我却对每一个从身边经过的快进入青春期的小姑娘欲火中烧。”[5](P15)在《洛丽塔》中,如果说,理性的亨伯特代表了大脑,而恋童癖的亨伯特则代表了身体的欲念。“当身体知道它渴望的是什么时,大脑却坚决地驳回它的每一项请求。”[6](P15)这双重身份造成了主人公人格上的分裂,使得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洛丽塔》产生了奇异的审美效果。当作为恋童癖的亨伯特讲述自己的真实欲望之后,总是遭到理性的大学教授亨伯特的冷嘲热讽,而一本正经出现的理性的亨伯特又时时面临着畸形变态亨伯特的解构。亨伯特·亨伯特的双重人格,使得《洛丽塔》呈现出一种特有的结构:它摒弃了传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在传统小说中,主人公的形象是固定的,其价值取向、性格等都是可把握的,因此,传统小说的阅读方向是固定的、线性发展的,当读者阅读完一部传统小说之后,其头脑中会形成对这一主人公形象的认可或否定,进而接受小说作者通过人物形象所传达的基本意识。而在《洛丽塔》中,理性的大学教授亨伯特和恋童癖亨伯特的相互解构使得阅读方向变得如此不可把握,以至于传统的阅读期待在这个作品中都不再适用。解构主义文学作品产生于结构主义的基础之上,如果说,结构主义文学作品强化其文本结构,强化主人公的理性分析能力,强化主人公具有某种特有的精神气质,其作品中的主人公很少有分裂性倾向的话,那么,解构主义文学作品则强化了去解构这一固定的精神倾向。因此,对解构主义文学作品来讲,要么它会设置一个与传统主人公精神上迥异的人物以解构传统观念,代表性作品有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其以典型的嬉皮士精神解构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要么在作品中设置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主人公,让主人公通过自我性格的矛盾去解构所有阅读期待和神圣意义。《洛丽塔》正属于后者。纳波科夫通过设置一个具有正面与反面、神圣与龌龊、理性与感性共存的主人公亨伯特·亨伯特,不仅解构了文学作品中人们习以为常的正面主人公形象,也解构了人们对文学作品应用一个单一性格主人公的阅读期待;而作品最终让亨伯特杀死奎尔蒂,代表了单一主人公的死亡,由于奎尔蒂只拥有一种欲望型人格,这一人格不能以另外一种角度观照自我,他的死亡是必然的。然而,双重人格的亨伯特在选择杀死奎尔蒂时,已经让作为欲望载体的恋童癖亨伯特战胜了理性的大学教授亨伯特,其死亡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者又没有让亨伯特死于人们通过理性对他的宣判,而是死于他自身的疾病——冠状动脉血栓,表达了作者在最终并没有将亨伯特的死归之于理性的胜利,从而逃避了任何一个单一性格的主人公的胜利。在这里,奎尔蒂和恋童癖亨伯特的死亡代表了单一人格的归宿和双重人格的胜利。
其次,《洛丽塔》对单面性格人物形象的解构主义倾向也表现在另一个主人公洛丽塔形象上。在传统小说中,人们对作为爱情主角的女主人公有两种描述倾向:一是强化其对于精神的神圣性,一是强化其肉体诱惑力,这符合人们对小说意义简洁性的基本要求。而由于小说《洛丽塔》总是从亨伯特的视野描述洛丽塔本人,从而使得这一人物也充满了亨伯特的双重人格隐喻。可以说,当成年的亨伯特将幼年的洛丽塔作为自己的追逐对象时,洛丽塔这个形象已经进入解构之中。在小说中,洛丽塔与其说是一个在现实中生活的少女,不如说是一个符号,是一个处于虚拟与现实中的人物。一方面,她是亨伯特眼中的生命之光,是亨伯特心目中的女神——阿娜贝尔的化身;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主动勾引继父、并引诱其进入这场不伦之恋的“小妖女”。如果洛丽塔是女神,是神圣的阿娜贝尔,那么,亨伯特的欲望解构了其神圣性;如果洛丽塔是欲念的化身,那她身上的神圣光环则不可理喻。因此,在这场意义与欲望的角逐中,作为女神的洛丽塔与作为欲望化身的洛丽塔之间互为解构,构成了洛丽塔形象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二、《洛丽塔》对传统叙事模式的解构
传统的叙事模式的基本原则就是强化意义的确定性以形成特定的中心。一般来讲,传统小说的叙事包含三个元素:事件、叙述和阐释。其中,事件是指发生的故事本身,叙述是通过叙述者的视角讲述故事,而阐释则追溯到叙述者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故事,当叙述者选择某个故事进行讲述时,一般而言,他都会赋予这个故事特定的意义,这一意义会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由于传统小说在中心化的原则中追求意义的明确性,因此,作者会采用一个单一叙述视角介入某一事件进行叙述。文学史上也有部分作品采用多个叙述主体对同一个事件进行透视,但在这些不同的叙述主体中,这些主体的视角都是明确的,小说只不过描述了某件事在不同视角那里所形成的不同印象。因此,对于传统小说来讲,叙事的目的就是为了表达人们对某件事情的解读,这一解读有着明确的主体诉求,这些明确的主体诉求都指向某个特定的中心。
《洛丽塔》不仅对传统单面性格的主人公形象进行解构,其叙事也呈现出一种特有的解构主义倾向。在《洛丽塔》中,故事本身并没有太大的争议:这是一个关于继父与继女之间的乱伦故事,故事的结局就是继父杀死了夺去其继女的另一个恋童癖者并因此被判入狱。但是,在叙事过程中,与现实主义小说强化故事的真实感不同,《洛丽塔》却将故事的真伪进行虚化处理,从而解构了人们对故事真实性的阅读期待。在作者前言部分与第36章的结尾,作者不停地向人们暗示亨伯特和洛丽塔的死亡,让人产生一种死无对证的感觉,在对洛丽塔的描述中,作者不停地解构洛丽塔的真实性,将洛丽塔还原为一个介于梦幻和现实之间的符号,“读者读到的故事将一直处于亨·亨的视角之中,也就是说,亨·亨引导我们进入了一段完全主观的讲述;而讲述者是否完全可靠尚不得而知。这就为小说一开始就营造了一种神秘莫测的气氛;而亨·亨在后来的讲述中时而突然出现的相互抵触的片断使得我们对故事的绝对真实性更加增加了怀疑。这些都为《洛丽塔》的故事情节增添了神秘性。”[7](P31)这一系列的手段,在阅读过程中形成一种奇异的效果:读者不能在现实社会寻找到《洛丽塔》的影子,因为作者自己已经解构了故事的真实性。这也就是作者不能容忍用道德分析、心理分析等方法分析作品的原因。读者要做的,就是“对此书的理解比本人在此间所能做出的解释更为深刻”[8](P324)。
“亨伯特的世界始终是一个独白的世界,没有激情的雄辩,只有无聊的令人绝望的口角。”[9](P166)但是,与传统小说视角明确的独白相比,《洛丽塔》的独白显然具有更多的内涵。在作品中,由于主人公的双重人格,亨伯特·亨伯特的独白在叙事过程中又具体分化为四种视角,这可从作品的人称代词上看出:作品的叙事者一会儿是“我”或“我们”,一会儿又变成“他”或“亨伯特”,“与其他作家的作品不同,纳博科夫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变异,即说的是第一人称‘我’的事,可用的是‘非第一人称’的口吻——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10](P165)这种自由转换的视角构成了四重叙事,这四重叙事分别是:(1)从理性主义者亨伯特视角出发的叙事;(2)从非理性的恋童癖亨伯特的视角出发的叙事;(3)从隐藏在正文背后具有双重人格的亨伯特·亨伯特的视角出发的叙事;(4)从正文前言中出现的小约翰·雷的视角出发的叙事。这四重叙事交织在《洛丽塔》的文本结构和阅读体验之中,形成了对传统的具有明晰视角的小说叙事方法的解构。
在《洛丽塔》的正文中,读者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理性的、彬彬有礼的绅士亨伯特,他遵循着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对一切不符合社会基本观念的非理性心态有着清醒的反思。在他看来,恋童癖亨伯特的行为是不可救药的,尽管这个恋童癖其实就是他自己。其次,读者又看到了一个非理性的、有着变态欲望的亨伯特,他了解自己不可告人的欲望并追逐着这个欲望。因此,表面上看来,这是两个互相对立的人格,构造了作品两种互相对立的视点:其中任何一个视点都在解构着另一个视点的合理性。因此,如果作品只写出了这样两个互相对立的人格,这一作品本质上就不过是心理分析小说。不同的是,《洛丽塔》将上述两个相互对立的视点上置于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亨伯特·亨伯特的视点,这一视点清醒地意识到上述两种互相矛盾的视点其实都来自于同一个亨伯特身上,从而增加了视点与视点之间的矛盾性和观点之间的解构性。“我”分化为两个亨伯特,“我”不但同时为两个亨伯特辩解,也同时嘲讽了两个亨伯特的逻辑。因此,在《洛丽塔》中,“我”的隐藏视角就形成了一种奇特的阅读经验:只要出现了一个亨伯特,读者总会想到另一个亨伯特,两个亨伯特互相解构、互相参照,使得恋童癖亨伯特的逻辑与理性亨伯特的逻辑构成巨大的反差,共同指向那个具有分裂人格的“我”。
如果《洛丽塔》仅仅将“我”的隐藏视角分裂为两个亨伯特,这实际上就建构了一个能自我反思、自我扬弃的理性主义者,因为观照自我仍是理性的一种建构,但纳波科夫显然意识到:如果仅仅用“我”的隐藏视角作为最终的统一体,其作品并不足以形成一种新鲜的阅读体验,甚至于有可能成为一种“精神病学的典型病例”[11](P3)。因此,在《洛丽塔》的作者前言中,纳波科夫又刻意虚构了一个编辑兼哲学博士小约翰·雷,通过小约翰·雷的视角,纳波科夫又继续解构了亨伯特·亨伯特的身份。在作品的前言中,小约翰·雷致力于解构亨伯特·亨伯特的真实性,指出亨伯特·亨伯特的真实性实际上只是“考虑到那些刨根究底,非要知道‘真人真事’的老派读者的利益”[12](P1)而蓄意编造的,这就指出了亨伯特·亨伯特绝不是一个精神病学的典型案例,也并非作品的心理分析方法,完成了对双重人格的亨伯特·亨伯特的解构。
《洛丽塔》的四重叙事,本质上就在于模糊了任何一个确定的视角,使其在“在场与不在场”之间不停地延异下去。这一叙事游戏被纳波科夫称之为“创造”。“文学是创造,小说是虚构。读某一篇小说是真人真事,这简直侮辱了艺术,也侮辱了真实。”[13](P24-25)
三、《洛丽塔》对传统阅读模式的解构
正是由于主人公形象的特殊性和叙事过程中的游戏性,使得《洛丽塔》的阅读模式不同于一般的传统小说。传统小说的阅读模式可分为两种:作者中心主义模式和作品中心主义模式。作者中心主义模式认为作品是作家意识的一种表达方式,阅读就是向作家原意的回溯;而作品中心主义的阅读模式则以作品为中心,认为作家一旦创作出作品,作品就成了孤立的个体,不再受外界任何因素的支配,要理解某一作品的意义,就必须从作品本身寻找依据。可以说,《洛丽塔》对这两种阅读模式都进行了解构。
如果读者按上述两种意义建构方式去寻找《洛丽塔》的意义,就会发现,作者中心阅读模式和作品中心阅读模式都不能概述《洛丽塔》的阅读体验。对于作者中心阅读模式,首先,要追求作者的原意,就要寻找作品中出现的人物、环境和情节等基本要素,但是,在《洛丽塔》中,这三个基本要素都被作者有意识地做了虚化处理:人物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主人公,其双重性格所遵循的基本逻辑就是相互解构,性格之间的解构成为这部小说主人公的基本特点。当读者在阅读中按文章表达的方式产生了某种阅读期待时,作品中的主人公的第二种人格就马上站出来进行冷嘲热讽,告诉读者这不过是主人公另一种人格的臆想,从而打断了读者的阅读期待。作者想通过这个主人公表达什么?只能说表达了一种解构,读者不可能形成一种明确的意义建构。其次,作者有意识地疏离了人物和环境的真实性。洛丽塔这个人是不是真实存在过?读完整个小说时,由于作品本身刻意营造的游戏感使得读者在读完整个小说时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早晨叫她洛,就简单的一个字……穿便服时,我叫她洛拉。学校里人们叫她多丽。表格的虚线上填的是多莉雷斯。可是在我的怀抱里,她永远是洛丽塔。”[14](P4)再次,在情节上,作者有意识地用多重叙述视角搅乱故事正常的发展,搅乱读者对故事正常的判断能力,打乱读者对故事的正常期待。四重叙事视角使得读者不可能站在某个固定角度探讨故事的线性发展过程。此手法的运用,“以至于读者的情绪会随之发生莫名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突出表现就是对自身认知的怀疑”[15](P144)。而对自身认知的怀疑使得读者在阅读时不断地否定自己传统的阅读经验,包括对作者原意进行追踪探索的想法。“本人碰巧属于那种写一本书并没有别的目的,只是想摆脱这本书的作者。”[16](P319)
《洛丽塔》同样解构了作品中心的阅读模式。这一解构主要表现于戏仿的叙事手段。作品中心阅读模式认为作者不能自主生产作品的意义,作品的意义是由互文性所决定。《洛丽塔》使用戏仿的手法解构了这样一种阅读模式。综观全书,戏仿手法比比皆是。比如,将洛丽塔参加的夏令营的组织者命名为夏洛莉·荷尔摩斯(Sherley Holmes),使其与柯南道尔笔下大名鼎鼎的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谐音;而小说后半部分不断追踪与反追踪的情节又使其具有侦探小说环环相扣的特点。如果按作品中心论的观点来看,这一侦探小说式的特点应能与别的侦探小说构成一系列互文并进而表达一种相似的结构。但《洛丽塔》的文本显然并不指向这种相似的结构,而是指向了对这一结构的不信任。以第一部第20章为例,亨伯特在与夏洛特游泳时想要杀掉她,作品中出现了对一个凶手的心理戏仿,“要干只需落后一步,深吸一口气,抓住她的脚踝,然后拖着这具尸体快速下潜”[17](P84)。但是,这一想象的结果却是“我无法说服自己下手”[18](P84),并最终指出刚才的凶杀只不过是诗人的想象,“而诗人从不杀人”[19](P85)。在这个过程中,戏仿的出现只不过是引起读者的某种特定的阅读期待并解构这一期待。在《洛丽塔》中,作者借双重主人公逻辑的相互解构,当其中一个亨伯特的叙事中出现了戏仿,另一个亨伯特必定会站出来告诉大家这只不过是一种戏仿,从而解构了由戏仿而形成的互文意义。以上文中提到的对侦探小说的戏仿为例,《洛丽塔》戏仿的目的并不是使其作品看上去像一个侦探小说,而是告诉读者本书绝不是一个侦探小说,从而拒绝将文本置于特定的互文之网,解构作品中心主义的阅读模式。
表面上看来,作者中心阅读模式和作品中心阅读模式的意义观是不同的,但是,在中心—非中心的二元结构中,二者却有着共同的追求:都强化阅读模式应追求一定的中心,排斥作品意义的多元化倾向。《洛丽塔》对作者中心阅读模式和作品中心阅读模式的解构,使我们认识到一种新的阅读模式:意义的去中心化。在《洛丽塔》中,作者自我解构了自己的原意,同时通过戏仿手法,使读者意识到意义的不确定性,进而解构了作品中心阅读模式。在具体的阅读过程中,当读者的传统的阅读期待一次次遭到否定之后,《洛丽塔》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作者拒绝回答的态度表明了一切,“对于本人来说,小说作为作品存在仅仅因为它能给人带来被我鲁莽地称之为审美快感的东西”[20](P323)。《洛丽塔》的阅读,就是期待读者参与的过程,“只要鲜血还在我写字的手中流动,你就和我一样参与了这件倒霉事,我就还能从这儿向远在阿拉斯加的你谈话”[21](P318)。
相对于《洛丽塔》之后具有更多解构主义元素的作者——如巴思、多克特罗和德里罗等,与他们无人物、无情节、无意义的作品相比,纳波科夫对人物形象、叙事和阅读模式的解构并不彻底,其作品仍有着中心化的痕迹,洛丽塔的形象也显得过于明确。但是,《洛丽塔》对单面性格人物形象、传统叙事和阅读模式的解构,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开始。可以说,《洛丽塔》的写作,引发了更多的以解构为目的的文学作品的出现,这些作品又为后来以耶鲁学派为中心的美国解构主义批评提供了特定的文学作品基础。这种承上启下的作用,正是我们今天探讨《洛丽塔》的意义。
[1]彭姝:《〈洛丽塔〉的后现代主义解读》,载《名作欣赏》,2005(9)。
[2][3]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5][6][8][11][12][14][16][17][18][19][20][21]纳波科夫:《洛丽塔》,桂林,漓江出版社,1989。
[7]彭佳:《“审美的福祉”:〈洛丽塔〉艺术手法试析》,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外国语言文学与文化卷)。
[9]李慧军:《论〈洛丽塔〉的双重结构及其表现内涵》,载《学术交流》,2008(7)。
[10]张薇:《〈洛丽塔〉的叙事奥秘》,载《当代外国文学》,2004(1)。
[13]纳博科夫:《文学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15]李慧军、潘慧影:《浅析〈洛丽塔〉的二重世界》,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