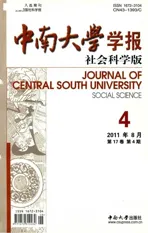传统中国与亚细亚生产方式
2011-02-09朱义明
朱义明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0)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总结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进程时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33)自从马克思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以来,他本人并没有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做出更多的解释与使用,以致于在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整个学界对这个概念内涵的阐发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性质等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已经被称之为社会科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自20世纪初以来,学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研究出现过四次高潮[2]。迄今为止,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讨论仍是热门话题,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点非常多,主要集中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亚细亚生产方式代表的历史阶段、中国是否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本文则重点在初步理清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的前提下,以中国封建社会基本政治经济框架为基础,就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传统中国超稳定性问题进行探讨与分析。
一、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提出与迄今的研究
(一)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相关特征的描述
1.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描述
19 世纪50 年代,马克思根据弗朗斯瓦·贝尔尼埃在《莫卧儿帝国游记》中的材料,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贝尔尼埃完全正确地看到,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3](265)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回信中,表示同意这种看法。他说:“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3](2650)接着恩格斯又继续分析“但是东方各民族为什么没有达到土地私有制,甚至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特别是由于大沙漠地带,这个地带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直到亚洲高原的最高地区,在这里,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而这是村庄、省或中央政府的事。在东方,政府总共只有三个部门:财政、军事和公共工程”[3](256)。“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4]
马克思指出:“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像在亚洲那样,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末,地租和赋税就合为一体……。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但因此那时也就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使用权。”[5]“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实际的公社却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6](473)事实上,我们知道在马克思所说的东方社会,或者说包括中国社会在内,土地历来是同国家主权相联系的,私人(包括封建地主)拥有土地,实际上只是一种对土地占有、使用与具体支配的权利,它固然可以给占有者取得财富提供条件,但是这只是一种相对所有权;在这个社会中所发生的土地买卖实际上是土地占有、使用与具体支配的让渡,它并不能否定国家对土地的绝对的所有权。
关于专制与政府的存在,恩格斯认为由于单个公社或个体的孤立性,基于它们彼此发生联系的需要,以及管理灌溉渠道、交通工具等公共工程的需要,便产生了高居于各个小公社之上的君主专制政府或者说中央集权的政府。他说:“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公共条件,如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以及交通工具等等,就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高居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6](473)
马克思认为,造成东方社会长期停滞的直接原因是东方社会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他说:“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6](473)东方社会结构中这种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能够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身生产出来,这种农村公社缺乏自我发展的紧迫要求和强大动力,分工和交换都缺乏真正的社会化的发展,这种发展被社会结构的机制严重地束缚和抑制,因而造成了东方社会这种自然经济结构的长期停滞不前。所以马克思针对与这种自给自足的公社还指出:“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历史的首创精神。”[1](33)
马克思在谈及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超稳定性特点的前提指出:“亚细亚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顽强也最持久,这取决于亚细亚形式的前提:即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生产范围仅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6](473)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结构中这种所谓的“亚细亚”特点,决定了东方社会不可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种没有内在发展动力的社会,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入侵才能动摇它的基础,使亚洲社会发生真正的革命。
2.国内学者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特征的描述
在国内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即: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科学与否,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内容和性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这里我们着重于国内学者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特征的理解与运用。
国内学者吴泽认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种形式》一文及其他有关著作中的论述,亚细亚生产方式有如下几个特征: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实行专制国家的土地国有制和公社的土地占有制;农村公社长期存在,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并成为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组织;政治上实行的是专制主义政权体制;具备这种生产方式的国家,还有管理公共灌溉工程等的职能。显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这种本质内容和特征,验诸古代东方国家的历史,是的确存在的。古代东方的奴隶国家,不论是古埃及、巴比伦,还是古印度和中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具备有上述诸特点[7]。国内学者江丹林认为,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是东方社会理论研究或说东方社会理论形成的深化阶段。因此,在归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的基础上,他描述了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的历史进程,即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提出的非西方社会的三个特点:土地公有、自给自足、闭关自守以及高度集中的中央专制政府。
国内学者武志军认为“在马克思看来,亚细亚所有制是原始所有制的一种形式,由亚细亚生产方式导致了亚洲各国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这种超稳定性的特点在于:封闭性、平衡性、中央集权性以及单一的国有化,“而且这种超稳定性必须要以频繁的或大或小的社会振荡为代价,也就是说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这种超稳定的结构从长远来看,对社会不仅不利甚至是极端有害的”。从这一观点出发,武志军批评了国际上流行的观点: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实现真正稳定的基础。他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农业文明的产物,与工业化有许多难以协调的方面。而且“由于没有带来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超稳定结构也就不会带来真正和长久的稳定”[8]。
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的认识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土地国有制、农村公社、自然经济和中央专制。
(二) 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
马克思终其一生没有给“亚细亚生产方式”下过明确的定义,但是通过上面资料的分析,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思想还是大体明确的。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描述东方社会结构的基本范畴。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东方社会存在着土地公有、自给自足、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基本单位是具有封闭性、落后性和顽强生命力的村社组织,居于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之上的社会政治结构是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马克思将这种土地公有、农村公社和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东方社会结构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土地所有制的公有制或者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过程中的一种形式下的一种社会模式,中国、印度、俄国都是从这种形式中发展起来的。而亚细亚生产方式带来的最令人吃惊的莫过于导致了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
结合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涉及的内容,以及学者们对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与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形成这样一种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土地公有、自给自足、封闭性以及专制主义。那么,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这些特性,就导致了这一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而这样一种超稳定性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不变,而是指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虽然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然而社会结构却没有变化。这种超稳定结构是通过封闭性和静态的形式实现的。它可能在各个历史阶段都存在不会被后来的社会经济形态取代。
二、目前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的不足与完善的尝试
(一)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的不足
亚细亚生产方式之所以被称之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除了这一社会结构分析的复杂性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马克思只是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一个概念,以及后续对这一社会结构非系统的研究认识,并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理论。对于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学说,其侧重点应该是古代东方文明中不同于古代西方文明的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或社会形态。至于对于这样一种形态,由于马克思从未到过亚洲,对亚洲或东方的研究主要是依据殖民官员的报告或报道,通过这些资料,对亚洲或东方的生产方式形成了一个相对的认识,所以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相比较于他的其他几种经济形态来说应该说是比较粗略和笼统的一个。同时,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出,对这一概念从未下过明确的、判断性的定义,很多阐发是基于后人的理解,往往带有自己的主观性意志,加之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信息也是残缺的、不完整的,使后人在试图对这一生产方式进行定性分析时缺乏足够的依据。应该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在科学不发达、资料掌握不充分的情况下用印度社会为摹本说明原始生产方式的理论,是一种并不是很成熟的理论。正是由于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存在于如此复杂的因素影响,使得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才会持续半个世纪而仍无定论,从而使得现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研究还不能形成成熟、稳定、科学的体系,因此各种结论的论证都给人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定性分析时缺乏足够的依据。
马克思在谈到亚细亚生产方式时,具体提到的东方诸国是印度、中国、俄国、埃及、波斯、土耳其等。但是这些国家显然并不都在各个方面完全吻合于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社会的总模式。例如,印度在政治方面与之不符,由于它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三面环海,一面依山)使其自古以来就很少受到侵扰,再加上气候湿润,雨量充足,所以相对来说缺乏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中国的不同点在于经济等方面,其土地制度更带有地主色彩,土地公有性不明显;而俄国的不同则在于缺乏马恩所说的水利灌溉的特点,其经济和政治的集权是由于其他原因造成(比如受到蒙古民族的入侵)[9]。对于这些差异,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并没有给出系统的答案。特别是马克思关于亚洲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论断,主要是依据西方著作家对印度莫卧儿帝国时期土地问题的描述所作出的,而这些描述似乎并不准确,早在公元前2700~1500年印度哈拉巴文化时期,就产生了土地私有制的萌芽。实际上,莫卧儿帝国时期带有土地公有制向土地私有制转化的一些特征,并不是纯粹的公有制[9]。此外,由马克思的土地公有、农村公社和专制主义这样几个亚细亚生产方式为要素,直接推导出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虽然有其合理的一方面,但感觉论证并不充分,是否这些条件就是充分条件?从条件推导到超稳定性是否还有中间环节?以及这种推导是否是必然的关系?超稳定性的最终被打破的条件是什么?难道只有受到资本主义方式的入侵才能解决吗?带着这些问题与思索,我们试图以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模式为标的,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研究与分析。
(二) 完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尝试
基于对马克思所描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我们注意到其中所包含的要素(土地公有、自给自足、封闭性、专制主义)与中国传统政治经济环境中所涉及的相对封闭、农业经济、大一统、中央集权几个要素几乎完全的近似。至于土地公有问题,国内的学者也已经大致有过比较一致的解释,中国历史上历来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土地私有,皇帝是所有土地的最终所有者,《诗经·小雅·北山》有诗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在中国私人占有土地,实际上只是一种对土地占有、使用与具体支配的权利,它固然可以给占有者取得财富提供条件,但是这只是一种相对所有权,土地买卖实际上是土地占有、使用与具体支配的让渡,它并不能否定国家对土地绝对的所有权。不管这种土地公有的解释有没有生搬硬套的嫌疑,总体而言马克思所描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的确与中国传统相对封闭农业经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社会形态比较吻合。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下,缺乏有效的对外贸易,社会财富只能进行内循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受到人口和土地产出量的限制,又使得社会财富总量处于相对有限的状态下,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形成是自给自足农业社会的客观需要,同时也形成了政府集团、豪强集团与劳动阶层这样主要的三个社会阶层,于是有限的社会财富就在这三个主体阶层之间进行分配与流动,而豪强集团通过土地兼并、权力对价、盐铁等垄断资源经营等途径,不断地进行社会财富的集中,并大量囤积,使得社会财富最终有流向豪强集团的趋势并且具有不可逆的特征。劳动阶层始终处于基本的生活线附近,土地是其创造财富的根本依靠,而政府税收、土地兼并、盐铁等垄断资源、权力对价这几个主要的财富转移途径最终导致了社会阶层的不均衡与主要矛盾,而这种不均衡与主要矛盾就导致了作为统治阶级的政府集团在肩负统治职能、管理职能与经济职能的责任下,形成了以“平衡”为社会管理与政治目标的社会政治需求,当这一社会政治需求与也同样产生于相同政治经济环境下的儒家思想意识形态有效地契合到一起的时候,就最终形成了以“民本思想”“重义轻利”“三纲五常”“德主刑辅”“重农抑商”“崇俭抑奢”等儒家思想为特征的“超稳定性”的农业社会结构。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儒家意识形态在这一所谓的“超稳定性”农业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儒家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通过精神层面的“义利观”等观念的强化,极力打压物质的、功利的思想,全力弘扬精神的、伦理的的思想,借以平衡劳动阶层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巨大不平衡的现实,并结合纲常伦理的社会关系结构,使基于封闭环境、自给自足农业经济、大一统、中央集权形成的生产秩序、财富流动模式、社会秩序和统治模式得以有效地固化下来,形成了所谓的超稳定性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然而在这一稳定环境下,还有一个因素必须着重考虑,就是土地兼并,由于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土地成为该经济体系中社会财富最主要的创造源泉,使得土地成为豪强集团最根本的追逐对象,“以末致富,以本守之”,这样就在客观上造成了与社会财富流动趋势相一致的土地兼并趋势,并成为最终打破政府集团统治平衡不可逆的根本因素,虽然政府集团已经试图将这一趋势的影响降低到最小。于是,在这一主要因素的影响下(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与偶然因素),在这种平衡被打破后,又由于重新分配了土地资源而进入新的相对平衡,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王朝周期性变迁的主要内因。然而,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秩序、社会财富的流动模式、社会关系秩序和政府统治模式以及契合这一传统政治经济环境的儒家意识形态却丝毫不受这一内部动态平衡周期性运动的影响,呈现出“超稳定性”。
在这里,我们借助于由传统中国农业经济基础以及内外部环境因素决定的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模式推导出社会的“超稳定性”结构,从某一个路径上较为系统地解决了马克思所说的土地公有、氏族公社和专制主义等因素到“超稳定性”的逻辑推导,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在这一环节上的完善。
三、传统中国与亚细亚生产方式
(一) 传统中国与亚细亚生产方式
在将传统中国与马克思所描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比较时,我们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特征的描述可以比较容易将传统中国与之对接上,特别是国内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学者对马克思及恩格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可能意思并不清晰或者并不完整的阐述,而把很多因素中国化。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特征的描述中更多的是提出土地公有、氏族公社或者村社制度以及专制主义,这里的“土地公有”是否就能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国土地模式划等号,以及马克思所指的氏族公社是否也能与自给自足的农业家庭单位划等号,依然是存在一定的商榷余地的,虽然彼此之间的确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此外,传统中国的确存在者所谓的“前市场经济”,并且具有一定的规模,与“前市场经济”相联系的还有相对发达的繁荣的城市,这在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构建思考中并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思维反映,在他的“超稳定性”构想中也没有论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意识形态因素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并没有体现出来,而事实上在我们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儒家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产生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有类似“超稳定性”社会结构的印度也形成了与其种姓制度相关联的宗教,俄国也将改造后的东正教作为其社会意识形态。
由于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并没有系统化,所以就存在这样两种的可能,一个是传统中国并不是纯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而仅仅是类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它有着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类似的基本初始因素,却也有不同与这些因素的其他因素和发展路径,同样也形成了“超稳定性”社会结构;还有一个就是传统中国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且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系统理论中的一个典型模式,但不是所有模式,只是各模式之间存在着初始与现实的某些共性,也存在着差异以及实现路径的不同,但最终都表现出社会的“超稳定性”结构,这就需要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二) 关于中国社会的“超稳定性”及其改变途径的辨析
在马克思看来,基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几乎是不可变更的,除非存在高于这一东方文明形态的文明打破东方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而这种打破往往是以侵入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马克思把这样的侵入以亚细亚的观点来审视,认为是历史的进步,例如对于资本主义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马克思指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马克思的分析得出结论:亚洲社会的这种稳定结构,自身不可能产生一个根本的革命。西方对亚洲的殖民侵略,对亚洲革命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中国和印度是当时亚洲举足轻重的国家,在中国由于西方的入侵,“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世界接触……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生地决斗中死去。在印度,英国人用蒸汽和科学破坏传统的经济基础的同时,又用火和剑把空前的政治统一强加于它。马克思指出:“是重建印度复兴的首要条件。并说,虽然在印度人民未摆脱英国殖民地枷锁之前是不会收到英国人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得到重建”[11]。
在这里,我们姑且把传统中国是否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搁置起来,就传统中国“超稳定性”社会结构的最终被打破进行一个探讨。不可否认的是,传统中国的确保持了长期的“超稳定性”,并最终由于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而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国的“超稳定性”社会结构,导致了中国走出封建社会,进入了现代化社会发展的进程,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历史实际似乎是吻合了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论断。然而我们不能够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就全球来说,公元1500年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分界点,在1500年以前,世界是孤立的,西欧被孤立在欧亚大陆的西端,中国则仍然在远东地区保持着其古老的生产方式。随着1500年以后全球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西方的资本主义在其不断加快的海外殖民事业中蓬勃发展起来,而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破土而出了。明清时期,中国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特征,到了清末年间,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发展缓慢,但的确还在行进着,如江南的丝织业,当时已经出现有上百织机的大户。另外造纸业、冶炼业、制茶业等许多行业,不但有雇佣工人的情况,甚至还出现了包买商人。只不过这些资本主义萌芽,在当时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相对比较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依然是社会经济的主流。我们注意到,16世纪至18世纪,西班牙、英国、荷兰、美国等殖民主义国家和中国贸易,带来大量银币向中国换取丝绸、瓷器、茶叶,从而导致长达280年的白银大规模流入中国的过程。据历史学家估算,从明朝到19世纪30年代,中国对西方国家贸易的白银入超达5亿两以上[12],而根据学者巴雷特提供的数据,即从1493年到1800年,全世界约85%的白银都产自美洲,那么世界白银产量的43%至57%可能都留在了中国[13]。而很有意思的是,这些流入中国的白银却不再流出,一位曾长期生活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传教士,在其1630年的著作中写道:“中国可说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我们甚至可以称它为全世界的宝藏,因为银子流到那里以后便不再流出,有如永久被监禁在牢狱中那样……”1597年菲律宾总督在给菲利普二世的信中不无忧虑地说:“所有的银币都流到中国去,一年又一年的留在那里,而且事实上长期留在那里。”[14]从这些数据与现象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自公元1500后,整个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海上贸易呈现全球化方向,传统中国不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由原来的相对封闭的地缘环境转向被动的开放,正如我们已经分析的,当传统中国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一旦多少地打开,就会触及传统中国的根本经济格局,传统的相对封闭的有限经济总量格局将呈现逐步被打破的趋势,而社会财富的流动也出现了海外流入的新路径,商人阶层成为最大的赢家,拥有大量的资本,并且也直接导致了商人阶层社会地位的实质性提高,商人被列入史籍,纂为族谱、传记、墓志铭之人数,远非前代可比。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新的经济血液或多或少地冲击着传统中国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格局,甚至包括儒家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变迁,邱溶、赵南星、黄宗羲等思想家时,已经形成“工商皆本”的思想[15],应该说无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程度之深浅如何,如果没有引发“鸦片战争”而任这一趋势延续下去,笔者认为传统中国社会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以及其在社会经济中所占比例的提升,社会各阶层新生力量的出现以及各方力量对比的博弈,中国传统的超稳定结构出现内生性解体、变动与革新,从而自我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尽管延续了近二千年的自给自足的“超稳定性”社会结构确实形成了很大的障碍。
依据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超稳定性”,以及对于这种“超稳定性”自身不可能产生一个根本的革命说法,显然并不完全适用于传统中国社会,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传统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格局下确实地存在着我们所定义的“前市场经济”现象,也就是有限同时也是统一的商品经济市场,这一商品经济市场能够相对容易地通过对外贸易与全球商品经济市场对接起来,虽然这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历程可能会很艰难,但却无法影响其呈现出在根本上改变传统中国经济格局的可能性。这样,马克思所描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超稳定性”,于传统中国来说,应该同时存在着由封闭环境转开放环境引发的自我革新的打破或者直接的外界入侵的打破两种路径。
结合以上所分析,如果我们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确定化与狭义化的情况下,显然传统中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虽然存在着某些该生产方式的特质。但如果我们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广义化,理解为东方社会存在着相对封闭、农业经济、大一统、强意识形态、专制主义、超稳定结构等要素的共性,同时也由于相对不同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格局产生的共性基础上的差异性,并可能导致几种特征明显的发展路径与社会形态,那么就需要在研究传统中国的同时,通过对印度、俄国、土耳其等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初步特征的地区与国家进行全方位的比较分析,从而真正建立其系统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体系。
[1]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3.
[2]朱政惠.1978年以来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研究的若干思考[J].史学理论研究, 1995(3): 17.
[3]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260−263.
[4]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140.
[5]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891.
[6]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473−474.
[7]吴泽.东方经济社会形态史论[M].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93:312.
[8]高天琼, 徐信华.国内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述略[J].湖北大学学报, 2005(3): 318.
[9]柴艳萍.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东方社会的深刻影响[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 2000(4): 1.
[10]徐少兵.马克思的历史分期思想与“亚细亚生产方式”[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1997(3): 53.
[11]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772.
[12]庄国土.16~18世纪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估算[J].中国钱币,1995(3): 8.
[13]Barrett, Ward."World Bullion Flows, 1450~1800", in Rise of the Merchant Empires: Long-Distanc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1350~1750, edited by James D.Trac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24−254.
[14]全汉升.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J].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学报, 1969: 66−67.
[15]吴晗, 费孝通.皇权与绅权[M].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