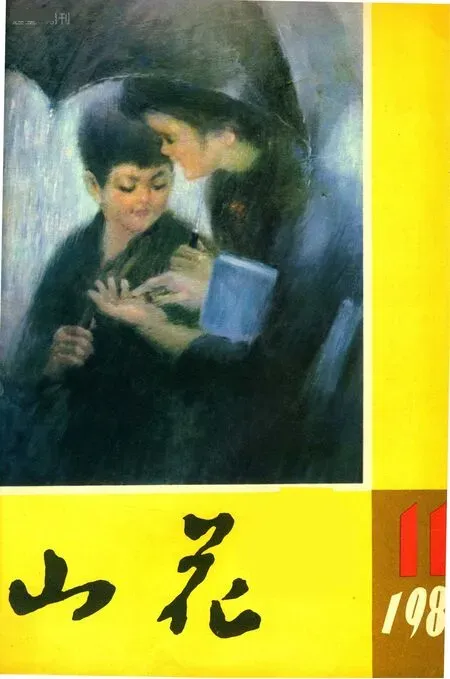老街的生命
2011-01-18陈启文
陈启文
老街的生命
陈启文
河流在浑浊地起伏,浮荡着南方春天的漂浮物。一条东江宿命般流到这里,已是下游,河流裹挟着泥沙滚滚而下,也带来了一座繁华人间城廓。十万株杜鹃花一夜之间全开了,南方总是充满了燃烧的信念,木棉花开,紫荆花开,一开就像热烈的、跃动的火焰。但这么多的杜鹃花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春风吹过大地,我的两眼已姹紫嫣红。
这里不是广州,也不是深圳。这里像广州,也像深圳。这种目眩神迷的幻觉在南方已反复出现,总让我把许多不同城市的幻像混为一团。走进南方任何一座城市,总要让我反复辨认,当幻觉消失却又忽然没有了方向。我好像已经忘了,我来这里,是为了寻找一条传说中的老街,但它如同早已不知去向的失踪者。挡住我视线的是一幢又一幢的高楼,它们像这个时代情欲旺盛、充满了力量的器官,在南方的阳光下坚挺有力地闪烁着光芒。这是一种占领的方式,一座崛起的现代高科技新城,理直气壮地占领了那座早已黯然失色的老商埠。我心里十分清楚,一座城市已经重新出生了一次。
对于一条老街和一些老建筑,遗忘也许是最好的状态。然而,就在你已然遗忘打算放下某个念头时,一个不经意的转身,便是转眼过去的日子。深深地望一眼,便有幽深的岁月气息扑面而来。一条暗藏在高楼大厦背后的老街就这样出现了。它安详,低调,淡定,像一个驼背的老人。街是石板街,但那些粗粝的、凹凸不平的老石板已经被撬掉了,新铺的石板是反复打磨过的大理石或花岗岩,连石头的斑纹也已经磨平,光亮,舒展,这上面没有了祖先走过的足迹,但适合小汽车在逝去的光影中驶过。听说在撬开老石板时出了一点意外,一条民国初年的蟒蛇像狐狸一样露出了尾巴。很多人都来好奇地围观,人们忽然想到这里还有一个隐藏得更深的传说,这里还暗藏着一条龙,一条石龙,它潜伏在东江最深的河底,蜿蜒着自上而下,偶尔会浮出水面翘首而望。它在望什么呢,兴许是在某个灯光与星光闪烁的夜晚看一眼这人间的福地。石龙就是个福地啊。也是在撬开这些老石板时,还发现了混杂在泥土瓦砾间的贝壳,这应该是在大海退却之后留下的,这样的贝丘遗址在珠三角随时都会发现,一旦某一片土地被深刻地揭示出来,你必然就会发现一些隐藏得更深的存在,远在新石器时代,这里便有人类聚居。曾经沧海难为水,一条民国初年的蟒蛇,实在算不了什么。
我放慢了脚步。这里有南方最慢的生活。一间间店铺迟到了早晨八九点钟才慢悠悠地打开。这里有很多杂货店,药店,凉茶店,竹器店,渔具店,花圈店,裁缝铺,琳琅满目七七八八的小商品,很多别的大街上找不到的东西,尽在这里。守着店铺的大多是一些女人和老头老太太,他们开始慢声吆喝,凉茶,凉茶哎!他们的吆喝会得到一些小贩的回应,麦芽糖——哎——糖柚皮——啊!这些小贩是没有门店的,他们挑着货郎担,走走停停,他们的叫卖声浑浊,沧桑,在不断拉长的声调中多次出现转折,伴随着咳嗽,和尘埃混在一起,听起来特别有市井味道。这些彼此呼应、互相传递的吆喝声,把岭南和石龙的一些土特产传达给三三两两从这里走过的行人,偶尔也会把那些繁华大街的人们召唤到这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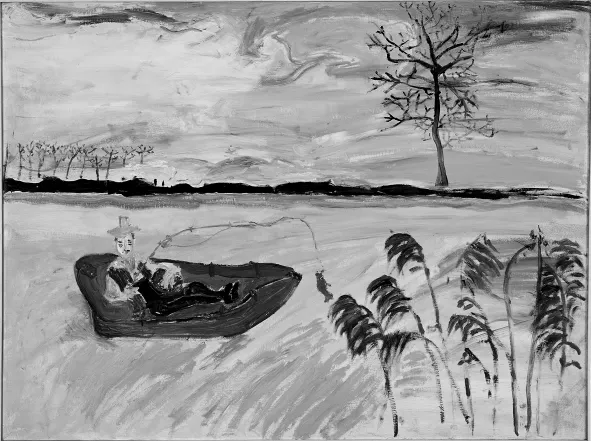
李雄伊作品·54
凉茶,看上去像浓黑的中药汁,它就是各种清热解毒的草药煎熬出来的,这是南方人最爱喝的饮料。哟,真苦!我看见几个打工妹在这里喝凉茶,只要是第一次喝,都会这样哟一声。但喝的次数多了,再苦,她们也不再说出来。那味道不是单纯的苦涩,还有十分古怪复杂的滋味儿。但喝下去了,又会转化为长久回味的清凉,连肺腑都是清凉的。这凉茶现在已经不是凉茶了,而是岭南文化里的一种重要元素了,喝凉茶不再是单纯地喝凉茶了,喝的已经国家非物质遗产了。麦芽糖和糖柚皮也是岭南的两样小零食,石龙李全和麦芽糖,已经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了。哟,真甜!每个人第一次吃又会这样哟一声。几个女孩子围着卖麦芽糖的货郎担,城里女孩的打扮,乡下妹子的长相,一看就是在附近某家工厂打工的打工妹。这里有很多的打工妹,在这十来平方公里土地上,就有近两万外来务工人员。一副货郎担,一块小小的麦芽糖,就让她们绽放出了甜美的欢笑,那红润的嘴唇绝对没有涂过口红。我在老街的一侧偷窥着她们,猜想着她们。两辆单车忽然并肩骑过来,一个穿着蓝色工装的小伙子拉着一个姑娘的手如同比翼双飞,这是在热闹的大街上不可能出现的情景。看着他们一骑而过的背影,我猜想,这可能是一对打工的恋人,也可能是一对打工的小两口。我曾经看到过他们擦完了机器又去擦汗的情景,但在这里,一条老街上,我看到了他们的欢笑和化成了一阵风的轻松……
下意识地打量着这条老街,我的目光已不像先前那样涣散。老街两边是中西合璧的老房子,或两层,或三层,楼下矗立着一根根顶梁柱,敦厚而壮实,用尽全力支撑起整个楼宇,坚持了一百年。我仿佛听到了它们沉重的喘息。这样的柱子可以成为女人的依靠,几个逛街的女子就慵懒地靠在上面。而一样东西只要坚持一百年,哪怕是一只寻常百姓家的青瓷小碗,也算是文物了。楼上,是一排排拱形的落地大窗,这样的大窗户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是非常罕见的。它属于西方,那些更接近海洋的民族。它的存在可以一直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后来广泛流行于欧洲,当一种流行历千年而不衰,就已经不是时尚而是一种经典了,而所有能成为经典的东西都源于人类的坚信。但直到近代这种欧式建筑才传到东南亚和我国岭南沿海一带。把它们带到中国来的不是传教士,而是那些漂洋过海在海外打拼之后的华工。就像现在进城务工的农民,他们在城里打拼之后便回家盖房子。他们带回来的不仅只有钱,还有他们觉得又漂亮又舒适的建筑样式。他们盖房子不止是用来居住,还要考虑自己和子孙的生存和发展,这些房子也就大都建在当年繁华的商业街衢上,楼上住人,楼下开店,前面是店铺,后边是作坊,在作坊里制造出来的产品,马上就可以在前边的店铺里出售。临街的门面一律向后退缩,这是对人的一种尊重和让步,哪怕这里寸土寸金,他们也要让出一条路来,从一座骑楼到另一座骑楼,屋宇之下的人行通道随着一条街衢而一直延伸,延伸得宽敞而深远。在烈日之下,当人们走进这柱廊式的通道,立刻就会感到一些荫凉。在风里来雨里去时,又有一条遮风避雨的路可以走走。在算盘珠子响成一片时,商业的铜臭味里也多少流露出了一些可贵的人情味儿。

李雄伊作品·57
这种在英文里被命名为Buildingoverhan的欧式建筑,在汉语中难以找到准确的直译方式,但一旦进入中国,它便成为了岭南的一种独特建筑,又渐渐超越了建筑的意义成为了岭南文化的一种独特象征。据说,骑楼最早是在东莞出现的,东莞比广州离大海更近。随后便风靡广州和沿海诸城。这是一个历史性事实。在这个过程中,又有一个历史性的倡导者和推广者,刘纪文。很多人都知道这位先生是宋美龄的初恋情人,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东莞横沥镇人。他任广州市长期间,把骑楼引进广州,这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为了改造广州的老城区。旧时的广州街,大多是明清时代的建造的麻石街巷和坊式商铺,阴暗,潮湿,狭窄,拥挤。作为一市之长的刘纪文,在下决心拓宽街巷的同时,也下决心把原来那种古老的坊式商铺改造成了新颖美观的骑楼。这样的建筑在那时的广州还是一种新颖的现代符号。刘纪文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儒雅绅士,在旧城区改造上他却是一个大刀阔斧的铁腕市长。这个人干什么好像都特别投入,特别容易进入一种状态。从当时的现实看,这其实也是对老城区的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只是当年的现实变成了今天的历史,这样的改造便成了历史对历史的改造。但历史也验证了这次改造的成功,他让广州变成了那个时代最繁华、最适宜人居、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

李雄伊作品·58
走进石龙这条老街,一下就感觉到了历史的漫长,这条街是当年岭南除了广州以外最长的一条骑楼街,现在又是岭南的骑楼保留得最完整的一条街。在历史的演变中,骑楼已涌现出太多的样式,哥特式,巴洛克式,南洋式,中国式,石龙的骑楼以仿哥特式为主,又经过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造,既有西洋风格的浮雕装饰,更有以松、鹤、麒麟、八卦等中国岭南文化元素的装饰,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在骑楼上隐秘地汇合,中西合璧,天衣无缝,好像它们原本就该在一起。我在此间穿行,如同穿过黑白电影和老照片中的情景,无处不在地洋溢着一种旧日洋场的繁华,街道两旁商铺林立,一路看过来,有著名的华茂烟铺,王珍金铺,还有香港著名影星郭富城的祖居——郭忠城金铺,这里还有广东当时最先进的电力碾米厂白花花的大米装上货船,通过东江和珠江的黄金水道,运到广州和香港,又把白花花的银子运回来。在那个年代,这里就开设了邮局,装上了电灯、电话,这南粤的商贸重镇,白日里车水马龙,涌动这如潮的人流,日落后又有万千灯火照亮了一个个灿烂的夜晚。早在明末清初,石龙已是与广州、佛山、陈村齐名的岭南四大名镇。在历史上石龙曾三次设市,而且一度是省属直辖市。如今变成了东莞的一个镇,石龙多少有些委屈了。
或许,就在我走着的这条路上,孙中山先生也一次次走过,在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石龙是离广州最近的前线重镇,中山先生曾十四次奔赴石龙指挥作战。或许就是他匆忙而踏实的脚步,把一条路走成了中山路。在这条路上走过的还有英气勃勃的周恩来。在国民革命军东征期间,石龙曾是东征军的大本营。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曾三次来到石龙,发表了两次著名的演说。他在这里留下了一座青砖建造的演讲台,他还伫立在这里,伫立为一座东征的铜像。值得铭记的先烈还有李文甫,他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唯一的东莞人,石龙人,在攻打两广总督府的激战中受伤遇害。当然,在这条路上走过的还有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在第二次东征中,蒋介石在遭遇惨败后,眼看坚持不下去了,他在绝望之中欲拔剑自杀,应该说他不缺乏勇气,杀身成仁无疑是一种决绝的勇气,他缺乏的是坚持的毅力。一把短剑已经举到了自己的胸口,但被他的学生陈赓一把夺过,陈赓背着他突出重围,逃过了死神的紧紧追赶,这不止是演绎了一段英雄传奇,也不止是挽救了一个人的生命,他挽救的是中国未来一段的历史。否则,历史将被彻底改写,没有了蒋介石这样一个主角,中国的现代史将是另一个版本,而杀身成仁的蒋介石很可能是一个至今被后世铭记的革命先烈。
坚持比决绝更难。如今,在广州,在东莞,在岭南诸城,许多的老街和骑楼都被拆除了,被一片片现代新城所占领,这是必然的。怀旧不属于南方,这里不需要怀旧也没有时间追缅什么,南方的现代汉语词典里充满了工业和现代化词汇,资本,研发,创新,高科技,GDP,出口总额,CPI,品牌,电子信息,EMC显示器……我在此叙述,却无法描述,我的叙述里或许有太多的颠倒与错置。对这些我原本充满了抵触情绪的词汇,甚至是对纯正的汉语构成了污染的词汇,现在我也能够坦然地接受了。南方就是由这些语词组成的,我就像感受这里的阳光、海风、荷尔蒙一样感受着它们的灿烂、活力和无与伦比的激情。这也是必然的。我来南方绝对也不是为了怀旧或追缅而来,让我理直气壮的一个理由,不就是因为这里的现代化程度和雄厚的资本已远远超过了我内地的故乡吗。在南方,我永远在不停地仰望,这也是我不断重复的一种姿态。

李雄伊作品·64
偶尔也会看到一些骑楼,在广州西关,在东莞可园老城区的凤来路、大西路和维新路一带,但由于年久失修,到处破破烂烂,东鳞西爪,只余一些断垣残壁,仿佛岁月中剩下的一些事物。它们的存在,仿佛是一种颓败而苍凉的坚持,好像在看谁能坚持的更久。拆,还是不拆?很多事都经历了过度的诠释,也成了现代人的一个悖论。很多地方拆了残破的老街,突然又后悔了,又开始拆刚建起没有多少年的高楼,然后建起一条条仿古的明清街、骑楼街。这是制度的强大实力,一个市长就可以把一座城市锻打一次。换一个市长又可以重新锻打一次。走进石龙的这条老街,看得出,它们也被重新修复过,粉饰过,古朴的气息里已混在了太多现代涂料和墙漆的气味,但骨子里的东西还属于过去的岁月。它们不是剩下的事物,而是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在这些老建筑的背后,是石龙人在抵御着商业大潮和强大诱惑中的艰难坚守。这样的城市中心地段,如果把这条老街交给建筑商来开发,这里的每一颗生锈的钉子都会变成金子。但石龙人对中山路的骑楼一直坚持不拆,一栋也不拆,不但不拆,还将进行原样原貌的重点保护。但如果仅仅以文物的方式保护下来,是否又是它们最好的归宿呢?中国大地还有太多比它们更重要更需要保护甚至急需抢救的文物古迹,如果把它交给石龙一个镇来保护,对这里的纳税人将是难以承受的重负。石龙人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在保护的同时把这里建成一条商业旅行步行街。这是它们的本质,它们原本就是一条商业街和商铺。我觉得这是石龙人可以找到的一种最好的方式,一种既能保护历史又能激活历史的方式。
没有历史内涵的老街和老建筑是浮浅,仅仅只是作为怀旧或追缅而存在老街和老建筑也只是另一种老照片式的陈列。房子得有人住,店铺得有人开,街道得有人走。它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呈现隔世的沧桑,还应该散发出生命的气息,让人感觉它的灵魂,听得见它的心跳。如果不是这样,哪怕把它们保存下来,也不过是一张历史蜕化的空壳。石龙的这条老街还是活的,听着一声声拉长了的吆喝声,让我觉得,很多早已消失的事物又像失踪的灵魂一样回归了这里。
老街上的另一些风景,是那些三三两两的老人,他们不知道自己也成了岁月中的一种风景。他们在这里消磨着多余的时光,而一条老街的故事,也许是他们一直会唠叨到死的话题。一些老人在这里下象棋,还有一些摆残局的职业骗子,都进行得十分缓慢,一盘棋漫长得可以走上一整天。而一盘残局若是遇到了真正的高手,一直下到天黑也许还是一个悬念。我甚至还看到了几个外国人,他们来这里干什么呢?他们显得十分高兴。他们是不是觉得走进这条老街让他们有一种回到故乡的感觉?一个金发女郎拿起一只在某家小店里出售的漂亮红珊瑚,在头上比划着,她可能把它当成一个头饰了。我以为她会买走的,很便宜。我像那个急切的充满了渴望的店主一样,希望有一笔成功的交易。但金发女郎比划了几下又把红珊瑚放下了,然后又走向了另一家小店。
在这里开店做生意无疑也是一种坚持,门庭冷落,顾客稀少,看那些店主的表情,在执著的守望中已夹杂着焦虑疲倦之色。他们也许要一直耐心地等到蝙蝠开始在老街上飞舞,这里才有更多的行人和顾客出现。这里最多的顾客还是那些刚从流水线下来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他们奔这里来,是可以淘到比淘宝网上更便宜的便宜货。三块钱两双袜子还贴着名牌的标签,趁人不备,还可以眼疾手快地偷走一双。各种地摊也在落日浑圆下摆出来了,地上堆满了游戏机、盗版碟和正版的黄碟,这是男孩子们最感兴趣的,一双双手伸向那里,有的手上还沾着油污,偶尔还会看到一些残缺的手,可能是被机器轧断了手指或轧变了形。一双双手像鸡扒食一样,这就是他们的精神食粮,可以给他们越来越机械的生活带来刺激,带来性幻想……
我看见一个英俊帅气的男人,戴着眼镜,他在这里摆摊。有人说,他前不久还是一个老板,最早就是从练摊开始发迹,住进了高尚住宅区,开上了靓车。现在,他又回来练摊了。这不是行为艺术,也不是一个富翁想要重新体验一下他当年艰辛惨淡的起步。他是真的在一场危机中完了,把房子卖了、车卖了还抵不上他欠下的债。南方就是这样的,一个摆地摊没几年就变成了某家大超市的老板,一个捡破烂的腰缠万贯,而一个老板刚刚赚了数百万,没多久又背上了上千万的巨额债务,连乞丐也不如了。但没完,只要你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南方就会给你奇迹般的机会。在这样的大起大落中,南方的意志总是超出一个文人的想象,也让我百思不解,匪夷所思,一个人已经拥有数百万上千万了甚至是亿万富翁了,一生一世也不愁没有钱花了,子子孙孙只要守住他们的家业也足以过上养尊处优的生活了,他们还要赚那么多钱干什么呢,发财是有命的,投资是有风险的,当你觊觎着巨大的利润时,也蛰伏着巨大的风险。然而,南方永远在一个文人思维的逻辑和情理之外,我在南方还很少看见一个觉得钱已经赚够了的富翁,一直到死他们都会保持着创造财富的激情。这也正是南方无与伦比的激情。
我在街灯温暖的光晕里偷窥着,一个刚刚经历过大起大落、背着巨额债务的南方男人,他是那样从容淡定,一条腿伸向前面,用一条后腿保持着平衡,这是一种随时都准备出发的姿态,或在一种下意识中完成。而更真实的,是他把接过的一张张皱皱巴巴的零钞,一元两元的,在手掌里仔细抚平,仔细地数过,然后折叠好,放进他的牛仔裤口袋里。他的这个动作,让我两眼咸湿,像海风的味道,一直伴随着我走出这条漫长的老街。
河流在浑浊地起伏,她已不太重要。一条广深线早已取代了当年的黄金水道,从石龙北上广州南下香港的距离,那条节奏缓慢的水路,一条船差不多要走上一天,现在已经缩短到了半个小时。我没有在这条河边停留,就直接奔向了每隔十分钟一班的和谐号。在南方这个春风沉醉的夜晚,在十万株杜鹃花簇拥的南岸新城景观大道上,我疾走如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