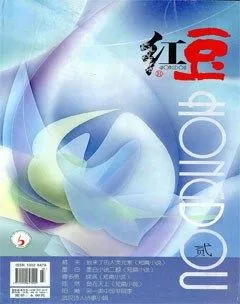鱼在天上(短篇小说)
2011-01-01陈然
红豆 2011年2期
陈然,男,1968年生。江西湖口人。已发表中短篇小说200多万字。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幸福的轮子》(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长篇小说《2003年日常生活》、《精神病院》等。作品多次被各选刊转载并入选多种年选。现供职于江西省文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我真不明白,她究竟要怎么样。难道我对她还不够好么?我自认为我还算得上一个好男人。我从不在她面前摆男人的臭架子。家务活我抢着干。洗起衣服来我比她还快。钱柜的钥匙,从来都是她管。她要什么,就可以买什么。当然,她并不乱买东西,虽然有时候会走神。她不像我认识的那些虚荣心强的女人,无论是衣服,还是手机,各种首饰,都想天下第一。如果不是我提醒,她几乎忘了要给自己买衣服。她的手机老掉了牙。我要她换一个,她不肯,说,又没坏,干吗要换?我给她买过一只白玉戒指,她也没怎么戴。其实她戴戒指是很好看的。她的手指是那么长,真的像书上写的,像葱尖一样。比电视上的手模要好看百倍。最让我惊讶的是她的皮肤,一接触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要过敏。那年我去外地玩,有一种手镯,既便宜又好看,我买了一只回来给她,谁知,她只戴了一会儿,手腕就起了泡,好像被什么烧伤了一样。还有化妆品,也是一样。她跟它们简直无缘。我说,我娶了一块试金石做老婆。我又笑她天生丽质。不过我说,你这个天生丽质可没为你带来什么好处,却为我节约了不少钱。我们互相开着玩笑。那时,我们多么快活。
可出了那样的事情后,我的快乐就不翼而飞了。有人说,是我对她太好了,把她娇惯成了这样。他们说,要是你对她严厉一点,或者来点家庭暴力,恐怕根本不会出这样的事。女人就这样,要你压她她才舒服。说着他们哄笑起来。我有点生气。他们是我的顾客,每天都要来我的小店聊天打牌。那台麻将机几乎每天都能为我带来八十多块钱的收入。要不是照顾到这一点,我就跟他们翻脸了。我很不喜欢他们用那种口气谈论我老婆。那是下流的口气。同时下流的,还有他们的眼神。有时候,他们的眼光像老鼠尾巴一样从我老婆的身上脸上溜过去,我恨不得上前猛踩它们几下。出了那样的事情后,我隐隐觉得,他们想我捉住老婆猛打一顿好让他们来看。是啊,我知道很多男人都会这么做的。见我一再不肯动手,他们急得不行。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我也想好好教训她一顿,可我就是下不了那个手。我把手拿起来,又放下,拿起来,又放下。最后我狠狠打了自己一巴掌。当然,我没让他们看到。我情愿打自己,也不肯打她。打一个人是那么容易的吗?尤其是一个女人,何况她还是百世修来与自己同床共枕的老婆。即使出了那样的事,我还是忍不住对她好。我不对她好对谁好?她长到二十多岁,忽然连父母都撇开了,跑来跟我过日子。我吃什么她也吃什么。我让蚊子咬她也让蚊子咬我。她说,我看你比看自己的老子娘还亲呢。这样的人,我不对她好行么?就是她不对我好我也要对她好的。她不理我,我理他。她发呆,我不发呆。她想跑出去,我让她跑出去。她回来跟个没事人一样,我也装作没事人一样。
我都觉得自己有点低声下气了。可在自己的老婆面前低声下气要什么紧?对她低声下气,我才舒服。哪怕要我在地上打两个滚我也心甘情愿。对她不低声下气,我就很难受。我要是当了国王,肯定也会烽火戏诸侯。我要是范蠡,肯定也会带着西施去隐居。所以,我从不后悔自己对她的好。这次,听说我老婆又跑了,店门口的人一下子又多了起来。他们装出关心的样子,说,你老婆什么时候回来啊?难道你又不知道她去哪里了么?还有一个人故意一惊一乍地问我,这是你老婆第几次往外跑啊?
其实我敢打赌,他比我记得更清楚。
是啊,这是她第几次“跑”呢?——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词好了。听我这样说,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是在跑步呢。好像她走着走着,就跑了起来。可用逃跑,也明显是不合适的。因为并不用谁去寻找,她自己会回来。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那个人说得对:往外跑。可仔细一想,又觉得不对,是废话。一个人不往外跑难道往里跑么?
总之,她跑的时间是一次比一次长了。我估计她大概是越跑越远了。头一次,她两天就回来了,第二次,她花了三天半,第三次,五天。这一回要几天,我不知道。我累。我想发火。我真的要发火了!我要看店,照顾孩子,还要进货,洗衣做饭。这次,我下决心了,她要再这样下去,我就到报纸上登寻人启事,或者到法院起诉离婚了。我受不了啦,哪怕把财产全部给她,我也要离婚!她要什么,我都给。她不是要自由吗,我让她自由好了。有个教授在电视里说了,要自由就不能要平等,要平等就不能要自由。还真有道理呢。说不定,她要是听了这话还会说,自由不是谁给的,谁要你给了?那好,我换一种说法,让她给我自由好不好?因为她到外面自由去了,我就不自由了。我也要自由。
可是,她真的是要自由么?我不能肯定。如果能肯定我也就毫不犹豫了。可这样一来我就要犹豫。她就像一只鸟,看到天空,忽然想飞了,但如果整天整夜在天上飞,行么?她总要落到什么地方来歇脚的。我就是她歇脚的地方。没有我,她就要一直飞呀飞,这样,她会累死的。想到这一点,我又心软了。我不能跟她离婚。除非她跟我离。她要是跟我离,说明她找到了别的歇脚的地方。她不离,我就等着她回来。
等她回来了,我就跟她说,谢谢你。
我知道,如果我把这话当着大家的面说出来,他们肯定会笑死我的。你不揍她已经很不错了,干吗还要谢她?!他们会说。他们说的没错。其实我也不知道谢她什么,但我就是想这么说。这样说了,我心里才舒服。
那天,我给小区里的一户人家送嘞酉。他是新搬来的。我一眼就看出来了。站在他家门口,我眼前一亮。按道理,小区里的人家,都是新买的房子,大多装修得不错,但没有谁家里让我这样眼前一亮过。事后我想起来了,他家客厅的墙上挂了一幅很好看的画,那画镶嵌在玻璃框里,像是中国画又像是外国画。桌上还有几本书。它们散放在那里,看上去是那么熨帖干净。我贪婪地吸了一口气,放下啤酒,他把钱递给我,说,谢谢!这时我正准备转身下楼,我以为自己听错了。便回过头来望着他,他朝我挥手,又说了声谢谢。我一时竟不知道怎么回答,低下头,像个小偷似的仓皇跑掉了。因为我从未受到这样的礼遇。明明是他帮我做生意,让我赚钱,按道理,该我谢谢他,可他却说谢谢我。弄得我像拿了不该拿的东西一样。事实上,那天我还真的拿了不该拿的东西。我多收了他两块钱。因为我每次送货上门时,那些人都要跟我讨价还价,不少两块钱他们就不高兴,其实我说的是实价。后来我就故意抬高价格,让他们来做减法,好满足他们爱占便宜的心理。谁知这个人不还价。这多收的两块钱让我难受了好几天。
我要像那个人很尊重地对我说谢谢一样,也对我老婆说一声谢谢。我似乎明白了,谢谢的意思,并不完全是谢谢。想到这一点,我心里充满了柔情。我已经不像开始那样焦躁不安了。这天,在他们闹哄哄的出牌声中,我像老婆平时那样坐在柜台里,望着外面。我感觉她悄悄藏在我身体里,我就是她。我试图像她那样去看她平时所看到的一切。在我看来,她似乎永远保持着这个姿势,现在,我也要把自己藏到这个姿势里去。我被自己的思维搞糊涂了。不知道我是我还是我是她了。有时候,她是一个姿势,我看得明明白白;有时候,她却像是一团雾。她坐在那里发呆。我不知道她究竟在想什么。她似乎一点也不快乐。哎呀她为什么不快乐呢?我真搞不懂。在老家,我们是多么让人羡慕啊。我们从乡下出来,用自己打拼来的钱在省城开了这个店。我们赚了不少钱。可她仍不快乐。想到这里,我又开始生气了,既生她的气也生我自己的气。她不高兴直接说出来好了,我最怕她把什么都关在肚子里,她光是不高兴,而不让人知道她为什么不高兴,我真受不了!
我的目光掠过桌上的电脑屏幕、棒棒糖、打火机和口香糖,朝外面望去。我首先望见的是那个公交站台。他们说,那天,我老婆出门的时候,跟平时没两样,她挎包都没背,他们还以为她要去逛街。这段时间,市内在搞一个很大的博览会,听说有的单位都放了假,所以公交特别拥挤。他们说,他们以为我老婆去那里了。其实我知道,她根本不会去凑这样的热闹。有时候,看她坐在那里发呆,我就说,你也去打牌啊。打牌的确是不错的消遣,说不定,她一打牌,就不会往外跑了。哪怕她天天打牌,也比往外跑好。可她不肯。以前她倒是打过,最疯的时候两天两夜不睡觉,后来不知怎么的,忽然不打了。我以为是生意渐渐忙起来了的缘故。那时,城市刚发展到这里来,路面都没弄好,那边又有一条大水沟隔着,生意清淡,人也打不起精神。几次我都想把店面盘出去,改行干别的。但她不肯。她说要是修了桥,这里马上会发展起来的。她还真有眼光。不久,政府修了桥,铺了路,搞了绿化,通了公交。那两所职业大学的学生可以过桥来买东西了。
远远望见一辆公交车过了桥。等车的人开始骚动起来。车还未到,他们已开始拥挤。公交车里黑黑一片。
对,公交车,我忽然明白,说不定问题就出在公交车上。看见公交车,就想坐上去往外跑。真的是这样么?
眼看着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为什么她反而坐不住了要往外跑呢?那时,我们坐在店门口,眼巴巴盼着生意好起来。那种盼望,现在想起来是那么甜蜜,值得回味。看到来店里买东西的人,是那么的亲切,恨不得上前拉住他们的手。每做好一桩生意,她都会高兴得像小孩子那样跳起来。那时,她正怀着孩子,她的脸上有许多雀斑,可我一点也不觉得难看。对于孩子,她也是有着向往的。她恨不得马上把孩子生下来,好看看他或她是什么样子。她红光满面,那些雀斑好像花粉一样被大风搅动起来,漫天飞舞。但后来,通了公交车,她的心思就不在店里,也不在孩子身上。她做生意像是公事公办。对孩子,也越来越随便。孩子要什么,她说,你不会自己去拿吗?孩子摔跤了,她说,你不会自己爬起来吗?她望着那个公交站台,出了神。刚开始,我以为她看到了什么熟人,但并没有什么熟人走下来,也没有什么东西引起她的注意。车开走了,她还那样望着。望着车屁股越跑越远。她的样子让我有些心慌。我说哎,哎,她转过头来,望着我,却并没看见我。不一会儿,她又转过头去。我不懂,那里有什么好看的。景象是相似的。人们上车,下车,裤脚有长有短,鞋跟有高有低,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区别?有两次,我倒是看见有人趁别人上车把手伸进别人包里。我忽然意识到那就是小偷,我想喊,又忍住了。我的店在这里,又不能藏起来,要是人家报复我,我怎么办?
但她可以一整天坐在那里望着站台发呆,除非玩电脑。
因此又有人说,你老婆就是玩电脑玩出毛病来了,从我到你店里来打牌时起,就经常看到你老婆在玩电脑。电视里不是经常说,好多年轻人玩电脑不是抢劫就是杀人,都玩到牢里去了么?女人玩电脑更不得了,容易上当受骗,被人骗财又骗色。
他的话让我心惊肉跳,但我并不赞同。难道没有电脑,就没有人被骗,就没有女人离家出走?我很反感有的人把什么责任都推到电脑身上。这电脑,我也用。其实我比她先学会电脑。那时,为了到外面打工,我还参加了县里的电脑培训班呢。后来她也去了。电脑有什么不好?在上面可以玩游戏,打字,听歌,看电影,还可以发帖子,炒股。哪怕跟美国人聊天也不要钱。照我看,要是每个人都有了电脑(尤其是农民),中国才真正地发展起来了。说电脑不好的人,要么居心叵测,要么是个傻瓜,完全被欺骗了。
当初,正是看她无聊,我才买了电脑的,只是没想到,有了电脑,她反而更无聊了。坐在那里发呆的时间也更长了。有一天,她不知不觉站起来,移动脚步,朝公交站走了过去。我以为她不过像往常一样,到市内逛商场去了。有一段时间,她对逛商场跃跃欲试。每次回来,都要给我和儿子买很多东西。其实有些东西,我们自己店里有,她居然忘了。我提醒她,她噢了一声,有些漫不经心。不过只要她高兴,我也无所谓。但那天,到了下午,她还没有回来。我眼巴巴望着外面,数着从公交车上下来的人。一个,两个。一辆,两辆。还是不见她。儿子从幼儿园回来,要妈妈,我说,妈妈逛街去了,给你买好东西去了。可直到晚上,直到旁边的水果店、建材店、理发店、炒货店、服装店都关了门,她也没有回来。这是从没有过的事情。我一遍遍打她的手机,都是关机。我真的慌了。我一会儿紧盯着电视里的《都市现场》,一会儿听到公交车刹车声又跳出来。听说,有个人在《都市现场》里看到一个地方出了车祸,镜头拉近,他一看,发现竟然是他老婆!我担心这样的事情也出现在我身上。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幸亏儿子懂事。那不是一般的懂事。他说爸爸别急,妈妈会回来的,回来了还会更漂亮的。我一听这话,很生气,恨不得狠狠给他一巴掌。他妈妈出去没回来,他居然还有心思说她漂亮不漂亮。后来我冷静下来。我记起来,我老婆每次向公交车奔去时,她眼睛发直,脸上是放着光的。儿子说对了,两天后,她回来,果真比以前更漂亮了!我肚子里像是装满了子弹,我无数次地设想怎么向她射击。可一见她,我却哑了火。她什么也不说,我什么也没问。不是我不想问,而是我了解她的性格,如果她不想告诉你,不管你怎么样,她也是不会回答你的。哪怕你骂她,揍她。虽然我从未试过,但我感觉就是这样。那时,她家里人反对她嫁给我,嫌我穷,把她关在屋子里,她就不吃,不喝。家里人拗她不过,才把她放出来。她每次偷偷出来见我,回到家里任父母兄嫂怎么问,就是不吭声。有一次,她父亲气极,把手里的东西朝她扔过来,出手后才意识到是一把竹刀,还好,没伤到要害部位,但额角上还是留下了一道月亮型的疤痕,阳光一照便闪闪发亮。那时,在我眼里,它更增添了她的个性和动人。可现在,它却深深刺中了我。我现在的角色是以前她父母兄嫂的角色,那么我呢?现在谁在担任我的角色?我眼睛冒火。她倒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脚步轻快,十分麻利地打扫着卫生,把货架也重新整理了一遍。好像她在外面学了什么手艺,重新一摆,那货架倒也焕然一新。忙完这些,她就坐下来,把那些红富士苹果擦了又擦,似乎要擦得跟她一样热气腾腾,红光满面。看到那些漂亮的红富士,我火气又消了很多。这种红润湿亮的水果,我甚至舍不得去咬它。我这人,真不争气,老是在好看的事物面前心软。我注意到,整整一天,她没再朝那个该死的公交站台望上一眼。她像是一头母牛,已经吃饱喝足,该美美地反刍一番了。我不知不觉原谅了她。虽然我不知道究竟该原谅她什么。她是否真的出轨了,跟什么人约会去了,我不知道,也懒得追问。如果我还爱她,追问起来又有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不爱她,追问起来就更没意思。她回来了,就说明她还爱我。至少还爱我们这个家。她不肯回答,说明她不想撒谎。难道我要逼她撒谎么?难道我要把她逼成一个爱撒谎的女人么?我最讨厌爱撒谎和虚荣心强的女人。爱撒谎的女人都爱虚荣。如果这样,还不如让人直接拿刀子在我胸口划几下来得痛快。这说明,她还跟以前一样尊重我,也尊重她自己。要是我揍了她,那只能显示我的穷途末路。
我们又回到了以前的生活轨道中。她守柜台,洗衣服,做饭,我进货,送货,到幼儿园接送孩子。日子又平稳起来。但我心里总不踏实,总觉得迟早又会发生点什么。果然,没过多久,她又神不守舍起来,那红富士的光泽也渐渐暗淡了。我找来布巾用力擦也没用。我明白,它们跟她一样灵魂出窍了。她的灵魂不在身上,整个人自然也就没有了光泽。我苦恼。揪心。为了让她快乐,我想了种种办法,可我的努力带给她的欢乐都那么短暂,她很快又不快乐了。我唯一的办法就是眼睁睁看着她再次出走。这时,她就像一片薄瓷,一碰就碎。有一次,我去景德镇,看到那里的瓷器,那种美,我真的一下子说不出。
于是我借故去办一件什么事。我知道,只要我在店里,她是不会当着我的面跑开的。她倒是挺照顾我的面子啊。我悲哀地笑了笑,朝桥那边走去。果然,等我回来,她就走了。我靠在那里,感到分外惆怅。就像我们刚谈恋爱时,每次看到她离开所感到的惆怅一样。
我又开始了期待。奇怪,好像我们还在恋爱。这次,我实在忍不住,查了她的QQ。有人说,电脑里肯定有文章,要我看个究竟。电视里播的那些案件,通常是在QQ上查到线索的。我没答应。我不想让她的秘密公布在别人眼里,就像她不想当我的面往外跑一样。但到了晚上,我把店门关好,等儿子上床睡了,又开了电脑。
我只在她的QQ签名上看到这么几句话:
云在哪里?
云在水里。
鱼在哪里?
鱼在天上。
那天晚上,我抽着烟,独自坐了很久。我在想着她的那几句话。然而我脑袋想痛了,也没想出个所以然。云在水里,那天我站在桥边就看到天上的云倒映在水里。但鱼怎么会跑到天上去呢?我真是个不善用脑子的人,只能想些浅显、简单的问题,一想复杂的、找不到答案的问题我就头痛或昏昏欲睡。我强迫自己用力想,结果很快就睡着了。
我被什么烫醒。原来是烟头掉到裤腿上,在上面烧了一个洞,接着掉到我的鞋面上,贴着了我的脚骨。我跳了起来。还好,要是烧到别的东西,后果将不堪设想。
那个客厅让我眼前一亮的人来买葡萄酒。毕竟,夏天已经过去了,现在是秋天。秋天是多么好看。自从上次多收了他两块钱,我看到他一直不好意思。我猜他以后再也不会来我店里买东西了。但他似乎并没发觉我上次多收了他的钱,照样来我店里。他买得最多的是葡萄酒。买这种酒的人不多,我每次去批发市场进货,都不禁要想到他。我会给他挑一些价格和酒质都比较公道的品种。这天,他在柜台边站了一会儿,忽然说,有意思。我问他什么有意思。他说,你老婆有意思。他又说,你也有意思。
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意思。甚至,我觉得他那有些居高临下的语气刺伤了我。我礼貌地笑了笑,没做声。我很高兴受了他的伤害,这样,我们就扯平了。当然,这只是我的气话。我跟他挥手再见。他穿着整齐,背着公文包,在我店门口上车,下车。每天都那么准时。如果他没出现,那一定是周末。要到下午,他才到桥头边去散步。有时,他来问问我又进了什么酒。或站在那里看一会儿人家打牌。不过据我观察,他的眼力和心思并未在牌上。他目光柔和,清澈,让人看了舒服。如果他站在店门口,他总是把头仰起来,朝什么地方张望。有时候,我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可我什么也没看见。每个人都有期望,也有渴望,他在望什么呢?难道他也想往外跑,或者忽然产生了舍弃一切的冲动?
有一件事,我在心里藏了很久。我想,等老婆回来了,我一定要告诉她。那一次,我去火车站取—个托运的包裹。很久没去火车站了,我忍不住四处走了走。这样,我就来到了铁轨上。站在四通八达的铁轨旁,我忽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随便地跳上一列车厢,管它把我带到哪里。这车与那车仅一拳之隔,可它们却南辕北辙,跑向完全不同的地方。我多想试一试。我多想探个究竟。我被这个魔鬼般的念头迷住了。它强烈地折磨着我。这时,一辆列车正在开动,我几乎就要不顾一切地飞身上去了!
我紧紧抓住了通道口的栏杆。只要稍一松手,我就不能控制自己了。火车驶过,我的衣角渐渐安静,我几乎是逃进了地下通道。我的手一直紧攥着,掌心隐隐作痛。
我想,她,肯定见到过与我同样的诱惑。每当她往外跑的时候,我便觉得自己也灵魂出窍。她的奔跑是一场大梦,我愿意为她收拾残局。当她跟那些红富士一同失去光泽,我不禁暗暗着急,开始悄悄盼着她出去。
于是我又有了期待。
这天,我站在门口,忽然发现天边的一朵云,像一条大鱼,悬而未动。紧接着,她出现在云下面。我结结巴巴高兴得说不出话来。我知道,我又要忙起来了。我又要围着她蹿上蹿下,跑前跑后,像是对待贵宾,像是迎接下凡的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