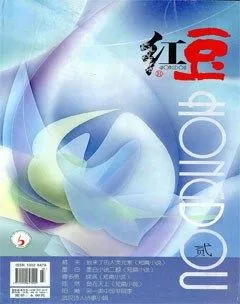墨白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探析(评论)
2011-01-01张明华
红豆 2011年2期
张明华(1977-),女。江西永丰人,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文艺学硕士,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作为先锋小说家的杰出代表,墨白的笔下流淌着一种来源于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人与自我间的畸形的异化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创伤、变态心理、悲观情绪和虚无意识。其作品对人物内心的挖掘,对生存现状的思索,对人性和灵魂的感悟都表现出一种卓尔不群的品质,在当下的中国文学呈现前所未有的多元的审美格局中亦不失独特的个性和品位。墨白的小说世界立足于墨白的一个梦境家园——颍河镇,在豫东农村文化大背景的映照下逐层展开,那里有熟悉而亲切的乡土平原,有依稀可辨的村镇、河流、房舍、寺观,有根深蒂固的生活风俗和行为模式,有祖祖辈辈耕作的男人和女人。这一道道自然人文景观融化于颍河的神秘和宁静中,在现实和文明进程的真实处境中一次次碰撞和沉沦,彷徨和孤独,在躁动和恍然的精神路途上归于惊叹之后的寂静和消弭。同样,在代表特定时期中国农村的颍河镇上,墨白讲述了无数封闭的、城市边缘化的颍河镇人的故事,关于生存和爱,关于梦和残忍。墨白笔下的人物群像图中,女性形象或者清晰或者模糊,都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生存定位,在墨白短篇小说中主要可以归纳出三种女性形象书写。
一、女性器官化、符号化形象书写
在墨白的小说世界中大多数故事都发生在颍河这个虚构的小镇,河流和土地养育着祖祖辈辈的颍河人,颍河成为作者情感之根,宛如一个遥远庄重的神灵,集合了记忆和生存的泉涌。墨白笔下的颍河镇有着豫东根深蒂固的传统血脉,一个遥远而神秘的贫穷乡村,淳朴而封闭的人群,他们在土地的召唤中世代耕耘,发生着颍河独有的故事和传奇。颍河镇的女人是墨白小说中不曾忽视的创作视角,她们在墨白笔下以特定的形式和形象展示在读者面前,其中对女性符号化、器官化定位和书写是墨白小说的一大特点。
在传统的古老观念中,女性与生殖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唯生殖论”的女性定位是封闭落后的陈旧观念的产物。墨白笔下的颍河女人不能逃离男性目光中的偏见和窥视,被符号化、器官化成为必然。如《蟾蜍》中哑巴的女人是一个没有个性没有正面描述的形象,整个文本中对主人公哑巴的女人的描写仅仅停留在一个没有个性言语的“烧好饭”、暖好炕的模糊形象,然而作品中对女人被人强奸后在炕上“呜哇”、“胸前的乳房像两个干茄子一样垂着”的器官化描写却成为女人极具代表性的形象符号。《红色作坊》中“成”眼中反复出现并让他兴奋的丰满美丽的“琳”的“屁股”,还有被“大屁股”借代的磨坊女主人,“明亮的灯光一下子把成和那个大屁股女人拉得很近”,“成看到她丰满的屁股在灯光里一错一错地走失了。”文段中的女人与符号化的生殖器官形成了相互呼应的两种颜料,交错融合。在墨白的小说文本中女J陛定位符号化的描写并不是偶然,在小说情节中,女性往往与姣好年轻的面容或起伏有致的身体合二为一,作为被审视和爱欲对象存在。不难推测,颍河这个作者回忆和成长的情感之源,这个在作者记忆中只有一条河与外界相连的贫瘠古老的地方应该有许多尘封而且古朴的事情在发生,其中传统文化中的女性观和女性视角也就应运而生。颍河镇的女人没有逃离男权目光中“窥视”和“生殖至上”的命运,丰乳肥臀的挑剔目光,男性确立的标准将女性之美等同于一种可以脱离人格个性存在的供男人审阅的特殊消费品,甚至被剥夺得只有“性”的特征。自从人类的父权中心体制形成以来,女性就作为男性欲望和窥视的对象存在着,女性的“第二性”,注定其供男性享乐的宿命。颍河这个古老却沧桑落后的特定情境,父权文化的屏障没有放过任何一个颍河人,包括墨白。男权体制中男性欲望的对象是最具有生殖能力的女性。其次当女性不再纯粹是生殖工具为某些男性所拥有时,女性身体的美丽成为男性追逐的另一目标。墨白笔下将女性特征器官化和符号化的描绘,具有典型的颍河文化气息。也许只有这样才称其为作者梦中的那个颍河,才是真实存在的颍河女人,那个神秘的地方在封闭古老陈旧的气息中才具有了更加令人深思和追问的意义。
二、强大男权理想下的贞妇怨女形象书写
在颍河镇的神秘和古朴气息中,墨白将写作的视角延伸到颍河女人的爱情和命运的思考中。在作者的文本中不能让读者忘却的是为颍河繁衍生命,世世代代依附男人的女性群体。她们曾经美丽动人,曾经幻想过爱情和浪漫,曾经也留下无限的遗憾和泪水,作者笔下这些女子以死亡的决绝来抗诉封闭落后习俗文化的情节,包含作者深刻的内心之痛。如《穿过玄色的门洞》,神秘而带着几分恐怖的玄色门洞里,送走了二奶,也看到了表姐年轻的死亡。而那年冬天,大哥和表姐在门洞进进出出,响亮的笑声从门洞里传出来,后来大哥当兵了,来了一封信,表姐哭了,朝门洞跑去,之后再也没有回来。人们告诉说她凉了,死了,有几个月的身孕了。《记忆是蓝色的》文本中,槐花妈和“爷爷”的爱情,阴差阳错承受着太多的谴责和目光,最后槐花妈溺水自尽,“爷爷”用自己的蓝布腰带吊死井口。在作者对生命和人生进行反思和追问的文字书写中,以血代墨的苦楚和绞痛折射出对人的生存无常和宿命的社会学问题,而文章中对女子的爱情命运的反思,对女子贞洁观念的颍河式再现无不透露出强大男权话语既定模式中对女性的不公和迫害。在封建社会几千年的规训中。到处是贞洁牌坊和烈女祠,“表姐”、槐花妈的自杀,出于一种对女性贞操观的恐惧,女性在婚前之“贞”,婚后之“洁”的千年牢笼中无法挣脱罪恶之手,女性自然天性在极为不合理的男权社会的贞操观下抹杀殆尽,女人的命运在原本属于自己的身体中完全脱离本真和公平,成为满足男人私欲的玩物和占有物,记述着女性悲苦的历史。墨白的笔下流淌出的异样女子,也许她们性格个性并不明显,然而对爱情的幻梦和忠诚,以及为贞操观所累却成为文本真实。她们的不幸遭遇和命运无常在引发人们深思的时刻,无不饱尝文本给以读者的启发和反思——为一种罪恶习俗和落后礼教的反思,我想这也是作者在文本中要传达的女性之恨,一种文化架居于历史和传统之上的俯瞰和大气。
三、天真单纯、柔美女性形象书写
在墨白的小说文本中女性的美丽也有多元化的表现,其中扣紧女性善良天真的个性特征进行人生命运的思索,表现出对女性特定生存处境的关注,呈现女性独有的特性和美丽,都表现出作者对发展变化中的颍河的洞悉。作者笔下的颍河,在经历城乡交汇和冲击的进程中,颍河女子的内心萌动和困惑无不凸显女性的天真和柔美。如《琳的现实及其以后的生活》,描写了女主人公琳的生活和梦境。戴了近视眼镜的她曾经做过很多梦,在高中的时候做过一个名叫“颍畔文学社”的副社长,会写诗爱文学。可是现实是高中毕业后她回到了农村,和做了一辈子老实巴交的农民的父母一样,操起了田活,与泥土为伍。她在现实的反差和不甘中渴望突破和改变现状,直到倔强的她决定自己去市场上卖蒜。她遇到了那个瓮声瓮气与女人有几分相似的老同学彭雯,他答应她等蒜的价钱好了派车去帮她拉到南方,叫琳回家等先把蒜挪一挪。琳带着彭雯给她的《颍水》杂志,上面有他发表的一首诗回家等。彭雯的诗叫《给琳》,是一首爱情诗。琳完全被感动得一塌糊涂,文学的圣洁殿堂中的爱情在她的梦中一次次激动点燃,从此琳至死不渝地相信彭雯的爱,马路上的汽车呜叫就是他呼唤琳的声音。她等啊等啊,等着彭雯的汽车来拉蒜,直到媛告诉她彭雯的那首诗是抄的。所有的梦和爱因为天真被残酷的谎言一掌击破,琳的痛让她的单纯和美丽具有了更多生命反思的含义。小说构思一波三折,女性的天真善良和执著地对爱和梦的追寻成为小说生发人性困惑的根基,女性的天真和柔美,美丽和单纯成为不能抹去的人性之初的一种本真和纯洁。“人类的救赎,是经由爱而成于爱。”在墨白小说世界中对人性、生命、宿命和生存的探索和历练中,女性的美丽和天真成为思考最初的原型和被毁灭后的一抹至真至纯的色彩。如《纪念》中的罗燕,为爱情投湖自尽,其纯情善良的窥伺爱情的选择包含作者无比的惊叹和惋惜。不难发现,在墨白的创作理念中,女性等同于美与善的认定,包含作者对女性形象的又一种定位。
遥远的颍河,与城市遥遥相望的颍河,是墨白记忆的根,创作的船。墨白曾说,地域是一个重要的精神符号,它使我们更清楚地感受到一个作家的精神家园的存在。福克纳和他的约克纳帕塔法,乔伊斯意识里的都柏林,沈从文建立在自然和人性之上的湘西,马尔克斯魔幻之中的马孔多,就是很好的例证。在这块神秘而封闭的土地上,墨白的精神之旅中女性具有了自己独特的颍河气息,作者将记忆的光影打磨在颍河镇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古老的故事中女人的出席显得单薄并不充实,其符号化器官化的模糊记忆却恰到好处地吻合了颍河的乡土人文,吻合了—个落后和陈旧的操守之镇,而女性之美之善,女性在杀人的礼教贞操观下的倒戈,依稀映出墨白对生命的反思和敬意,浸染出墨白的心路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