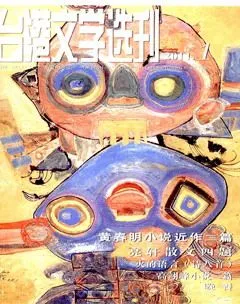伯父梁披云二三事
2011-01-01梁雁
台港文学选刊 2011年1期
伯父是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十分在澳门镜湖医院逝世的,但是,我总感觉他没有离开我。他毕生为追求远大理想所做的一切,已化为一系列影像,一直在我心中萦绕;他的慈爱、笑语、谆谆教诲,还有他的书,也仿佛依然给我力量。
二〇〇二年,伯父住进伊丽莎白医院,我问他需要什么,他说要看书……他生于一九。七年,若加上闰月他已将届百岁,依然嗜书如命。上天许是受到感化,赐他好眼力,看书不用戴眼镜。
他爱眯着眼睛看书,爱用食指在大腿上练笔势;他爱喝家乡永春的茶,笑时总会露出一排染了茶色的牙;他老爱穿件藏蓝色的中山装和白底的黑布鞋,我老觉得他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介布衣超过像一位学者。一次,他提着刚脱下的黑布鞋笑吟吟地对我说“活到老,鞋到老”,他特地把“鞋”字拉长(闽南腔普通话“学”“鞋”字音相近),我起初一愣,看他的表情,突然醒悟,和他一起笑了。十足的老顽童!这款鞋,不离不弃陪他跋涉祖国的大江南北、家乡故地,伴他筹办黎明高中从学园选址、建校,直至伴他终老上路,也见证了他“活到老,学到老”百年求知不倦所走的好学之路。
伯父家里案头枕边茶几到处是书,即使外出,旅行箱里也是装着他搜购蒙赠或预备送人的书。有个记者到文第士街43号老屋里采访他,用“顶天立地”形容他那既高且宽、横列整面墙的大书柜,实不为过。书如此之多,可当友人或陌生的作者馈书,他照样捧读一番,然后说出读后感,像一位善意学长,把知识和爱心寓于言传,让人在毫不尴尬的处境中愉悦吸收,并印象深刻地记下。伯父一生尊崇“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奖掖后进,对后学或子侄都一样循循善诱。从我懂事开始,每回他从澳门回来开会或探亲,见面的赏赐总是书,乡人总认为,千里迢迢带那些笨重又不值钱的书真不可思议。
伯父常引宋朝大书法家黄庭坚“一日不读书,言语乏味,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的话说,一个人可以穷,但不可以不充实自己,不可以没有知识。然而,他从不勉强下一代学某些科目,他只是用言行默默熏陶、影响我们。我们习惯于索取文字多于索取金钱,子侄辈向老人家要求的不是他的书就是他的字。伯父赠送的书或条幅通常先题“某某存念”再署名“披云”,最后写赠送日期。有时事先写好,有时当面写。而我,最喜欢能当面看他写。他写钢笔字也一样有毛笔字的笔势,讲究运功。从他一笔一划的运笔、一丝不苟的专注,我感觉得到,伯父对我们的关爱是深沉的、永恒的。
爱书的伯父对书也有过反常的“评价”。“输(书)得离谱”是他拿自己钟爱的书来自我解嘲的一句话。说的是他一九七四年在香港创办的《书谱》,这是一本当时惟一在海外出版、发行弘扬中国书法的杂志,坚持十多年之久。因为是赔钱生意,伯父常拿来开玩笑。粤语的“书”“输”谐音,故香港人不喜欢在过年喜庆或赌马日与“书”字扯上关系;店号首字更不会用“书”字,认为不吉利。这是伯父对书的一种爱恨无奈。如今,看着已泛黄的“雁侄存念”书页,几十年来希望能看他写字、送书、翻书给我们讲解的心情清晰如昨,这不仅潜移默化影响了我,我也有意识地将它拿来影响我的下一代。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也在床头茶几书桌上摆几本书,让他们随手可拿、触目可看。
港澳之距并不远,可惜我来港后忙家庭忙工作,与伯父相处时间不多。现在回想,身边难得有这样一位博古通今、人品高尚的老师,我却没有好好把握机会!我不知道,伯父是否带着这样的遗憾走的,但我肯定遗憾终生!
直至二〇〇二年六月二十二日,伯父因病情恶化,得到时任澳门行政长官何厚铧先生特别的关照,送他来香港伊丽莎白医院医治养病,我与伯父才连续相处了一段长日子。他的病时好时坏,有一阵子真让我们担心得坐立不安,捏一把汗,而他那时也有点悲观、失意。伯父是个名副其实的文弱书生,虽然又高又瘦,但每当站立,都挺拔笔直,毫不含糊,一米八几的个子总是高人一头。他的好友潘受用“满城无不知有长身鹤立之一杰出青年人物曰梁龙光者”来形容他。伯父修身洁行,有君子之风,他翩翩然的外表气质、遐寿,在我眼里犹如仙风道骨的鹤,永远给人美的感受。即使过了百岁,给人的感觉也是清清新新,没老朽之状。八十多岁的人走路,步履仍然轻盈,不必旁人扶持;一百岁依然牙齿未掉一颗,看报不戴眼镜,即使后来行动不便需坐轮椅,他仍习惯正襟端坐。活脱脱的,一下子躺倒在医院的病榻上,他和我们一样难以面对。做梦都没想到,我和伯父天天近距离见面,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但我必须真心感激何厚铧先生能这样善待一位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老人!
我特地从家里挑出一些与他一生有关的书,带到医院给他,其中有《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于右任诗集》、《九七香港回归诗词三百首》等。“哦,书来啦!”他满心欢喜接过书便手不释卷。一九二四年伯父考入上海大学中文系,于右任时任校长。伯父常说他的书法得益于这位恩师的指导,因此,他的书法多少也有于老的风骨。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每次伯父回乡,总会站在于右任为家里小楼题的“思基楼”牌匾前沉思,神情恭敬、肃穆。《于右任诗集》首页,是于老草书的对子,伯父念“养天地正气”,我念“法古今完人”。伯父对我说,要成为恩师所说的完人并不容易,要终生效法完人的精神,所以用“法”字而非“达”字,这就是中国文字的精髓所在。我知道,伯父是在教我如何注意遣词造句。
伯父住进医院不久,是香港回归祖国五周年的日子。香港回归前,北京《光明日报》与香港《大公报》曾联合举办“全世界华人迎接香港回归祖国诗词大赛”,《九七香港回归诗词三百首》一书是甄选参赛作品编成的,我写的《香港放歌》没得名次(所以我一直都没告诉他)却也有幸入集。回想五年前,伯父出席中英双方主权交接仪式,我想这一天他会感怀往事,便特地带了这本诗词集给他。伯父一页一页很认真地翻看,看到书里有相识的文坛老友,他会高兴地点一点这人的名字。当翻到“香港施子清”的名字时,他兴奋得如晤其面。他经常赞赏施先生的书法造诣,称他很难得。“哦,是你啊……”伯父发现书页上有我,便念着:“一缕汉魂,百载奇冤……拂袖送斜晖……”他提高了声调:“看雄鸡晨唱,醒狮昂首,抖落百年寂寞。呵,与你免冠徙跣,唐山汉水的亲缘……”“不错不错!”他笑了,这是他住院十天来笑得很开心的一次。他告诉我,写诗要注意韵律,诗也是音乐,要读起来琅琅上口才动听。看他这晚的精神挺好,我又拿出一篇一九九九年写的《园记》(简称)给他看。“泉南山水,南安有胜迹……天赐独峰,位峙海浒。钟神秀,金鸡飞止……九溪挹注,晋水潆洄……”他念着念着,没了声响。他告诉我,应该简洁一些,把主要的思想体现出来就好。我请他写下意见,起初,他不肯,我再三央求,他才拿出钢笔一笔一笔写下“宜略加简洁使文字更趋流畅”。伯父说,他是第一次看到我的文章,文字功底不错,他鼓励我多看好作品。九七纪念之夜,伯侄俩在医院白墙下促膝谈心这一幕,我至今不能忘怀……
半世纪一遇的香江之聚,跨越伯侄情感的教益,虽来迟却及时。看得出,伯父有时会因行动不能像以往那么自如而烦躁沮丧,但当看到自己的孩子和我们晚辈关切、不安的眼神时,他会马上收敛情绪,很不安地瞟一下我们。他这一霎眼神,令我感动一生一世。
那段时间,除出差到厦门两夜外,我每晚必到医院探看老人家。我住在港岛,上班在九龙,下班后,要先赶回家煲些汤水,带到医院时大都九点多了;听保姆阿桂及照顾他的姐夫说,每到九点左右,伯父会一直望向门口。是的,爱看书、爱热闹、爱说笑的伯父,在医院里太寂寞了;但那或许也是关心的眼神。我每次推开房门,第一眼总看到伯父高兴地抬了抬头:“哎呀,你不用每晚都来……”地道的家乡话真亲切!和他聊天,听他讲过去的事、小时候的事、年轻的事;讲香港的事、书谱的事;讲泉州黎明大学的事、国家的事;讲家风、做人、做事,每晚,我都在用心感受……我知道,这些充满哲理的话语,是百年阅历的积淀、智慧的结晶,使你无论是做人处事或遇到艰难险阻,都能站在更高处去看去想去理解。难怪习近平副主席会很赞同和欣赏伯父早几年为他写的“近其所欲近,平其所不平”这对充满哲理的嵌名联。
可惜,伯父走了。留下了他毕生矢志不渝的家国情怀、锲而不舍的教育兴国之志;留下了他感人肺腑的百年心路,这里有他的爱、他的情、他的遗憾,还有他离世前难以言喻的依恋。也许老人已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每次讲到故乡、亲人,他的眼圈会红红的,此时,我的心总一阵阵酸楚……泪盈于眶,但伯侄俩都在黑夜里千方百计掩饰着各自的悲哀……
(选自香港《城市文艺》2010年10月号)
责编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