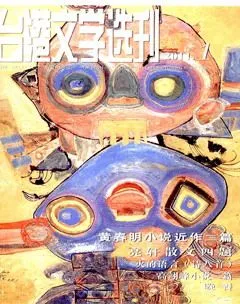在孤独里安身立命
2011-01-01林丽如
台港文学选刊 2011年1期
映照在书墙上的身影
走进亮轩家,映入眼帘的是杂志上见过的角落——那是陶晓清和马世芳在客厅落地窗前坐着阅读,一同入镜的画面。踏入这个熟悉的画面,让人感受到一股宁静的气息,一面又一面的书墙,展示着爱书人的读书进程;茶几上,是亮轩正在读的书——楚戈的《龙史》。安静的午后,我们的访谈沉浸在书香的世界里。
亮轩出道甚早,十来岁就自行养成读书写札记、批注的习惯;十二三岁毛遂自荐,经试音录取,加入了广播公司的广播剧团;二十来岁,在桑品载邀请下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写方块,此后,散文、专栏长期见诸报章杂志。
亮轩作品多为散文、时评。异于一般的阅读经验,他的著作,书序总是自己来写,往往另成一篇风格独具的散文,犹如浓缩了全书精华,也帮助读者迅速理解每一本书的背后成因。著作颇丰的他说,习惯自己写序,原因是自己帮别人写序的经验有点辛苦,所以书序从来不麻烦人。他的作品,只有一次是隐地为他的《边缘电影笔记》写短序,但是他事前不知:另一次是《2004/亮轩》收入张晓风旧作为序。
张晓风这篇旧作《未绝:一位作者的成长》,原载于一九八二年五月三日的《台湾时报》副刊,收在张晓风的《我在》一书,如今旧作当序,自有其特殊意义。这篇文章叙述亮轩童年至青壮年的成长轨迹,读未有点心酸,让人稍稍了解亮轩的人格特质以及写作脉络。
亮轩两岁时,同是留学生的父母离异,他和姐姐归父亲,母亲因思念他,找人把他偷偷带走,藏身上海附近某城的一座尼姑庵里。没多久,被父亲找到,后随父亲来,却因寄养姑母家,记忆里尽是童年常常挨打的凄楚。亮轩的父亲马廷英教授是著名的地质学家,毕生钻研学问。父子俩剑拔弩张多年,亮轩甚至在年少时,负气离家,直到有娶妻成家的打算,为了避免岳家不放心,做儿子的才回家向父亲低头,而为父的,则欣喜儿子成家,父子俩放下倔强,终于拾回亲情。
亮轩在自己的创作里,反倒很少提及这些。他说,一方面,关于父母的历史,自己知道的也少,何况,到目前为止,似乎也没写自传的必要。如果将来要写有关家族史的部分,他觉得隐地《涨潮日》以及桑品载的《岸与岸》,融合大时代与家族故事的写作风格可以参考,把时代和众生当作主角,自己只是站在旁边的观察者,iyNaCZa6TWqzUFp6RI41+v2Qpu5fYtjSaiNEUnjiYDg=写出乱世中的遭遇,而这些遭遇大部分也是身不由己的。亮轩说,写下来,让往后有智慧、有兴趣的人可以借着这小小的材料,更深入地了解那个时代。这个写作念头已经酝酿,也在计划中,但还没开始动笔。
回归到质朴纯粹的写作状态
提到写作计划,亮轩今年有一个重大的决定:也就是写作工具的转变。他在2月10日当天,决定恢复以稿纸写作,未来,电脑只保持写日记、做课程纲要和资料汇集的功能。和多数不熟悉电脑的资深作家不太一样,亮轩从Dos、倚天286的时代就开始使用电脑,这一回,下定决心要和电脑保持距离,是因为在写作上有些体悟,除了长期使用电脑造成肩膀腰酸不适;另一大原因是,他愈来愈觉得电脑打出来的东西有很严重的问题。
他体会到,恢复手写稿至少有几点好处:一来,手写会有些涂改,可以看出思路过程;第二,手写稿时而端正、时而潦草,有时精致、有时马虎,这也可以表现出当时的情绪状态,甚至健康、年龄状态;第三,手写速度较慢,自己一向打字快,可能会造成文章有些累赘,甚至出现不必要的言语,手写速度变慢,可以想得更清楚,节制一点,让文章更干净。
亮轩精神奕奕地说,下定决心和电脑保持距离,几天下来,果然重回到“蛮有感觉”的岁月,这种体会真好。他一一细数电脑在创作世界中的不足,也深感网络上的东西多半不好,不论是从审美角度还是到生活状态。电脑的迷思是,它只能有固定分类模式,把人和知识分到固定的模式里头去,如果没有模式假定的话,电脑的程式就出不来。亮轩警觉到:“我们身为人,凭什么属于模式?没有道理!”所以,经过重新思考,并且,慎思到创作的整体结果,他决定疏远电脑。何况,电脑也没有办法提供他书法的需求。
碍于双手已因敲键盘而受伤,未来,稿件打字将交助理处理,目前,他勤做体操复健,成效良好,他也下定决心:复健是要奉献给手写,不再给电脑了。
在孤独与空白里安身立命
长期的写作生涯,亮轩非常喜欢孤独,在文章里也屡次提及:孤独是必要的。甚至,为了这个孤独,保持一些人生的空白也都是必要的。然而,身处当今这个时空的知识分子,又要如何保持这些空白?亮轩缓缓地说,“空白”这个概念是相对于比较世俗、物质化的工作和生活而言,人生并没有绝对的空白,应该尽可能追求思想上比较高的境界,而这个境界是需要沉默的,这种沉默较接近他在若干文章里所说的空白。
他非常享受创作过程的孤单。他强调,孤独是伴随空白相当重要的条件,太好热闹就一定没有境界。但是,孤独得太甚,又可能变成孤僻,远离了人群也不好,因为生命不该是离群索居的,所以,保持适当的空白,也需要花一点工夫来思考。亮轩的创作与人生,正是如此。尤其,他这辈子的工作,多半是要自己独力完成,很少需要与人合作,正好与他的“孤独”没有太多冲突。亮轩最常着墨散文,题材多由生活经验中直接、间接体悟,观察着人群,保持着空白,以文章进行思想交流。他认为空白是以一种观照来表现,相对于世俗的忙碌、纠缠,那些我们自主不了的价值观念,那样的一些心理状态,都可归在空白的这个概念上。
如此强调空白,又如此喜欢孤独的亮轩,如何在“名嘴”光环下安适着?
亮轩哈哈一笑,先就“名嘴”的时代定义做了一番诠释,他很不能认同当今的所谓“名嘴”。早年他被称为台北四小名嘴时,年纪是二十岁上下,其他三位是罗青、司马中原、赵宁。当年,四小名嘴对应的是四大名嘴(孙如陵、王蓝、陈西滢、尹雪曼)。那个年代对名嘴的定义,亮轩还能接受,当年他曾在《联合报》有个专栏叫“名嘴开讲”,和时下对名嘴的概念相去十万八千里。
亮轩对时下的“名嘴”颇不以为然:“爆料、说一些不负责任的话,渐渐甚至于狂妄、自大。他们坐在那儿,自以为是蒙着眼睛的雕像,提着天平和利剑,这是名嘴的境界吗?这是不行的!”亮轩说,所谓口才好,必然伴随着人格特质、核心思想、素养、机智、趣味。要言之有物,平日的修炼、充实自己都是必须累积的。
与时俱进的人生志向
也因为有此自觉,教书这么多年,亮轩没有中断充电,却也主张能少说就少说,说出来的话都是要努力对人有助益,还时时警惕自己:若要别人长进,自己要先长进。曾经,为了弥补课堂不足以表达的思想,可以让学生在教室之外、课业之余,方便搜寻他的文章,进而读到更广泛完整的想法,于是,设立了博客。不管是已发表或未发表的,都往里头装,有些旧作甚至是助理帮忙打上去的。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效果不大,因为学生们也都忙着自己的事,忙打工、忙上网、忙聊天、忙活动,所以渐渐就觉得无所谓了,也愈来愈觉得自己不能管太多事。除了上述的体悟,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太忙,经营博客太花时间。何况,一开始并没有想用博客来扩充读者,或者与读者交流,因此少上些文章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亮轩对学生的期许,让人觉得分外可贵,他曾对学生说:“读语言传播系的人,更要有口德。”面对如斯年轻的学子,他认为他们是可以体会的,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听他的课,读他的某些文章,同时,学生们也可以看到事实——老师从来没有卖过速食的知识,也从来不相信包装。
这位力行孤独的作家,非常了解学生们在这个年纪的踌躇。青少年时期的亮轩,常常立志,比如,八岁时,看了牛伯伯漫画,遂立志当漫画家;课外读物读得多,十岁更明确地想当时事漫画家;十四岁,读了孙中山三民主义讲辞,遂兴起立志当政治家;十五岁,立志当播音员;十七岁,以“与世乐其乐,为人平不平”为终身职志……这些志向,激励着年少时的亮轩,而今,他力行自己在十来岁立下的座右铭。
为人平不平的入世生活
从亮轩家的阳台望出去,就有那么些“与世乐其乐,为人平不平”的故事。先从落地窗讲起。亮轩对生活细节的美感追求,是无时无刻的。平时,他总坐在客厅面对着落地窗阅读,这扇明亮的窗原是采用四十年前老旧的建材,几年前他自己动手设计更改,把原有玻璃全部敲掉,重新制框,更改尺寸,打造全新落地窗。何以如此大费周章?原来,望着窗外的亮轩,把景象当画,改造窗户规格之后,在视觉上,会有一个完整的画面;但“设计画面”的同时,又要注意安全,所以,推翻自己设想中整片没有窗格的构想。亮轩很满意目前的窗景,每天一打开窗,就是一幅画,最棒的是,窗外几株大树,四季都有不同变化,每年四至十月,还会茂盛到把附近的房子全遮住了。
这几株树所在位置,原本被规划改建地下停车场,非常重视住家品质的亮轩,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安全问题,他身体力行,亲自奔波带领住户抗争,成功推翻了这个建设提案。这场仗一打三年,亮轩与一两位邻居结伴,一家家去说服,十几度来回“议会”与“议员”办公室,几个人花了六七个月的时间,联合周遭有公众意识的人,请教专家之外,还得熟悉法规、控制开销。因为深知工程隔离墙会对老房子造成危害,他们写标语、喊喇叭、画漫画、找媒体、上节目……最后,台北市有关单位赔偿建筑商,才圆满保留住这块公园。
亮轩对社区事务涉入很深,在写作上传达理念,也在公共事务上亲身参与,这些“平不平”的事,不知凡几。也是几年前,亮轩担任台湾人权协会理事长,去马祖、新竹、宜兰等地收容所参观了解。亮轩说,那时还写专栏,多多少少可以帮上一些忙,现在没有这种版面,自然也少了影响力,所以干脆辞去不做。但是,他今年又被推举当选“少数族群促进协会”理事长,这个协会特别针对弱势族群,亮轩觉得出出力气、打打电话、写写信、讲讲话等都可以,只要帮得上忙,就尽力去做。
看尽无数江湖人物故事
参与、经历的事情太多,亮轩在半百之际,决定尝试以小说写下这些故事,也订下一百个人物故事的目标,这些名不见经传的人,有些是听来的,有些是亲眼所见。先后结集出版的有:《江湖人物》、《情人的花束》、《亮轩极短篇》,这些生活周遭小人物的故事,他还是陆续在写,手上也累积了相当的稿量。他认为,作家就是要写人,作家写下来的人,和历史学者写下来的人是不同的;社会上总有些人,虽然不识字,但却是优秀、有智慧、有原则的人物,没人把他们写下来,就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损失。他总觉得,“如果不写,这些灵魂无法超生”。他笑称:“我要持续地写,让他们一个个上天堂去。”
这一两年,亮轩上报竟是在竹联帮老大陈启礼出殡的新闻里。这个丧礼由张大春做挽联、亮轩挥毫。新闻见报难免引起臆测,让人关注亮轩和黑帮大哥的关系。不料,亮轩说:“完全不认识。”写挽联的缘由是,朋友提出要求,亮轩考量死者为大,加上整个事情非常单纯,于是答应了下来。和许多对于时事的观察一样,亮轩认为,陈启礼事件,有时代因素,那时的人,更是在当时的框框里长大的。亮轩强调,他当然不认同黑帮,也担心黑帮新闻被炒作。比较好笑的是,大家看到新闻之后,传言亮轩是竹联帮分子,更有学生看到新闻之后,悄悄去问助理究竟。
笑谈时事的亮轩,文如其人,他甚至在“红潮”时期,也和老朋友们上街头,但他笔下关心,却从不在课堂上谈政治。因为,他很清楚:“我们吃这个亏,吃太多了。”
《2004/亮轩》里,亮轩谈了不少时事,这一年,台湾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件。犹记得,那是个人人都很容易激动的年份,然而翻阅着《2004/亮轩》,却读不出笔下的激动。亮轩说,那一年的日记,他的习惯是清晨醒来再写前一天的记事,但是,“三·一九”当天,他是当晚写的,他坦白,情绪上的确没有太多波动。直到如今,扁案天天上演,他心里头还是有个不同的声音响起:“也许我们的社会制度出了问题?为什么要等到人民承担那么大的损失后才处理?这个社会的制度,为什么会让一个人贪得这么多并且卸任了,我们才想办法弥补?从某个角度来讲,这对当权者也未尽公平。但是,现在整个台湾,却没有听到重新检讨法律、制度的声音,归咎起来,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承担若干责任。”
点滴记录寻常日子
亮轩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类似这样,比如:警察取缔色情,他想到的却是报道与图片可能侵害了人权、隐私权。每天每天,看很多新闻事件都有各种想法在窜,他也曾想过把这些林林总总的念头挂进博客,后来觉得,实在是太忙,算了。亮轩把时间分配规划成:重要的事情、次要的事情、更次要的事情,在时间表里没有位置的事情,就不必耗费心力去做了。
谈到《2004/亮轩》,这是尔雅出版社的点子,出版社负责人隐地打算出版十年系列,由不同作家执笔的日记,也因为每一个人的取舍、风格不一样,恰可作为台湾十年的见证。经隐地、郭强生、亮轩、刘森尧、席慕蓉、陈芳明等陆续执笔,亮轩参与后,发现了这事对自己有一点意义,从《2004/亮轩》之后,他的日记再也没有间断过,真的去做了,才知道履行这个出版承诺并不容易。他曾在那一年自问:“是为了日记而活,还是活着为了写日记?”因为平时工作忙,生活步调非常地紧凑,眼前堆着很多很多的事情,在这种状态之下,亮轩还是天天写日记。那时每天早晨醒来写昨天的日记,让他养成早起的习惯。现在,则为了运动调整写作时间,当天晚上固定写日记。他说,每天晚上写日记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是要衡量精神状态、思索能力,还有,当晚是不是另外有工作要完成。
除却这些细微的工作节奏,亮轩发现,写日记可以跳脱专栏写作的状态,因为思绪飞舞,写日记很自由,自己打字的速度又快,晚上常写到下半夜两三点。一个念头、一个人物、事件,他都可以很快联想到其他的东西,所以,日记就渐渐不断地膨胀。亮轩举左拉、巴尔扎克的作品为例,他相信真的可以把一天的日记写成十万字,尤其,身为文学创作者,他自觉念头特别多,感情也较丰沛。相较于以往写专栏,总是把公益放在比重较大的方面,日记写作则往往随便一写就几百、几千字。每天碰到一点点事情,总有非常深刻的感受,总想要把事情说清楚。所以,《2004/亮轩》最初有七八十万字,后来大删,现在有三四十万字,原稿都在电脑里。后来继续写,其中有一个因素是,现在日记不出版,没有人可以看自己的日记了,更可以完整地保留下来。
带着钢笔与稿纸继续行走
有四张书桌的亮轩,笔墨纸砚与书本笔记整齐地分配在不同的桌子上。一向嗜读如狂的他,不为什么而读而写,读书和写作就是生活。他要求自己必读某些书、必写某些文章,也因此,即使没有外在催稿的压力,从去年、前年一直累积的素材,都堵在眼前,事情愈来愈多,渐渐地,难免也会造成阅读和写作上的焦虑。亮轩自况,人生已到夕阳无限好的阶段,却还是一直有想要躲起来的念头,因为,一般日子里的杂事太多,他非常珍惜稍微留给自己的空白,那种想要空白一下,却又空白不起来的状况,时常就会干扰读读写写的进度,他甚至计划,教职退休之后,找个清净所在,专心写作。
五十岁开始写小说,亮轩长篇写得少,手上累积的单篇随便拿出未都有十本书的量。眼前,他有很多写作计划,开始使用稿纸、钢笔写作,他预期自己的写作生涯会有一些改变。未来,不必再背着电脑,不用管它有没有插座、有没有网络,更不必一打开电脑,就东看西看;不论在哪里,只要有稿纸,坐下来就可以写,未来,如此海阔天空,亮轩一想到,就开心地笑了。
(选自台湾《文讯》2009年4月号)
责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