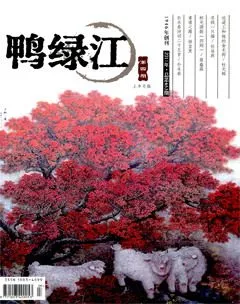雪魂
2011-01-01孟黎明
鸭绿江 2011年4期
孟黎明,男,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华文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骚动的山庄》《黎明文集》《留在故里的脚印》《金兰花轶事》《柳月的故事》等。其长篇小说《骚动的山庄》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文艺界专家、学者、评论家关注。短篇小说《煤殇》发表在当代《华文文学》杂志,作为经典作品推出。1991年入选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2010年入选《当代散文大辞典》,散文作品《我一直在走》在2010年全国散文作家论坛征文大赛评选中,荣获一等奖,被评为“论坛最佳散文奖”,并被编入《全国散文作品精品集》。
奓孩来家的时候阴沉沉的天空已擦黑,奓孩望着福生爹娘满脸沟壑纵横,驼背弓腰步履艰难的样子,禁不住坐在前炕角的炕沿边,佝偻着头抽着闷烟,心觉着滴血般疼,眼里就不由得潮水四起。两个鬓发苍白的老人眼睛红红的,悄没声息地坐在地面的一张矮木凳上,木偶般毫无一丝表情,屋内静得掉一根针都能听见,偶而房梁上发出灰鼠啃啮木头的吱吱声,布满灰尘的梁上就会抖落下一片两片的浮土。奓孩琢磨着如何张口,他咳嗽了一声,焦黄夹烟的手指就不由一阵颤抖。凡事开头难,总得要有一个摊牌的时候,奓孩耸动一下肩膀,有种欲起身的举动,却又坐下没动。他索性解开黑棉布系着的圪塔,脱下一只臂膀袖,把紧紧贴身挂着的军绿色帆布包卸下,又套上袖子。布包就放在他左手边,奓孩几欲张张嘴,复又低下头猛抽一口烟,星火闪烁间隐约映射着奓孩复杂而又无奈的表情。只见奓孩咬了牙终于开了口,“叔、婶”,说着打开帆布包取出报纸裹着的一沓钱,“这是后山里家退的五万块钱,咱过门彩礼一并送去八万块,就只能回这些了,嘴皮子差点没磨破,两条腿就差没跑细了,我算是尽力了,就这还多亏了淑良这闺女是个烈性子,非让她爹娘给不可。”
福生爹娘依旧面无表情,苍老的面孔上两双浑浊的眼珠子偶尔咕噜一转,闪烁出一丝微光复又暗淡。福生爹说:“事情都这样了,唉,也真难为你了。”说完又是一声长叹,屋内紧接着又是一阵沉闷。
这时,屋外忽然刮起了一阵子急风,有雪花飘进屋内。奓孩说:“叔,婶,下雪了,我还得赶回去。”
福生爹娘就也异口同声说:“下雪了,那你就回吧。”奓孩就站起身出了门,夹裹着风雪走进了雪地里。
这是一个寒冷多雪的冬天,连日来老天像罩了一层灰色的幔子,天地间到处浑沌沉闷,雪花见天纷纷扬扬飘落个不停,满世界都仿佛铺上了白色的被子。荒原上毫无生机的树木裸露着肢体木愣愣地呆立着,枝叉间寒风凛雪中站立着的各种不知名的山雀,不时眨巴着眼睛从尖咀中发出饥饿的叫声,野地里偶尔会蹿出一两只山兔、狍子,留下纵横越过丛林的踪迹。
雪依然狠劲地下,没明没黑地下,仿佛无休无止的样子,下得人直闹心。村里人闲着无事,就躲在屋子里垒长城、斗地主、下象棋、看电视、撇闲话,有的干脆蒙上被子搂着婆姨睡起了大觉。也有不甘寂寞的就吆喝纠结三五人结伴踏了雪到山上的林子里套野兔、药山鸡、炸獾子,围攻捕猎狍子、山猪。
一旦获取猎物,就扒皮、开膛、冷水浸泡,然后灶炉生上一炉旺火,大铁锅煮上一锅肉。待肉香扑鼻时,就打开一壶陈酿老白干,咕咚咚倒到几个粗瓷大海碗里,美美地吃上一顿大肉,喝上几大碗烈酒,就这样打发寂寞难耐令人生厌的毫无生机的雪冬。
若是天晴路干,村里人可是闲不住,他们会上山采摘点蕨菜,寻点药材,雨后进山弄点木耳、磨菇,等山珍炮制后变卖贴补家用。也有的人家上山砍柴禾,从山里挑上一担柴禾徒步进县城里卖,一担干柴可卖到二十元钱。虽是费了点脚工,但对于农家来讲总是点收入。
福生爹娘得儿迟,三十多岁年纪才生下福生。待福生一天天长成大小伙子,爹娘却日渐衰老,地里的苦营生就干不动了,爹娘就在院子里养头猪、喂十多只鸡维持生计。
福生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年迈的爹娘实在供不起他上学,福生就回到村里预备着实实在在过光景。卖柴禾这营生福生就干过几年,每年冬季福生都会挑着柴禾从山里进城往返六十华里去卖,但这几年生意也不好做了,县城里林林总总建了许多楼房,楼房取暖都用上了煤气,用柴禾的人家很少了,也就断了福生的财路。福生在家里坐得憋闷,就寻思着要有个谋生的法子。
刚巧村子里的金贵在外面的一家小煤窑下窑,这几年赚了不少钱,整个人也变得活眼道色的。他约了福生一起去,福生正愁没挣钱的门路,听说下窑能挣钱,也就乐得同金贵一道出了山,到一个叫黄原村的煤窑去谋生。
黄原村村子不大,有三百余口人,村子的后山圪垛里有一个小煤窑,夹在两座山峰的中间,紧靠山脚处有一口斜井。生产工具很简陋,场子里有一台柴油发电机哒哒哒地响着,绞车用钢丝传带着矿工把一辆辆拉着煤的小平车从洞口里拽出。场子里堆了山一般高的煤堆,空气中散发着烧饭时焦糊的味道。煤窑两山的土圪奓上依山挖有十多间土窑洞,这就是矿工居住的地方。
金贵领着福生见了老板,这是一个留着大背头满脸横肉,长着粉刺疙瘩的中年人,他西装革履大腹便便,口里叼着一支中华烟,翻着白眼珠,连正眼也不看福生一眼就扔出一句话,他娘的到这地方干活要能吃苦,能吃苦就有票子花,金贵领他去挖煤吧!福生就这样到工具房领了一把阳镐,当天晚上就进坑挖煤。初来几天腰酸腿疼有点不适应,但干了一阵子就适应了。尤其是当福生见了淑良后,福生就铁下心要在这个矿上干下去,哪怕是每天能看淑良一眼,都使得这个年轻小伙子对生活充满了希望,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劲。
淑良也是附近村子里的一个女子,她也是来矿上打工的, 她的工作就是同一个中年妇女为矿上二十多个矿工做一日三餐。福生来矿上吃饭的第一天见到淑良,两人一见面就都愣住了,仿佛前生他俩就有缘分,淑良望着他停顿了盛菜汤,他瞅着淑良呆若木鸡。直到紧跟在后排队的工友催促打饭,淑良的脸颊上才飘溢着两朵红云恢复了常态。
这往后他俩的接触就频繁了。福生在坑下干活时老想着淑良,老觉着这坑下的世界太漫长,总想让时间过得快点,下了班好同淑良见面。
淑良每次给矿工打饭,逢到福生时总会在不经意间给他一种温情,抑或是矿上食堂改善生活,她总会给福生碗底多夹几片肉,或深埋几个“手榴弹”。恰似盈盈一滴水,时常感动得在一旁蹲着吃饭的福生会不时转过头冲淑良多看几眼,内心深处就有一股柔情蜜意涌上心头,这个时候,福生就感觉到他是这个世上最幸福的人。
一个清朗凉爽的下午,正逢福生换班上夜班,他早早换了衣服,洗漱干净,约了淑良来到窑场外的一个僻静的山头,两人默默地坐在一个绿色的山洼间。他俩头顶高耸的蓝天上盘旋着飞鸟,大鸟张翅在空中不时俯冲,不时直上云霄,山下隔着的是一条几尽干涸的河流,河水浑浊,正发出低沉的呜咽声。
淑良扎一对羊角辫,身着一件粉红色花格上衣,一对眸子清澈透亮,眉宇间却呈出一丝淡淡的愁意。她一手托下巴一手伏在膝盖上静静地注目着远方的山峰。福生手里夹着一支烟紧挨着淑良。福生问淑良家里有几口人,淑良说她上有父母爷爷奶奶,下边还有两个弟弟,家里很穷。她初中还没读完就辍学了。父亲说丫头片子迟早都是外姓人,识个字会计个数就行,重点是要让弟弟上学将来好立门户。福生不由觉得淑良的情形竟同自己有着惊人的相似,同是家境贫寒,又都是初中辍学。所不同的是淑良爷爷、奶奶健在,姊妹兄弟多,而自己虽是独子,两个老人却已风烛残年,眼下家里的唯一希望全都在他身上。淑良对福生说她其实活得并不舒心,父母还指望她找婆家要彩礼给弟弟娶亲,在家里三天两头儿有人上门提亲,她实在厌烦呆在这个家里,就跑出来到窑上打工了。淑良说着就抹起了眼泪,福生也对淑良的不幸处境深表同情。福生说坚持吧,坚信苦日子总会有好转的。
北方的秋风在华北平原刮了过来,天气开始转凉了,天快擦黑的时候俩人才依依不舍返回了矿区。
转眼间,福生来到这家小煤窑干了快四个月了,手里也赚了三万多块钱,很快就到年关,福生思念着父母决计回家。这几个月来,他有了自己的心上人,他同淑良的关系迅速升温加级,形影不离。他挣的钱多,还给淑良买了一身鲜亮的衣服让她新年穿;淑良做得一手好绣花活,她给福生精心绣了六双鞋垫,预示着福生“六六”大顺。两个年轻人,已经在谋划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矿上放假时,福生同淑良在山道上走了一程又一程,难舍难分,两个人决计明年再来小煤窑打工。临分手时,淑良羞涩地对福生说:“福生哥,别忘了来家提亲。”说完羊角辫一甩,红花格上衣夹带着银铃般的笑声便消逝在山路的拐角处。福生也踏着坚韧有力的步子往家里走去。
第二年一打春,福生就找金贵打算去窑上干活,金贵愁眉苦脸地说,小煤窑出了事,老板被抓了,煤窑也炸了。去年年关老板留守外地几个工人在矿上加班挣双倍工资挖煤,结果坑下出现塌落,砸死三个外地人。福生听得一身冷汗直冒,头发根子都竖起来了,他暗自庆幸多亏自己年前就离开窑上,要是再干下去说不定也成孤魂了。
一时找不到活路,福生就想起了淑良说的话,就同爹娘商量提亲的事,爹娘听说儿子寻下了媳妇,两个老人就整天有了菊花般的笑。
于是就同本家侄儿奓孩商量福生提亲的事,经福生爹娘一说,奓孩说他在后山里干过木活,认得这家人,还给这家人打过寿木哩。福生爹娘就让奓孩去后山里辛苦一趟。奓孩答应着就去了后山。后山距福生村子里二十多里山路,一天打个来回没问题。奓孩头脚走,福生一家子就在家里等起了好消息。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奓孩回来了,娘给奓孩煎了荷包蛋,一家人蹴到跟前等着开口。奓孩不紧不慢地吃完荷包蛋喝了汤,抽了一口烟终于开了口:“叔,婶,这事有门儿,开始人家不愿让女子嫁到咱这地方,后来我好说歹说总算应允这门婚事了。可就是彩礼钱太贵,要八万块哩。”刚才还喜滋滋的娘一听这天大的价,差点没晕过去。
“少了八万块钱,这事肯定黄了,后山里家咬的硬哩。”奓孩说。
福生暗自算了算这几年自己攒下的钱加起来也顶多五个数,距离八万元还有不小的距离呢。不过福生觉得钱是人挣的,为了淑良这钱花得值。福生笑笑说:“爹、娘,钱的事你们甭操心,儿子挣就是了,只要人家那头愿意比啥都强。”两个老人能有什么能耐,儿子说了这样的话,也只得这样了。
福生外出打工走时,见了淑良一面,淑良说家里实在是太困难,她爹就指望这八万块钱给弟弟娶媳妇哩,她也没有好办法。福生说钱我会挣下的,你放心。淑良说你在外多保重,不管有多艰难我都会等着你回来。两个有情人抱着头痛哭了一场,福生就起程南下打工走了。
福生在外干了三年总算是挣了四万块钱回了村里,有了钱胆儿也就壮了,奓孩在后山里又来回跑了两三趟,福生和淑良总算是订婚了。
这三年来,福生和淑良度日如年,相思相盼无时不在煎熬着他们的心。淑良爹娘着急要给淑良弟娶媳妇,曾多次要淑良打消等福生的念头,淑良情贞意坚,现在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
再过十天福生就要迎来大喜的日子,福生想起淑良这么多年对自己的坚贞,就总觉得愧对淑良,总想着要把婚事办得排场点,盖房子是没有这个力量了,只把窑洞里粉刷一新,打了几件家具,就差买一台彩电的钱了。眼看婚礼在睫,福生就寻思着如何再去挣点钱完成这个心愿。
一个冬日的晚上,雪依然下得很大,寒冷的天气刮着西北风,福生冒着雪来到了金贵家,金贵媳妇翠英坐在热炕头和两个孩子看电视,却不见金贵。福生就问翠英金贵呢?翠英就说金贵到窑上背煤去了。福生说哪里有窑下,翠英就说你走了三年,咱村东山洼里有人打窑出原煤了,你可能还不知道。福生一听喜出望外,下窑挣钱来得快,买彩电的事儿这不就有着落了吗?福生问金贵啥时候回来?翠英说得明天早上吧,福生就说那我明天过来找他,你让他等着我,翠英就说好。福生踏着埋膝的雪哼着“信天游”一路欢快地回了家。
白雪映衬的山路上,行走着一群娶亲归来的人,四个壮汉子举着唢呐鼓着腮帮子或冲向浑远的天际,或腑视苍茫的大地,发出呜哩哇啦的乐曲声,灰毛驴上骑着披红着绿秀气的新娘子,咯吱咯吱地在积雪中行走着,福生胸前别着一朵新郎花,白雪映衬下分外显眼。快进村子里时,喜庆的鞭炮声就噼里叭啦地轰炸着,年迈的爹娘喜滋滋地在院子里迎来送往亲朋好友,不时地领着乡里乡亲们看他新房里打的家俱,一台21寸彩电正播放着宋祖英唱的“好日子”。人们围在院子里,淑良和福生正在那里行拜着结婚大礼,一群孩子们正撕扯着新娘讨要喜糖吃。“福生,福生,快起来,金贵过来找你。”爹扯着破嗓门推搡着他,福生一骨碌爬起来方知是做了一场梦。
金贵说:“福生,我听翠英说你夜黑间去家里,我寻思着你就快娶媳妇了,看有甚事就过来了。”福生笑笑说:“还有几天哩,这两天也没啥事,我看你这段时间干啥哩,就过去了。”“唉,能有啥干的,在窑上黑间背煤哩,县里查得紧,白天不敢干,晚上在窑里挖点煤拿蛇皮袋子装上人工运到路上,三轮车就转走了。”
“人家这个老板关系硬,小舅子是乡长,乡长的外甥是派出所所长,国土所长又同派出所长是连襟关系。别人不能干,人家照干不误,现在人家在咱们乡里已形成了一个关系网。上边有情况,人家马上就知道,上边下来查,这里就早关闭了。你县里是睁眼瞎子聋子的耳朵——摆设,能查出个奓。现在煤价这么暴利,不眼红才怪哩。背一晚上挣个二百多元钱那是耍哩,要是肯吃点苦,挣三百块也有的是。”福生听着听着眼睛就发出了光泽。
福生为了使这个婚事能办得圆满,也为了完成他最后一个心愿,就同金贵一起加入到背煤的队伍里。
天空依旧阴沉着,雪花依旧没完没了地下着,地上的积雪越来越厚,福生为了多挣钱、快挣钱,比别人就多背一蛇皮袋子煤。他踏着没膝的积雪艰难地在山路上踏出的一条羊肠小道上踽踽行走着,他一只手伸起扶着肩上的两个煤袋,一只手打着手电,不时要在稍宽的路上换一下肩,减轻过重的压力。天幕上飘落的雪花不时遮住了他的视线,他努力顽强地支撑着,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快了,快了,再支撑几天,彩电有了,媳妇也就娶回来了。
从窑上到转运的地方两里多路,路不算远,却难走,可要不难,能挣下钱吗?福生浑身淌着热气,棉布袄湿得精透,但却一点不觉得冷,依旧咬紧牙关在山崖上艰难地跋涉着。
这个晚上他已经背了五趟煤了,累得筋疲力尽,两眼直冒金花。金贵劝他说你才开始干这活,身子骨禁不住,背了这趟算了,明天晚上接着背,福生说啥也不依,非要再背一趟不可,第六趟上山时,他累得实在不行了,在换肩时一失脚掉下了路边的一道深沟。
村里人闻讯赶到山崖下时,福生早已躺在雪地里摔死了。白雪覆盖的大地上,殷红的鲜血蔓延着,仿佛是血的海洋。福生的两只眼睛还明晃晃地睁着,舍不得闭上。
几天后,天空依旧下着雪花,村子里东面山上很快就竖起了一座新坟堆,坟堆上早已落满了雪花,仿佛是一个被白雪包裹着的硕大无比的馒头。
一天,村子里有人发现福生的坟头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趴在雪地里哭得伤心欲绝,痛断肝肠,村里人说那是福生未过门的新媳妇淑良……
责任编辑 盖艳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