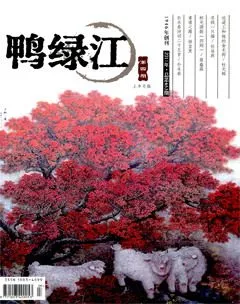马桥头
2011-01-01严正冬
鸭绿江 2011年4期
严正冬,男,生于1982年。江苏淮安人。毕业于苏州大学文学院。曾在《萌芽》《长城》《青春》《作品》《百花洲》《青年文学》等刊物发表作品40余万字。其中,小说《上海亲戚》获第三届“四小名旦”青年文学奖。散文《讲古的夜晚》于2008年初被收入《大学语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现供职于淮安日报社副刊部。
马桥头是一处小集镇,它依傍着从城里通往乡村的那条石子路,身侧还有一条不窄不宽的灌溉渠。每年夏天发大水的时候,这条河里总会漂着一些来历不明的鸡鸭猪狗,臭烘烘的,临河人家推门就能闻到,这些肚皮朝上的死货顺着水流一路飞奔,一天半日的工夫便没了影,所以,沿途仍然有人在码头洗菜淘米——这条河的确有了年岁,可它带走了多少人事,却改不了庸常日子里的生活习惯。
有河便有桥,此地以马姓为主,在这里架起的桥自然就叫马桥。也因这桥大大方便了周围的乡亲,一年四季,春耕秋收,走亲戚的、候车的、过路的、到镇上赶集的……人来人往都要经过这儿,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此处就成了小小的集镇中心。尽管规模很小,零零落落,但毕竟已是小集镇的样子了。
什么样子呢?早晨有卖猪肉的、卖鱼的、豆腐摊子、烧饼炉子、炸油条卖豆腐浆的担子,还有用柳条筐子装着地里的青菜来卖的。说实话,生辰婚丧办宴席的人家根本不会到这里来买菜,这点东西哪拿得上桌面子?家常吃吃了不得了。办大事的人家大清早或者提前一两天就会到镇上去配菜,掏出厨子的菜单一样一样地买,蔬菜荤菜冷盘子干货,镇上的菜场可是都齐全啊。逢年过节呢,鱼肉菜蔬一般人家也不愿意到这儿来买,价钱贵又不好挑,熟人熟事的,有句话怎么说的——鬼挑熟的昧。所以说,马桥头在当地人的心目中,也没有什么地位可言,至多是寻常日子里,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买两袋盐打一斤酱油,应急一下罢了。偶尔有人在此割肉买鱼,大概也是家里突然来了亲眷,临近午饭的辰光实在没有办法了。当然,这些卖主自身也心明眼亮,他们多是一些不急不躁的老头老太太,每天很有规律地做着波澜不惊的生意,其实质更接近于消闲聚会:太阳出来出摊子,坐在随身携带的凳子上一边择菜一边互相拉家常,东家长西家短,说着说着,差不多午饭时间就到了,于是他们不紧不慢地收拾物什,准备打道回府,而雨天雪天呢,他们一律给自己放假。
除去以上这些从四下里汇集至此的摊子担子,马桥头还有十来户在此建房落户的人家。房子都不怎么体面,因为地方太挤了,有的人家大门都被夹在狭长的巷子里,有的人家还是泥砌的墙面,屋顶就更简单了,几张石棉瓦一盖,完事。还有的在原先的老屋上新添一层,成了有阳台的楼房,但显得很扎眼——下半身的旧房子灰不溜秋,而上头却用瓷砖装饰一新,那种不协调连三岁小孩都看得出来。很快,这些人家的屋子自然而然成了做生意的铺子。深究起来,他们做生意与那些做豆腐卖菜的又不太一样,他们是一门心思扑上去,态度坚决,打算一辈子就干这个营生了。剃头的剃头,做衣服的做衣服,开诊所的开诊所,各家都摆出打江山的派头,用不着摩拳擦掌就上战场了,说不准这战场就是一辈子,或者更长,经子子孙孙一直传承下去。从此,这些人家的生活就与马桥头紧紧系到了一块儿,过日子和做生意变得难解难分——外头的柜台上堆放着满满的货物,顾客一脚跨进来,一边斟酌挑选着,眼睛的余光已经透过旁边的门洞看见了店主家正在奶孩子的女人,那当儿,女人旁边还蹲着一只炉子,飘着袅袅的肉香……
杂货店
紧贴石子马路的第一间房便是冯瘸子家。门朝东,窗子开在北面,靠近路口。从前他腿还没有断的时候,这家杂货店就开在这里了,但那时的主人是他父母。那会儿,他还是个毛头小子,正在读初中,说是成绩顶呱呱的很有希望,家里的打算是让他报考一个中专或师范,将来就是铁饭碗了。退一步讲,就算考不上,回家学个手艺,木匠瓦匠漆匠什么的,也能混一口饭吃。老两口原本就没指望让孩子守着杂货店,一个小店,卖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挣不到几个钱,勉强熬着,要是把孩子一辈子的前途押在上面就更不值了。
其实,值不值,人说了并不算数,人是没有前后眼的,摊上什么灾祸逃也逃不掉,这就是命。那年春天的一个清晨,下着厚厚的大雾,对面望不见人,他出门推着车子准备上学,刚上马路就遇上了一辆卡车。他在那场大雾中晕死过去,醒过来之后就成了冯瘸子,就是今天这个胳膊里架着一双拐、裤腿下面空悠悠飘着的冯瘸子。
断了腿,书也不读了,冯瘸子慢慢接受了无可挽回的现实,开始跟着父母打理杂货店。他本来就是向上要强的人,做起事来样样不落人后,平时跟别人一块儿到城里去进货,他能算能弄,简直比手脚伶俐的人做事还要活络周全。后来他父母相继过世,店里只剩下他一个人,每年到了年终岁末,跟别的生意人一样,他拿个账本夹着双拐挨个去那些欠账的人家收账。换了其他人还好找托辞推搪玩花头,可是,人家一个没腿的人年关上门要债,看你给不给?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眼看着冯瘸子一年一年大了。离三十不远的人,横在面前的难题便是婚姻大事。是呀,腿断了没有法子,但不能一辈子就独和尚一个,终归要成一户人家的。旁人也是这么想的,不少同情冯瘸子的妇人都一心想着给他寻个合适的对象。不久之后真的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家在北乡里(当地的地域界定,北乡里以穷著称)。那天,两人在杂货店里见面,他说了不少话,而自始至终人家半句都没吭声,他以为没戏了,当晚便抢先回绝了人家,事后才晓得原来那女的竟是个哑巴。这门亲事没成他也没后悔过,只是觉得心里堵得慌,为什么呢?因为别人已把他冯瘸子归入了另一类,介绍对象的依凭均以残疾为准,这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之后又有人相继给他介绍了几个残疾姑娘,一概都被他否决。渐渐的,就没什么人再给他说媒了,倒是他自己心里有了新的盘算。这盘算便是后来花钱托人从云南带来了一个女人,实质是买,买回来后就直截了当地结了婚,一年后喜得大胖儿子。眼看着日子一天比一天明朗,生意也蒸蒸日上,往来的熟人照面时总要打趣地说,冯瘸子,抱儿子啦,恭喜恭喜,散喜烟啦。他听后乐呵呵的,眼睛眯作了一条线,赶紧把一支烟恭恭敬敬地递上前去。
然而,这幸福到底没有延续下去,孩子两岁未满的那年冬天,女人竟不声不响地跟人跑了。有人说侉子(当地对口音不同的异乡人的称呼,此处指冯瘸子的女人)是和到店里买香烟的外地司机一起走的。起初,亲眷熟人都帮忙找了好一阵子,但一直没有任何音讯,时日一长,最后连冯瘸子自己也死心了。不死心也不行,女人没有了,日子照旧要过。不知不觉中,儿子一天天地长大,冯瘸子的生活又开始有了新一层的盼头。
那时候,在马桥头,来来往往的人经常看见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子,肉乎乎的,猫眼团脸,他被大伙你抱过来他抱过去,没有哪个不喜欢,谁见了都要上去亲一口拧一把。那当儿,正在屋里屋外忙活不停的冯瘸子心里应该是暖洋洋的吧。
卫羊布店
每天,隔着玻璃窗,人们都能够看到里头花花绿绿的布匹,还有坐着踩缝纫机的戴花姑娘。这便是布店。门廊那儿悬着一块白底红字招牌,字是红漆写上去的,卫羊布店。一清二楚,店主便是叫卫羊的男人。三十出头,头发有些自来卷,往后梳起,高高地浮着,使他本来并不太高的个子高出了许多。他皮肤苍白得厉害,病色的,浓眉瘦脸,整个人看起来像电影里旧时大户人家的少爷。
在马桥头这地方,他委实是与众不同的一个。一个孤儿,在乡邻亲眷的相帮下长大成人,吃足了苦受足了罪,十九岁独自跑到上海去谋生,半年后跟一个能做他娘的女人结了婚,也不叫结婚,骈居吧,乡人都是这么说的,不久便添了一个女儿……都说他发的是那上海老女人的财,三年后他带着女儿回乡,之后就花钱在马桥头买了两间房,打通后成为一大间,开起了裁缝店。店铺的开张仪式非常隆重,鞭炮响了大半天,又是花篮又是剪彩,还在镇上的人民饭店摆了饭局,整整十几桌。这是1992年前后的事情,那时候城里的摩登风气微微吹到小镇上来,然后辗转再吹到马桥头。人们的思想开始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许多念头跃跃欲试的,带着一点点惶恐。大多数人仍安分地过日子,可心里并不平静,他们的眼睛惊奇地张望着外面,这一天一个样的世界啊。随后小镇陆续出现了美发厅、台球室、录像室、小型商场等。人们的胆子一节节地拔高,心里开始盘算着什么,青年人对这一茬接一茬的变化是欣喜激越且乐于接受的,老人们则实在有些晕——世道怎么了,人心怎么都变成这样?
布店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不单是卫羊的手艺好,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在上海待过,做出来的衣裳就是洋气,穿他这里的衣服就颇有些城市人的味道。青年人最热衷追赶潮流,这潮流旋风似的刮着,卫羊的名声渐渐传开了,打响了。此后经常有不少外镇的男女成群结伴地到马桥头来做衣服,慕名而来的人见到卫羊的模样就更加笃信不疑。从此,卫羊这个名字就像一个醒目的商标为许多人喜爱着、惦念着,现在的很多广告是不好比的,人家那才叫实实在在的做工——款式料子样样都看得见,半点也不掺假,花钱买的完全是信赖和惊喜。而上了年纪的人对卫羊布店的态度仍旧没什么改观,他们喜欢循着老习惯做事,譬如说做衣服,他们大半辈子都在张桂兰那儿做,也就是马桥头过了桥拐一点,人家可是老资格老裁缝啊,不少老人的寿衣都是在那儿提前做好的。也没什么,张桂兰和卫羊井水不犯河水,一直相安无事。能有什么事呢,黄牛角水牛角——各归各,各做各的生意而已。
过了几年,卫羊被迫又结了一次婚。事情缘于他用皮尺给一个姑娘量尺寸,量完之后那姑娘便哭嚷着说卫羊的手到处乱摸,过后她家里来了不少人,闹得不成样子……闹了十几天,后来终于谈妥了:人家黄花闺女遇着这种事,以后哪还有脸见人?只能嫁给你了!一开始,他女儿就与这个晚娘水火不容,为这卫羊跟她隔三差五地吵架,两口子折腾了好几年,最后实在过不下去,就离了。而后,卫羊就一直独自带着女儿过,再没有结婚。一些喜欢嚼舌根的妇女则在背后说,他结不结婚都一回事,店里那么多姑娘,想睡哪一个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有的还巴望不得呢!
是呀,那时候,布店里确实有了不少学徒,她们都是附近的女孩子,读了几年书,小学或初中毕业,之后父母便央熟人让她们到这儿来学裁缝。说实话,大伙还是挺佩服卫羊的手艺,不然哪来这么多的学徒。而人家结不结婚的说法,也只是旁人瞎议论罢了。
理发室
冯瘸子的对门是一间巴掌大的理发室,两张大方桌就能把它塞满。墙上刷着黄影影的石灰,没有招牌,门是学校教室的那种,淡蓝色,暗锁。屋子委实太小了,里面的东西更加寒碜:一张梳头桌子,迎面的墙壁上贴着一樽到处是裂痕的镜子,桌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剪子、推子、梳子、掏耳爬之类的东西。镜子前安放着一把可以前后左右旋转的摇椅,坐垫又松又软,坐在上面倒是一种享受,只是椅身剥了不少漆,像牛皮癣一样难看。此外,角落里还有一个铁制的洗脸架子,上头卡着一只惨绿色的盆,旁边的炉子专门烧水给客人洗头。
这屋子真的很小,三两个人一进来连转身都觉得困难了。叫庚成子的矮老头便是屋子的主人,矮墩墩的一个人,颧骨很高,总穿着不太干净的大褂子,一直拖到脚底板,且还是个沙眼,动不动就淌眼泪。所有这些均给人一种压抑感,也因此对这剃头师傅生出无限的怜悯之情。
其实都是错觉,原来庚成子一家的生活相当殷实。他本人五十岁不到,白日里在马桥头剃头,生意还说得过去,老主顾不少,常来的孩子他也能叫得上名,甚至连他们上回剃头的日子还清楚地记得。晚上他不住在这里,天暗了就把工具收起来,取了抽屉里的钱——贼还是要防的,锁了门回家去。他女人也是个矮子,非常勤快,平时养鸡养鸭,还做针线活,地里的活计忙得紧紧当当的,吃得苦,农忙从来不叫帮手。到了腊月里,她还要去夹堆上割芦苇背回家,编毛窝子(一种御寒的鞋子,由芦苇编成,既结实又暖和)是她的绝活,大大小小的尺码她要编上一大箩筐,等到下雪前赶个晴天挑到镇上去卖,买的人特别多,卖个好价钱绝对不成问题。女儿呢,虽是抱养别人的孩子,但结婚后对老两口子还说得过去,每年八月半过年呀都要送礼,还塞钱,多少亲生儿子还不如呢。如今女儿出嫁已有六七年了,外孙子都那么大了……
还是说他的手艺吧。从前学徒,老师父性子急脾气犟,庚成子个矮话少,是几个徒弟中最老实忠厚的一个。那时他眼慢手笨,没少遭客人的斥责,师兄弟的嘲笑和师父不绝于耳的责骂更是家常便饭。这些都没什么——老话不是说,手艺不是学出来的,而是骂出来的打出来的。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那在镇上的犟师父早已过世,当年的几个师兄弟,混得都不孬,大家彼此离得不远,平时碰面的机会很多。就说过去那个小李子,还是最后一个入门的,现在人家已经在镇上开起了美发厅,风风火火的,里面一大拨人,修剪吹烫,好不热闹,跟戏班子差不多。也有不堪的,同是镇上的刘三,却是个惹事的主,打架杀了人,末了被逮捕起来,留下老婆和两三岁大的儿子。记得那年开审判大会的时候,人山人海的,喇叭里言辞汹汹,说是连刘三在内拢共枪毙了十几个。话说回来,看得自叹弗如或者惊心动魄,别人的遭际于他庚成子又是无干的,他本是想过安稳日子的人。
也不知从何时起,他打心眼里喜欢上了剃头这一行,假如有一天不到马桥头心里就特别堵得慌,浑身都不自在。对于自己手头上的功夫,他很有信心,他给几十年的老主顾推鬓发、剪鼻毛、刮胡子、掏耳朵。修面,现在的理发店里几乎没有人会这个了。满月孩子的头他也剃,对门冯瘸子儿子的头就是他剃的,中间留一小撮,旁边光溜溜的,仙桃似的。有时他也会被人家请到家里去,多是丧事,老人死了,家里的子孙后代都要剃头,挨个儿地排着队到他跟前剃,那一天他忙得连喝口水的闲暇都没有。而平日里,剃的最多的还数学生模样的孩子,通常,他们被一个个面色蜡黄的妇女领进来,做娘的只说一句话:尽量剃短一些。他知道她们的心思,剃短了才挺得时间长啊。孩子剃个头才五毛钱,可见过日子都不太容易。于是,他笑道,板寸头,我晓得的。
想起来,也有遗憾。他一个徒弟都没有,学徒的全都到镇上或者更远的城里去了。碰到人们到镇上赶集的时候,有许多人从马桥头路过,老远的常听见有人笑着说,庚成子,你也太落伍了吧,店里火钳有吗染头行吗?他光笑不答。这时候,他想,剃头就是剃头,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他才懒得去管。
这马桥头乌七八糟的事情还真不少。就说卤肉店的王家和李家吧,算起来还是表亲,两家女人却常常当街拌嘴吵骂,骂得那个狠劲呀,咬牙切齿的,所谓同行冤家真是一点也不假。吵架时一般双方的男人都不参与,不插嘴也不制止,躲得远远的。两家的女人都不是省油的灯,嘴皮子相当,小手段也都会耍一些。倘若今天李家的生意略微好一些,明天王家女人就会对人讲李家卖的都是死猪肉,她绘声绘色地跟人讲,看到了吗,那肉红得不正常啊。风声很快就刮到李家耳边,这次李家女人不吵不闹,以牙还牙也玩起了阴毒的招儿,她逢人就嘀咕王家的女人查出来是肝炎,唉呀,传染病治不清爽的。终于,后来的某一天傍晚,两个女人竟在门前动起了手,又是食刀又是棍子,两家的男人恰巧都不在家,等左邻右舍跑过来拉劝时,两人已撕打成一团,衣衫沾满了血迹。可是到了晚上,两个女人一前一后跑到旁边的诊所里去涂药包扎,她们见了面当作没看见,径直和先生(当地对医生和老师都叫先生)说话。这还不算什么,第二天天亮了,她们照旧生炉子熬柏油拔猪毛,见了熟人边嬉笑边打招呼,好像昨天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
还有炸油的和修电器那两家,也是一天到晚不得安生。都说炸油的使诈骗了顾客的菜籽油,可惜谁也找不着证据,但疑心依然很重。也不能怪顾客,半袋子的菜籽连一壶油都炸不满,当然会怀疑。但附近又没有别的炸油铺子,到镇上去路远不说,还得排队,所以只好来此处,因此那里天天发生口角,都是些车轱辘老话题。不过,这家的生意一直做着,且很红火。那修电器的马四手脚也不清爽,总是把顾客电视机录音机里的零件换走,被当场逮住了还死不承认,简直吵翻了天,后来生意逐渐清冷下来,他又改修手表,结果呢,还是成天跟人吵。文明人说,人品这样子没办法的,也有人很直露地说,狗改不了吃屎。
倒是忘了说,我外婆家老早就住在马桥头了。就在冯瘸子家的隔壁,门藏在巷子里头,巷子真的很窄,勉强够一个人推着自行车进去,故容易被人忽略,但走进去便豁然开朗。三口锅的灶头,一层连一层的蒸笼,几只不大不小的和面盆,以及成捆的柴禾,堂屋的门后还堆放着雪白雪白的面粉。一目了然,这里专门为人加工馒头,分扁的和尖的两种,尖的点了洋红、洋绿就变成了很好看的寿桃,价格要贵一点,顾客买回去给人祝寿。那时候,我总是管不住自己的手,到处乱摸那些白白胖胖的馒头。为这,手心手背不知挨了小姨舅舅们多少回痛打,每次连打带吓,但就是不长记性。好在后来慢慢长大了,长大了就知道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了。
这些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住在外婆家。三岁到十三岁,这中间,一个孩子人生中最美好的光阴在这个叫做马桥头的小集镇上驻足停留,他看见这个世界的人来人往和喜怒哀乐,从此刻在记忆里,一辈子也忘不掉了。
责任编辑 高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