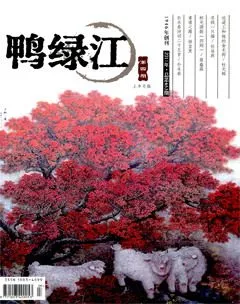散文二题
2011-01-01徐国良
鸭绿江 2011年4期
徐国良,湖南沅江市人,大学本科文化,大校军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海南省文联委员,海南省作协理事,三亚市作协副主席。先后出版作品5部。《德行天下》《诚行天下》《度行天下》,均为论说公民道德行为的随笔散文,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引起众多新闻媒体的关注。《人民日报》《中国文艺报》《中国出版》《人物》等报刊予以评论。
想起了结婚证
那是1993年9月的事了。作为广州军区的代表,我应邀去北京参加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并观摩第七届运动会。因夫人从未去过北京,她想自费随我了却那三十年的渴望。
解放军十个代表下榻在商务会馆。这种国家级会议是不能照顾家属住宿的,我打听商务会馆总台,仅剩几间套房,四百多块一间。屈指数来,会期十天,要扔四千多块钱不值得。服务小姐说会馆附近只有一个很便宜的地下旅店。一听“地下”,我心中咯噔一下,北京还有违法开秘密招待所的?但观小姐表情,似无丝毫神秘状。听说很近,我们带着疑虑走去。
打听两次便找到了这个招待所,店牌挂得还是趾高气昂的,只是进旅店需顺着台阶朝地下走。越往下越有一种迈向定陵地下墓室般的阴森感──这是个地地道道的地下旅店,由一栋宿舍楼的地下室改建的,有两个退休人员管理,招了几个乡下姑娘做服务员。有身价的人是决不会光顾这种地方的。我见它离会议代表驻地近,总台值班的大爷和蔼可亲,服务员热情实在,房间干净,价格也还合理(双人房仅38块钱一晚,只是厕所洗漱间是公用的,这在北方也很正常),便建议夫人将就着住了下来。她说她一个人住地下室好害怕,我只好晚上来陪她。许是连日的东跑西颠太辛苦,一上床我就不管它是地下还是地上,鼾声如雷了。
“嘭、嘭、嘭”,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是起火了还是地震了?干吗这么晚还有人敲门打火。我急问:“谁呀?”“查房的!”门外的声音比我更急。
“查房的?”我一看表,已是凌晨2点。 这年头居然还有人半夜三更打扰客人来查房,不是发现了案犯,至少也发现了嫖客,没搞错吧?许是我们长住海岛,囿于军营,孤陋寡闻之故,对半夜查房(尤其是老婆在房间的情况下),很不习惯。我叫夫人穿戴整齐。她确实太困,忸怩着不想起:“这鬼地方,还查什么房?”门外又“嘭嘭嘭”地敲起来了。我说,也许真碰见鬼了,你还是起来的好。
开了门,一个目光冷峻的公安进来。“我们是派出所查房的。”说着,他亮出了公安工作证:“干吗半天不开门?”
“有女同志在,总要穿上衣服吧。”我也懒得客气。
“哪里来的?”他急急地问。
“海南来的。”我慢慢地答。
一听说海南来的,他好像发现了敌情,眼中顷刻充溢着警惕和鄙夷,似乎马上就要逮住一个坏蛋了。
“干什么的?”他态度变凶。
“拿枪的。”我倒平静起来,故意不说是当兵的,想和他逗逗。
“身份证?”
他还没有进门之前,我就想到了这码事,趁夫人穿衣服的当儿,便把两口子的身份证和国家体委专制的带有照片的出入人民大会堂会场和七运会赛场的代表证找出来放在桌上。
看了我俩的身份证、工作证,气氛缓和了些许。他脸上凶气渐消:“会议应该安排你们的住宿呀?”我说只安排代表,不安排家属,只好就近找个地方对付几天。无奈她胆子小,我来做保安。
“你怎么能住这地方?”他眼里透着疑光。
我不理解他的意思,是我的身份不该住这么贱的旅店,还是这个地方太污秽、不干净或有黑店之嫌。但瞧站在门口的那个守总台的老大爷祥和的面色,似无任何邪污之嫌。我只好照实说了:“您别以为现在海南人都有钱,我们当兵的其实更穷。能在这里住几天,就很满足了。这地方便宜、干净、实在。”听我这么一说,他东拉西扯几句后,走了。好像我左右的房间都没查,专查我们这间房。第二天早晨,我问在总台值班的老大爷,为什么专查我的房?他说:“都查,都查,只是看到您在登记本上写着‘海南’、‘政委’,他就在你那里查得认真些。”
第二天晚上,我满以为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刚脱下衣服,门口又“嘭嘭嘭”起来。我当是老大爷叫我接电话,夫人只穿件上衣歪在床头,我去开门。见鬼,又是查房的,并自我介绍说,他是这地方派出所的头儿。我说你们昨晚不是查过了吗?“为了您的安全,再看看证件。”我又把所有证件全部递给他,他并无心思细看这些证件,懒懒地扫了一眼后,抬起眼皮,不屑地一瞥:“你当团政委的,应该去住宾馆嘛。”“应该的多了,只是没有钱啊!”我倒感激起他的关心来了。“不能报吗?”“找谁报去?”他忽然掉转话题,伸出手来:“有结婚证吗?”
一听“结婚证”,我陡然紧张心慌起来,仿佛真的带着别人的老婆同居时被抓了似的,无言以答。
片刻的紧张心慌之后,我立马镇静下来。扯淡,都什么年代什么年龄的人了,谁还想到夫妻出门带结婚证?我哈哈大笑起来:“我们都四十多岁的人了,还有什么结婚证,早都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我告诉他,我的身份证明上清清楚楚地标明我是53608部队政委,夫人身份证明上明明白白写着她是海南屯昌县计划生育指导站干部,你可以向我们军区向国家体委会务组查证。
他说,查也不必了,按规定没有结婚证的男女不能在旅店同宿。听说夫妻不能在旅店同住,我猛然记起北京好像还有这些规定,这也是“中国特色”。既已犯规,就决不能硬来,必须软着点。我向他求情说,听说你也当过兵,你说我这个在部队当政委的,两口子都这把年纪了,第一次夫妻紧紧张张出远门,哪还想到带结婚证呢?老实告诉你吧,不是你提醒,我早忘记我曾有过结婚证了,你就照顾照顾这个实际吧,我们去睡马路也不雅观。我见他笑了,又开了一句玩笑:“你放心,我们是百分之百的合法夫妻,要不然,不会带这么齐的证件在这里住的。”我夫人也来劲了:“他要找情人,也不会找我这么个半老徐娘嘛,现在到处有小姐。只是哪个情妇也不会跟他来住地下室,没这么便宜!”
公安也忍不住笑了起来,看来再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深更半夜赶走我们了,他说:“今晚就住下吧,明天必须弄个具有法律权威的证明来。”他转身时,那表情告诉我,明晚没商量。
他说得轻松,却叫我丈二高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是具有法律权威的能够证明我们是合法夫妻的证明呢?唯有结婚证。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北京市,我去哪里弄结婚证。
公安走后,我辗转反侧,老想着结婚证的事:其一,我不知道我们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老总们带着夫人出国考察、旅游时,带结婚证没有,倘若没带结婚证在国外与老婆同住,要是遇到外国公安来查房,当嫖客抓了起来,多难看,岂不出了国际洋相,丢了中国人的老脸?就是不抓起来,像我这样深更半夜几番遭盘查,也怪难堪的了。其二,我不知道我们中国现存的合法夫妻中有几成保存了结婚证(至少解放后结婚的我的父母和岳父母的结婚证早已做了灶中的引火纸了),没有结婚证,他们出门旅行多不方便。尤其每年冬天到我们海南去旅游的老老少少的夫妻们,我敢说有八成没带结婚证,若是半夜查他们的房,没有结婚证不准同住,该叫多少人流落街头或遭罚款。(当然,罚款也是某些部门生财的重要渠道。)其三,持有了结婚证,就能保证婚姻的真实性吗?就能保证男女坚守“围城”,不在外面寻花问柳、养奸偷小?钱钟书先生曾将婚姻比作“围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要是保存这张结婚证就能保证城门紧锁,没有开小差的,那结婚证必定成了唐僧的紧箍咒。其四,倘若仅凭一张结婚证就可以确保公开同居平安无事,在这个连人民币、存款单、汇票都可以造假的年代,造结婚证更是小菜一碟,那些地下交易所、那些不法分子,不又开发了一个赚钱的项目——贩卖假结婚证。其五,我们那张结婚证丢了怎么办?以后还能出远门吗?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出门在外,老伴同行而不能同住,是不方便的。一口气接不上或血压升高,叫谁去?像我们这些独生子女的父母,就全靠“少是夫妻老是伴”了。
结婚证,你在哪里?
我的思绪,如父亲傍晚上山寻找砍柴未归的儿子,向黑夜、向过去开始了坎坷漫长的搜寻。
行走在戈壁
在老战友顾平主任的陪同下,2004年仲秋,我去了一趟罗布泊。行走在戈壁滩上,我特别渴望的是能够看到绿色,看到生命。可惜走了几百公里,没见一丝绿影,没看到一个生命体。
正午时分,终于在走进一个通信站的营门时,看到一行绿色植物组成的字:戍边卫国,不辱使命。我想,这个部队能用绿草在这死亡之滩上种出这么几个大字来,真是不容易啊!我兴奋得几近忘乎所以地奔了过去,用手轻轻触摸这些绿色时,我的神经倏忽绷紧起来——这些绿字是用异常坚硬扎手的枯茅草,切割整齐,涂上绿色油漆后“种”在地上的。这一路上,我只听人们赞美戈壁沙漠上的胡杨树能活一千年不死,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烂,哪成想到在这戈壁沙漠上,茅草的生命力竟也这般坚强!正是这些早已死亡的枯草,用它们不朽的生命,为戈壁战士奉献着绿色的爱心、绿色的希望。虽然它们早已不是生命的载体,但它们依然承载着共和国士兵绿色的憧憬,坚强挺拔地伫立在戈壁滩上。
在主人的盛情挽留下,我们在这个通信站吃了一顿终身难忘的午餐。饭后,我在整个营区搜索了一遍,未能寻觅到一点绿色的影子。几棵奇形怪状、呲牙咧嘴的枯死胡杨树蔸,被战士们当作盆景雕塑,很是艺术地摆在营区一角。其实,那干枯而苍老的生命,除了能给人们带来岁月的苍凉感,自然的冷峻感,戈壁的萧杀感,激发不了人们对生活的半点美感。教导员看到我的表情,颇有一些难为情地说:“首长,我们曾经千方百计想在营区种活一棵树,一片草,甚至以党委决议的形式号召全站官兵,谁种活一棵树,给谁记三等功一次。但在这里,人是改变不了自然的。虽然我们在营区看不到一点鲜活的绿色,但全中国的绿色土地都装在我们心中。我们奉献,只愿祖国绿色常在;我们辛苦,但求人民幸福安康。”
多么伟大的绿色观啊,只有在戈壁滩军人的心中,才能生长和茂盛出来。
带着遗憾和渴望,我们继续前行。其实,我长期生活和工作在三亚这个四季如春的绿色世界里,一年到头,我的日子溢满绿色,我不稀罕绿色。只是当我行走在这茫茫戈壁,浩瀚沙海,看不到一丝绿色的星影时,我在心底对绿色的渴望比戈壁战士们更加浓烈。这时,我是多么渴望有生命的同类出现,我甚至用职业的习惯展开了思绪的翅膀:假如一场残酷的追击战打到这里,只剩下一个孤独的我,此时一个持枪的敌人、一个唯一的生命伙伴朝我走来,我该怎么办?我想,我一定是喜出望外,只要他不朝我打第一枪,我是决然不会主动朝他射击的。在这渺无人烟的生命绝地,能见到一个生命载体,都是我生命旅途的福气,都是我生命的伙伴和支撑,更别说人了,我怎能忍心将他击毙呢?我怎能无知地将自己投入到孤独和悲怆的境地呢?在这渺无生机的戈壁沙漠,见到任何一个生命载体,就是见到了生存的曙光,见到了延续生命的希望。
当我的这种思想刚刚出头,我立马用政治领导的惯性思维提醒自己:我是否走进了“立场不稳,敌我不分”的认识误区呢?可是转而一想,如果把这仅有的生灵杀绝了,留下徒有其名的阶级和政治又有何用?
在现今的地球上,大自然的戈壁是上天造成的,我们没法改变。如果人们再造出心灵的戈壁来,那就是天灾人祸,地残人缺了。建立和谐社会,首要的是铲除心灵戈壁,建设心灵绿洲。一个美好的和谐的社会,不是诞生在自然的绿洲中,而是诞生在心灵的绿洲上。同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为什么解放前军阀混战,战乱不断,民不聊生,解放后国泰民安,繁荣富强?是因为人民有了心灵的绿洲。只有当人的心灵变成了绿洲,才会有真正的人间春天,美丽家园。只要人的心灵春色常在,再大的仇恨都会在心灵的绿洲中消融化解;再苦的希望都会在心灵的绿洲中开花结果。建设和谐社会,贵在建设和谐心灵。正如那首歌中所唱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是美好的人间。
责任编辑 盖艳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