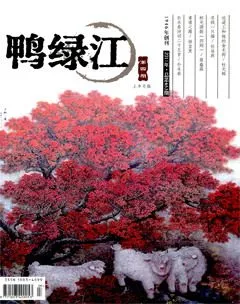奔跑
2011-01-01徐永
鸭绿江 2011年4期
徐永系笔名,原名徐勇。七十年代出生,现居德州,经商。在《长江文艺》《时代文学》《海燕》《青春》《文学与人生》《山东文学》《星星》诗刊等文学期刊发表过中、短篇小说和诗歌。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第四届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2002年初辞职经商后辍笔,2009年始重新业余写作。
一
刘翔跨栏的一瞬间,三儿摁摁自己的腿,偷偷地看着小玉。在三儿眼中,小玉比那些电影明星还要漂亮。
小玉是“好再来”便利店的营业员,这个便利店就在火车站广场东边,三儿经常到这个店里来,买一点可用可不用的小东西,顺水推舟地看一看小玉。今天,三儿来到店内时,电视屏幕上正好在重播世界田径锦标赛跨栏比赛,刘翔身子腾空的样子让三儿想起小时候见过的一种烟盒。墨绿色的烟盒上,几笔勾勒出一只栩栩如生的雄鹿,雄鹿的姿势就像马上要飞起来。
三儿倚着收款台,他左腿站得笔直,右腿蜷曲,脚尖着地,好像随时就要迈出去。三儿嘴里的烟头歪叼着,上面挂着长长的烟灰。当刘翔冲过终点线的时候,他不由自主地狠狠掐了掐右腿。同时,收款台内站着的小玉跳了起来,巴掌也跟着响了,嘴里嚷道,刘翔真帅!
三儿撇撇嘴,叼着的烟差点从嘴里掉下来,他赶忙拿手捏住,烟灰却落了下来,掉到了右腿的裤子上。他边用手掸着裤子边说,帅什么啊,满脸的疙瘩。
你知道什么啊!人家那是青春美丽痘。小玉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撇了一下嘴。
拿包烟。三儿扔到收款台上五块钱。小玉打开收款机,把钱放进去,收款机随即开始吱呀呀打印小票。这声音让三儿不由自主地打了个激灵。从小玉手里接过“将军”烟,他顺手在收款台上拿了一个打火机,然后肩膀一耸一耸地出了便利店。小玉在身后喊道,打火机还没给钱呢。他摁了几下打火机,看着时着时灭的火苗,嘴里应着,下次给。
在便利店里吹着电扇,没觉出多热,出来才知道,外面太阳很毒。三儿眯着眼,一只手遮在额头,不紧不慢地走在广场上。
在毒日头下晒了会儿,三儿有些头昏眼胀。没走几步,汗就冒出来,裤子贴在腿上,有些黏糊,每迈一步,裤子就像又瘦了一圈。火车站广场空荡荡的,广场的中间矗着个垃圾桶,很突兀,仿佛一张白纸被滴上一滴墨汁。路过垃圾桶时,三儿瞥了一眼。敞着盖的垃圾桶里的垃圾满得快要溢出来,最上面有被揉搓成一团的烟盒、发霉的香蕉皮、一桶康师傅方便面桶,还趴着几只颤动着翅膀的绿豆蝇。
候车室四周安静,偶尔冒出个人。走着走着,三儿觉得自己就像一片被晒蔫的叶子。走到售票厅的门口,他感到有微风吹过,于是把圆领衫撩到胸口,露出干瘦的腰身。那风吹到裸露处,意外的清凉。
售票厅的屋顶很高,几个老式吊扇吱吱扭扭地转着,屋里有一股空气不流通发霉的味道。每次进来的时候,三儿总会下意识地抽动一下鼻子。只有一个售票窗口开着,买票的就五六个人。其中一个穿白衬衣的年轻人不停地打着哈欠,不时伸出手捂住嘴。当年轻人排到第二位的时候,他从屁股兜里掏出几张浅红色的纸币,抽出一张,又把其余的放回去。三儿走一步顿一下地来到买票的队伍边,侧身插到年轻人的身后。这时候身后响起轻微的嘟囔声。回头一看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对三儿的插队脸上露出不满的神情。三儿横了他一眼,中年人的眼神马上飘到了别处。好像有人在后面推了三儿一下,他刚转过身就倒在了前面年轻人的身上,年轻人没有防备,一个趔趄又扑到前面买票的人身上。买票的队伍开始混乱。三儿站稳了,回头嚷道,挤什么,挤什么,就这么几个人。身后的中年人惶恐地解释,我没有啊,我没有啊。三儿嘴里骂道,一点素质都没有。手揣在裤兜里,晃悠着出了售票厅。
来到外面,三儿的步伐明显加快了。他没有走广场,而是钻进售票厅一侧的胡同里。他走得有些急,差点一头栽倒在地上,幸亏扶住了墙。回头张望,后面没有人,他长吁一口气,溜着墙根儿出了胡同。
胡同的尽头是条大道,大道斜对面有家网吧,网吧的名字叫伊甸园。伊甸园分两层,一层是大厅,二层是一间一间的单间儿,三儿只要得手后,就会到这里找个单间儿眯会儿,算是避避风头。
三儿一进网吧就嚷,来瓶可乐。当网管起身去拿的时候,他又补充道,要冻出冰碴的。网管从冰柜里拨拉几下,摸出一瓶可乐,瓶身布满了霜,冒着白气。网管在柜台上拿起起子,熟练地打开瓶盖,然后递给三儿。三儿接过来,一仰脖儿,可乐就下去一大截。冰凉的液体迅速流淌到胃里,然后一股气体又从胃里泛出来,他不由自主地打了几个嗝。正抹着嘴的时候,一只手重重地拍在他肩上。他吓得一哆嗦,可乐差点从手里飞出去。等稳过神,回头一看原来是王胖子。
王胖子穿一条蓝格短裤,两条腿上的黑毛茂盛,怎么看也不像人身上的毛。络腮胡子遮住大半个脸,像沾满了黑泥。肩膀上搭着背心,上身裸露,草包肚挺着,像怀着七个月的小孩。一条青龙从后背盘旋到肩膀上,张牙舞爪地冲着三儿过来。三儿苦着脸,看着王胖子伸出来的手说,哥,最近活儿不好做。
快点拿出来,别他妈惹我。王胖子歪着嘴说。
三儿慢吞吞地从裤兜里掏出三张淡红色的纸币,纸币潮乎乎的。他刚想从里面抽出一张,就被王胖子一把全夺了过去。王胖子把纸币掖进裤兜,扭身就要走。三儿使劲抽了下鼻子说,哥,我也得活啊!
王胖子回过头冷笑一声,我要活不好,谁也甭想活。话音落下,就推门而出。门咣啷一声关上,王胖子消失在三儿的眼前。三儿又抽了下鼻子,往地下吐口吐沫,狗日的。这声音只有他自己能听到。
二
橡胶跑道上,三儿单膝跪地,他夹杂在各种肤色的选手当中,黑头发,黄皮肤,特别醒目。带着运动帽的裁判咕噜出几句鸟语,然后扬起发令枪,其他选手马上蹶起了屁股。他一看,赶忙跟着蹶起屁股,左腿成九十度弯曲,右腿蹬地,两只手摁住跑道。发令枪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一股白烟从枪膛里冒出来。三儿的右腿使劲一蹬……这时候他突然醒了。
不知道几点了,反正天还黑着。由于出了一身汗,一动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三儿两只手交叉放到脑袋后面,就这样枕着。怎么没跑起来就醒了?他问自己。他经常做这个梦,每当发令枪响起的时候,他总会醒来。这让他很沮丧,因为他没有体会到奔跑起来的感觉。
那台华生牌的老电扇吱扭扭地转着,风吹在三儿的身上,又吹向别处,窗帘被吹得不时撩起一角。他没了丝毫睡意,坐起来,靠在床头,在床头柜上摸到烟和打火机。打火机打着的一瞬间,在跳跃的火焰中,屋里的一切依稀可见,随后又随着火苗的熄灭消失了。烟雾在明明灭灭的烟头中舞蹈,这让他突然想起小时候的场景:母亲半蹲在地上,微笑着伸出双手,他在几米处犹豫着。母亲不停地鼓励,他终于跌跌撞撞地跑过去,一头栽进母亲的怀抱。他的两只手死死地抱住母亲的腰,心还在扑通扑通跳着。母亲的怀抱里有股淡淡的香味,和香烟的香味不同,是那种让他晕眩的香味。这情景仿佛是睡觉前刚刚发生的事情,触手可及。一只针扎在他心上,他想到这个家现在就他一个人了。三儿的鼻子仿佛被捏了下,他被烟呛了,不停地咳嗽,身子跟着抖动,烟被扔到了地上。过了好久咳嗽才平息下来。寂静中,他听见自己粗重的呼吸声,还有隐隐的虫鸣声,他突然有想和谁说说话的冲动。
三儿起身从衣兜里找出手机,拨了个熟悉的号码,电话那边传来的是一个冰冷的女声,你所拨打的号码已关机。他站在屋里犹豫了会儿,还是出了家门。
外面冷冷清清的,马路边只有一侧亮着路灯,泛出的光让三儿有些恍惚。他坐在马路牙子上点上一根烟,烟吸到大半截的时候,他招手上了一辆出租车。一会儿的功夫,就到了蓝天洗浴城。蓝天洗浴城的门头灯箱有些破旧,上面只有两个字闪烁,远远看去,以为店名叫“天浴”。他进了灯光昏暗的洗浴城,一个睡眼惺忪的少爷给他拿来了拖鞋。夏天的衣服也好脱,他三下五除二地就把衣服塞进了橱子。
一进浴池,扑面而来的就是潮湿、霉烂、肥皂还有尿骚混合在一起的气味,三儿不由皱了皱眉头。池子里的水有些发浑,他去了淋浴区。喷头流出的水一会儿热一会儿凉,他匆匆洗了洗,就穿上浴服直奔二楼按摩室。还没等少爷给他推荐,他就说,叫21号过来。
静姐推门进来的时候,刚想鞠躬问好,却发现是三儿。她走到坐在床帮上的三儿跟前,埋怨道,打个电话,我直接去你那儿不好么?
三儿挠挠后脑勺说,天热,睡不着。
静姐的手指戳着三儿的额头说,这儿多贵啊,你个败家爷们儿。三儿边躲边咧嘴笑。静姐把身子贴过去,咬着他的耳朵说,是不是想我了?他没吭声,静姐的手开始在他胸前游弋,他一把抓住,说,说会儿话吧。
别浪费时间了,这里记钟收费的。静姐说着就把三儿的上衣给脱了。
两个人折腾完,三儿脸朝外侧卧,静姐在身后搂着他,头埋在他脖子里,深深地呼了口气说,小玉是你的新相好吧?静姐的身上泛出一股咸咸的味道,一下把他笼罩了。
小玉是谁?三儿装糊涂。
哼,你刚才都叫出声了。
我叫人了么?三儿好像在问自己。
静姐的手指在三儿后背上轻柔地滑动,她叹了口气,我老了,对你没吸引力了。
你别胡思乱想,三儿扭过身子,紧紧抱住静姐。他的眼睛却看着天花板出神。
你收手吧,我整天替你担惊受怕的。静姐钻在三儿的怀里,用鼻子轻轻地蹭着他的胸。
再干一段时间,攒够钱就不干了。三儿说。
我这存了点钱,咱们开个店吧。静姐说。
男人哪能要女人的钱,再说你那点钱还是留给你儿子吧。三儿松开手,仰面躺着。
静姐坐起来抿抿头发说,你和我还分。
我这钱快攒够了。放心吧,我会小心的。三儿把胳膊放在脑后枕着。
起来,赶紧走吧,马上到钟了。静姐轻轻拍打着三儿的脸。
三
天气有些阴沉,微风夹杂着潮湿的气味,不停地吹来吹去,让闷热的天气有了些许凉爽。三儿从火车站广场的一角冒出来,他一只手插在裤兜里,一只手前后甩着,嘴里吹着口哨,眼睛滴溜乱转四处寻摸,一不小心被地上翘出来的花砖绊了,一个趔趄差点摔倒。他赶紧站稳,嘴里吐出一句脏话。
瞎子阿文坐在广场边上,抱着一把吉他,摇头晃脑地在卖唱。他跟前的搪瓷缸子里,是一眼就数得清的几枚硬币。三儿知道,那里还有三四个是阿文自己的,他偷偷看过多次,每次阿文坐到这里,都煞有介事地把缸子放在面前,一枚一枚地放上三四个硬币。
阿文的白眼珠不时往上翻翻,支楞着的两只耳朵,在三儿看来如同兔子的耳朵。阿文唱道: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想要飞呀飞
却飞也飞不高
我寻寻觅觅
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
这样的要求
算不算太高……
阿文的嗓音很浑厚,只是吉他音有些乱。三儿本来已经走过去了,可越听心里越不是个滋味,他自言自语道,这狗日的咋唱得这么动情呢?三儿又踅回到瞎子跟前。他没和瞎子说话,蹲下身子,放到搪瓷缸子里一张五元的纸币。瞎子还在唱:
我是一只小小鸟
有一天栖上了枝头
却成为猎人的目标……
三儿站起身边走边回头看,瞎子居然向他点了点头。那白森森的眼珠翻动着,看得他心里有些发紧。
火车站派出所警长郝大头倒背双手迎面走过来。他没带警帽,上衣只系了两个扣子,露出红丝丝的胸脯,腰里别着的报话机发出刺啦刺啦的声音。他不时打量打量从身边背包拖行李走过的人。三儿一见扭头想溜,郝大头眼尖一下发现,喊道,三儿,你给我过来。他一听躲不过去了,只好心下惴惴地挪过去。
你在这晃荡什么呢?郝大头训斥道。
没什么事,转悠玩儿。三儿堆起夸张的笑容,脸蛋上的肉绞在一块,表情异常地生硬。
没事儿瞎溜达啥?别在我地盘上多事,否则饶不了你。郝大头撇嘴仰脸地教训三儿。
您老在,我哪敢啊!
没事儿就赶紧滚蛋。郝大头说罢倒背着手往前走。
三儿三步并作两步地追上去,悄声在郝大头身后说,我给您老买了两条玉溪烟,放在“好再来”便利店了。
郝大头停住脚步,瞪了三儿一眼,少来这套,别他妈给我生事就行。
三儿忙点头哈腰称是。
望着郝大头远去的背影,三儿心想,这王八犊子,真能装。
三儿刚到“好再来”便利店的门口,就看见隔壁卖扒鸡的猴子趴在收款台上和小玉说着什么。小玉咯咯乐着,活像一只刚刚下了蛋的小母鸡。见三儿进来,猴子不再说话,抄起刚买的东西跟小玉打了个招呼,走了。猴子在三儿身边走过的时候,三儿恨不得在他洋洋得意的脸上来一拳。
三儿绷着个脸,来到小玉面前。你和这种人来往什么?他可是个流氓。
小玉没搭理三儿,举起手,在半空翻翻,仔细打量刚染的指甲。
你怎么把指甲染成黑色的了,那些小姐们才弄成这种颜色。三儿急赤白脸地说。
你知道什么?现在就流行这种颜色。小玉摆弄着双手说,多好看啊。
流行个屁,越这么弄越恶心人。三儿开始恶毒攻击了。
我的手,我愿意怎么弄就怎么弄,你管得着么。小玉横眉立目。
一看小玉真急了,好,好,好,我管不着。三儿自嘲道。他摸出五百块钱,摔到柜台上,来两条玉溪。
小玉从货架上找出两条玉溪烟,扔到柜台上。他摆摆手,哄弄谁啊,这烟都是假的,我不拿,你们继续卖吧。
小玉哼了一声,把烟又放回原处。
郝大头给你涨工资了么?三儿问。
早就说涨,到现在还没涨。就是涨也涨不了多少,没什么意思。小玉拿出一把锉刀开始修指甲。
我钱快存够了,到时候开个饭馆,你去当收银员,我给你一半股份。三儿紧张地看小玉的表情。
小玉吹了吹指甲沫,你打去年就说钱快凑够了。
这不是我妈给留下了点钱,我一直不想动嘛。现在想明白了,也不能老干这个。三儿赶忙解释。
到时候再说吧。小玉又把手举在半空,翻转着打量。
三儿看小玉有些不耐烦,只好说,那我走了。走几步他又想起什么,说,以后晚上别关机,前两天我想请你宵夜的,可是你关机了。
四
三儿和静姐、静姐刚从乡下来的儿子在步行街前的加州牛肉面馆吃饭。静姐让儿子黑子喊三儿叔叔,黑子抬起头瞅瞅三儿,又耷拉下眼皮继续吐噜吐噜吃牛肉面。静姐作势打了下黑子的头,说,这小子,真不听话。
三儿解嘲般地笑笑,问静姐,他爸走了多久?
快三年了。男人是天,女人是地。天塌了,地也得撑着。静姐边说边用温柔的目光抚摸着正低头吃面的黑子的头。
“哐”,桌子开始晃动,上面的碗跳了起来,然后迅速落下,整个过程才几秒钟,屋子里的人都感觉到了震动。
三儿和静姐过了好一会儿才醒过神来。静姐脸色有些变,嘴里说着,别是地震。说罢扯着黑子就要往外走。西南大地震刚过去不久,各种传言都有,闹得人心惶惶。屋里这时候已经有人开始往外跑,剩下的人放下筷子,东张西望,神色仓皇。三儿心里有些发慌,但故作镇静地说,不会吧,是不是附近有搞爆破的。黑子不听这些,他抬起头打量下静姐和三儿,又忙着往嘴里填东西。三儿的手机突然响了,铃声异常响亮,一个男人唱道,你说我容易么?上辈子欠你的……手机在裤兜里使劲叫着。静姐用眼睛示意他一下,他才恍然大悟把手机掏出来。是小玉打来的,三儿有些心虚地偷瞅了静姐一眼。静姐正在看他,他赶忙低头看手机,说,又是王胖子,催保护费了。说着他摁下接听键,嘴里说着喂,人向外走去。
电话那边传来了小玉的啜泣声,三儿一下慌了,怎么了?小玉。小玉还是在哭。小玉,你别哭,有事你说啊。
小玉开始断断续续地说,我妈病了。是癌症。话音还没落就嚎啕起来。三儿回头看了下店里,静姐正在吧台结账。他接着对小玉说,我现在有点事,一会儿给你电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三儿刚挂了电话。静姐就带着黑子出来了。静姐看他的表情有些不自然,关切地问,怎么了?
没事。三儿强装笑容。
我说你别干那个了。不光危险,还受那些混子欺负。静姐又开始劝三儿,跟我一起开个服装店吧。
再说吧。我头有些疼,就不陪你和黑子转了。三儿用手使劲摁了摁额头。
那你自己照顾好自己,有事给我电话。静姐用手模仿电话听筒在耳边比划了一下。
看着静姐和黑子走远了,三儿就给小玉打电话,打了好几遍小玉也没接。他慢慢地往家走,走得心神不宁。正当三儿坐在家中闹心的时候,小玉把电话回了过来。小玉的声音很平静,她告诉三儿,她母亲要马上住院,缺两万块钱住院费。尽管小玉没说借钱的话,可还是让他的心乱糟糟的,两个念头就像两个势均力敌的拳击手在格斗,你来我往,难解难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只好安慰小玉说,不要着急,这两天想想办法。
挂掉电话,三儿还是没有一点头续。他在屋内呆了一会儿,索性脱了衣服,脱得只剩下一条裤衩,坐在沙发上已经塌陷的坑里看电视。拨了几个频道,电视中人们都在忙着援助灾区。三儿想,现在灾难太多了,也不知哪儿来的这些灾难。最后他把遥控器定格在一个频道上,画面里出现的是一个女孩的面孔,看上去有些稚嫩。主持人告诉大家她是位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