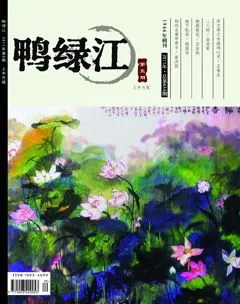草木来信
2011-01-01张羊羊
鸭绿江 2011年5期
张羊羊,七十年代末生于江苏常州,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江苏省作协签约作家。习作散见《散文》《十月》《鸭绿江》《钟山》《天涯》《山花》等刊物,有诗集《从前》,散文集《庭院》等出版。
看麦娘
池莉有部小说《看麦娘》我没读过。每每看到读过小说的人有诸如“开始看小说,才知道看麦娘是一种杂草,而且在乡间田头随处可见,还有个俗名叫做狗尾巴草”、“看了池莉的小说《看麦娘》后,才晓得平常的狗尾巴花还有一个如此令人动容的好名字”的感叹,更有甚者感慨差点被这美丽的名字幸福地击倒,我有点忍不住要为这感叹而感叹。如果你真被这个名字和名副其实的看麦娘击倒,那也许才能称得上幸福。
在写过很多植物之后,因涉及的资料较多,我发现往往每种植物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叫法,多的甚至可达数十种。加上科属上的亲缘关系,也往往出现不同的植物有相同的名字。我没去武汉的乡间探询过,也许那个地方就是把狗尾巴草叫做看麦娘的,可我想的是这狗尾巴草为什么会叫看麦娘呢?看麦娘的表意是看护着麦子长大成熟的另一种草,这个名字有着类似于奶妈一般的温情,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狗尾巴草就是看麦娘多少有点令人费解。而且据我儿时对田野的记忆,麦田里是鲜有狗尾巴草的,那草多长于田埂、沟渠和河坡。麦田里和麦子夹杂生长最多的是另一种草:细圆柱形灰绿色的穗,大约长3至8厘米,小穗含一朵花密集于穗轴之上,花药橙黄色。这种草的长相倒有点“看麦娘”的味道。如果我时常能把植物的名字和它本身搞错的话,那池莉也同样有这种可能,何况在她体量较大的小说中作为象征手法微小部分的呈现远远比我用一篇散文的容量专门著述要无关紧要。
当然,我写《看麦娘》也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坦白说,我并不具备知识普及的能力和野心,但为还事物本来面目,冒点风险也值得。我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就是过继给李姓人家的孩子,他需要找个人倾诉自己原本姓王。即便我一步步求证最终未能还看麦娘本来面目,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使更多喜爱植物的人来共同努力说出真相。
我曾写过一句诗:“我有五月麦芒为竖琴,我有十月稻穗为琵琶。”这首先涉及到中国南方稻麦轮作一年两熟的农业耕作系统,它受地理位置、热量条件及生产条件的制约:长江流域各省及华南一带栽种冬小麦,秋季10至11月播种,翌年5至6月成熟;栽种水稻则是6至7月育苗、插秧,9至10月收割。与水稻和麦子伴生的禾本科杂草主要有:野燕麦、雀麦、看麦娘、稗草、早熟禾、狗尾巴草等。这样一个条目,已经很明显地把看麦娘和狗尾巴草作为两种不同植物区分开来,而且一个“杂草”身份一下子把看麦娘所具有的表意的温情打消得荡然无存。
顾景星的《野菜赞》分两个部分记录过一种叫“看麦娘”的植物。第一部分“高下二种,在麦田中,稂稗类也。一名草子,似燕麦,子如雕胡。尔雅谓之皇守田稂,亦名守田。俗名宿田翁。”第二部分:“有看麦娘,翘生陇上。众麦低头,此草■望。布谷飞鸣,妇姑凄怆。谁当获者,腰镰而往。”一会宿田翁,一会看麦娘,把这植物说得不男不女的。燕麦的样子我见过,“子如雕胡”据查《本草纲目·谷二·菰米》[集解]引苏颂曰:“菰生水中,叶如蒲苇,其苗如茎梗者,谓之菰蒋草,至秋结实,乃■胡米也”,菰米与燕麦的外形也颇像。我的脑海中大致有了看麦娘的肖像。再循蛛丝马迹。《尔雅·释草》说:稂,童粱。对《诗经》里草木鸟兽虫鱼的考证做了开创性工作的陆玑在《草木疏》中也有:“禾秀为穗而不成,■嶷然,谓之童粱。今人谓之宿田翁,或谓之守田也。”由此我基本认定看麦娘就是一种叫“稂”的植物。然而在各类图考中惟独没有“稂”的对应图案,那么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呢?《诗经·小雅·大田》有“既方既皂,既坚既好,不稂不莠”,描写了禾苗地里没有什么杂草,庄稼从谷粒初生、灌浆饱满、表皮坚硬到完全成熟的一个过程。我翻阅众多资料,大多解释为稂是狼尾草,莠是狗尾草。狗尾草的穗子粗短刚毛也短,从淡绿色变为黄褐色;狼尾草的穗子细长刚毛也长,从淡绿色变为紫色。而且狼尾草有许多奇怪的别名:稂、童粱、守田、宿田翁、狼茅、小芒草……甚至也有狗尾草、大狗尾草、黑狗尾草、狗尾巴草的叫法,狼尾草的生长习性和狗尾草差不多,也多长于田埂、沟渠和河坡,在我家乡喊它芒草。难道看麦娘是狼尾草?
有一个值得推敲的地方,《诗经·小雅·大田》的禾苗地种植什么庄稼时“不稂不莠”呢?禾在古代指粟,周代种植的应该是一种粟的粮食作物。中国北方称粟为谷子,中国南方则称稻为谷子,那么稂和莠这两种所谓的“恶草”是与谷子地相关的。且谷子地里的杂草样子长得非常像谷子,比如稗子和水稻,麦子地的杂草样子应该长得像麦子。谷子地的“稂”与顾景星所记录的“在麦田中”的稂稗类杂草“看麦娘”是否产生了冲突?顾景星写《野菜赞》的背景是在老家湖北蕲州,他结茅为庐采野菜充饥的地方也是池莉所在的湖北。我不知道顾景星在“众麦低头,布谷飞鸣”的时节看到的“看麦娘”究竟是怎样昂望的一种草,说不定在湖北看麦娘真有狗尾巴草的叫法,但放在更为广阔的地域来看,狗尾巴草是鲜有看麦娘的叫法的,基于此我还是想给真正的看麦娘一个公道。因为即便是狼尾草在麦田里也是少见,我坚信看麦娘就是我儿时所见的“细圆柱形灰绿色的穗、花药橙黄色”的植物。
池莉在《看麦娘》里说,汉字就是这样,只这三个字,就能令你爱上中文。我深有感触,坦白说我倒是被这三个字幸福地击倒后,才竭力去寻找“击倒”我的那种植物的容貌的。我找到了现代植物学中“看麦娘”的一张图片,发现在故乡的田野间遍地皆是,我曾拔着玩过,割了喂过羊,正是我所说的“细圆柱形灰绿色的穗、花药橙黄色”。请记下看麦娘的生长习性:8月底至9月上旬出苗,10至11月进入生长高峰期,翌年4月上旬抽穗开花,5月上旬种子成熟,经2至3个月休眠即可发芽。这样的生长周期完全和麦子吻合。
田野一步即故园,一步之内的芳草犹如一个同宗的家族,禾本科的植物聚在一起正如我和堂兄堂姐表兄表妹之间的关系,它们寓意繁茂,我们寓意繁衍。看麦娘的样子和狗尾巴草是两码事,你说看麦娘会是狗尾巴草吗?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问麦地田里“细圆柱形灰绿色的穗、花药橙黄色”的草叫什么名字?母亲说:“叫看麦娘。”为了双重确认,我再问仍在麦田守望的祖母,她说:“叫看麦娘。”我可以安心被这三个字幸福地击倒了。
香椿头
作为苏童“枫杨树乡”之外的另一南方地理标志“香椿树街”,也是我所向往去走一走的地方,一个自小就在我耳边萦绕的植物名词“香椿头”,至今还未见过它的出处。在一条街的两旁,栽植着与南京的梧桐或北方的白杨显然不同的香椿,想来是另一番蔚然壮观的景象。加上一个香字的衬托,仿佛整个春天你都在扑鼻的风里游过那条虚构又真实的街道。况且,我对中国汉字的独一结构性向来敬畏,而这“椿”字赋予着某一树种与春天的唯一关联,不免令我心生好奇。
三月,在溧阳的苏园喝早茶时有好几次碰到那个年近八旬的老太太,苍苍白发,拄一拐杖,那拐杖做得较随意,几乎看不见手工制作的痕迹,大概是随地取材的那种,一根比较符合拐杖结构要素的枯树干,与她饱经沧桑的年龄正相匹配。那老太因身体过于佝偻就显得更矮小了,她右手拄拐左臂弯挽一破旧的竹篾篮子,篮子里盛满两样东西:十几扎整齐干净的紫红色香椿嫩芽,下面数十只白晃晃的小个头鸡蛋。苏园主人霍益民先生总是以香椿两块一扎、鸡蛋一块一枚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照单全收,然后嘱咐老太太路上小心并送至门口,看着裹小脚的老太太颠簸着摇晃远去。其间的美丽情感无须多问,这乡间采摘来的香椿芽倒映着她垂暮之年脸上为数不多的春天,如我们接下来继续饮茶般细品这早晨的个中滋味。
香椿头,谷雨前后采摘,南方与茶树一起用嫩叶向早春致意的美好植物,可炒笋、炒蛋、拌豆腐、煎香椿饼,是政治失意却能体恤百姓疾苦的朱■(1361—1425年,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明成祖朱棣的胞弟)在《救荒本草》里记录的值得信赖的414种野生食用植物之一。李渔有个精妙的感受表达,他说他对待葱、蒜、韭是有区别的,蒜是永远不吃,葱虽然不吃,但允许用来做调料,韭菜则是不吃老的而吃嫩的,这点和我差不多。接下来他有个类比,使人唇齿芳香的是香椿芽,使人唇齿和肠胃都带有难闻气味的是葱蒜韭,明知香椿芽香吃的人却少,明知葱、蒜、韭臭喜欢吃的人却多,原因是香椿芽的味道虽香却比较淡,不像葱、蒜、韭的味道那么浓。味道浓就被人喜爱,甘愿忍受难闻的气味;味道淡就被人们忽视,就算香气能引起注意,也不被接受。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再一想也毫无道理,不过是南人和北人的饮食习惯而已。我一北方的朋友嗜好蒜子,常剥几颗放兜里,时不时地往嘴里塞一颗,脆生生的声音听起来就不舒服,毫不夸张地说甚至有点发毛。但他同样喜欢点一道“香椿煎蛋”。香椿头我也吃过,平时想不起来,偶尔在菜桌上遇着了也尝几筷,不是特别喜欢的那种。味道略带点苦,然余香绕舌,那性格也和茶叶惊人地相似。生命的蕴藏有时候就是苦与香的互融,看你如何来品。
与楝科香椿对应的苦木科臭椿,形态相像,据说可以这样来区别:香椿叶根部是浅绿色,叶梢部是黄褐色,而臭椿叶根部是深绿色,叶梢部是灰绿色。另外,香椿叶的边缘有稀疏锯齿,而臭椿叶则没有。还有个特点是香椿每一枝叶片数目总是双数,而臭椿每一枝叶片数目则是单数,它总是在几对之外,上端再多长出一片来。如果从气味上鉴别两者,可以拿一片叶子用手一搓,用鼻子闻闻,那味道就与它们本身的命名相对应。我倒有个想法,这叶子是单数的臭椿就不能摘其嫩叶炒上一盘?叶子气味是臭了点,但不碍于尝试。比如好好的豆腐制作成霉绿、瞄一眼就恶心的臭豆腐,油炸、蒸煮后吃起来却特别香。中药文献记载,臭椿供煎汤外洗使用,吃了臭椿叶虽无大碍,但最好还是不吃为好。既无大碍,那么来年春天,我不妨先来一试。
常州有一桥叫椿庭桥,位于和平北路与新丰街的交接处。原以为桥附近多多少少种植这香椿才有了这么个由来,实为民国22年邑人实业家顾椿庭捐资兴建,民国23年建竣,以椿庭命名。椿庭桥曾在文革时期改称为全国一色的名如“红旗”、“解放”之类的东风桥,1981年恢复原名。椿与椿庭皆可指父亲,这顾姓实业家可能是宗氏家谱上的“椿”字辈或“庭”字辈,这两个字又碰巧遇上了,弄得他父亲喊他名字时就像在口口声声地喊父亲,颇有些好玩。唐代牟融有诗“知君此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