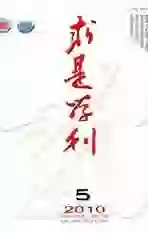明代学者论历史撰述中的“心术”与“公议”
2011-01-01毛春伟
求是学刊 2011年5期
摘要:史家品德和史书公正性问题,为历代史家所重视。明代学者从对作史之难的探讨出发,不仅对史家“心术”予以特别的关注,并使之逐步成为史学批评的一个术语,同时,他们还认为史书有“明公议”的社会功用,而史家有“持公议”的社会责任。明代学者的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前人对史学的认识,同时亦引起后人对史学社会价值的深入思考。
关键词:明代学者;历史撰述;“心术”;“公议”
作者简介:毛春伟(1982—),男,云南宾川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0)05-0132-07 收稿日期:2010-06-15
一、明人论作史之难:问题的提出
对历史撰述之难的探讨,往往能促进人们对历史撰述的各方面条件的思考。唐代史家刘知幾提出的“史才三长”论,即是对这一史学难题的一种回答。明代学人对作史之难有一些归纳,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明代学者中对这一问题论述较早的是生活在明代中前期的叶盛(公元1420—1474年)。叶盛历仕正统至成化四朝,久居言官之职而勇于进谏,史称“有古大臣风”。他曾指出当时的史官对一些有价值的史事、文献未予以记录和整理,批评他们没有尽到责任。正是看到史官有失职之处,他在留心军政的同时也很重视撰述,其笔记《水东日记》记录了明代前期的典故且考证翔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历史撰述之难,他的看法是:
信史,古今所称。欧阳予曰:“有欲书而不得书,有欲书而不敢书。”则遗漏,一也;讳,二也。曾南丰曰:“公以龃龉终,公行不得在史氏记,藉令记之,当时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欤?”则拘于著令,三也:偏私不公,四也。朱子曰:“一时馆职,岂尽刘向、扬雄之伦。”则史官职才不足,五也。斯五者,盖当尝有之,固不敢谓无。于是乎,信史诚有未足信者矣。以上提到的这五个方面的原因,其论点分别出自欧阳修、曾巩和朱熹的论述,可见叶盛此论受宋人影响之大。叶盛所总结的遗漏、避讳、拘于著令、偏私不公和史官职才不足五个方面,似可概括为“五难”。除这五个方面以外,明代有的学者还尝试从修史的具体操作上来探讨作史之难的原因。
明万历年间,曾有一次较大规模的修史活动,取得一些成绩,但随着主要负责人陈于陛的去世而“史亦竞罢”,最终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时任史官的陈懿典亲身经历了这次未获成功的官修活动,因而对修史之难特别是信史之难有较深的感触。他说道:
居草泽所闻,朝家固实一凭邸抄,而省直流传详略已异,其它遗散,益复无纪,苟纲罗或阙,即荟萃不光,其一难也。取材欲博而义例欲简,多弃则椴柟亦断沟中。赅存则瓦砾何当席上,三长所重,识莫先焉,其难二也。朝廷是非得失之林,甲可乙否,朝佞暮贤,自匪持平所衷,何繇顜若画一,其难三也。由此可见,陈懿典认为修史的三个难处在于:一是史料的驳杂且详略不一;二是若史识不足则在撰述史书时对史料的取舍和编排无从下手;三是由于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史家对时人的褒贬难以把握。在第三点上,陈懿典还特别指出对于本朝历史的撰述史家即便能够“勇于笔而健于舌”,也难以“皆直达无婉转”。因而史家只有具备“持平所衷”的品质,才能撰写出令人信服的史书。
无论“偏私不公”,还是“持平所衷”,都包含着史家与撰述历史之间的某种关系,而这常常是作史中的困难之处。从叶盛、陈懿典二人的论述,我们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看到其中包含的互相有关联的问题:一是历史撰述者能否做到客观无私,这是史家修养中的品德问题;二是史书记载能否公正平允,这是史书记载的公正性问题。明代学人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有一些认识,以下分别加以论述。
二、论史家“心术”:对史家品德与历史撰述的认识
上文叶盛、陈懿典二人虽然将史家品德与作史之难联系起来,不过他们的归纳都比较具体。明代学者文徵明(公元1470—1559年)的论述。则把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嘉靖己亥,吴郡重刊《唐书》成”,而此次重刻的《唐书》即是《旧唐书》,刊刻者请文徵明为之作叙。在明代史学史上,这篇叙文较早地对两《唐书》有所论述,其对二者的比较及评价颇有可观之处。文徵明认为大概是因为“五代抢攘,文气卑弱”,因而《旧唐书》显得有些“纪次无法,详略失中,不足传远”;然而《新唐书》也常受到后人的批评,并不能取代《旧唐书》。两《唐书》虽各有佳处,但其不足也比较明显,由此文徵明感到了撰史之难。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他说:
甚矣,作史之难也!心术有邪正,词理有工拙,识见有浅深,而史随以异。要在传信传著,不失其实而已。这一段文字把“作史之难”的原因分为三点,一是“心术”,二是“词理”,三是“识见”。在这三点里,文徵明把“心术”的邪正作为历史撰述之难的首要因素提了出来,并把史家的品德明确为“心术”。循着这一论述我们发现,在明代,史家“心术”这一观念并非只有文徵明提到,而可以说是明人的一种共识。
谈到史家的“心术”,我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清代学者章学诚的论断。他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章学诚对“著书者之心术”的解释是:“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章学诚是在他的史学理论体系中来谈史家“心术”的,其认识也较前代史家深刻得多。不过,将历史撰述与“心术”联系在一起来论述的,在章学诚和文徵明以前已经有人说到了。就目前来看,对此问题谈论较早且有一定影响的学者。当属元代史家揭傒斯。据《元史》记载:
诏修辽、金、宋三史,侯斯与为总裁官,丞相问:“修史以何为本?”曰:“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文中所说的“丞相”,即是元史的监修脱脱。将这番对话放在元修宋、辽、金三史的背景下来考察,是值得注意的。揭侯斯认为史官需要有三方面的条件,即有学问、会写文章和心术正,而其中心术之正又是最重要的。他明确地把史家品德与历史撰述联系起来,并且用“心术”二字加以概括,这在中国古代关于史家修养认识的发展中,特别是在史家品德的认识方面是一种进步。
揭侯斯之后,明代学者继续对史家“心术”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杨士奇(公元1366—1444年)早年“以史才荐”,其后多年担任内阁辅臣,参与主持、修纂了成祖、仁宗和宣宗三部实录。据曾与杨士奇同修《宣宗实录》的王直(公元1379—1462年)的记载:“三朝史事皆公(指杨士奇——引者注)总裁,是是非非悉征诸实。每与同列曰:‘天下万世之事,当以天下万世之心处之,苟出于私意,无论厚薄,皆当获罪神明。’”杨士奇的上述言论是否直接受揭侯斯的影响,我们还看不出来,但是他对史家之“心”的重视,却和揭傒斯有相似之处。
叶盛对揭、杨二人的观点很赞赏,他说:“揭文安公尝论史官不当专尚史才,必以心术为本。而杨文贞公亦云:‘天下万世之事,当以天下万世之心处之,苟出于私意,无论厚薄,皆当获罪神明。’然则修史者,又必有揭、杨之心之才而后可。”可见,叶盛认为后世史家要“以心术为本”,具备“揭、杨之心”,才能撰写出可信的史书来。
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论及史官沿革时,谈到史官之选若非“如刘知畿所谓兼才、学、识三者之长,曾巩所谓明足以周万事之理,道足以适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这样的人才,则“不足以称是任也”。然而,在丘溶看来,刘知幾与曾巩所论的这些史家修养并不是最根本的。他说:“若推其本,必得如元揭篌斯所谓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正者,然后用之。则文质相称、本末兼该,而足以为一代之良史矣。”丘溶眼中的“良史”,是以“心术”为本,同时具备学问和文章等多条件的“文质相称、本末兼该”的人才。丘溶的这一论断被史家陆深称为当时的“名言”。
稍晚于陆深的杨慎(公元1488—1559年)是明代学者中较为博学的一位,他在考史与论史方面有一定的成就。他在考察前代史书和当朝史书的不实之处后,总结说“至于国史亦难信,则在秉笔者之邪正也”,认为史家心术的正邪不仅直接关系到史书的可信与否,而且影响到史书社会功能的发挥,因而史家必须抱着对社会历史负责的态度,公正地撰述历史。
胡应麟(公元1551—1602年)对史家“心术”的论述,则在一定程度上对前人有所补充。他从刘知幾所论“史才三长”出发,强调史家还应该具备“公心”和“直笔”,并归之为“二善”。不过胡应麟的论述偏颇之处不少,对他的言论需要有所辨析。他说:
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焉。董狐、南史,制作亡征,维公与直,庶几尽矣。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闻。左、马恢恢,差无异说;班书、陈志,金粟交关;沈传、裴略,家门互易。史乎,史乎!
胡应麟把“公心”和“直笔”这“二善”,置于和“史才三长”同等的地位来看待,这在史学批评上有其可取之处。大致可以这样说,胡应麟将史家“心术”阐释为“公心”和“直书”。不过,他的这番议论可议之处甚多。一是“秦汉而下,三长不乏”。则把刘知幾提出的“史才三长”看得太简单了,与其前人所论大相径庭。二是所说“班书、陈志,金粟交关;沈传、裴略,家门互易”,亦是轻率之言,以传闻为事实,岂可以此立论。此番言论。正可表明胡应麟所归结的“公心”和“直书”的史家品格,并不容易做到。说之易而行之难,胡应麟的上述议论,足以为戒。
明代学者对史家“心术”的探讨,往往还和当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环境有关系。明代中后期的内阁辅臣多出自翰林院,而当时翰林与史馆合而为一,因此一些史官有机会进入内阁。叶向高(公元1559—1627年)在万历后期至天启间就曾任内阁辅臣,并主持修纂《光宗实录》,在史学方面也有一些见解。在为《皇明史概》作序时论及史家的“心术”问题,他说道:
国朝史官,即备辅臣之选,一主直笔,一职平章。盖皆从神明上发出,相互运用,而史为之先。正欲其端心术,辨邪正,贯通今古,他日运之掌上。从中不难看出,叶向高非常强调史官心术的重要性。其原因大约有两点:一是史官心术的端正与否,直接关系到史书的可信与否;二是联系到明代内阁制度的具体状况,即史官有可能成为辅臣,那么史官能否端正心术、辨别邪正已不仅限于修史活动本身,它还可能关系到朝中臣僚的心术。因而在叶向高看来,史官的心术问题不仅是学术问题,也是现实的政治生活问题。从这一点上看,叶向高对史官心术重要性的认识较之时人更为突出。同时他还注意到史馆与内阁的特殊关系所带来的问题,这就是“近弛骛止为枚卜之阶,殊失其质”。即把史官仅仅作为进身之阶,这样就违背了当初设立这一制度的初衷。明代史馆与内阁之关系对史馆修史的影响,是明代史学具有时代特点的问题之一。由于史馆职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内阁的储备人才,史官的职责和权力、地位,较之前代有了变化。
“心术”之端正与否,实际上还反映了史家在撰述历史时是否具有敢于直书的勇气。明代藏书家、学者谢肇涮(公元1567—1624年)就特别强调史家的这种品格,他说:“董狐之笔,白刃临之而不变;孙盛《阳秋》,权凶怒之而不改;吴兢之书,宰相祈之而不得;陈桎之纪事,雷电震其几而不动容,如是可以言史矣。”他称赞董狐、孙盛、吴兢、陈桎等史家不畏强权、不谀胄贵、勇于直书的品格。他还推崇司马迁,说道:“太史公与张汤、公孙弘等皆同时人,而直书美恶,不少贬讳;传司马季主而抑贾谊、宋忠,至无所容;《封禅书》备言武帝迷惑之状,如此等书,令人非惟不能作,亦不敢作也。”司马迁对同时代上至君主下至大臣都能善恶并书。谢肇滞认为这并不是所有具备史才的史家都敢于这样做的,这需要有秉笔直书的胆识。在谢肇淛看来,史家“心术”与史家胆识是分不开的。
无论是“心术有邪正”、“秉笔者之邪正”还是“端心术,辨邪正”,这些论述都是对史家品德或者说主观因素的一些认识。其内涵大约有三层:一是史家“心术”是存在的。即史家自身的主观意愿对修史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史家在撰述和评价历史的时候难以或者说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客观和公正;二是史家“心术”是有“正邪”之分的,即主观意愿有好有坏,史家应尽可能地以公正的态度来对待和撰述史书,力求发挥“心术”中“正”的一面;三是史家应以“心术”为本,也就是说不论史家的自身修养,还是在史官选择上,都应以“心术”为本,把道德品质作为评价史家的第一要素。此外,由于明代内阁制度的特点,史官有机会进入到内阁,从而可能成为在政治上有一定影响的朝臣。一位重视“端心术,辨邪正”的史官。在进入政治权力中心集团后,对政治生活多少是会产生积极影响的。
三、论“公议”:史书的社会功用与史家的社会责任
与史家品德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便是史书的公正性问题。在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上,我们可以看到明代学者的论述中常常有“公议”这一词语。“公议”一词战国以来就见于书籍,后世也并不少见,但明人将其与史学紧密联系起来,丰富了它的内涵,并且成为他们史学评论的一个重要术语。
明朝初年,在政权并未稳固之时,官修《元史》完成了。这部《元史》虽因成书仓促,后人不断予以批评和修正,但是它在及时保存和整理元代史料方面是难以代替的。宋濂(公元1310—1381年)所撰的《进元史表》,不仅集中反映出《元史》编纂的指导思想,从中我们亦不难看到明初君臣对历史评论公正性的重视。
钦惟皇帝陛下奉天承运,济世安民。建万世之丕图,绍百王之正统。大明出而爝火息,率土生辉。迅雷鸣而众响销。鸿音斯播。栽念盛衰之故,乃推忠厚之仁。佥言实既亡而名亦随亡,独谓国可灭而史不当灭。特诏遗逸之士,欲求论议之公。文辞勿致于艰深,事迹务令于明白。苟善恶了然在目,庶劝惩有益于人。此皆天语之丁宁,足见圣心之广大。从“欲求论议之公”,可以看出朱元璋对《元史》撰述的要求,力求对历史予以公正的评价。同时,这也可以看作是以宋濂为代表的修纂史官对历史撰述的自觉认识。
与宋濂齐名的学者王祎(公元1322—1373年),其学问在明初也有一定影响。明太祖朱元璋曾称赞其才思卓越,说道:“江南有二儒,卿与宋濂耳。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洪武初年,王祎与宋濂同为总裁修纂《元史》,史称:“祎史事擅长,裁烦剔秽,力任笔削。书成,擢翰林待制,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他在史学上所取得的成绩,已有学者作了研究。王神在《唐起居郎箴并序》一文中谈到起居郎作为记录君主言行之官的重要性,还由此引发了其对史书公正性的议论,他说:
起居郎,古左史也。人君动则左史书之,是非之权衡,公议之所系也。禹不能褒鲧,管、蔡不能贬周公,赵盾不能改董狐之书,崔氏不能夺南史之简。公是公非。记善恶以志鉴诫,自非擅良史之才者,其孰能明公议以取信于万世乎?故人极天下之尊,而公议所以摄人主;公议极天下之正,而史官又所以持公议者。”这段话指出了史书有权衡是非的作用。并且关系到“公议”。史书若能持“公议”,即“极天下之正”,则君主也须恪守此“公议”。史官一旦成为持公议者,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君主的言行。这番言论表明了王祎对史学功用的深刻认识,同时也反映了明初史家对史学功用的信心。他进而认为史书要做到“明公议”,则必须先做到“公是公非,记善恶以志鉴诫”,而只有具备良史之才者才能达到这一要求。他着重强调“取信于万世”,即史书的可信与否并不仅仅取决于当时人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后人的评判。在他看来,史书只有可信,才能肩负起“明公议”的责任。后来,丘潜在著述中也引用并赞成了王祎的论断。
嘉靖时期,史官董玘(公元1487—1546年)在《校勘实录疏》中谏言皇帝下旨校勘《孝宗实录》,这份奏疏首先强调了实录可信的重要性,说道:“臣惟今日之实录,即后日之史书,所以传信于天下万世者也。此岂容以一人之私意,参乎其间哉!”董玘认为实录作为史书是要传诸后世的。因而不能参以个人的私意。他追述了明武宗即位之初修纂《孝宗实录》的情况,那时由于刘瑾之乱,修史活动受到了干扰,实录中多有不实之处:“于时大学士焦芳依附逆瑾,变乱国是,报复恩怨。既已毒流天下矣,而犹未足也,又肆其不逞之心于亡者,欲遂以欺乎后世。其于叙传,即意所比,必曲为拚互;即夙所嫉,辄过为丑诋。又时自称述,甚至矫诬敬皇而不顾。”因而董玘谏言借助修纂《武宗实录》的机会,来校勘《孝宗实录》。他说:“兹者恭遇皇上人继大统,敕修《武宗毅皇帝实录》。内阁所藏《孝宗皇帝实录》副本,例发在馆。誊写人员及合用纸扎之类,不烦别具,欲加删正,此其时矣。特旨将内府所藏《孝宗实录》正本,一并发出,仍敕总裁大学士等,及比时曾与纂修备谙本末者数人,逐一重为校勘。”这样可以使弘治朝“凡十八年之间,诏令之因革,治体之宽严,人才之进退,政事之得失,已据实者,无事纷更”。这里他还特别强调要区别对待《孝宗实录》中的记录,他说:“至若出焦芳一人之私者,悉改正之。其或虽出于芳,而颇得实状者,亦自不以人废。”
董玘认为校勘《孝宗实录》“为费不多,事亦易集”,对实录的校勘,其实是对所载史事的辨证,这可以“使敬皇知人之哲,无为所诬;诸臣难明之迹,得以自雪”,由此“而人皆知公是公非所在,不容少私”,以正视听。他还说道:“孝宗圣主时多良臣,而芳意诬妄。惜乎,至今未之改也。如芳者,纵或肆行于一时,而竟亦莫掩于身后。庶乎孝宗一代之书,藏之中秘,而传于无穷者,必可据以为信矣。不然,万世之下,安知此为芳之私笔也哉!”董玘认为实录要摒除私人之意,方能“据以为信”,传之后世。从他所说的“公是公非”来看,其与“公议”内涵相同。
继之,史家余继登(公元1544—1600年)在向万历皇帝所进的《修史疏》中同样强调撰述史书不得偏私,他说:“臣惟代之有史,捃摭故实。备册书明示将来,用垂法戒。非一人之书,而天下之公也;非一时之书,而万世之公也。”余继登认为史书的作用是“明示将来”、“用垂法戒”,因而是“天下之公”、“万世之公”,非一人一时之书。而如何才能做到“公”,他回答说:“是非虚实之间,子不得私诸其父,臣不得私诸其君,而后可以言公。”他认为在史书撰写上,能够子不私其父、臣不私其君,按照实际情况记载其是非曲直,即做到“信”,之后才可以言“公”。余继登在这篇奏疏中表达了他的修史态度,认为应该为建文帝修实录,因为“且事须有实,直道难枉,今野史所记已多失真,若不及今明为之纪,令后世以久愤之心信传疑之语,则史臣之失职不足惜,如圣祖何?”他还认为不应为“恭穆献皇帝”(嘉靖皇帝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修实录,说道:“献皇帝事,只宜附见于世宗肃皇帝纪之前;或别起一例。亦宜与圣帝纪有别,庶使名实不紊,体裁不淆。不然以献皇帝之子孙臣庶,欲纪则纪矣,如天下后世之公议何。”这段话表明余继登认为兴献王的事迹要么附在嘉靖皇帝事迹之前,要么另起一例,但是不能与皇帝实录相同,否则会造成混乱,是置“天下后世之公议”于不顾。
从上文所述的几位明代学者对“公议”与历史撰述的论述来看,其历史意义大致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追求历史撰述真实性的角度说来,明代学人对历史撰述的认识在某些方面较前人有所突破。刘知畿在《史通·曲笔》中有一段对曲笔的认识,他说:“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已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刘知幾认为史书有曲笔不足为奇,对君亲的隐讳是出于名教的需要,而且是合理的。而我们在前面所看到明人的评论,如王祚的“明公议以取信于万世”,董圮说史书是“公是公非所在,不容少私”,余继登说史书“非一人之书,而天下之公也;非一时之书,而万世之公也”等,则批评偏私的行为,强调史书的公正性。他们在这一点的认识上不再囿于名教,较刘知幾有所进步。他们强调了史书具有“公议”的作用,代表着“天下人之公”和“万世之公”,不再是一人一时之书。当然,这并不是说出自他们之手的史书,都能做到完全的公正,但是具有这样的认识总是有积极意义的。清人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序》中指出:“且夫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齿奇)龁前人,实以开导后学。”这一中和平允的史学批评旨趣,常为后人所称道。若从学术观点的演进来看,钱大新昕之论可以说正是对明人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第二,明代学者认为“公议”具有一种权力,这一权力可以对政治权力进行某种平衡,因而史书具有“明公议”的社会功用,而史家具有“持公议”的社会责任。“公议”赋予史家不同于直接政治权力的另外一种权力,这一权力具有评价人物、权衡世事,甚至限制皇权的作用。在这些学者看来,由于史书能够“明公议”,因而可以产生不同程度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功用。而对这种社会功用的实现,正是史家的社会责任。由于史书的社会功用和对政治的权衡能力并不具有制度上的规定性,因而往往受皇权或其他政治权力的影响,从而令这种“明公议”的功用往往成为了一种美好而落空的愿望。在这时候,史家的努力就非常重要。史家肩负起“持公议”的社会责任,则史书的这一社会功能就有可能实现。历史上,一些“治世”的出现,除了君主和政治家的推动之外,史学家对自身社会责任的履行,应该说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这一方面来说,明代学者对“公议”与历史撰述的见解,对现实社会也有一些积极意义。
四、结语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到,明代学者从探讨作史之难出发,重视史家的品德,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史家“心术”。丰富其在史学上的内涵;同时还强调史学之“公议”。认为史书有“明公议”的社会功用,史家有“持公议”的社会责任。这些论述的学术意义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把“心术”与“公议”运用至史学批评中,增加了史学批评的概念,丰富了史学批评的内容。史家“心术”的邪正,直接影响到史书的可信程度,而史书的可信度又是史书为社会所接受的前提。只有“心术”正的史家才能撰写出可信的史书,只有可信度高的史书才能为人们所承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心术”是史家立足的根本,明代学者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加以反复讨论,成为了他们史学评论中的一个常用的概念。从学术发展上来说,章学诚提出的“史德”说,正是对明人史家“心术”说的继承和发扬。此外,明代学者认为史书有承载“公议”的功能,“公议”既包含了当时众人的议论,也包含后人的议论。在史学批评中引入“公议”的概念,一方面凸显了史学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引起了人们对史学社会价值的思考。“公议”成为了中国古代学者对史学社会作用认识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后的清代史家也常用“公议”来进行相关的史学评论。
其次,加深了对史学功用的认识。明人对“心术”与“公议”的不断论述,反映出他们对史学功用的重视。在明人看来,“公议”可以被看做一种权力,它能够对社会产生某种约束作用。他们认为史书具有“明公议”的功能,也就是说史书对于包括帝王在内的所有人都有某种限制,尽管这种限制并不是强制的。这是因为事件、人物一旦作为史书记录下来,则不仅对当代有影响,还影响到后世。正因如此,人们不得不考虑到史书的这种软性的权力,考虑自己需不需要对历史负责。史书的这种约束作用,与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等强烈的历史自觉意识是分不开的。明代学者还强调,“明公议”这一软性的约束力是掌握在史学家手中的。他们认为史家具有“持公议”的社会责任,这一方面道出了史家要勇于肩负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史家拥有“持公议”的权力。而无论是史书的“明公议”,还是史家的“持公议”,其前提都是史书的可信,史书的可信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史家的“心术”的公正。因而明人所论的“心术”与“公议”在实现史书功用上是统一的,他们把这二者结合起来,使得人们对史书功用的认识加深了一步。
要之,明人对历史撰述中的“心术”与“公议”的论述,即对两个概念的阐释和运用,反映出他们对史家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史书所具有的社会功用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这在中国史学批评的发展上无疑是具有进步性的。
参考文献
[1]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叶盛,水东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沈国元,两朝从信录[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
[4]文徵明,文徵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章学诚,文史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7]黄训,名臣经济录[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8]丘潜,大学衍义补[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9]陆深,俨山外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0]杨慎,升庵全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1]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12]朱国桢,皇明史概[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
[13]谢肇淛,五杂俎[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14]王祎,王忠文公集[M],丛书集成初编本
[15]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6]刘知幾,史通[M],北京:中华书局,2009[责任编辑 王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