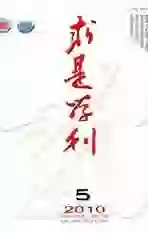论意象与超象
2011-01-01于茀
求是学刊 2011年5期
摘要:文学的意象是作家传达审美经验的工具,作家要通过具体的意象而达到一般和普遍,通过有限而达到无限,通过物质而达到精神。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文学又是超象的。如果说意象的具体是个别的具体,那么,超象的具体就是由个别上升为一般的具体。如果说意象的可感还主要是形貌的可感,那么,超象的可感就是形貌以上的精神内容的可感。我们可以把“超象”当做一种“象”,一种更高的象,表面看来它是无形的,但它是具体存在的,所谓“大象无形”。
关键词:文学;审美经验;意象;超象
作者简介:于茀(1964—),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文学理论和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0)05-0119-05 收稿日期:2010-03-11
文学的传达方式,一般认为是意象的。但是,实际上,文学作为人类审美经验的一种传达方式,它既是意象的,也是超象的。本文将对文学的意象与超象及相关问题作出思考。以期对理解文学的核心问题有所裨益。
一
关于意象,有一个比较通行的解释:意象是主观的“意”与客观的“象”的结合。这在一般原则上是正确的,至少说明了文学意象不是纯粹客观或主观的东西,不是现实的机械反映,也不是作家的呓语。但是,这种解释也有一个潜在的危险,那就是很容易使一些人产生错觉,认为文学创作就是把主观的“意”用客观的“象”表达出来。事实上,意象作为一种复杂的审美经验,作这样的分割剖析,是不妥当的。文学作品,无论诗歌还是小说都是由一些复杂的审美经验构成的。
在意象所提示出的经验世界里,包含了什么呢?清代文论家叶燮指出:
子但知可言可执之理之为理。而抑知名言所绝之理之为至理乎?子但知有是事之为事,而抑知无是事之为凡事之所出乎?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叶燮《原诗》)每个人都能讲述的事,都能说明的道理,就不用文学家来讲述和说明了,文学家所要讲述的所要说明的是一般的人不能讲述的不能说明的事与理,这样的事与理,就在意象所提示的复杂的经验世界中。
与科学求证所得概念命题相比。经验世界常常被看成一个变动不拘、不可信赖的世界,充其量是科学、理性、逻辑认识的低级阶段。但是,经验世界中全部有益的东西都能上升为理性的概念命题而被传达出来吗?中国人早就认识到,逻辑概念的语言不能“尽意”,所谓“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国古人更知道“立象以尽意”,进而解决这一困难。
在文学意象中,“名言所绝之理”,得到呈现,可谓伊挚可以言鼎,轮扁能够语斤。温庭筠有诗云:“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商山早行》)在这首诗中,听觉经验与视觉经验的直接连接,看似有悖常理,但这却极为准确地呈现出诗人的整体经验,有几分空旷,又有几分孤寂。
文学作品中着意强为的名言之理,往往会破坏审美经验,我们可以把陶渊明的两首诗做一比较: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陶渊明《饮酒》之五)
山涧清且浅,可以濯我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陶渊明《归园田居》之五)其实,第一首的前四句和后两句都算不得精彩,就诗的意象和韵味来看,第二首要胜过第一首。
有人在总结意象特征时,常常讲到意象的多义性。的确,意象所提示出的意义是丰富的,这种丰富往往是概念命题所不及的。多义不是模棱两可。不是模糊不清。而是审美经验的完整性。在文学作品中,意象是一个浑然整体,任何分割式的分析。都是不知何谓审美经验的做法。严沧浪说:“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严羽《沧浪诗话》)后来谢榛称赞说:“沧浪知诗矣。”(谢榛《四溟诗话》)何止是汉魏古诗难以句摘,其实,所有的诗都是难以句摘的,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难以机械地分割分析的。即使以句摘,也不能以“象”摘,我们都知道王维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塞上》),其中,任何一个物象分割出来,都是没有什么意蕴的。可是,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时,意蕴就出现了。在整体意象中,传达的是人的审美经验的丰富性和混融性,任何细微的经验片断都不会漏掉,相反,概念语言和命题语言却必须过滤掉这些细微的经验片断,因此,意象所提示出的经验就不仅是完整的,而且是丰富的了。多义性的说法,会使人们觉得文学传达的东西是模糊的,相比之下,丰富性更能说明审美经验的根本特征。从根本上讲,作家创作文学作品就是要传达这种概念语言逻辑推理无能为力的复杂的精神世界的经验,而不是制作谜语。多义性只不过是对丰富性的一个不十分准确的概括,当然,有的作家,利用语言的象征,写出了令人费解甚至可以多解的作品,但这不应被看做文学的根本目的。由于人们片面地把意象所提示的审美经验的丰富性理解为多义性,所以常常喜欢到意象密集的唐诗中去寻找例子。其实,所有成功的伟大的作品,都很好地传达了精神经验的丰富和完整。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是《诗经·秦风·蒹葭》的一节,苍苍芦苇,清露凝霜,美丽伊人,却在江的那一方。诗人对美丽伊人的无限思念,通过诸种经验的片断所构成的经验整体得到了完整的传达,这里有视觉经验:苍苍芦苇;有时间经验:深秋;有空间经验:水道漫长:有心理表象经验:美丽伊人。在这诸多的经验瞬间聚合中,传达出了核心经验:无尽的思念和惆怅。
如果把意象从审美经验中剥离出来,孤立静止观之,那么就可以分出写实意象和想象虚构意象。反过来说,人们之所以区分出写实意象和虚构意象,就是由于把审美意象从审美经验中剥离出来的结果。这种剥离,作为一种在有限的范围内的技术性分析是可以的,这个有限的范围就是在不涉及文学的本质界定之内。章学诚说:
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营构之象。天地自然之象,《说卦》为天为圜诸条,约略足以尽之;人心营构之象,《睽》车之栽鬼,翰音之登天,意之所至,无不可也。然而心虚用灵,人累于天地之间,不能不受阴阳之消息。心之营构,则情之变易为之也:情之变易,感于人世之接构而乘于阴阳倚伏为之也。是则人心营构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下》)《睽》车之载鬼,自然为虚构之象、人心营构之象。但是,《诗经》中的苍苍芦苇,凄凄白露,还是天地自然之象吗?文学中的意象作为审美经验的传达,不都是“人心营构之象”吗?苍苍芦苇,凄凄白露,现实中有其物,可是谁又能以实际的眼光来对待?当然,在审美经验的意象中,也有由于“情之变易”而导致经验意象的变形,诸如八戒悟空、宝玉衔玉,现实中无其实,由于是审美经验的聚合,所以无人怪其虚。因此,只究其实,或只究其虚,是不能领悟审美经验意象的本质的。
我们之所以不囿于意象的写实与虚构,是因为意象不是一切,意象不是文学艺术的最终目的。作家在文学作品中传达出来的是形名以上的东西,如上述所举《诗经·蒹葭》是写苍苍芦苇吗?是写凄凄白露吗?是写美丽伊人吗?是写水道漫漫吗?诗人所写的既在这些之内,又在这些之外。所谓在这些之内。是指诗人只有通过这些意象才能传达它的情感经验,对于读者来说也是如此。只有借助于这些意象才能把捉诗人的情感经验。但是,无论诗人还是读者,如果拘泥于这些意象,是不得要领的。
对于言不尽意的局限,中国人很早就提出立象尽意的解决方法。“立象尽意”最早见于《周易,系辞》: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这个命题主要提出了一种表达方式:“立象”。“立象”的表达方式,实际上是一种象征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的目的同样也是为了描述事物的,本质和普遍性:
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周易·系辞下》)
“立象”的关键是“取类”。“取类”,就不是囿于“象”本身,或者说是不拘泥于某一具体事物的状貌,而是通过它来表达同类的情与理,这就是“其旨远”,而这些要表达的东西是通过某一具体的“象”来启示的,这就是“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
可以看出,《周易》的这种表达方式。与文学艺术是相通的。所以章学诚说:
《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易》象通于诗之比兴。(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下》)
在文学艺术中,作家所要传达的审美经验,既在意象之中,又在意象之外。也就是说,文学艺术是意象的,也是超象的。这正如文学是语言的又是超语言的一样。
对这一辩证命题的理解,中国道家的认识论是富有启发的。《周易》中所提出的言、意、象三者关系问题,在庄子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而且是更加专门化的探讨。首先庄子探讨了“言”与“意”的关系: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在庄子看来,“意”是根本,“言”只是手段。人不应拘泥于语言,而重在把握语言中的“意”。
庄子还在认识论意义上。探讨了认识“道”的途径: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吃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庄子·天地》)
玄珠,喻道;知,即智;离朱,喻视觉;吃诟,喻语言;象罔,即罔象,即无象。庄子通过这个寓言来说明,用“知”、视觉和语言是不能领悟“道,,的,只有超于有形,才能达于道真,即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之真理。
所谓无象,不是真的没有象,而是超越象,不要拘泥于象。也就是不要囿于事物的形名。正所谓“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
王弼在三玄(易、老、庄)基础上,对言象意三者关系作了精辟的总结:
(1)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2)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现意。(3)意以象尽,象以言着。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4)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5)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忠言。……(6)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王弼这段话分了六个层次,并加了序号。总的来说,王弼阐述了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对“意”的表达,一个是对“意”的接受。表达,涉及的是作《易》者;接受,涉及的是用《易》者。第一层是就表达来说的:象是表达意的工具,言是表达象的工具。只有象才能完整地表达意,只有言才能充分地表达象。第二层是讲接受:由于言是因象而生,所以,通过语言可以得象。由于象是因意而生,所以,通过象可以得意。第三层也是讲接受:因为象是用来表达意的。言是用来表达象的,所以,得象可忘言,得意可忘象。第四层还是讲接受:言虽是因象而生,但是,拘泥于言,就不会得到产生言的象。象虽是因意而生,但是,拘泥于象,也不会得到产生象的意。第五层又是讲接受:只有不拘泥于言,才能得到象。只有不拘泥于象,才能得到意。第六层对表达和接受都有意义:对于表达和接受来说,都不要拘泥于象,关键在于能够抓住同类事物的本质和特征。
王弼的阐释对我们理解文学意象的超象性质会有很大的启发。意象是作家用来表达“意”的,即审美经验,“神用象通”(《文心雕龙·神思》),“象”是工具,“象”又要由语言来构造。语言又是一层工具。可是语言是有限的,象也是有限的。作家能否充分传达自己的审美经验,取决于对这两层工具的掌握水平。对语言来说,必须抛弃“名言”,即抽象的概念语言,使用那些能够提示“象”的语言:对于“象”来说,必须能够把握审美经验中最本质的方面。这要求语言和象都必须是富有提示性和弹性的,而不能太着实。即所谓“不落言筌”。所谓提示性和弹性,就是刘勰所说的“文外之重旨”:
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曼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文心雕龙·隐秀》)
人类对世界的感悟是无穷无尽的,精神的活动是深远的,审美经验是新鲜的、跃动的、丰富的、复杂的,要把这些都传达出来,就使得文学作品中,有“秀”和“隐”的出现,“秀”就是警句,而“隐”就是文外之“意”,是“秘响傍通”。所谓“秘响傍通”,就是“文意的派生与交相引发”。意象是具体的、可感的,超象同样是具体的、可感的。如果说意象的具体是个别的具体,那么,超象的具体就是由个别上升为一般的具体。如果说意象的可感还主要是形貌的可感。那么,超象的可感就是形貌以上的精神内容的可感。意象好比是引渡我们到精神世界的渡船,船的空间越大,渡的人就越多,同样,意象留有的象外空间越大,传达出的审美经验就越多,例如“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江雪》)。在这首诗中,意象并不多,极具写意色彩。从“象”的层次来看,诗人为我们传达了一个空间上的空旷感,但是,诗的意象,由空间的空旷引向了精神的“空旷”:孤寂。这就是意象的魔力所在。
有人在“意象”范围说明“超象”问题,认为超象是意象的一个特征,这当然也可以。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超象”当做一种“象”,一种更高的象,表面看来它是无形的,但它是具体存在的,所谓“大象无形”。中国古人把超象的具体性称为“象外之象”:
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司空图《与极浦书》)
所谓“超象”,是中国古典诗人所创造的诗的一种境界,还是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过去很多人都认为“象外之象”,只是中国古代一些诗人所创造的诗境。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在我们认识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时,往往把文学艺术与科学相比。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认为意象或形象是文学的特征。但是,从文学艺术自身来看,就“言”与“象”的关系来说,“象”是“体”,而“言”是“用”,就“象”与“意”的关系来说,“意”是“体”。而“言”是“用”。即所谓言象者筌蹄也。正如概念命题是科学理论的表达工具,但它并不是理论本身,更不是科学本身。形象或意象只是作家传达审美经验的工具,作家要通过具体的意象而达到一般和普遍,通过有限而达到无限,通过物质而达到精神。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文学又是超象的。因此,我们认为,超象对于深入认识文学艺术的本质具有重要的普遍的理论意义。
严羽对文学艺术从意象到超象。从有限到无限,有更深刻的认识,他认为: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性情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严羽《沧浪诗话·诗辨》)
有的人认为严羽以禅喻诗,甚至以为他所说的是禅境。其实,严羽的观点触及了文学的本质方面。文学艺术不是弃绝一切“知”的空门顿悟,文学艺术与学识、知识、理性并不是矛盾的,不仅如此,而且还要建立在学识、知识、理性的基础上。但是,文学不能以抽象的概念语言为手段,不能把才学和理性知识直接作为传达的对象,而是用意象来传达精神世界的美感经验,而且,成功的文学意象,必须把精神世界美感经验的深奥和复杂充分传达出来。
“象”,仍然带有“物”的成分,司空图认为,只有“超以象外”,才能“得其环中”;只有“持之非强”,才能“来之无穷”(《二十四诗品·雄浑》),此乃深明之论。
所谓超象,并不是否定象,或不要象,而是不拘泥于象,这对作家或读者来说都是如此。实际上,“体”与“用”是难以截然分开的。象与超象,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离开意象,何来超象?而拘泥于意象,必然与文学艺术相去甚远。
但是,必须注意,说意象犹如筌蹄,只是析而言之。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是作家用意象所构造的有生命的世界,意象与作家的审美经验是浑然一体的,是美的呈现,是美感经验的传达。以说理比喻之意象来类比文学艺术之意象,是不得要领的,是对文学艺术的贬低。王弼所谓,只要“象类”,“何必牛马”,对于说理的比喻,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文学意象的从具体到一般,从有限到无限,决不是修辞学意义上的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法之类。钱锺书先生对此作了精深的辨析:
《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故谓之象。”是“象”也,大似雏果所谓以想象体示概念。盖与诗歌之记物寓旨,理有相通。……然二者貌同而心异,不可不辨也。
理赜义玄,说理陈义者取譬于近,假象于实……古今说理,比比皆然。……至以譬喻为致知之具……《易》之有象,取譬明理也,“所以喻道,而非道也”。求道之能喻而理之能明,初不拘泥于某象,变其象也可;及道之既喻而理之既明,亦不恋着于象,舍象也可。到岸舍筏、见月忽指、获鱼兔而弃筌蹄。胥得意忘言之谓也。词章之拟象比喻则异乎是。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变象易言,是别为一诗甚且非诗矣。故《易》之拟象不即,指示意义之符(sign)也;《诗》之比喻不离,体示意义之迹(icon)也。不即者可以取代,不离者勿容更张。钱锺书先生敏锐地看到了文学意象与所传达的内容的浑然一体,文学艺术正是凭借语言,凭借意象,“体示”了概念命题所不可言说的审美经验世界,这也就是以有限“体示”无限,以有形“体示”无形,由物质而达于精神。所谓的超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讲的。
参考文献
[1]王弼,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叶维廉,中周诗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2
[3]钱锺书,管锥编,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责任编辑 杜桂